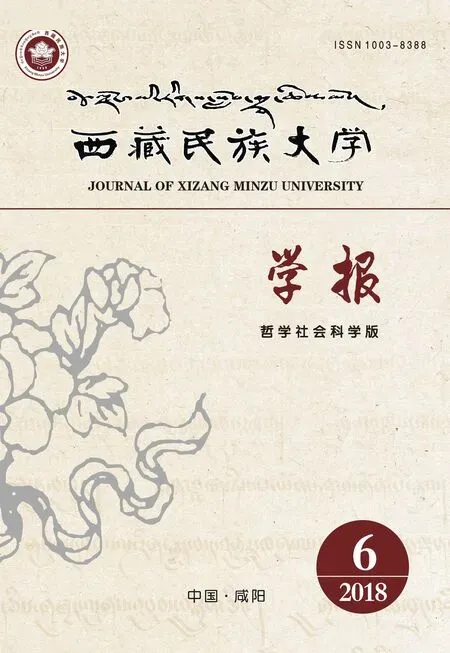门巴族“拔羌姆”神舞功能变迁考察
赵 勇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羌姆”(vcham)藏语意为跳神,是一种寺院祭祀舞。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承载形式和传递宗教情感的媒介,盛行于藏传佛教文化圈。羌姆的产生和发展与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密不可分。流行于藏族先民中的巫术仪式、拟兽舞等为羌姆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佛教在西藏的兴盛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流行于门隅地区的拔①羌姆是一种具有门巴族特色的羌姆形式。
一
公元779年,在西藏首座佛、法、僧俱全的佛教寺院桑耶寺的开光仪式上,首次表演了羌姆神舞②。据传,这种哑剧似的宗教舞蹈是由莲花生大师根据佛教密宗教义结合藏地土风舞而创作。其后,藏传佛教的诸多教派如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以及苯教根据发展的需要创作了大量适于自身教义的羌姆。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大多数羌姆是由“拟兽舞”和“法器舞”混杂而成,没有唱段,仅鼓乐伴奏,气氛肃穆。从内容上看,羌姆一般都包括净场迎神、送祟酬神、斩杀邪恶、串场故事等,涉及人物包括黑帽咒师③、护法神、各类动物、串场角色等。就功能而言,羌姆作为佛教传播到西藏的载体,其传统功能一直在酬神驱邪的主旨下,宣扬佛教教义。“具体而言,羌姆是深奥神秘的藏传佛教与广大信教群众间的重要连接纽带,以欲语还羞的姿态将藏传佛教最核心的教义向信众做了十分形象的精彩展示,为他们理解、解读、崇信藏传佛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对象,大大增强了藏传佛教的生命力。”[1]
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羌姆流传到了西藏东南部的门隅地区、西藏以外的藏族聚居区④以及蒙古地区⑤。流传在门隅地区的羌姆被称作“拔羌姆”,现在可见于西藏错那县勒布地区⑥的吉巴乡和贡日乡。据传拔羌姆产生于15世纪,由德登·热那林巴根据经书“桑堆”和“朱巴嘎吉”改编而成,最初是为了纪念一位门隅地区年轻的英雄。传说很久以前的一个鸡年,吉巴村来了一个吃人的怪物,一个年轻人不顾个人安危射杀了那个怪物。为了纪念和感谢这位英雄,热那喇嘛就给吉巴村民编演了拔羌姆,规定每隔十二年逢鸡年演1次。后改为每年都演,一般为1人敲鼓击拨控制节奏,8人上台演出,逢鸡年就12人表演。鸡年时“十二生肖”都会在拔羌姆中出现。按照规定,每年藏历新年前后在吉巴杂嘎寺和贡日白日寺前表演拔羌姆。
拔羌姆既是羌姆的一种形式,又独具自身特色。“藏传佛教传入门巴族地区后,寺院跳神活动也随之传入。”[2]门巴族拔羌姆源于藏传佛教寺院跳神舞,并随藏传佛教在门隅地区的传播而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一种带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羌姆形式。首先,它与其他形式的羌姆一样都源于寺院宗教跳神舞,而且对表演者、表演内容、表演流程、表演时间、表演地点都有严格的规定;都包括净地、酬神、除恶几个主题。在正常的法舞外,也有内容丰富的串场情节。但由于门巴族所处的独特自然和人文环境,拔羌姆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从内容上看,在拔羌姆中,有门巴族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巫术信仰的仪式舞蹈,也有藏传佛教祭祀舞的一些特征。从功能上看,门巴族复杂的宗教信仰和特殊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拔羌姆承载着多种社会功能。
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门巴族拔羌姆的功能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拔羌姆的传统功能明显弱化,其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气质的传统文化形式,逐渐承担起助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
拔羌姆主要是介绍“十二生肖”与诸神一起将妖魔赶下地狱的故事,同时穿插一些表现门隅地区人文习俗的情节。传统的拔羌姆表演时,“羌本”⑦在表演前需前往勒布官员驻地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演出。跳拔羌姆时,当地群众还会到寺庙内向神灵进献贡品,并通过寺院里的长者祭供鹿神和湖神。
杂嘎寺拔羌姆由八段羌姆和三个串场情节剧组成,表演的顺序大致如下:
第一段:“萨堆”。此段共两个角色,1个戴猪相面具,1个戴牛相面具。主要表演祭土地神,其目的是向土地神借地以便演出。
第二段:“措萨堆”。4人戴红色护法神面具,4人戴黑色护法神面具,右手持经幡,左手持彩箭,由羌本带领出场。
第三段:“潘羌姆”。此段与第二段大致相同,这两段的目的都是为了接下来的表演热场。
第四段:“刀羌姆”。此段由8人表演,分别戴牛、猪、马、兔、虎、狗、猴、羊面具,右手持刀出场。在表演过程中有刀与刀相碰撞的打斗场面。
第五段:“鼓羌姆”。由8人表演,戴护法神面具,右手持鼓槌,左手持鼓把,击鼓慢踏步入场。这段表演完后,插入第一个小情节剧——“吉塾俄追”(介绍人间)。
剧情大意:父亲见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没有对象,十分发愁。突然从内地来了两个汉族姑娘,父亲十分高兴并极力撮合他们结婚。
(3)从混合式教学在中小学领域的时区图中可以看出,从“混合式学习”到“混合式教学”再到“混合式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在一步步的深入和发展,并且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但是在中小学领域发展的力度还是不够,发展中的关键词数量太少。
第六段:“咒师羌姆”。仍由8人表演,前三人持鼓,后五人拿叉依次缓慢入场。此段最大的特点是,表演者不戴面具,而是头戴黑色阿巴帽。接着插入第二个情节剧——“铃巴俄追”(介绍猎人)。
剧情大意:父亲与两儿子去打猎,见两只鹿。后来另一猎人介入与父子三人为鹿的归属而争吵。此时圣者米拉日巴出现,劝诫四人不要杀生。猎人们听从了劝告,发誓不再打猎杀生。
第七段:“仙羌姆”。由8人戴女性特征面具进行表演。演员右手拿双面鼓,左手拿法铃,缓慢入场。队形成圆圈后,集中在中间抖鼓。接下来,插入最后一段小故事——“巴多俄追”(介绍地狱)。
剧情大意:阎王正在听取白神和黑鬼对一个亡灵的审判。白神认为死者生前做了许多好事,应该将其灵魂引向天堂;黑鬼则持相反意见,认为这个亡灵应该下地狱接受惩罚。双方争执不下,阎王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白神建议用秤对死者生前所做的好事儿和坏事儿称重。结果死者所做的好事多于坏事,其灵魂最终被引向了天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段羌姆。
第八段:“棍羌姆”。由8人手持长1米左右的木棒进行表演。跳完这一段整个拔羌姆的表演就结束了。⑧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拔羌姆的内容和表演流程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随着门巴族社会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观念的传入,拔羌姆的功能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拔羌姆的主要功能从其内容本身对人们宗教情感的满足和日常焦虑的释放转向其形式为给门巴族带来关注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加快社会经济发展,尽快带领门巴族同胞奔小康,成为了当地政府的主要任务。经过包装和宣传,拔羌姆等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成为了当地的名片和增收的保证。它们吸引着大量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向往的游客和媒体来到勒布地区。现在,拔羌姆更多的时候是在庆典和节日的舞台上表演。如,每年在勒布地区举办的“仓央嘉措情歌文化旅游节”上,就有拔羌姆的专场演出;山南的“雅砻文化节”等也有拔羌姆表演。另外,拔羌姆表演的传统地点——杂嘎寺,作为当地为加快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源加以利用。杂嘎寺有制作香的传统,再加上它一直是拔羌姆表演的固定场所,历史上远近闻名,这些特质使其成为了勒布地区门香特色产业发展的文化资本。
在分享着由拔羌姆带来的经济红利时,我们注意到拔羌姆的传统功能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新角色。在这一过程中,表演者由羌本和严格筛选的僧人变成了班头和临时演员;表演地点由寺庙移到了节日的舞台上和媒体的镜头前;观众由僧侣、信众变成了游客和媒体。
三
在传统社会里,拔羌姆是一种藏传佛教在门隅地区争夺信众的手段,也是适应于门巴人精神需要的一种独特的神舞形式。拔羌姆是把门巴人与宗教信仰联系起来的纽带,通过展演(仪式)来释放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焦虑和满足宗教情感需求,同时,也成为门巴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力量源泉和参照蓝本。
拔羌姆作为宗教的符号将表演内容、表演者、观众联系在一起,表演者作为中介将深奥的教义具体化为能被观众理解的形态动作和情节,观众将表演者视为角色的化身,寄托宗教情感。与大部分藏族地区不同的是原始宗教、苯教一直在门巴社会广泛存在且与佛教形成了并存之势。这就决定了拔羌姆在满足当地人宗教情感需求方面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传统社会中,拔羌姆中除了表现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图腾信仰、鬼魂信仰以外,还有许多苯教和佛教的特点。在苯教信仰中,巫师的作用特别重要,他们是沟通人与神鬼的中间人。要完成人与神鬼的沟通必须通过一定的仪式,只有通过仪式才能使人们相信巫师的特殊能力和承认巫师“中间人”的地位。拔羌姆中的第四段“刀羌”、第五段“鼓羌”就是对苯教巫师的送鬼仪式的展演。拔羌姆中的第七段“仙羌”,由舞者男扮女装戴女性特征的面具,手持双面鼓和法铃缓慢入场,并集中在一起抖鼓的场景,就是对苯教女巫师请神仪式的模仿。此外,拔羌姆中还有许多地方再现了苯教巫师的仪式过程。佛教元素在拔羌姆中表现,集中体现在各种护法神面具的出现。
拔羌姆在门巴族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时,也起到了缓解、调适焦虑的功能。在拔羌姆开演前的祭神和第一段“萨堆”中,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敬畏和焦虑,而在表演过程中,通过祭祀和借助图腾神力等手段又把其中的焦虑一一化解。在门巴族的观念里,把宇宙分为天上、地上和地下三层,对应的神鬼是“拉”、“赞”、“鲁”。人们认为江河、泉水、湖泊里住着“鲁”神。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门巴族先民只能饮山泉和湖泊的水,他们既感激山灵湖泊的恩赐,又担心水质变化影响他们的生活,这就产生了对泉水和湖灵的敬畏和焦虑。在拔羌姆展演前,正是通过对居住在湖泊泉水中“鲁”神的献祭和讨好,化解人们的这种焦虑情绪。以门巴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万物有灵论观念为基础,通拔羌姆这种形式的展演,化解了门巴人与自然的矛盾。在第一场舞“萨堆”中,则是通过图腾崇拜的展演来减缓当地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萨堆”开始,一人戴猪面具,一人戴牛面具上场表演祭地借地仪式。“门巴传说中,最初,有鬼魔在土地上兴风作恶,降灾于大地。后来猪、牛诞生了,与魔鬼战。猪、牛驱赶魔鬼入地府,保护了土地上的安宁。‘角包呛木’(牛舞)、‘帕呛木’(猪舞)、‘东金呛木’(即‘萨堆’)可能都是源于原始的图腾神话。”[3]门巴族居住的地方土地资源缺乏,以前常被称为“饥饿的山谷”,家养猪和牛的出现,部分弥补土地不足。所以,在“萨堆”中,猪、牛就化身为神灵,与地上的恶魔作斗争,保护土地的安宁。通过这段表演,缓解了现实中人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门巴人不再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对自然的焦虑上,他们开始了对自我人性的思考——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如果说起初人们对自然的焦虑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的话,那么鬼魂观的出现,则反映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焦虑。鬼魂形象在拔羌姆中出现,正是为了调节人与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释放生活的压力,消除人们的困惑,指明生活的方向。在拔羌姆结尾那段“介绍地狱”的小情节剧中,在对亡魂进行审判时,开始的时候阎王、白神、黑鬼都不知道怎么判定一个亡魂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就是人对自身的焦虑的一种表现,人们困惑于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上天堂或下地狱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也就是说,在人与人相处过程中不知道何为善何为恶。最后,白神找到了一个称生前做好事重量的办法,这就给人与人相处定下了一个方向——多做好事。消除了人们在现实中交往的困惑。
当门巴族社会进入现代发展的新时期,物质生活丰富,社会机制健全,发展经济成为了社会的主导。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人们担心的主要问题,人们焦虑的是如何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过得更好,如何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需求和焦虑的转变,拔羌姆和其他门巴族的传统文化一起承担起了对外宣传门巴族的功能。对于门巴族来说,拔羌姆演出的具体内容已经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而是拔羌姆这种门巴族特有的艺术形式能否带来关注,能否把他们与外界社会联系起来。
可见,拔羌姆功能的变化,是门巴族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
偏居于喜马拉雅东段南坡的门巴族聚居区,本应是羌姆传统功能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但拔羌姆却率先充当起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宣传员”。如果说,发展是时代的潮流,拔羌姆功能变迁是不可逆的事实,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社会在进一步的发展时,如何保护与传承拔羌姆这种形式。
其实,如何保护羌姆这种传统文化形式,西藏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我们高兴地看到,包括门巴族拔羌姆在内,2014年已将桑耶寺羌姆、林芝米纳羌姆、门巴族拔羌姆、江洛德庆曲林寺尼姑羌姆纳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但在笔者看来,拔羌姆传承最大问题是其传承的基础已经开始瓦解,文化的传承没了载体。当下,拔羌姆已经不再是情感的寄托,而仅仅是舞台上的一个节目。大多数人对拔羌姆已经不再有过去的热情,大人们在忙发展,小孩们在忙升学。拔羌姆在各类节日庆典上的展演,虽然能起到一定的普及作用,但这对于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的保护和传承远远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着眼点在于传承,只有传承,才能谈得上保护和发展。传承与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问题。”[4]而真正的传承人需要从小就开始“培养”。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和普及融入孩子们的成长过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传承基础和传承人的问题。只有落实“传统文化进校园工程”,拔羌姆一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才能得到较好的传承。现有的教育教学体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是值得的。因为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者主体性地位的保障,也是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继承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形式的折中选择。
[注 释]
①“拔”,藏语意为面具。
②《贤者喜宴》(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摘译[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3))和《西藏王臣记》(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西藏王臣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9页.)都记录了这一盛况。
③黑帽咒师服起源于刺杀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的僧人拉龙贝多。因他刺杀灭佛藏王达玛时,身着黑帽黑袍,从此黑帽黑衣成了咒师们的传统服饰,代表复仇之神。
④青海等地将“羌姆”称作“跳欠”,云南、四川藏区叫“麻羌”⑤蒙古族称“羌姆”为“查玛”。
⑥勒布地区为我国门巴族主要聚居地,由麻玛、贡日、吉巴、勒四个门巴民族乡组成。
⑦“羌本”意为领舞师或跳神老师,一般由寺庙喇嘛担任。
⑧以上“八段三串场”的杂嘎寺传统拔羌姆,是2015年暑期在勒布地区调研时收集所得。由吉巴乡拔羌姆传承人勒吉康珠口述,吉巴乡文化干事平措翻译,笔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