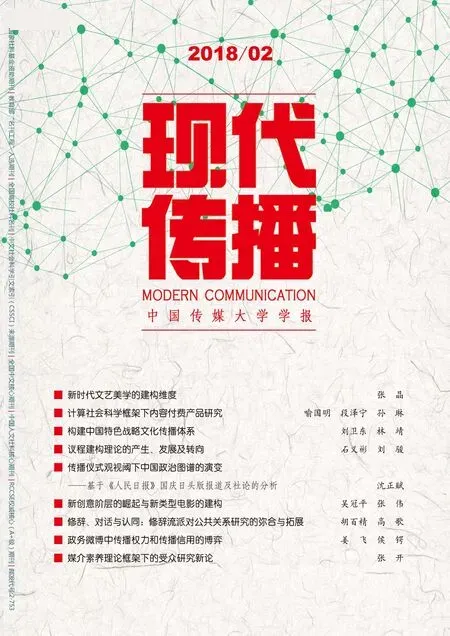修辞、对话与认同:修辞流派对公共关系研究的弥合与拓展*
■ 胡百精 高 歌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关系修辞流派兴起于20世纪晚期,是公关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转向,对于构建新的公关学术范式,特别是弥合行为主义取向公关研究的问题和局限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转向发生于更开阔的三个学术和思想背景之下: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的修辞学转向,以及新修辞学的发展及其对话转向。通过对这三个转向的衔接和借用,修辞流派使公关理论建设获得了如下拓展机会:建立公关哲学体系,以改变“公关罕言哲学”①的窘境;重返语言行为和话语实践——公关理论研究的核心地带,从人的存在、对话与社会互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切入考察公关现象,并因此突破了行为主义公关研究的某些关键阻碍;兼顾了功能、诠释和批判等传统公关研究的经典路径,提供了多元路径相互敞开的可能性。
然而,公关学界并未善用这些机会。除了希斯(Robert L.Heath)等个别学者的成果,修辞取向的公关研究与哲学、语言学领域的新修辞学未能真正贯通。大多数参与其中的学者只是在语词和话语分析层面搬运了新修辞学的部分概念和方法。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分别考察了新修辞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公关修辞流派理论主张和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将前者的思想资源进一步转渡至后者,进而探讨确立和拓展公关修辞范式的可能性。
二、新修辞学:语言、认同与世界
希斯、托斯(Elizabeth L.Toth)、库姆斯(W.T.Coombs)、班尼特(W.L.Benoit)等人都承认,修辞取向公关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思想来源乃新修辞学。②20世纪中前期,传承自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修辞学在哲学、语言学领域于沉寂中被唤醒,并逐渐发展为新修辞学。新修辞学的诞生和成熟,得益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语言学的修辞学转向。
20世纪太喧嚣和复杂了,这是哲学家们的普遍感受,“我们所见到的20世纪是一个充满变革、动荡、战争和冲突的时代,一个物质进步、环境恶化、自人类统治地球以来前所未有的时代”③。为了解释人类在这个新时代的境遇,哲学家们不得不改造古典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把哲学研究的范畴由主体内在形而上的运思,拓展至形而下的外在世界和世俗生活,以理解新时代于外部强加给个体的复杂性——危机与繁荣、战争与和平、野蛮与文明、交往与冲突。在此拓展过程中,一些哲学家发现语言乃联通主体内在与外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媒介,故将研究焦点转向语言。这就是后来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普泛影响的所谓语言学转向。
在语言研究受到重视后,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皮尔斯(C.S.Pierce)等人发展了形式主义或曰结构主义语言学,探究语词句法普遍共时的内在结构。虽然他们也宣称语言是一种社会契约,但是对语言符号形式和结构的关切导致他们往往把文本当作孤立的考察对象,忽视文本的语境、修辞和意义问题。索绪尔明确提出:“意义不是符号学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应该把它交给心理学或其他学科”。④而理查兹(I.A.Richards)、奥格登(C.K.Ogden)则认为,意义、修辞、文本、语境才是哲学和语言学研究的重点,“语词不是复制生活的媒介”,它在交往者的阐释和理解中生产意义;意义反映过去与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复杂链条,同时也建构了这些链条;语词及其意义可能产生误解,而修辞的目的在于达成理解。⑤
理查兹的全部论证皆围绕两个原初问题展开:词语何以产生意义?交往何以消除误解、达成理解?他给出的答案是修辞。语词(象征或符号)与其指称对象(所指)之间存在一个中介地带即意义,三者构成了一个语义三角,而修辞乃搭建三角关系的表达机制和话语行为。语词并无确定意义,所指可能抽象亦可能具象,因此意义只能来源于人的话语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编码、解码、对噪音的克服、对语境的适应,以及对指示(indication)、描述(characterizing)、体验(realizing)、评价(valuing)、影响(influencing)、控制(controlling)、目的(purposing)等语言功能的综合运用。理兹查指出,这正是一个修辞过程,人类运用符号和象征生产意义,并通过意义达成理解,建构交往者之间的共同世界。⑥在1930—1970年代,柏克(Kenneth Burke)、佩雷尔曼(Chaim Perelman)、韦弗(Richard Weaver)、图尔明(Stephen Toulmin)、乔姆斯基(Norm Chomsky)——广义上还包括巴赫金(M.Bakhtin)、格拉斯(Ernesto Grassi)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也加入到修辞研究中来,共同推动了语言学的修辞学转向,形成了与古典修辞学遥相呼应的“新修辞学”运动。新修辞学派总体上抱持如下主张:
一是意义乃语言和修辞的核心问题。语言是人的天赋,而此般天赋的核心价值在于创造和分享意义,使人类的沟通、理解、合作、和谐以及维系共同体成为可能。除了理查兹,佩雷尔曼、巴赫金、格拉斯等人也都特别看重语言行为——修辞的意义生产功能。譬如在格拉斯看来,人类拥有想象、工作和语言三样天赋⑦,而正是语言使人类能够以自身的经验理解和表达世界,赋予存在和现象以意义,从而改造自然、教化自我、创造历史。对意义而非形式的重视,使新修辞流派与语言学转向中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研究区隔开来。
二是凡表达皆修辞。柏克提出:“哪里有说服,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说服。”⑧人是象征的动物,藉由语言行为与他者和世界进行象征互动,以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改变个体与生俱来的孤立、隔绝状态。因此,修辞的情境是遍在的。“人一旦运用语言,便不可避免地进入修辞情境”。⑨图尔明等人也认为修辞乃人类生活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形成和表达一切动机、实现所有交往和互动的基础。⑩这就把修辞研究从文学、演说、辩论等狭隘领地解放了出来,将之推向人的日常存在和更开阔的社会交往空间。政治、商业、外交、传媒、广告、公关以及日常生活等全部人类交往活动皆可视为修辞,皆仰赖修辞而运转。
三是语言的“反仆为主”。在传统观念中,语言乃人之工具。语言学的转向抛弃了这种工具论,发现了语言反仆为主的功能——建构人和世界。索绪尔认为语言有其内在结构,并依照自身的结构编码世界。而语言建构的世界与真实世界并非全然对应,有时简直是两码事。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认为在语言运动中,不是表达者绝对主导言说,而是言说反过来建构了表达者的角色和地位。柏克明确指出:“人类主要生活在语言之中,用语言谈论语言,用语言解释语言。”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语言观更加激进,“人以语言的形式拥有世界”。新修辞理论认为,语言反仆为主的动力机制正是修辞,修辞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生产和控制意义,命名世界和建立秩序,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与行为。
四是修辞论证与完整认识世界。在古典修辞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审慎区分了辩证法和修辞论证:前者遵循形式逻辑,基于必然性和明确的因果关系实现对世界的理性认知,故可用来获取知识;后者则奉行或然性逻辑,谈论的只是某种相关性或可能性,故可用来说服听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据此认为,辩证法乃认识世界的高级手段,修辞论证则相对低劣。这种看法影响深远,以至于知识精英尤其是科学家总是在辩论中强调自己“没有使用修辞”。新修辞学派对高高在上的辩证法强烈不满,指出了形式逻辑认识世界的局限。佩雷尔曼等人在考察大量政治家、道德家和律师辩论个案后提出,并非所有社会领域都奉行形式逻辑。譬如在舆论、情感、道德、审美诸领域,苛求形式逻辑上的必然性和因果律往往徒劳,甚或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修辞论证恰可以为这些领域提供或然的理性基础。因此,修辞论证并非低劣的认识手段,它与辩证法的相互联合有利于人类完整地认识世界。
五是修辞的前提和目的皆为认同。新修辞学并未抛弃或颠覆古典修辞学,而是继承、拓展了其核心思想。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韦弗、柏克等人几乎完全接纳了这个定义。韦弗认为“语言即说教”,凡语言使用皆带有说服性质,皆内蕴伦理问题,即修辞性的。柏克也承认,修辞即藉由话语行为影响交往者的态度和行为。那么新修辞学何以为“新”?一则如前所述,柏克等人将修辞视为遍在于人类交往活动,关系到人类如何认识自身和世界的大问题,不再像古典时期那样将修辞局限于特定语境、文本,或风格、技巧之类的“雕虫小技”;二则新修辞学将认同视为修辞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旧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说服……新修辞学的关键词是认同。”
1986年,希斯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现实主义与相对主义》(Realism and Relativism),系统介绍和批判了新修辞学特别是柏克的修辞思想。之后,希斯并未像他的学术偶像柏克那样深耕修辞哲学,而是以其修辞学训练投向了公共关系研究。进入1990年代,以希斯为代表的一批公关学者持续借鉴、应用新修辞流派的思想资源,逐步确立了公关修辞流派的格局和地位。自此,公关理论研究出现了管理流派、关系流派、传播流派和修辞流派多足鼎立的新局面。
三、公关修辞流派:意义、对话与情境
希斯并非第一个行动者。1983年,克莱伯(Richard Crable)等人对里根总统的某场演说进行了修辞分析,以考察政治信仰表达中的语用资源和符号选择;1988年,斯普卢尔(Michael Sproule)提出了新管理修辞(new managerial rhetoric)概念,将组织视为修辞者(rhetor),按修辞框架研究了组织在海报、宣传册、新闻稿和公告等文本中所欲传达的组织形象(persona)和意识形态。希斯、托斯合作出版了《公共关系修辞与批判研究》(Rhetorical and Critical Approach to Public Relations),该书被认为是公关修辞流派崛起的标志。此后十余年,希斯、托斯、库姆斯、班尼特等人相互呼应,为公关理论研究开辟了一条修辞取向的通途。
尽管加入公关修辞流派的学者越来越多,但希斯始终是旗手。他的公关修辞理论筑基于新修辞学的几个核心概念和观念。
一是公关即修辞。公关与修辞有着天然的联系,二者皆属以说服为目的的语言实践。在管理流派、关系流派和传播流派看来,公关与修辞乃从属关系,后者是前者谋求说服效果的诸多手段之一。希斯则持以柏克的修辞遍在论,主张公关就是组织和公众彼此适应的修辞过程,“组织可根据消费者和公众的偏好采取行动、设计产品和提供服务。同样,如果组织的某项倡导足够有说服力,消费者和公众也会主动采信、诚意跟随”。希斯相信,藉由持续的动态影响、相互调整,组织和公众能在对话中达到彼此适应的平衡。这一判断显然受到了新修辞学能动语言观的影响:修辞使观念适应人,也使人适应观念,并建构人与人、观念与观念之间的平衡关系。
希斯进一步提出,公关和修辞都承认世界的未知、不确定性和矛盾性,试图介入和解决那些存在争议的人类事务。那些遍在的“不确定性和未知,以及(人类面对同一对象时)复杂的动机、迥异的主张乃修辞和公关得以存在的共同前提”。从此前提出发,公关致力于在多元对话中建立信任、消除误解、达成理解,形塑程序或实效上的认同,而这正是组织以修辞者身份介入社会互动的话语行为和说服过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公关的主体和对象——个体、组织和社群皆属语言和修辞的存在,基于修辞和象征互动来理解、影响外部世界。
二是意义乃公关的核心问题。这是希斯从新修辞学那里直接借用的一个观念。理查兹等人认为,修辞生产意义,并通过意义的社会建构、连接和接纳,使交往者进入共同的世界。从修辞视角看,公关即组织生产意义,并期待与多元公众构建共通意义空间的过程。这种意义中心论使公关修辞流派同盛行的管理流派区别开来。管理流派认为,公关的核心问题是力求卓越地管理传播过程,以期实现组织与公众在利益上的双赢。希斯的合作者托斯指出,“管理学派的量化取向假定传播是符合一定标准和流程的实践行动,重视对这一过程的管理,而不是通过修辞分析研究传播究竟实现了何种程度的意义建构。”修辞流派则更关切公关的意义生产及其达成理解和认同的可能性,而理解和认同从来不只是一个利益问题。
这就涉及到新修辞学派对认同问题的深入讨论。柏克认为新修辞学对古典修辞学最大的改造是对认同的强调,“旧修辞学的重点在于说服力建设,强调语言技巧的审慎设计,而新修辞学则主张修辞是为了靠近本体层面的认同,并且重视来自本能和表达场域的无意识因素。”古典修辞学片面追求表达技巧和说服力建设,忽视了认同才是交往的基础。柏克特别重视基于身份和无意识的“本体认同”:听者对言者身份的认同是如此牢固,以至于有人不管讲什么听者都愿意相信,也有人纵口吐莲花亦属枉然;直觉、本能或无意识的心灵认同,以及宗教性的神秘认同往往也比说理更强大。因此,形塑认同较之表达技巧和沟通过程更具基础性和优先性。同时,意义和认同不单指向理性和利益问题,而且包含了本体、直觉乃至宗教意义上的“同一性”。
三是修辞和公关的对话转向。语言学发生修辞学转向后,修辞学又出现了对话转向。这场转向至少存在三个动力来源:古典修辞学过于强调修辞的规劝、教育和支配功能,导致修辞学看起来极像一门不光彩的“统治术”,新修辞学因此强烈期待以对话、同一、认同等概念取代教化、支配和统治,以为修辞确立正当的价值观;修辞以意义为中心,而意义乃编码与解码、表达与阐释等双向协商的产物,因此修辞和话语行为理应走向对话,“对话才是意义的真正所在”;面对20世纪复杂的社会交往实践,尤其是民主政治和大众社会的持续发展,旨在消除误解、达成理解、增进和谐的修辞也要因应时势、转向对话。
公关研究同样存在新修辞学派的上述三个诉求。希斯敏感地捕捉到了修辞学的对话转向,并将之转用于公关理论建设。人们之所以需要修辞,试图真切、有力、灵动地表达自己,就是因为“修辞假定有多元声音加入对话,而不是陷入独白”。若非为了对话和认同,则修辞是不必要的。希斯引述柏克说,社会乃观点的市场,多元主体围绕事实、价值和公共政策争论不止,修辞和对话使人们相互理解对方所主张的事实、价值、政策、所欲认同之物及其叙事方式,从而做出正确抉择。专业的、良善的公关可以确保某项事业、某个产业、企业或个人加入众声喧哗的观点竞争,并在对话中彼此倾听、达成认同。
批评者指出,修辞调适各方意见的结果未必是理想的平衡,精英总是通过操控大众心智制造共识,最终强化了主导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希斯回应说,修辞确实可以用来做好事,也会做坏事,但是“人们只需稍加留意就会注意到,任何以信任为代价的策略,最终只会让事情和自己的处境变得更糟”。在现代民主社会,对话的价值不仅是在多元声音中寻求“相对较佳”的问题解决方案,而且它本身就意味着信任、开放和平等,并持续、动态地引导人们趋向认同。这也正是藉由对话取向的修辞重构公关角色和道德的原因所在。
希斯还借用了柏克提出的“辞屏”(terministic screen)概念来说明对话、合作的必要性。柏克认为语言因其呈现和遮蔽的双重本质,同样有摄影透镜的“滤色”功能。人们在交往时使用的词语,就像独特的修辞滤色镜,柏克称之为辞屏。人们透过辞屏看世界,有所选择,也有所背离(deflection)。当某一群体被描述为消费者而不是公民,表明修辞者意在选择和凸显其经济属性而非政治属性。希斯进一步指出,“每种辞屏代表一个不同的视角”,每一视角都代表一种观看之道。人们倾向于认同持相同视角者,信任叙事和伦理判断与己一致的人。在高度市场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辞屏之间形成了鲜明比照和激烈竞争。无论人际交往还是社会互动,若欲达成认同与合作,修辞者就要持续调整辞屏、促进对话。柏克和希斯的辞屏概念也呼应了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后者认为多元、独立、差异化的主体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弥合各自的视域剩余,从而形成完整的理解力和判断力。
除了前述意义、认同、对话等问题,希斯还注意到了新修辞学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指控——语境、情境研究缺位。他基于修辞学家比彻尔(Lloyd Bitzer)的情急状态(exigency)概念,考察了公关领域的修辞困境(rhetorical problem)。所谓修辞困境,即组织在公关实践中面临的一种情急状态,这种状态揭示或激发了利益相关者对组织行为、决策及相关影响的质疑或异议,组织需要针对情急状态制定适当修辞策略,以化解困境。此中,话语必须契应情境,情境决定了意义生产的可能性、对话与认同的有效性,以及伦理和价值观的正当性。
库姆斯在公关修辞情境研究方面做出了更丰富和实用的贡献。他指出,“组织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在利益协商、意义生产,乃至对事实的认知、理解和价值诠释上存在着鸿沟”,“双方在动机、利益的解读、价值判断、行为选择以及结论等方面皆出现难以弥合的断裂”。为此,组织要因应情境变化采取灵活的修辞策略:在危机发生阶段(crisis phase),回应利益相关者对健康、安全等核心关切,不仅要提供有关核心关切的说明性信息(instructing information),还应积极开展补救行动,提供情感和精神抚恤等修复性信息(adjusting information);在后危机阶段(post-crisis phase),修辞困境发生迁转,组织要兑现对利益相关者的承诺,还要开展形象修复和声誉管理。无论在哪个阶段,组织作为修辞者的德性和信誉都直接影响危机传播的成败。总之,危机传播就是一种化解修辞困境的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组织要引导利益相关者以共同的视角理解危机,于对话中寻求认同。
班尼特是另一位深耕公关修辞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被广为引用的形象修复理论区分了多种危机情境,提出了针对性的修辞策略:否认事实(Denial),包括简单否认和转移批评;回避责任(Evasion of Responsibility),包括申明被挑战,无力为之或不可抗,纯属意外或无心之过;淡化处理(Reducing Offensiveness of Event),包括轻描淡写事态,提供证据显示该事件带来的利益和好处,进行比较、寻找差异,以及反击对手、降低指控者的信誉,或合理补偿利益受损者;修正行为(Corrective Action),制定和实施解决方案,改善自身行动,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诚意致歉(Mortification),表示遗憾和歉意。
一些中国公关学者也注意到了修辞研究的重要性,代表性的成果包括:张依依简要介绍了公关修辞流派的兴起,分析了该流派与传播、管理、关系诸流派的异同;吴宜蓁将希斯、库姆斯、班尼特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危机情境,探讨了危机修辞的理论框架;胡百精比较了西方新旧修辞思想同中国修辞思想,考察了柏克修辞理论在公关叙事中的应用。
四、范式创新:改造、拓展与融合
传播流派、管理流派和关系流派是既往研究中较为成熟的三大流派,三者分别强调了公关的传播、管理和关系维护功能。在1990年代,格鲁尼格(J.E.Grunig)等人确立了卓越公关理论的主导地位,公关即传播管理的定义深入人心,传播流派与管理流派渐趋合流。如是,公关的经典研究取向就变成了传播管理和关系管理两大流派。也恰在同期,修辞流派强劲崛起,与前二者形成鼎足之势。
公关修辞流派的崛起有其内因和外因。从理论建设的内部情况看,修辞流派大体确立了公关修辞理论的核心概念与观念、框架与方法,扎实开展了特定公关情境的修辞策略研究。事实上,除了希斯、托斯在基础理论和库姆斯、班尼特在情境理论方面的探索,还有更多公关学者于微观层面对组织话语展开修辞分析,在应用、功能和效果方面取得了丰富、精致的研究成果。譬如,一些学者基于组织即修辞者的假设,从语词、句法、主题、动机、调性和价值观等微观问题切入,深入考察了包括口号、标语、公告、公共演说等多样文本的意义生产方式和效果。可见,公关修辞流派搭建了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层面的理论框架,初步确立了修辞取向公关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从外部情况看,修辞流派有效弥合了传播管理和关系管理研究取向的不足,为创新公关理论范式提供了可能性。早前的公关传播流派也重视说服,强调通过设计、控制信源、信息、信道等传播自变量,改变信宿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等因变量,试图构建系统的、集成的理论范式。公关之父伯内斯的看法最能代表传播流派的主张:“包括公关专业人员在内的少数社会精英是对社会进行隐蔽治理的专家,他们以简单的文字或图像捕捉并驯服大众的想象,守护进步社会的稳定秩序。”他后来虽然也主张公关是“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双行道”,但仍是组织说服、支配公众,而不是反过来。传播流派在20世纪中后期的发展堕入了行为科学主义的陷阱:越来越看重传播变量、过程和预期结果的设计,而公关的基本问题——话语建构和意义生产的核心地位却遭弱化。譬如,麦奎尔的说服矩阵,包含了5个自变量、13个因变量,话语、意义问题湮没于繁复的传播要素和过程之中。这就犯下了一个吊诡的错误:传播流派认为公关以说服为业,话语和意义问题却在公关研究中边缘化了。
管理流派将公关定义为组织的一种管理职能,有效的公关有利于组织管理战略性公众(strategic public),降低组织成本,构建“组织—公众”共生的双向开放系统。及至格鲁尼格夫妇、亨特、多泽尔等人发展出卓越公关理论和双向均衡模式(symmetrical model),公关的定义被明确为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传播管理,旨在谋求二者双向均衡的沟通、互蒙其惠的双赢。作为“公关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范式”,卓越公关理论亦存在明显的局限:在真正的平等几无可能的情况下,组织与公众何以实现理想中的双向均衡沟通?作为一种管理职能,公关可以避免零和博弈或双输局面而实现组织与公众的双赢?虽然格鲁尼格强调了“公关世界观”的重要性,但它的来源何在?是谁的世界观?是否仍会堕入组织强加或一厢情愿施予某种世界观的窠臼?而当我们谈论公关世界观时,公关的哲学是什么?
关系流派的一些主张在公关学术史的早期即已出现,但它的真正兴起也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卡塞(Shawna Casey)、里奇(James Ritchey)、莱丁汉姆(J.A.Ledingham)和白朗宁(S.D.Bruning)等人批判传统公关模式重“公共”(public)轻“关系”(relations)的倾向,进而提出了建立“以关系问题为中心”的公关新范式。格鲁尼格、多泽尔等管理流派的关键人物随后也加入关系研究,流派边界呈现了突破、融合之势。关系流派主张建立和维护组织与公众的长远战略关系,并因此确立了测试关系质量的若干指标:信任(trust)、互控平衡或曰势力均衡(control mutuality)、关系的满意度(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关系互动中承诺的兑现程度(relationship commitment)和目标的达成程度(goal achieved)。格鲁尼格等人还提出了关系管理的六种策略:接近(access)、积极卷入(positivity)、开放(openness)、保障(assurances)建立关系网络(networking)和任务共享(sharing of tasks)。
关系学派开启了公关研究的新维度,更加重视公关中的信任、结构和控制等问题,但也遮蔽了其他流派的一些视域和洞见,譬如相对轻视了传播要素、管理过程和互动情境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以情境问题为例,关系是一个强烈受到文化和社会情境影响的交往范畴,譬如中国式关系和美国式关系分殊甚巨,以至于一些西方公关学者不得不用guanxi而非relationship来指代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关系。此外,关系管理与传播管理研究皆抱持强烈的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倾向,注重变量调节、过程管控和实效实惠,而对公关的哲学观照、意义阐释和批判分析则无力或无意为之。而修辞流派恰好可从这些留白或虚弱处下手,为公关理论研究拓展新的视野和空间。
托斯概括了公关修辞流派的四个基本观点(four perspective of rhetoric):人文主义、对话、象征和批判,可以看作对前述拓展可能性的积极响应。人文主义是修辞流派与其他公关流派相区隔的核心特质之一。理论界普遍认为修辞流派所承继的人文而非社会科学的传统。与社会科学尤其是行为科学偏重以实证、量化方法测定传播行为对群体产生的影响不同,人文主义取向的修辞研究不崇拜方法和工具,也不抽象地谈论群体,而是明确承认个体在传播和意义生产中认知和选择的合理性。
对话是修辞流派的另一个核心观点,它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了长期由组织主导的单向、线性话语模式,淡化了公关宣传、教化和操纵的色彩。虽然管理流派也提出了“双向均衡”的概念,但是修辞流派则向前一步,明确将之落实为意见交换和意义建构的多元对话。希斯反对行为科学取向的“传者中心论”,认为修辞绝非某种语言幻术,平等、开放的对话才是修辞的应有之意。克莱伯和维博特也提出,企业的修辞过程即是各方意见交换的对话过程。
修辞流派的第三个重要特质是重视象征研究。人类世界由象征所建构,象征无处不在,修辞流派的一个独特优势是使公关研究真正认识到了“语词和其他象征符号的影响”。托斯在考察修辞流派的代表性成果后发现,不同于管理流派和传播流派重视传播流程设计、对信息流通方向和效果的控制,修辞学者更关注信息和意见在人际间传布、交换的深层象征本质(symbolic nature),以及多元对话和公共决策中的意义生产机制和语言策略的选择,“修辞有关象征的研究填补了公关其他流派视域的空白”。
在兼顾功能和诠释研究取向的同时,修辞流派的批判主义取向深度涉入了公关伦理和哲学问题。修辞具有影响、塑造人和社会的独特价值,因此以批判的眼光检视修辞的文本设计、策略规划和效果达成,有利于深入评估修辞背后的动机和权力问题,并从哲学高度探讨公关的伦理规范。希斯将这一过程称为把握“社会可持续性的框架”(evaluative frameworks that give continuity to society)。他认为修辞可以拨开信息的迷雾和文本的表象,从批判的进路探知意见和意义如何创造或打破社会运行的持续性。譬如,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乃公众是否认同决策者的伦理、责任感和价值观,而非事实层面政策条款和风险评估所呈现的信息和数据。这就弥补了公关管理、传播和关系流派“信息中心论”(information-centered)的不足,不唯信息至上,而是批判性地关切信息背后的伦理价值。循此向上,更可将公关、修辞对人与社会的塑造拓展至哲学层面进行考察。
总体而观,公关修辞流派为公关理论发展和范式创新敞开了新的通路。新范式基于人文主义视角,以象征互动和意义生产为中心,从功能、诠释和批判诸路径出发,考察作为话语行为和对话实践的公共关系语境、文本和效果。然而,公关修辞流派的理论建设远未达到完善、圆满之境。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新修辞理论思想资源的借鉴、转渡仍显表面化和碎片化,因而限制了公关修辞流派的整体解释力和想象力。理查兹、柏克等人构建了贯通哲学、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庞大思想体系,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话语行为、象征互动和意义生产皆有复杂、深刻的讨论。而除了希斯,公关修辞流派的代表人物中大多缺少语言哲学和修辞哲学的系统训练,往往仅根据自己的论证需要挪用、嵌入某些新修辞学的概念或命题。这就导致新修辞学在一些重大和基本问题——修辞与人的存在、修辞与真理、修辞与权力、修辞与伦理等领域的厚重思想遗产,并未充分转化、应用于公关修辞理论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公关修辞流派并未如人们期待的那般,发展一套有完整解释力和丰富想象力的公关哲学。譬如,公关修辞流派借鉴了新修辞学的对话概念,但关于对话何以改造交往者之间的“主体—客体”关系,以构建互为主体关系,却未能像后者那样在哲学认识论层面展开完整、深入的阐释。而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那么所谓对话不过是一种充满道德温情的交往乌托邦。
二是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看,新修辞学中一些经典、“好用”的理论尚未被创造性地应用于公关研究和实践。譬如理查兹的有效沟通概念(effective communication)、图尔明的实用辩论模式(model of practical argument)、韦弗的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柏克的认同(theory of identity)和戏剧主义修辞思想(dramatism rhetoric)皆对公关理论和实践创新有重要、直接的启发意义,但它们在公关修辞流派的研究成果迄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引介。以图尔明的论辩模式为例,该模式视辩论为“从事实出发的修辞旅行”,它由六个要素构成:主张(Claim):某人试图在论证中证明为正当的观点或结论;根据(Grounds):作为论证基础的事实/证据;理由/担保(Warrant):连接根据和结论的桥梁,确保主张合法地基于根据;支援(Backing):通过回答对正当理由的质疑而提供的附加支持;模态限定(Qualifiers):指示从根据到理由这一步的强度;反驳(Rebuttal):举出阻碍主张实现的因素,限定主张所适用的范围。抛开图尔明复杂的哲学论证不谈,仅从语用上看,该模式亦可为多元公关情境提供明确的修辞指南。
三是修辞、管理、传播、关系诸流派的相互敞开、融合和共创尚处起步阶段,公关修辞流派并未真正履践自己的对话主张。如前所述,管理、传播和关系流派的融合创新已见标志性成果,而修辞流派与其他流派的彼此开放和介入显著不足。从现有成果看,修辞流派主要以批判视角和反思性框架干预其他流派过度的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取向。批判固然是可贵的,协同创新和价值共创更不可少。有效对话缺位至少辜负了新修辞学派有关对话的核心主张,譬如韦弗宣称的“修辞通过把所有个体对于修辞的经验和意义融为一体,从而成为超越个体的普遍经验……在人们寻求文化的象征时,它能把一种共同文化的所有头脑连接在一起”。哈贝马斯的说法则更直接,“研究对象越复杂,用单一某个学科的方法就越难以奏效”。
五、结语
最近十余年来,已有一些学者起而行之。伯顿(C.Botan)和泰勒(M.Taylor)提出了公关的共创模式(co-creational model),试图协调传播、修辞和管理等不同视角,将组织和公众视为平等的对话者,双方皆以主体身份进入诠释共同体,分享意义,共创价值。皮尔森、肯特和泰勒、梅森巴赫、胡百精等学者持续将对话理论引入公关研究,以之确立公关的哲学前提、伦理基础和实践模式,并尝试构建多流派相互敞开的新范式。诚如巴赫金指出的那样,对话不一定走向某种确定的结果或结论,但它至少会许诺持续的倾听、表达、理解,只要对话得以发生和持续,超越的可能便一直存在。
注释:
① 赖祥蔚:《公共关系学想像:社群主义观点》,《新闻学研究》,2004年总第80期。
② 具体论述可参见本文中对希斯、托斯、库姆斯等学者核心观点的介绍和引用,在此不一一赘述。
③ [美]迈克·亚达斯、彼得·斯蒂恩、斯图亚特·史瓦兹:《喧嚣时代》,大可、王舜舟、王静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序言第1页。
⑤ I.A.Richards.PracticalCriticism:AStudyofLiteraryJudgement.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1929.p.174.
⑦ 温科学:《当代西方修辞学理论导读》,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58页。
⑩ Sonja K Foss et al.(Eds.).ContemporaryPerspectiveonRhetoric.Long Grove:Waveland Press.Inc.1991.p.173-181.
(作者胡百精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歌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