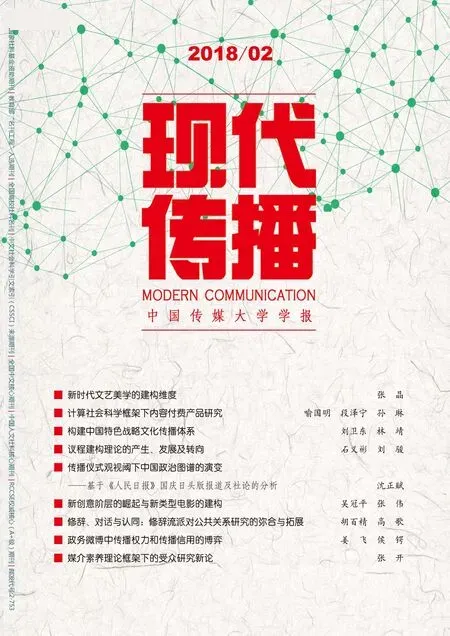从空间转向到空间媒介化:媒介地理学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
■ 谢沁露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空间理论研究思潮引发了一些学科围绕着空间论题开展了交叉融合的跨学科研究,“西方文化思想界兴起发动的空间理论转向,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活、文化政治和学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①。在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思潮的文化影响下,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地理学研究(文化地理学的分支)相互“文化转向”,逐步将研究视野转向了“空间”。上世纪末期,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进一步与媒体、传播研究相结合,围绕空间生产理论与大众传播、地方社会文化生产等新的研究题域产生的“媒体与传播的地理学”(即媒介地理学,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或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逐渐成为媒体与传播研究、地理学研究的新兴焦点。该学术领域发展至今,以跨学科视角,在以欧美国家为主的西方学术界已经成为媒体与传播学研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学科分支。
媒介地理学是一个典型的媒体、传播、地理与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交集下产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既是一种研究思潮,也是一种现象;既是一个研究过程,也是一个研究结果,还是媒介作用下思考空间与地方问题的一种方法论。我国学术界对媒介地理学的关注研究多集中于近几年,对国外媒介地理学发展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成果译介较少,尚未激活媒介地理学研究兴奋点。但媒介地理学研究的潜力是巨大的,也逐步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②。本文在文献回顾基础上对国外这一支学科分支的兴起进行学术背景介绍,试图通过对国外媒介地理学研究的背景和历史阶段、研究内容、研究特征的梳理及发展趋势的探讨,展现其从最早的空间转向研究到当前空间媒介化的发展脉络。
一、媒介地理学兴起的背景
媒介地理学研究兴起的时间较晚,概念缘起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历史溯源。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出版的《传播的偏向》探讨了空间时间与地域、政治、权力、文化、宗教之间的关系模式并“确定了媒介的属性: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③。1964年,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中也对时间的诉求和空间的问题进行了阐释,认为“每一件物体或一套物体凭借它与其他物体之间的关系而产生自己独特的空间”④。同一时期,法国著名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67年做了一场题为“其他的空间”的演讲中提出:“当前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时代……我们在时间上经历的经验的世界远不如空间网络点的连接与交叉所形成的混乱的网络中获得的多”⑤。
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的地理学家开始关注大众媒体(更明确的说是当时的报纸)的空间组织与分布问题”⑥。1965年,在美国传播效果研究受到推崇的背景下,瑞典地理学家托斯滕·海格斯特兰德(TorstenHögerstrand)发表文章运用创新扩散理论对瑞典城市的使用时间与城市规模之间更精确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以阐明“社会传播在创新扩散中的作用”⑦,同时他还通过农业社区的传播研究发现农业社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关系⑧。1974年,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出版了著作《恋地情结: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观研究》⑨,基于地方现象与人的感知经验结合,以他独特的“人文主义”视角提出了“恋地情结”(Topophilia)的理论概念,解释因感情联系而产生了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人对地方的感知、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观等。其后的文章⑩中也认为地方感应包括对地方客观特征的依恋与想象,因为“想象力是一种对世界的感悟能力,文化则是想象力的产物。人类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想象力”。加拿大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于1976年出版了《地方与无地方性》一书,他通过探讨地方的地理现象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关系,重视个人第一手经验对地方的决定性意义,得出“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第一手经验,媒体提供的只有二手经验。因此,媒体与时空扭曲”有关的结论。
从上可见,虽然有学者思考媒体与地理、空间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生产问题,多是基于研究者的兴趣,离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相去甚远。“没有一个学者、独特的事件或具体的出版物可以被看作是媒介地理学的发起者或开始。相比之下,传统研究运输地理、交通地理,如扩散理论的研究和时空压缩的工作,可以看作一个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先驱”。
伴随着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以及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爱德华·索杰(Edward W·Soja)对空间问题的理论分析与探讨,地理学者在研究中不断结合媒体的效力,关注文化地域的空间问题如何被不同的媒体以不同的角度表述与提出。80年代初期文化地理学家关注新闻报道如何对空间区域进行覆盖,涌现出第一批对媒体与地理关系研究产生兴趣的地理学家及相关研究。从内容上来看,主要讨论内容包括:媒体地理的主要理论在环境背景下的影响、新闻报导的空间偏见以及大众媒体和空间意识、媒介对空间领域进行区域的类别生产与认同的可能、新闻的空间信息内容等;从研究者地理位置分布来看,代表学者有瑞典地理学家海格斯特兰德、加拿大地理学家拉尔夫、澳大利亚地理学家D.J.沃姆斯利(D.J.Walmsley)、德国地理学家汉斯·海因里希·布洛特福格尔(Hans Heinrich Blotevogel)以及英国杰奎琳·伯吉斯(Jacquelin Burgess)和约翰·戈尔德(John Gold)、芬兰地理学家安西·帕西(Anssi Paasi)等。
到80年代中期,新文化地理学者率先展现出媒体与地理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1984年,德国地理学家布洛特福格尔通过日常报纸的空间组织对中心区域空间、日常报纸以及广告市场三者关系的传播功能区分,认为媒体是地理研究的一个课题,分析出区域报业市场的存在以及对结算系统的依赖是由报纸的出版场所和流通领域决定的。二是专门的媒体、地理与大众文化研究文集的出现。1985年,英国地理学家伯吉斯和戈尔德编写了《地理、媒体和流行文化》的文集作为第一部明确地指向这个主题的书籍出版,该书“主要的方法论灵感来源于英国文化研究,特别是关于媒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受众积极塑造媒体产品的意义问题,主要是当时在编码和解码方面展开的争论。”文集的出版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升了研究的意义,明确了媒体、地理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及讨论的重点,为媒介地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思想及方法论的启示。
“空间理论的另一个重大意义是空间生产作为一种媒体和社会实践的结果”。同一时期的社会学家也没有忽视媒介与地理之间存在的关系问题。1985年,“社会心理学家乔舒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传播学者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基础上,结合戈夫曼(Goffman)的心理互动出版了对媒体研究空间转折的重要贡献。他断言,电子媒体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看法,而且还促进了社会角色和社会的改变。”而“以英国社会学家格雷戈·费罗(Greg Philo)为首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Glasgow Media Group)开展了关于主流电视新闻报道与矿工罢工、福克兰群岛冲突、权利、性别和空间相互关联的创新研究,并成立了‘女性与地理研究小组1984’”。
文化研究学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是较早关注空间与微观地理关系的学者,在电视成为焦点的时代,发表了《全国的观众》和《家庭电视》。莫利以民族志方法关注电视与日常生活的空间地理(区域)关系,“延续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编码/解码理论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焦点小组访谈,了解不同社会群体解读国家范围时事电视节目,以及这些合成模式如何阐述社会经验”,总结出电视对私人和家庭公共空间的关系和建构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后在《家庭电视》的研究中莫利通过观察家庭收视行为及情况,以家庭性别权力关系为主题,从观看电视的行为复杂性中分析性别的权力动态与观看电视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密切关系,展示出在“家庭”这一微观区域中存在性别权力与地位的问题。
就整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研究情况来看,早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媒体与传播研究,文化研究学者以及地理学者对媒体与大众文化产生“空间文化转向”的研究兴趣而出现。这些新的研究兴趣虽然不是系统性研究,看上去也是薄弱的,媒介地理学也还远不够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出现,但对后来媒介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跨学科思想延伸和一个令人兴奋而有趣的研究方向。
二、媒介地理学的确立与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期是媒介地理学确立的重要时期,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大众媒体成为人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改变并影响了人的生活与社会文化发展,也引起了学者对于大众媒体与环境之间的关注。1984至1997年期间,延续了段义孚(1974、1977)人文主义景观与环境感知的研究,以美国学者利奥·佐恩(Leo Zonn)、斯图尔特·艾特肯(Stuart Aitken)、克里斯蒂娜·肯尼迪(Christina Kennedy)、克丽丝·卢金比尔(Chris Lukinbeal)为代表的美国地理学者关注电影文本叙事和结构与人、环境背景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影响,成果丰富。相互影响论成为了这一时期美国学者讨论媒体与地理的主要理论。1987年,在文化研究思潮的时代背景下,英国地理学家伯吉斯在其《景观客厅:电视和景观研究》一文中建议语言学和符号学是用于分析风景的合适工具,提出索绪尔的语义学和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对于图像的意义生产和解释具有一定的作用。她“以传播学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地理研究议程……应用文化研究中的理论观点,从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中得到证据来证明环境意义在不同形式的媒体文本中被编码的方式,以及由不同群体组成的受众的解码方式”。与莫利和他的受众研究一样,伯吉斯“参考了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和斯图亚特·霍尔的工作,试图在地理学中建立媒体研究的环境氛围。”她认为媒体的地理学应该考虑四个方面内容的研究,分别是:媒介文本背后的生产过程、文本本身、读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读、以及将这些意义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篇文章,被称为“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关键部分”,“不是作为地理学家研究媒体的一个‘秘方’,相反的是,伯吉斯从文化和媒体研究的视角提出更广泛的地理研究”。
此后,芬兰学者帕西对大众媒体与地理关系的研究做了进一步探索。他的作品关注文本、自传、人的故事、地理教材、符号、地图、绘画和照片的表征、符号和隐喻。1989年,帕西在他的《媒体作为地方和区域文化的创造者》一文中讨论了大众媒体如何创造地方及区域的文化以及区域文化的主题与身份塑造、维护身份问题。此文延续了他1986年对报纸如何影响芬兰四省区域意识问题的研究,关注地方和地方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如何创造特定的区域身份构建,突出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区域地方存在的特定关系,也提出大众传媒积极生产和维护的刻板印象,不一定会促进形象建立反而有反作用。另一位英国的地理学家吉莉恩·罗丝(Gillian Rose)偏好通过视觉材料分析和追踪图像如何生产展现出一个特定的世界。罗丝通过调查研究视觉生产、媒体产品和受众,“形成了她以分析讨论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的照片为基础,包括对图像的生产情况问题,在图像本身的动机和颜色选择,以及不同的观众和他们对图像的形象解读问题……证明了受众意义生产的多样性文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列斐伏尔引入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从社会与空间的本体性关系的关注进一步延伸到社会空间所生产出来的空间构成、空间实践过程与空间表征。多琳·玛茜(Doreen Massey)在这一时期也将研究视角转向了空间、地方与社会关系产生的问题,她的作品《空间、地方与性别》(1994)从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批评的视角展开空间与地方的认识。1996年,受列斐伏尔和福柯的启发,索杰提出“第三空间”(Third Space)概念,超越和取代二元知识,提出在地理范围的想象中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的探索。从文化研究批判视角,“鼓励你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空间的意义和意味,思考地点、方位、方位性、景观、环境、家园、城市、地域、领土以及地理这些有关概念,它们组构成了人类生活与生俱来的空间性……以期打开并且扩展你先已确立的空间或地理想象的范域和鉴别情愫”。
空间论的进一步探讨与展开很快引起了媒体和传播学家对空间维度的兴趣,研究焦点开始明确地转向空间,开展了与地理学者相对应的研究。1995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论道:“我们看到,正在重新构建信息图像空间并形成新的传播地理……我们正在大大改变空间与地域的概念”。明确提出现代媒介对于我们想象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具有构筑新地理的效应影响,并进一步思考媒介如何参与到日常现实地理与虚拟地理中“电子媒介构建虚拟时空和虚拟社会群体的新体验”。在谈到媒介新秩序下地方文化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时,他们认为全球化与认同感的危机带来全球媒介的新景观,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已经形成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产生了媒介作用下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矛盾下空间及地方发生变化,即“解域化”“再地域化”“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等现象功能。也就是在虚拟与现实中交错进行的空间实践产生了空间压缩、空间折叠、空间拉伸和地方想象等新的空间问题。这些现象的形成与媒体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虚拟可移动、多层想象的空间结构是空间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空间属性,是时间与空间在各种社会关系连接下形成的多重而复杂的空间几何关系。
从研究内容来看,超越了早期主要通过“对地方的意义生产和如何促进改造,规模重新配置”的媒体文本分析研究,呈现“以媒体为焦点,研究文本与文本阅读的意义,转移到文本与媒体作为实践的更广泛的基础上发展”。同时结合批判性思维探讨不同社会空间下的社会阶级、人文、政治、经济、种族、性别、消费、女性主义、霸权等问题。20世纪末的媒介地理学研究呈现出以利奥·佐恩、斯图尔特·艾特肯、克里斯蒂娜·肯尼迪、克丽丝·卢金比尔等学者为代表的美国电影地理学研究;以爱德华·雷尔夫、杰奎琳·伯吉斯、约翰·戈尔德、托斯滕·海格斯特兰德、汉斯·海因里希·布洛特福格尔等学者为代表的地区媒体与地理空间意识问题研究;以吉莉恩·罗丝、安西·帕西等学者为代表的媒体对地方与区域文化创造的研究和以多琳·玛茜、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等学者为代表的特定区域与媒体关系研究的学科研究分布地图。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前10年是媒介地理学研究最关键的发展期。首先是跨学科的领域交叉研究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相关研究讨论。在早期研究思潮发展关系的延续下,形成了以欧洲(瑞典、芬兰、丹麦、英国、德国等)与北美地区(加拿大、美国)为代表的两大媒介地理学研究阵地。研究内容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整体研究趋势相同。鉴于下面要讨论研究的特点与趋势,此处不再对派别的发展进行介绍。更重要的是,媒介与日常生活存在一种明显或隐藏的空间关系,即空间作为媒介的体验与实践渗透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感知和想象中,空间的生产也成为了一种媒介,展现出空间奇妙而丰富的人文与社会内涵,呈现出空间媒介化的特征和作用。其次是新技术下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数字遥感系统(RS)、计算机的技术协助了媒体报道对于地域、空间信息的数据采集、储存、分析、显示和描述,使多媒体融合更加顺应全球数字信息化、移动全媒体可视化的发展而融入人类日常生活。也使空间压缩、空间折叠、空间拉伸和地方想象、地方感知等新的空间思维关系与媒介传播之间明与暗、虚与实的关系更进一步凸显。
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的媒介地理学研究伴随着新青年的崛起涌现出大量专门的媒介地理学综合性研究论著。这些著作综合了相关内容、理论、视角、实践等多方面不同类型的研究,为媒介地理学成为一门学科分支及发展奠定了基础。德国美因茨大学从2008年开始推出的媒介地理学研究系列著作“美因茨媒介地理学系列丛书”(Media Geography at Mainz)陆续出版,成为德国媒介地理学研究的代表阵地。在多方努力下,媒体、传播与地理作为一门专业进入大学成为一门学位课程;专门的媒介地理学杂志《以太:媒体地理杂志》(Aether:The Journal of Media Geography)在美国诞生;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成立了“媒体与地理学专业组”。媒介地理学,正式以地理学科中的一个分支的身份,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子领域受到关注与认可,并逐步构建了较完善丰富的媒介地理学研究共同体,形成一支典型的跨学科结合的研究分支。呈现出以保罗· C·亚当斯、朱莉·库普勒斯、克丽丝·卢金比尔、苏珊· P·梅因斯、安德烈·约翰逊、杰斯珀·法尔克海默、肖恩·穆尔斯(Shaun Moores)、吉姆·克雷恩(Jim Craine)、贾森·迪特默(Jason Dittmer)、凯文·格林(Kevin Glynn)、印加·萨罗瓦拉-莫林(Inka Salovaara-Moring)等为代表的媒介地理学研究者和以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德国美因茨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英国邓迪大学、瑞典马尔默大学、瑞典隆德大学等为代表的媒介地理学研究重镇,积极热情地带领着一批年轻的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深入研究的著作也仍在日益增多,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媒介地理学研究学术地位的巩固与研究的深入发展。
三、国外媒介地理学的主要特点与研究趋势
从媒介地理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媒介地理学经历了复杂而丰富的理论与经验分析,凝聚了许多国家地区几代研究者的智慧。当下的媒介地理学研究在积累中逐步深入与系统化,呈现出其特点及研究发展趋势。
(一)国外媒介地理学的主要特点
从上个世纪后半期至今,国外媒介地理学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媒体、传播与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现有文献的回顾展示了国外媒体与传播研究者早期关注了“空间转向”话题,但媒介地理学首先发起于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的学者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对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及空间关系的关注,最终结合媒体与传播研究成为一个研究分支。尽管相关研究在早期延迟且薄弱,但在该领域的发展是积极而有潜力的,这种现象的一个解释在比较晚的现在被认可为一种“文化转向”的理解。媒体与传播参与了社会发展与社会空间的生产,与流动的空间和地方空间之间存在着多样且复杂的意义生产和交流互动,媒介的出现意味着空间和地方的出现,媒介研究的空间转向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转向。同时,“地理和传播之间的联系在于,所有形式的传播都发生在空间,所有空间都是通过传播的表现形式产生的。换句话说,空间生产理论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传播和介导的理论。”尤其是20世纪末,“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曼纽尔·卡斯特尔、戴维·哈维、爱德华·索贾等将结构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进一步发展壮大了社会空间理论”。在媒介地理学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空间理论与媒体、传播理论的结合一直与媒体、科技信息技术和时代社会的发展齐头并进,使得媒介与地方、时空的关联越来越紧密,媒体传播与地理时空之间存在一种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依存,既互相照应又互相生产的关系,相关的不同媒介产生了不同的空间、不同的生产过程和不同的理解。
2.明显的文化研究的焦点
英国文化研究为媒介地理学研究的早期工作提供了“主要的方法论启示”,而从文化地理学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新文化地理学“是与当时英国的文化研究运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背景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空间与地方本身就是社会重要的一部分,空间研究是社会研究的一部分,“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组成的,是日常的生活的实践,不同的空间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经验、意义、进程;关注了地理学家们很少关注的社会生活领域,提出精英群体对空间和文化的权力、支配、控制等问题……”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使人类的空间与媒体、世界、传播、信息、时间紧密关联,构成并创造了更为丰富而复杂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经验,扩展了经济、政治、消费、文化、身份、行为等社会问题的空间性,这些关联点的形成产生了媒体、传播、空间、地方四个象限下的新的文化研究焦点,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价值与文化表征。使文化研究开启了新的多领域而又有价值的交叉学科研究路径。
3.媒介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的媒介化解释
经历了从媒体对地方、空间的传播生产研究到以媒体为焦点关注媒体创造建构了什么样的现实与想象的空间、地方及社会,再到形成以空间、地方为介导的空间媒介化研究。媒介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是:媒介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的媒介化解释。与早期关注大众媒体影响下空间与地方的生产不同的是,空间与地方开始作为媒介,执行媒介的生产与传播功能,体现出空间与地方的特质及关系。“空间媒介化”是空间再生产再建构的路径,对于解释空间的虚拟与现实,超现实与超空间,空间隐喻与想象的空间以及空间地方感知等现象,更符合网络与融媒体时代的空间关系。“‘媒介化’概念鼓励我们捕捉复杂的社会变化过程,……通过在日常实践和(超)结构条件下的社会力量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的,而这种概念并不意味着改变只会影响某些个人或暂时的情况。媒介化指的是更大的图景。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概念引入到与现代社会平行发展的理论中去,尤其是个性化。”因此,空间与地方是媒介生产的结果,也是生产媒介的媒介。媒介传播既是起因,又是过程,也是结果,是普遍的也是个性的,诠释着空间生产力的强大与变化。
4.研究整体呈现出混合且高度零碎状态
不限制于固有的科学话语,媒介地理学多学科跨域交叉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研究必然是复杂而丰富的。从上个世纪至今,整体上来看,媒介地理学的研究是比较独特而少量的。无论是研究对象、内容,还是研究者身份、研究历史、研究方向和目的,媒介地理学研究是混合的、令人兴奋的、高度零碎的,“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或单一奇异的重点”,让人望而生畏又难以回顾。“这门学科的碎片化本质是一个弱点,也是一个更紧密合作的独特机会”,展现出媒介地理学丰富而广泛的势态。也正是如此,每一个研究成果的问世,都不可能包括媒介地理学研究的所有领域。时代的变化发展,物理空间的现实生产、价值和改变,与文化研究相联系,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变化与发展。我们欣喜的看到空间、地方、时间的多元交叉点也逐步受到关注,在许多问题领域都出现了媒体、传播与地理之间的重合。
(二)国外媒介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媒介地理学经历了媒体观照下空间与地方的生产、空间转向认识论的讨论、空间介导理论与实践生产分析再到空间与地方自身媒介化再生产研究的理论与经验分析,以及对空间想象的介导等研究发展历程,呈现出其独有的研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从分歧到融合的研究
从媒体与传播、地理学的相关文化转向研究以来,学者们各自均立足本学科视角方法进行研究,得出各自研究的认识与解释,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首先是概念定位分歧:北欧学者认为媒体研究的空间转向产生了“传播地理学”,通过地理学家和媒体研究者的合作在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一个独立的研究区域。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学者认为媒介地理学研究始于新文化地理学,尽管主要研究方法的灵感受文化研究启发,但媒介地理学关注的媒体与大众文化的问题始终是围绕不同地理维度展开的,是地理学研究中一个新兴而重要的研究分支,是“媒体与传播的地理学”。其次是派别的分歧:《地理,媒体和大众文化》的编辑指出“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之间存在根本的分歧”“美国学者采用了一种基于传输者(多个)和接收者(多个)之间的传输模型,都是个人和重点转移保真度的构思,以及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的影响,有点刻板的特征;相比之下,欧洲人把框架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力量,采用主张社会模型,揭露和批判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范式。”然而随着当代学术研究高度关联与学科交融的增加,欧洲与美国学者的合作研究越来越多,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界限已经模糊,“这个鸿沟基本消失”。格林和库普勒斯(2017)认为“我们对‘传播地理’或‘媒体与传播地理学’没有根本的异议,因为它是一个松散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名称。在这方面,我们的方法主要是务实的。”媒介地理学研究总体呈现出研究的融合态势。
2.从空间转向到空间媒介化的研究
万事万物皆可为媒介。作为一种中介体,媒介介入的动作状态,在社会与文化中扮演着介导的角色,引导了包括媒体在内的敏感介质的区域关系连接,产生了新的空间和地方。早期空间转向的研究主要关注“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媒介”如何影响、改变、生产了空间。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电影等大众媒体通过文字、图像、音频、同期声、视频新闻等符号,构建起信息涵盖范围内多元文化社会“中心—周边”的空间、时间、地域关系,以媒体为中心产生的周边相关内容对空间进行了分解,生产出新的空间及社会文化问题,凸显了大众媒体的象征性、建构性与权力。新媒体技术下以融媒体为主流代表,在空间分解和空间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空间折叠、空间压缩、空间拉伸、空间想象与感知等现象,进一步进行空间再生产,衍生出符合当代信息对人类社会、文化产生重大变革和影响的生活习惯及观念,凸显了信息时代空间媒介的虚拟性。时下,以环境、景观、气候、文化、地点、事件、美食、服饰、音乐、历史背景、情感等为代表的“非媒体为中心的媒介”在人类日常生活实践、互动和体验感知的过程和结果中,各种不同的元素与符号叠加起认知的代码,更加突出了媒介介导下虚与实的空间介导感知。在普遍中强调了地方空间维度的特别之处与独有的“地方感觉”,形成了特定的空间想象、感知与流通,显现出空间媒介化的特征。因此,空间媒介化作为一种虚实相间的交流形式,连接了事物之间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成为媒体、传播与地理之间多维界面的研究趋势。
3.从虚拟到现实的研究
“大众媒介给地理学家及其相关领域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空间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媒体代表的是世界、个人和社会概念的一部分,而且是因为媒体具有概念化和传播政治思想、加强霸权秩序的力量”。而在迷恋移动媒体的时代,空间的媒介化下时空转移带来了白日梦的实现也带来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想象与不确定性。一方面是媒介、传播与地理的关系是每一次虚拟与现实的连接,过分的强调并关注媒体与空间媒介化议程产生的新形式与问题,以及以非媒体为中心的媒介空间生产了种种假设与想象带来新鲜感,而较少“尝试连接空间与生活世界问题的媒介化概念”;另一方面,全球数字信息技术融合带来媒体、视觉数字信息化与地理空间科学技术(如卫星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等)的空间结合。媒介化的数字地理知识与媒体传播的数字化解释,打破了传统媒体平台二维的空间理解,展示了空间媒介与媒介空间的网络数据化形态。“媒体研究的分析框架需要对媒体进行‘中心解构’,以便更好地理解媒体的发展进程及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面对未来传播科技发展建构起来的虚拟世界,“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去媒介中心化的媒体研究模式,从而理解新老媒体彼此的适应和共存共生的各种方式”。与生活更贴近,在日常感知、互动和体验中关注生活具体化实践的现实生产,使数字化信息空间更加体现出数字化生活空间,让过程与结果更接地气,更形象生动,更有说服力是媒介地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使媒介地理学结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更真实地进入日常生活研究中,跨越虚拟环境,结合现实在媒介环境中的体验与实践。
4.空间的不平等与威胁
媒体、传播与地理学的结合也带来了空间的不平等与威胁问题。首先,“空间也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再现的空间是‘被统治的空间’”。在介导的过程中,涉及权力分配和使用的空间生产及关系便会带来空间分配的不平等与不平衡;其次,媒介空间的界限模糊使得移动、技术融合、互动下无空间界限的电子监控深入了日常生活当中,产生了私人生活如监狱般受到控制等隐私监控问题;再次,媒体的出现减少了人类面对面交流见面的机会,改变了群体活动、社区活动等共同活动空间的原有地位,尤其是“过分依赖虚拟电子连接破坏了我们与实际物理位置的联系,威胁到我们的公共空间交流,在网络空间漂流”。此外,在空间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空间和地方会经历折叠、压缩、延伸等空间形态的变化,带来了空间形态的不平衡现象。空间被先进的通信技术所替代的同时,空间与地方的位置是媒体和通信技术控制下的地方感,形成了“超空间的移动空间控制”。还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大众媒体、社会文化、集团企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在内的介质,在介导过程中空间的时间表征与时间的空间再现会呈现不均衡的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呈现出“时空扭曲”,削弱了地方(或空间、景观等)身份的代表性意义和定位再生产。因此,媒介对空间的影响也存在空间分裂,促进了空间发展也影响并约束了空间发展,这种对立又统一的空间辨证关系在虚拟与现实的空间环境中决定了我们需要思考空间生产如何有序地存在。
四、结语及局限性
本文从媒体与传播的地理学研究发展的历史线性实践出发,分别从媒体与传播研究、地理学研究两个学科领域为切口进行分析,试图在“媒体、地理与空间研究”的脉络中寻找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进程、特点与研究趋势,呈现出从上个世纪学科之间空间文化转向思潮下的研究发展到当今时代下产生空间媒介化为新特征及趋势的研究。因媒介的快速变化发展带动着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变化发展,媒介地理学也呈现出复杂分支态势,在历史溯源方面,本文只聚焦至21世纪前10年媒介地理学研究。同时作者自身文献参考视野与文章篇幅有限,在本文历史梳理中难免有遗漏局限,此文仅为我国发展中的国外媒介地理学的研究作以借鉴参考之意义。
注释:
② 参见熊壮、方惠、刘海龙:《2016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期。作者以2016年中文新闻传播期刊中传播学方向的论文为基础总结了2016年中国的传播学的重要议题与主要成果。指出我国传播学研究集中在包括“城市传播与媒介地理学”在内的十个领域或话题。
③ [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言。
④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⑤ 英译本见Michel Foucault,OfOtherSpace,Diacritics,vol.16,no.1,1986,pp.22-27.
⑧ Bo Lenntorp,Gunnar Törnqvist,OlofWärneryd,Stureöberg,TorstenHägerstrand1916-2004,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Human Geography,vol.86 issue 4,2004,p.325.
⑨ 参见Tuan,Yi-Fu,Topophilia:AStudyofEnvironmentalPerception,AttitudesandValues.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74.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工程师,澳门科技大学传播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