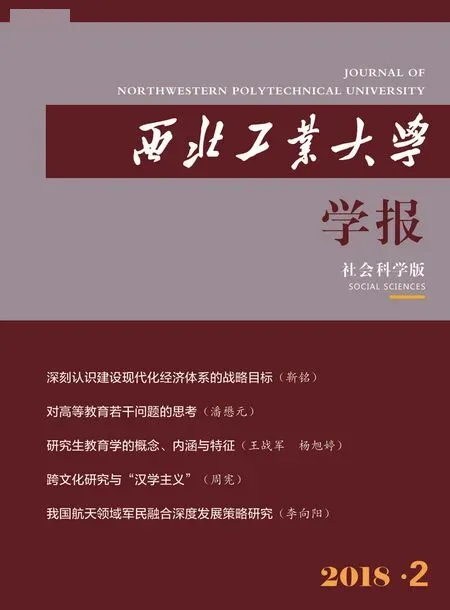情感史与跨越边界的文学研究
法国理论家朗西埃著有名篇《为什么一定要杀死包法利夫人》,分析了主人公的死亡所揭示的意义。包法利夫人的问题在于把小说中的缠绵情意和贵族家庭中目睹的奢华精致误认为生活的目标,不满足自己作为乡村医生夫人的平庸境遇,为了虚荣骄纵的生活负债累累,最终无助而亡。包法利夫人把想象当真的能力无疑是死亡的根源,自尽是对她的惩罚,对中产阶级女性的警戒。问题是小说为什么要杀死把想象当真的人?朗西埃的答案是福楼拜杀死包法利夫人,表明她将想象和生活融为一体的行为只是对贵族审美趣味的拙劣的模仿对粗劣模仿的一种抵御,只是将一个阶层的旨趣奉为圭臬,产生这也是自己原生欲望幻觉,并对之加以粗暴的复制,这种模仿远非欲望的民主。朗西埃认为,《包法利夫人》创造了一种新的写实主义,用和主人公不一样的方式实现文字与现实的融合。福楼拜的写实不是粗劣的模仿,而是将此间的所有自然扰动和感官体验悉数呈现,将瞬息万变的感官体验和情绪悉数传递给读者,打破“可感知物的等级式分布”,让他们在阅读中培育一种不加辨别的感受模式,这才是真正的欲望的民主,情感的民主①。这个评论告诉我们的是:小说形式的变迁往往是对某种情感模式的反抗,而新的叙事风格和新型情感模式总是互相包含、相互依赖的。小说史与情感史不可分离。
对于世界小说史的研究,本文想从小说形式与情感模式之间的关系入手,以小说史进入情感史,以情感史反观小说史。下面首先梳理情感文化史研究,说明18世纪小说在这个领域的重要地位。随后逐一探讨理查森的《克拉丽莎》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小说”的不同形态,以及它们暗示的不同情感模式。比较文学不仅跨越语言与文学传统的界限,也同样含有打破文化与文学边界的意思,本文将从这两方面同时入手,对18世纪欧洲小说和情感史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情感研究(emotion studies)的众多理论渊薮
在心理学之外,情感研究发轫于历史学和人类学。 早在1985年,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和卡萝尔·斯特恩斯夫妇就在《美国历史评论》中提出“情感学”(emotionology)研究的必要性[1]。2010年,伦敦大学的伊恩·普兰普尔在《历史与理论》期刊上提出“情感转折”这个观点[2]。而《美国历史评论》又于2012年举行了一次名为“情感历史研究”专题讨论,邀请六位人类学学者和历史学者一起与编辑探讨他们进入该领域的不同路径以及在研究中采用的不同方法。专家都指出“语言转向”的不足之处,但同时又以语言建构的思路来考察情感,提出情感借助概念才能形成,并遵循成文的社会情感规范。这种理解与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对于情感的理解非常一致,文学学者蕾·特拉达曾写过一本非常好的专著《情感与理论》,探讨情感在后结构主体观中间的地位。她从德里达开始梳理,认为他改写了胡塞尔和卢梭对于“自发情感”(autoaffection)的认识,将情感理解为对于内心世界的阐释,其基础也是“自我的分裂”(self-deference)以及“自我对自我的再现”(self-representation),并非自我感受本身[3]。这个观点其实从笛卡尔时期就开始萌芽,笛卡尔在《灵魂的激情》(1649)中就认为激情是理性的一部分,和理性一样,情感是可以被自我认知的,只要它足够清晰,自我与自身的理性思考和激情之间存在沟壑,但是可以被弥合。而后解构主义者认为理性思考与激情都不能克服主体内部的裂痕,所谓直觉可感受的内心情绪,离不开使之得以成形的概念,而概念也不像康德所论内在于个人的认知结构,而是外在语言强行加诸个人的。
除了解构主义理论,情感研究在文化研究领域内还有很多其它理论依据和源头。首先是工人阶级文化、女性文化和流行文化研究的兴起。伯明翰学派创始人、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先驱理查德·霍佳特在《读写能力的功用》中采取了动之以情的写作模式,对阶级不公后果的感性叙述为文化研究开拓了在社会学描述之外体察所观察对象所面临的“不同情感压力”的学术脉络[4],其研究思路在霍尔、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安德鲁·罗斯等学者这里有所延续,虽似乎式微,但并未全然泯灭。更重要的是另一位雷蒙·威廉斯提出“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理论,在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与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不同,“情感结构”关注工人阶级日常生活与流行文化所产生的情感体验,而且是尚未沉淀为意识形态的 “形成中”(emergent)的情感特征,就像溶液中飘浮的微尘,有隐性的结构,但还没有显而易见的形状[5]。沿用此概念的学者多强调变动中的文化和经验,指向的是还没有定型或者不能僵化为“结构”的流动的经验[6]。不一定要在当代文化中寻找,过去时代中的不明显情感结构也是可以根据这个思路提炼的。 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概念与胡塞尔和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不一样,不是指作为个体意识背景和框架的既定文化世界,而恰恰是还没有固定下来的情感线索,激烈、真切,捉摸不透。
与早期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一样,女性文化和流行文化研究也培育了一个对于情感问题十分关注与友好的批评氛围。对于“感伤小说”或“情感小说”的批评也大有助益。从简·汤普森1985年的专著《耸动的布局》(Sensational Designs,探讨1790—1860年间的美国通俗小说)以来,出现了大量研究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的通俗小说的研究,为研究文学传播及其效应的研究提供了启发与思路。
其次要追溯至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中对于主体建构的拷问。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延续、发扬了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结合在一起的主体理论,对资本主义所需要和构建的主体进行了细致分析。詹明信也承继了关注主体建构的左翼批评传统,后现代情感的学者都难免要遭遇他关于后现代文化中“情感的萎缩”(waning of affect)的论点。詹明信借用列奥塔《力比多经济》中反宏大教条的思路与语汇,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情感已经脱离了固定的主体,并把这种与主体无关的情绪称为“强度”(intensities),指出它具有 “自由扩散、非个人化的特征,往往呈现为一种特殊的狂喜”[7]。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于当代情感理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当代学者对弗洛伊德的“忧郁”“重复冲动”“创伤”和“集体心理”等概念都进行了重新阐释,要么把弗洛伊德变成后现代理论的对立面,要么变成后现代理论的先兆。
主体建构理论在德勒兹这里达到了高峰,他开始致力于发现主体“产生”的机制,而不再满足于康德对于主体存在的超验前提的解释。借用尼采、伯格森和斯宾诺莎的语汇(谱系、多元性、一元性)来想象一个不断产生,不断变化的现实和主体。无独有偶,福柯也用自己的《性史》开启了研究情感谱系的方法,和德勒兹一样强调欲望和“感受”欲望的主体所产生的过程。这两位精神息息相通的理论家对情感和主体的形成进行了重新阐释,从根本上将两者都解释为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德勒兹也是更为理想主义的一个,认为存在的形式即无意识的生理能量和对外界产生影响的能力,即“强度”,正是这尚未进入语言和概念的“强度”在不断变幻中塑造着时刻变换的主体②。德勒兹和福柯两位理论家对于情感(包括通过语言中介的欲望,也包括无意识的“强度”)在文化史研究中的崛起至关重要,也使研究者得以跳出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窠臼。在福柯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以格林布拉特和凯瑟琳.加勒格等人为代表,在对早期现代和现代文化的研究中关注情感模式的变迁,模糊次要和经典文化作品的区别,寻找被社会规则所限定但又包含变化潜能的文化现象。格林布拉特对于“自我观念”形成的历史和加勒格关于19世纪“身体经济”的研究等都凸显这个特点③。而同时,德勒兹的译介直接促成了狭义情感研究,或称之为“情动研究”(Affect Studies)的崛起,以帕特丽夏·克劳为代表的学者用“强度”的概念来提议各种打破社会对身体进行控制的手段④。
最后,情感研究在当代文化理论之外,也可以在“传统”理论中发现一些先兆。《论崇高》以来的审美理论大多与情感有关,也从情感史研究的角度得到了新的阐释⑤。韦伯以降的文化社会学也对社会变迁的情感因素与制度支撑做出了细致的梳理。德国诺贝尔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荷兰史家约翰·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秋天》,H.O.赫施曼的《激情与兴趣》等书籍都是文化史研究的先驱,也可以在与当代理论的碰撞中产生新的火花。另外还有一个传统也进入了情感文化史研究的领域,那就是心理学、解剖学,以及脑科学关于意识形成和结构的话语。这些科学话语对现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介入很深,当代文学研究也已经开始深入关注科学对于文学文化发展的影响⑥。
总之,我们可以说,在情感研究中,必须厘清两种类型的关系。一是主体、意识与身体之间的复杂关联。“主体”强调社会关系,“意识”与“身体”侧重心理和生理过程,对前者的理解比较依赖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而后两者比较依赖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和生理学,但这三个概念在情感研究中都有不可或缺的位置。另一种关系指的是日常生活与再现的关联,文本和社会规范、礼仪风俗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都包含错综复杂的情感结构。研究者必须兼顾经验与文本,勾勒情感结构形成的过程,又避免机械地将情感结构削减为韦伯所说的“理想型”。
18世纪在情感研究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这是被弗莱(Frye)称为“感性年代”(Age of Sensibility)的世纪,是“私人领域”形成的时期,也是情感在哲学和社会伦理道德话语中突然崛起的世纪,是同情、慈善、博爱等资产阶级“情感结构”的关键元素逐渐显露的时期。这同样是现代英语小说兴起的年代,图书市场的完善也使得阅读越来越多地成为情感塑造的场域。小说甫一诞生,就以强大的娱乐和移情作用著称,形成了最早的媒体文化,小说表现情感模式的重要变化,能引发幻觉,锻造思维,早期小说作者和批评家们对小说的社会功用充满期待,同时也心生恐惧。这个时期有许多以情感探索为中心的著名小说,最为畅销、影响最广的莫过于英国的《克拉丽莎》和法国的《新爱洛伊丝》。卢梭明显借鉴了理查逊的作品,而理查逊也受到法国文学的影响,互相勾连紧密,但他们对于情感与小说关系的理解又有很多区别。资产阶级“情感结构”在以这两部作品为代表的小说中找到土壤,但却始终没有沉淀为静止的世界观。谈小说与情感结构的关系有两层涵义,第一是深入分析文本如何再现复杂的情感结构,第二是探讨小说如何在阅读中产生移情和塑造情感的过程,进而推动情感结构的变化和生成。本文聚焦于第一点,第二点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笔者在其它场合有所涉及[8]。
二、《克拉丽莎》的复调写作
《克拉丽莎》是目前所知世界上篇幅最长的英语小说,也同时是写男女感情冲突最出色的小说。爱情与婚姻是小说诞生之初就专注探讨的主题,一般将现代小说的源头追溯至古希腊以来的散文或诗体罗曼司,那么与情爱——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更是无法脱离。对待婚姻和爱情的态度都在18世纪发生了重要改变,贵族和士绅阶级的状况记载尤其完整,注重个体权益的资产阶级伦理观的兴起,隐私与婚姻自主观形成,单身女性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这种种变化又与叙事形式的革新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研究情感结构变迁的肥沃土壤。
英国书信体小说可以追溯至历史学家詹姆斯·豪威尔(James Howell)在1645—1650间整理出版的《家常信札》,出版时是以真实书信为名义,不过目前大部分人认为这个合集中有些信件属于虚构,实际上可以看成英语中书信体小说的源头。一般认为,法国书信体小说对理查逊的影响也比较大,1669年出版的《葡萄牙修女的情书》在法国乃至欧洲都有巨大影响,开启了17、18世纪以直接记叙、表达情感为叙事形式的书信体小说的脉络,随后,马里沃(Marivaux)的《玛丽安的生活》也对理查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理查逊并不只是承继了前人精髓,他对书信体小说这个体裁做出了两个重要创新,一个是在书信体小说中充分运用书信写作所特有的自省写作模式——正如克拉丽莎所说的“写下每一时刻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对未来有用的所思所为”(135封信)。同时,理查逊也通过重写“男女之战”这个文学母题开创了让人物在书信中互相品读的传统。克拉丽莎和追求者勒夫拉斯不仅对于同一个事件的叙述往往体现了截然不同的视角,同时又彼此互相试探观察,这在书信体小说中开创了一种特殊的复调式写作。把男女情爱比作战争始自奥维德的《爱》与《爱经》,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也经常有把俘获女士的芳心或者把自己的心灵被爱情俘获比作狩猎。可是,在《克拉丽莎》里,男女求爱的过程不再只是激情消泯了理智之后的攻城略地,而是理智和判断力的一种较量,这种判断力中包含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对他人内心的解读。这点是至关重要的创新,理查逊之前从来没有作家在描写求爱过程中如此细腻地展示男女双方互相揣测的环节。《克拉丽莎》中两位主人公之间矛盾的根本缘由并非外界干扰(与《汤姆·琼斯》不一样),而是两人意念上的差距,也是互相之间的误读所致。误读在早期现代戏剧和早期小说中也时常有所发生,但一般都与化装、易装、或故意的误导有关(参见莎士比亚喜剧、海伍德的《范特米娜》,以及菲尔丁的各部小说)。理查逊的第一部小说《帕梅拉》中,男主人公因为一个巧合有幸读到女主人公的手迹,因此得以窥见她的内心。在《克拉丽莎》中,这个作者干预手段被抽离,两个主人公只能依靠揣测琢磨对方内心。小说的悲剧走向不仅是对历史话语中男女地位差异的反映,也源于理查逊对男女情感互动中巨大错位的认识。
男女冲突的内心化不仅开了书信体小说的先河,在英国叙事文学中是从没有发生过的现象,可以说是理查逊最重要的首创。我们可以考察小说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段落,仔细看看克拉丽莎在离开家后是如何同意跟勒夫莱斯去罪恶之地伦敦的。克拉丽莎在给密友安娜小姐的信中说,勒夫莱斯听到了她家里人要强行带她回去的消息,就提议他们去温莎(116封信)⑦,后来又表示温莎人多而杂,或许不妙,又提出伦敦。此时克拉丽莎为了判断他是否早有带她去伦敦的预谋,“不断盯着勒夫莱斯的眼睛,考察他内心的诚实程度”(125封信),她最终判断勒夫莱斯其实并无意伦敦,并没有设计陷害的意思,便同意前往,正如她自己所说,“假如他对伦敦早就深谋远虑,那么她就不考虑了”(125封信)。但勒夫莱斯早已读出克拉丽莎的疑虑,所以其实是有意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为了让克拉丽莎选择伦敦,故意先提议温莎,更有甚者,他将自己的算计归咎于女性的心机:“是她们让人不得不狡诈以对,等受了骗,又反过来控诉一个借用其人之道的男人。(127 封信)”这段心理冲突异常纠结,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规律的例证。克拉丽莎不断用直接的方法来对他进行观察揣测,而勒夫莱斯做的许多事情都基于对克拉丽莎可能做出反应的预测。在小说中还出现了克拉丽莎不断揣测他人心思的段落,因为勒夫莱斯长辈贝蒂夫人给她写的信(实为勒夫莱斯假造)没有明确邀请她前去拜访,便拒绝前往暂住,揣测说“夫人心知对错的界限,既然是为了担心我不接受才不给我邀请,那么假如我真的接受了邀请,一定觉得我很无礼”(123封信)。克拉丽莎自始至终的性格特点就是“delicacy”(敏感),这个词在小说出现得非常频繁,其意义就是对举止得当和谦卑辞让等礼数感知敏锐,而遵循礼数又要求她对同阶层人士的习惯心理体悟准确。同时,勒夫莱斯也显示了很强的判断力,在很多场合都正确估计了克拉丽莎的反应,比如他第三次求婚后,克拉丽莎没有拒绝,只是表示不能太快,勒夫莱斯在信中就这样揣度她的内心:她不同意快速结婚是因为她“至死恐怕也不会放弃的‘敏感’不会允许她逾越礼法”(152封信)。
两人的互相揣测有切中要害地方,但误读的阴影挥之不去。克拉丽莎很早发出了勒夫莱斯“没有心”的慨叹,对他总体的认识——过于骄傲又过于谄媚,不尊重女性意志——比较接近他自己信中流露出的性格特征,但她毕竟失算了,完全低估了他为了征服自己而可能采取的手段。而勒夫莱斯就更为失败,他在整个小说中都充满了对克拉丽莎的操控欲望,想要提前揣测她的心理,诱导她走向他所决定的方向。但他也和克拉丽莎一样失败了,他施加强暴行为正是对自己的心理控制能力失去信心的体现,对克拉丽莎的暴力是二人判断力共同失败的表征。如果说克拉丽莎的失败源于缺乏对险恶社会的见识,那么勒夫莱斯的问题在于世俗偏见的流毒。他在强暴克拉丽莎后对贝尔福德坦言说希望他最终能被原谅,但又希望“在类似情况下我是她唯一能够原谅的人”(259封信),态度十分矛盾。究其根源,是因为勒夫莱斯一直坚信绝大多数女性在遭受强暴后就会屈服,所以虽然因为无法说动克拉丽莎而对她施以强暴,但同时也担忧她会印证女性无法逃脱的软弱。勒夫莱斯对女性软弱的担忧一方面是出自他自己对女性始乱终弃的经历,一方面也受文化思维定式的影响。他将女性不能坚守忠贞的念头强加于克拉丽莎,又希望她能推翻这个期望,这显然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这表明,男性对女性期望的内在矛盾被转嫁到女性身上,使她们不堪重负,克拉丽莎的死正是这种重负的代价。而勒夫莱斯也是一名牺牲者,他最后向克拉丽莎表兄莫登发出挑衅,致使后者提出决斗,勒夫莱斯这里的行为无疑是拿生命赌博,是他彻底失去对克拉丽莎的操控后绝望心情的体现。可见,这部小说的悲剧走向印刻着社会与个人认知中不可纾解的矛盾,书信体小说的“复调”转向为一种新型情感悲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理查逊所开创的多重视角叠加的叙事手法意义深远。视角的掌握是从奥斯丁到纳博科夫的小说中一直最为重视的叙事元素,读者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判断各叙事片段出自哪个视角,不同视角间或叠加或折射,互相遮蔽修正,而理查逊用书信体首先进行了一番史无前例的探索。理查逊的天才就在于将笔下人物阅读他人的能力推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在多视角叙事中融入了彼此互读的艰难过程,将“男女大战”母题的悲剧阐释至极致,为之后的英语小说树立了一个无法规避的标尺。他也给读者的认知和解读制造了美妙的障碍。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往往能发现“内心”的复杂与不可知性,这当然不至于会阻止他们阐释内心,但会让他们对每一种阐释都保持对其对立面的警觉,思考小说中其他人物以及目力所及处其他读者的相异阐释。
勒夫莱斯与克拉丽莎之间的心理大战也提醒我们,不仅要把小说中单个人物的心理放在不同视角的交叉互动中来理解,也要将理查逊的小说放置于它所回应和关照的语境中来解读。因此,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男女就婚姻和情爱问题进行交锋的历史就格外重要。在这个世纪里,女性提出了自己对于婚姻的强烈诉求,而男性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弹,矛盾不断激化,呈现出拉锯的态势。首先,17世纪中叶英国内战期间,适龄男性减少,未婚女性向议会请愿要求男性尽早结婚,最早的一篇请愿文出现于1642年,标题叫做《失去心上人的处女之怨》(The Virgin’s Complaint,1642)[9]。复辟时期,由于浪荡子文化的崛起等因素,又大量出现了指责男士行为不端,或拖延不婚,使得女性无法正常成婚的文字,会出现在有“悲叹”“怨词”字样的标题下,或者虚构的女子议会的章程和决议,借此抨击男性对婚姻不负责任的态度。随着17世纪晚期英国现代宪政的确立,女性的政治权益意识增强,对于男性的不满也上升到直接表达的地步。
而男性对这种情况的变化也做出了可以想见的反应。一方面是书写劝导手册,为恨嫁女士提供策略和方法,一方面针锋相对书写婚姻生活的困扰和对男性的拖累。这种拉锯不久也促成单身生活理念的兴起。而单身女性经济地位上升也为自主选择单身女性的几率增大提供了条件。
18世纪早期,以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为代表的女作家开始把单身作为一种比不幸婚姻要更可取的选择,并探讨社会如何为单身女性准备空间。由于修道院在17世纪的英国大规模解散,单身女性缺乏其它欧洲国家所能提供的容身之处,如济贫院(almshouses),女修道院(beguinages),和妓女收容所(Magdalen house)等场所。阿斯特尔便倡导女性学院,设想使女性在不受男性干涉的情况下,与其他女性一起接受现代职业和技能教育,成为独立的个体和群体。虽然设想没有实现,但也毕竟在思想上超越了笛福等男性文化人士建议通过女子学院,让女性接受教育,从而为婚姻做好准备的思想⑧。反过来说,单身女性概念的兴起又引发了对这个群体的尖刻嘲讽,“女光棍”(spinster)一词的意味在18世纪有所丑化,和新出现的“老小姐”(old maid)一样成为攻击女性的利器。当时的文化名流斯蒂尔、笛福、艾迪生等人都在杂志中发表过嘲讽“老小姐”的文章。
理查逊在小说中重写“男女大战”的主题无疑是在回应和重写这段复杂的历史。他通过对勒夫莱斯的心理刻画暗示男性对女性主体意识增强的抵触和无奈,及其引起的女性污名化现象。理查逊的小说经常被诟病为“小气”“逼厄”,实际上却能在主要人物寄寓变化中的情感机制,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彩和深入。
理查逊对男女双方在互动中体现的心理机制的考察往往不被人欣赏,后世的批评家经常做出一边倒的批评。在阅读《克拉丽莎》的历史上,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界曾经掀起了一场小高潮,围绕克拉丽莎被强暴到底是谁的错意见纷纭。威廉·沃纳1979年的著作《阅读克拉丽莎》(Reading Clarissa)使用解构主义理论,通过精致的细读论证克拉丽莎对事件的进程也是有所掌控的,并非全然的受害者。随后,特里·卡瑟尔和伊格尔顿分别出版了一本专著,反驳沃纳著作中架空历史的论证。他们同样强调小说中复杂的权力与话语斗争,但认为还是应该突出克拉丽莎作为一个女性在小说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卡瑟尔认为克拉丽莎是被控制、被随意解读的,虽然她自己也患有“阅读病症”,经常做出误判[10],伊格尔顿抓住强奸被快速掠过的事实,指出这也正是小说中很多人物和许多批评家同样无法正视的男女权力的不均,导致他们在质询克拉丽莎在此事件中责任的时候忽略了女性的总体社会地位。批评家的不同结论体现对18世纪性别关系史和婚姻、情感史的不同认识,取决于对权力分布状况,及其对个体命运影响的不同观点。情感建构是主体建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里面少不了权力关系的影响,而权力之网到底有没有空隙,多少空隙,永远是文学争辩的关键,也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答案。这场关于克拉丽莎的争辩重复了理查逊和他的读者之间对于小说中两位人物的争论⑨,也恐怕是一场只要有人读《克拉丽莎》就会不断被重复的争论。文学人物应该如何行动和感受,应该如何展现历史的重压与主体的应对策略,是文学研究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克拉丽莎》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践。
三、《新爱洛伊丝》的异托邦
卢梭和理查逊有着很鲜明的共同点,两者都以书信体小说的形式探讨现实爱情的可能,而并非可能或理想的爱情,并且手法细腻,比英语、法语传统中的前辈贝恩、马里沃等人的勾勒要丰厚细腻得多,并以此来引发读者认同。《克拉丽莎》和《新爱洛伊丝》都有明显的说教意味和企图,理查逊劝诫女性谨慎,卢梭则想要勾勒“没有罪恶的爱情”(第五卷12封信)⑩,但两人最终都并不强加教条,虽然提出伦理命题,但最终都显示了命题在现实中承受的诸多阻碍,以不可逆转的悲剧收场。卢梭的小说也是在理查逊的《克拉丽莎》的启发下写就的。如果说理查逊小说的悲剧在于男主人公在情感和女性地位的观念上无法企及女主人公的理想境界,二者无法调和共存,那么卢梭《新爱洛伊丝》的矛盾在于两主人公理想中的爱情在现实中难免露出或自私或妥协的面貌,难免走向衰败,只能让于丽在风华正茂时突然死亡,让故事定格于情感纯净之极的顶点。卢梭小说受理查逊启发是毫无疑义的,但也拓展了理查逊的情感研究工程,展现情感困境的另一侧面,探讨真诚无私的情感如果形成,能否在现实中长存的问题。
世俗的浪荡子之爱在英国小说和戏剧中的传统都十分旺盛,拉克洛的《危险关系》众所周知,其实之前就有克雷比永的《心灵与头脑的流浪》(1736),最早也可以追溯至西阿诺与索雷尔、帕斯卡尔这些人对于宗教制度和社会规范的抵制、反讽。可与英国托马斯·奥特威戏剧的《孤儿》(“The Orphan”1680)和尼古拉斯·罗尔的戏剧《美丽的忏悔者》(“The Fair Penitent” 1703),以及曼利的小说《新亚特兰蒂斯》(New Atlantis 1709)和克利兰德的小说《芬妮·希尔》类比。卢梭想要写的小说是反其道而行之,与《克拉丽莎》一样,《新爱洛伊丝》也是对浪荡子文学发起的抵制。正如于丽在小说中所说:“用教学来玷污女士的心灵是所有引诱手段中最为卑劣的;而如果用小说来打动心上人那么就太没有手段了。”(第一卷第8封信)在这句话里,卢梭否定了之前的小说传统,说明作为一名家庭教师,圣普乐所应该做的就是要摈弃以知识和言辞进行引诱的惯常套路。与《克拉丽莎》不一样,在卢梭设定的情节里,女主人公占据主导地位,她称呼圣普乐为自己的“学生”,并在死前深刻影响了男主人公的情感走势,在与沃尔玛成婚之后,也将原来炽烈的爱情转换为“崇高的友谊”(sublime friendship)。女性视角的胜利很为罕见,而且这还不是对世俗有抗拒能力的“知性”女主人公,而是类似克拉丽莎圣洁女性的形象。
这种规训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于丽对于圣普乐的影响体现出来的,这里的男女主人公没有情感不对称的问题,两人都对对方有很深的爱恋,但是于丽一开始就指出了一点:
我的愿望是你能够理解一个很重要的事,那就是依靠我来关照我们两人共同的未来。难道你怀疑你对我就像我自己一样亲近,你认为我感受到的任何喜悦会对你有所保留吗?不,我的朋友,我和你志趣一致,但理性略多,更懂得驾驭。我承认比你年幼,但你是否注意到,虽然女性的理性通常弱些,更容易凋零,但形成也更早,就像柔弱的葵花比橡树萌芽早,生长也更快。我们从幼年起就被委以危险重任,为保存理性很快就唤醒判断力,而要洞察事情发展的结局,必须深刻感知其签字风险。就此事而言,我越是思索,越是发现我的爱与你的理智对你有着同样的要求。所以请你聆听她甜蜜的声音吧,接受另一个盲人的指引吧,那个盲人至少还有一些依傍。(第一卷第11封信)
这段话里有不少当代读者无法接受的陈旧话语,尤其是女性与理性的关系。这与后来于丽奉父命成婚,并认同宣扬婚姻中男女应有分属领域,做同样的事可能抵触频发的观念一脉相通。卢梭对爱情中的美德极端强调,却也和理查逊一样,接受了18世纪对于女性能力的贬抑以及对她们行为领域的束缚。同样,他也和理查逊一样,将女性美德与超越身体需要与情感的纯洁联系在一起,这个美德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精神性,对身体的忽视,另外一点也同样重要,那就是无私地将对方置于自己之上,卢梭对爱情的阐释也是极其理想化的,根基在于美德:“美丽的于丽,你的魅力闪耀我的双眼,但如果没有那个更强大魅力的激活,它们绝不会让我的心灵迷失。打动我的是你鲜活的敏感,不变的温柔,对他人苦难轻柔的同情,是你的良好的判断和高尚的品味,它们的纯洁正是你纯洁灵魂的延伸。”(第一卷第1封信)卢梭也借鉴了理查逊小说中对于“纯洁”友谊的歌颂。在小说第一卷中,我们就看到克莱尔给于丽写的信中的这样一句话:“我们几乎是从摇篮里就开始结下温暖柔和的友谊,从不曾分离,可以说,正是这友谊点亮了我们心中所有其它的激情。(第一卷第7封信)”卢梭与理查逊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纯洁情感的歌颂与之前《爱弥儿》《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早有显现。《新爱洛伊丝》中圣普乐又提出了“理智造就了人,情感为他指路”的见解,与休谟《人性论》中对于情感的道德作用的表达颇为相似(第三卷第7封信)。
于丽命令圣普乐离家之后,他在欧洲各地游历,并继续与她通信,其间对法国上层社会的情感方式发出颇为严厉的斥责。他说法国名流无一不喜欢谈论情感,辞藻华丽,却没有一丝真情:“哦,于丽,我们心灵简单,从不知道这些美丽的格言,不过我担心,对这些所谓经历老道的人来说,情感就像身处学究包围的荷马,他们制造了一千句美丽的辞藻,却没能发现荷马真正的美”(第三卷第17封信)。圣普乐对虚假法国人的看法让人想到史达尔夫人在《德国》(1813)一书中对于法国社会普遍逢场作戏的轻蔑之词。
卢梭对于真实情感的赞颂对法国大革命的情感观念影响深远,至少从埃德蒙·伯克开始,卢梭就被看作法国革命的主要精神鼻祖之一。美国历史学家威廉.莱迪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合法性基于对自然情感的推崇,而这种推崇的精神源泉就是卢梭[11]。但卢梭也很清楚地知道纯真的情感得来不易,这种领悟不仅来自他自己的个人情史,也来自他对历史的见解。在小说中,于丽的突然死亡也给卢梭的理想主义蒙上一层尘土,连他也不知道这样无私的情感能否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保持,即使是想象也难以延续,这与克拉丽莎最后精力交瘁而亡具有同样的悲剧力量,也同样展现了萌动的情感结构与社会限制之间的巨大张力。
理查逊和卢梭的小说都被认为是欧洲“情感小说”的重要源头,本文不拘泥于文学形式的演变史,将体裁发展的历程与情感结构的变迁结合起来考察。18世纪欧洲对于婚姻与爱情的认识普遍有所变化,女性地位也发生了重要而矛盾的变化,一方面是圣洁的美德化身,人类精神的引导者,一方面因为追求情感自主成为被丑化的对象。
四、结语
法国与英国文学交流非常广泛,都在18世纪中期发展起以情感探索为主题的小说,但是在情感表现的方法上很不一致。这方面研究很多,值得我们认真梳理。情感研究与文学与文化的交叉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研究热点,它使我们得以回到文学自18世纪以来就致力探索的日常生活和生活经验的传统,将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精神分析,和福柯开创文化史研究传统的方法结合起来,在文学和其它文化形式中发现“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无法囊括的精神史线索和云团。用情感史的视角,批评者可以将文学形式以及性别、阶级等社会范畴的讨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对于崛起中的“意识”结构的考察,全面打开我们的批评维度。
情感文化史的研究不局限于小说,但以此入手也不失为一条好的途径,正如威廉斯所说:“语义形象”(semantic figures) 中飘浮着不曾定型,却因此更为鲜活的情感结构⑪。18世纪欧洲小说更是这项研究不容质疑的重镇。现代小说的崛起产生了一个极其具有穿透力的早期媒体文化,这个发展与18世纪“情感文化”的兴起交织在一起,为我们研究情感的隐秘历史提供了一个显著的场域,一个合适的入口。理查逊和卢梭对“情感小说”的期待远不止我们常说的感怀涕零,而是希望能激发向善的情感,拿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中的话来讲:“小说恐怕是人心溃烂后唯一迸发教诲作用的终极手段了;我希望只有诚实理智的人们才被允许创作小说,用作品书写心性,只有具有人类缺点的作家才不会把美德描写为人类不可企及的天堂盛景,而会让人觉得美德不是那么严肃,继而逐步从罪恶的怀抱中挣脱,慢慢走向美德。(第二卷第2封信)”这段话是对小说诞生之初作为娱乐和教化双重作用的最佳描述。当我们理解了18世纪小说的精妙之后,便可以由此进发至18世纪小说阅读史来考察小说的实际情感效应,然后转移到其它时间段,或进入与欧洲以外的文化进行比较的路径,前景不可限量。
注释
① Jacques Rancière, "Why Emma Bovary Had to Be Killed," Critical Inquiry 34, no. 2 (Winter 2008):237.此处的翻译是笔者的,原文是“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② 关于“强度”的解释参见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lated by Brian Masumi,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 31. 两位作者延续了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将“欲望”重新阐释为“情动”(affect)的做法。
③ 参见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Catherine Gallagher, The Body Economic: Life, Death, and Sens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Victorian Novel,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④ Patricia Clough,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⑤ 将美学与情感研究相结合的重要著作参见Sianne Ngai的Our Aesthetic Categorie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
⑥ 参见Eric Kandel,Age of Insight: the Quest to Understand the Unconscious in Art, Mind, and Brain from Vienna 19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Deidre Lynch, Loving Literature: A Cultural Histor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等著作。
⑦ Samuel Richardson, 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edited by Angus Ross, London, NY:Penguin Books, 1985. 出自本书的引文均为笔者所译。
⑧ Daniel Defoe, “An Essay upon Projects, London”,Printed by R. R. for Tho. Cockerill, 1697. 笛福在这个小册子里提出了建立女性学院的建议,目的是为她们踏入婚姻做准备。
⑨ 理查逊在出版前后与许多女性朋友通信,求取她们对这本小说的意见,他不断对女性对男性惊人的原谅能力震惊,以致于他在第三和第四版的后记中专门为自己不安排完满结局做出辩护。相反的,他不断向反方向修改自己的小说,突出勒夫莱斯的不可救药。在第三版里把在第一版中删除的细节加了回去,比如Isle of Wight阴谋,还增加了其它令人匪夷所思的坏事。
⑩ 卢梭,《新爱洛伊丝》,伊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自这本书的引文是笔者在译文基础上修改过的版本。
⑪ 参见威廉斯Raymond Willliams, 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