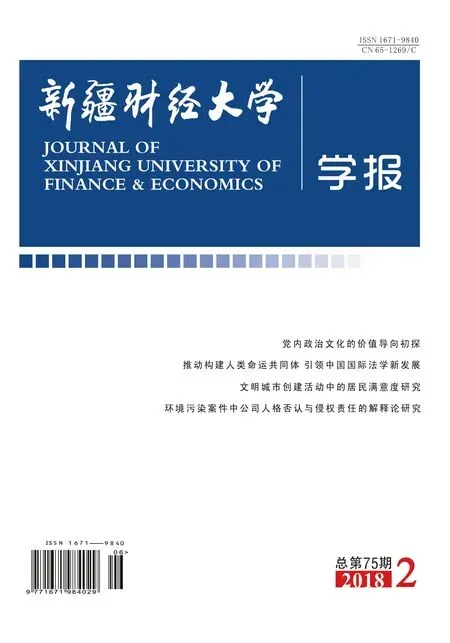大众创业创新、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研究回顾与述评
达潭枫
(新疆财经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830012)
毫无疑问,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对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也是各国(地区)政府的首要职能。经济增长不仅可以有效吸纳就业,满足日益增长的就业需求,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而且也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支撑。19世纪初,英国著名人口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曾预言,由于食物生产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世界人口将会遭受饥荒,或至少生活在最低生存水平上。但之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世界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停滞,反而取得了长足进步,产品和服务极大丰富,绝大多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较200多年前有了质的提升。那么,是什么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曾在同一起点的国家,有的创造了发展的奇迹,有的却掉进了贫困的陷阱?特别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一些西方国家,为什么过去百年来其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较之发展中国家(地区)取得了更好的表现?为了弄清上述问题,破解经济增长之谜,大量学者、专家进行了长期艰苦不懈的探索,并逐渐形成基本共识,那就是,草根阶层或大众干事创业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是经济富有活力的源泉和基础,而由大众创业创新和充分竞争所培育和释放的企业家精神,则是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组织创新并使一个国家(地区)不断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这些观点、结论及其蕴含的政策含义,无疑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应对经济新常态下的挑战,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创新、竞争与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现象作出合理解释并找到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持续的艰难探索。在早期,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通常体现为机器设备和厂房等物质资本的增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条件,甚至是唯一来源,对这一观点的理论概括包括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阿瑟·刘易斯的“过剩劳动力”模型等。然而,上述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我们并不清楚是谁在决定资本积累的数额和种类,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制于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为维持一定的增长率,投资率必须不断提高。这显然很难实现,也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事实不符*详见吴敬琏为《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一书所作的序,原载于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著,刘卫、张春霖译的《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Solow[1]采用1909年—1949间美国的经济数据,对劳动和资本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进行了估算。研究结果表明,投入(劳动和资本)的增加只能解释产出变化的12.5%,他将其余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技术进步。不过,Solow并没有对技术进步给出内生的解释,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外生的因素[2]。此后,很多学者都证实了这一基本认识,其他经济学家也相继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Solow开创性的研究引发了很多学者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特别是对引发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到底是外生因素还是内生于经济活动这一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积极进展。Kenneth等学者研究发现,支撑技术进步的那些想法和主意是新设备投资的意料之外的副产品,具有溢出效应,可惠及经济的其他领域*详见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著,刘卫、张春霖译的《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页。。因此,更多的投资将带来更多的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前者。这种投资带来溢出效应的一个政策含义是,政府能够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一观点与索洛—斯旺模型中的投资悲观主义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后,以Romer和Lucas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开拓者对技术进步机理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创建了一套正式的内生创新理论[4-6]。他们认为,技术进步是个人和企业有意识地投入时间和金钱的结果。换言之,技术进步本身是内生于经济活动之中的*详见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著,刘卫、张春霖译的《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页。。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创新与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持续不断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才使得经济得以保持持续较快速度的增长[1,2,7-11]。Solow[2]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研究中发现,创新或“精明的增长”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长期产出增加中起到了比“蛮力”(更多的投入)更为重要的作用。Kuznets[9]指出,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以及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改善的过程,它构成了商业开发和财富创造的环境。威廉·鲍莫尔[12]认为,尽管很多其他经济类型中也有惊人的大量发明,然而它们都没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出创新机制,更不用说将这种机制固定下来成为一种常规,而正是这种机制下产生的创新成为了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一种特征。Charles的计算表明,美国在1950年—1993年间的经济增长,80%的贡献来自其以前发明的科学创意的应用*详见蔡昉著《从国际经验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原载于《比较》第78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20页。。埃德蒙·费尔普斯[13]也强调,一个国家的繁荣取决于其民众特别是草根阶层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
既然创新对一个国家(地区)繁荣或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那是什么机制促成了资本主义创新源源不断地产生呢?从已有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学者对竞争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哈耶克[14]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指出,“只要能创造出有效的竞争,就是再好不过的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他认为,“竞争之所以被视为是优越的,不仅是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人们所知的最有效的办法,更因为它是使我们的活动在没有当局的强制和武断的干预时能相互协调的唯一方法……而且,它给予每个人一个机会,去决定某种职业是否足以补偿与其相关的不利和风险”。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的熊彼特也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真正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书中所说的那种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的竞争,这种竞争要求竞争者必须掌握决定性的成本和质量优势,与此同时,这种竞争冲击的并不是现存企业的盈利空间和产出能力,而是它们的基础和生命。这种竞争比所有其他方式都要有效”*详见威廉·鲍莫尔著,郭梅军等人译的《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页。。菲利普·阿吉翁[15]进一步分析认为,熊彼特增长理论让我们理解了创新导向的增长与较高的企业和工作转换率相关,此外也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竞争与增长正相关。二战后德国社会市场体制的缔造者Ludwig Erhard将德国战后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归结为“来自竞争的繁荣”。他强调,市场经济的要旨在于自由竞争和自由定价。自由竞争是实现基本经济目标的最好手段,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主要支柱。只有通过自由竞争和自由定价,才能保证经济体系协调顺利运转*详见熊华乔著《充分竞争与永续繁荣——从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所想到的》,原载于《新理财(政府理财)》2013年第6期,第90页。。威廉·鲍莫尔[12]则对竞争压力如何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史无前例增长的机理进行了解释。他认为,这种压力在其他类型的经济中是不存在的,它迫使经济相关部门中的企业坚持不懈地投资于创新活动;与此同时,这种压力为在整个经济中不断地传播和交换新技术提供了激励。路易吉·津加莱斯[16]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真正的天才之处不是私有财产,也不是利润动力,而是竞争。没有竞争的私人财产会导致垄断泛滥,而私有财产即使不够安全,通过竞争也仍可实现福利最大化的奇迹。
国内学者吴敬琏、林毅夫和蔡昉等也充分肯定了竞争在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吴敬琏[17]在谈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时曾指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竞争是市场制度的“灵魂”,没有公平竞争就不可能发现价格,也难以实现优胜劣汰和促使企业努力创新的目的。林毅夫[18]也强调,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竞争性市场都是经济中资源分配的根本机制。他认为,有效市场的重要性在于,只有充分竞争的市场才能形成充分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而只有这样的价格体系和市场竞争压力才能引导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生产出的产品才会成本最低、最有竞争力,从而创造最多的剩余和资本积累。蔡昉[19]认为,在产业结构剧烈调整时期,要把握新的比较优势和提高生产率,常常需要千千万万中小型民营企业的风险投资,而那些未来的产业和技术领先者,往往是在一种“创造性破坏”的竞争中胜出。
二、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
“企业家精神”一词最初是由富兰克·奈特提出的,是指企业家的才华和能力。熊彼特于1934年提出“创造性破坏”的概念,较早地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创造性破坏”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核,由“创造性破坏”来调整产业结构,并通过知识外溢、竞争溢出和多样性三种效应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详见刘现伟著《培育企业家精神 激发创新创业活力》,http://www.china-reform.org/?content_677.html。。对于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萨伊早在19世纪初就已指出,“没有企业家,(科学的)知识可能一直都在一两个人的记忆中或书本里长眠”*详见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著,刘卫、张春霖译的《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页。。彼得·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具体手段”*详见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著,刘卫、张春霖译的《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页。。他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甚至直接将创新视为企业家精神。198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rygve Haavelmo也强调,“经济生活中的重大差异”,或者特别要解释资本主义经济非同一般的表现,我们就不能轻视企业家这一角色*详见威廉·鲍莫尔著、郭梅军等人译的《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56页。。Millan 和 Woodruff认为转型经济能否取得成功,与企业家的表现密切相关*详见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著,刘卫、张春霖译的《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页。。威廉·鲍莫尔等[3]将企业家分为复制型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家,并认为大多数成功的经济是那些创新型企业家与较大型的成熟企业相结合的经济。
Moore和Davis进一步解释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并指出如果没有企业家,那些改变世界的技术以及企业家型资本主义都不会存在,是企业家们看到了一种出售某种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商品或服务的机会,然后采取了行动。他们指出,前沿性的突破更多是由个人或新企业研发并提供到市场上的,虽然这些突破背后的理念是在大企业(或大学)里孕育的*详见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著,刘卫、张春霖译的《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页。。玛格丽特[20]对1920年—2000年间美国企业家精神的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20世纪美国经济之所以“卓尔不群”,就在于大型一体化公司中的企业家对技术的充分利用;并强调美国体制中推陈出新的推动力建立在企业家和企业之间的互补关系上,前者富于创新精神,后者积极进取。
Rothschild从提高生产效率视角对企业家精神给予了肯定。他指出,比起那些在政治上争权夺利的政客,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家更值得赞扬。因为政治上的权力斗争都是零和博弈,而企业家们的活动却能提高生产率*详见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著《国家的经济繁荣:繁荣依赖于活力,活力取决于制度》,原载于《比较》第41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Kirzner揭示了企业家在市场发现方面的作用,认为寻找盈利机会、促进市场均衡等是企业家的重要本性。前者推进生产前沿,后者促使生产向前沿移动*详见胡永刚和石崇著《扭曲、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原载于《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第87~88页。。
企业家精神在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和技术进步中的作用也被大量经验研究所证实。大量实证分析显示,处于工业化和产业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或地区,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21],且拥有较多企业家的经济会有更高的增长率[22],这表明企业家组织的微观经济活动和创新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有学者的定量分析显示,地区间和城市间经济增长的差异确与是否充分发挥了企业家精神密切相关[22]。
三、大众创业创新、经济活力与经济增长
早在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在其影响深远的巨著《国富论》中就对大众创业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行了精辟总结。他指出,“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详见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丝·弗里德曼著《自由选择》,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艾哈德在总结战后十余年西德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曾指出,“如果德国这个例子对其他国家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在社会市场经济原则下,有机会来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并认为,创业精神和个人的主动性,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所系*详见熊华乔著《充分竞争与永续繁荣——从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所想到的》,原载于《新理财(政府理财)》2013年第6期,第90页。。米尔顿·弗里德曼等[23]在谈及美国农业发展的奇迹时认为,农业生产创新的主要源泉,仍然是自由市场机制下的私人主观能动性,自由市场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并进一步指出,一个主要以自愿交换为特征的经济体,内在地具有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质。威廉·鲍莫尔等[3]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自由市场和机会最大化的经济的优点在于,它发挥了很多人的才能。这样的经济能容纳持续不断的头脑风暴和实验,而这会带来回报,因为拥有多种技能和不同知识的广大人民群众比任何一组计划者或专家都更可能提出和实施好的主意。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一书中总结到,国家的繁荣取决于其经济是否有活力,而态度和信仰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主要指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它们促成了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同时认为本土创新源自人们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它们一直深入到社会的草根阶层,并且有相应的制度使这种愿望得以实现,使人们能以这些冒险活动为生[13]。Landes也强调,那些拥有乐于创业的文化的国家经济增长很快,而那些没有这类文化的国家经济增长就慢得多,或者根本不增长*详见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著,刘卫、张春霖译的《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55~78页。。菲利普·阿吉翁[15]认为,熊彼特增长理论揭示了经济增长和企业活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一个国家越来越成为技术前沿者时,开放、竞争与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就与日俱增。
四、构建企业家型经济及大众创业创新激励机制
威廉·鲍莫尔等[3]将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分为四类,即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及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并认为在上述四类经济形式中,企业家型资本主义是最具活力的经济。原因是在这种经济类型中,经济的大量参与者不仅有无穷的动力进行创新,而且会主动从事前沿性或突破性的创新并使之商业化。这些发明比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特有的增量性创新要大胆得多。还有一些学者则强调通过新知识的扩散或“干中学”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如Lucas就认为,一个欠发达国家要想转变为一个现代的经济体,必须经历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的过程。社会及其公民必须对“发展创造的各种新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详见林毅夫著、张建华译的《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德隆·阿西莫格鲁等[24]主张,一个国家(地区)要想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建立包容性制度很关键。包容性制度要求的不仅仅是市场,而且是能够为大多数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和机会的包容性市场。该制度强调实施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鼓励在新技术和新技能领域投资。与该主张相类似,布拉德福德·德龙[25]、埃德蒙·费尔普斯[13]及威廉·鲍莫尔[12]等学者认为经济自由在促进大众创业创新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指出,自由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增长自其诞生起就是激励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源泉,市场经济鼓励人们探索如何让那些昂贵的产品变得更加便宜,如何让经济活力更有效率,并自然地把创新活动引向最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地方。威廉·鲍莫尔[12]进一步强调,财产和契约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保证这两点得以实施的机制,是资本主义产生和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他建议改进和完善专利保护制度,使专利保护既能有效地保障技术发明者的权益,又能有助于企业间技术的转让和自愿传播。大量经验研究显示,完善的法治确能有效激发企业家精神向生产性活动的配置[21]。
乔尔·莫克等人[26]在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企业家精神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不仅正式制度(包括法律规则、知识产权及对工业家有利的政府立法等)正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支持“技术上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一些非正式制度也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如公认的行为准则、信念模式、信任关系和类似的社会模式等;并由此认为,将创造力导向生产性活动是创业成功的关键。菲利普·阿吉翁[15]则强调了政府在保障企业创新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他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的第一个重要角色就是扮演知识经济的共同投资者,使企业能够将创新的外部性内部化。考虑到创造性破坏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的暂时性不利影响,他还建议由政府扮演保险人的角色,帮助工人从一个工作调换到另一个工作。一些学者还探讨了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如何保护企业家精神。他们提出,在国力薄弱、国家职能缺失或玩忽职守的地方尝试建立私人保护技术,或将有助于支持生产技术投资;同时认为,要为生产层面的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营造出所需的环境氛围,开发财产安全私人保障技术保护层面的企业家精神不可或缺[27]。
五、简评
从对以上国内外学者研究现状的回顾、梳理及代表性观点述评来看,我们对经济增长现象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大众创业创新是经济保持活力的源泉和基础,而由大众创业创新和充分竞争所催生和激发的企业家精神,则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并取得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对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并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释放了农业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吃饭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便是明证。改革开放后,大量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涌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近年来,我国在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无可辩驳地表明了大众创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文献研究中学者们就促进创新创业发展及企业家经济的形成,提出了一些带有共性的激励机制和做法。如为大多数人和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有利环境和包容性制度;改进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发明家和企业家进行创新并传播其创新;加强对财产和合同权利的法律保护等。对于正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创业发展的我国来说,这些做法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加之国内外现实情况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巨大差异性,人们对经济增长现象的认识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观性和片面性,需要不断深化认识。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国外做法,而必须结合我国的自身实际和现实特点,制定并执行切实可行的政策、制度与措施,同时加强政策制度和激励机制建设的前瞻性和针对性,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使经济增长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1]Robert M.Solow.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y of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1):65-94.
[2]Robert.M.Solow.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312-320.
[3]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M].刘卫,张春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4]Paul M.Romer.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5):1002-1037.
[5]Paul M.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5):71-102.
[6]Robert E.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1):3-42.
[7]Denison,Edward F.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ternatives before US[Z].New York: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1962.
[8]Denison,Edward F.Why Growth Rates Differ:Postuarexperience in Nine Western Countries[Z].Washington: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67.
[9]Simon Kuznets.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Structure and Spread[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10]Douglass C.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1981.
[11]William Easterly, Ross Levine.It's Not Fator Accumulation:Stylized Facts and Growth Models[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1(2):225-227.
[12]威廉·鲍莫尔.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M].郭梅军,唐宇,彭敬,李青,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13]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M].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14]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5]菲利普·阿吉翁.政府与经济增长[A].吴敬琏.比较:第67辑[C].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16]路易吉·津加莱斯.繁荣的真谛[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7]吴敬琏.什么是结构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A].吴敬琏.比较:第85辑[C].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18]林毅夫.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推动转型升级[N].人民日报,2015-05-07.
[19]蔡昉.中国未来20年的可持续增长引擎: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与教训[A].吴敬琏.比较:第67辑[C].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20]玛格丽特·格雷厄姆.美国的企业家精神:1920—2000年[A].戴维·兰德斯,乔尔·莫克,威廉·鲍莫尔.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C].姜井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21]胡永刚,石崇.扭曲、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6(7):87-88.
[22]李宏彬,李杏,姚先国,张海峰,张俊森.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10):99-108.
[23]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自由选择[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24]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M].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25]布拉德福德·德龙.美国经济增长的前景[A].吴敬琏.比较:第70辑[C].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6]戴维·兰德斯,乔尔·莫克,威廉·鲍莫尔.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M].姜井勇,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27]彼得·里森,彼得·波特克.双层面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发展[A].吴敬琏.比较:第55辑[C].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