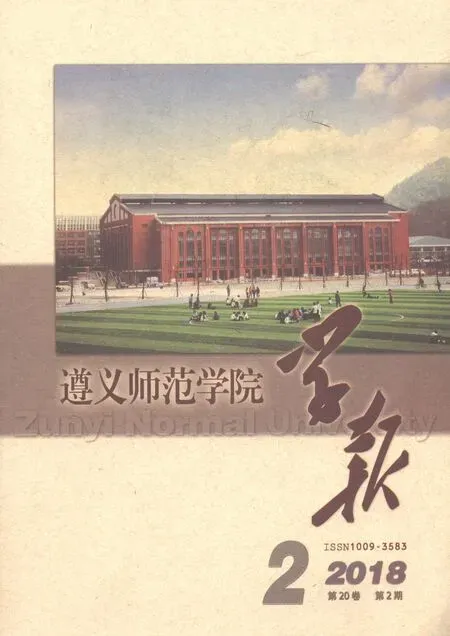以儒为本的苏轼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丁佐湘,蒋燕娜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根据近代西方科学主义的定义而言,成为一门学科必须形成知识论体系,否则不能称之为“学”,但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某种思想的有无并不确切。以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为例,并未形成完备的具有逻辑性和体系性的学科,但中国古代的经济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它产生于先秦时期,代表观点有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见利思义”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汉魏晋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盐铁会议上思想家们以“轻重之辨”为核心,展开激烈争辩,至隋唐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又复苏;宋明时期,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得到了完善,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儒家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引发了“利”和“义”的思考。由上可知,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始终与伦理道德密不可分,可以说伦理化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典型特征。苏轼正出生于商品经济发展,经济伦理思想得到完善的北宋,因此将其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融入到文学作品中。研读相关文学作品即能了解到苏轼个人的经济伦理思想和当时社会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苏轼的经济伦理思想
苏轼一生为任多地地方官,所经历之地理人文各有异同,但无论为官何处皆颇受当地百姓爱戴和敬仰,因其所倡导之主张和执行之策略无一不以仁政爱民为核心,切实考虑百姓疾苦,从而决定应对之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血管里流淌着儒家思想的血。经时济世、学以致用是他们的人生理想和社会责任。”[1]放之于苏轼身上,亦完全适用。因出生于商品经济发展时期,苏轼经济思想丰富而独到,又融入了伦理因素,形成了强调“民富”、“节用”和“渐变”的经济伦理主张。
1.“民富”为基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官吏的主张和策略最终目的是实现国富民强,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但官吏们对于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却各持己见,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强调的是富国方能富民,而苏轼则认为富民乃是富国之基,唯有先使民富,方能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创收。
民富之观点源自于苏轼的民本思想。孔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在君与民的关系中,苏轼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亦是强调民之本位。“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2]P289他认为当以民为本,安民方能实现安国。而安民最为首要的是富民,百姓富足,生活安定,社会秩序才会稳定,如此良性循环,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生产发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他说“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生死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也。甚矣,斯言之可畏也,以是亡国者多矣!夫理财者,疏理其出入之道,使不壅尔,非取之也。”[3]威胁到百姓经济利益的人就有可能危害到百姓的生命,“人之所以为盗者,衣食不足耳。农夫市人,焉保其不为盗,而衣食既足,盗岂有不能返农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盗者,开其衣食之门,使复其业。善除小人者,诱以富贵之道,使隳其党。”[2]P129(《续欧阳子朋党论》)倘若衣食足,没有百姓愿意为盗贼,行宵小之事。清朝范文程也建议废除不必要的税收,并“以国家政令的形式从根本上结束了长期以来强加在老百姓身上的沉重赋税负担,使清王朝从利益层面赢得了故明遗民的认同。其实,这是范文程对中国传统富民思想的具体运用。”[4]可见富民可安民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是得到认可的。
此处苏轼所言“富民”不分等级一视同仁,富有之民和贫穷之民都属于“民”的范畴。中国古代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农业为本,商业为末,而苏轼认为“农末皆利”,富人多为商人,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致富应该予以肯定和保护,“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己先成之矣。”[2]P118在当时“重农抑商”政策和思想居于主流地位的时候,苏轼能够独抒己见,可见其更为开放的经济思想和对百姓的博爱。
苏轼所言富民还包含有“藏富于民”之意,反对国家“与商贾争利”。在他看来“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民富则国富,民穷则国富不久矣。所以国家不可“与商贾争利”,当鼓励其发展。
足见苏轼的经济思想始终是以他“以民为本”的伦理思想为核心,形成“富民”的经济伦理思想。
2.“节用”为要
苏轼反对国家“与商贾争利”,坚持“藏富于民”,那么当国家处于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只有“节用”。“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人之为易也。”[2]P267他认为国家应当“节用”,国家广增税赋以充盈国库,不如一改北宋奢侈之风,改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集中解决官俸、宗室和军费问题。苏轼指出:“今者骄兵冗官之费,宗室贵戚之奉,边鄙将吏之给,盖十倍于往日矣。”[2]P214如此巨额的费用实不合理,严重增加了国家财政的负担。这一点与王安石的主张截然不同,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紧张是因为理财不善,没有采取正确的理财措施,国家是很富有的,不必依靠节用来省下费用,只要理财措施合理,不增加税收也可以使国家财政富足。而苏轼秉承了司马光的主张,“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不通过增加税收来充盈国库必定是以其他更为隐蔽的手段剥夺了百姓的利益,这种隐蔽的谋利手段比之增加税收危害更甚,国库在短时间内的确会得到充盈,可百姓的利益一旦被过度损害,必然导致整个国家财政拮据。因此,归根结底,在政府利益与百姓利益发生冲突时,首先要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以百姓的利益为先,必要时可以令国家节用而先富民,以达到通过民富实现国富的目的。事实上,从经济角度出发,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源自于商品和货币的流通,商品和货币流通的速度越快,创造的价值就越高,流经每个百姓的财富就会增加,以此促进经济的发展,百姓就会更加富足,整个国家的税收不须提高也能大幅度地增长,从而实现国富。这其中依然是受“民本”思想的指引,所以苏轼“节用”的经济思想仍旧具有极为显著的伦理化色彩。
3.“渐变”顺时
苏轼入仕途时正逢王安石极力主张变法,大刀阔斧,异常激进,改革政策纷出,苏轼等人虽知变法之紧要,但并不赞成王安石变法的节奏和主张。苏轼认为欲速则不达,须得“渐变”,且要掌握合适的时机。“渐变”的原因在于变革社会是牵涉到整个国家、各个阶层利益的大事件,一着不慎易引发社会动乱,危及封建统治。放慢变法的速度一则留有充足的决策时间,二则有利于即时发现和解决变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变法想要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合适的时机就隐含了政策实施的时间恰当,主持变法的人正确引导以及所实施的地点合适三个要素。《上神宗皇帝书》言:“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2]P738就是说,要讲究循序渐进,追求速度,急功近利,那么即便是正确的策略,所得结果也会不如人意,甚至导致失败。苏轼“渐变”的主张源于儒家“中庸”思想。《礼记·中庸》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5]要把握事物发展的“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就能使天地万物往好的方面发展,反之,超过了这个“度”,就违反了事物发展的本来规律,不利于事物的发展。对于变法一事便是如此,无论从变法推行者还是变法政策适用者而言,速度快就要求推行者和适用者在极短的时间内适应政策,但实际情况是,一个新生陌生事物的发展存在磨合期,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适应政策之人少之又少,在经济发展方面更是如此,经济的发展本身就需要时间,并非通过管理方法就能促进经济大发展大繁荣的,追根究底是需要掌握正确的时机,顺应规律,农业、商业共同发展才能推动。苏轼深谙经济发展规律,又受“中庸”思想的影响,故而形成“渐变”的经济伦理思想。
综上所述,苏轼的每一种主张都有内在的儒家伦理思想作为核心和指导,自然凝聚成上述三种经济伦理思想。
二、苏轼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原因
在北宋,苏轼以儒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应当属于比较开明的,如“农末皆利”之观点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重农抑商”之大环境下极其难能可贵。其开明的经济伦理思想形成原因有三:
1.“三冗”之弊
苏轼经济伦理思想产生是有其社会背景的。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看似歌舞升平,繁荣安定,但敏锐的文人们已经察觉到了社会积弊,亟需改变现状,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忠君爱国的责任感促使他们思考社会积弊的解决之法。一国之强弱首看经济,北宋已是积贫积弱,边境之患加剧了财政危机,所以王安石变法首要是经济理财。实际上,在经过了百年无事的休养生息之后,北宋中叶几乎读过书就可以当官,官吏人数骇人,却都躲懒偷闲,身处其位,不谋其政,只知安逸享乐。国家所养之军队士兵,懒散软弱,人数广而精英稀少。百姓在国内贪官污吏剥削,国外边境敌国压榨的双重逼迫下,赋税加重,尽其所有尚不能满足国用。加之各地起义此起彼伏,已让苏轼意识到想要维护统治必须要先安抚百姓,百姓安定的前提在于生活富足,因此苏轼的经济伦理思想强调“民富”。另一方面“三冗”问题摆在眼前,最为直接和针对性的措施就是上层统治阶级的“节用”,将不必要的开支节省下来。此外,王安石大刀阔斧地骤变,外任地方官的苏轼在各地看到了百姓受压迫更甚,更坚定了他“渐变”的主张。
2.儒学启蒙
苏轼的经济伦理思想中所体现的“民本”、“中庸”思想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深深融入了每一位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之中。苏轼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苏洵善作古文,对苏轼兄弟的教育十分重视,常一同谈论古今朝政之得失,《题东坡制策稿》中说苏洵“大究六经百家之说,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此先生所自得者,文忠兄弟,学亦有所本欤”。[6]苏轼的母亲程氏出身名门,是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其父在外游历之时,兄弟二人的教育就由其母程氏负责。程氏为苏轼读东汉范滂传,苏轼问其母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其母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范滂有“澄清天下之志”,以天下为己任,苏轼受此鼓舞,又得母亲支持,从小就胸怀大志,以范滂为榜样,以为天下苍生谋福利为己任。苏父苏母皆教之以儒家处事之道,“民本”、“中庸”思想早已深入骨髓,在这样严格的教育下,苏轼将满腹经纶运用于时事,以传统儒家思想为理论指导,融入到他政治生涯的方方面面,经济变法思想也不例外。经济思想只是一种途径,而伦理思想却是苏轼作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他的目的就是实现儒家的济世爱民,因此可以说苏轼的家庭教育尤其儒家思想教育是其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
3.为官经历
苏轼为官直言时弊,一切只以如何解决民间百姓疾苦为标准,这样的性格自然在朝堂之上格格不入,宋朝又有不杀文人之例,是故造成了苏轼漂泊的一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为官,从杭州通判到密州太守、徐州太守、湖州知州,紧接着贬黄州,后又知登州,第二次请求外调时又历经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直至最后一贬英州,再贬惠州,又贬儋州。但苏轼每至一处皆有政声,为百姓谋福祉,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足见苏轼每到一处都深入到百姓中间,亲眼目睹百姓之疾苦,从基层实践中发现问题根源所在,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所谓“实践出真知”。丰富的地方官经历对他的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当目睹过朝臣官员的奢侈享乐,再对比各地百姓之不堪重压,又因地方官之职务,自然地站在百姓的角度考虑变法之策,所以王安石主张先富国,而苏轼主张先富民,民不聊生则社稷不稳。也因他出任地方官,所以他了解百姓之财几被取尽而国用仍不能足,问题在于国家机构的冗员冗费太多,而从事生产,创造财富的人却少,如此唯有精简国家机构,令上节用,则下可安心从事生产。
三、苏轼经济伦理思想的评价及启示
苏轼以儒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作为他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从思想上而言,苏轼“民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大胆反传统的。当时诸多官员反对“民富”的原因在于追求个人利益会导致大义的缺失,没有道德大义作为限制,百姓就难以约束,造成社会动荡,这就是“义利之辨”。而苏轼在此问题上的考量是,安民当先富民,佐以教育,教育才是安民利器。“其心安于为善,而忸怩于不义,是故有所不为。夫民知其有不为,则天下不可以敌,甲兵不可以威,利禄不可以诱,可杀可辱,可饥可寒而不可与叛。”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其所以教民之具,甚祥且密也。学校之制……莫不有法”。[2]P253以教育来教化百姓是典型的儒家思想,仁政、博爱、富民,既是对儒家经典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超前于其他文人士子的经济伦理观,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基本是一致的。“节用”之思想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所提倡的,“渐变”之思路与当今社会改革相比较,也可以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今倡导的“又好又快”,将“好”置于“快”之前,就是强调了社会发展首要的是“质”,放之于宋代就是要稳步发展。这一儒家中庸的经济发展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从实践上看,为实现“民富”,苏轼反对国家“与商贾争利”,反对官府专卖。苏轼知登州时上《乞罢登州榷盐状》,希望取消官府榷盐。因为官府专卖会导致原本以卖盐为生的商贾无以为生,成为流动人口,不利于社会稳定,且官府专卖本身就违背了价值规律,盐就不能够自由流通,其价格也不会因供需关系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如此,储盐富足地区的百姓无法利用地域优势获得利润,供盐不足地区的盐价则因物以稀为贵而居高不下,以致百姓无力负担,那么官府的盐也就无法卖出。苏轼看透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流通,流通才能降低商户成本和购买者的消费成本,可以满足民需,刺激国民消费,消费增长又能鼓励商贾流通,如此良性循环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显然苏轼的经济伦理思想存在不足,以儒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仍然脱离不出封建地主阶级的限制,他的以民为本,仁政爱民最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较之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真正为百姓谋福利,国家是每一个国民的国家,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在这一点上,苏轼的经济伦理思想是落后的糟粕。
纵观利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值得借鉴的一点在于富民的同时通过教育来引导和约束国民的思想。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追求财富成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在此情况之下最容易造成的是“义”,即道德的缺失,道德缺失是社会动乱的极大隐患,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教育净化和约束国民思想,以保证国家健康、快速、稳定地发展,保证国民生活富足安定。
参考文献:
[1]任在喻.同写宦游感意象各有别——苏轼、柳永的《满江红》词对读[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3,(4):33-34.
[2]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苏轼.东坡易传[M].龙吟点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314.
[4]魏登云.满清第一功臣范文程民本思想探析[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7,(4):5-8.
[5]王国轩,张燕婴,蓝旭,万丽华译.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118.
[6](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淸点校.滋溪文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