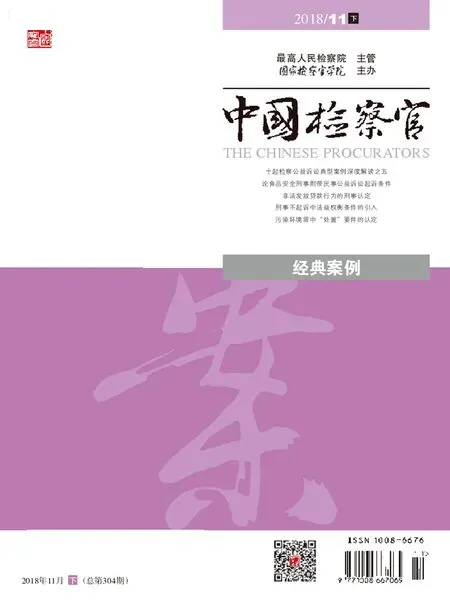刑事不起诉中法益权衡条件的引入
——以“药神”案为例
文◎周寅行 费 聪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不起诉的范围和条件规定的非常具体明确,带来的便宜之处在于适用的标准清晰,不易引起争议。但缺陷也非常明显,对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保护更大法益、节约诉讼成本甚至为了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等其他考虑而不适宜起诉的案件,在程序上并无出路可走。笔者以“药神”案的法律价值冲突为例展开。
一、“药神”案的价值冲突及解决方式
(一)案情回顾
根据公开披露的报道,犯罪嫌疑人陆勇在34岁那年得知自己患有慢粒白血病,在医生的建议下,他服用瑞士生产的格列卫抗癌药物,一盒120粒,售价23500元,每天4粒,也就是每天800元。他服用了两年,花费56.4万余元,几乎掏空了自己的家底。36岁年那年,他偶然发现了一款印度仿制药,价格只有正版药的1/20,疗效却几乎一样。他将这个消息传遍病友圈,并帮助在印度代购。这期间,为了方便购药,他在网上购买了3张他人姓名的信用卡,3个月时间交易资金已经达到300万。2015年,公安机关以涉嫌销售假药罪、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将陆勇抓获。其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看守所狱警甚至在他的指导下,帮他网购了3瓶印度仿制药。300多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
(二)本案价值冲突
案件在社会引起了较大争议,随着电影《我不是“药神”》的热映,争议更被得到广泛地讨论。陆勇的行为的确违法了,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第48条和《刑法》第141条的规定,仿制药格列卫未经我国药监部门批准而进口,不仅不能在我国流通,而且以假药论处;明知是假药而予以销售的,构成销售假药罪,应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同时,陆勇的行为还违反了我国《知识产权法》。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原研药瑞士格列卫,在印度属于得到知识产权强制许可,可以予以仿制。然而在中国,它被授予了专利,未被许可他人使用。在专利权期限届满之前,陆勇的行为就涉及到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另外,陆勇还可能违反我国《海关法》等等。
涉及多项违法行为的陆勇,之所以还能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同情,根源在于其行为侵害的法益与公民健康权甚至生命权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新药尤其是罕见病药品的研制过程难度高、风险大,往往需要耗费巨资,投入极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以瑞士格列卫为例,其研发经历了40年的漫长周期,花费了约50亿元的高昂成本。因此,在一定时间内赋予研发企业合法的垄断地位,保障其收回成本、获取利润,不仅可以增加研发新药的动力,也可以为药品专利技术的后续研发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基础,促进医药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然而,作为一种具有锁定效应的特殊商品,药品是公民实现其基本人权——健康权、生命权的必要组成部分。当药品因其价格、充足度等原因而不具有可及性时,[1]我们又怎能要求公民放弃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而去遵守法律呢?这似乎可以以缺乏“期待可能性”作为一个刑事抗辩的理由。但该理论同样未被引入我国《刑法》。
(三)解决方式
“药神”案曾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检察机关又撤回起诉,并对陆勇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该案的最终处理经过了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的反复讨论,并听取了法律专家的意见,不可谓不慎重。从最终的决定来看,检察机关认为陆勇代购印度药品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帮助别人,不能视为销售,从而不构成销售假药罪。同时陆勇在网上购买借记卡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事其他违法活动,而是用于为其他病友支付购买药品款项提供一个账户,且只使用了一张,情节显著轻微,虽然违反了我国金融管理秩序,但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也不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2]
二、法律价值的冲突及其权衡
虽然案件最终得以妥善解决,但是该案暴露出的制度漏洞是显而易见的。在“药神”案件中,陆勇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完全符合《刑法》关于销售假药罪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构罪标准的,这也正是检察机关将本案提起公诉的原因。然而,因为激烈价值冲突的存在,检察机关在案件起诉后又重新对该案的处理予以斟酌考虑,并最终作出了绝对不起诉的决定。虽然检察机关给出的不起诉理由看似是陆勇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这实为陆勇的犯罪行为在法律上找了一个可以合理处理的理由。
众所周知,《刑法》罪名并不以犯罪目的为要件,不论根据四要件学说还是三阶层学说,犯罪构成考虑主观但不考虑目的早已在学界和司法界达成共识。正基于此,劫富济贫、大义灭亲等目的正确的行为,才能够被评价为犯罪。而在“药神”一案中,检察机关为陆勇寻找的出罪理由却均来自其行为目的:因“目的并非为了盈利,而是为了帮助别人”,故不构成销售假药罪;因“网上购买借记卡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事其他违法活动,而是用于为其他病友支付购买药品款项提供一个账户”,故不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上述将犯罪目的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加以评价的方法,无需赘述,其不妥之处极甚。其似乎给了社会一个错误导向:为了合法合理目的的犯罪行为不构成犯罪。
本案检察机关之所以要以犯罪目的作为陆勇出罪的理由,实乃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条件的严格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绝对不起诉仅有法定的六类情形,对于不符合该六类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绝无对其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的权力。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不符合六类情形,情节也并不显著轻微,但不宜定罪处罚的情况却并不鲜见。香港“警廉冲突”时期,对于犯罪警察的不起诉是基于政治考量,美国检察官“辩诉交易”过程中,对于犯罪者不起诉是基于司法的成本和效率考虑。而我们现实遇到的更多案件,是存在类似于“药神”案这样的价值冲突。
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最草率的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3]利益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法律价值的多元性使得法律价值之间必定会发生冲突。如更偏向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与更强调国家权力的“秩序”之间的冲突,自由难免有打破既有秩序的倾向,秩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压抑自由以维持平衡。又如“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注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影响效率。再如“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冲突,美国辛普森案是该两种价值冲突在司法案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
法律价值的冲突可能发生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解决法律价值冲突,是人类一个普遍性的难题。面对法律价值冲突,司法者将面临法律价值选择。在进行价值选择时,法学界一般认为应当坚持以下原则:(1)价值排序原则。法律价值存在层级和位阶,不同位阶的法律价值发生冲突时,应当首选位阶高的价值。(2)比例原则。是指“为保护某种较为优越的法价值须侵及一种法益时,不得逾越经目的所必要的程度”。[4](3)个案平衡原则。综合考虑社会的特定情况、法律主体的具体需要和利益,兼顾各种要求,处理各种关系,进行慎重选择以取得个案平衡,进行全面性选择。进行法律价值选择时,需要确立选择的目标,考虑选择的手段,从而实现选择的结果。[5]
三、刑事不起诉中法益权衡条件的引入
在“药神”案中,检察机关以目的的合法性否定了犯罪嫌疑人行为的违法性,但在其他案件中,该方法却未必始终有效。试想,当一名小偷为了救治病重的父亲,而盗窃他人数额巨大的财产时,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再以目的的合理,来否定其行为的违法。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必须依据法律,尊奉公平、正义之原则,保证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具有正当性。而将法益权衡引入刑事不起诉的条件,能够为价值冲突案件在公诉环节寻找一条符合实体与程序的出路,避免“药神”案尴尬的重演。
笔者认为应当将法益权衡作为相对不起诉的条件之一加以引入。对于存在价值冲突而需要做非罪化处理的案件,其前提应当是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故而不可能作出存疑不起诉处理。其不应当仅限定于未成年人范围,故而不可能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目标行为本身必然已经违反我国《刑法》的规定,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否则亦不可能存在价值冲突。因而其并非不存在犯罪事实的不起诉,而是犯罪事实不需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起诉,更符合我国当前相对不起诉的概念与适用标准。同时,绝对不起诉适用的是“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绝对化标准,而相对不起诉适用的是“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相对化标准。对于需要进行法益权衡的案件而言,权衡即意味着可能存在或左或右的未知结果,进行绝对化的规定反而有悖于其设立初衷,也难以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综上,建议可以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修改为:“对于犯罪情节轻微,或者为保护国家、社会、公民其他更大合法权益而实施危害相对较轻犯罪,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由于法益权衡的复杂性和个人价值观的差异性,我们不能将价值判断和法益权衡的权力赋予单个司法人员,这极易引发价值判断的错误或错位。为此,应当设置一定的程序以保障该类案件的审慎处理。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设置不起诉的公开听证程序。法益权衡应当以“对话”的方式开展,而不能成为“黑箱”中的“内部操作”。价值冲突涉及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有权利在决定作出之前行使知情权和陈述权。社会公众也应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案件情况,参与案件背后价值冲突的讨论。通过如此公开的审查程序,检察机关可以了解案件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普遍价值观的倾向,有利于最终作出更符合普遍正义,可被接受的决定。
第二,建立不起诉说理制度。对于因法益权衡而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往往在实体上存在较大争议。即便整个程序公开、透明,司法者秉公执法而毫无偏见,也应当将其决定的理由通过详尽的阐释公之于众。这既是保障不起诉决定合法性的需要,也是化解当事人矛盾的需要,同时,更是对公众态度的必要回应和未来行为的指导。不起诉说理制度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一是增强不起诉决定书的说理部分内容;二是在不起诉决定宣告后对当事人开展当面说理工作;三是通过新闻发布会、释法说明会等形式向社会公众进行说理;四是通过典型案例的发布进行说理,并为今后类似案件提供参考指引。
第三,完善与社会福利、慈善机构的衔接。犯罪嫌疑人因价值冲突而不得不违法,在此背后,必然隐含着法律不能解决的问题。“药神”案中陆勇在被不起诉之后,仍然面临着“药向谁买?”的困境。法律不可能赋予陆勇从此在国内合法销售印度仿制药的权利,案件背后的问题势必仍然需要通过案件以外的途径加以解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社会福利机构、慈善机构等各方面的支持。对此,检察机关应当完善与这些机构的衔接、对接制度,在案件处理之后,确保冲突的价值得以修复,不再成为当事人永久无所适从的殇痛。
注释:
[1]参见殷莹:《发展中国家药品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的冲突及平衡》,载《中国药业》2015年2月20日。
[2]参见《独家专访,放走“药神”的检察官:“三年前,不起诉陆勇的决定是我做的!》,长安剑微信公众号,访问日期:2018年7月9日。
[3]参见[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沈宗灵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页。
[4][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5页。
[5]参见高其才:《法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