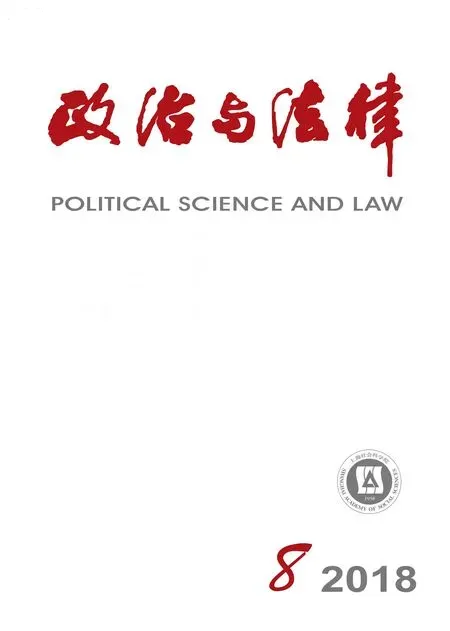侵权责任免责权:既有理论商榷基础上的概念构造尝试*
谢 潇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44)
就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而言,学界通常将其解释为侵权责任抗辩事由或者免责事由的规范群,指称“那些因其之存在而使侵权责任不成立的法律事实”。①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不过,将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受害人过错与第三人原因等事实仅仅在要件事实层面予以理解却存在一系列理论上的疑问:第一,所谓“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是否是侵权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第二,作为抗辩事由或者免责事由的“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究竟如何影响加害人过错、受害人损失等通常的构成要件;第三,仅从法律事实层面解释与适用“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是否妥当,有无其他更为合适的理论路径。笔者于本文中拟就以上问题作出探究与解答。
一、抗辩事由论的路径依赖与解释错位
(一)抗辩事由论的基本理论路径:继受法思维的本土化展现
持抗辩事由论的学者认为,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是被告在侵权诉讼中据以抗辩的实体法依据,其本质上是阻却法律效果发生的消极构成要件要素。②参见冯珏:《论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法律科学》2011年第4期。这与自罗马法以来的侵权法传统,以及德意志法和英美法不谋而合。
众所周知,抗辩(exceptio)是罗马时代的诉讼活动中,被告一方对抗原告一方所提出的诉(actio)的一种法律方法,其旨趣在于“能够使诉讼(Klage)归于无效,并最终产生该诉讼将被视为从未发生过之法律效果”。③Albrecht Schweppe, Das Römische Privatrecht in seiner heutigen Anwendung, Erster Band, 1828, S. 400.在罗马法时代,诉与抗辩都属于实体法与程序法杂糅的法律工具,两者均不同程度地带有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重属性。不过,在19世纪,德意志潘德克顿法学家温得沙伊德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二元区分的法理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罗马法意义上的诉应当做实体法与程序法二元区分意义上的再类型化,申言之,罗马法意义上的诉其实包含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与纯粹程序法意义上的诉权两种权利,当事人之所以能够提起诉讼,申请获得司法救济,乃是因为在司法程序展开前,其便享有一项基于市民法实体规定的应然权利,即请求权(Anspruch)。④Vgl. Bernhard Windscheid, Die Actio: Abwehr gegen Dr. Theodor Muther, 1857, S. 8.尽管温得沙伊德也承认对于罗马人而言,请求权寓于诉、诉讼与诉权的概念之中,⑤Vgl.Bernhard Windscheid,Lehrbuch des Pandektenrechts,Erster Band,1862,S.92ff.不过,罗马法中的诉的确是实体法上请求权的一种表现,故而这并不妨碍在当代法立场上将请求权作为一种实体性权利而自罗马法素材中提炼出来。⑥Vgl.Bernhard Windscheid,Die Actio des römischen Civilrechts,vom Standpunkte des heutigen Rechts,1856,S.5ff.作为防御性的法律工具,罗马法上的抗辩概念也经历了类似诉那样的类型化过程,其被区分为诉讼法意义上的抗辩(Einredeim Zivilprozessrecht)与实体法意义上的抗辩权(materiellrechtlichen Einrede),前者属于诉讼过程中被告就原告诉讼请求的反驳,后者则是一项得以对抗原告所享有的实体法上请求权的实体性权利。⑦Vgl.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Aufl.,2010,S.47.这种“请求权对抗辩权”式的实体法上攻击防御方法的分配技术,在侵权法领域,深刻影响了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理论。
就德意志法系中的侵权法而言,在构成要件领域,系以侵权行为为中心展开思考,具体而言,德意志式的侵权法预设了如下法权模式。
第一,侵权行为是法定债务关系的一种原因,倘若发生了侵权行为,则必然产生相应的法定债务关系,在该债务关系之中,侵权人负担相应的法定债务,并且,由于责任系属债务之内容(Haftungals Schuldinhalt),⑧Vgl. Josef Esser/Eike Schmidt, 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Teilband 1, Entstehung, Inhalt und Beendigung von Schuldverhältnissen, 5. Aulf.,1976, S. 58.倘若侵权人并未主动承担该法定债务,则被侵权人有权通过司法途径令侵权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侵权行为的构成,应当从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予以考量。以一般侵权行为为例,自积极层面而言,一项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必须满足行为人存在加害行为、行为人之行为具有违法性、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过失、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损害的发生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五项要件;自消极层面而言,一项一般侵权行为仅满足前述五项积极要件并不意味着必然成立,倘若侵权人得以主张自己系无侵权责任能力者,或者存在其他违法性阻却事由,则该侵权行为便无法成立。①平野裕之『民法総合6不法行為法』(信山社,2013年)19頁、210頁。
第三,作为消极构成要件的抗辩事由以阻却或者削弱侵权行为积极构成要件的方式发挥作用。例如,正当防卫(《德国民法典》第227条)、紧急避险(《德国民法典》第228条)、自助(《德国民法典》第229条)与紧急状态(《德国民法典》第904条)这四种抗辩事由,即藉由阻却或者削弱积极构成要件中的违法性要件(Rechtswidrigkeit)而使侵权行为不成立或者减轻侵权人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②Vgl. Hans Brox/Wolf - Dietrich Walker, Besonderes Schuldrecht, 38. Aufl., 2014, S. 535ff.此外,作为抗辩事由的因第三人作为或者不作为中断因果关系链条的情形,则凭借对积极要件中因果关系要件的否定与削弱,从而阻却侵权行为的成立或者削弱侵权责任。③Vgl. Erwin Deutsch/Hans - Jürgen Ahrens, Deliktsrecht: Unerlaubte Handlungen, Schadensersatz, Schmerzensgeld, 6. Aufl., 2014, S. 31 - 32.
总的来说,德意志式的侵权责任构成包含两个方面,即正面的积极构成要件与反面的消极构成要件(抗辩事由),前者决定侵权行为上请求权是否成立,后者决定侵权行为上抗辩权是否生成,而最终的侵权责任,取决于请求权与抗辩权之间的攻击防御之结果。申言之,在实体法范畴内,首先,考虑侵权责任请求权是否成立;其次,考虑该请求权是否存在与之相对抗的抗辩权(诉讼法意义上的抗辩不具有构成要件属性,而是单纯对积极构成要件的反驳);最后,若无抗辩权,则侵权责任请求权得以无阻碍地发生效力,成立侵权行为及其责任,若存在相应的抗辩权,则该请求权的主张将受到阻却或者削弱,从而最终导致侵权行为成立不能或者削弱与减轻侵权责任。
英美法系的侵权法,也与德意志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原告而言,即使其已经藉由证明而满足侵权的各要件,但若被告提出了一系列抗辩事由(defences),如受害人同意、公共政策、与有过失、无法避免的意外事件、不可抗力、私力救济、紧急避险、受胁迫、职务行为等,则原告仍然可能败诉。④SeeW.V.H.Rogers,Winfieldand Jolowiczon Tort,Tomson Reuters,Sweet&Maxwell,2010,p.1131.在英美法系侵权法中,抗辩事由本身具有消极要件地位,倘若被告能够提出抗辩并予以证明,则“侵权责任将无法必然产生或者无法完满地产生”(not necessarily arise or arise in full)。⑤JohnMurphy,Christian Witting,James Goudkamp,Streeton To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88.
因此,根据以上阐述可知,从罗马法到德意志法与英美法,将抗辩事由作为侵权行为或者侵权责任的消极构成要件已成惯例。职是之故,我国侵权法理论在继受与比较过程中也大体采纳了这种理论路径。例如,早期由王家福研究员所主编的,对我国民法学具有重大影响的《民法债权》一书,便在“一般侵权行为”中专节讨论了“抗辩事由”,并将抗辩事由定义为“被请求承担民事责任的当事人在承认加害事实存在的前提下,据以主张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者不完全成立的某种相反事实”,⑥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页。这一表述因强调抗辩事由对诉讼请求的防御性而带有浓厚的英美法风格。抗辩事由论的影响极为深远,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便采纳了“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的表述,但在法学理论层面,免责事由仍然常常被作为抗辩事由的同义词予以对待,并被视为侵权责任构成的一部分。例如,杨立新教授将免责事由置于“侵权责任构成”的框架之中,⑦杨立新:《侵权法论(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目录)。并认为所谓免责事由,“是指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提出的,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的事实。……又称免责或减轻责任的事由,也叫做抗辩事由”;⑧同上注,杨立新书,第347页。王利明教授也指出:“免责事由是指减轻或免除行为人责任的理由,也称为抗辩事由。”⑨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页。由此可见,抗辩事由论仍然在我国侵权法学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二)抗辩事由论的解释错位:与实定法安排之间的抵牾
自比较法的角度而为观察,抗辩事由论无疑具有一定合理性,其承继着罗马法传统,在逻辑上也颇具有自洽性,似乎并无可指摘之处。在欧洲私法统一化运动过程中,抗辩事由也是《欧洲侵权法原则》《欧洲民法典草案》等最新学术成果所青睐的术语。①参 见欧洲侵权法小组编著:《欧洲侵权法原则:文本与评注》,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以下;[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范: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五卷“无因管理他人事务”、第六卷“造成他人损害的非合同责任”、第七卷“不当得利”)》,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页以下。不过,站在法教义学的立场上,则抗辩事由论难谓合理。
所谓法教义学(Rechtsdogmatik),系阐述某一特定法律秩序之学问,②Vgl.Jan C.Schuhr,Rechtsdogmatik als Wissenschaft,2006,S.23.其基本立场是对于法律的分析与解释,应当以特定的实在法对象为限展开,其以法律自身的系统性正确与不可批判性为预设前提,③Vgl.Kaufman/Hassemer/Neumann,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philosophie und Rechtstheorie der Gegenwart,8 Aufl.,2011,S.1-2.凭借对法律的体系化解释实现对形形色色法律问题的无漏洞解答。基于法教义学的要求,对既定实在法的解释,应当忠实于实在法本身。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构造上来看,关于“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之规定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不属于侵权责任构成的内容。从结构设置上来看,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章规定了侵权的“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其第三章单独规定了侵权责任中“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这表明,在立法机关看来,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应当与侵权责任的构成区分开来,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并非侵权责任构成意义上的消极构成要件,在侵权责任是否构成的问题上不需要一并考虑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
第二,在将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从侵权责任构成中剥离之后,妥当的逻辑链条应当是,侵权人侵权责任的成立,仅以满足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责任构成规定为必要。具体而言,侵权人侵权责任的成立,就过错责任而言,以满足行为、过错、损害以及行为人行为与受害人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这四大要件为标准;在无过错责任的情形,则在去掉过错要件的基础上,增加“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要件;对于过错推定责任,则在去掉过错要件的基础上,增加“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这一过错推定要件。④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2-56页。在以上三种侵权责任中,只要满足这些构成要件,侵权责任即告成立。
第三,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构成对既存侵权责任效力的祛除或者减损。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文本结构进行分析,应认为,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系在侵权责任构成之外,对侵权责任施加外部影响的独立制度构造。具体而言,在侵权责任因符合相应构成要件规定而成立的基础上,倘若存在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则这些情形便在规范层面上对既有的侵权责任予以消解或者削弱。一个恰当的比喻便是,侵权责任构成方面的规定犹如一位面包师,其负责制作面包(即侵权责任),而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方面的规定类似一位食客,其所意欲的,便是吃掉面包师所制作的面包。
基于上述分析,以抗辩事由论解释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便存在解释错位的问题。
第一,抗辩事由论所预设的基本法权模型是,抗辩事由是广义上侵权责任成立的消极构成要件。⑤参见前注②,冯珏文。根据抗辩事由论,侵权责任的成立需要做两方面的考虑,即正面的侵权责任积极构成要件的考量与反面的侵权责任抗辩事由的考察,唯有既符合积极构成要件,且无抗辩事由,或者虽然存在抗辩事由但只能免除部分侵权责任的情形下,才成立侵权责任。这一逻辑进路在德意志法与英美法的语境中自然毫无障碍,其缘故在于,在不考虑实体法与程序法区分严格程度的前提下,德意志法与英美法的相似性在于,两者在思考侵权责任的成立时,将侵权责任的成立分为了两个阶段,在积极构成要件层面,德意志法与英美法所考虑的是是否存在一项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侵权行为,如果存在一项行为符合积极构成要件,那么在该阶段的法律思考中,行为人便应基于该侵权行为负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不过这只是一个中间性的结论,侵权责任尚未成立,其是否最终成立仍有赖于第二阶段的思考;第二阶段的思考,便是关于消极构成要件即抗辩事由层面上的分析,具体而言,倘若加害人(被告)提出了法律所承认的抗辩事由,那么在第一阶段中因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预备状态的侵权责任便会被消解或者被削弱,而最终所呈现的侵权责任,便是积极构成要件与抗辩事由综合作用的结果。
然而,从我国的《侵权责任法》文字安排来看,我国并未将侵权行为单独作为法的规范对象,而是径行以侵权责任为中心展开了规范构造。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层面,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未将侵权责任的成立区分为侵权行为分析与侵权行为应然责任的祛除或者削弱两个阶段,而是将侵权责任的成立限制在了传统侵权法理论的积极构成要件的范畴之中。换言之,对于我国《侵权责任法》而言,侵权行为应然责任的祛除或者削弱并非侵权责任成立所应考虑的因素,甚至侵权行为这一术语也并非独立的法律事实,其所具有的行为涵义,其实最终蜕化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行为人加害行为这一要素,而不再如德意志法一般,具有行为意义上的债因地位。因此,抗辩事由论无法准确阐述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特性,对于我国《侵权责任法》来说,抗辩事由与侵权责任的构成与成立没有直接关联,其并非侵权责任的消极构成要件,而是独立于侵权责任构成与成立之外的制度构造。
第二,抗辩事由论认为,抗辩事由系在构成要件层面对侵权责任的积极构成要件发生作用,藉由削弱或者消解侵权责任的积极构成要件,从而最终达到阻却侵权责任发生或者削弱侵权责任的效果。这在德意志侵权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德国民法典》第227条、第228条所规定的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作为抗辩事由,其正是通过消解侵权责任中的违法性要件而产生阻却侵权责任发生之法律效果的,而作为抗辩事由的因第三人作为或者不作为中断因果关系链条的情形,是典型的将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要件予以消解而产生阻却侵权责任产生的结果。不过,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语境内,抗辩事由论仍然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如前所述,在德意志侵权法中,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作为抗辩事由,直接作用于违法性这项独立的侵权责任积极要件,但对于我国而言却欠缺学理与规范基础,因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未将违法性要件置于侵权责任构成之列;①参见前注①,程啸书,第161页。在法学层面上,通说也认为违法性并非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②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0-301页;前注④,王家福主编书,第399-400页;高富平:《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91页。故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难以解释为在微观的构成要件层面上,具有对侵权责任积极构成要件的直接作用,而只能认为,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对作为整体的侵权责任所能发挥的实际法律效力,施加了阻却或者削弱的影响。又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这表明,在侵权责任的认定中,被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对侵权责任的实际效果具有直接作用,而依抗辩事由论的路径,由于“一定的抗辩事由总是以一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为前提”,③同前注②,冯珏文。应解释为,被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削弱或者消解了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即实现了过失相抵。尽管在过失相抵的具体认定上,并不是直接将侵权人的过错与受害人的过错径行以类似抵销的方式予以混同并产生苏联民法上“混合过错”之主观状态,而是通过对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的过错进行比较,最终依受害人过错程度的轻重而减轻侵权人的侵权责任,④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但其核心内涵仍然是受害人过错这项抗辩事由对作为积极构成要件的侵权人过错发挥了削弱作用。不过,值得商榷之处在于,就法理而言,受害人过错与侵权人过错并非同一法律事由,前者系侵权损害扩大层面上的过错,后者才是侵权责任成立意义上的过错,两者并不直接相通而具有交叉的内涵,更为妥当的解释路径应当是,受害人过错独立地因构成减轻责任的情形而在外部削弱了侵权责任的法律效力,并未在内部的构成要件层面上构成对侵权人过错要件的减损,两者应当分属侵权责任构成与侵权责任减损两个制度构造之中,其既不能混合,也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就教义学体系而言,受害人过错被设置在了侵权责任构成之外的独立的“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之中,其并不属于侵权责任构成的内容,因此,在解释上也只能依据这种立法体例,认为受害人过错系对之前的侵权责任构成发挥外部性影响的制度工具之一。
综上所述,抗辩事由论是在继受德意志法与英美法的过程中,未对我国《侵权责任法》体系构造作深入法教义学审视的产物,尽管在法理与逻辑上,抗辩事由论既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又能够实现逻辑上的自洽,但在法教义学立场上,它却并非契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理论,因此,有必要寻求新的替代性理论,以便更为妥当地适应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特点。
二、免责事由论的基本观点及其不足
(一)免责事由论的基本观点
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出台后,也有部分学者发现,以原有的经由继受而获得的抗辩事由论来解释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的“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并不合适,这些学者认为以免责事由指称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所规定的诸多情形更为恰当。例如,程啸认为,抗辩事由与免责事由并非同义词,事实上抗辩事由包括但并不只限于免责事由,免责事由是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表面上满足之后,免除行为人侵权责任的法律事实,抗辩事由则不仅包括这种情况,也包括证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欠缺而主张责任不成立的状态,故免责事由较抗辩事由而言是更为妥帖的术语表述。①参见前注①,程啸书,第214页。王利明教授也指出,严格来说,免责事由与抗辩事由存在一定区别:第一,范围不同,免责事由常常由法律所规定,而抗辩事由则非常宽泛,不仅包括法定的免责事由,也包括当事人约定的抗辩事由与构成要件不满足的抗辩;第二,原因不同,免责事由基于法律直接规定而产生,而抗辩事由则相对灵活,可以由约定产生;第三,是否需要当事人主张不同,免责事由可以由加害人主张,也可以由法院依职权调查,抗辩事由则系针对请求之概念,往往需要由加害人自己提出。为此,王利明教授认为,采用免责事由,而非抗辩事由,在概念使用上更为严谨。②参见前注⑦,王利明书,第389-390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也采相似见解,其核心观点在于,免责事由系法律直接规定之产物,而较抗辩事由范围为窄,故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使用免责事由术语更为科学,并且,在更高抽象程度上,免责事由也难以包含减轻责任的情形,因此,在免责事由概念的基础上,融入减轻责任的情形,最终决定采纳“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的术语表述,既在逻辑上具有周延性,又通俗易懂,便于民众理解。③同前注③,王胜明主编书,第138页。
(二)免责事由论的不足
与抗辩事由论相比,免责事由论在理论上具有一定优越性,其注意到免责事由较之于抗辩事由而言,更具有法定色彩,同时也极为敏锐地指出了对于免责事由而言,其“前提是有责任”,④同前注③,王胜明主编书,第138页。换言之,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中所规定的免责情形,系以侵权责任已经成立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免除侵权责任,其不属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也不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只是会削弱符合构成要件的侵权责任之效力。尽管如此,免责事由论仍然存在如下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免责事由论与抗辩事由论的第一个分歧在于,免责事由论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中所规定的免责条款,系属于法定的免除或者减轻侵权责任情形,这些情形是真正的免责事由,其属于抗辩事由的一部分,抗辩事由则不仅有法定的免责事由,也可能由当事人约定产生。此一结论似有武断之嫌。以英美法为例,英美法所承认的侵权一般抗辩事由,诸如公共政策、与有过失、无法避免的意外事件、不可抗力、私力救济、紧急避险等,均具有制定法或者判例法根据,绝非可供当事人约定。在实务上,使用免责事由的表述,也并不意味着其必然带有法定色彩,例如,在保险行业,免责事由便常常存在于保险合同之中,其隶属于当事人约定的范畴,而非法律规定的情形。①在保险合同中,常常会以“责任免除”“免责条款”等方式明确约定保险公司免除保险责任的事由。免责事由这一术语本身并不具有法定色彩。因此,免责事由与抗辩事由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前者局限于法定的情况而后者包含了法定和约定的情形。
第二,王利明教授所持的免责事由论认为,免责事由不仅可以依当事人意思而主张,而且可得由法院依职权予以调查,与之相对应的是,抗辩事由则不一定具有这一性质。这一结论的基础在于,王利明教授认为,免责事由其实是侵权责任构成的独立部分,申言之,侵权责任不符合一般构成要件,自然不成立侵权责任,不过,即使侵权责任符合一般构成要件,但如果存在免责事由,如受害人故意、第三人行为、不可抗力等,便意味着加害人可能没有过错,也可能表明加害人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免责事由的存在阻却了构成要件的充分,故而亦可认定为责任不成立。②参见前注⑦,王利明书,第3 8 8页。上述推论表明,王利明教授的免责事由论在内核上与传统的抗辩事由论并无轩轾,两者所指向的法定的、具有实体法性格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侵权责任的情形,本质上都是对侵权责任成立的一种阻却,其发挥效力的方式是直接毁损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而非在外部削弱或者消解侵权责任的效力。两者唯一的区别只是,抗辩事由所涵盖的范围比免责事由宽广一些,免责事由只是一种特殊的抗辩事由。这一理论路径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体系设置存在矛盾,与抗辩事由论相比,其只是以免责事由这一术语简单取代抗辩事由,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抗辩事由的范围以便实现免责事由与抗辩事由之间的区分,而未深入考察抗辩事由论内部的机理与逻辑,故而并不足取。
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所持的免责事由论虽然存在第一点所提到的缺憾,但却富有逻辑性地指出,免责事由之存在,系以侵权责任之存在为前提,从而清晰地勾勒出“侵权责任成立——侵权责任免除”这一两分法的逻辑结构,值得赞同。不过存在疑问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却认为,免责事由无法涵盖减轻责任的情形,③参见前注⑦,王胜明主编书,第138页。这一结论有待商榷。事实上,减轻侵权责任系部分免除侵权责任之展现,故而将减轻侵权责任的情形纳入免责事由之中并无理论障碍,将免责事由表述为“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似有人为复杂化之虞。
(三)小结
综上所述,免责事由论尽管较抗辩事由论而言更具有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合理性,但免责事由论内容仍然存在较多分歧,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职是之故,实有必要在免责事由论的基础之上,推进理论上的探索与构造。
三、侵权责任免责权及其构成:基于权利思维与法教义学的展开
(一)侵权责任免责权概念的提出及其优势
对于民法而言,其逻辑展开与分析的基础应当是主观权利。在传统欧陆民法理论中,存在客观上的法(Recht im objektiven Sinn)与主观意义上的法(Recht im subjektiven Sinn)之分,前者系法律规则所构成之整体,后者依通说,则系指保护特定利益的意思力(Willensmacht),又称主观权利或者简称权利。①Vgl.Dieter Leipold,BGBⅠ:Einführung und Allgemeiner Teil,7.Aufl.,2013,S.75.恰如德国民法学家Andreas von Tuhr所言:“私法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法律生活多样性最后抽象所得的,系主观意义上的法,即主观权利。”②Vgl.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Aufl.,2010,S.35.对于民法体系而言,主观权利位居枢纽与核心地位,以主观权利为中心,结合义务概念,使市民社会成员在交往的过程中,依据私法自治而各自享有相应的权利,并对应地负担义务,构成民法型构与规范市民社会的基本逻辑路径。职是之故,在分析民法中各主体之间利益的损益与分配问题上,应当尽量将这一问题纳入权利思维的视域之中。
对于抗辩事由论与免责事由论而言,尽管理论上存在分歧,但其共同点在于,均将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视为影响侵权责任成立或者影响已经成立的侵权责任效力的单纯法律事实,却没有将其纳入权利思维的范畴之中,其结果便是,抗辩事由论与免责事由论均倾向于将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解释为对侵权责任积极构成要件具有直接影响的法律事实,区别只是抗辩事由论正式地将这些法律事实纳入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体系之中,并将其定性为消极构成要件,免责事由论则倾向于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单纯从结果角度强调不可抗力、紧急避险等事由客观上具有免除或者减轻侵权责任的法律效果。一言以蔽之,抗辩事由论与免责事由论所择取的观察视角,系被侵权人是否能够向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正因为如此,在这一视角中,不可抗力、紧急避险等事由才非常自然地被作为被侵权人权利的反面限制因素予以考虑,换言之,抗辩事由论与免责事由论在理论上的偏好乃是,从被侵权人角度考虑其向侵权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应当得到满足,而在这一思维进路中,不可抗力、紧急避免等事由当然只能依附于侵权人权利之下,成为是否减损或者消灭侵权人权利之斟酌因素。
然而,上述视角的择取忽略了一个重大事实,即在诉讼中,主张存在“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的主体并非被侵权人,而系侵权人。对于被侵权人而言,其只要证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章所规定的责任构成方面的构成要件系真实且充分的,即可导致侵权责任的成立,倘若侵权人并无可以对抗被侵权人的合理事由,那么该侵权责任则对侵权人发生完满效力,侵权人便应向被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倘若侵权人能够举证证明存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中“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那么反过来,被侵权人根据责任构成所获得的主张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权利便会遭到否定,其状态是根据不同的事由,根据责任构成所成立的侵权责任既可能完全失去效力,也可能只是部分地被减损其效力。由此,站在被侵权人的视角观察,“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其实赋予了被侵权人对抗侵权人的权利。具体来说,在存在“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的情况下,并不是这些事由的出现直接影响了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而导致侵权责任成立受阻或者效力减损,而是这些事由作为一种权利的构成要件,导致相应的实体法上权利的诞生,而后,该权利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消灭或者减损了侵权责任,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法是,该权利阻却或者减损了被侵权人主张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权利。该权利可以表述为“侵权责任免责权”,系指侵权人所享有的,在特定事由下,得以免除或者减轻侵权责任,对抗被侵权人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主张的权利。
基于主观权利理论,将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中“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解释为侵权人基于这些特定事由而享有侵权责任免责权,与抗辩事由论与免责事由论相比较,具有如下优点。
第一,对于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而言,侵权责任免责权是更为优越的分析工具。在抗辩事由论与免责事由论中,隐含的分析视角,其实都是被侵权人的角度,因此,抗辩事由论或者免责事由论,实际上真正关心的是被侵权人是否能够成功地向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倘若不存在抗辩事由或者免责事由,那么被侵权人在完成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证明之后,其主张便会获得法院支持,而如果存在特定的抗辩事由或者免责事由,则被侵权人的主张就只能获得部分支持,甚至无法获得支持。这一分析视角其实相对忽略了侵权人的能动地位与利益。在引入侵权责任免责权概念的背景下,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非单向维度地仅关涉被侵权人能否顺利向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的问题,而是被侵权人与侵权人各自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权利,所展开的权利对抗问题,申言之,在引入侵权责任免责权概念的情况下,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呈现一种攻击防御的态势,被侵权人一方享有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权利,该权利具有积极性与攻击性;侵权人一方则享有依据特定事由,主张减轻或者免除自己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的权利,该权利具有消极性与防御性。这种主观权利视野下的分析框架,不仅更为清晰,也更为符合民事诉讼法学主流学说所倡导的当事人主义精神。
第二,能够较为妥当地处理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与免责事由之间的关系。抗辩事由论与免责事由论均承认,抗辩事由,或者说免责事由,系通过直接削弱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而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但恰如笔者所分析的那样,对于有的特定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而言,因为违法性并非我国《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所以并无可供其影响的构成要件;对于与有过失这类特定事由而言,也并非受害人过错直接影响了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侵权人过错,而是在过错比较的基础之上对侵权责任的实际效力作了损益,以达到利益平衡之效果。真正可以从削弱构成要件角度分析的特定事由,应系受害人故意与第三人原因,其缘故在于,这两种特定事由属于中断因果关系型免责(抗辩)事由,①参见前注①,程啸书,第226-229页。其直接在逻辑上否认了侵权责任构成中受害人损害与加害人之间的因果关系要件,因此将这两种事由解释为系对构成要件直接发挥作用,自然难谓不当。不过,径行将仅适应受害人故意与第三人原因的理论路径扩大到所有减轻或者不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则有过度类推之虞。况且,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观点,免责事由所作用的,系已经成立之责任,因此,作为免责事由的受害人故意与第三人原因,与其说是对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具有直接影响,不如说是对已经成立之侵权责任具有外在的削弱或者消灭效力。在引入侵权责任免责权概念的前提下,免责(抗辩)事由则无须与构成要件发生关联,其并非侵权责任成立的消极构成要件,而是侵权责任免责权得以成立的积极构成要件。在引入侵权责任免责权的情况下,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与侵权责任免责权的构成要件即免责(抗辩)事由“各为其主”,两者在构成要件层面上并无牵连关系,两类构成要件只是间接地透过被侵权人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权利与侵权人主张免除或者部分免除其侵权责任的权利之间的博弈发生关联,并无直接交融之必要。在侵权责任免责权的概念背景下,免责(抗辩)事由能够摆脱在抗辩事由论中暧昧不明的消极构成要件地位,真正地作为独立的侵权责任免责权构成要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一思维进路中,免责(抗辩)事由能够获得绝对的独立性,同时,也无须依抗辩事由论而将其解释为构成要件的派生性产物。②参见前注②,冯珏文。
第三,能够突出侵权人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主体地位,维护当事人主义之下的诉讼双方之间的平等关系。在免责事由论中,部分学者认为,免责事由作为法定的免除或者部分免除侵权责任的情形,法院可依职权予以调查。这种观点与民事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主义相悖。尽管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当事人主义应为大陆法系式的受约束的当事人主义,法院在实际诉讼中,仍然保有依职权主义介入诉讼,行使释明权的权利,①参见许可:《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我国法上的新进展》,《当代法学》2016年第3期。但在实务与理论上均获得通说地位的当事人主义,其所蕴含的处分权主义与辩论主义却已经成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性理念。②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基本模式:争鸣与选择》,《现代法学》1996年第6期;韩波:《民事诉讼模式论:争鸣与选择》,《当代法学》2009年第5期。根据处分权主义与辩论主义,诉讼中的原告受自身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事项的约束,③高橋宏志『民事訴訟法概論』(有斐閣,2016年)101-104頁。在此基础上,原告与被告在辩论阶段就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事项,各自依据自己所知晓的事实与享有的权利进行诉讼上的攻击防御活动,④藤田広美『講義民事訴訟』(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40頁、71頁。法院则在双方辩论的基础上作出裁判,仅在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引导诉讼,推动诉讼的正确发展,法官方可行使释明权。⑤高橋宏志『民事訴訟法概論』(有斐閣,2016年)124-127頁。因此,根据当事人主义,免责事由并不适合成为法院职权主义的调查对象,尽管免责事由的确是法律所直接规定的特定事由,但法律直接规定这一特性并不必然导致其属于法院依职权考察的事项。倘若免责事由被解释为职权主义的调查对象,则会破坏当事人主义,变相赋予作为被告一方的侵权人更为优越的诉讼地位,这对于作为原告一方的被侵权人而言并不公平。倘若转换思维视角,从侵权责任免责权的角度出发,则不难发现,我国《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免责事由,其实仅仅赋予了侵权人在存在这些特定事由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主张这些事由之存在,而免除侵权责任或者部分免除侵权责任的权利。对于侵权人来说,其是侵权责任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之一,倘若在诉讼中,侵权人并未主张免责事由,或者尽管其主张存在免责事由,但并未尽到必要而充分的证明义务,难以证明免责事由之存在,那么只能认定为侵权人并无侵权责任免责权或者无法藉由证明而行使其侵权责任免责权,被侵权人便可通过完成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证明,令侵权人最终承担侵权责任。这一逻辑路径充分展现了民事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主义,突出了侵权人的主体能动地位,同时也维护了被侵权人与侵权人在诉讼活动之中的平等地位。
(二)侵权责任免责权概念构造的具体展开
根据上述分析,引入侵权责任免责权概念,将免责(抗辩)事由作为侵权责任免责权成立的构成要件,具有明晰法律关系,突出侵权人主体地位,维护诉讼中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妥善安置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与免责(抗辩)事由之间关系等优势。接下来的任务,便是清晰界定作为一项主观权利的侵权责任免责权。
1.侵权责任免责权:侵权责任生效阶段的规范分析工具
从概念形成(Begriffsbildung)的角度来看,法律概念是自生活俗语中所提炼出的专门术语(Fachsprache),⑥Vgl.Rolf Wank,Die juristische Begriffsbildung,1985,S.5.尽管在法的概念形成过程中,其必须以实际生活为基础,但是,在法学技术层面上,准确、精炼、可供模式化法律分析的概念是法律事务与法律科学必不可少的规范性分析工具。
就此而言,侵权责任免责权所提供的分析框架较之抗辩事由论与免责事由论而言更为清晰,也更为规范,在侵权责任免责权的概念背景下,侵权责任最终所发生的确定效力可以分为侵权责任的成立与侵权责任的生效两个阶段。
第一,在侵权责任的成立阶段,被侵权人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章所规定的责任构成要求,证明了相应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后,针对侵权人而言的侵权责任已经成立,当然,在此之前,侵权人也可以运用诉讼上的抗辩,对被侵权人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证明活动予以削弱和对抗,例如反驳被侵权人所主张的事实并不存在或者并不真实等等,在这一阶段,侵权人所实施的诉讼防御活动,系属权利障害事实之证明,具体而言,在这一阶段,侵权人主要通过证明被侵权人所主张之权利存在构成要件方面的欠缺和瑕疵,从而达到阻却侵权责任成立的效果。①新堂幸司『新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1年)611頁。
第二,在侵权责任的生效阶段,倘若侵权人无法阻却被侵权人对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充分证明,则在实体法意义上,侵权人便可藉由证明存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的特定事由(特殊侵权责任还可能存在由其他特别法所规定的免责事由),主张自己享有免责或者部分免责的权利,从而削弱或者消灭被侵权人已经通过构成要件的证明而成立的侵权责任。一言以蔽之,作为主观权利的侵权责任免责权,并不是在责任成立层面上阻却侵权责任的成立,而是在侵权责任成立的基础之上削弱或者消灭侵权责任的效力,对于被侵权人主张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权利而言,侵权责任免除权构成一项权利消灭和阻却事实,②新堂幸司『新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1年)611頁。其并不关涉侵权责任的成立问题,而是与侵权责任的可强制性(Durchsetzbarkeit),③Vgl.Reinhard Bork,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4.Aufl.,2016,S.132.或者说司法保护效力有关。当然,须予以提示的是,倘若侵权人并无主张侵权责任免责权之可能,则已经成立的侵权责任即告发生效力,而不会受到削弱乃至归于灭失。
2.侵权责任免责权与抗辩权:概念相似性及其区分
从术语比较的角度上看,侵权责任免责权与传统民法所承认的抗辩权具有相似性,甚至站在德意志民法的立场上来看,此处所构造的侵权责任免责权其实亦可在宽泛意义上被纳入实体意义上抗辩权的范畴。不过,就我国的法教义体系而言,侵权责任免责权仍然是一项与抗辩权存在较大差异的权利。侵权责任免责权应当自抗辩权概念中被提炼出来,成为一项新兴的主观权利,其理由如下。
第一,侵权责任免责权与民法意义上的一般抗辩权所作用的对象并不完全相同。抗辩权所减损与削弱的,是请求权;④Vgl.Manfred Wolf/Jörg Neuner,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10.Aufl.,2012,S.243.侵权责任免责权所指向的直接对象,并非被侵权人主张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请求权,而系侵权责任本身。与通常情况下单纯的“请求权对抗抗辩权”法权模型相比,侵权责任免责权的理论逻辑要更为复杂一些,具体而言,因为我国《侵权责任法》在立法目的上具有制裁侵权行为的因素,所以在解释上不宜将被侵权人主张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权利简单解释为类似合同中一般债权所具有的请求权,严格来说,被侵权人所进行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证明活动,乃是向代表国家强制力的法院作出的,其目的在于意欲自法院处获得关于侵权人侵权责任成立的司法支持,以便依据国家强制力制裁侵权人,并填补自身所受损害;侵权人行使侵权责任免除权的行为,也主要是向法院表明其主观意志,即因为存在特定事由,所以令自己承担侵权责任,接受我国《侵权责任法》之制裁,赔偿被侵权人之损失并不正当。一言以蔽之,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并不是纯粹的请求权与抗辩权之间的直接攻击与防御关系,而是以侵权责任为中心展开的间接攻击防御关系,双方所享有的权利,分别为主张侵权责任成立的权利与削弱或者消灭侵权责任的权利,其所共同指向的对象,都是具有制裁性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侵权责任。
第二,侵权法上抗辩的内涵与外延较侵权责任免责权而言更为宽泛。在德意志民法理论中,尽管请求权(Anspruch)藉由温得沙伊德的理论而彻底实现了实体法化,但具体到抗辩领域,就术语使用而言,抗辩的术语使用则仍然像罗马法那样,既有诉讼法的意涵,也有实体法的含义,抗辩(Einwendung/Einrede)这一术语,具有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双重意涵。⑤8Vgl.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0.Aufl.,2010,S.47.有的时候,抗辩指的是诉讼法意义上的权利障害型抗辩(rechtshindernde Einwendung),有的时候,抗辩则是指实体法意义上的权利消灭和阻却抗辩(rechtsvernichtende Einwendung),即真正意义上的抗辩权,①Vgl.Manfred Wolf/Jörg Neuner,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10.Aufl.,2012,S.243.唯有后者,才与侵权责任免责权具有外延上的同一性。从术语发展与教义解释要求的角度出发,不宜简单继受德意志民法的理论,而应在此基础上,将侵权责任免责权从宽泛的抗辩概念中提炼出来,并根据这项权利的特点,与一般意义上的抗辩权予以区分,专门用于解释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以及其他特别法中减轻或者免除侵权责任的事由的法律适用。这样能够更有针对性,并可收到法律分析层面上清晰明确之效果。
综上所述,侵权责任免责权尽管与抗辩权存在相似之处,均系防御性权利,但却不应混为一谈,侵权责任免责权应当更为准确地表述为侵权人所享有的,因特定事由之发生而产生的,具有消灭或者减损侵权责任效力的权利,其在主观上系侵权人所表达出的主张自己不应承担或者不应完全承担侵权责任的意思力,客观上则具有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所应承担之侵权责任,从而减少侵权人利益损失的效果,符合主观权利的定义。
(三)侵权责任免责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一项完全性法律规范,常常由构成要件(Tatbestand)与法律效果(Rechtsfolge)所构成,两者的逻辑关系是:构成要件系抽象描述性事实(generell umschriebenen sachverhalt),而一旦生活事实与法律规范所预设的抽象性描述事实相契合,就会引发特定法律效果。②Vgl.Karl Larenz,Methodenleher der Rechtswissenschaft,6.Aufl.,1991,S.251;Hans-Joachim Musielak,Wolfgang Hau,Grundkurs BGB,14.Aul.,2015,S.10.所谓侵权责任免责权的构成要件,即指存在于侵权责任法规范中,能够导致侵权责任免责权产生的抽象描述性事实,与之相对应,侵权责任的法律效果,便是因满足构成要件而诞生的侵权责任免责权所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的文本来看,有关侵权责任免责权的规定是以具体列举的方式展现的,具体来说,其第26条规定了基于被侵权人过错的免责权,其第27条规定了基于受害人故意的免责权,其第28条规定了第三人原因免责权,其第29条规定了不可抗力免责权,其第30条规定了正当防卫免责权,其第31条规定了紧急避险免责权。因此,仅就文本与教义学而言,侵权责任免责权并无一般构成要件。不过,从法学上看,这些侵权责任免责权仍然存在一系列具有共性的一般构成要件,具体而言,有以下三大要件。
第一,侵权责任已经成立。对于侵权责任免责权而言,其得以发生的基础性事实是一项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规定的侵权责任已然成立。侵权责任免责权系侵权责任生效阶段的规范分析工具,其旨趣在于减损或者消灭已经成立的侵权责任,从而影响侵权责任最终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因此,倘若并无作为其作用对象的侵权责任已经诞生这一事实,那么侵权责任免责权也无从发生。
第二,侵权人具有社会自由意义上的特定事由。德国法学家Axel Honneth指出,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自由应当在三个层次上予以理解,其一,凭借社会契约之构造而产生的消极自由(negative Freiheit),③Vgl.Axel Honneth,Das Recht der Freiheit:Grundriß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2.Aufl.,2015,S.44ff.即得以免于作出一定行为的自由;④Vgl.Matthias Mahlmann,Rechtsphilosophie und Rechtstheorie,4.Aufl.,2017,S.347.其二,基于正义而取得的能动自由(reflexive Freiheit),即个人得以贯彻自己意志的自由;⑤Vgl.Axel Honneth,Das Recht der Freiheit:Grundriß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2.Aufl.,2015,S.58ff.其三,特定制度所造就的社会自由(soziale Freiheit),即作为个人自由(包括消极自由与能动自由)媒介与条件的社会现实所造就的自由状态。⑥Vgl.Axel Honneth,Das Recht der Freiheit:Grundriß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2.Aufl.,2015,S.81ff.笔者认为,侵权责任免责权的正当性,恰好源于法律在社会自由意义上对市民社会各成员间自由空间的妥当性设置。概言之,从被侵权人的角度来看,倘若被侵权人能够充分证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则毫无疑问,被侵权人的自由空间受到了侵权人的侵害,侵权人应当为此而承担一定程度上的侵权责任,不过,从侵权人的角度来看,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设置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第三人原因、不可抗力等免责事由,这也就意味着法律制度承认侵权人得以在具备特定事由的情况下介入他人自由空间的社会自由,这种介入性自由因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供给,得以被祛除法律与伦理上的归责基础。
第三,侵权人不承担侵权责任或者只承担部分侵权责任不至于严重悖于公序良俗。所谓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是一国之内的社会公共秩序、生活公共秩序以及全体社会成员所普遍认许、遵循的道德准则。①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0页。我国《民法总则》第8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意味着公序良俗构成一切具有私法意义的行为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侵权责任免责权之行使,作为一种私法上的权利行使行为,也应当遵循公序良俗原则,倘若侵权人因为行使侵权责任免责权而得以免除侵权责任或者减少侵权责任,但却会导致严重违反公序良俗,则此时应当以公序良俗为由而限制侵权责任免责权的发生。接下来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公序良俗要件应当在何种情况下影响侵权责任免责权的构成。在客观层面上,侵权人的行为有悖于公序良俗,则应将这一事实纳入侵权责任免责权是否成立的考量范围之内。不过,存在疑问的是,是否应当在主观层面上为侵权人违反公序良俗而不成立侵权责任免责权设定一个合理的标准。
就此而言,德国侵权法具有借鉴意义。《德国民法典》所塑造的侵权责任体系由三阶层构成,第一阶层是对于权利与法益(Rechte und Rechtsgüter)的保护,具体而言,倘若行为人因故意或者过失而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这四大法益,或者所有权等其他权利的,则应当负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②Vgl.Hein Kötz/Gerhard Wagner,Deliktsrecht,13.Aufl.,2016,S.62ff.第二阶层是对于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之法律(Schutzgesetzes)的行为的规制,具体而言,倘若有特别法设定了保护他人之条款,则一旦违反该条款,行为人便应当负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甚至可能是无过错的侵权责任;③Vgl.Erwin Deutsch/Hans-Jürgen Ahrens,Deliktsrecht:Unerlaubte Handlungen,Schadensersatz,Schmerzensgeld,6.Aufl.,2014,S.100ff.第三阶层是对悖于善良风俗(verstoβgegen die guten Sitten)行为的规制,具体而言,倘若行为人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之方法而加损害于他人,则也应当负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④Vgl.Maximilian Fuchs/Werner Pauker/Alex Baumgärtner,Delikts-und Schadensersatzrecht,9.Aufl.,2017,S.173ff.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阶层的侵权责任中,悖于善良风俗(德国民法中的善良风俗相当于我国民法中的公序良俗)的行为负担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是故意,换言之,德国侵权法理论认为,尽管行为人无需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符合道德标准(Bewusstein der Sittenwidrigkeit nicht erforderlich),但必须在主观层面上存在有意对他人施加损害(einem anderen vorsätzlich Schaden zufügt)之心理事实。⑤Vgl.Peter Bassenge/Gerd Brudermüller/Jürgen Ellenberger/Isabell Götz/Christian Grüneberg/Hartwig Sprau/Karsten Thorn/Walter Weidenkaff(bearbeitet),Palandt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74.Aufl.,2015,S.1414-1415.之所以这么规定,其缘故恰如《德国民法典立法理由书》所言,善良风俗乃“一切有关公平与公正思考的礼貌观念”(Anstandsgefühl aller billig und gerecht Denkenden),⑥Vgl.Bernd Rüthers/Astrid Stadler,Allgemeiner Teil des BGB,18.Aufl.,2014,S.396.善良风俗本质上是道德的合法部分,是法律对道德进行截取的产物,⑦Vgl.Dieter Medicus,Allgemeiner des BGB,10.Aufl.,2010,S.276.而正因为善良风俗所固有的道德属性,为了防止善良风俗因被滥用而过分约束行为人的行动意愿与预期,最终形成道德强制,德国立法者制定民法的政策就是,倘若行为人并无侵犯法益、权利或者违反保护他人法律之情况,而只是有悖于善良风俗,则唯有在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心理状态时,才令其负担侵权责任,倘若行为人主观上并无故意,或者只具有过失,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笔者认为,这一思维进路对于侵权责任免责权的构成要件设计而言具有借鉴意义。公序良俗乃“现代民法之框架性民事裁判伦理”,⑧谢潇:《公序良俗与私法自治:原则冲突与位阶的妥当性安置》,《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6期。其作为侵权责任免责权的一般构成要件,应具有一定程度的谦抑性。具体而言,即使侵权责任免责权之行使有悖于公序良俗,也不应一概认定侵权责任免责权因此而不发生,而应当对侵权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予以考察,倘若侵权人系故意侵权,由于其主观恶意非常严重,严重违反公序良俗,则此时即使侵权人具有前述所提及的以社会自由为基础的特定事由,如第三人过错等,也不应认可侵权责任免责权的发生,一旦被侵权人充分完成了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证明,则侵权人即应负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而不得减轻或者免除其侵权责任。
就法律效果而言,侵权责任免责权存在两种类型的法律效果。其一,完全免除侵权责任。有些侵权责任免责权在符合其构成要件的情况下,能够产生完全免除侵权责任的法律效果。例如,基于受害人故意的免责权、正当防卫免责权、不可抗力免责权与紧急避险免责权,在符合其既定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便能产生完全免除侵权责任的效力。其二,部分免除侵权责任。有些侵权责任免责权虽然无法产生完全免除侵权责任的法律效果,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侵权责任的法律效果。例如,基于被侵权人过错的免责权,便能够部分免除,或者说减轻侵权人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此外,有些完全免除侵权责任之免责权在符合其他构成要件的情形下,也可能不发生完全免除侵权责任之法律效果,而仅产生部分免除侵权责任之效力。例如,在正当防卫的情形中,倘若符合“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之要件,正当防卫人也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换言之,从最终的法律效果上来看,原本具有完全免除侵权责任效力的正当防卫免责权,即因前述所提及之构成要件的满足,而被减损为仅能部分免除侵权责任,正当防卫人仍然必须负担适当的侵权责任。
四、结 论
德国法学家温得沙伊德曾经指出:“法律秩序之旨趣在于依循某种价值调整人之意思,而所谓权利,便是以法律关系为本座,而由法律秩序所赋予之意思所能支配的范围。”①Bernhard Windscheid,Lehrbuch des Pandektenrechts,Erster Band,3.Aufl.,1870,S.86-87.对于民法而言,权利思维是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思维模式,而权利也是最为便利与最为有效的法律分析工具。在抗辩事由论与免责事由论的基础上,将免责(抗辩)事由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间的关联性予以切割,并在免责(抗辩)事由的基础之上构造侵权责任免责权,将免责(抗辩)事由改造为侵权责任免责权的构成要件,既能够在权利思维之下,厘清侵权责任成立与生效的逻辑链条,合理安置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与侵权责任免责(抗辩)事由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在法教义学层面,更为贴切地展现我国《侵权责任法》所蕴含的体系特点与逻辑构造。因此,侵权责任免责权概念及其相关理论,较之于抗辩事由论与免责事由论而言,更具有理论构造与规范解释上的妥当性。
——以《民法典》第1182条前半段规定为分析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