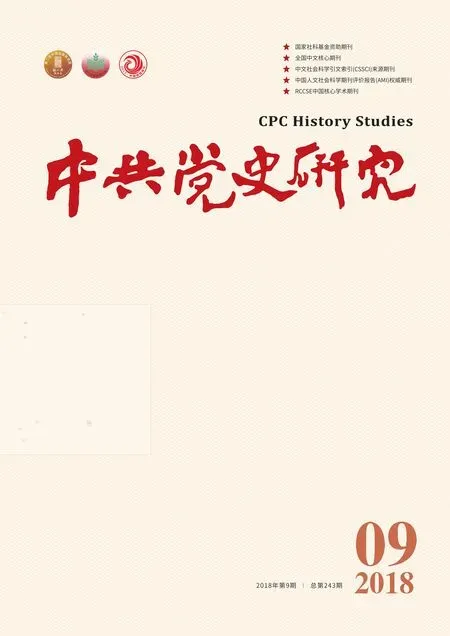知青集体编写回忆录的特点和发展过程
定 宜 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结束,持续了20余年,影响到1955年至1975年上山下乡的几乎每一个人和他们的家庭,给这代人的人生烙上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从知青运动结束迄今,又是将近40年,知青一代行将从历史舞台上逐渐退出,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回过头来看这场运动,分析其成败得失,考察它在当时社会经济以及历史进程发挥的作用,尤其是考量它对这代人的人生造成的影响,应该比以前各个时期更完整、更清晰。而对于每个人来说,知青这个身份对于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漫长的几十年人生中,这段并不太长的日子究竟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对于日后自己的人生经历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也正到了该总结的时候。
一、知青集体回忆录的编撰和特点
官方对知青运动的宣传,从运动伊始就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知青自己也始终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出版物中,以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各种小品文)、影视媒介、宣传展览等各种形式,顽强不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还因此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浪潮,并且持续至今。在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作品中,有一类为数甚众而且独树一帜,那就是知青集体撰写的回忆录[注]本文讨论的对象只限于知青集体撰写的回忆录,不包括学术性的研究专著,也不包括个人的纪实性文章和所有文学作品,以及影视类作品。。之所以将这类作品单独挑出来,是因为不同于文学书写和史学书写,它是知青的民间书写中分量最重也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
知青集体回忆录这种由集体写作、以自己真实经历为内容的形式,再好不过地体现了知青行为的共同特征。
特征之一——一代人的“集体性”。一般的回忆录往往由个人撰写,但知青们早就习惯于“群众运动”,习惯于“抱团”,连回忆录也要集体撰写,这种情况恰恰反映出这代人的行为特征。有知青说:“这代人与其他人有个明显不同,其他人是‘个体’,而这代人是‘集体’。”这个说法可谓一语中的。这代人所谓的“集体主义精神”,既出于当时的宣传和教育,也与上山下乡的特殊境遇有直接关系。他们有过共同的经历,遭遇过共同的挫折,产生过共同的情感,又在经过几十年磨砺后,对那段生活留下共同的,也就是集体的记忆。知青中颇有人以此自诩,将其誉为值得赞美的“团队精神”。近年来,虽然很多人逐渐意识到所谓“集体主义”对个人的压抑,但这种精神已然成为一代人的终身烙印。
特征之二——小群体的多样性。“集体”并非意味着“划一”,集体回忆录反而是最能够体现知青多样性的一种编写形式。一方面,它最充分地展现了知青中各种小群体的多样性。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大多数都是集体结队前往,人员的构成具有某些共性。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之外,知青的组合也多少有些自由度,譬如“文化大革命”时同一派的同学会集体报名前往某地,同校、同班或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乃至邻居好友也会选择同一个插队地区,等等。下乡之后多年同命运共患难的磨砺,又使他们对那段生活拥有了共同的回忆。而回城之后,尽管经历不同、地位各异,但凡是还能够集聚在一起撰写回忆录的,往往多年来并未完全中断联系,互相间的影响也使他们对当年经历的反思多少具有某种共性。另一方面,知青来自不同的城镇,北京与上海不同,南方与北方也不同,大城市与中小城镇更不同。知青去往的地区更是千差万别,仅以北京知青来说,有内蒙古的草原,有新疆的军马场,还有延安、山西等地的农村和山区。从知青的处境看,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与到农村集体插队之间的差距尤其巨大。知青集体撰写的回忆录往往能够集中反映某个群体的特点,以及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总之,不同群体的知青对自己生活的反省与思考,可以为人们留下一代人反思这段历史时参差不齐的蹒跚足迹,会使人们对知青这段历史的认识更丰满、更多样,这是以个人为主所写的回忆录及其他形式作品难以充分展现的,也是研究知青史最需要了解的内容。
特征之三——个体感受的差异性。绝大多数的集体回忆录是不会将虚构作品收纳其中的。从原则上说,这种回忆录是若干个人自传的合集。它最大的好处是能够把去往某个地区(一个县、一个兵团或一个农场等等)的一群知青的共同经历,通过每个撰写者个人的角度和感受,相对全面和完整地呈现出来。回忆录的撰写者尽管出自同一个学校,落户到同一个地区,生活在同一种环境中,但也会因为出身、年龄、性别以及个性的不同,对同一段经历有着差异甚大的体验和表达,这应该是集体回忆录中最有意义和趣味的内容。或者也可以说,通过集体回忆来表现特定地区、特定群体的故事,集体回忆可算是一种最便利、最充分的形式。
当然,集体回忆录也有其特定的缺陷和问题,主要问题往往出在主编身上。当集体回忆录设立主编,而主编又较为强势的时候,每每会要求所有来稿都遵照他的意旨,符合他的理念,甚至要突出所谓的“集体”和“统一”。还有的编委会,会人为地给来稿设立一个“底线”。这样的集体回忆录,真实性和多样性便都打了折扣。这也是如今大量涌现的知青集体编写回忆录水平参差不齐的原因之一。
二、最初的涌现
据考,在有案可稽的以集体回忆录形式出现的作品中,北京知青编写的几部图书最受人关注,其中最早的一部是石肖岩主编的《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辑录了将近200篇北京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所写的文章,形式多样,有报告文学、特写、回忆录、日记、书信等,以能反映和折射兵团生活和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为宗旨。随后出版的,是由北京赴内蒙古牧区的知青集体撰写的《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以编委会名义出版,未具主编姓名。还有一部,即王子冀主编的《回首黄土地——北京知青延安插队纪实》(沈阳出版社,1992年)。与此同时,在北京之外,有重庆到云南支边的知青编写的《红土热血——云南支边生活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成都知青编写的《青春无悔——成都知青赴滇支边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资料汇编》(1991年)以及四川插队知青的回忆录《知青档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实(1962—1979)》(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等等[注]四川等地知青的这类书籍均被编入“知青岁月书系”,除文中提到的之外,还有《命运列车:知青返城沉浮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等,但该书系编入的并不都是集体回忆录,也有个人撰写的作品,恕不一一。另外,其他地区知青若有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编写并出版此类回忆录而为笔者所遗漏者,还请回忆录作者原谅。,其中尤以《青春无悔》的书名最为醒目,甚至一度成为公认的“主流话语”而为众多知青广为认同。
已经有人提出疑问,即为什么在下乡、返城的20年之后,才有这样的集体回忆录突然涌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有知青们人到中年之后开始萌生怀旧意识,在历经求学求职、成家立业等奋斗之后生活和事业基本稳定下来等诸多因素,同时也与其中部分人尤其是“老三届”此时的人生诉求紧密相关,当他们认为自己经历过各种艰难困苦,终于到了该登上历史舞台大显身手的时候,知青经历便成为他们最拿得出手的资本。“青春无悔”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恰逢其时地喊出来的。在知青最初出版的几部集体回忆录中,即可看出这种或隐或显的踌躇满志之迹。
不过,有着这种诉求的人,在知青中毕竟还是少数,就在以上列举的几部书中,四川、云南知青的调子就与北京知青颇为不同。随着参与集体编写回忆录活动的知青群体越来越多,回忆录的书写在体例、立场和观念上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知青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其中,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就是具有自己的思考,并且发出了不同声音的一例。这不仅表现在该书撰稿者主要为上海知青,有着与北京知青不同的风格,还表现在作为史学家的编者更重视文章的史料价值,并且明确表示“除了在文字上作修改外,十分尊重原文的旨意”[注]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引子”第3页。。在该书收集的100余篇文章中,不少都对“青春无悔”的口号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无论回忆录所呈现的思想、观念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知青们终于寻找到了一种最适合集聚在一起并且发出自己声音的方式。这种做法广为各地知青所认同,一旦面世,便一发而不可收。其后几年,北京到延安、山西等地,以及全国各地赴兵团、农村插队的知青撰写的集体回忆录不断涌现,其势恰如雨后春笋,恕不一一。
进入21世纪之后的最初几年,这样的集体回忆录虽然还不时可见,但数量始终不多,似乎陷入某种低谷之中。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众多原来处于“边缘”位置的知青群体开始越来越多地加入这场活动,遂使这种集体回忆所涉范围越来越广,参与的群体越来越复杂多样,所述内容也因之而越来越丰富了。
这里所谓的“边缘”群体,指的是不属于“老三届”的众多知青。“老三届”系指1966年、1967年、1968年在校的中学毕业生,按照当时的政策,他们被要求一律上山下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老三届”与知青可以等同来看。自从知青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展现自己,“老三届”就一直占据着主角位置,而那些“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下乡的以及“老三届”之后陆续下乡的中学生们,却往往被视为“边缘”而受到忽略。重庆老知青编写的《魂系大巴山:重庆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邓鹏主编,内部发行,2005年)尽管出版时间较晚,却使“文化大革命”前下乡的知青群体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这部回忆录后来重新命名,分为正编和续编两部,正编为《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重庆出版社,2006年),续编为《无声的群落(续)——“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上、下卷,重庆出版社,2009年)。其中续编极具规模,集结了1964年和1965年从北京、上海、重庆、沈阳、武汉、成都、长沙、杭州、西安等地下乡的知青撰写的回忆文章。编撰者称,这是全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文化大革命”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全国性回忆录,其意义和成绩不可低估;而在笔者看来,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呼吁与激励诸多“无声群落”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近年的高潮
作为一种写作的体裁和方式,更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活动,知青集体撰写回忆录在最近几年达到高潮,而且还在持续之中,参与人数之多、出版物数量之巨,甚至可以用“群众运动”来形容,因为在动员形式和产生的作用上,都可以看到当年“群众运动”的影子,当然影响面仅限于知青,远不能与当年同日而语了。近年来这种活动之所以突然在数量上急剧增加且参与者众多,主要是因为知青特别是其中的“老三届”都来到了一个特定的年龄段,那就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年过六旬,到了退休年龄,有大量余暇,同时身体精力尚佳,“余热”需要找到发挥之处。他们中有责任感的一些人更是深切地意识到,这是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最后一次机会,从而有一种急迫感;更多的人则愿意通过撰写集体回忆录的活动而相聚在一起,共同回忆往日时光,以此作为增进感情、填补空虚的晚年生活的最好方式。而在晚年回首往事时,将上山下乡视为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经历,既是这代人的共同特征,也是这代人将编写回忆录作为一项集体活动,共同地热心参与进来的思想基础。
最近几年知青集体编写回忆录高潮的出现,虽然是此前这项活动的延续,但新完成的回忆录也具有与以往作品不尽相同的特征。
首先,也是最突出的,就是撰稿“单位”的细化。这里所说的“单位”,指的或是某个县、某个乡(公社)甚至小到某个大队(村),或是某个当年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团、营甚至连,有些村子接收的知青不过十几人或二十余人,但也会集体编撰一部回忆录。这种明显的越来越“小”的趋势,与此前知青回忆录对“单位”宏大的追求,形成了鲜明对比。以前文提到的几部最初出版的集体回忆录为例,《草原启示录》是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的北京“老三届”知青撰写的回忆文章合集,而当年到这里插队的知青人数多达数千名;《北大荒风云录》所涉范围更为广泛;稍后出版的《无声的群落》则力图将“文化大革命”前下乡插队的全国知青都包括在内,为读者呈现一幅全景,须知这部分知青在知青总数中占比虽小,其人数却也曾多达130万名。
小有小的长处。单位愈小,参与者愈众,作品也便愈多元。知青群体本来就是由各种不同出身、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族群构成的,各种群体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差异,单位太大,尽管也都由个人的叙事组成,但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不同却难以凸显,这也是早期一些知青集体编写的回忆录难免失之空泛的一个原因。再者,单位越小,越便于众人广泛加入,回忆录的群众性也就越强。最早集体编写回忆录时,往往由某知青群体中几个最有名气的作家、学者或成功人士牵头,组成编委会,然后向众知青征稿,参加者虽系自愿,但也多是有写作能力者。但当撰写单位由某个乡、某个村的数十人组成时,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这就使更多的普通知青,包括那些几十年不提笔写作的人,也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
其次,以往的知青集体编写回忆录往往都由正规出版社编辑出版,本文所举的几部都是如此,这就必须在主题、体例、文字诸方面符合正式的出版要求。但近年来的回忆录绝大多数却都属于自费的非正式出版物,自行出书,自行编印,也自行销售,由于读者面小,往往也无须考虑发行问题。这样编写出来的回忆录,好处是可以大体保持原貌,而且不必顾虑数量的限制。“一花引来万花开”,一处知青组织书写,各处知青纷纷效仿,到目前为止,这股热潮仍在持续之中。
再次,少数集体回忆录写得非常认真,参与者不再停留在对自己经历的感怀和叙述上,而是将知青的个人回忆与所在公社、大队的社史、队史(村史)结合起来,更何况很多知青当年就有作社会调查的积累。这种做法不仅为知青们的经历提供了重要背景,也为后人了解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存状态和文化冲突提供了一手资料,是知青集体回忆录中重要的、有价值的内容。当然,这样做的还只是少数,大多数知青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不得不说的是,近年来知青集体编写回忆录虽然为数可观,但水平参差不齐,由于主题、内容分散,影响力大的著作不多,一般性的作品占据多数。这些作品大多是对自己真实经历的质朴记叙,生发的多是个人感慨,鲜有对这场运动深入的批判与反思。但从研究者的角度看,这些民间书写却是了解知青一代人目前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和认知水平的最好史料之一。毋庸讳言,从整体上看,这些作品所反映出来的这代人对知青经历的体验和反思,还没有超越十多年前出版的那些回忆录的水平。这是知青一代目前状况的一个真实反映,也是任何一项活动演化成一场“群众运动”时的必然结果。当然,要求所有知青都要对往事进行反思,这对他们而言既做不到,也不公平,在他们都已进入晚年的时候尤其如此。
——纪念上山下乡48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