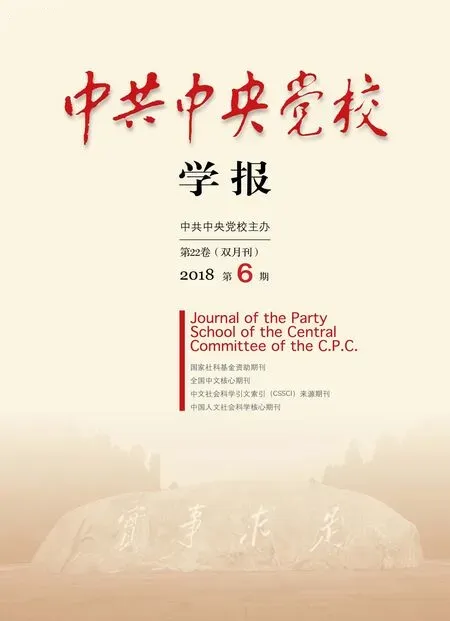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基层妇女干部的培养
韩晓莉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海淀 100089)
中共建立之初就对干部队伍建设格外重视。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被认为是中共赢得民众支持、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干部问题也一直是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思想、制度、培养方式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①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靳玉娟:《抗战时期邓颖超对培养妇女干部问题的思考》,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1期;龚大明:《抗战时期中共干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载《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岳谦厚、董春燕:《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载《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郑 刚:《中国女子大学:抗战时期中共培养妇女干部的一次有益尝试》,载《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6期;谢 敏:《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载《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把增强:《从上层包办到简政放权:抗战时期中共干部作风建设之进路》,载《河北学刊》2015年第2期;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等。,但仍有尚待深入之处。比如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对中共干部培养机制的考察,较少关注基层干部被选拔和培养的具体过程;研究多以集体群像的方式呈现干部的整体面貌,容易忽略干部群体内的差异性。鉴于此,本文以华北根据地基层妇女干部为考察对象,分析中共如何从根据地妇女工作的实际需要和妇女干部的特点出发,贯彻和调整原有干部培养思路,实现对基层妇女干部的发动和培养的,进而对中共干部队伍建设的艰巨和曲折有所揭示。
一、妇女干部队伍的壮大
尽管中共从建立之初,就提出解放和发动妇女的问题,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共对妇女的发动一直较为有限,动员对象也主要集中于城市女工和知识女性阶层。抗战爆发后,随着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中共妇女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培养大批党的与群众团体的女干部”,自上而下地建立妇女组织,成为新时期妇女工作的“中心一环”[1-1]。
在中共革命进程中,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最初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毛泽东曾以先锋和桥梁来形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华北各根据地妇女工作开展之初,女学生首先成为中共妇女干部培养的对象。1936年冬,中共利用与阎锡山政府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会,在太原组织“山西军政训练班”,培养革命力量。训练班吸引了不少来自北平、天津、上海以及山西本省的进步女学生,1937年1月成立的第11连就全部由女学员组成,人数达190余人[2-1]。训练结束后,这批学员中的很多人由组织安排到地方工作,筹建基层妇女组织,成为最早一批活跃在华北地区的中共妇女干部。在训练班学员外,随着八路军进入华北,一些因战争而返乡的女学生或在从事革命工作的亲友的支持下,或在同学的带动下,或在八路军的帮助下,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成为早期基层妇女干部的主力,华北很多地方的县区级妇救会就是由这些女学生为主体建立起来的。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中强调,要首先动员和组织知识界的妇女及女学生,培养和训练她们成为妇运的干部,成为到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中去工作的桥梁和先锋[1-2]。据1939年4月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妇救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统计,在全区384名脱离生产的县级以上妇女干部中,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达70%,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达25%[3-1]。到1940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县级以上妇女干部中,学生占75%,与基层干部总合起来,学生仍占到45%,在干部队伍中处于绝对多数[1-3]。
华北各根据地建立初期,女学生在县级妇女干部中的优势地位既是中共有意识培养发动的结果,也是女学生自身特质决定的。和其他社会群体相比,知识青年不仅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理论素养,而且更富社会责任感和革命热情,这使她们较普通农妇更容易接受中共的革命主张。但另一方面,就华北根据地整个妇女群体而言,女学生所占的比例极低,学生出身的女干部只能满足县级妇救组织的需要,要普遍建立村级妇女组织,实现对广大农村妇女的发动,就必须要从农妇中寻找和培养妇女干部。
事实上,根据地妇女工作开展之初,中共就提出了“干部地方化”的要求,鼓励从农妇积极分子中培养干部。193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妇女工作大纲》明确要求,训练一批下层群众领导与实际工作的干部[1-4]。1939年3月,中共中央妇委在指示信中强调,“应办专门的女干部训练班,特别注意训练女工、农妇的党员”[1-5]。1940年,康克清在阐述华北妇女工作任务时,也提出工农的妇女干部是“支撑华北妇运的大厦”的基础[1-6]。
虽然中共一直要求地方政府和各级妇女组织要注意从农妇中培养干部,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面临很多困难。由于对中共妇女政策不了解,再加上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来自家庭、社会的舆论压力,一般农妇对“抛头露面”心怀顾虑。为了解决基层妇女干部短缺的问题,这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基层妇女干部或是从乡村社会敢于说话行事的妇女中选择,或是从划定的干部人选中由组织直接任命。在北岳区,村级妇女干部多是从已有妇女干部的亲朋、同学,或农会干部和原地下工作时期老党员的家属中物色和培养的[4-1]。完县建立村妇救会时,遇到阻力较大的村子,农会主任便同妇救会干部一起出面,“要求每个农会会员都要动员自己的妻子参加村妇救会,并且由村农会一个干部的妻子担任村妇救会主任”[4-2]。在寿阳县,很大一部分妇女干部是从受压迫、受虐待的童养媳和不满父母包办婚姻的女青年中动员出来的[5-1]。在根据地妇女工作开展初期,迅速扩大干部队伍是中共妇女干部培养的首要任务,很多时候,地方政府和妇女组织只能借助行政力量去发展干部。
根据地建立初期,大量的农妇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干部队伍中,保证了基层妇女组织的建立。到1939年,在定县194个村中就有183个村建立了妇救会,唐县223个村成立了妇救会。1938年晋察冀边区妇女代表大会通过的县妇救会简章规定,村妇救会组织系统与县妇救会相同,每个村妇救会将设立5名不脱产干部。按此标准推算,仅定县、唐县就分别有上千名村级妇女干部[3-2]。据1939年4月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妇救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统计,全区共建立村妇救会16784个,这也就意味着在晋察冀边区有着8万名左右的基层妇女干部[3-3]。
黄道炫在对根据地时期中共干部的培养机制进行研究后指出,虽然中共在干部培养过程中强调量与质的平衡,但实际工作中多会表现出强烈的效率优先原则,即遵循“先求量的做大,再求质的提高的发展模式”[6]。华北根据地基层妇女干部队伍建设同样如此,为迅速建立妇女组织,打开工作局面,数量众多的知识青年和劳动妇女在短时间内被吸收到干部队伍中,这其中既有接受中共革命主张而主动加入的女学生,也有根据出身和社会关系由组织任命的普通农妇,甚至还有村中名声不好但表现活跃的妇女。按照先量后质的发展模式,在干部队伍达到一定规模后,巩固和提高其素质就成为基层妇女干部培养的必然要求。
二、妇女干部政治觉悟的提高
基层妇女干部数量的增长为妇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但干部整体素质的低下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工作的深入。华北根据地妇女工作开展初期,有两种妇女在妇救会中表现积极,一是因不愿青年妇女“抛头露面”而代替她们出来工作的老年妇女,二是村中名声不好但敢说话行事的妇女,很多村妇救会就是以她们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于这些早期干部,中共承认她们在参战动员方面发挥的作用,但也认为她们的不当行为容易引起民众对妇救会的误解,需要在工作中注意对她们的改造[1-7]。此外,很多以政府指派方式加入干部队伍的女学生和农妇,由于缺少工作经验、政治觉悟有限,也存在着工作被动或流于形式的问题,“学生成份的好灰心丧气,不能吃苦耐劳,很少知道社会上事情;家庭妇女封建意识很深,好羞羞答答”[3-1]。面对这种情况,尽快提高干部素质就成为当务之急。
干部训练班一直是中共解决基层干部缺乏,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方法。抗战时期,中共制定干部轮训制度,要求区以上组织建立训练班,党员、干部要轮流接受训练。华北各根据地妇女干部队伍壮大后,组织干部训练班也被运用到妇女干部的培养中。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妇女工作大纲》明确提出,党要吸收大批女党员到各级党校与训练班学习,要开办短期妇女训练班,训练一批基层妇女干部[1-4]。此后,在中共关于妇女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和妇女领导人的发言报告中,都反复强调干部训练班对提高妇女干部素质的重要性。按照中央指示,妇女干部训练班在华北各地纷纷开办起来。在北岳区,从1938年边区妇救会筹备之初,就办起了妇救干部训练班,培训县级妇救干部。到1940年,区以上的妇救会干部都经过了两个月以上的轮训,村妇救会干部也普遍经过了轮训[4-3]。截至1939年“三八”节前,晋西北11县共开办妇女干部训练班33个,培训了624名妇女干部,这些受过训练的妇女干部随后又在各县普遍举办了区、村妇救会干部、妇救会积极分子训练班[7]。到1939年,晋东南仅第五行政区就开设了30余班,训练了1400多名区乡级妇女干部[3-4]。
由于基层妇女干部政治素养、文化水平、工作性质各不相同,各级干部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和方式也各有侧重。1940年北方局妇委组织的两期干部训练班主要面向县级妇女干部,在组织形式和训练内容方面都显得严格正规。训练内容包括马列主义理论、抗战形势、统一战线、党的基本知识、根据地妇女工作等。训练方法借鉴了延安陕公、抗大经验,学员划分小组进行讨论学习。训练班期间,不仅有北方局妇委干部浦安修、卓琳、刘志兰等辅导学员学习,而且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也先后为学员作过报告。经过学习,学员们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她们纷纷要求到前线、到基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很多学员毕业后又分赴各地,以“滚雪球”的方式层层开展训练妇女干部的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2]。
与北方局妇委组织的干部训练班不同,县、区组织的妇女干部训练班主要面向村级妇女干部。针对村级妇女干部工作地点分散、文化程度较低、又直接面向农妇开展工作的特点,这些干部训练班时间普遍较短,内容更为浅显,组织方式更加灵活,与具体工作结合紧密。在定襄县,县妇救会根据当地敌人据点较多的情况,组织游击干部训练班,在运动中训练了一大批村级妇女干部[8]。1940年冬,寿西二区妇救会组织了为期5天的村妇救会干部训练班,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干部们讲解妇女运动发展史[5-2]。在武乡县举办的干部训练班,教师将当地妇女受压迫的故事编成歌曲教唱给学员[2-3]。在满城县,县妇救会先后组织了两期“草帽训练班”,在教学员编草帽的同时,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使学员在劳动中提高了觉悟,并掌握了从组织生产入手开展动员的办法[4-4]。此外,各地还针对基层妇女干部的工作内容开设过纺织训练班、卫生训练班等。
对大多数由组织指定被动加入到干部队伍的农妇来说,训练班的学习不仅使她们对中共革命和妇女运动的知识有所了解,而且这种集体学习的经历也让她们对自己的干部身份有了真实感受,进而产生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转变。武安县十里店的王雪德和其他4名妇女刚担任妇女干部时都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她们首先被送到干部训练班学习了15天。训练班的民主气氛让王雪德深受启发,虽然已经50多岁,但王雪德还是剪短了头发,放开了双脚,以一个“全新的妇女”形象回到十里店,“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到组织妇女的工作中”[9]。定县西城一位45岁的妇女在被任命为妇救会主任时,工作热情并不高,经过训练班学习回到村里后,她马上敲起锣在大街上喊:“姑娘们!快参加妇救会呀!妇救会是给咱们求解放的;是叫咱们不受虐待的!”在她的号召下,当地很多妇女自动加入了妇救会[3-5]。紧邻定县的安国县,早期一些地方干部为完成任务,委派村中“不正经”的妇女担任妇救会干部并把她们送去参加训练班,这些妇女经过学习,有的进步很快,“洗掉旧习”[3-5]。
妇女干部训练班以集中学习的方式,对基层妇女干部进行政治理论和工作方法上的指导,这对提高她们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无疑具有重要作用。除却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的提高,这些短期干部训练班对基层妇女干部还有更大的意义,即来自官方的重视和走出家门集中学习的体验,强化了她们对自己区别于普通妇女的干部身份的认同感和对中共革命事业的参与感,进而激发了她们开展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三、对妇女干部工作方式的指导
无论是借助行政力量扩大干部队伍,还是以干部训练班提高干部素质,中共妇女干部培养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干部实现对基层妇女的发动。与关系农民经济利益的其他工作相比,根据地妇女运动在开展之初,并没有得到乡村社会的热烈响应,不仅乡村男性成员对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表示不满,甚至竭力阻碍,而且妇女自身也缺乏权利意识和参与的自觉性。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妇女工作开展之初,中共鼓励妇女干部以斗争方式扩大妇女组织在基层社会的影响,树立威信。
193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以“斗争纲领”为题明确了妇女工作的总目标,即“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迫”[1-8]。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对农村妇女提出了“反对一切封建压迫,反对买卖婚姻,主张婚姻自主,反对打骂虐待,反对童养媳制”的要求[1-9]。按照这样的目标和要求,很多基层妇女干部选择通过发动妇女斗争的方式开展工作。
沁县妇救会建立不久,妇救会干部就对当地虐待妻子的丈夫进行了斗争,不仅帮助受虐待妇女离了婚,还把她的丈夫监禁了几个月,“有效地发动了妇女,教育了群众”[2-4]。完县妇救会干部抓住某村女青年因反对包办婚姻自杀的事件,在各村召开妇女群众大会,号召妇女向封建势力做斗争,并在一年中解决妇女受虐待和婚姻问题180多件,提高了妇救会的威信[4-5]。阜平县城南庄妇救会干部刘克在开展工作之初,首先以开群众大会的方式处理了两个当地虐待妇女的典型,“给广大妇女撑了腰,壮了胆”,鼓舞了她们参加抗日活动的勇气[4-6]。武乡一区妇救会常委孙芝兰,在听说木兰村赵三雷逼死老婆后,带领七八个妇女去赵家为死者申冤,要求抗日政府惩处赵三雷。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轰动,县妇救会趁机提出向模范妇女干部孙芝兰学习的号召,《新华日报》也以《武乡的新女性》为题进行了报道[10]。在根据地妇女工作“自上而下的,大刀阔斧”的发展阶段,以批判、斗争方式解救受压迫妇女成为基层妇女干部开展工作的普遍经验,“那时只要听到有挨打受气的媳妇,各级妇救会干部都去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4-7]。
依靠上级支持,发动妇女斗争确实有利于打开工作局面,但也容易出现干部对政策教条化理解和急于求成心理下盲目斗争的现象。比如有的地区就出现了妇女干部代替群众斗争的事情,“不管是贫苦人家因生活琐事的口角,还是一时的打骂,都机械地反对或斗争”。有些妇女干部只将离婚看作是妇女的进步,把离婚件数当成工作成绩,甚至在群众不自愿的情况下鼓动和强制别人离婚[3-6]。这样的斗争不但无法起到动员作用,反而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1941年,在华北某区妇救会主任发起的斗争婆婆的群众大会上,婆婆不仅被戴上纸帽游街,还挨了打。结果适得其反,婆婆说:“媳妇是我的,以后还要虐待,虐待得更厉害些,看你们把我怎么办!”围观的人说:“世界真变了,为着一点儿家常小事,竟这样对付一个老年人——带高帽子,游街,挨打还要当众晒太阳,这算什么样子呢?”[11]
对于基层妇女干部工作中出现的过“左”问题,中共进行了及时纠正。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总体目标下,中共也主动调整了妇女工作的方向,建议基层妇女干部采取斗争之外更温和的方式争取家庭团结,化解矛盾。1939年中共中央妇委在关于目前妇女运动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中,表扬了晋察冀边区提出的“家庭和睦”和陕甘宁边区奖励模范婆婆的经验,要求妇女团体和妇女干部要对轻视妇女、侮辱妇女的行动和言论作“恰当的斗争”,“绝不应过于干涉她们的家庭细事”[1-10]。1941年,区梦觉发表文章指出,妇女干部不能用愤慨的情绪来对付一切轻视妇女的言行,斗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她主张妇女干部要通过“刻苦地、耐心地、点点滴滴地工作”,“情辞恳切地说服一些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男子和老年妇女”,“在团结抗战的原则之下,适当地保护妇女切身利益”[1-11]。
抗战中后期,革命形势的变化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使妇女工作的重心发生了从争取妇女权益到发动妇女生产的转向。尽管这时期中共还是要求妇女干部开展“恰当的斗争”,但随着中共对各地盲目斗争批评的增多和工作重心的转移,越来越多的基层妇女干部主动用调解和教育的方式取代斗争来处理家庭矛盾,以达到团结目的。
阜平县妇女干部前期主要通过领导妇女斗争的方式打开工作局面,但当青年妇女被发动起来,向妇救会干部提出更多的离婚和斗争要求时,干部们却没有给予支持,而是发出“母慈子孝”“婆爱媳、媳尊婆”的倡议,号召青年妇女积极劳动,以经济上的独立来获得家庭中的平等地位[4-6]。在棉上县,有妇女找到妇救会,要求干部帮助她解除家庭痛苦,实现男女平等,妇救会干部卫明秀教育她说:“要和男人平等,就得劳动,自己不劳动,光靠人家吃,用一条线也向人家要,这还能平等?你教咱开会和人家说理,咱就没说的,你以后要纺织‧‧‧‧‧‧”[12-1]与前期带头离婚形成对比的是,这时期一些原本准备离婚的妇女干部开始主动改善家庭关系,以响应政府“家庭和睦”的号召。沁源县某村妇救会秘书和丈夫关系紧张,后来她改变态度说:“我过去是嫌男人不顺眼,不愿和他闹人家,这样一来什么事也办不好,今后我一定好好闹人家,如果做不到,让大家批评。”[12-2]
就大多数基层妇女干部来说,工作经验的缺乏和对中共革命的理解有限,使她们对如何开展工作并没有具体思路。妇女工作的紧迫性也使中共无法给予基层妇女干部更多方法上的先期训练,只能让她们按照妇女工作的总体要求,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并通过表彰先进、批评错误的方式对她们进行方法上的指导。作为中共妇女政策的最终贯彻者和执行者,基层妇女干部工作方法的选择和工作重心的转移主要是中共围绕不同时期中心工作,自上而下规定和有意引导的结果,这也体现了中共基层干部培养与实际工作的紧密结合。
四、对妇女干部性别困境的破解
作为干部队伍中以性别划分的群体,妇女干部在工作中经常要面对女性身份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生理层面的,也有社会观念层面的,都在无形中增加着女性从事革命工作的难度。对于女性身份带给妇女干部的困难,中共和地方政府也从政策和思想层面给予了保护和引导。
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妇女干部经常要承担和男性干部同样的工作,但男女有别的生理差异往往使她们承受着更大压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疾病和生育。在全国妇联档案一份关于晋察冀边区妇运发展概况的材料中特别提到,由于在经期跋山涉水地工作,妇女干部得病的很多,有的因而死亡[3-7]。有些地方,妇科病甚至成为影响妇女工作开展的原因之一,“妇女干部有病的很多,并多是月经病,不能工作的很多又无人去治都是回家休养,有的一二年,有的好几个月”[13]。在北岳区,妇救会干部90%长了疥疮,很多人月经不调[4-8]。疾病之外,简陋的医疗条件和紧张的战斗生活也增加着妇女干部生育时的风险。很多地方都发生过妇女干部因生育或流产后得不到照顾,失去生命的事情,即使顺利生下孩子,由于缺少照顾,孩子的夭折率也非常高。以雁北地区为例,1940年到1944年间,专、县两级的12个妇女干部共生育了16个孩子,一个也没有活下来,还不包括流产的[4-9]。为了克服生育对工作的影响,一些妇女干部选择暂缓结婚或不生孩子。
对于妇女干部遇到的上述困难,中共主要通过制定保护措施的方式,给予她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关照。1939年,中共中央妇委明确要求各级党委负责人尽可能地帮助妇女干部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尤其是疾病、生育等问题[1-5]。1941年7月27日,晋察冀边区发布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保护政民妇女干部及其婴儿之决定》,对妇女干部的卫生费、生育补助费、婴儿保育费、产假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特别提到“对于怀孕或携带婴儿之妇女干部,应将其工作时间酌量减少”,工作内容改为轻便工作[14]。1945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又根据妇女干部的实际困难和物价上涨情况,对保护妇女干部的规定进行了细化和修改,如丰富了卫生用品的种类,延长了休假时间,提高了生育补助的标准,增加了流产后的休养时间和补助费用,扩大了干部子女的照顾范围,等等[15-1]。从1941年起,华北各根据地借鉴陕甘宁边区经验,相继成立了儿童保育会、保育院,收容脱产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以解决妇女干部无法照顾孩子的困难。
在制定具体保护措施的同时,中共还在各种关于妇女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中反复强调,地方政府和男性干部要理解妇女干部的现实困难,尽可能给予她们照顾和帮助。虽然囿于条件所限,根据地政府制定的优待和保护措施只能覆盖县区级以上脱产妇女干部,但这些措施还是表达了中共对妇女干部性别困境的理解,给予了她们极大的精神支持。
生理因素之外,女性身份带给妇女干部的另一层压力来自传统性别观念。在传统观念下,女性被赋予了养老抚幼的家庭责任,从事革命工作就意味着要减少对家庭的付出,自然会遇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阻力。根据地妇女工作开展初期,为尽快扩大干部队伍,中共鼓励妇女通过与家庭做斗争的方式参加革命,也倾向于从受虐待的童养媳和不满父母包办婚姻的女青年中培养干部。1939年5月,洛甫提出了对妇女干部的几点希望,其中一点就是希望妇女干部具有一切服从革命利益的牺牲精神,打破家庭至上的倾向[1-12]。事实上,根据地很多基层妇女干部确实是通过与家庭决裂的方式参加到革命工作中的,也有一些妇女干部是因为工作需要被迫舍弃家庭责任。如怀仁县妇女干部邢培兰服从组织安排,离家赴外地工作并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16]。武乡县妇救会干部胡春花为照顾伤病员无暇顾家,导致孩子因生病耽误治疗而夭折[17-1]。妇女干部李先花因忙于工作与丈夫关系疏远,在丈夫的坚持下离了婚[17-2]。逃离家庭参加革命或为革命事业牺牲家庭的事例在根据地妇女干部中比比皆是。
尽管中共强调干部应具有牺牲精神,但一味要求妇女干部为工作放弃家庭责任并不现实,这一方面容易引起民众对妇女工作的误解,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干部队伍的稳定,因为很多妇女干部同时也是干部家属,弱化妇女干部的家庭责任,必然会增加男性干部的后顾之忧。1942年,周恩来发表《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在批判男权思想的同时提倡尊重母职,认为“妇女于尽母职的时候,少做一点其他的事业,不仅是许可的,而是分工的必需”[1-13]。1943年“三八”节,区梦觉发表文章指出,当出现事业与家庭的矛盾时,选择家庭或事业都是一个好女党员所能走的,好好地照顾革命的丈夫,抚育革命的后代,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1-14]。当然,从干部培养的角度,中共更希望妇女干部能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困难,兼顾事业与家庭。蔡畅建议有孩子的妇女干部以集体轮流带孩子的方式争取更多工作时间[15-2]。对于有妇女干部提出的生了孩子能不能工作的问题,蔡畅指出,“问题不在于有了孩子能不能工作,而是有了孩子怎样把工作搞好”,“那就看我们是否有毅力,能不能吃苦,和办到科学的管理家务和孩子”[15-3]。
对华北根据地大多数农妇出身的基层妇女干部来说,家庭仍是她们的立身之本,这就要求妇女干部要能“吃苦”,用更多付出来换取家庭的支持。基层妇女干部队伍建立起来后,中共也通过表彰模范干部的方式,鼓励妇女干部多承担家庭责任,实现事业与家庭的兼顾。棉上妇女干部明秀为避免工作耽误家事引起婆婆不满,就白天工作,晚上碾米磨面干家务,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家庭和睦,被评为模范干部[12-3]。《晋察冀日报》在对阜平史家寨妇救会主任邓德华模范事迹的报道中,特别提到她努力干家务,对丈夫“处处体贴”[18]。涞源县村妇救会干部韩凤龄在带领妇女生产的同时,还开店做买卖,管理家务,赢得了丈夫的支持,被评为晋察冀边区的劳动英雄[19]。抗战中后期,妇女运动与大生产运动的结合,让很多基层妇女干部从带领妇女生产中找到了事业与家庭的结合点,生产带来的收益也使她们容易获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当然,这也意味着妇女干部还是要承担事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
根据地时期,中共对性别身份带给妇女干部的种种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理解,也尝试从政策和思想层面对她们进行保护和引导,帮助她们实现事业与家庭的兼顾,但战争的艰苦环境和乡村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使妇女干部经常要面对较男性干部更多困难和压力。可以说,性别身份一直是影响妇女干部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中共妇女干部培养中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难题。
根据地时期,中共所培养的数量众多、素质过硬的基层妇女干部对妇女运动和中共革命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基层妇女干部培养的艰巨和复杂。战争环境下,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开展,始终面对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两大课题,进而经常与乡村社会中的传统观念产生碰撞,这都在无形中增大了基层妇女干部培养的难度。为了推动妇女工作的开展,中共按照先求量的做大,再求质的提高的发展模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大量女学生和劳动妇女发动到干部队伍中。紧接着,中共又以集中训练的方式提高基层妇女干部的政治素养,帮助她们完成从外化身份到内化能力的转变。根据民众反应和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中共及时纠正和调整基层妇女干部的工作方式,体现了干部培养与实际工作的紧密结合。对性别身份带给妇女干部的种种问题,中共也尝试从政策和思想层面予以帮助和引导,努力破解妇女干部的性别困境。根据地基层妇女干部的培养既遵循了中共一贯的干部培养思路,又从实际工作和妇女干部特点出发进行了灵活调整,这正是根据地基层妇女干部队伍能够迅速壮大并切实发挥作用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