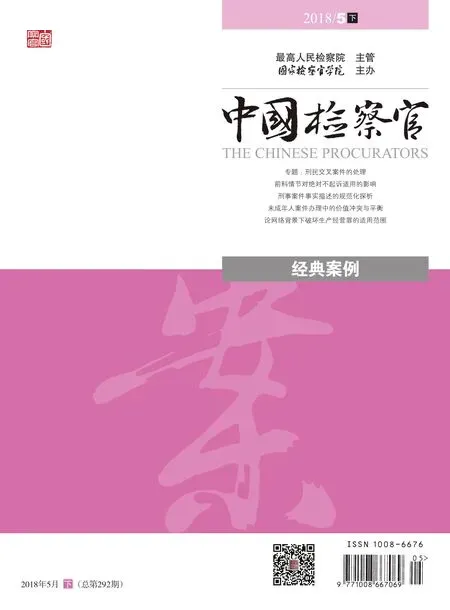主题:论网络背景下破坏生产经营罪的适用范围
文◎吉善雷
【基本案情及诉讼过程】
北京智齿数汇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在淘宝网注册网上店铺,主要经营论文相似度检测业务(俗称论文查重),并由南京分公司负责。2014年4月,董某为在相同业务上谋取市场竞争优势,雇佣指使谢某多次以同一账号大量购买智齿公司淘宝店的商品,导致智齿公司被浙江淘宝网络公司作出搜索降权等市场监控措施,造成损失10万余元。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董某、谢某属于“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属于共同犯罪。2016年12月19日,江苏省南京市中院二审维持原判,认为两被告“有不正当竞争、打击竞争对手的目的,采取了网络虚假交易的手段,并给被害公司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符合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1]
【破坏生产经营罪之内涵解析】
两级法院的判决都认为两被告“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而网络淘宝店是否属于 “生产经营”、该“反向炒信”行为是否属于本罪的破坏行为是争议的焦点。笔者从本罪的法益、目的动机、生产经营及其他方法在网络时代下的新含义进行分析。
(一)破坏生产经营罪所保护的法益是“生产经营的经济价值”
对于本罪的客体,从97刑法修改之后便一直未有定论。学界主要有四种主张:第一种主张本罪所保护的客体是生产经营正常秩序;第二种认为本罪的客体是财产所有权;第三种主张客体是复杂客体,犯罪行为既侵犯生产经营秩序,又侵犯了财产所有权;最后一种主张本罪的客体是生产经营安全,包括两个方面,即生产资料财产安全和生产经营顺利进行的安全。
应当明确的是,刑法分则一共十章,每一章所保护的法益是不同的,而各个章节下的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应当具有共同性。既然刑法修改对本罪所在章节作了调整,那么本罪的客体一定是发生了变化的,否则无法解释立法者的此行为。“破坏集体生产罪的保护法益是正常的集体生产秩序,而破坏生产经营罪属于侵犯财产罪的一种,其保护的法益则是生产经营的经济利益,侧重于保护财产。”[2]从本罪与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罪的区分来看,本罪所保护的绝非“机器设备、耕畜以及其他生产经营资料本身作为财产或财产利益所具有的价值”。若真如此,则本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便无法区分,因为机器设备本身便是财物,且有价值。主观上两罪都是“毁弃型”,行为上都表现为“破坏”,如果客体都相同,两罪便完全无区别。
具体而言,《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两罪都没有规定“本法另有规定,从其规定”,那么这两个罪名也并不是特殊法条与一般法条的关系。两个罪名连在一起,立法者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将两个具有绝大部分重合的罪名规定在一起。因此,本罪的客体绝非“行为作用的对象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是“生产经营的经济价值”。
另外,两罪的法定刑是相同的。“故意毁坏财物罪”所保护的是财物本身的价值,且“数额较大或者其他严重情节”是作为构成要件的,即单纯地毁坏他人财物不一定构成犯罪,需要满足数额要求,其法定刑升格条件也是“数额巨大”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与之相对,破坏生产经营罪中,规定了毁坏他人财物的行为(无论机器设备还是耕畜,都是属于生产经营者的财物,即使并不是该财物的所有权人,刑法在此问题上与民法并不相同。民事关注损害,真正的所有权人才会受到财物被毁坏的财物本身价值丧失的损害;而刑事关注的是行为,行为指向的直接对象是生产经营者所占有的机器设备及耕畜),而单纯毁坏机器设备或者耕畜并不意味着构成犯罪,而是要达到破坏了生产经营这个条件,如果毁坏机器设备而未破坏生产经营,那么行为人不可能构成本罪,如果机器设备价值够大,则有可能成立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罪。因此本罪与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罪需要区分,就需要明确两罪的不同点,即保护法益的根本区别。前者是财物本身的价值,后者是因财物被损害而导致的生产经营被破坏的价值。各个罪的法条之间多少会存在重叠,而立法者为了减少重叠,必定会谨慎确定对犯罪的罪状描述。“减少不必要的重叠,意在使各种犯罪都有其处罚根据,但又没有多个处罚根据;或者说,在避免形成漏洞的前提下,使各个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罪状形成各自的分工。”另外,“应当根据不同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或者根据刑法条文所要保护的法益,确定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减少不必要的交叉重叠。”[3]
应当肯定,立法者是有智慧的,不会做无意义的立法;但是立法者的智慧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社会变化又是很有限的,所以对立法者的原意根据社会变化作不同的解释是解释者的应有之行为,但是对立法原意的修改是一定要通过立法来完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是财产利益,但不是“机器设备、耕畜”等财物本身的价值,而是要将关注点定位到“生产经营”,即生产经营的财产利益。
(二)破坏生产经营罪不是目的犯,而是行为犯
“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的表述使得学界对于本罪是否是目的犯以及该“个人目的”是否属于构成要件要素产生了争议。对于是否是目的犯的争议,现在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并不是目的犯中的目的,本罪也不是目的犯,对此已无争议。而本罪的构成要件是否一定需要具备该要素,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肯定论者认为《刑法》第267条明确规定了本罪的“其他个人目的”中并未将非法获取财产利益的目的排除,另外本罪中的“个人目的”指的是动机,而非故意犯罪中的“目的”;否定论者认为对“其他个人目的”进行任意解释有扩大甚至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4]笔者赞成否定说。
首先,本罪与“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罪”并称为两大“毁弃型”财产犯罪,但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毁弃”并非要求把对象毁坏,只要求物理上、功能上、效用上导致财物无法使用即可构成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罪,理论上已经达成共识。那么本罪的“破坏”也并非指一定要造成生产经营完全无法进行,刑法条文中规定了许多“破坏”,在条文中的意思,“破坏”可以等同于“妨害”,因为市场经济秩序是无法破坏到停止运行的情况的。现实中生产经营,特别是如今网络经营的情况下,对生产经营的破坏多是指通过各种方式使得生产经营难以继续、或者继续的成本太高、维护的时间太长等。“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的行为直接作用于具体的生产工具上,即使缺少了这些机器设备或耕畜,生产经营也并非完全停止,只要经营者再采购一批机器或者买几头耕畜,生产经营便又可以继续。
其次,刑法上多处规定“以……为目的的”,典型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取得型犯罪无论法条是否明文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刑法适用之时都要考虑其主观目的;而本罪“其他个人目的”却不同于“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罪中,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符合数额要求,取得了财物,便认为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盗窃罪论处;而本罪行为人实施了毁坏机器设备的行为,并无法确定其应当认定为“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罪”的毁坏行为还是“破坏生产经营罪”里的破坏行为,本罪规定“其他个人目的”本质上来讲是指犯罪动机,用以区分行为人不同的主观方面,但是动机并不能影响定罪。
最后,笔者认为“其他个人目的”仅表示本罪行为人的动机,而法条并未对“其他个人目的”进行限制。根据“同类规则”,认为本罪的目的应排除“非法获取被害人财物的目的”,但是应当包括“非法毁坏他人财物”、“不正当竞争”等。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与“泄愤报复”同质即可,本罪行为人的目的是作用在“破坏生产经营”上,其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作出什么行为,本质都是为了破坏生产经营,这也是区别本罪与其他财产型犯罪的本质,即侵犯的法益不同。
【“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并非“口袋”】
普通用语一般是具有多义性的,事物的复杂程度以及文字用语的局限性决定了刑法条文无法明文规定所有的可罚行为,因而刑法解释学成为刑法学的核心。在解释刑法条文时,必须抓住犯罪的本质特征,判断某种要素对行为的可罚性影响,以及如何解释才能既符合法条的客观含义,又能与其他法条相协调。
(一)网络背景下“生产经营”的含义
有学者解释“生产经营”时采用形式解释的方法,认为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生产经营”就是指生产性经营,而非生产和经营。[5]但是无论怎样解释,在信息时代下都应当重新审视对“生产经营”的定义。
随着《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的大量信息网络犯罪的出现,信息网络犯罪成为了刑法新的关注焦点,理论界以及实务界基本都认为,网络时代给刑法提出了新的挑战,犯罪手段的不断专业化,以及各种客体及行为范畴的扩大,都使得刑法难以跟上迅猛变化的网络时代。“生产经营”在网络背景下的范畴已经被扩大,众多网络电商行为被接受是生产经营行为。既然认可“生产经营”包含了信息网络中的电子商务行为,那么由此可以看出,解决“以其他方法”的内容,需要明确利用信息网络所进行的生产经营具有什么特点。网络经营的典型特征之一在于“非接触性”,即分为线上与线下的不同平台,网络平台属于线上,而实体交易则属于线下。准确地说,商家更多的经营行为是在线上而非线下,当然并不是说线下就并非商家的经营范围,只是信息网络时代各个经营阶段的分工越来越明确,每个商家经营自己的业务范围,其他相关的范围都由其他商家承包,形成一条条产业链。正如有学者指出,电商平台已经是重要的生产经营“场所(空间)”,是电子商务开展经营的基本“物理空间”。[6]
(二)“以其他方法”的含义
由于犯罪的复杂性与语言的局限性,为了尽可能将复杂的犯罪类型描述下来,而不至于产生遗漏,刑法分则条文常常规定复杂的犯罪构成。对于不同的行为或者对象,立法者可以规定一个上位概念来概括。但是有些行为或者对象没有一个或者很难找出一个上位概念,因此立法者只能逐一列举,从而形成并列关系。如“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就对象而言,只要符合其一即可,但是没有一个上位概念,便采取列举形式。就行为而言,同样也没有一个上位概念,但是几种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性是相当的,因此立法者也只能主要列举这四种行为。
“生产经营”的性质接近于生活秩序,而我国刑法中“破坏”的含义不单纯是“毁坏”,还会包括“扰乱、妨害、改变、影响、干扰”等,如“破坏集会、游行、示威罪”、“破坏选举罪”等,因此破坏生产经营其实就是妨害生产经营,是对生产经营的干扰、影响或者妨害。我国刑法规定的“破坏选举罪”的行为就是“……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7]所以本罪并不要求行为人的行为达到“毁坏”的程度,只要能够妨害生产经营的经济利益即属于本罪要求的 “破坏”行为(前提是情节严重,达到值得处罚的程度)。
本罪的“破坏生产经营”,法律制定时的原意是:直接损坏生产资料或者通过其他方式破坏生产经营,致使生产经营无法继续。具体而言,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直接破坏生产经营,通过直接损坏生产资料的方式;第二,间接破坏生产经营,通过其他手段作用于其他对象,导致妨害生产经营,而生产经营的被妨害是该行为存在的因果关系。
在本罪中,“毁坏机器设备”和“残害耕畜”两个行为其实是可以有一个上位概念的,即“毁坏生产、经营工具”。按照上述立法者的逻辑,既然有上位概念当然应当规定上位概念而非采取列举的方式,否则会增加法律条文的篇幅,既然如此,为何在本罪中有上位概念而立法者却不直接规定而是以“列举+概括”的方式呢?这是因为立法者是有智慧的人,法律有其固有的缺陷,那就是滞后性,而立法者深知这一点。因此,立法者可以预见到“生产、经营”方式的不断变化,因此留下了可以解释的方式。
不难发现,“残害耕畜”针对的是农业的生产经营,“毁坏机器设备”更多是针对工业的生产经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第三产业已经呈现出发展的态势,立法者应当预见到随着社会生产类型的不断变化,理应有个行为用来应对将来信息时代的生产经营,因此,立法者规定了“或者以其他方法”。更何况,仅规定一个上位概念也不足以涵盖所有应受处罚的行为,因此立法者一一列举之后并留下一个兜底的“其他”。
如前文所述,网络环境下的生产经营特点在于“非接触性”,基于此,网络平台的经营在于非接触性,那么本罪的客观行为“以其他方法”理应包含“非接触性”的行为。网络时代的经营者的“生产经营工具”并非传统的“机器设备”或者“耕畜”,当然一切线上的事物都需要实体的工具作为载体,比如计算机,但是这些机器设备具有可替代性,即以前的织布厂的“生产经营工具”有织布机、缝纫机等,一旦行为人将其破坏,将立马导致“生产经营”无法进行。而现在,淘宝店家的经营工具可以说主要就是一个“淘宝店铺”的账号,计算机只是其打开店铺的载体或者说钥匙,行为人即使找到了该淘宝店家并砸坏其计算机也无济于事,甚至不需要重新买一台计算机,去网吧或者现在手机客户端也可以实现登录店铺进行交易的功能。所以现在的行为人想要破坏线上平台的 “生产经营”并不需要靠接触性的手段,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同样的信息网络手段来实现。因此,在承认信息时代网络平台“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必然需要承认“以其他方法”同样涵盖了利用信息网络平台等“非接触性”的行为手段,且不违反“同类解释规则”。
语言学上的同类解释,要求的是词义的相同;刑法学上的同类规则,追求的是法益侵害相同。“国外刑法也认为对物的暴力和欺诈手段属于同类行为,如意大利刑法第513条规定:‘采用对物的暴力或者欺诈手段妨碍或者干扰工业或者贸易活动的……’就是把暴力和欺诈作为同类行为加以规定。”[8]而将“以其他方法”解释为其他足以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目的在于保护本罪的法益,即“生产经营的经济价值”,从法益保护角度,与“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的行为是有同类性的。
【破坏生产经营罪并不是非改不可】
“反向炒信案”对本罪提出了新的挑战,众多学者主张对本罪进行修改以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不乏学者提出了详尽的修改方案。诚然,司法实践中本罪的适用的确存在问题,从法院组织几次“恶意好评捧杀竞争对手如何定性”的研讨会也可见一斑。但是通过对本罪的解释,笔者认为并不需要对本罪进行立法修改,而自97刑法制定以来九次修正案新增许多应对网络犯罪、网络经济犯罪的罪名,但本罪从未被涉及,司法解释以及指导性案例也未涉及过,这也可以侧面反映出,立法者以及司法者均认为本罪的适用并不存在重大问题。
“反向炒信案”二审判决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网络经济下保护生产经营活动的司法意图也很贴合立法原意。立法的滞后性是固有属性,即使无法及时反映网络时代网络经济的现实需要,但是,通过适当的扩大解释,完全可以将新的危害行为方式解释入罪。只要“恶意好评”行为破坏了电商平台上的生产经营,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且满足了情节严重的前提,便可以认为该行为构成本罪,“防止电商平台沦为无法无天的真空地带”。[9]
好的解释者发现刑法条文无法快速适应社会发展的时候,不是一味批判法律的漏洞,因为漏洞与重复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应该努力地通过正确的解释方法对条文本身的含义进行重新定义。法一经颁布生效,就应当推定其是良法,并首先通过解释的方式弥补其看似不合理之处,当然如果真的发现问题,再寻求立法者的修改。
注释:
[1]案例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6e117fc1-5a46-42f8-a0ea-a71a00a510fd,访问日期:2017年3月20日。
[2]罗猛、王波峰:《故意毁坏财物罪疑难问题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6期。
[3]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4]参见张能、杨江立:《破坏生产经营罪:设置动机要素无必要》,载《检察日报》2005年5月20日。
[5]参见王守俊:《破坏生产经营罪若干问题探析》,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8期。
[6]孙道萃:《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网络化动向与应对》,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7]同[2]。
[8]高艳东:《合理解释破坏生产经营罪以惩治批量恶意注册》,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11月18日。
[9]于志刚:《防止网络成为两个意义上的“无法空间”》,载《中国检察官》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