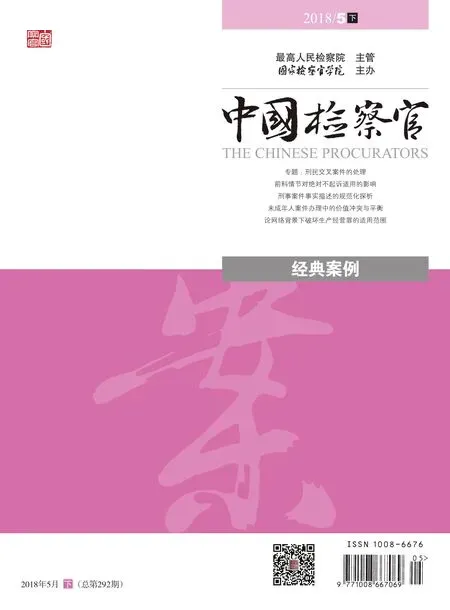电信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
文◎董媛媛
一、问题的提出
(一)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决定其类型的多样化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通信设备的普及,电信诈骗犯罪呈现高发态势。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在其官方微信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以每年20%~30%的速度快速增长。其中,2015年1月至8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电信诈骗案件31.7万起,同比上升31.5%。[1]2017年,全国共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53.7万起。[2]在这些案件中,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将传统诈骗犯罪与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相结合,二是高科技、远程、非接触性犯罪,三是具有取证难、打击难、抓捕难、定性难等特点。[3]电信诈骗犯罪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类型的多样化,从而加大了司法认定的难度。
(二)认定方式没有统一规范性标准使其认定更加困难
司法作为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最后一道也是最有力的防护线,其公正性是法律精神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是民众对法制的必然要求。[4]为了能够使司法发挥其应有作用并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司法机关对于电信诈骗犯罪的认定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前期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司法机关对于电信诈骗犯罪类型的司法认定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此以一个典型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一]2011年4月份,被告人朴锦龙(中国国籍)等人采取向韩国拨打电话的方式对韩国人实施诈骗,以对方涉嫌洗钱为由,诱骗被害人登录钓鱼网站输入自己的银行卡号和密码。被告人通过上述手段从后台窃取到被害人的银行账号和密码后,立即将被害人账户内的存款转入被告人朴锦龙等人事先购买的韩国银行卡内,然后通过他人将款项取出,经地下钱庄转移至国内分赃。[5]
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我国法院对此案件拥有管辖权。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其为诈骗罪。但是,仔细分析被告人的作案手法,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被告人采取欺骗的方式实施犯罪,但是所有采取此种方式的犯罪都应认定为诈骗罪吗?我国《刑法》对诈骗罪定义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可见,其定性是相对模糊的。而学理和实践中通常认为,构成诈骗罪需要有“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理财产”的要件。本案中,被害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输入了个人的银行账号和密码,进而导致被告人可以通过获取的账号和密码取走被害人的钱财,但是被害人并没有处理自己财产的意思表示。那么,将本案认定为诈骗罪是否合适,笔者认为有待商榷。由此可见,我国法律法规条文的模糊性致使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种犯罪没有统一规范性标准,从而导致对此类案件的司法认定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二、定性及其常见类型
了解“电信诈骗犯罪究竟是什么”是我们探讨如何解决电信诈骗犯罪类型司法认定问题的第一步。电信诈骗犯罪并不是刑法上的特定概念,因此,对于其含义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在2011年4月8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对于电信诈骗的相关规定,其中第2条将电信诈骗定义为:“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行为。”可见,其对电信诈骗采取文义解释的方法。但笔者认为,此种解释容易产生误解。“电信诈骗”作为一个新兴词汇,应从广义上对“电信诈骗”一词进行解释。笔者更倾向于将“电信诈骗”一词定性为: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子通信技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的具有欺骗性的行为。[6]
对“电信诈骗”定性后,从不同犯罪类型的特点入手探讨司法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把犯罪类型分为以下三类:
(一)“被害人无处分自己财产的意识和行为”类电信诈骗犯罪
在电信诈骗犯罪中有这样一类犯罪,被害人并没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意识和行为,只是在不法分子的诱导下输入了有关个人银行账户的信息或者点开某个链接,之后自己的钱便被划入到不法分子的账户之下或被不法分子消费。
[案例二]2014年12月,被告人姜士星、何振喜经密谋后开始通过互联网发送“相册.APK”木马下载链接到广州市等地的用户手机上,骗取用户点击安装。之后,被告人姜士星、何振喜利用木马病毒程序盗取的用户关于个人银行账户的信息,通过网上支付的方式盗刷用户的银行卡进行购物。[7]
本案被害人没有处分自己财产的意识和行为,仅是在错误的意识下输入了个人相关信息,并没有自己财产被非法处分的预见可能性。此类电信诈骗犯罪类型的特点有:一是不法分子通过电子网络技术诱使被害人输入与财产相关的个人信息。二是被害人个人财产相关信息的填写与不法分子借此非法处分被害人财产有直接关系。三是被害人无处分自己财产的意识和行为。
(二)“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自己财产”类电信诈骗犯罪
这类犯罪在电信诈骗犯罪中最为常见,是电信诈骗犯罪的鼻祖。与此相关的案例也很普通。
[案例三]不法分子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拨打被害人的电话,以被害人涉嫌犯罪为由,要求受害人向相关的银行账户汇款以配合相关国家机关调查。最终不法分子会让被害人将钱存入所谓的“安全账户”中。[8]
此案例中,虽然不法分子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理由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借助受害人错误认识处分财产的行为非法处分或者占有他人的财产。
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政府的公信力[9]。此类电信诈骗犯罪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权威,降低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因此,2016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对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达到相应数额标准的“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酌情从重处罚。
[案例四]被害人肖某在QQ空间看到可以代办高额信用卡的广告,肖某点了广告上的网站链接后按提示留下手机号码、名字。过了几天,一女子通过电话让他往对方指定的户名周山清的邮政银行账户汇了200元。三四天后,他收到邮寄来的平安银行信用卡后联系对方,对方让他再汇1000元激活费,于是他以无卡存款的方式存了1000元到对方账户上。
本案例的突出特点是犯罪分子利用被害人出于办理高额信用卡的目的,引导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中,从而非法取得被害人财产。本案例是与信用卡相关的电信诈骗犯罪,在下文中笔者会将此案例与其他涉及信用卡电信诈骗方式的案例(第三类)进行对比,以此说明不同的行为模式,司法认定也不相同。
此类电信诈骗犯罪类型的特点有:一是此类犯罪是不法分子采取多样化方式虚构事实,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二是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自己的财产。三是传统方式与新型方式相结合。
(三)“与信用卡相关,未有处分财产的意识和行为”类电信诈骗犯罪
此类犯罪与第一类有相似之处。笔者将其单独划分出来,一是出于对我国信用卡类诈骗司法认定特殊性的考虑,二是将其划分出来,为司法实践中第一类电信类诈骗的认定提供借鉴意义。
[案例五]2014年12月11日,被害人唐某某接到被告人朱某A群发的办理高额信用卡诈骗广告短信后,与短信中留下的电话取得联系。被告人朱某B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要求唐某某在其自己的工商银行储蓄卡内存入25万元作为“保证金”并开通网银。朱某B后将被害人唐某某个人信息、银行存款额度等情况告知被告人王爱智,王爱智随后冒充银行工作人员通过QQ向被害人唐某某使用的电脑发送名为“工商银行申请协议”的木马病毒,植入木马后,要求被害人唐某某在木马病毒生成的假工商银行网站上填写姓名、身份证号、验证码等信息。被告人王爱智则通过后台获取了这些信息。利用获取的信息,被告人王爱智将害人唐某某的工商银行卡上的196304元转走。[10]
本案中,被告人最终是利用被害人填写的信息进而非法窃取被害人的财产。显而易见,被害人并没有处分财产的意识和行为。
[案例六]2014年3月份,被告“飞胖子”利用多部手机群发内容为“能帮办高额贷款信用卡”的短信到他人手机上。当受骗对象回拨手机时,相关人员接听手机,以代办高额低息银行信用卡为名诱骗受骗对象在卡中存入款项作为“升级”所需的“流水”,并将在此过程中收集到的受骗对象身份证资料、电话号码、信用卡卡号、信用卡密码等资料交给“飞胖子”,由“飞胖子”在办“升级”的过程中将受骗对象信用卡内的存款转出骗走。
本案被告人同样是利用获取的被害人相关信息实施电信诈骗的行为。此类电信诈骗犯罪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借助办理高额信用卡的形式,获取与被害人财产相关的信息。二是被害人财产信息的填写与不法分子借此非法处分被害人财产有直接关系。三是被害人无处分自己财产的意识和行为。
三、司法认定
在前文电信诈骗犯罪的定性中已提及,笔者更倾向于将“诈骗”进行扩大解释。由于电信诈骗犯罪是新兴犯罪,前期司法实践倾向于将所有电信诈骗犯罪都纳入诈骗罪的范畴,这样一来实际上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后来随着我国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相关法律的不断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不断成熟,电信诈骗犯罪类型开始有了相应的区分,对于不同分工的人员也有了不同的罪名。如2015年11月1日生效的 《刑法修正案(九)》第28条、第29条增加了两个罪名: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另外《刑法》中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等与电信诈骗犯罪相关的罪名,我国司法认定中对于不同分工人员的定性开始细化。但是司法认定中对于电信诈骗犯罪中何时定性为盗窃罪,何时定性为诈骗罪,何时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仍然存在争议。因此,对此问题的探讨尤为重要,不同的定性可能带来不同的量刑结果。笔者就此问题结合上文中不同电信诈骗犯罪类型进行探讨。
(一)电信诈骗犯罪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1.盗窃罪中“秘密窃取”构成要件争论
我国《刑法》第264条将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描述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此种规定较为模糊。我国刑法通说中通常将盗窃罪描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11]在众多理论中,传统观点认为“秘密窃取”是构成盗窃罪的必要条件。其理论基于不完全归纳,即他们看来人们所看到的盗窃罪都是秘密进行,进而推出所有盗窃罪都是秘密进行。而这便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即使大多数盗窃罪是秘密进行,但也有少数盗窃罪是公开进行的。例如,甲被车撞倒后,钱包掉落在地,这时乙走过来,甲眼睁睁看着乙捡起了钱包。乙的行为成立盗窃罪,但并不是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现代观点认为“秘密窃取”并不是盗窃罪的必要条件,这就为本文讨论的电信诈骗犯罪下的盗窃罪作了铺垫。由于电信诈骗犯罪具有快速性、隐蔽性强的特点,犯罪分子大多采取的并非“秘密窃取”的方式,但是当犯罪行为满足一定构成要件后,仍旧可定为盗窃罪。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将电信诈骗犯罪下的盗窃罪定性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违背当事人意愿或在当事人没有处分财产的意识和行为下,采取平和手段,将他人财物占为己有或者交由第三人占有的行为。”
2.诈骗罪
我国《刑法》第266条将诈骗罪定性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可见,同上述刑法中对于盗窃罪的定义方式相似,此种定义方式较为模糊。而国外许多学者[12]将诈骗罪的构成描述为 “行为人虚构事实——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在错误状态下处分财物——行为人得到财物”。[13]我国学术界对此定义基本认同。其中关于“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意识,并且是否在此种状态下处分了自己的财产”这一构成要件,虽然学界关于被害人是否需要具备此种错误认识并无争议,但是对于被害人处分财产的认识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被害人需要具有完全的认识(细节认识说),[14]即对所转移的财产的数量、价格等具有完全的认识;另一种观点则不要求被害人具有完全的认识,只要认识到自己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人占有即可(转移认识说)。[15]笔者认为,电信诈骗犯罪下的诈骗罪中被害人不需要有精确的认识,只需具有转移的认识即可。这是因为在实践过程中,要求被害人具有完全精确的认识是很困难的。如果一味地苛求被害人具有完全的认识,实则不利于诈骗罪保护被害人合法财产权益的实现。例如,在一个案件中,犯罪分子甲某冒充公安局工作人员给被害人乙某打电话,告知乙某涉嫌洗黑钱,要求乙某将3000元转入到某个指定的“安全账户”中。乙某采取了两次转账,第一次转了1000元,第二次转了2000元。在警方调查取证时,乙某第二次的转账记录由于某种原因丢失,且乙某忘记了被骗的具体数额。但是,警方在犯罪分子甲某的作案工具银行卡上发现了乙某的转账记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诈骗公私财物价值3千元以上、3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如果根据细节认识说,乙某必须对于自己转移的财产具有完全精确的认识,否则其被诈骗一案将无法立案。这无疑是增加了被害人的举证难度。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转移认识说。
综上,笔者认为,电信诈骗犯罪下的诈骗罪应定性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被害人因陷入错误认识并受该认识支配处分(交付)财产为前提,将他人财产占为己有或者交由第三人占有的行为。
人们通常认为,盗窃罪是以偷偷窃取的方式进行,而诈骗罪则是通过虚构事实使被害人相信的方式进行。即行为人的方式不同,将成立不同的犯罪类型。但是,人们忽略了行为人作案方式的多样性特点,盗窃罪也可以采取欺骗的方式进行。例如,甲某给乙某发微信,让乙某点开一个价值为666元的红包。乙某信以为真,点开红包后根据提示输入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和一个验证码32000。过了一会儿乙某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转走了32000元。此时,甲某的行为是成立盗窃罪还是诈骗罪?乙某并不存在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他根本不知道输入的32000其实是转移银行卡的金额。因此,甲某的行为不能满足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如果不考虑“秘密窃取”这一要件,甲某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成立盗窃罪。由此可见,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区别并不在于行为人是采取何种方式取得财物。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一个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普通意义中的盗窃罪与诈骗罪区分的关键之一在于侵犯的客体是财物还是不限于财物,还有财产性权益。[16]但是,电信诈骗犯罪下的盗窃罪与诈骗罪,基于电信诈骗犯罪处分的财产多为动产,具有非接触性的特点,对此不作明确的区分。
电信诈骗犯罪下盗窃罪与诈骗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自愿处分自己的财产,是否有处分财产的错误认识和处分财产的行为。电信诈骗犯罪下的盗窃罪是违背被害人的意愿取得财物,被害人不具有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和处分财产的行为。而诈骗罪则是基于被害人的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从而取得财物的行为。
笔者将进一步以一个典型案例的形式区分电信诈骗犯罪中的诈骗罪与盗窃罪。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中,臧进泉等盗窃、诈骗案为区分电信诈骗犯罪中的诈骗罪与盗窃罪指明了方向。
[案例七]2010年5月,被告人臧进泉、郑必玲、刘涛分别在淘宝网上以虚假身份开设无货可供的店铺。被告人臧进泉和郑必玲通过将虚假网络连接植入到网游充值程序中的方式,诱使买家点击虚假链接进行付款。其中,交易金额标注为人民币1元但实际植入了支付人民币305000元的计算机程序虚假链接,被告人谎称只要点开此链接就可以看到付款成功的记录,从而使被害人实际损失305000元。另外,三被告采取出售套现的方式,通过假借出售游戏点卡、腾讯Q币、女装、女包等进行诈骗。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臧进泉和郑必玲盗窃罪与诈骗罪数罪并罚;被告人刘涛犯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此案的裁判要点中提及: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诱骗他人点击虚假链接而实际通过预先植入的计算机程序窃取财物构成犯罪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虚构可供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欺骗他人点击付款链接而骗取财物构成犯罪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17]
在本案的裁判理由中,法院认为对于既采取秘密窃取手段又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有财物行为的定性,应该从行为人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和被害人有无处分财物意识方面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当对行为人获取非法财物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手段是秘密窃取而非诈骗行为时,即诈骗行为只是盗窃行为的一个幌子,并且被害人也没有“自愿”交付财物的,应当认定为盗窃罪;但是,如果行为人获取财物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手段是诈骗行为,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财物,当盗窃行为只是辅助手段时,应当认定为诈骗罪。
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被害人有无处分财产的意识并且被害人是否在行为人的欺骗下陷入了错误的认识,从而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自愿地处分自己的财产。
(二)电信诈骗犯罪下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的区分
《刑法》第196条关于信用卡诈骗罪构成要件中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在《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所称“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1)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2)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3)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4)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由此可知,在上述电信诈骗犯罪类型三中的案例符合 “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使用”的构成要件。那么,信用卡诈骗罪与诈骗罪又有何不同之处?将上述电信诈骗犯罪类型二中的案例五与电信诈骗犯罪类型三中的案例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最主要的区别是,诈骗罪是建立在不法分子利用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的行为进而非法占有和处分被害人财产之上的犯罪行为。而电信诈骗犯罪则是利用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透露个人与财产的相关信息,进而导致不法分子利用信息获取非法财产的行为。其关键在于被害人有无处分财产的意识。
电信诈骗犯罪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对于不同电信诈骗犯罪类型,应作具体探讨,不能一味地将所有与电子技术相关的类诈骗行为都认定为诈骗罪。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互联网等通信技术深入到千家万户。对于电信诈骗犯罪类型的划分将会进一步细化,对其司法认定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电信诈骗犯罪日益横行的年代,随着司法的进步,人们的防范意识也要不断提高。警惕电信诈骗,让电信诈骗这颗毒瘤从我们的社会中清除。
注释:
[1]吴朝平:《互联网+背景下电信诈骗的发展变化及其防控》,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2]公安部刑侦局官方微信:《来看看咱刑侦的2017年》2018年1月19日。
[3]黎宏:《电信诈骗中的若干难点问题解析》,载《法学》2017年第5期。
[4]高其才:《法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306页。
[5](2014)威刑二终字第 31 号。
[6]笔者认为,“诈骗”与“欺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诈骗”是“欺骗”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二者均具有“骗”的含义,但是,“诈骗”在我国刑法中有具体相关的罪名,所以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而“欺骗”一词,则更能将有关电信诈骗犯罪的形式包含进去。同时,此种定义也是为下文如何对不同电信诈骗类犯罪类型进行司法认定作铺垫。
[7](2017)粤 01 刑终 95 号。
[8]《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电信诈骗犯罪典型案例》,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10月10日。
[9]本文所称的“政府”,并非仅指行政机关,是广义上的政府,即指所有国家机关。
[10](2016)湘 02 刑终 242 号。
[1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66页。
[12]多为日本学者。
[13]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第1000页。
[14]周光权:《刑法各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页。
[15]同[13],第 1003 页。
[16]张明楷:《论盗窃财产性权益》,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
[17]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2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