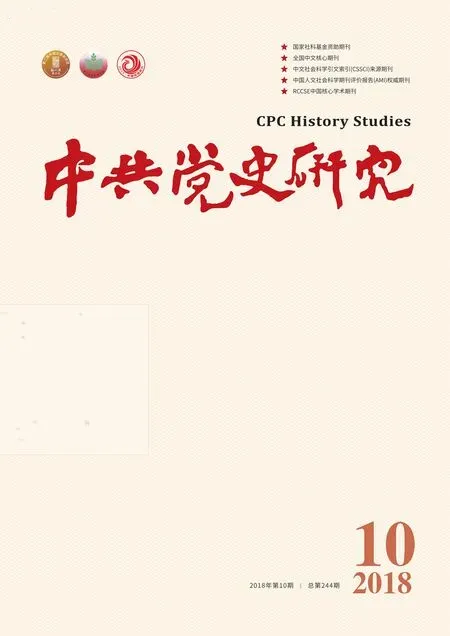一九四九年“安契塞斯号”事件经纬
吴 泉 成
1949年5月底,中共解放上海。6月中旬,为了阻挠中共恢复和发展上海经济建设,国民党利用占领上海周边沿海岛屿的优势,不仅对上海进行海上军事封锁,切断英、美等国船运公司与上海的船运贸易往来,还派出空军对上海及附近沿海地区实施轰炸。其间,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商船“安契塞斯号”[注]关于该英国商船船名的翻译,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该船被炸一事时,译为“安契塞斯号”(《解放日报》1949年6月22日)。《大公报》不同日期将该船译为“安基塞斯号”(1949年6月22日,上海)、“安奇赛斯号”(1949年6月22日,香港)。《中央日报》不同日期对该商船的翻译亦有所不同,有“安诸色施号”(1949年6月22日,湖南)、“安琪色施号”(1949年6月23日,湖南)、“安琪士号”(1949年6月23日,昆明)等。本文正文统一采用《解放日报》对该船的翻译,即 “安契塞斯号”。(Anchises)遭到轰炸,成为当时国民党轰炸上海波及外国商船和在华企业的情况中有重要影响的一次事件。事件发生后,一方面,英国政府不承认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并就该事件向国民党表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英国外交部和太古轮船公司要求国民党予以道歉,并赔偿因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目前,有关这一时期英国对国民党封锁上海以及上海解放前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国内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注]陈谦平:《上海解放前后英国对中共的政策》,《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马丁:《上海解放后英国针对国民党封锁上海的对策及成因》,《史林》2016年第1期;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以〕谢爱伦著,张平、张立、蒋清宏译:《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企业在华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美〕爱德温·W.马丁著,姜中才、韩华、苗立峰译:《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ShaoWenguang,China,Britain and Businessmen: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1949—1957), London: Macmillan, 1991。但是就国民党封锁上海期间轰炸英国商船“安契塞斯号”以及双方就此事件的谈判尚无较为详细的论述。因此,本文拟借助英国外交部对华政策解密档案(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等原始档案和当时《解放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的相关报道,论述英国对“安契塞斯号”事件的政策以及国民党就此事件的反应。
一、“安契塞斯号”事件发生的背景
解放初期的上海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物资严重匮乏,需要尽快从苏南、皖南、浙江等附近地区调运大米、面粉等粮食物资,以及急需的石油等经济建设物资。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恢复对上海陆路运输尚需时日,因此开放上海对外航运迫在眉睫。6月1日,中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开放黄浦江、长江及吴淞口、三岔港航运,商用及民用船只准许自由往来,但外国军舰不准进出[注]《今日起开放长江、浦江航运》,《解放日报》1949年6月1日。。6月15日,为了切断上海与外界的贸易联系,阻挠中共通过航运贸易获取恢复和稳定上海经济的必要物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并通过了封闭中共解放区沿海港口的决议,并交国防部研拟封闭措施及实施日期[注]《封闭共区海口》,《中央日报》(昆明)1949年6月18日。。 三天后,国民党发出准备关闭上海、天津、秦皇岛、温州、宁波等沿海港口的消息[注]Sir A.Grantham to Sir P.Brind, June 23, 1949, FO371/75900/9205.。 然而,外国船运公司并没有在意国民党发布的封锁令。就在国民党发出封锁消息当天,美国总统轮船公司宣布恢复对上海的航运,其他外国船运公司的商船也陆续开始驶往上海[注]参见《外轮只顾生意经 纷自各地开赴上海》,《中央日报》(湖南)1949年6月20日。。
6月20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新闻处处长鲍静安发出正式实施封锁声明:“本月十八日起,自闽江口北东经119度40分、北纬6度15分之点起,往北至辽河口东经122度20分、北纬40度20分之点止,沿海岸领区范围以内地区,暂予以封闭,严禁一切外籍船舶驶入。凡外籍船舶之违反此项决定者,中国政府即予以制止。外籍船舶因违反此项决定而遭遇任何危险,由其自行负责。目前包括永嘉、宁波、上海、天津、秦皇岛等口岸在内,禁止一切海外商运。以上各节,均经外交部分别通知各国政府,转饬遵照。”[注]《闽江口以北失陷港口 政府定期全部封闭》,《中央日报》(湖南)1949年6月22日。
换言之,国民党正式发布封锁令,实际也是对外国船运公司发出了封锁的声明。
二、“安契塞斯号”遭到轰炸以及英国的反应
6月18日,国民党空军发出了对封锁地区实施轰炸的消息,“空军预告即将出动轰炸沿海及沿江一带。一旦开始,其强烈将超过从前之记录,并将继续彻底实施”[注]《空军预告即将出动 轰炸共党作战机构》,《中央日报》(湖南)1949年6月19日。。 不仅如此,在已经开始轰炸上海工业设施的基础之上,国民党又把进出上海港的外国商船纳入轰炸范围,在上海航运贸易中占重要地位的英国船运公司船只首当其冲。
(一)对“安契塞斯号”实施的第一次轰炸
6月21日上午9点,已经迁至台湾的国民党空军派出P.51野马轰炸机,对刚从日本神户到达上海黄浦港的“安契塞斯号”进行了轰炸,附近的壳牌石油公司仓库也遭到轰炸[注]Sir R.Stevenson to Foreign Office, June 21, 1949, FO371/75921/8952;〔美〕爱德温·W.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第66页;《政府轰炸机三架 隔昨空袭上海》,《中央日报》(湖南)1949年6月22日。关于飞机的型号,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马丁的论述和《中央日报》对此事件的报道略有出入。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提到的是“P.51”,马丁在其著作中记述的是“P-51S”,而《中央日报》中则是“P151”。。 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详细报道了“安契塞斯号”遭到轰炸的经过:“昨晨九时三刻,英船‘安契塞斯号’由吴淞进口驶到高桥江面时,遭到加拿大制式匪机两架轰炸。船身有二十度倾斜,船尾浸水,英籍船员四人受伤。”[注]《匪机昨再肆虐 英伦一艘中弹受伤》,《解放日报》1949年6月22日。英商亚细亚油库公司油库损失汽油9000余吨,参见《中央日报》(湖南)1949年6月24日。《中央日报》(湖南)也报道了该事件:“6月20日,下午三时前不久,三架P151型战机对上海空袭约二十分钟,在沪市西南郊龙华机场附近投弹九枚……对英国邮轮‘安诸色施’实施了轰炸,有四人受伤。”[注]《政府轰炸机三架 隔昨空袭上海》,《中央日报》(湖南)1949年6月22日。《大公报》(上海)对“安契塞斯号”遭到轰炸亦有报道:“昨日上午八点卅五分,国民党两架飞机飞临上海……在黄浦江上投掷三枚炸弹,将英商太古公司所有的‘安基塞斯’号货船炸伤,四名船员受伤,其中一名重伤。轰炸殃及英商亚细亚汽油公司的B字火油堆栈。”[注]《匪机又飞沪扫射》,《大公报》(上海)1949年6月22日。《大公报》(香港)同日也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需要注意的是,就英国轮船“安契塞斯号 ”遭到第一次轰炸的时间,《解放日报》《中央日报》和《大公报》的报道有所不同。《解放日报》和《大公报》都是报道该事件发生在6月21日上午,而《中央日报》(湖南)则报道发生在6月20日,且未说明是上午还是下午。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发给英国驻华大使馆和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则是6月21日上午9点左右,参见Sir R.Stevenson to Foreign Office, June 21, 1949, FO371/75921/8952。
“安契塞斯号”遭到轰炸的当天,英国驻广州外交代表柯希尔(Coghill)就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注]《空军昨再空袭上海 英对商轮被炸抗议要求赔偿》,《中央日报》(湖南)1949年6月23日。。同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也向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郑天锡送出书面抗议书,声明国民党使用飞机轰炸没有武装的商船是无法容忍的,也是一种不友好行为,要求国民党对因轰炸造成的英籍船员受伤和商船财产损失予以全额赔偿,并承担全部责任[注]Sir E.Bevin to Sir R.Stevenson, June 22, 1949, FO371/75921/8952;《贝文昨接见郑天锡 对英轮事件亲送抗议书》,《中央日报》(湖南)1949年6月23日。。贝文还把该事件通知美国国务院,指出国民党的封锁政策违反了国际法;即使实施封锁,但没有事先警告而进攻一艘商船不是实行封锁的合法措施,希望美国支持英国的要求,即国民党停止对港口的封锁[注]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 June 22, 1949, FO371/75900/8972.。为了进一步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英国外交部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党空军提供航空汽油,还建议给国民党空军提供军事培训的美国军事官员对国民党空军施加压力[注]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 June 22, 1949, FO371/75900/8974.。在“安契塞斯号”遭到轰炸的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得知国民党正式发出对上海以及沿海港口实行海上封锁的消息后,就通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告诫国民党,轰炸可能会引起上海人民的仇恨,以及外国公众舆论的负面反应[注]Washington to Foreign Office, June 20, 1949, FO371/75900/8972.。事件发生后,鉴于美国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和国民党轰炸殃及美国部分公司财产,也为了回应英国政府的强烈要求,美国国务院表示,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尽管对国民党政府表示同情,但是国民党政府封锁部分港口以及相关水域不具有合法性,除非国民党政府宣布和维持有效的封锁[注]Washington to Foreign Office, June 24, 1949, FO371/75900/9263.。
(二)对“安契塞斯号”实施的第二次轰炸
虽然英国外交部和驻广州外交代表柯希尔向国民党空军对“安契塞斯号”实施轰炸提出强烈抗议,还向美国政府寻求反对国民党封锁的支持,但国民党空军还是对“安契塞斯号”进行了第二次轰炸。6月22日,国民党空军两架飞机在黄浦江附近,对已经搁浅的“安契塞斯号”进行了第二次轰炸,这次轰炸没有造成伤亡[注]Mr.Urguhart to Foreign Office, June 22, 1949, FO371/75921/9061.关于第二次轰炸,《中央日报》《大公报》和《解放日报》都予以报道。详见《对于封闭港口 美正研究官方报告》,《中央日报》(湖南)1949年6月24日;《匪机昨又肆虐》,《大公报》(上海)1949年6月23日;《安奇赛斯轮再遭袭击》,《大公报》(香港)1949年6月23日;《匪机两架 昨又来肆虐》,《解放日报》1949年6月23日。。
6月23日,英国外交部和柯希尔再次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就“安契塞斯号”遭到轰炸向柯希尔表示惋惜,并说明这一事件与封锁上海无关,是因飞行员对英国商船的旗帜不熟悉所造成[注]Mr.Coghill to Foreign Office, June 23, 1949, FO371/75921/9111.。英国驻淡水领事馆也向国民党政府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和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提出抗议。陈诚声明,国民党政府实施封锁是必要措施,希望英国和美国停止帮助中共,英国商船和军舰也不要靠近中共控制的港口,亦可以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并表示英国的商船不会再遭到轰炸。[注]Mr.Biggs to Foreign Office, July 2, 1949, FO371/75903/10821.需要注意的是,陈诚只是确认对“安契塞斯号”实施了一次轰炸,即6月21日进行的第一次轰炸,但是没有承认6月22日对该船进行的第二次轰炸[注]6月23日,叶公超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记者提出英国商船“安契塞斯号”复遭炸射的问题时,以“外交部尚未接到正式报告”予以否认。《叶公超答记者问》,《中央日报》(湖南)1949年6月24日。。在此之后柯希尔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就“安契塞斯号”事件进行的多次谈判中,国民党始终否认存在第二次轰炸。
三、英国对国民党封锁及“安契塞斯号”事件的反应
(一)不承认国民党实施的海上封锁
“安契塞斯号”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不但认为国民党空军在轰炸前没有发出警告,而且国民党实行的海上封锁也属于无效。英国驻香港总督葛量洪向英国殖民大臣提交了一份关于“安契塞斯号”事件的报告,认为国民党空军轰炸“安契塞斯号”并没有事先发出警告。英国殖民大臣也认为,虽然国民党关闭了在一些地区的港口,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宣布封锁令。[注]Sir A.Grant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June 22, 1949, FO371/75921/9170. 国民党实施有关封锁中共解放区沿海港口的政策时,权衡国际法有关实施封锁以及交战权的相关规则,所以始终坚持是“封闭”或是“关闭”,而非“封锁”,包括在“安契塞斯号”事件发生前后。英国海军部在发给外交部助理次官斯卡莱特(Peter W.Scarlett)的一份报告中认为,根据国际法的惯例,当一合法政府宣布封锁令,实际上就等同于承认了国内与其对立的“反叛一方”的交战权。同时,合法政府只是声明封锁“反叛一方”占领的港口,却不能维持有效封锁,因而该合法政府的封锁声明则是无效的。所以,英国海军部认定国民党实施的封锁只是为了获取战争权而无视国际法所规定的附加条件,这是不合法的。首先,国民党没有承认中共的战争权;其次,封锁并不是通过派遣飞机和轰炸船只来实现的。况且英国政府得知国民党正式发出封锁令之前,“安契塞斯号”已经在上海附近。[注]Mr.Cardo to Sir P.Scarlett, June 22, 1949, FO371/75921/9367.英国否认国民党实施封锁的合法性,也就否定了国民党的交战权,国民党也就无权关闭港口。[注]Sir T.Smith to Sir P.Scarlett, June 30, 1949, FO371/75932/12666.这其中既有维护英国对华船运贸易利益的初衷,又有对中国国内交战双方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海上争端的考量。英国担心交战双方若发生海上对抗,不仅会使从英国经香港到华北、韩国、日本的贸易航道中断,也可能会波及香港的安全。此外,英国否认国民党封锁的合法性,是因为其还顾及着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的安全。“安契塞斯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尚搁浅在长江,而英国与中共的谈判正陷入僵局。若是承认国民党封锁的合法性,也就意味着承认了中共的交战权,会影响“紫石英号”的安全。[注]Admiralty to Sir P.Scarlett, June 27, 1949, FO371/75932/9823.
7月5日,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郑天锡会见贝文时提出讨论有关封锁港口问题时,贝文表示拒绝讨论,坚持不承认国民党封锁政策的合法性[注]《郑天锡访贝文 谈关闭港口问题》,《中央日报》(湖南)1949年7月6日。。 7月12日,英国外交部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英国绝不遵守6月20日宣布封闭中共各港口之命令,不能认为此命令为有效”,“倘英轮船因封闭令而受损失时,应由国民政府负责”[注]《英再度提出照会 表示决不承认》,《中央日报》(湖南)1949年7月13日。。
(二)关于派出军舰进行武装护航
“安契塞斯号”事件发生后,为了保证英国商船的安全,英国政府一部分官员以及英商中华协会认为,应该对出入上海港的英国商船提供军舰护航。英国海军部主张,按照国际惯例,一国有权派遣军舰和地面部队到无法给本国侨民和财产提供保护的地区[注]Mr.Cardo to Sir P.Scarlett, June 22, 1949, FO371/75921/9367.。一份由英国海军部致内阁会议关于商船遭到轰炸的备忘录中也显示出其关于护航的态度。上海解放后,英国军舰“黑天鹅号”在上海长江出海口附近巡弋,以阻止国民党军舰干扰英国商船进出上海港。当“安契塞斯号”遭到轰炸,“黑天鹅号”前往救援时,却发现“安契塞斯号”在黄浦港内。由于中共在解放上海后就已经发出声明,没有得到允许,外国军舰无权进入上海,加之早在4月下旬发生的“紫石英号”事件的影响,这使得“黑天鹅号”不敢贸然进入黄浦港救援“安契塞斯号”,从而出现了英国商船遭到轰炸并发出紧急救助请求,但在附近的英国军舰却无法施救的局面。因此,英国海军部认为有必要修改对英国军舰的指示,即使会进入别国内部水域,但为英国航运提供救助或其他人道主义援助是军舰的职责。然而,海军部也注意到两个现实问题:一是中共上海市政府已经声明,没有得到允许,外国军舰无权进入上海;二是需要确保英国军舰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时不会遭到攻击。鉴于此,海军部认为英国政府应通知中共上海市政府,解释英国军舰实施救援的公正性,并请求中共确保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军队不会干扰英国军舰救援。英国海军部还提出了对国民党空军的反制措施,远东舰队司令命令在长江入海口附近的英国军舰在以下情形中予以反击:一是自卫时;二是国民党空军袭击无论是否在中国领水内外的英国或其他中立国商船时。[注]Memorandum by the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June 22, 1949, FO371/75921/9367.然而,无论是军舰护航还是反制国民党的袭击的提议,都没有获得英国政府同意。一方面,1947年2月,中共公开宣布外国军舰无权进入中国领水,不承认国民党与外国政府达成的有关外国人在中国领水活动的一切协定[注]Sir J.Kerans to Sir P.Brind, May 24, 1949, FO371/75892/7550.。英国驻华大使馆也持同样看法,认为英国军舰在中共声明的领水内对中国人采取行动会招致所有中国人深深的怨恨[注]Mr.Franklin to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23, 1949, FO371/75914/17349.。此外,英国与中共之间的“紫石英号”事件尚未解决,英国政府更不愿因英国军舰再次进入中国领水护航激怒中共而破坏了英国政府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建交的既定方针。
另一方面,虽然英国外交部以国际法为依据不承认国民党实施的封锁,但是英国军舰护航也因国际法就领土主权的相关规定而自缚手脚,最主要的就是不能扩大到中国领海[注]马丁:《上海解放后英国针对国民党封锁上海的对策及成因》,《史林》2016年第1期。。国民党实施的封锁范围恰恰是在中国领海之内,英国军舰若是进入中国领海以内护航,就形成了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实,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与国民党的冲突,进而可能会影响英国与中国台湾的商业贸易,甚至是英国政府在中国香港和马来亚地区的政治稳定[注]Foreign Office Minute by Mr.Franklin, February 24, 1950, FO371/83425 FC1261/48.。更重要的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重创,战后英国政府的政策重心在恢复本国经济和欧洲事务。在无更多精力关注亚洲事务的前提下,又要实现维护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目标,因此,即使英商中华协会多次请求英国政府派出军舰进入中国领海护航,英国政府都审慎地加以拒绝。
英国军舰护航无法实现,而“安契塞斯号”事件是否能顺利解决又直接关系着英国在华的航运贸易和在上海的商业利益,加之受制于自身实力所限,英国政府转而诉诸外交途径。因此,英国驻广州外交代表柯希尔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进行了多次谈判,“安契塞斯号”是否遭到两次轰炸和赔偿问题是双方谈判的焦点。
四、关于“安契塞斯号”事件的谈判
“安契塞斯号”是否遭到国民党空军两次轰炸是英国方面与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的重要内容,而“安契塞斯号”是否悬挂有标志其身份的商船旗又是双方关于是否实施两次轰炸的焦点。 6月23日,在双方谈判开始之前,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是否看到“安契塞斯号”挂有标志其身份的旗帜一事,英国驻淡水领事毕格斯(Biggs)专程前往国民党空军司令部质询此事。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解释,可能是飞行员错认了英国船只的身份,所以轰炸了“安契塞斯号”。但是,王叔铭否认了6月22日进行的第二次轰炸,称飞行员已经进行侦查,识别了“安契塞斯号”的身份,没有进行再次轰炸。[注]Mr.Biggs to Foreign Office, June 23, 1949, FO371/75921/9193.为了确认“安契塞斯号”遭到轰炸时悬挂有旗帜,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厄克特(Urguhart)向英国外交部发去报告称,经“安契塞斯号”船长证实,虽然没有在前桅杆悬挂有醒目的旗帜,但是船只在遭到轰炸前、轰炸中和轰炸结束后, 始终悬挂有4面信号旗、1面领航旗,主桅杆挂有1面公司旗(太古轮船公司),在船尾一直挂着一面3码大小的红色商船旗。遭到第二次轰炸时,“安契塞斯号”的船尾仍然悬挂着同一面商船旗,而且前桅杆也升起了红色商船旗。[注]Mr.Urguhart to Foreign Office, June 24, 1949, FO371/ 75921/ 9349.
6月25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与柯希尔进行了第一次谈判,其中谈判焦点之一就是“安契塞斯号”在遭到轰炸时是否悬挂有可以识别其身份的旗帜。叶公超提出,据相关报告,飞行员轰炸的目标船只可能载有上海需要的物资,而且飞行员也没有看到“安契塞斯号”的商船旗帜,表示愿意在收到该事件的全部报告后,根据国际法的相关条款来处理有关事宜,并表示外交部没有收到英国方面所提出的“安契塞斯号”遭到第二次轰炸的报告。柯希尔反驳叶公超说,遭到轰炸当天,“安契塞斯号”悬挂有标志其身份的红色商船旗。[注]Mr.Coghill to Foreign Office, June 25, 1949, FO371/75921/9338.鉴于双方对“安契塞斯号”是否悬挂有红色商船旗的观点不一致,英国外交部要求国民党对事件进行调查并重新给予答复。7月10日,在经过对整个事件调查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终于承认,在第一次轰炸时,飞行员误把船尾一面小旗看成是中共的旗帜而造成了对“安契塞斯号”的误炸。[注]Mr.Coghill to Foreign Office, July 10, 1949, FO371/75922/10132.
关于第一次轰炸和是否悬挂有红色商船旗帜,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以及空军司令部最初表示没有看到“安契塞斯号”悬挂有商船旗,到飞行员误把船尾的小旗当成中共旗帜而造成对船只的误炸,表明在第一次轰炸“安契塞斯号”的问题上,相比较其实行强硬的封锁政策,国民党对英国政府已经妥协。然而,无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还是空军司令部都极力否认对“安契塞斯号”实施过第二次轰炸。为了进一步证明国民党空军实施了第二次轰炸,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Ralph Stevenson)征得英国外交部同意,建议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厄克特从第二次轰炸的目击者那里收集信息,包括在岸上的人,比如壳牌公司的工作人员[注]Sir R.Stevenson to Foreign Office, July 16, 1949, FO371/75922/10544.。8月18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经过调查,收集到包括5名船员和2名附近岛上工厂的机械师在内的7份目击者的证明,证实国民党空军对“安契塞斯号”实施了第二次轰炸[注]Mr.Evans to Foreign Office, August 18, 1949, FO371/75922/15014.。然而,令英国失望的是,这在督促国民党承认对“安契塞斯号”进行了第二次轰炸的问题上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
9月5日,柯希尔再次与具体负责谈判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欧洲司司长袁子健进行会谈。关于轰炸问题,柯希尔重申了英国的立场,即要求国民党承认对“安契塞斯号”实施了两次轰炸。但是,袁子健表示外交部不愿反复提及这一问题,而且强调国民党对任何有关他们没有遵守正确法律程序的提议都很敏感,仍然否认国民党空军对“安契塞斯号”进行过第二次轰炸。[注]Mr.Coghill to Sir P.Scarlett, September 5, 1949, FO371/75922/13277.袁子健的答复让柯希尔非常失望,而更令英国政府忧虑的事情也出现了。随着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不断在南方取得胜利,国民党政府已经准备由广州迁往重庆。经过谈判,虽然国民党已经承认第一次轰炸“安契塞斯号”是由于飞行员错误所致,但是英国政府再与国民党政府纠缠于“安契塞斯号”是否遭到第二次轰炸已无实际意义,英国政府更担心国民党政府因再次迁移而无法赔偿“安契塞斯号”的相关损失。这样,英国方面就“安契塞斯号”事件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重点逐渐转移到船只以及船员的相关损失的赔偿问题。
关于“安契塞斯号”的赔偿问题是英国与国民党之间谈判的另一个焦点,也是双方谈判的重点。鉴于国民党已经承认误炸,在英国看来,国民党就应该赔偿“安契塞斯号”的相关损失。英国太古轮船公司一方面强烈谴责国民党轰炸“安契塞斯号”,造成商船受损以及部分船员受伤;另一方面,由于“安契塞斯号”受损无法移动,只能停泊在黄浦港,而上海的船厂又无法修复该船,太古轮船公司只得用拖船将“安契塞斯号”拖到日本神户的船厂进行修复。[注]7月26日,英国派出拖船前往上海将“安契塞斯号”拖往日本。国民党海军允许英国拖船进入,中共也派出船只将携带国内发往香港、日本及国外各地邮件的“安契塞斯号”拖送至长江口,后由英国“黑天鹅号”护送。参见《英准备派船拖出安琪色斯号》,《中央日报》(湖南)1949年7月22日;《安奇赛斯轮驶日修理》,《大公报》(香港)1949年7月27日。同时,太古轮船公司也无力承担“安契塞斯号”在受损期间无法担负航运任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修复该船所需的巨额费用。6月7日,太古轮船公司向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出申请,要求英国政府支持太古轮船公司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赔偿申请,由柯希尔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交涉有关赔偿事宜。太古轮船公司建议柯希尔就“安契塞斯号”赔偿事项提出如下要求:(1)海上救援和拖到上海船厂。(2)从上海拖离。(3)暂时在上海修复。(4)在某地长期修理。(5)上述所有费用以及附带费用。(6)从1949年6月21日失去动力直到重新投入商业服务期间的损失。此外,太古轮船公司要求,赔偿中应包含轰炸中受伤船员的补偿以及对“安契塞斯号”上货物的所有者的赔偿。第(1)至第(5)条的确切赔偿数额还无法估算,总额可能约是20万英镑;第(6)条要求赔偿每天600英镑的滞留费。同时,一旦赔偿评估数额得到确定,要求国民党政府发出以英镑支付赔偿的声明。[注]Alfred Holt & Co.to Foreign office, July 6, 1949, FO371/75922/10048.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收到太古轮船公司的赔偿要求后,表示愿意根据国际法的有关条款处理此事件,但是并没有正面回复赔款问题。同时,柯希尔也建议太古轮船公司不仅要提出赔偿要求,还需要提交一份有关“安契塞斯号”详细损失的评估报告,也有必要说明“安契塞斯号”因受损而无法使用的时间期限,并提供船只不能重新投入商业服务的证明。[注]Mr.Coghill to Foreign Office, July 15, 1949, FO371/75922/10515.
在英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之时,国民党政府正计划从广州迁往重庆。同时,鉴于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过程,虽然不能确认国民党会拒绝支付“安契塞斯号”的赔偿,但柯希尔认为国民党赔偿的困难在不断增加。[注]Mr.Coghill to Sir P.Scarlett, July 6, 1949, FO371/75922/10735.为了尽快获得赔偿,太古轮船公司决定对国民党施加压力,尽快提出赔款总额。8月17日,太古轮船公司向英国外交部提出赔款数额申请,维修船只费用大约需要20万英镑;由于上海船厂无法完全修复“安契塞斯号”, 太古轮船公司要求把船只拖到日本神户的船厂修理,加上滞留上海期间的费用以及其他费用,赔偿要求总额达到32万英镑。[注]Mr.Coghill to Dr.Yeh, August 17, 1949, FO371/75922/12825.面对太古轮船公司的巨额赔偿和维修要求,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表示先要对船只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后才予以答复。
不仅国民党对太古轮船公司的赔偿总额没有正面答复,就连柯希尔也对太古轮船公司提出的赔款数额不是完全赞成。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即将准备再次迁移,与国民党谈判的时间已经不多,而目前太古轮船公司又无法准确评估损失和滞留费用。根据柯希尔的建议和中国革命发展形势以及中英双方的谈判情况,经过内部讨论,太古轮船公司再次向英国外交部提交了赔偿数额请求,基于对维修和滞留费用的评估,希望国民党给予“安契塞斯号”所遭受的预期损失的一半,即16万英镑。[注]Mr.Coghill to Dr.Yeh, August 17, 1949, FO371/75922/12825.由此可见,无论是太古轮船公司还是柯希尔都认为国民党不会对“安契塞斯号”予以全额赔偿。为了尽快使受伤船员得到赔偿以及商船得到修复可以尽早重新投入使用而减少公司的损失,英国方面不得不降低赔款数额要求来督促国民党尽快支付赔偿。然而,当9月5日柯希尔与袁子健会谈时,袁子健声明,只能赔偿 “安契塞斯号”的直接损失。虽然柯希尔认为,既然国民党已经承认是由于失误而造成对“安契塞斯号”的误炸,国民党就应该对此事件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袁子健的表态再一次让英国方面对获得赔偿感到失望。此外,“安契塞斯号”事件发生后,原本英国国内公众就已经对政府表示不满,要求英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若国内民众获悉国民党政府只是赔偿有限的直接损失,英国政府担心会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批评。[注]Mr.Coghill to Sir P.Scarlett, September 5, 1949, FO371/75922/13277.
面对国民党政府坚持只赔偿直接损失,英国外交部提出,因误炸而造成的直接损失的赔偿,应包括对财产和个人所造成的实际损害,以及可以证明的因轰炸而造成的特殊损害;按照国际惯例,对于船只滞留期间的滞留费的赔偿则是必需的[注]Sir P.Scarlett to Mr.Coghill, September 25, 1949, FO371/75922/13277.。太古轮船公司也质疑国民党的答复,请求英国外交部尽最大努力要求国民党接受太古轮船公司提出的赔偿要求,能尽早收到赔款。9月23日,为了督促国民党尽快支付赔款,太古轮船公司把一份详细的赔款清单提交给英国外交部,由英国外交部转交给国民党政府。赔款清单包括各项直接、间接的赔款明目和赔款数额,以及遭到袭击后从在上海黄浦港停泊至前往日本神户船厂期间的滞留费,并委托太古轮船公司驻香港公司代表与柯希尔继续协商赔款数额事宜。[注]Alfred Holt & Co.to Foreign Office, September 23, 1949, FO371/75922/14435.10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到重庆,太古轮船公司的赔偿要求依然没有解决。英国驻重庆总领事吉勒特(M.C.Gillett)也多次就赔款事宜与国民党政府协商,但是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答复。更让太古轮船公司焦虑的是,该公司已经垫付了“安契塞斯号”在上海船厂期间和在日本神户船厂的部分费用,急切希望国民党政府尽快支付船只的赔款以减轻太古轮船公司修复船只的经济负担。[注]Mr.Gillett to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14, 1949, FO371/75922/17974.
国民党政府准备迁都到广州之际,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遵照英国政府指示继续留在南京。同时,英国政府要求驻北平、天津等地领事馆在解放军进城后继续开放。此外,英国外交部让施谛文以信件方式通知北平和天津领事,让他们向中共地方政府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并直至局势明朗前,英国愿意在事实的基础上与中共来往[注]陈少铭:《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3期。。英国此举引起国民党的强烈不满。南京解放以后,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正忙于作战,已经无暇顾及英国政府以及太古轮船公司的赔款要求。虽然国民党已经承认对“安契塞斯号”的误炸,但是并没有放松海上封锁。即使面对英美提交照会抗议,国民党仍在不断强化其封锁政策。7月1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通过有关截断海上交通的办法:“政府对关闭共区港口政策,并未因英美之抗议而有所考虑,决定采取积极而又强硬之措施,继续加紧执行。行政院于一日晚特举行行政会,通过了《截断匪区海上交通办法》。”[注]《关闭共区港口政策,政府绝不考虑》,《中央日报》(湖南)1949年7月2日。“截断办法”内容共有14条,“由国防部命令海军司令部负责执行,空军司令部协助办理”。
由于国民党海上封锁的不断加强,英国与国民党间就航运贸易的摩擦也在不断升级。“安契塞斯号”事件发生后,又有多艘前往上海的英国商船相继遭到国民党海军扣押或驱离,导致英国船运公司与上海以及附近港口的船运贸易不断下降,也影响了英国在远东地区的贸易发展。就英国政府和太古轮船公司对“安契塞斯号”事件的政策来看,英国政府认为既然国民党承认对“安契塞斯号”存在误炸,就应该赔偿相应的损失。然而,鉴于国民党对赔偿问题的消极态度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更为了维护英国在华的巨大经济利益以及英国在远东贸易的正常开展,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降低英商在华企业的损失,积极寻求美国政府的合作以反对国民党的海空封锁。[注]马丁:《上海解放后英国针对国民党封锁上海的对策及成因》,《史林》2016年第1期。
五、结 语
1949年6月发生的“安契塞斯号”事件是国民党实行海上封锁期间的一次重要事件,是国民党实施海上封锁和强化封锁效果的一次“实验”,也是英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一次正面冲突,该事件严重影响了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首先,相比对“紫石英号”事件的克制态度[注]详见王建朗:《衰落期的炮舰与外交——“紫石英”号事件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英国政府对“安契塞斯号”事件以及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反应强烈,一方面公开对国民党空军实施轰炸以及所造成的商船损失和船员受伤提出强烈抗议,并根据国际法相关规定和太古轮船公司建议,要求国民党予以道歉并对商船损失以及附加损失给予全部赔偿;另一方面,为了反制国民党的封锁和保证出入上海港英国船只的安全,一部分英国政府官员和英商中华协会提出军舰护航的要求,英国外交部积极寻求美国的合作,要求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空军施加压力,以防止国民党再次对出入上海港的外国船只进行空袭。然而,由于多种因素所限,均未能实现英国的目标。
其次,“安契塞斯号”事件以及国民党的海上封锁直接冲击了英国在上海和远东的商业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对外政策重点在欧洲,其在远东地区的目标主要是维护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商业利益,尤其是经香港与中国各沿海港口、韩国、日本等地之间的船运贸易。 解放前夕的上海是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和主要的进出口贸易港口,有大量外国商业公司、团体聚集在此,其中尤以英国为甚。1946年,英国船运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26%,而上海的对外贸易则相当于中国所有其他港口对外贸易的总和。[注]Ministry of Transport minute, August 2, 1949 , FO371/75920/11916.英国在华投资居各国之首,达3亿英镑,其中1.9亿英镑集中在上海[注]W. Strong to Prime Minister, 1949-7-29. PREM 8/943, P.R.O., London.。由于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国内陆路运输还无法恢复,所以海上航运对于上海经济恢复与发展和英商企业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安契塞斯号”事件以及国民党不断加强的海上封锁,阻断了英国企业与中国大陆沿海港口之间的贸
易往来,打乱了英国政府维护其在华商业利益的计划,这是英国政府以及在华企业所无法接受和容忍的。
最后,“安契塞斯号”事件也反映出英国这一时期对华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受制于自身实力所限,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事件发生后,虽然英国政府以及英国船运公司强烈谴责国民党对“安契塞斯号”的轰炸,要求国民党道歉、赔偿,也否认国民党封锁政策的合法性,但是就“安契塞斯号”事件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过程中,既受中国解放战争以及英国拟承认新中国的影响,又遭遇了国民党的消极对待,甚至联合美国反制国民党的封锁也因美国的“不干涉”和朝鲜战争的爆发而无果。然而,“安契塞斯号”事件并没有恶化英国与国民党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英国在台湾的淡水仍保留“领事馆”,借口处理地方事宜,强调“只与台湾省政府保持事实接触”,而不与“中央机关”发生联系。[注]王建朗:《台湾法律地位的扭曲——英国有关政策的演变及与美国的分歧(1949—1951)》,《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此外,英国商业团体看重与台湾贸易对英国在东南亚经济利益的重要作用,以及台湾与香港贸易往来对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英国对华政策的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