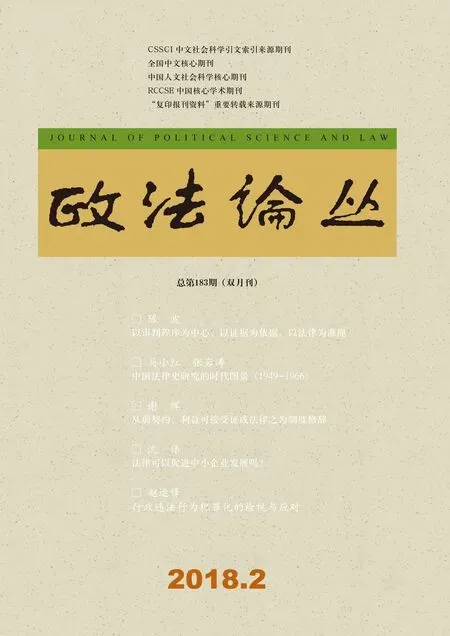“德主刑辅”说的学说史考察*
李德嘉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5)
引言
儒家关于德刑关系的思想是中国法律史上的重要命题,深刻影响了传统法的特点和发展。儒家德刑关系思想渊源于西周人所提出的“明德慎罚”的主张。先秦儒家继承了西周的“礼治”传统,他们坚持以德礼教化的方式来治理社会,警惕过度运用刑罚手段而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西汉时期的思想家董仲舒对德刑关系思想的阐释最具有代表性。董仲舒针对于汉初的弊政,提出了其“任德不任刑”的政治法律主张,将德与刑之间的关系比喻为“阳德阴刑”。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德礼为本、政刑为用”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唐律疏义》的作者将这种德刑关系概括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二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现代学者常以“德主刑辅”来概括和总结古代儒家的德刑关系思想,并且认为中华法系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德主刑辅”。检讨近百年来法律史学界关于“德主刑辅”说的研究发现,学者们对于“德主刑辅”说的内涵解读并不一致。有学者从道德与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关系角度来理解“德主刑辅”,认为古代社会主要依靠德礼教化进行统治,法律在其中起到次要的作用。[1]另有学者从儒家“德治”的角度出发,认为法律不过是辅助“德治”实践的工具。[2]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都将古代的“刑”理解为法律,从而得出了古代社会轻视法律作用的结论。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陷入一种悖论:为什么奉行“德主刑辅”的中国古代社会会有如此发达的律令体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当‘中国法律思想史’教科书将‘德主刑辅’作为中华法系主导思想时,‘中国法制史’的教科书却把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主线定位在‘以刑为主’‘重刑轻民’上。”[3]
确切地说,“德主刑辅”是现代人对古人思想观念的概括和总结,古人在现存的主要文献和典籍中都不曾将自己关于“德刑关系”的思想总结为“德主刑辅”。①董仲舒所说“刑者,德之辅也”②,往往被现代学者视为“德主刑辅”思想的史料依据,但是,关于“德”与“刑”的内涵关系解说,学者们却莫衷一是。如果深入研究古代儒家德刑关系思想就会发现,古代的德与刑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儒家的“德”观念内涵丰富,不仅规定了政治的正当性基础,还代表了一种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时我们发现,儒家所理解的“刑”常与“政”连用,意味着一种依靠强力的统治方式。如果与现代的法相比较,儒家的“刑”更接近现代法理学中所说的“命令”。儒家所主张的“德礼为本,刑政为用”的德刑关系思想实际上具有社会治理模式的意义,目前的“德主刑辅”说并不能够很好地诠释古代儒家德刑关系思想所具有的深刻内涵。 欲对古代儒家德刑关系思想作出新的诠释,需要我们回溯“德主刑辅”说的学术源流,对其产生的话语背景和思想脉络进行梳理。
一、“德治-法治”话语背景下产生的“德主刑辅”说
(一)以“德治主义”概括儒家的政法思想
近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特点是以西学的话语来定义中国古代思想,又以依照西学话语定义过的中国思想来比附西方的学术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德治”视为“法治”的对立物,就成为学界的通说。
考诸古籍,“德治”一语并非古人自己的表达,而是近代学者对古代儒家式社会治理模式的总结。比较早的以“德治”来概括总结古人的治理模式的是王国维,他在《殷周制度论》中将西周的典礼制度均概括为“道德之器械”,从而指出“德治”“礼治”是周人的治国之根本。他说:“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是周制刑之意,亦本于德治、礼治之大经;其所以致太平与刑措者,盖可睹矣。”[4]P451由此可见,在王国维看来,所谓“德治”“礼治”其实本质皆为“道德之器械”,也就是制度化了的道德伦理规范。与王国维将“德治”简单视为“道德之器械”不同,梁启超也在其著作中将儒家的政治思想概括为“德治主义”,在他看来,儒家之“德治主义”与“人治主义”实是同一意思。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梁启超所言人治,与今日作为法治对立面的人治并不相同,梁启超所言的人治或德治颇有社会自治的意义。他说:“儒家深信非有健全之人民,则不能有健全之政治。故其言政治也,惟务养成多数人之政治道德、政治能力及政治习惯。”[5]P98可见在梁启超认为,儒家“德治”并不是将统治的希望寄托于一二贤君在位,而是认为政治的关键在于通过教化培育百姓的自治力。
梁启超关于儒家“德治”内涵的解读并未将其与法治相对立,可惜后世学者关于“德治”的研究中却很少有人注意梁启超关于儒家“德治”思想在培育民间自治力方面的意义。相反,梁启超关于先秦政治思潮的简单分类却影响甚巨,尤其是其标签式、概括式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学者往往径直借鉴梁启超“德治”、“人治”、“法治”的思想分类方法而忽略了其实质内容。这种以“人治”和“法治”的简单对立来概括儒法两家政治法律思想之不同的分析方法对后世思想界、学术界影响巨大,尤其是对法学界的影响尤为明显。④比如,民国时期的法理学家王振先在其《中国古代法理学》一书中就直接承袭了梁启超关于“德治”、“法治”的分类。王振先在其书中将法家之说列为法治思想而大加提倡,并将许多历史上的法家人物都列为弘扬法治的先驱,全然不顾获得汉人司马迁“刻薄寡恩”之评价的法家其实与现代以自由、正义为内涵的法治格格不入。法家之“法治”的对立面就是儒家的“人治”论、“德治”论。在此基础之上,王振先将我国法治不发达的原因全部归结于“独尊儒术”之上,不仅儒家之“人治”思想受到批判,连汉儒注解的律学思想也被认为是“皆属望文生义,从事解释,非复战国法家之旧。”[6]P49
在法律史学界,以“德治”-“法治”相互对立的研究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瞿同祖、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曾经这样阐释儒家的“德治”思想:“儒家既坚信人心的善恶是决定于教化的,同时又坚信这种教化,只是在位者一二人潜移默化之功,其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同德治主义又衍为人治主义。所谓德治是指德化的程序而言,所谓人治则偏重于德化者本身而言,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7]P232
瞿同祖认为,儒家“德治”的关键是由统治者对百姓自上而下实施教化,此种教化之所以能够得到实现,根本在于最高统治者自身的人格具有高度的道德感召力。因此,在瞿同祖看来,儒家的“德治”思想实质上存在着“人治”的危险:社会治理的根本在于最高统治者的道德感召力是否足以教化万民。“德治”与“人治”其实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教化的过程而言是德治,而就德治的本质而言则需要依赖人治的实现。瞿同祖关于儒家“德治”思想的认识是十分典型的,代表了近代学者关于儒家“德治”思想的主要看法。比如,民国法律学者王伯琦在《法治与德治》一文中说:“实则在我们的传统思想上,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重要的还是表现在人治与法治上面的。人治与德治是相通的,讲人治亦就是讲德治。”[8]P104同样持此见解的还有同一时期的杨乃昌,杨乃昌认为,与“礼治”相辅而行的是“德治”,而这种“德治”或“礼治”的极致就是“人治主义”。⑤
(二)杨鸿烈首提“德主刑辅”说
首先提出“德主刑辅”说的是法律思想史学科体系的奠基者杨鸿烈,其在《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第四章“儒家独霸时代”中单列一节来梳理总结历代关于“德刑关系”的思想,并精炼地将古代儒家德刑关系思想概括为“德主刑辅”。杨鸿烈认为,古代关于德刑关系的思想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儒家所提出的“德主刑辅”说,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德主刑辅”的思想实际上源自于先秦儒家:“德主刑辅是春秋孔子、战国孟子以来儒家一贯相承的学说。”[9]P12在杨鸿烈看来,“德主刑辅”是儒家“礼治”思想的一部分,所谓“礼治”,更多的就是强调德礼教化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他说:“法吏坚主‘法治’,法足以应时代的要求……差不多都是衍战国时代法家的余绪。但经这一场大论战之后,两千年以来就算有很少主持‘法治’的人,但已非法家的真面目,所以还是儒家的‘礼治’或‘德主刑辅’说最为得势。”[9]P35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杨鸿烈始终是在以儒家的“德治”思想来分析历代的“德主刑辅”说,“德主刑辅”是儒家“德治”或“礼治”的核心表现。如果系统分析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书中所梳理、罗列历代关于“德主刑辅”的讨论,我们发现杨氏罗列的所谓“德主刑辅”说的资料主要是中国古代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讨论,基本都是儒家关于道德教化之重要性的议论。可见,杨鸿烈所谓“德主刑辅”的实质是在国家治理中将法律作为道德的辅助工具,古代关于德刑关系的争论其实是古人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思考。
杨鸿烈认为,“德主刑辅”是儒家“礼治”思想的一部分,所谓“礼治”,更多的就是强调德礼教化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礼治”无非“德治”的代名词,从某一角度而言也可以称之为“人治”,因此,“礼治”从来都是作为“法治”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从治理方式来看,“德主刑辅”就是所谓“德治”,主要是以“德化”或是“德教”的方式管理社会,而不是以法律的规范来统治社会。而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德主刑辅”意味着道德和法律的混同,法律的目的在于实现道德,而道德则是更重要的法律。归根结底,杨鸿烈关于“德主刑辅”说的解读核心原因在于其对儒家“德治”观念的简单化理解,不仅将儒家的“德治”混淆为“礼治”,而且将“德治”的实践简单化为“道德教化”。有了这些误解,那么进一步得出“德主刑辅”说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结论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如果说杨鸿烈首次在其教科书中明确了“德主刑辅”说所包含的思想内涵和范畴,指出了“德主刑辅”说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思想的重要部分。而瞿同祖则系统地论证了儒家“德治”思想的理论结构,并且将其与法家的“法治”主张进行相对应的比较分析,因此影响也就更为深远。瞿同祖于其书中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框架已经成为现在大陆法律史学界教科书中的主流见解,甚至深刻地影响了教科书的基本结构和写法。⑥
(三)“德主刑辅”说的内涵与层次
杨鸿烈与瞿同祖的理论框架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以来的法律史学者对于儒家德刑关系思想的研究。近百年来的学者基本将儒家德刑关系思想定位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范畴,甚至是教化与刑罚的关系范畴,“德主刑辅”遂成为学界理解儒家德刑关系思想的通说,也被认为是中华法系的主要特点之一。综合学者们对“德主刑辅”的分析解释,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种观点,细究之下这两种对“德主刑辅”的理解和概括却相互对立,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在许多论著中,对“德主刑辅”的不同理解经常同时存在,并且缺乏一种合理的解说。
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德教为主”说。该说将“德主刑辅”简单理解为“德教”与“刑罚”孰轻孰重的讨论,认为“德主刑辅”说的思想实质是主张道德教化在社会治理中具有比刑罚更为积极的作用。在这类研究中,以张国华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张国华在其《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中将“宽猛相济、德主刑辅”看成是孔子“德治”思想的体现之一,他说:“在儒家看来,教化可以‘防患于未然’,可以起到严刑峻法所不能起的作用:既能麻痹人民斗志,又有利于使统治阶级的思想比较迅速地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10]P185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张国华虽然认识到了“德主刑辅”思想有促进刑法思想向纵深发展的一面,但是仍然强调“德主刑辅的说教却往往产生轻视法律(主要是刑法)的副作用”[10]P186。“德主刑辅”思想抑制法律发展的观点对法史学界影响深远,比如何勤华、陈灵海的新著中就指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道德文化占有如此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从而导致中国古代的法律丧失了其独立性,法律成为了道德的附庸和体现。”[11]P39
第二种理解可以称之为“德政为主”说。该说认为,所谓“德主刑辅”就是要求统治者首先实施“德政”,重视百姓的要求,以民为本。杨鹤皐在著作中就将儒家尊重民意、以民为本的种种思想列为“德主刑辅”思想的重要内容。[12]P203龙大轩也指出,德主刑辅思想从广义上说是一种治国方略,在政治上要求德政,主张为政以德,在经济上强调富民养民。[13]台湾学者耿云卿的观点独树一帜,认为儒家“德主刑辅”的思想接近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他认为在西方自然法思想中,法律不论如何发展,始终脱不出宗教及伦理的范畴。而西方自然法思想中的正当与善的概念,都属于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说的道德教化范畴。因此,可将“德主刑辅”的思想与西方自然法思想加以比较。[14]P55
二、近代误读儒家“德”观念的内在逻辑
(一)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思潮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近代衰落之原因乃在于文化的劣根,而中国文化的精神象征就是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因此,一场针对儒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就此展开。激进的知识分子将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认为孔子所代表的“孔教”是压制中国二千年精神发展、文明进步的罪魁祸首,他们认为在儒家所提倡的“礼教”的外衣之下,所掩盖的是文化压制和吃人的道德束缚。因此,要建立“新道德”、“新文化”,首先就需要对儒家所提倡的“旧思想”、“旧文化”作彻底的批判。而在对儒家的批判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儒家所提倡的“礼”,在激进知识分子那里往往称之为“礼教”。1919年,“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礼教与吃人》一文,将儒家之“礼”视为精神枷锁的“礼教”,作为吃人文化的典型。自此之后,激进知识分子便开始了对儒家“礼”的思想的彻底批判。
在这场“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中,对于儒家的理性批判并没有占据运动的主流,而是采取了一种否定性的立场,将儒家及其“礼治”、“德治”思想视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思维工具。孔子和儒家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更多地成为了“专制”、“封建”和“旧文化”的象征。在否定儒家以及传统文化的思潮之下,人们很自然地将儒家的一切都视为专制的、人治的。包括儒家所提倡的“德”,也很少有人能以公允的态度来进行审视,人们对儒家“德”观念的想象就是作为“人治”思想而存在的典型的“德治”文化,给人们所造成的印象是:统治阶级高高在上,不仅手握一切权力,而且拥有先天的道德优势,草民则是天然愚昧而且是无“德”的,因此,需要统治阶级的教化。
另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派以新启蒙者自居的学者,自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掀起了对儒家文化的彻底批判。其中最为主要的人物是陈伯达,他说,要“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15]有学者指出,这些以新启蒙运动自居的学者修正了原本胡适“打孔家店”的主张,将原本在理性整理国故基础上对传统文化的温和批判变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表现为偏执和非理性。[16]
在从新文化到新启蒙的近代思想演变过程中,学者们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态度逐渐趋于激进,理性的因素远远小于全面否定的声音,最终导致了近代学术界对儒家思想的彻底批判和否定,并且对后来的学界影响甚深。以上种种因素都造成了学者们对于儒家“德”观念的简单化和标签式的理解与否定。
(二)以西方为参照物的学术想象
近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特点是借用西方的概念构建理想的类型体系,来衡量、分析中国古代的人物与思想,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概念打造的体系框架相匹配。有学者将这样的研究风格形象地比喻为“洋货观照下的故物”。[17]近代学者将儒家概括为“德治主义”,而将法家概括为“法治主义”,这种“德治”与“法治”相互对立的概念本身就是西方的。近代学者以西方的概念体系来对照中国传统,同时又以中国的传统概念来附会西方的思想,其背后所反映的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即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进而寻找出中国文化传统上的落后之处。这种比较所产生的结果无非两种:一是将中国历史上某种思想附会西方近代的概念体系,以证明中国古代早有此文化因子,比如将法家关于法律适用的主张附会为“法治”,然后大加颂扬;二是对自己传统思想中与西方思想相异者妄自菲薄,进行否定,儒家的“德治”思想就是在这种研究思路中被加以否定的。
在西方参照物的观照下,学者们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出“法治”的因子,这时,中国古代经常谈论“法”的重要性的法家思想就被抬了出来。比如,梁启超就在《管子传》一文中认为:“故不问为立宪、为专制,苟名之曰国家者,皆舍法治精神无以维持之,盖为此也。管子以法家名,其一切设施,无一非以法治精神贯注之。”[18]P1858梁启超的观点颇具有代表性,此法治观实际上就是将“法治”简单理解为以法治国。自梁启超之后,将法家言论误认为“法治”遂在近代学术界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见解。⑦
而关于“德治”的误解,将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概括为“德治”的观点则不仅仅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参照物的观照下所进行的创造,更是受到了西方汉学界的影响。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传统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一个“一个伟大的儒家政治虚构,即德治的神话”,所谓“德治神话”在费正清看来,就是皇帝通过个人德行来影响群臣及天下百姓,然后对愚顽不化者进行刑罚。⑧需要注意的是,费正清敏锐地注意到了,古代中国的外交秩序其实也是依靠“德治神话”来维系的,即天子依靠德行感化番邦使其臣服于文明中心,因此,这些国家在中国国力衰弱时也能维系表面上的服从关系。[19]P93费正清关于“德治神话”的理解可以代表海外汉学对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主流看法,将儒家德教的方式解释为君主通过树立个人道德榜样来使百姓臣服,符合海外汉学界对中国古代皇帝兼具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的集权主义想象。美国学者列文森甚至认为儒家之“德治”只是对君主统治道德合法性的粉饰,他说:“当一个王朝还能正常运作时,他们便为王朝的君主们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但这也将掩盖统治的真实基础。”[20]P60以费正清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开展的中国儒学与历史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思路被学界称为“冲击-回应”论。有学者认为此种思路具有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传统的弊病,试图以西方为参照物分析出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落后的,本质都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21]P210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下,费正清等学者将中国传统政治法律视为一种封闭、迟滞的体系,只有在面对西方巨大的冲击之下,才会被迫作出回应。
以西方中心主义为视角的研究进路其实是一种他者的想象,即将中国的文化传统视为与西方截然异制的他者,并且按照西方的“现代”观来衡量中国文化传统,认为其是封闭和僵化的体系,中国传统的“德治”政治要想走入现代的世界,必须依赖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中国近代学者以西方为参照物对本土政治法律传统所进行的研究,也无非是要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结构中找到符合西方“现代”法治标准的因子,或寻找“阻碍”中国政治法律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文化根源。近代中国学者对本土法律传统的研究在不知不觉间走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路径,总是试图以西方的“现代”观念为标准解构中国“传统”,其结果自然是削足适履的。无论是西方汉学界的“冲突-回应”论,还是中国近代学者以西方为参照物的研究进路,实质上都是以西方的政治、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衡量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治理模式,两者合力完成了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视角下的“德治”想象。
将法家附会为西方意义的“法治”而将儒家之“德治”视为“人治”的结果是,“国家本位”的法家思想被弘扬,儒家思想被遗弃,并被彻底否定。法家“法治”观的基础是“国家本位”的,法家主张为了“富国”、“强兵”而不惜压抑个人的价值,章太炎批评法家是“能令其国称娖,而不能与之为人……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22]P115近代学界选择了“国家本位”的法家学说,既是当时“重国家,轻个人”的政治思潮的反映,同时,选择法家思想也促进了“国家本位”思想的滋长。而以“忠恕”、“中庸”为核心价值的先秦儒家学说,从根本上来说重视对人伦与社群的维护,“富强”对于儒家而言,则为保障人民之手段。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近代学界,以实现国家富强为目的的法家“法治”思想显然更容易博得时人的青睐。
三、近代“德治”论之得失及“德主刑辅”说的不足
(一)近代“德治”论之得失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所作的关于儒家是“德治主义”、“人治主义”,而法家是“法治主义”、“物治主义”的分类对近代学界影响深远,以至于近代杨鸿烈、瞿同祖等学者均将“德治”视为“人治”之代名词,而与“法治”对立,此观点自近代以来遂成为不刊之论。⑨
虽然,梁启超首倡“德治”、“法治”相对立之观点,但是梁氏并未简单弘扬法家之“法治”,一味地贬损“德治”。梁启超关于儒家之“德治”实有独到之见解,儒家之所谓“德治”和“人治”并不是简单将政治之兴旺寄托于圣君明主的身上,而是希望君主能履行教化之责任,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和自治能力。因此,梁启超说:“儒家固希望圣君贤相,然所希望者,非在其治民莅事也,而在其‘化民成俗’”。[23]P99可见,梁启超所理解的儒家“人治”或“德治”核心在于养成全民的政治道德,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公民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儒家之“德治”与现代法治并不冲突,反而可以成为法治之补充。
梁启超关于“德治”、“法治”相对立的观点是一种典型的类型化研究,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晚清以降的学界往往有一种类型化的研究倾向,学者们喜欢不断地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分类、概括、抽象,然后以西方的概念进行类比和归纳,甚至是贴标签。类型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华法制相较西方而言的异质性,然而法律传统中的鲜活个性和时代特征也往往因此受到遮蔽。[24]比如,梁启超就以先秦每个学派的政治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为立脚点,从而精炼地归纳概括各学派的实质内涵。因此,他根据儒家重视“德化”,强调人民政治习惯养成这一特点将儒家的本质概括为“人治主义”(或称“德治主义”、“礼治主义”),同时,他又抓住法家是使“人民惟于法律容许范围之内,得有自由与平等”这一关键将法家思想概括为“法治主义”。类型化的归纳总结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将复杂的历史中的思想在西方概念的类比之下所总结出的所谓“特征”往往有以偏概全之弊。显然,近代以来的学界就对梁启超“德治”-“法治”的类型化研究进行了望文生义的理解,从而将儒家之“德治”与现代法治相对立,甚至认为“德治”就是“人治”。
近代学界关于“德治”的最大误解在于将儒家之“德”错误理解为道德,从而认为“德主刑辅”的意义就是在治国的方略中以道德为主要的治国手段,法律只是推动道德实现的辅助工具。事实上,西周以来政治军事原则和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中就包括了“德”与“刑”两种基本的方式,一手软,一手硬,“德”是对臣服的百姓示以怀柔的一面,而“刑”则是以“硬的一手”对反叛者进行镇压。例如,《左传》中这样来定义“德”与“刑”之间的关系:“伐叛,刑也;柔服,德也。”⑩又有所谓“御奸以德,御轨以刑。德刑不立,奸轨并至”的说法。“德”与“刑”由西周以来所代表的怀柔与征伐的两种政治原则,发展为两种社会治理模式的象征。这一重要转变是从先秦儒法的思想争鸣中开始的。先秦儒法两家关于“德”与“刑”的对立,代表了两种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政治理念的治理模式的差异。透过儒家对“德与力”、“王与霸”的不同价值判断,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儒家在“德”与“刑”这两种不同政治原则间的取舍,此种与传统“德”观念相表里的政治原则对汉代以后的政治思想及社会治理模式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始终坚持从政道与治道的正当性角度阐释“德”观念的进路,并且加以体系化和复杂化,使西周时期的“德”观念成为儒家政治法律思想中的核心理念。就政道而言,儒家以“王道”思想阐释德政的基本框架;就治道而言,儒家以仁政充实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以礼乐作为德教的基本方式,形成了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治理模式。汉儒在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中充分借鉴儒法之争中“德”与“刑”的重要思想并且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而有所取舍,最终采取儒家“德治”理念为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同时工具主义的态度发挥法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了“德本刑用”的社会治理模式。
就近代以来关于“德治”的研究而言,学术界对于古代德治模式基本局限于从道德层理解立人之“德”。目前对德治的研究尚无法回应学界对于德治的如下批评:一是将统治之得失寄托运于君主个人的德行上,其本质是一种人治;二是传统德治的道德治国模式无法回应现代法治所带来的冲击。儒家之“德”实为判断统治者及其统治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规范性依据。从政治正当性的角度看,儒家之“德治”不仅与现代法治不冲突,甚至可以为形式主义的法治观提供形而上的德性基础。
(二)从“德主刑辅”到“德本刑用”
学界对“德主刑辅”说的不足之处,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质疑。其中,最有力的见解是,学者指出了“德主刑辅”说的问题在于对古人“德”观念的理解不够准确。 “德”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是一种统治方法的体现,更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德主刑辅”在古代社会的意义在于为法之善恶提供了判断的标准,即以儒家之“德”中所体现的社会善恶观、道德价值观来评判现实法的善恶。[25]所谓的“德主刑辅”说未能很好地把握“德”观念的实质,因此产生了研究视角单一的问题。对于“德主刑辅”的解说,学者主要在法律与道德关系范畴来讨论“德主刑辅”,因此不难得出古代社会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的结论,也会产生传统社会不重视法律的印象。事实上,儒家“德”观念包含了深刻的政治内涵,其主要意义在于指出统治之“德”是政权正当性的基础,儒家理想的统治建立在有德的统治者所实施的“德政”之上。儒家之“德治”并非期待圣君明主对群氓实施教化,而是对统治者的德性提出了规范性要求,统治者不仅要施德政,更具有进行德教以提高百姓自治力的道德义务。
从古代“德”与“刑”的观念本身所具有的内涵意义入手,进一步对儒家的“德刑关系”思想进行研究来看,儒家对于德刑关系的认识并非从统治的手段上来说明德与刑的比例关系,而是从社会治理模式上提出“德治”,同时借鉴先秦法家“刑治”主张中的合理成份。大一统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虽然可以说是“礼乐刑罚综合为用”,但是“德”与“刑”并不是“主”与“次”的比例关系,“德”与“刑”不仅地位不同,而且功能性质根本不同,“刑”在大一统时期已经简化为一种手段,而“德”则不仅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在德与刑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德治”才是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刑”只是在“德治”模式下所运用的具体社会调整方式。从功能性质上看,“德”是政治之本,规定了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和统治的基本精神,而“刑”则是政治之用,在推行“德治”的基础上,配合以“刑”的手段。陈顾远曾经指出:“在中国法系之形成方面,如就其系统性之建立而言,可知由法家创造其体格,由儒家赋予以灵魂也。”[26]P99因此,简而言之,不妨将大一统时期的德刑关系概括为“德本刑用”,只有将“德”置于“本”的位置才能真正认识古代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
以“德本刑用”来认识古代儒家德刑关系思想的实质,关键在于从社会治理的角度重新发现“德”在社会中的作用和价值。儒家以德化厚风俗、正人心的努力实际上增进了民间社会的自治能力。传统社会的治理依赖具有儒家价值观念的乡绅在民间通过“化民成俗”的德教实践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念和共识,率领百姓在民间社会形成乡里互助和共济的自我管理机制,这些举措都足以促进民间社会自治力量的良好发展。从社会治理创新的角度看,儒家“德本刑用”的社会治理思路与现代法治并不矛盾,德治完全可以成为法治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有力补充。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共识并不能单纯依靠国家立法所主导的建构主义法治所形成,法治社会中社会共识的形成同样需要良好的道德基础和制度环境,这需要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融合社会与道德的双重作用。法治建设需要以道德培育为基础,在道德教育中增加法治内涵,通过道德教育培育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
注释:
①笔者曾于“汉籍全文资料数据库”以“德主刑辅”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但一无所获。“汉籍全文资料数据库”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开发的中文全文数据库,一共收录历代典籍六百七十多种,囊括了《十三经》与《二十四史》等重要典籍。资料库网站地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②《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③梁启超在其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将先秦的政治思潮分为四种,分别是:道家的“无治主义”,儒家的“人治主义”或称之为“德治主义”、“礼治主义”,墨家的“天治主义”与法家的“法治主义”或称之为“物治主义”。
④有学者根据梁启超的分类方法而将先秦的政治思想分为四类:德治主义、法治主义、无治主义、人治主义。参见:李绍哲:《儒家德治主义与礼治主义述略》,载于《青年与战争》,第四卷第10期,1934年。
⑤参见杨乃昌《礼治主义与法治主义》,《新动向》第93期,1934年。
⑥从教科书的编纂体例和结构框架看,大陆法律史或思想史教科书是杨鸿烈式的,基本为编年史或思想家的人物谱,而瞿同祖于其书中提出的“法律儒家化”和“引礼入法”等问题则是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无法回避的。
⑦比如民国学者孙彼得就在《我国之法治精神》一文中将道家归为无治,墨家归为天治,而认为儒家颇似教育家,主张人治,采感化主义,只有法家思想最有法治意味,采干涉主义,为实行之政治家。参见:孙彼得:《我国之法治精神》,载于《震旦法律经济杂志》第1卷第2-3期,1944年。
⑧Fairbank, John K. Senate Testimony on China, March 1966.
⑨已有学者讨论了梁启超“德治-法治”的分类对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所起到的误导作用,瞿同祖为解释结构的意义专门举出儒家与法家来论证,其分析框架直接来自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参见姜金顺:《在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以瞿同祖为中心的阅读史个案:1934-1965》,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⑩ 《左传·宣公十二年》。
参考文献:
[1]张晋藩.中华法系特点探源[J].法学研究,1980,4.
[2]钱逊.先秦儒法关于德刑关系的争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
[3]马小红.中华法系中“礼”“律”关系之辨正——质疑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某些定论[J].法学研究,2014,1.
[4]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6]王振先.中国古代法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
[7]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民国丛书”第一编第29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
[8]王伯琦.法治与德治[A].载王伯琦法学论著集[C].台北:三民书局,1999.
[9]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10]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1]何勤华,陈灵海.法律、社会与思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2]杨鹤皐.儒家“德主刑辅”论形成初探[A].载孔子法律思想研究[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13]龙大轩.关于“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再思考[J].宁夏社会科学,1993,4.
[14]耿云卿.先秦法律思想与自然法[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
[15]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J].读书生活,1936,9.
[16]马克锋.“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辨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2.
[17]程燎原.“洋货”观照下的“故物”——中国近代论评法家“法治”思想的路向与歧见[J].现代法学,2011,5.
[18]梁启超.管子传[A].载梁启超全集(第六卷)[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19]Fairbank, John K. 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0]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Volume Two[M]. Routledge,1964.
[21][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北京: 中华书局,2002.
[22]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24]陈景良.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另一种思路[J].法商研究,2004,5.
[25]马小红.“中华法系”中的应有之义[J].中国法律评论,2014,3.
[26]陈顾远.从中国文化本位上论中国法制及其形成发展并予以重新评价[A].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陈顾远法律史论集[C].范忠信,等编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湖北亿立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