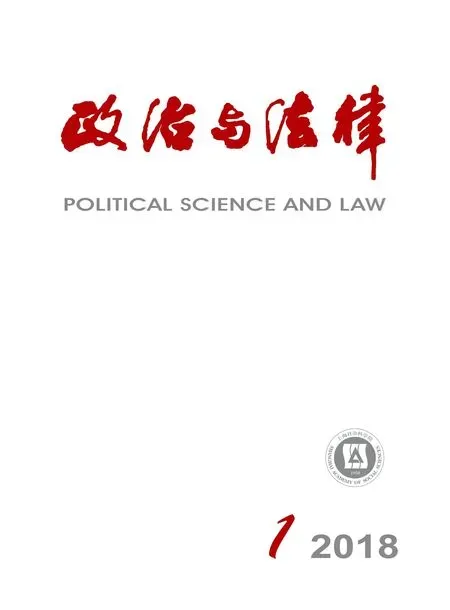论公共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困境消解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论公共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困境消解
贺大伟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对公共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法律属性的认识是厘定航空运输合同纠纷中承运人责任的重要问题。我国法并未明确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法律属性,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对此存在不同的观点。应从“条件”的法律涵义与航空运输合同的法律结构等角度出发,合理认定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法律属性。鉴于运输总条件具有格式条款之特征,结合国内运输条件中所惯常规定的航班延误及取消、客票超售等特别条款备受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议,以及国际运输条件中存在的承运人单方指定合同适用准据法等情况,此类条款是否对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法律效力构成法理障碍,应当予以论证。应当利用我国《民用航空法》正在修订的宝贵契机,适时在法律中明确承运人运输总条件是航空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这一法律属性。
公共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特别条款;客票超售;公约排他适用条款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民航业的快速发展,公共航空运输服务领域的法律纠纷日渐增多,做为航空法领域特有的概念,公共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受到司法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实践层面,航空运输服务合同案件的数量在航空法律纠纷中的占比持续提升,*中国民航运输协会法律委员会对近年来针对国内航空承运人的近千例航空纠纷案例进行归类、总结和分析,编写了《中国民航法律案例精解》一书,在其精选的86个案例中,航空运输合同履行中产生的合同之诉(包括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和航空货物运输合同)和侵权之诉(主要包括航空运输旅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共计48个案例,占比高达55%。参见中国民航运输协会法律委员会编著:《中国民航法律案例精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特别是航班延误、客票超售、行李破损或遗失等问题几乎成为航空承运人与消费者之间的“死结”,此类纠纷主要涉及运输总条件对各方权利义务的事前调整,承运人往往举证其运输总条件以对抗对方的请求,各法院对其法律效力的认定并不一致,更未形成统一认定标准。在学理层面,对于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若干基础性法理问题仍未完全达成共识,包括由航空承运人单方发布的运输总条件在航空法、合同法上应如何定性,其与国际民航组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ICAO)主导的“华沙-蒙特利尔体系”项下系列国际公约,*国际民航组织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1944年为促进全世界民用航空安全、有序发展而成立,总部设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是191个缔约国(截至2011年)在民航领域中开展合作的媒介。2013年9月28日,中国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国际民航组织第38届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一类理事国。以及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以下简称:IATA)发布的运输条件之间应当界定为何种类型的适用关系;*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是一个由世界各国航空公司所组成的大型国际组织,1945年12月18日在加拿大正式登记注册成立,总部设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执行机构位于日内瓦,其目标在于统一全球各航空公司经营中的技术、商业、监管等共同事项。作为市场主体的承运人发布的运输总条件与作为行业主管者的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四项运输规则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这四项运输规则指中国民用航空局(原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发布的四件部门规章:《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2004年修订)》(CCAR-271TR-R1);《旅客、行李国际运输规则(1998年生效)》(CCAR-272TR-R1);《货物国内运输规则(1996年修订)》(CCAR-275TR-R1);《货物国际运输规则(2000年生效)》(CCAR-274)。对于承运人运输总条件中航班时刻、航班延误及取消、客票超售、拒绝和限制运输、承运人责任限制等特殊规定与航空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的冲突应如何规制等。这些问题的核心均在于清晰界定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法律属性,进而为航空运输服务活动、司法实践乃至民航业立法提供理论支撑。
二、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法律属性之厘定
公共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general conditions of carriage)在学理上又称“运输共同条件”、“一般运输条件”等,实践中各航空承运人的表达也并不尽一致。*参见《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国内/国际旅客、行李运输总条件》、《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国内/国际运输条件》、《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国内/国际运输条件》。笔者认为,运输总条件一般是指由公共航空服务提供者事先制定的规范承运人与消费者因公共航空运输服务而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仅就名称而言,“运输总条件”应当作为一种泛称而存在,且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做更进一步的区分。根据航空承运人提供运输服务的不同类别与属性,运输总条件可以区分为航空旅客、行李类运输条件(以下简称:旅客/行李运输条件)和航空货物类运输条件(以下简称:货物运输条件);根据航空承运人提供航空运输服务的不同航段,运输总条件可以区分为航空旅客、行李/航空货物国内类运输条件(以下简称:国内运输条件)和航空旅客、行李/航空货物国际类运输条件(以下简称:国际运输条件)。*“国际航空运输”与“国内航空运输”的区分由《华沙公约》(1929)即被确立,但是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国家理论上只存在国际航空运输活动。我国《民用航空法》第107条明确区分了“国内航空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输”,由于法律制度上的差异,我国大陆飞往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航班事实上按照国际航空运输规则处理。
(一)关于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法律属性的主要观点
长期以来,学理界与司法实务界对于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一直存有不同的观点。
1.合同说
在航空运输实践中,承运人运输总条件常由航空承运人事先统一拟定,并在其与旅客/货主正式签署航空运输服务合同之前以特定方式告知对方。*笔者于本文中所称的“货主”为行业内的泛称,包括航空货物托运人、收货人及付款人等,而非仅指航空货物所有权拥有者。在航空承运人的相关声明之中,多数承运人一般都将运输总条件视为航空运输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赋予其合同的地位及属性。在航空法学界,部分学者针对司法裁判中的争议,积极主张在立法层面赋予运输总条件以航空运输服务合同(或其主要/核心内容)的法律地位,*参见郝秀辉:《论“航空运输总条件”的合同地位与规则》,《当代法学》2016年第1期;赵劲松:《航空运输总条件法律地位路在何方?》,载杨惠、郝秀辉主编:《航空法评论(第4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81-97页。但是,对于运输总条件与航空运输合同之间的关系,仍存有一定的争议。主张承运人运输总条件合同说的学者大都认为运输总条件构成了航空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但是对于客票的地位和航空运输合同其他内容的界定并无完全一致的认识。
在主张合同说的研究者中,有一部分人持部分条款无效观点。持此观点者基本以承认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合同地位为前提,同时认为总条件由承运人单方面事前发布,属于格式合同,对于其内容有属于我国《合同法》第40条所规制的免除提供格式条款者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格式条款的,应属无效。例如,国内多家承运人在其运输总条件中所规定的“退票仅限原出票处办理”的机票不能异地退票规则就曾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批判;*由于民航业内承运人对代理人管理乏力,为避免代理人借旅客退票的方式侵害航空承运人的利益,此类条款被绝大多数承运人吸纳进入其运输总条件中,甚至还引发过要求旅客跨国退票的纠纷与诉讼。此外,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还曾对某承运人运输总条件中关于规范旅客支付与承运人出票行为关系的“系统产生票号后即为支付成功”的条款判决无效。*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25394号民事判决书。目前,我国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对于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管理,采取国内运输条件需经批准并公布方可生效、国际运输条件需经备案方可生效的制度,那么,对于履行了中国民航局报批与备案程序而生效的运输总条件中的部分条款经由法院做出无效判决后该如何处理,值得探讨。
2.业务文件说
我国《民用航空法》等民航领域的立法并未明确界定公共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法律属性,致使国内部分航空承运人以中国民航局先后发布的四项运输规则为蓝本来制定其运输总条件,并将其视为承运人内部管理过程中的一种业务文件来对待,这样,运输总条件仅成为承运人业务操作规则的文本汇编,无法发挥规范航空承运人与旅客/货主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功能。之所以有观点将运输总条件的法律属性作为一种业务文件,与我国民航业多年的改革背景密切相关。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航业历经了从“军队领导为主”到“军转民、企业化”、从“政企合一”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从“机场与航空公司分设”到“航空公司重组与机场属地化管理”等一系列改革,航空承运人在真正转变为市场主体之前,曾做为政府的生产部门而存在,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四项属于部门规章性质的运输规则,也先后在此背景下出台,并为国内航空承运人所广泛采纳。这样,部分承运人至今仍将其运输总条件视为企业自身为落实中国民航局四项运输规则的内部业务文件。
3.国际商业惯例说
持国际商业惯例说者认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特别是超售、拒载等特别条款)系经由国际航空运输实践形成的商业惯例,且为各国航空公司和旅客/货主所认可并遵循,主要体现在IATA版本的运输条件中。作为国际航空公司间的行业性民间组织,IATA在履行“统一国际航空运输规则”的职能中,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制定运输条件(conditions of carriage)范本供会员采用。为了弥补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以下简称:《华沙公约》)的不足,*《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于1929年10月12日签订于华沙,于1933年2月13日起生效,习惯上称为《华沙公约》。《华沙公约》共分5章41条,主要规定了发生飞行事故之后的赔偿责任,对国际运输的定义、运输凭证和承运人责任作了明确的规定。该公约规定,在运输中由于承运人的过失使旅客、托运人或收货人遭受损失,承运人应承担赔偿责任。IATA先后发布了多个版本的运输条件,目前最新的版本是1986年IATA承运人服务会议(passenger service conference)通过的“建议措施(recommended practice)”第1724号文件,即《运输条件(旅客及行李)》,*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IATA先后提出过多个版本的国际航空运输“标准条件”。在旅客运输方面,1927年IATA制定出了第一个版本的《维也纳条件》;1933年修订后成为《安特卫普条件》,1949年制定出新的《百慕大条件》,1953年在檀香山又加以修订。内容涉及客票、行李、票价、定座、值机、拒绝与限制载运、航班时刻、退票、行政手续等。这一文本虽无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但鉴于IATA在全球航空业界的广泛影响力,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航空承运人均广泛借鉴了该版运输条件的相关内容。这也使得各承运人的运输总条件常被视为全球航空业界的商业惯例而存在。
有部分学者认为,鉴于目前各国法院对于运输总条件的认识停留在弹性合同条款阶段,在裁决航空运输案件时,仍然是有选择性的适用,因此,解决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法律属性的问题的路径在于将IATA发布的运输条件上升为刚性国际惯例,而非停留在目前的建议版本阶段;其具体的路径在于通过制定运输总条件标准范本,在行业内广泛推广适用,使其最终走向刚性国际惯例。*参见前注⑧,赵劲松文。
4.回避适用说
在我国,有部分法院在审理航空运输合同纠纷案件中,对于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采取回避认定其法律属性的态度,通过直接援引我国《合同法》或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方式回避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存在,*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民申字第1955号民事裁定书。该案系因航班延误引起,历经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在该案件审理中,四川航空公司做为承运人向法院举证其运输总条件之相关内容,法院在裁判中并未采纳,法院直接援引我国《合同法》之相关规定进行裁判。甚至对于中国民航局发布的《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CCAR-271TR-R1)、《旅客、行李国际运输规则》(CCAR-272TR-R1)、《货物国内运输规则》(CCAR-275TR-R1)、《货物国际运输规则》(CCAR-274)等行政规章也采取回避态度。*参见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2民初5181号民事判决书。
(二)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合同属性的初步厘定
目前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对于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功能的认识尚不尽一致,尤其对于其法律属性仍存有较大争议,笔者认为,从航空运输总条件的实践功能及其内容的法律特征分析,将其定为航空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较为合理。
1.从“条件”的法律涵义分析航空运输总条件
在大陆法系民法理论中,“条件”做为法律行为之附款而存在,即当事人对于法律行为效果之发生、中止或消灭所加的限制。传统民法上,法律行为之附款包括条件和期限,分别构成了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因此,大陆法系民法理论中的条件,“谓构成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之一部,使其法律行为效力之发生或消灭,系于客观的不确定的将来之事实”;*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3页。换言之,此处条件的内容是将来客观上不确定的事实,效力在于决定法律行为之效力。具体到合同领域中,当事人依自由意志创设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条件制度则是在此基础上对合同风险进行分配的一种方式,构成了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限制。以附条件合同法律制度为例,条件的成就与否视为确定合同效力发生、中止或消灭的关键。在大陆法系民法理论中,条件有多种类别,如明示条件和默示条件、先决条件和解除条件、肯定条件和否定条件等;违法的、不符合社会公共秩序的和不可能发生的条件一般无效。
合同法中常有所谓“合同交易条件”之概念,此处的“条件”是否即为传统大陆法系法律行为理论中之“条件”,理论上存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作为契约内容的“交易条件”应与作为法律行为附款的“条件”相区别,前者如买卖契约中关于标的物、价金、清偿时间及地点等条款。*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0页。大陆法系合同法中所使用的“交易条件”或“一般交易条件”与“格式合同”的称谓相通,具体而言,其在德国法中称为“一般交易条件(Allgemeine Geschäftsbedingungen)”,在法国法中称为“附合契约(contract d’ ad-hesion)”,*同前注,史尚宽书,第14页;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在日本法中称为“普通条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中称为“定型化契约”,在英美法多称为“标准条款(standard article)”或“格式条款/不公平契约条款(unfair contract terms)”。在立法例上,德国曾于1976年制定《一般交易条件法》,其内容涉及对一般交易条件的界定、一般交易条件纳入具体合同的要件、对一般交易条件内容的法律控制、该法的适用范围以及一些过渡性规定等。2002年1月1日,随着《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的正式生效,《一般交易条件法》被废止,其主要内容被纳入《德国民法典》“债法编”,成为该编第二章“以一般交易条款形成意定债务关系”(置于“债法编”原第二章“因合同而产生的债的关系”之前)。*参见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可见,此处所指的“一般交易条件”与作为法律行为之附款的“条件”并非指同一概念,前者实质为格式合同本身,后者为限制法律行为之效力的一种将来客观上不确定发生的事实。
笔者认为,“条件”这一概念虽为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广为采纳,但却源自普通法,且在英美法上常作为合同中已明确的条款内容而存在。英美法中的合同系由当事人双方的各种声明和承诺所构成,其性质和重要性各有不同,这些已被明确为合同条款的声明和承诺可以依当事人的主观意愿以及违反时的效力区分为两类,即“条件(condition)”与“担保(warranty)”。其中,条件被视为对事实的陈述或承诺,此种陈述或承诺是合同不可缺少的条款,且为当事人高度重视,如果陈述不真实或者承诺得不到履行,则无过失当事人可将违约当做拒绝履行,并可使自己免除进一步履行合同的义务,甚至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相对而言,担保处于次要的地位,意指当事人对某事加以明确或隐含的陈述,这种陈述可以成为合同的一部分,或者虽然是合同的一部分,但对于合同的明确目的而言是次要的,并且无过失当事人在对方违反担保的情况下,无权拒绝履行合同,只能要求损害赔偿。由此可见,在普通法上,条件构成合同之“基础(root)”,担保仅为合同中次要的条款。*参见杨祯:《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289页。
进一步而言,英美法上条件制度所包含的范围要比大陆法更为广泛。英美法系对于条件之于合同作用的认定有所谓“对流条件(concurrent condition)规则”或“共存条件规则”,即合同一方的履行被推定为另一方履行其义务的先决条件;换言之,通常意义上的条件是一方当事人承诺履行合同的重要前提。在这一意义上,条件承担着类似大陆法上履行抗辩权的功能,*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此处所谓的条件也被称之为“承诺的条件”。*[英]A.G.盖斯特:《英国合同法与案例》,张文镇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在特殊情况下,条件才具有了“附属的条件”的特征,即合同的生效与否取决于条件是否得到履行,此时的条件才具有了与作为大陆法系“法律行为之附款”的条件相通的功能与涵义。从这一意义出发,将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中所述之“条件”归入“承诺的条件”更为恰当。
本质上,“条件”在英美法系合同法中的地位与其在大陆法系法律行为理论框架内的不同功能,也与两大法系早期对于合同属性的不同认识密切相关。大陆法系学者对合同的属性秉持“协议说”,认为合同是意定之债的主要发生原因,*同前注,王泽鉴书,第6页。本质上是当事人之间合意的结果,是一种协议。英美法系对合同属性持“承诺说(允诺说)”,*比如,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1条规定:“合同是一个允诺或一系列允诺,违反该允诺将由法律给予救济,履行该允诺是法律在某些情况下所确认的一项义务。”转引自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合同被视为是一种承诺或允诺,合同法所规范的乃是包含一个或者多个允诺的交易,此种承诺或允诺为一方向他方当事人作出负担某种行为或不行为的义务的表示,进而引起受允诺人的信赖。*作出允诺表示的人是为允诺人(promisor),接受允诺表示的人是为受允诺人(promisee)。将合同视为是一种允诺,最早是由英国的历史习惯和诉讼程序所决定的,*在中世纪的英国法中,并没有形成合同的概念。最早出现的,只是所谓的“允诺之诉”,即当允诺人违背其允诺时,受允若人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执行诺言。参见王军:《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同时也与英美法将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等关系作为“准合同”对待的做法有联系;从强制执行允诺的本质来看,无论是“作为履行的强制执行”还是“作为激励的强制执行”,*[加]本森:《合同法理论》,易继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都表明此种允诺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允诺,而是建立在交易基础之上的允诺。由于“允诺说”容易导致将合同视为单方允诺的误解,因此,一些英美法学者也开始完全采纳大陆法关于合同的见解,将合同视为一种协议,*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将合同定义为“二人或多人之间为在相互间设定合同义务而达成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协议”。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牛津法律大辞典翻译委员会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由此,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法系在合同的概念上有逐步接近的趋势。*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2.从航空运输合同的法律结构分析航空运输总条件
从航空运输合同的法律结构分析,承运人运输总条件契合航空运输合同的基本要素,发挥着系统规范因航空运输活动产生的私法关系的积极功能,为航空运输服务合同的核心内容。
现行我国《民用航空法》并未规定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法律属性,亦未界定“航空运输合同”的内涵与外延,其第111条、第112条和第118条分别规定了客票是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订立和运输合同条件的初步证据、行李票是行李托运和运输合同条件的初步证据、航空货运单是航空货物运输合同订立和运输条件以及承运人接受货物的初步证据。然而,学理上在讨论运输总条件的法律地位时,常视其为航空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或核心内容,但是对于航空运输合同的具体构成却存在争议。*主张承运人运输总条件合同说的学者大都认为运输总条件构成了航空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但是对于客票的地位和航空运输合同其他内容的界定并无完全一致的认识。参见郝秀辉:《论“航空运输总条件”的合同地位与规制》,《当代法学》2016年第1期;吴建端:《航空法学》,中国民航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我国《合同法》第288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比照这一规定,狭义的航空运输合同可以被界定为航空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机场运输到约定机场,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广义范围内的航空运输合同除涉及起降机场之间的航空运输服务外,还包括承运人或其代理人通过自有或第三方物流体系所提供的门到门等物理距离上的延展服务等。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合同法立法例中,运输类合同作为一种重要的合同类别,一般不以承运人与每位旅客/货主签订正式的运输合同为必要形式,而常以承运人向旅客/货主交付客票/航空货运单为运输合同成立要件。这是基于交易效率和交易便利的考量。航空运输虽然不签订具体的协议,仅通过旅客购票和托运人通过承运人填写货运单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不存在航空运输合同。应当说,航空运输合同至少由运输凭证、承运人发布的运输总条件、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等三部分内容构成。
首先,航空运输凭证作为航空运输合同订立的初步证据而存在。航空运输凭证是航空运输中使用的来确立旅客、托运人、收货人和承运人及其代理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以航空旅客运输合同为例,我国《民用航空法》第111条规定:“客票是运输合同订立和运输合同条件的初步证据。”该条明确了客票的性质、法律地位以及承运人违反客票规则的法律后果,它是参考1955年关于《修订1929年华沙公约的议定书》(以下简称:1955年《海牙议定书》)第3条第2款的规定和我国航空运输发展的实际情况拟定的。*1955年《海牙议定书》对1929年《华沙公约》做了部分修订,修订后的《海牙议定书》第3条第2款约定:“在无相反的证明时,客票应作为载运合同的缔结及载运条件的证据。客票的缺陷,不合规定或遗失,并不影响载运合同的存在或效力,载运合同仍受本公约规定的约束。如承运人同意旅客不经其出票而上机,或如客票上并无本条一款(三)项规定的声明,则承运人无权引用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航空旅客运输合同一般于旅客购入客票时即告成立,客票只是此项合同订立的初步证据,而不是合同本身。初步证据是普通法中的概念,普通法把证据分为初步证据(prima facie)和最终证据(conducive evidence)。初步证据又称表面证据,它表明了对其所证明的事务的基本肯定,其作为证据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即证明力已经达到法院可以据以认定事实、进行判决的程度,但是如有相反的、更为确凿的证据予以相反事实证明时,初步证据可以被推翻,因此,初步证据的证明力是初步的,而不是最终的。最终证据的证明力是完全充分和有效的,其他证据不能否认最终证据的证明力。两相比较,最终证据可以否认初步证据,初步证据不能否认最终证据。
其次,承运人运输总条件集中载明了航空运输合同各方当事人的主要权利义务。我国《合同法》第293条规定:“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然而,客票等运输凭证并非运输合同本身,因为它缺少对旅客与承运人等合同当事方之间权利义务内容的规范。运输总条件集中载明了航空运输合同当事方的具体权利与义务,以及违反合同时当事方(尤其是承运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为航空运输这种特殊的、典型的交易事件创造了一个固定的“法律框架”,从而避免每次订立同类型的单个合同时总是去重新确定合同的内容和样式,实质上涵盖了航空运输合同的主要内容。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作为一种格式的“一般交易条件”,因此为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个履行航空运输合同给付的统一的“法律基础”,进而公司载明此类内容的声明成为嗣后订立的各个航空运输合同的组成部分。*参见前注,郝秀辉文。
再次,其他相关法律文件构成了航空运输合同的重要补充。如果说客票是航空运输合同订立的初步证据、运输总条件是航空运输合同的主要或核心内容的话,运输合同究竟还包含哪些法律文件,也需进一步厘定。有学者认为,在“航空运输总条件”之外,航空运输合同还包括其它可适用的重要规定和条件,其中包括特殊旅客的运输规定、电子设备的限制使用规定、在飞机上引用酒精饮料的规定等。*参见前注,郝秀辉文。笔者认为,在航空运输合同中,除客票、承运人运输总条件之外的其他法律文件,不应仅仅局限于上述文本,从类型化的角度分析,应当包括可以引起航空法及航空运输当事人民商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中止、终止的特殊法律文件;此种特殊法律文件所调整的事宜并未由承运人运输总条件所规范,并且既可以是承运人与旅客/货主之间的特殊民商事性质的约定,也可以是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等。从这一角度而言,构成航空运输合同重要补充的此类特殊法律文件是动态变化的,并且需由个案具体认定。
此外,有学者认为在航空运输合同所涉的系列法律文件中,“运输条件”与“合同条件”也不尽一致。*参见前注,吴建端书,第160页。航空运输中的合同条件一般是指机票(指纸质客票、非电子行程单)背面和货运单背面规定的条款,确立了航空承运人与消费者和顾客之间的基本合同关系,而运输条件所涉及的内容则要广泛得多,也构成了航空运输合同的组成部分。以IATA决议为例,IATA除了通过第1724号决议(即“运输条件”)之外,还曾发布过文件名为《旅客机票——通知与合同条件》的第724号决议,该决议规定了机票上必备的各种通知和合同条件。笔者认为,鉴于现行我国《民用航空法》并未单独使用运输总条件的表述,而只是于第111条、第112条和第118条分别就客票、行李票及航空货运单对于运输合同及合同运输条件的证据效力做了规范,且第118条虽然使用了“运输条件”的表述,但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应与第111条和第112条所使用的“合同运输条件”做并列理解,可见,现行我国《民用航空法》并未严格区分“运输条件”与“合同条件”。
(三)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核心内容应由国内立法确立
由于运输合同是附和合同,其条款一般是由承运人一方拟定而不是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旅客/货主只在是否订立合同上有自由选择权。为了防止承运人一方将不公平条款强加给旅客/货主,国际航空运输公约和各国立法基本都把运输合同条件法定化。“华沙-蒙特利尔体系”项下有关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条款在法理上属于缔约国之间法定的国际航空运输合同条件的核心内容(包括国际公约转化为国内立法中有关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在IATA运输条件广泛影响之下由各承运人自行发布的运输总条件之合同属性理应为立法所认可。
当前,我国《民用航空法》正在修订过程中,作为突出承运人在民航市场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方式,从立法角度赋予航空运输总条件以合同地位正当其时,我国《民用航空法》应当在我国《合同法》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运输合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法律规制的立法体例基础上,明确厘定运输总条件的法律属性,通过运输总条件平衡承运人与旅客/货主的权益,构造符合航空业惯例的新型契约关系,并鼓励承运人通过优化其运输总条件的方式来推动民航市场承运人之间的良性“制度竞争”,*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是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而非外生变量,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中至关重要;人类的理性选择(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将创造和改变诸如产权结构、法律、契约、政府形式和管制这样一些制度,这些制度和组织将提供激励或建立成本与收益,最终这些激励或成本与收益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将支配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进而言之,在市场竞争及竞争法领域,市场主体之间的制度竞争较其行为竞争更为重要。参见[美]舒尔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载[美]罗纳德·H·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75-184页。以进一步推动民航业的市场化发展以及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2016年8月8日,中国民航局发布了《关于〈民用航空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并于此版《民用航空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107条规定:“本法所称航空运输合同是航空运输承运人将旅客、行李或者货物从出发地点运输到目的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公布的运输总条件是航空运输合同的组成部分。”
三、“特别条款”适用困境的消解:以“客票超售条款”为例
从学理乃至立法层面明确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是航空运输合同主要内容的法律性质,所面临的现实难点问题之一就是各承运人在其运输总条件中对航班超售、航空旅客黑名单、航班延误及取消等是否与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制格式条款以及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等规范相冲突。在学理层面,此类问题凸显了航空运输与传统运输方式之不同;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争议的热点和难点。从类型化角度考虑,笔者于本文中拟将运输总条件中的此类条款统称为“特别条款”,并拟就此类特别条款对于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为运输合同主要内容之法律属性的影响做探析。
(一)特别条款对运输总条件法律效力的影响
做为对“华沙-蒙特利尔体系”项下航空承运人责任认定规则的重要补充,各航空承运人发布的运输总条件所调整的内容一般涉及航空运输服务链条的全部程序,以旅客运输条件为例,内容一般涉及客票、票价与税费、定座与购票、航班超售、乘机、行李运输、航班时刻、航班延误及取消、拒绝和限制运输、退票、客票变更、旅客服务、第三方服务、航空器上的行为、行政手续、连续承运人、损害赔偿责任等。其中,航班超售、航班延误及取消、拒绝和限制运输、行政手续等条款颇具特殊性。一方面,尽管我国《合同法》将运输合同单列为一种有名合同予以规范,同时,鉴于民用航空业高风险、高科技含量、高成本、高敏感度、低收益的独特产业特征,决定了包括承运人运输总条件在内的航空运输合同与传统运输合同存在着若干重要差别,这往往是航空法与合同法边界之所在,当客票超售、黑名单等有别于传统运输合同的事件发生之时,如何通过运输总条件平衡承运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契约关系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合同法上格式条款的产生对于增进交易、便利消费者至关重要,同时,因其由优势企业一方所拟定而限制了合同自由,所以强制缔约义务的产生可谓是对合同自由的一次修正与保护,即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满足和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法律规定,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格式条款提供者不得拒绝消费者的缔约请求;具体到航空运输服务中,承运人运输总条件对于航班超售、黑名单等问题的界定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正当理由”的范畴,应慎重考量。基于此,如何认定此类特别条款的效力,对于承运人运输总条件合同属性的认定颇为重要。
(二)特别条款的适用困境
一般而言,在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中,客票超售条款往往作为特别条款之一为承运人所单方面设置。客票超售是目前国内实践中约定俗成的说法,其英文是“overbooking”,中文译意为“超定座”,指为了避免航班座位的虚耗、满足更多旅客的出行需求,航空承运人往往会在某些容易出现座位虚耗的航班上进行超过航班最大允许座位数适当比例的客票销售行为。
航班超售是为了避免座位虚耗。座位虚耗的原因主要包括:(1)旅客原因,又如由于旅客通过航空订票的周期较长,在购买机票并订好座位后,往往存在少量旅客最终未按约定时间前往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情形,也即航空法上的“NO-SHOW”,或者旅客可能同时与多家机票代理联系购票,各家代理都定座,无意中造成重复等;(2)代理人原因,比如航空公司代理人的虚假订座等;(3)其他原因,比如旅客由于乘坐另一航空公司或同一航空公司的航班,由于航空承运人或天气原因延误而错过衔接航班,或者航空公司不要求旅客“再证实”座位等。
航班超售具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被视为“飞机经济学”的典型例子,但对于航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极易造成侵害。一方面,各航空承运人都会实行一定比例的超售,规模越大、管理越先进的航空公司的超售范围越广,超售收益也越大;这些航空承运人会通过相关数据分析系统抽取历年定座和离港数据,同时参考前期被延误行程人数和补偿费用,以决定是否对航班进行超售以及超售数量,且必须权衡合理超售和拒载两者之间的利弊,找出一个既有效利用空位又能将拒载登机损失压缩到最小的平衡点。*参见前注,吴建端书,第165页。另一方面,由于超售极有可能造成航班旅客的溢出,致使部分旅客无法登机,在补救措施无法满足溢出旅客需求的情况下,甚至产生承运人拒载等一系列问题。
基于此,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于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中超售条款的合理性始终存有争议,其可以概括为“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肯定说”的主要理由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在产生原因方面,超售源自航空承运人为避免座位的虚耗以及满足更多旅客出行的需求,而非基于承运人之主观恶意,航空承运人基于市场竞争、运营成本、客源流失等考虑,对航班进行超售也符合国际航空业的售票惯例,且法律上对超售行为未予以明令禁止。其次,在控制措施方面,全球民航业对于适宜超售的航班及超售的比例都有明确的行业限制,而非承运人不受控制。再次,在补救措施方面,超售一旦发生后,承运人需针对溢出旅客及时采取寻找自愿者、尽快安排下一班航班、现金补救等措施,且此类补救措施需作为明示条款与超售条款一起列入运输总条件中。最后,在责任认定方面,对于自愿接受补偿金的溢出旅客,承运人一般会提供《非自愿弃乘及免责书》,其中载有“把赔偿金视为弃乘而引起或可能引起的一切索赔要求、费用支出及损失的最终解决”等类似条款,从而在旅客与承运人之间形成了一份新的认定双方责任的协议。*参见前注,吴建端书,第165页;王立志、杨惠:《航空旅客权益保护问题与规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136页。
“否定说”又可细分为“欺诈说”和“违约说”。“欺诈说”认为,航空承运人在旅客购票之时并未告知消费者关于客票超售情况,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进而影响了消费者的缔约意愿,并客观上造成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背真实意愿订立合同,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欺诈,因此应按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的“退一赔三”的罚则处理。*2010年11月,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工商管理分局对国内某航空公司开出关于机票超售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其对旅客黄某一行八人中两人的机票超售行为违反了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之诚实信用原则,剥夺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赋予旅客的知情权,同时违反了《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51条第15项的规定,构成了以欺诈方式超售机票的违法行为,责令该航空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5000元。此案是我国机票超售行政处罚的第一案。“违约说”认为,旅客自购票之时其已与航空承运人之间达成运输合同,航空公司未按客票载明的时间和班次运输旅客,即使已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但无法阻却迟延运输违约责任的构成,也属于未按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应承担承运人的违约责任,赔偿因违约给旅客造成的经济损失。*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946号民事判决书。
由此可见,在承运人运输总条件中,以航班超售为代表的特别条款,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中,极易遭遇适用上的困境,这既源自航空产业与航空法相对于传统运输行业及其法律规则的特殊性,也与立法缺失和行业导向的模糊性有关,由此导致了此类纠纷案件司法裁判的非一致性。
(三)特别条款订入运输总条件的规制方式
应当承认,特别条款所规范的超售、拒载等是航空运输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合法实践,*参见美国运输部消费者保护处的“Fly-Rights A Consumer Guide to Air Travel”,转引自前注,吴建端书,第169页。无论是IATA版本的“运输条件”与“合同条件”,*IATA第724a号决议明确了该协会会员可以在机票上适用的有关超售的相关规则。还是“华沙-蒙特利尔体系”项下的国际公约,都明确认可了航空运输过程中客票超售、航班拒载、延误及取消等行为作为航空业惯例的客观性。从航空运输合同角度来看,存在争议的是此类行为作为特别条款载入运输总条件的过程中,如何在保持条款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同时,亦能有效维护航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通过运输总条件在航空承运人与消费者之间构建平衡的契约关系。诚然,这一方面有赖于立法与行业主管机关的指引与规范,以及航空消费者对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相关规则的事前审查机制,另一方面也需进一步规范承运人在制定运输总条件过程中的各项实体义务和程序义务。前者包括科学、合理制定各项条款尤其是特别条款的义务,后者包括承运人的告知义务等。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对特别条款订入运输总条件予以规制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对于特别条款拟约定事项的规制
在对客票超售、航班拒载、延误及取消等特别条款具体规制规则的设置方面,立法的作用至关重要。应当在充分了解此类问题的法律属性基础上,广泛借鉴欧美等航空业起步较早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规则,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引导承运人在运输总条件中合理设置特别条款,使承运人与旅客之间的格式合同兼顾我国《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要求和航空运输产业的特殊性。目前,在超售等行为的规制领域,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第14篇第250节所规定的“超售规则”(14 C.E.R Part 250-OVERSALES)和欧盟《关于航班拒载、取消或长时间延误时对旅客补偿和协助的一般规定》(以下简称:欧盟261/2004条例)最具代表性。
美国的民航运输总量长期居于全球首位,其航空法律体系由国际公约、国会立法、司法判例、行政规章等构成。在国际公约层面,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判例,适用公约的航空运输,排除国内法律的适用(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另外,由于国会的立法具有较强的原则性,美国运输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DOT)、美国联邦航空运输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等行政机构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行政规章,以使国会立法具体化,并确保其有效执行。DOT于1978年就发布了专门调整有关超售和拒绝登机的规则,并沿用至今,即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第14篇第250节之“超售规则”(14 C.E.R Part 250-OVERSALES),适用于因持有经确认的定座和客票的旅客超过航班实有座位,致使航空公司无法全面提供原先确认预定的座位的情形。DOT超售规则重点对于非自愿拒载登机遴选程序(priorities procedure)中旅客权益的保护和航空承运人的义务做了重点规范,细致规定了遴选自愿者与非自愿者的程序和方法、补救的措施、补偿的标准、支付的方式、补偿资格的获得等一系列具体规则。同时,DOT对于超售规则的实施情况也予以监督,要求航空承运人如实报告超售和拒绝登机情况,并将其汇总在航空旅游消费者报告(Air Travel Consumer Report,ATCR)中。美国机票超售规则自1978年生效以来能沿用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确立了超售规则的基本框架外,还建立了赔偿金额的通货膨胀自动调整机制等。*赔偿金额通货膨胀自动调整机制,指由DOT每两年对赔偿金额进行审查,并根据城市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来计算最高赔偿额的增幅。此外,DOT在执法方面也体现出了与航空承运人良好的互动性。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虽然超售规则在美国已实行多年,但是关于航班超售的合理性问题始终存有争议。2017年4月,美联航UA3411航班超售并暴力驱客事件发生以后,*2017年4月,越南籍旅客David Dao与妻子乘美联航UA3411航班,由芝加哥飞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在航班登机后、起飞前David Dao被强行拖下飞机,致使其鼻梁骨折,失去了两颗前牙,并有脑震荡情况。事件发生后,全球航空业与消费者组织哗然,关于航班超售合理性与否的争论再起。最终,David Dao与美联航达成和解协议,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涉及的金额保密。有关机票超售的话题又掀起了新一轮争论。然而,即使如此,由于美国航空运输的法律体系相对较为完善,尽管航空公司的旅客运输总条件中约定了极具争议的客票超售等条款,但是一般而言,旅客在选择航空承运人出行之前,需要根据法律的规定先了解和阅读其“旅客须知”,如果旅客选择购买了一家航空公司的机票,那么双方合同达成,航空公司和旅客都要承担自己的义务,以最终促使航空运输市场的自由竞争。*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本土的许多低成本航空机票价格非常便宜,但出现超售不仅没有补偿,而且也无后续航班安排,从而在航空市场上实现多样化的选择与竞争,以使航空市场的旅客运输交易更为公平且自由。
欧盟的航空业发展水平及其航空法也始终走在全球前列,在航空法律体系方面,除国际公约优先适用外,亦采取单独立法的体例。在机票超售方面,欧盟早于1991年就颁布了《关于在定期航空运输中建立拒载赔偿制度的规定》(以下简称:欧盟295/91条例),之后,为了更好地保护航空旅客的权利,欧盟于2004年新修订了欧盟261/2004条例,并完全取代了欧盟295/91条例。欧盟261/2004条例的主要内容是在旅客被拒绝登机、航班取消以及长时间延误的情况下,确立如何对其进行赔偿和协助的具体规则。该条例适用范围为欧盟成员国境内机场出发的旅客,也适用于从第三国出发、前往欧盟条约适用的欧盟成员国内的机场且承运人为欧盟成员国内的承运人的旅客,除非该旅客在第三国内收到益处、赔偿或获得帮助。该条例将客票超售的后果即拒载划分为自愿拒载和非自愿拒载,并规定了承运人的告知义务以及拒载后补偿金的额度、标准与支付方式等,体现了欧盟对于航空旅客优先保护的强烈色彩。*除了欧盟261/2004条例之外,欧盟对于航空旅客权利的保护还包括:EC Regulation 1008/2008,要求航空公司在网站上对价格进行透明化公示;EC Regulation 2111/2005,要求承运人告知旅客航班实际承运人;EC Regulation 1107/2006,对残疾旅客及其他行动不便旅客的保护等。然而,欧盟261/2004条例的内容因为与欧盟成员国在之前条约中的义务相冲突,并且与“华沙-蒙特利尔体系”项下有关航空承运人责任中的第三国义务相冲突,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国际争议。IATA曾就此提起诉讼,虽然最后诉讼结果是欧盟维持该条例的合法性,但国际航空业界尚未放弃重新审查该条例的努力。*The Queen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European Low Fares Airline Association v.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Judgment of the Court(Grand Chamber)of 10 January 2006,Case C-344/04.
截至目前,在航班超售问题上,我国民航法律体系内尚未有直接对其进行规范的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中国民航局消费者事务中心曾于2014年发布过作为行业标准的《公共航空运输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行业标准号:MH/T 1060-2014),并于2015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国内首个直接针对航班超售问题而制定的文件,但由于该处置规范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尽管对于各航空承运人具有参照意义,但实际上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尽管如此,对照2006年我国机票超售第一案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函》,*2006年7月21日,旅客肖某以1300元的价格购买了南航CZ3112航班(北京-广州)机票,在旅客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南航告知由于机票超售的原因,CZ3112航班已经满员,原告无法乘坐,于是南航为旅客肖某办理了签转手续,但随后签转航班也发生了延误,南航方面又将旅客唤回,将其转签至南航CZ3110航班,并免费为其升舱至头等舱(头等舱机票价格2300元),当日22时39分,原告乘坐CZ3110航班头等舱离港,此时距其原定起飞时间已过了近3小时。2006年9月,旅客肖某将南航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定虽然南航方面的行为并未构成欺诈,但未尽到告知义务,并判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向当时的中国民航总局(现为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南航发出《司法建议函》,建议中国民航总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能够承担起制定规则的责任,尽快制定航空客运机票超售的规章制度并指导航空运输企业适用。这已是明显的进步。如果我国《民用航空法》能够以本次修订为契机,在行业基本法中增加关于规范超售等行为及责任的相关条款,进一步明确承运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将对完善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合同地位并且在维护航空消费者权益与保护航空业商业惯例之间做出理性平衡大有裨益。
2.承运人就运输总条件特别条款的告知义务
2.1 出血型甲状腺囊性结节新型硬化剂聚多卡醇微创治疗后随访结果 15例结节术前平均体积(17.41±13.84)mL,治疗后 1周、1个月、3个月超声复查甲状腺囊性结节的囊腔体积变化,囊腔逐步缩小,结节平均体积分别为(8.20±5.97)mL,(1.88±1.66)mL,(1.18±1.51)mL,术后 1个月及3个月复查,囊腔体积均较术前明显缩小,两者与术前囊腔体积比较,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司法实践中,承运人的告知义务往往成为法院对于运输总条件中特别条款效力认定的争议焦点,*参见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2014)官民一初字第1745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5)历城商初字第1082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6762号民事判决书。基于此,笔者认为,在确认承运人运输总条件为合同主要内容这一法律属性的前提下,合理界定承运人的告知义务,对于运输总条件中特别条款适用困境的消解尤为重要。
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分别规定了格式合同提供者和经营者的告知义务,虽然二者在告知义务的范围和违反告知义务时相对方的救济途径方面存在差异,*万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告知义务之法律适用》,《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5期。但是,相对而言,这两部法律较之我国《民用航空法》对承运人告知义务的规定远为充分,后者只规定了承运人就责任限额进行告知的义务。有鉴于此,建议在我国《民用航空法》修订过程中,应当合理、科学界定承运人告知义务的边界。
其一,告知的时间。从告知时间来看,航空承运人的告知义务主要集中在订立合同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董念清:《论航空承运人的告知义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一般而言,航班超售、拒载、延误等运输总条件特别条款所约定的事项往往发生于合同履行之中,此时航空承运人固然需要承担及时、合理的告知义务,并且立法及行业惯例对于此时的告知均给予了较为详尽的规范,*以欧盟261/2004条款为例,该条例特别要求承运人在航班延误等情况下就旅客的权利进行告知,具体为承运人应保证在值机柜台以清晰易读的方式展示包含如下内容的通知:如果旅客被拒载或旅客的航班被取消或延误至少两小时,请在值机柜台或登机口索要权利书,特别是与赔偿(补偿)金和帮助有关的内容;承运人拒载或取消航班,应给受其影响的每位旅客提供一份包含本条例赔偿金和帮助内容的书面通知;承运人也应向延误至少两小时的旅客提供同样内容的通知;以书面的形式向旅客提供(本条例第16条规定的)国家指定机构的联系资料等。此外,对于盲人和视力受损的旅客,承运人也需以合理的备选方式来告知。但此种告知在性质上属于承运人就特别条款所规定事项的补救义务,相对而言,从航空运输合同证成的角度分析,承运人在订立阶段就运输总条件尤其是其特别条款的告知义务对于航空运输争议的定性往往更为重要。
其二,在告知的范围方面,尽管航空承运人在其运输总条件生效之后,往往会将其公布于所属各售票场所、订票网站等,并在客票/货单背面记载其全部或主要内容,以履行承运人的基本告知义务,同时,旅客通过购买客票与承运人签订航空运输服务合同之际,被承运人视为已接受运输总条件之全部内容。但是,一旦围绕特殊条款所约定的事项发生争议,法院往往会以承运人对特别事项的告知“欠缺明确性和指向性”为由,*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676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承运人未充分履行经营者的告知义务。笔者认为,所谓“欠缺明确性和指向性”,核心的指向为承运人告知范围的特定性。我国《合同法》第298条明确将承运人的告知义务界定为“有关不能正常运输的重要事由”和“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前者与承运人运输总条件中特别条款之事项较为契合,但也并非完全重合。笔者对于特别条款的界定侧重于影响正常航空运输的事项,但是对于广义范围内的航空业惯例(比如特价客票等不属于上述两项事项的特别事项)的告知范围及其程度,在司法实务界仍存在不同认识。较为妥当的处理原则是,其一,仅根据行业惯例或者交易习惯,不能直接推定消费者对相关信息明知;其二,告知作为经营者的一种法定义务,不能仅因为消费者的知情而被豁免;其三,若以行业惯例之方式履行合同而免除或限制己方责任,则法院会要求经营者履行特殊的告知义务,即以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该等条款并按消费者的要求加以说明。*参见前注,万方文。
四、承运人国际运输条件中“公约排他适用条款”的法理依据
与国内航空运输不同,国际航空运输合同涉及到准据法的适用问题。我国《合同法》及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于我国涉外民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均采取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的原则。我国《民用航空法》第188条规定:“民用航空运输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为我国国内航空承运人设定涉外航空运输合同的准据法适用方法和模式设定了基本规则。我国绝大多数航空承运人均在其与旅客/货主的国际航空运输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准据法。在航空承运人国际航空运输条件中,这一适用模式常常被表述为“根据本合同进行的运输,应遵守某某公约”。*参见《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国际旅客、行李运输总条件》第16.13条、《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国际运输条件》第17.4条、《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国际运输条件》第19.4.1条。此即所谓“公约排他适用条款”。
在航空实践中,目前国内绝大多数航空承运人在其国际运输条件中选择的准据法为199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以下简称:《蒙特利尔公约》)。以对航空承运人责任体系中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例,我国多数航空承运人均要求约定“在旅客、行李运输中,有关损害赔偿的诉讼,不论其根据如何,是根据所在国法律、根据合同、根据侵权,还是根据其他任何理由,只能依据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条件和责任限额提起”等类似内容。*参见《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旅客、行李国际运输条件》第19.4.1条。问题在于,国内航空承运人在涉外航空运输合同中单方面约定强制性适用《蒙特利尔公约》,是否对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一种违背,进而是否影响对承运人运输总条件合同属性的认定。相应地,承运人单方面在运输总条件中约定排他性地适用《蒙特利尔公约》的法理基础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航空承运人单方面指定合同准据法的合理性
笔者认为,我国国内设立的航空承运人在其国际运输条件中单方面指定适用某一公约,对当事人在合同准据法选择方面的意思自治并不构成实质性法理障碍。现代航空运输业为高度发达的规模化产业,承运人单方面提供的格式条款大大提升了交易效率,消费者与其以个别磋商的传统缔约方式已不适应,更无法就涉外航空运输合同所适用之准据法进行单独谈判,因此,从交易习惯角度分析,旅客一旦付款并购得机票,即视为接受航空运输条件并订立航空运输合同,也理应视为双方当事人对选择本合同适用的法律达成了一致。这一规则也为国际民航业所广泛接受,并且在民航运输实务中,双方当事人对合同适用的法律另行协商选择的情况很少发生。*按照IATA统一的票样要求,承运人在客票上载明“根据本合同进行的运输,应遵守某某公约”,旅客购得机票即视为接受承运人之运输总条件,也视为双方当事人选择了该运输合同适用的法律为某某公约。
(二)《蒙特利尔公约》排他性适用的法理基础
目前国内多数航空承运人在其国际运输条件准据法适用方面唯一指向性地适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既是因为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原本就是对“华沙-蒙特利尔体系”承运人责任规则的重要补充,更源于“华沙-蒙特利尔体系”项下国际公约排他适用的独特性。
1.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系对“华沙-蒙特利尔体系”承运人责任规则的重要补充
回顾航空法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作为国际航空运输规则体系在航空私法领域的重要成果,是航空承运活动中商业惯例规则化的体现。早在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出第一架飞机“飞行者1号”并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成功首飞之前,作为人类探索“管理空气空间的使用并使航空、公众和世界各国从中受益的一套规则”的努力就已经开始。*Diederiks-Verschoor:An Introduction to Air Law,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edition(October 1,2001):2. 事实上,早在1784年4月,法国即颁布过警方指令,规定除非事先获得批准,否则航空活动不允许进行,以直接和排他性地针对蒙哥尔费兄弟的气球试验。这被视为航空法之滥觞。1889年,欧洲19个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一次讨论航空法的国际会议。此外,法国法学家福希(Fauchille)于1900年就建议国际法研究院(The Institute Droit International)制定一部国际航空法典,成为“为数不多的法律进程走在技术之前(指1903年莱特兄弟首飞成功)的例子之一”。参见[荷]I·H·Ph·迪德里克斯-范思赫:《国际航空法(第九版)》,黄韬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商业性航空运输活动与各国航空立法活动的蓬勃开展,航空法无论作为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均具有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并逐渐成长为新的部门法。与此同时,国际航空法的统一化运动也得到持续推进,统一航空运输规则的成果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1944年《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芝加哥公约》)为代表的航空公法,*《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于1944年12月7日在芝加哥缔结,为国际民用航空的宪章性文件,也是包括国际航空运输法在内的现行国际航空法的基础,是目前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的公约之一。《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巴黎公约》)的基础为1919年《关于管理空中航行的公约(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Regulation of Aerial Navigation)》,以及1928年《泛美(或美洲国家间)商业航空国际公约(Pan-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ommercial Aviation)》(《泛美公约》)。《巴黎公约》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涉及国际民用航空活动的国际航空公约。解决了诸如空域主权、航空器国籍、统一规则便利空中航行、航空事故调查、遇难救助等方面的问题,形成“芝加哥公约体系”;*“芝加哥公约体系”还附属了包括针对航空器上犯罪、非法劫持航空器及其它危害民航安全的数个国际公约。二是以1929年《华沙公约》为代表的航空私法,解决了诸如运输凭证、航空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航空运输纠纷的关系法院和诉讼时效等,形成“华沙公约体系”。*“华沙公约体系”含《华沙公约》名下的一系列议定书,包括1955年《海牙议定书》、1971年《危地马拉城议定书》、1975年《蒙特利尔四个议定书》等,此外,一般认为还应包括1961年《瓜达拉哈拉公约》、1966年《蒙特利尔协议》等。
1929年《华沙公约》旨在建立与诠释一种主要原则来处理关于航空承运人对造成旅客、行李和货物以及航班延误损失所进行赔偿的问题,以便使旅客/货主进行航空旅行时可以知晓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统一规则来规制承运人的责任,与此对应的是承运人在知晓其自身责任承担的前提下,可以对可能造成的损失做好事先安排。*参见前注,I·H·Ph·迪德里克斯-范思赫书,第109页。然而,《华沙公约》仅涉及航空运输规则的一部分,并不能覆盖旅客/货主与航空承运人在航空承运活动各个环节的所有规则。因此,由IATA主导的运输条件对华沙体系提供了大量且重要的补充,以此作为弥补承运人以及旅客/货主之间的合同安排规则。由于IATA从组织形式上是一个全球航空企业的行业联盟,属于非官方性质组织(实际上已具有半官方属性)。其发布的运输条件虽然并不必然具有强制性的法律适用力,但因IATA在全球航空业具有的广泛影响力,其运输条件也为全球范围内的航空承运人所广泛借鉴。
1999年5月30日,作为长期努力及各方利益妥协后的重要成果,ICAO于其总部所在地加拿大蒙特利尔通过了《蒙特利尔公约》。作为《华沙公约》的最新发展,《蒙特利尔公约》在积极吸纳华沙体系有益成果与国际共识的基础上,旨在以其“现代化”后的责任规则“取代”支离破碎的华沙体系,在协调承运人与旅客利益的同时为当前国际空运实践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董念清:《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民用航空》2004年第1期。《蒙特利尔公约》目前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缔约国之间取代已适用70余年的《华沙公约》及其议定书,进一步规范、统一了国际航空运输私法领域的各项制度和规则。IATA于1986年通过的运输条件也随之做出了更新,截至目前已更新过多个版本。
2.“华沙-蒙特利尔体系”项下国际公约排他适用的独特性
航空承运人责任规则作为“华沙-蒙特利尔体系”项下各公约的核心内容之一,一般涉及承运人的责任与义务范围、责任人、“事故”术语、可赔偿的损害、责任期间、责任的免除、损害赔偿限制等内容。作为“华沙-蒙特利尔体系”项下公约的共同、重要特点之一,该体系项下的公约规则具备有别于其他非公约规则的重要适用特点,即“排他适用属性”,其基本含义是公约诉由、公约责任规则与公约管辖权规则在其规定的事项与范围内具有一律排除适用国内法规则与使用其他任何规则的属性与效力,从而使“华沙-蒙特利尔体系”下的公约规则得以独占支配承运人赔偿责任的认定。*郑派:《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在该书作者看来,“公约规则”涵盖1929年《华沙公约》、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等七项公约文件项下的责任规则与管辖权规则,“非公约规则”包含通过纳入承运人运输条件而发挥作用的承运人间协议以及欧盟261/2004条例等国内立法中规定的承运人责任规则。“华沙-蒙特利尔体系”项下国际公约排他适用的独特性,具体体现于1929年《华沙公约》第24条、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29条之规定。*1929年《华沙公约》第24条规定:“一、如果遇到第十八、十九两条所规定的情况,不论其根据如何,一切有关责任的诉讼只能按照本公约所列条件和限额提出。二、如果遇到第十七条所规定的情况,也适用上项规定,但不妨碍确定谁有权提出诉讼以及他们各自的权利。”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29条以“索赔的依据”为标题,规定:“在旅客、行李和货物运输中,有关损害赔偿的诉讼,不论其根据如何,是根据本公约、根据合同、根据侵权,还是根据其他任何理由,只能依照本公约规定的条件和责任限额提起,但是不妨碍确定谁有权提起诉讼以及他们各自的权利。在任何此类诉讼中,均不得判给惩罚性、惩戒性或者任何其他非补偿性的损害赔偿。”这一规则的确立,既是基于国际航空运输不断发展的实践对于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责任规则统一化、一致性的客观需求,也是“华沙-蒙特利尔体系”项下国际公约得以落地的必要保障,进而为国际航空运输领域内公约诉由、承运人责任规则与管辖权规则等国际私法规则统一化建构奠定了基础。
以国际航空承运人责任规则中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例。承运人责任限制制度,是指发生重大的航空事故时,作为责任人的承运人可根据法律的规定,将自己的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赔偿的法律制度。这是对民法中一般民事损害赔偿原则(即按照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做出的特殊规定,其目的在于促进航空运输业和航空保险业的发展。我国《民用航空法》制定于1995年,彼时对于国际航空运输中承运人的具体限额是参考1955年《海牙议定书》规定的以金法郎为单位的数额,以及1975年《蒙特利尔第2号附加议定书》规定的以特别提款权为单位的数额制定的,并体现于我国《民用航空法》第129条。我国于1999年加入《蒙特利尔公约》,《蒙特利尔公约》与我国《民用航空法》所规定之赔偿责任限额制度的具体数额与计算规则均有不同,在我国《民用航空法》未修订之前,国内航空承运人可依据我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之规定,通过在承运人国际运输条件中以合同约定的形式适用《蒙特利尔公约》规定之赔偿限额标准,来调整承运人与旅客/货主在国际航空运输过程中关于双方权利与责任之相关约定。
五、结 论
做为规范航空运输活动中承运人与旅客/货主之间法律关系的重要载体,航空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理应被立法尤其是我国《民用航空法》赋予相应的法律地位。尽管目前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对于运输总条件的法律属性仍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是将其定位为航空运输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这一法律属性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通过对承运人国内运输条件中普遍存在的类似于航班延误及取消、客票超售等特别条款的分析,以及对国际运输条件中准据法适用条款合理性的论证,可以发现,尽管运输总条件中的许多规则系承运人单方事先拟定,对于承运人与旅客/货主的合同权利义务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但其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且需要立法或行政手段的同步规制,因此,对于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合同属性的证成没有实质性的法理障碍。同时,应利用我国《民用航空法》正在修订的宝贵契机,适时在法律中明确承运人运输总条件的合同属性,以利于统一指导司法实践。
TheStudyonLegalNatureofPublicAirCarrier’sGeneralConditionsofCarriageandtheResolutionofDifficultiesinItsApplication
He Dawei
For defining the carriers’ responsibility in air transport contracts’ disputes, keeping a clear-sighted view of the legal nature of public air carrier’s general conditions of carriage is vitally important. However, the existing Chinese laws do not clearly regulate such legal nature, which caused many debates in academia and juridical practice. The legal nature of carrier's general conditions of carriage shall be reasonally determined in light of legal connotation of conditions and legal structure of air transport contracts.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general conditions of carriage enjoy characteristics of standard terms, combining the situation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disputes in academia and judicial practice over special terms usually set out in the conditions of domestic carriage such as delay, cancellation of flight and overbooked passenages’ tickets and the applicable law is unilateraly appointed by the carrier in con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carriage, discussion shall be made regarding whether such terms impose judicial barrier to legal effectiveness of the carrier’s general conditions of carriage. China shall take advantage of the important opportunity of amending Civil Aviation Law to clarify the legal nature that the carrier’s geveral canditions of carriage are the main part of air transportation contract.
Public Air Carrier; General Conditions of Carriage; Special Clause; Overbooking; Exclusivity Clause of the Convention
DF934
A
1005-9512-(2018)01-0134-16
贺大伟,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徐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