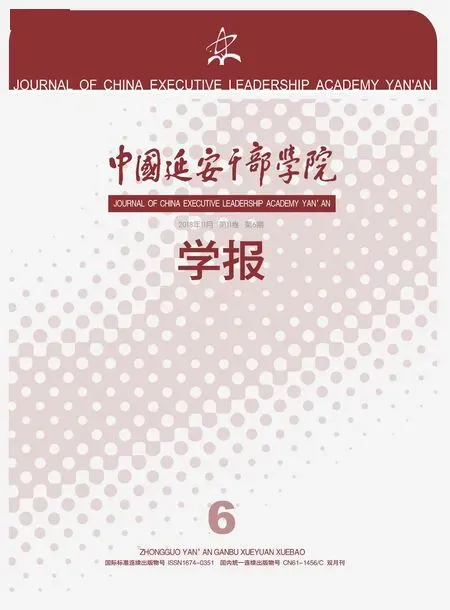“女权焦虑”与话语建构:建党初期妇女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建构
陈 曦
(浙江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海淀 100086)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进入到近代社会思想最为激荡和变革的时代。期间,中国思想革命从反封建伦理,强调个人价值的“纲常革命”,到1923年转变为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制度革命”。中国妇女运动目标设计也从“宜家善种”的国民母,家国同构的女国民进入到反对纲常伦理、呼唤个人情欲的觉醒。之后,随着“革命”统领一切的集体主义兴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和唯物史观也随之进入妇女解放运动,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妇女理论建构总体上保持与中国社会变革同步,但中国女性主体性意识不断地自我觉醒并没有将两者合二为一。被称之为“革命祖母”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向警予,在女权道路上的“焦虑”映射出两性在国家民族革命洪流中不同的社会性别身份述说,促使我们探究党内妇女工作者是如何在男性主流革命话语中建构革命女性的主体身份,并在党内妇女工作实践中开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一、向警予的“女权焦虑”
向警予牺牲后,前夫蔡和森在悲痛中撰文《向警予传》。此文用极其精炼的文字描述了向警予的革命生涯,在革命语言的述说中树立了向警予“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女英雄”的革命形象,“勇敢”、“忠实”、“热情”、“无产阶级化”、“积极”、“战斗”是文中对向警予革命者身份的颂扬。即便是对曾经亲密伴侣的怀念,蔡和森的语言表达也是与向警予的革命身份紧密相连,“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1]344在热情颂扬中,蔡和森也多次使用了“痛苦”一词,这痛苦不单是蔡和森对亡妻追忆的痛苦,更是蔡和森以一个男性革命者视角体认向警予作为女性革命者的痛苦。在蔡和森的追忆中,向警予自1922年积极投身革命以后,往日“绝对的与一般娇弱女同学不相同”的女学生的奋争形象少了,革命工作中的女权“焦虑”带来的“痛苦”却日益增多。
其一,革命中的男同志和女同志。在蔡和森的眼里,向警予是一个“事业的野心家”。她经常这样激励自己,“将来我如若做不出大事业,我要把自己粉碎起来,烧成灰。”[1]3421920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尽管求学生活异常艰辛,但向警予在《给爹爹妈妈》的信中,仍然显示出强烈的“野心”,“你的九儿在这里,努力做人,努力向上。总要不辱你老这块肉与这滴血,而且这块肉与这滴血还要在世界上放一个特别光明。”[1]3041922年,向警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担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从倡导国民教育的女权先锋到处理各种妇女事务的共产党的女部长,向警予将身心完全投入革命事业。但此时蔡和森已觉察到,“她精神上常常感受到一种压迫,以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在她看来,仿佛是‘奇耻大辱’。”[1]343而且这种精神压迫并不因工作受到肯定而减弱,“同志们愈说她是女同志中最好的一个,她便愈不满足”[1]343。尽管她极力排斥传统的女性形象,不苟言笑,衣着朴素,革命活动中与男性一样冲锋在前。但同志们对她的尊称“革命老祖母”仍然是与其性别身份相连。向警予焦虑于革命工作的男女有别,纵然蔡和森认为“以向警予的能力来说,本可担任一般党的工作”[1]343,但革命中的“女同志”被认定为从事“妇女”工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勇敢走出封建家庭,革命工作却依然是传统性别分工,性别敏感使“她总是不甘于‘妇女’工作”。对自己性别身份的质疑和抗拒,和由此产生的革命活动中的紧张和矛盾常使向警予陷入到女权焦虑的痛苦之中。
其二,婚恋与革命。向警予在常德女子师范读书期间,因目睹好友余曼贞备受封建家庭伦理折磨的婚姻生活,遂产生不婚的念头。1918年,面对后母为攀附当地权贵而包办的婚姻,向警予毅然拒绝,并立志“以身许国,致力教育,终身不嫁”。1920年,向警予与蔡和森结为伉俪,但二人的婚姻模式却别具一格。结婚纪念照是二人共同捧读《资本论》,并以“同盟”代替“婚姻”。这对于当时许多正处于批判旧式婚姻的年轻人来说,“向蔡同盟”无疑是一次婚姻模式的巨大革新。对此,青年毛泽东曾在给罗学瓒的去信中大为称赞,并提议“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1]323。
婚姻改称为“同盟”,称谓上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摆脱了传统家庭的性别角色和道德观念。别人眼中的“蔡太太”和母职身份不仅让她无法掩饰自己的性别,更增添了在工作中无法挣脱的自身性别局限。革命中创造的爱情同盟形式在现实中并不能挣脱旧式家庭道德和情爱伦理的束缚。由于向蔡二人的感情变化,在莫斯科的向警予情感生活处于极其紧张的状态,“每当她个人或同着和森最痛苦的时候,她每每回转心肠咬紧牙齿这样的叫甚至这样的写道:‘只有为革命而死,绝不为爱情死!一点泪一点血都应为我们的红旗而流,为什么爱情而流呢?可耻!’。”[1]343蔡和森体会到了这种情感伦理的痛苦,但他坚信革命者的向警予必定是以革命的方式来面对痛苦,“她纵然禁不住自己愈加痛苦起来,同时又愈加强固了自己只有为革命而死的决心。”[1]343作为男性知识分子精英的蔡和森,一贯持有国家民族解放的性别隐喻。他站在男权中心立场将向警予的命运与国族命运相联系。在革命洪流中的向警予,她的情欲,理应被革命所取代。
然而,如果向警予仅是焦虑于革命与爱情的不可兼得,那么,向警予和彭述之,蔡和森和李一纯之间的情感变化,却似乎难以用革命与爱情的取舍关系做注脚。向警予勇敢地向蔡和森坦白了自己的感情变化,但仍无法逃离党内受制于传统观念对女性的伦理约束。“向蔡同盟”也无法摆脱传统婚姻观念的窠臼。五四运动对女性解放最终的婚姻指向决定了觉悟女性的离家出走,实现个人独立后的最终归宿仍然是婚姻,且除婚姻之外,别无它路可寻。革命中的女性婚姻也仍是置于传统婚姻框架内,女性革命者与男性革命者迈入婚姻殿堂就意味着成为辅佐丈夫革命事业的革命伴侣。这与妇女在传统婚姻家庭中对丈夫辅佐和服从的两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相似性的。
在向警予生命的最后两年,女权焦虑和大革命的失败让她陷入到极度痛苦中,她以坚定“只有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和加倍地忘我工作来缓解痛苦,直至牺牲。无可否认,男性知识分子倡导了近代中国的女性解放启蒙,尽管表象上是女性被置于男性中心所建构的话语体系下,但向警予的女权焦虑映射了女性主体性的觉醒和男女两性对于社会改造的不同性别诉求,也印证中国妇女解放自晚清以来与中国社会变革相伴相生,但又独具自我延续的脉络。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中国化成为这一脉络中最为显著、也最具实效的主体力量。
二、消解“焦虑”与话语建构
向警予的“女权焦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党内男权思想的顽固性和觉悟女性在探索女性主体性时的困惑,以及妇女在国家民族语境中解放自身、争取主体独立性时的艰难。同时,向警予的“女权焦虑”也促使我们去探究中共早期从事妇女运动的同志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实际结合中去消解焦虑。通过考察20世纪20年代中共党内革命家对妇女解放思想的相关文本,本文从向警予“女权焦虑”的两个方面:革命中的性别角色塑造和革命与婚恋的关系,尝试探讨党内妇女工作者在建党初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建构。
(一)在无产阶级解放的宏大叙事中争取妇女解放的革命空间,策略性地运用男性主流话语建构女性的主体身份
早期中共男性党员大多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妇女问题,将性别问题纳入阶级分析,把妇女解放等同于劳动妇女的解放,进而等同于阶级解放。陈独秀认为社会制度造成的不平等需要社会主义来解决,妇女问题在该过程中“自然是连带发生”,当时社会上所列举出的种种妇女问题不过是经济问题,“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因而生出无数痛苦的事情”,所以,同属于弱者的女子和劳动者,“除了社会主义,没有别的办法”[2]。陈望道把“女人运动”(妇女运动)分为两类。一是为恢复女子“自由和特权”的“女人对男人的人权运动”,二是消除贫富不公的“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他认为前一种运动“反对男女差别”,其结果不过是有产者的平等,并非是人类的平等,但后一种目的是“驱穷”,获得人类平等,是男女合力的阶级解放运动。[3]这些观点普遍认为阶级解放就是妇女解放,不需要单独的妇女解放运动。
1923年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全面开展,在解决中国妇女运动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时,较早具有性别觉悟的党员不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而是将马克思妇女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性别议题实际。在阶级与革命的话语体系中区隔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利用妇女工作的性别优势,在男性主流的阶级解放理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初步建构,形成了具有中国妇女运动经验的理论特色。
1.建构了被压迫妇女从统治阶级手中“取回”权力的理论,从而论证了妇女解放具有的自身特性和价值合理性。肖楚女在《“女子解放”底根本义》中提出,中国妇女解放的两重要义的内核:第一,摆脱传统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玩具化”形象塑造,“女性自身提高女性美”;第二,妇女解放的目标具有价值合理性,是取回应有权力,而不是争夺他者的权利。反对把女子解放“看作是女子对于社会的要求或者可以由社会给予女子的事”,如果把女子解放放在“待解放”的位置,“到底得不到解放”[4]98。肖楚女把妇女解放由“争”转为“取”,无疑是从性别视角来看待妇女解放,通过对妇女解放的重新定义,建构了妇女解放的价值立场,并尝试将社会性别视角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视角的互补使用。向警予《力争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也大声疾呼,“权利不是支配阶级给予我们的恩赏物,而是我们向支配阶级手里夺回来的战利品。”[1]224
2.立足于劳动妇女立场认识国内妇女解放观点的差异,配合国民大革命的革命要求,建构“妇女群众”作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体地位。恽代英在《妇女运动》中指出,新文化运动中“投机派男子”假借妇女解放来求自身的解放,一旦目标达到便“把一切社会问题都抛之脑后”,“少数所谓‘解放的妇女’”的中产阶级女权团体也与这些“投机派男子”一样。所以,妇女的解放是“全妇女的解放”,“只有全体的解放,没有个人的解放”[4]290-292。“全体妇女的解放”意味着妇女群众的解放,反对把妇女解放割裂为妇女内部各阶层的解放。
杨之华《中国妇女运动罪言》分析了大革命时期国内各派妇女运动的缺点,归纳总结了各派的政治思想,分别为“守旧的宗法社会见解”,“基督教会式的‘欧化式’妇女观”,“妇女主义者的妇女观”和“国民革命妇女观”。她提出,各派别应“抛弃自己政治上的特别用意”,以国民革命妇女观为指导,用“妇女切身利益的总要求”来建立中国妇女运动的大联盟,“使妇女群众参加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这样中国妇女才有男女平等的希望。”[5]
尽管1928年中共六大《妇女运动决议案》认为,随着大革命失败,“妇女的联合战线”已不具有积极意义,也将妇女群众等同于工农妇女,但党的妇女运动的群众化工作宗旨被保留下来,这就使“妇女群众”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指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绝大数成员的总和。妇女群众虽然在中国历史各个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但一切争取解放的妇女都属于妇女群众。这就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拓了更为宽广的空间,争取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3.结合中国妇女运动阶级分化的实际和国民革命的大背景,把阶级解放运动转化为妇女运动的实际工作,以“妇女事业”作为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经验的基本原则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实践特征。杨之华在“五卅惨案”后总结上海妇女运动经验,认为五四之前的中国妇女是以被压迫妇女的整体概念出现,“直到五四运动,一般女子才被新潮流冲动了自身的问题”,原因在于“五四运动之后所谓新文化运动之中便开始阶级的分化,妇女运动也是如此”。她以作为全国妇运缩影的上海妇运为例,对妇女运动中的各派别进行了归类描述。尽管各妇女团体代表的利益不同,但各派都在为中国妇女解放努力,面对强大的敌人,唯有大家团结起来,“组织能代表一切被压迫妇女做运动的团体”[4]309-313,才能获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向警予从实际出发,提出“以社会主义的互助协进代替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的妇女解放途径的具体实施方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宣传设计、组织婚姻自觉联盟、儿童公育、妇女教育经费借贷、工读互助团等6项极具建设意义的措施。[1]11-21从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妇女运动的决议》到1928年中共六大的《妇女运动决议案》,短短7年间,中共中央通过了十多份关于妇女运动的正式决议案。早期从事妇女运动的中共党员正是将妇女运动的实践经验转化为中央的决议,从而把妇女的性别话语纳入主流话语,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把“妇女事业”作为基本原则的妇女解放运动,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特征。
(二)以女性立场建构革命中的女性与性、爱情与革命的新型关系来消解传统社会对革命女性的性别角色塑造
胡适在其日记中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划分,提出以1923年为线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是“集团主义时代,1923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皆属于反个人主义的倾向”[6]277。在革命宏大叙事下,属于私领域的爱情、家庭都进入公领域。革命是无私的,要先革命后恋爱。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和无政府主义成为当时党内情欲与革命关系的主要思想来源。施存统认为婚姻本质上对感情和性专属于某一个人的要求,让人无法忍受。[7]陈乔年甚至将革命者的情欲激进地表达为如同“同喝一杯水和抽一支香烟一样”简单。[8]991927年6月胡汉民发表对当时存在不同恋爱观的态度时,就明确以“最讨厌无产阶级专政尚未成功,但痨病已到第三期”[9]来嘲讽当时共产党人的情爱观。
革命的激进转化为对情欲的激进态度,对传统两性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的男性来说,两者并无不妥。无论是封建家庭伦理中性的“保守”还是革命浪潮推动下性的“解放”,男性总是基于男性中心立场来要求女性。女性在自由恋爱呼吁下走出家门,但最终却无奈地发现自由不过是选择嫁给男人甲还是嫁给男人乙,婚姻仍旧是女性唯一的归属,且两性关系依旧受传统家庭格局限制。在传统家庭礼教的框架下,革命女性相较之普通女性而言,对于女性与性、爱情与革命的紧张体验更为明显。
党内对女性与性、爱情与革命关系在感知上的性别差异,既反映出革命女性的性别敏感与革命男权中心之间的紧张,另一方面也促使具有性别觉悟的党员通过党员活动和思想交流,努力消解传统文化的性别刻板印象,“使党组织不仅是一个革命团体,也成为一个变革传统性别关系、挑战传统文化的亚文化群。”[10]304
1.党内妇女工作者尝试以唯物史观来看待两性关系,并基于女性立场建构革命女性与性的关系。1920年,沈雁冰以性道德为例,批评社会对待妇女问题缺乏对实际问题的关注。他认为男女两性的性道德不平等,是“第一解放”。但“解放”不是让女性效仿男性在传统关系上的霸权,而是创造两性共同遵守的新道德,“才是‘人’的办法,不然便入兽的行为”[11]。沈雁冰以“妇女问题原是社会改造问题之一”尝试将两性关系问题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用平等的两性新道德来建构女性在此问题上的话语权。
如果沈雁冰是尝试以唯物史观来看待两性关系,那么肖楚女则是希望不仅要用唯物史观挖掘出女性在性别问题上不平等,而且更需要在女性立场上建构革命女性与性的新关系。他在《“女子解放”底根本义》开宗明义提出,女性需要解放“性”。解放“性”就是改变性别刻板印象,使女子不能以“女性特质”成为男子的玩具。他认为,导致女性“玩具化”的原因不单是文明进步引发的“人类底‘趣味刺激’”提高,更在于“经济日益偏向男性中心”,因而对女性的尊重仍停留在“不是在尊敬‘女’性的‘人’而是在尊敬‘美人’”的传统两性观念。女性的生理性征在两性世界里仍然是对女性的能指,而人的“意思总是只指男人”。女子只有“从自己解放自己做起”,改变自身对女性“柔弱的‘我是女人’”的性别刻板印象,否则男女就无法在心理上达到“性的平等”。对于如何激发革命女性主体能动性,进而改变对自身的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肖楚女提出“‘忘其所以’的性解放”。所谓“忘其所以的性解放”,就是在承认两性生理差异的前提下,用“心理学的两性同观”来进行社会性别建构,通过“女性自身提高女性美”,并以“和愉而含刚健,婀娜而现庄严者也”的标准来建构女性美。[4]99-101尽管受时代限制,肖楚女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仅表述为生理学的性和心理学的性,但俨然已触及了性别的社会建构问题。更令人佩服的是,他提议抛弃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本身就是动摇男性中心的性别塑造,这是在女性立场上对革命女性与性关系的建构与言说。
2.党内妇女工作者普遍接受革命高于爱情的恋爱观,但反对以革命或反传统的名义绑架爱情,呼吁革命女性在恋爱与婚姻中的主体能动性。年仅17岁的张若名在1919年《觉悟》创刊号上撰写《“急先锋”的女子》文章,高呼“女子解放从女子做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号召具有“真心提携”,“牺牲精神”和“独身主义”的“急先锋”女子作为妇女运动的代表,来引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12]。她的呼声代表了当时女性主体意识日益觉醒的大多数革命女性对于革命与爱情关系的基本看法:只有不婚才能真心投入革命,无私地为革命牺牲。倘若革命者必须面对爱情,也只有将两性之间的爱慕转化为共同的革命事业,恋爱成为“革命同志爱”,似乎才是革命与爱情的正解。但当恋爱的私领域完全被革命的公领域代替,最终演变为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革命爱情的时候,个人的情爱标准就同质化为革命理想的一致与否。由于向警予和蔡和森的感情变故,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二人不得不离开火热的国内革命前线。爱情影响了革命工作,向警予焦虑于力争做去性别化的革命家却又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女性情欲。“当革命介入恋爱,很可能解决不了恋爱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被扭曲的恋爱是可以反噬革命的。”[8]100
面对革命,舍弃爱情。这仅是五四之后革命女性在婚姻爱情上所面对的一个场景,而另一个场景是以革命和反传统的名义绑架爱情。1922年7月到8月,《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先后刊登了两篇批评所谓新青年恋爱观的文章。文章针对某男青年曲解反传统婚姻恋爱观,将自己的感情以革命和反传统的名义强加于所爱慕的女子的荒唐做法,辛辣讽刺了当时男女青年在恋爱自由上不对等的性别地位,而文中的女子和文章的作者就是中共妇女运动的卓越领袖杨之华。
杨之华批评当时所谓的“新”青年把男女社交与恋爱同质化的错误观点。男子对女子社交的鼓励,不过是美化为爱情至上、被暗恋女子必须接受的“单相思”,更有甚者把社交当做“吊膀子”手段。在杨之华看来,打着“新”的名义用社交绑架恋爱,其结果不过是“新新旧旧混合起来竟比旧的还要旧,比污浊的更污浊”[13]。她在文中大声疾呼女子恋爱自由的前提必须是自由意志。对于求爱者把无产阶级的求爱方式当做“吊膀子”的谬论,她指出“吊膀子”实质是“不生产者虚伪的没廉耻的诱骗异性的专有名词”,用无产阶级来掩饰“两性间一种恶行为”,“简直污蔑了纯洁的无产阶级”[14]174-177。以革命和反传统名义绑架爱情的荒唐做法让杨之华认识到,即便在进步青年中仍然存在两性间的不平等。女性依旧被简单地视为男性的对象,男女社交也被狭义地定义为两性出于吸引而进行的社会活动,完全将革命女性走出家门进入公领域的社会革命贬低为“自由婚恋”。
反观五四社交公开的模式,它内生于男女性别权力秩序的等级社会中,自由的婚恋是建立在知识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想象基础之上,男子决定恋爱自由权。婚姻基本形式仍是以男性传承为婚姻关系的轴心,两性性别塑造的社会机制仍牢固不变。女性如若不能改变在婚恋中的被动地位,婚恋自由不过是男性家长制的另一种表述罢了。对于这个问题,杨之华认为婚恋自由一定要强调离婚自由。不仅受旧式婚姻制度压迫的婚姻可以离婚,自由恋爱的婚姻也可以离婚,“即使恋爱是自由的、自然地、长期的,也须得经过不满意的过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还是应该出于离婚底一途”。这对于当时社会认为女性的婚姻不幸在于被封建礼教迫害,把新式婚姻作为妇女解放最终归宿观点给予了有力的反驳。文末,她鼓励女性勇敢摆脱婚姻的各种束缚,尊重自己的自由意志。“经济不能独立,也不要紧,只要身体强壮,终有生活可度。一人有一人的天然力量,何必定要依靠别人,别受一番痛苦呢?!。”[15]
除了杨之华强调的离婚自由,党内妇女工作者也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提到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家务劳动社会化获得启发,提出用儿童公育等实际措施改变婚姻家庭中女性的传统性别定位。向警予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中把组织婚姻自觉联盟和儿童公育作为女性全体解放的途径。可以看出,区别于当时国内其他女权思想仅限于理论讨论,中国共产党不仅寻求妇女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而且更注重在实践中创造中国妇女解放的女性经验。
结 语
早期在中共党内工作力量上占据优势的男性,尽管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但在实际工作中仍部分延续了传统男权思想在语言上的控制权以及机构上的支配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向警予陷入了革命工作的“男同志与女同志”性别分工,婚恋与革命的双重女权焦虑之中。从向警予的女权焦虑出发,本文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党内革命家对妇女解放思想的文本梳理,发现党内早期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同志尝试通过理论探讨,发动和组织妇女群众开展解放运动,并与残存于社会和党内的传统男权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她们在无产阶级解放的宏大叙事中争取妇女解放的革命空间,策略性地运用男性主流话语建构革命女性的主体身份,并以女性立场建构革命中的女性与性、爱情与革命的关系来消解婚姻家庭中的传统性别角色塑造。这种跻身主流话语结构,为女性解放赢得支持的做法也成为日后中国妇女解放本土化实践中最典型的特质。而与此同时所建构的具有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特色的基本话语,如“妇女群众”“妇女事业”等,日后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工作话语体系的建构基石。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最为详尽的一份妇女文件。议案较为系统地总结了自大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的经验教训,肯定了妇女运动在革命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今后的妇女运动指示了方向。与此同时,1928年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的《改组中央党部案》,以“妨碍本党代表国民之利益”为由,取消原中央党部的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五个部,另设民众训练委员会取代上述各部工作,以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来代替争取解放和自由的女性形象。[16]20世纪20年代末国共两党对女性不同的态度表明,经过中国共产党早期倡导和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同志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已经开始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
【责任编辑 赵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