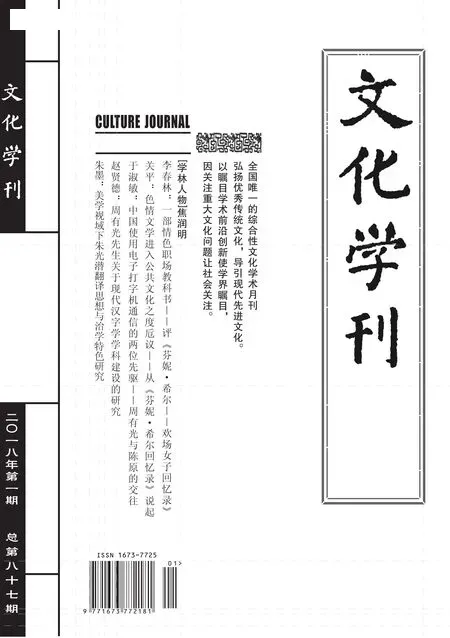突厥碑文中叙事人称的功能特征
——以古代突厥三大碑文为例
任仲夷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一、古代突厥三大碑文简介
“暾欲谷碑,于1897年由克莱门茨夫妇(D.A.E Klements)在距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东60公里的巴颜楚克土图(Bayin-tsokto)地方发现。碑文刻在两块碑上,共62行,似为暾欲谷生前自己撰写,立于716-725年之间。暾欲谷为第二突厥汗国(618-744年)三代可汗的重臣。他生于7世纪40年代,曾在唐朝受过良好的教育。碑文主要介绍了如下内容。第一行,讲述了暾欲谷的童年和青年时期以及突厥隶属于唐朝的情况。(2-4行)讲679-681年突厥不成功的起事。(4-6行)以颉跌利施为首的突厥人成功起事和暾欲谷参加起事。(7-11行)讲述迁阴山前的事件。(12-15行)讲迁到突厥传统圣地于都斤山林的情况(687年)。(15-17行)讲述征服乌古斯的情况。(18-19行)讲述山东地区的入侵。(19-29行)讲征讨黠戛斯的情况。(29-43行)讲征讨西突厥和突骑施之事。(43-47行)讲远征铁门之役。(48行-结尾)讲颉跌利施可汗和暾欲谷辅佐他及继承人的功绩、结束语。”[1]
“阙特勤碑,于1889年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额尔浑河支流河谷和硕柴达木地方发现。该碑现在仍在原地。碑为大理石刻成,上刻汉文和古代突厥文两种文字语言。碑文为纪念第二突厥汗国重要人物阙特勤(685-731年)而立(732年)。碑高335厘米,东西宽132厘米,南北宽46厘米;古代突厥文共66行,刻在大、小两块石碑上,大碑东面写40行,小碑南北两面各写13行,应为碑文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其余部分刻在碑的边上。背面为汉文部分,为唐玄宗开元20年(732年)亲笔书写。古代突厥文部分由药利特勤(yollig tigin)书写。”[2]
“毗伽可汗碑与阙特勤碑于同时同地发现,该碑也为大理石制成,高375厘米。原石碑立在石龟背上,现石龟已碎成数块,现碑文仍在原地,碑文用古代突厥文和汉文写成,破损程度比阙特勤碑更甚;东面41行,南北各15行,西面为汉文;东南、西南和西面也写有古突厥文,似由其子登利可汗建于公元735年(唐开元23年)。古突厥文部分出自药利特勤之手。南面10-15行似为登利可汗的话。西南面为药利特勤的话。”[3]
二、第一人称叙事的功能特征
(一)真实性
“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人称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概括起来看,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有很多优点。首先,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真实感强,尤其是在当叙述内容中夹杂有某些具体可考的历史事件与明确的时空背景时。”[4]如:《暾欲谷碑》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机制,当读者阅读作品时,很容易把“我”与作者重合。但从整个碑文的内容来看,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突厥隶属于唐朝。“我”帮助颉跌利施可汗起事并取得了成功,“我”帮助可汗迁到突厥传统圣地于都斤山林的情况以及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发生的战争。“我”用了回忆往事的叙述方式,按照时间顺序,从童年到衰老,追忆了“我”过去的经历,讲述了“我”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一生。这里把“我”的人生经历通过“我”的情绪、行为和语言表述出来,使叙述主体“我”与作品中的“我”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使碑铭作品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增强了真实感。
(二)抒情性
“伴随着这种真实感而来的,是一种亲切感,即没有距离、不显得居高临下,叙述者如同是在同朋友作促膝肯谈,真诚、坦白。所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亲切感也往往意味浓郁的抒情性。”[5]《阙特勤碑》虽然是碑铭文献的典型代表,但也可以看作是一首抒情的长诗。例如《阙特勤碑》北面10-11行:
“要是没有阙特勤的话,你们都将死掉。我弟阙特勤去世了,我自己很悲痛。我的眼睛好像看不见了,我能洞悉一切的智慧好像迟钝了,我自己十分悲痛。寿命是上天决定的,人类之子全都是为死而生的。
我十分悲痛。眼睛流泪,我强忍住;心里难过,我强抑住。我万分悲痛。我想,两设及我的诸弟、诸子、诸官、我的人民将哭坏他们的眼睛(直译:眼眉)。”[6]
这段话记录阙特勤去世了,对于突厥人来说这是巨大的损失。回想阙特勤一生的战功,对我来说他的逝去,也是令我悲伤的。我十分悲痛,强忍住我的悲伤,但是人的寿命由天决定,也无法挽回。我和我的诸弟、诸子、诸官、人民都为他而流泪。这一段叙述充满了悲伤的情绪,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拉近了读者与叙事主体的距离,真实感更强烈,显得更为感伤,带有强烈的主体抒情性。
《暾欲谷碑》东面51-58行:
“默啜可汗二十七岁时,我辅佐他即位。我夜不能眠,昼不能坐,流鲜血,洒黑汗,我为国贡献了力量。我也派出了远征军。我扩大了禁卫队,我自己的努力,国家才成为国家,人民才成为人民。我自己已衰老年迈了。不论什么地方,凡是有可汗的人民中,只要有像我这样的人,就不会有什么不幸。”[7]
这段文字讲述暾欲谷作为一个谋臣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一生。虽然语言朴实无华,却凸显了暾欲谷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夜不能眠,昼不能坐,流鲜血,洒黑汗”的细节描述深深地感染读者,使人物血肉丰满,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碑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抒发了略带感伤的情感,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结构上开合自如
“第一人称的优势同样还表现在结构上的开合自如,能给叙述者在叙述时间上的转换提供更大的方便,和对叙述手段的更自由的调度。”[8]如《阙特勤碑》,在南面叙述了“我(毗伽可汗)”的事迹,东面1-4行叙述“我”的祖先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东面30行叙述“我”弟阙特勤的功绩。这种结构的安排,让人觉得碑文似乎与多位叙述者撰写有关,一会儿说“我”,一会儿说“我”的祖先,一会儿说“我”弟阙特勤,结构的安排似乎没有逻辑性。但就碑文的整体来看,正是因为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使看似散漫的材料顺理成章地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重要的并不存在于对人称的选择,而在于这种选择的背后存在着的叙事主体对叙事文本的总体效果和全盘的考虑。因为叙述的人称并不像我们先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小说家为了讲述某个故事便从词典里随手拽出来的几个代词:而是意味着一种叙事格局的确立,这种格局关系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方式”[9]。碑文先说“我”的功绩及刻碑的目的,之后又讲述“我”的祖先怎样努力地建立国家,在国家衰落之后,“我”和我弟阙特勤使国家强大。叙事技巧表现在叙述人称上便是对三组代词即“我(我们)”“你(你们)”和“他(他们)”的灵活调度。结构不受情节的束缚,显得开合自如。
“第一人称叙述的另外两个特点是,以概述手段为主干和叙述者“我”总是作品中的一个具体人物。这两个特点的长处是有助于强化叙述趣味,便于描写其他人物,缺点是场面效果的减弱和不能让读者清晰看到担任叙述本人的真实面目。因为在这样的文本中,我向我们描绘介绍自己的唯一方式是表白,这极易导致自我表现。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倾向,叙述者有必要采取自我限制,尽量少谈自己的事。所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真正重心其实不在“我”,而在我周围的其他人物,处于光环中的那个“我”其实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主角,他在作品中的真正意义是充当叙事主体。”[10]
《阙特勤碑》的书写者为药利特勤。碑文的南面介绍了毗伽可汗的事迹,“我,像天一样的,从天所生的毗伽可汗,坐上了汗位,你们全都聆听我的话,首先是我的诸弟和诸子,其次是我的族和人民,右边的诸失毕官,左边的诸达官梅录、三十姓(鞑靼)”[11]。从碑文的南面看,似乎是在写毗伽可汗的功绩,但是从碑文的整体来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阙特勤的事迹,碑文通过“我”的眼睛,呈现了阙特勤一生中重要的战功。“《阙特勤碑》当我父可汗去世时,我弟阙特勤七岁。当他十六岁时,我叔可汗这样获得了国家和法制,我们出征六州粟特人,破之。当他二十一岁时,我们与沙吒将军交战。当阙特勤二十六岁时,我们出征黠戛斯。当阙特勤二十七岁时,我们战于圣泉”[12],此处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来表述其他人的故事,此时的“我”只是起到了一个旁观者的作用。
三、第三人称叙事的功能特征
“第三人称的叙事完全是过去的,这种过去性使时间概念在这类叙述中反而被模糊。因此在第三人称的叙述中,故事时间与阅读时间的距离名存实亡。而正是这种时间距离的消亡,使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被拉大,作为其具体反应的是接受心态上的相对超脱。阅读实践也清楚表明,当一切都以第三人称叙述时,旁观者就好像绝对的与事无涉。正如天然具有一种独白的架势,在这时,叙述接受者处于倾听的位置。第三人称本质上似乎就存在一种描写的情势,叙述者处于旁观的位置。”[13]
《阙特勤碑》东面31-39行:

北面1-9行:
“他与……交战,并与哥舒都督交战,他杀死了全部勇士。他获取全部毡房和财产。当阙特勤二十七岁时,葛逻禄人成为敌人,我们交战于圣泉。

《阙特勤碑》按照时间的顺序记载了阙特勤一生的主要功绩。这里从阙特勤青少年时期开始叙述,描写了阙特勤在十六岁到三十一岁时的几次主要的战争以及阙特勤骑马进击的过程。以上两段碑文叙述客观和有序,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叙述者可以通过对“他”的描述介入进来,这样人物本身也就成了我们所观察的对象。
第三人称又能使叙述更加客观,这种叙事方式可以抑制作家个人情感的泛滥,防止过多投入主观情感,以达到叙述的客观化和有序化,比第一人称叙事更便于较客观地审视人物、理解人物,做到对某种生活现象的深入剖析。例如《阙特勤碑》东面1-4行:
“当上面的蓝天、下面褐色的大地造成时,在二者之间创造了人类之子。在人类之子的上面,坐有我祖先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他们即位后,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这时四方都是敌人。他们率军出征取得了所有四方的人民。全都征服了。他们统治着二者之间没有君长的兰突厥。他们是英明的可汗、勇敢的可汗。他们的大臣也是英明的,勇敢的;他们的诸官和人民也是正直的。因此,他们这样统治了国家。他们这样统治了国家并创建了法制。他们去世了。”[16]
这段文字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没有投入叙事主体的情感,没有分析人物心理,只是客观叙述了我祖先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创建了自己的国家和法制。这种不动声色、不露情感的表述,却也达到了相应的效果。使我们感受到了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为建立国家和法制所付出的努力,也展示了大臣的英明、人民的正直,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如果把这段话改为第一人称,则就会转变成一种倾诉的语调,就达不到相应的效果。
四、结语
古代突厥三大碑文主要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这种对人称的选择反映了叙事主体对叙事文本总体效果和结构的思考,有助于把握叙事艺术的发展变化。其中第一人称是最常用的人称,它真实感强又有抒情性;而第三人称通常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世界,客观性强。对于人称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突厥三大碑文的结构脉络。
[1][2][3][6][7][11][12][14][15][16]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92.119.148.144.111.116.136-140.136-139.139-143.123.
[4][5][8][9][10][13]徐岱.小说叙事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6.306.307.308.310.31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