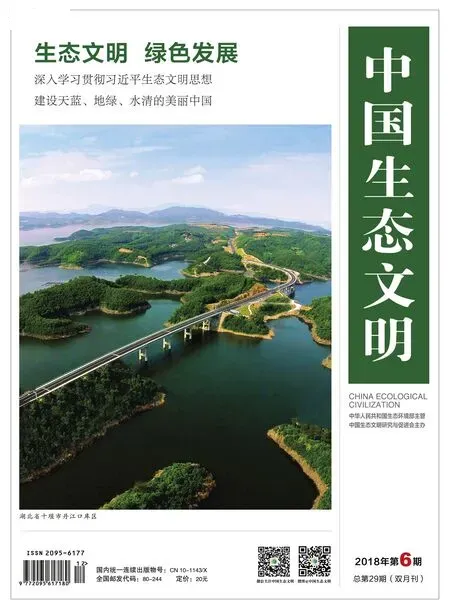践行严密法治观 完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
论坛共识(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王树义现场总结):大力推动、促进、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这部法律可以叫做《生态文明促进法》。这个提议不仅恰逢其时,时不我待,非常必要,而且也十分可行,有关思想、理论、实践、法律准备已经完全成熟。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
环境与健康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公众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作为法律人,需要回答:环境保护的法律需求是什么?是否等到损害后果发生后才能进行法律救济?以救济为中心的既有模式是否足够?源头治理、风险规制是否应该成为环境法的制度主体?健康风险的特征,对环境法规制提出了需求,必须在法律上建立适应型的制度体系:危害后果的不可逆性要求确立“风险预防原则”;风险发生的交互性要求建立“整合式管理体制”;因果关联的不确定性要求明确“科学决策机制”;利益冲突的广泛性要求广泛的“公众参与”。这也意味着,新型环境法必须改变“污染控制”的规制模式,“危机应对”的规制理念,“罔顾科学”的决策程序。中国环境法必须走向第二时代——风险控制时代。
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别涛: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推动环境法治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由于小平同志“点名”推动环保立法,1979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环境保护法(试行)》。四十年来,我国环境立法最为活跃,修订最为频繁,成效也最为显著,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涵盖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自然资源管理、核安全以及环境管理,并包括党内环保法规在内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环保法治成就,我们更加缅怀邓小平同志的杰出贡献,要继续推进新时代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孙佑海:
建议制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其制度构想应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8方面。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执行副会长李庆瑞:
应借着生态文明入宪的大好时机,加快推进法律生态化。具体来说,应尽快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生态化改造,起草制定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综合性法律,适度实现环境法律法典化,不断配套完善生态环境资源法律体系,同时还要加强行政执法和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等。
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高级法官李明义:
中国特色的环境司法理念应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理念,服务国家污染防治战略的理念,准确把握发展与保护的理念,最严格执法的理念,遵循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的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厅长付朝阳:
《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的颁布施行,具有标志性意义,福建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有了从整体和全局规制牵头抓总的法规。下一步将根据新形势、新要求,科学规划推进试验区建设的立法项目,积极探索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先于国家进行立法,及时将切实可行的改革成果和经验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与时俱进完善生态文明立法体系。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辛世杰:
重庆在全国率先建立三级法院纵向“全覆盖”式环境资源审判组织体系,探索建立“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成立环境安全保卫总队,出台《关于加强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意见》《环境保护与公安机关执法衔接工作实施办法》《关于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案件咨询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构建了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司法机关共同保护环境公益的新格局。
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教授李永宁:
推动生态文明的大政方针已经很充分、完备,建设活动也已经全方位深度铺开,现在需要的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把成熟的政策逐步上升为国家法律,其意志性、稳定性、长期性、可预期性也才会更加明确并不断得到增强。因此,制定《生态文明促进法》不仅恰逢其时,而且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实践准备、法律准备也已经完全成熟。其立法目的可以表述为: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法律原则可以概括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坚持生态优先、自然有价、循环发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原则。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管理系主任、教授梅凤乔:
提议中的《生态文明促进法》或《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应定位于“弘扬先进”,而传统环境法则侧重于“守住底线”。生态文明立法应当全面落实《宪法》规定的政府“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责,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让各种积极因素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具体来说,既要体现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引导、激励作用,又要明确要求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必要时,还应当通过制度创新,创造市场,让市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迸发出活力。
北京华盛坤泰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司军:
人民要生态权益,国家要生态产业,而很多污染问题是历史形成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污染治理资金从哪里来?我认为需要一部生态文明促进法来解决和完善。其中可以设计一种机制,比如成立生态产业类的基金,为修复生态环境以及必要的生态补偿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