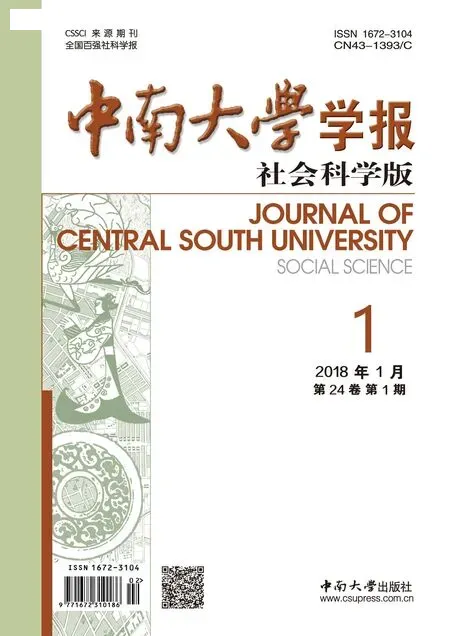法律与政治的对话:论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
董静姝
法律与政治的对话:论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
董静姝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102249)
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思想不仅推动法学思考自身学科的根本问题,也直面人类行动领域中法律与政治、规范与失范之间的对话,并对主权概念作出了更加有力的反思。此外,就实践而言,当代世界是一个法治与法外治理同时极大化的张力场域,一方面,在“规范性框架中运行”是权力的标准说辞;另一方面,权力的实际运行总是越过规范性边界。对此,只有超越实在法视野,对例外状态进行严肃思考,才能探索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秩序的整体之“法”。而以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思想观照中国的政治法律实践,也将获益良多。
乔治·阿甘本;例外状态;主权者
当今世界处于“法治”与“法外治理”同时极大化的张力场域之中。这一论断乍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只要我们冷静地审视,就能够轻易地找到佐证:美国号称是法治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法律在门类齐全性、内容丰富性、实施有力性、民众意识健全性等多项指标上都被认为优势明显;但同样也是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后颁布了《爱国者法案》(),对内大幅度“解放”行政权力,悬置若干保障基本人权的宪法规范,对外则通过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延续这种“悬置”,将法外空间扩张到世界版图中,从而引发跨越主权疆界的“内战”。而许多人(包括法学家)对此竟视而不见,仍然沉醉于“法治”梦境。殊不知他们所忠诚与歌颂的对象——法律(自实证主义思潮风靡后,这个概念已被压缩为逼仄的“国家制定的实在法”)——究竟在何种意义以及多大程度上维持存在和发挥作用,已变得相当可疑。触目皆是的悬置法律的景象,将我们抛入法律与政治彼此角力又彼此融贯的场域,或言之,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
然而,一般人对此漠不关心也就罢了——例外状态的常态化(或曰规范化)已使得他们安之若素——法学家漠不关心却无异于放弃或回避思考自己学科最根本的问题:正是在例外状态中,法律秩序的根源、主权者的面目、从事实到规范的转换、法律与政治的交锋等问题才异常清晰地暴露于视野。无怪乎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就曾像牛虻一样质问:“你们法律人为何对那与你切身之事保持沉默?”[1](题记)
因此,尽管法治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但这个主题是内涵和表现形态已经发生变化的主题。而例外状态不仅在学理上有被思考的价值,在实践中也需要被严肃审视。本文将对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思想作出考察:沿着阿甘本的理论路径,首先进行例外状态概念的历史脉络梳理,然后从规范−失范和神圣−主权者切入到对这一概念本身的解剖,最后通过相关实践揭示例外状态的常态化这一乍听之下不可思议、事实上却渗透(尤其是当代)人类行动领域的现象,并为中国自身的相关政治法律问题打开新的思考路径①。
一、例外状态概念的历史溯源
追溯一个概念的雏形或原初意义,并观察其在历史中怎样获得丰富性和发生演变,将有助于我们完成对概念的透彻理解与反思。阿甘本对例外状态作出了知识考古,使得我们能够直面这一概念的复杂内涵与由此而来的真切困局。这里旨在对阿甘本的例外状态词义系谱考察作一个简单概述,为阿甘本对例外状态更加深入细致的概念剖析作一个理论史铺垫。
在探索例外状态概念的蓝本或模型时,不同于施米特追溯至独裁(dictatorship)②,阿甘本追溯至古罗马的institium概念:共和时期,当发生威胁共和国政治生存的极端情势时,元老院发布终极咨议,号召执政官、裁判官或护民官,甚或是一般公民,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拯救国家。而这往往便导致institium——悬法(suspension of law),即法律的悬置。这意味着法律效力(validity)和实效(efficacy)的割裂,或曰规范之存在与其实现之间的对抗强度达到峰值,即曾经被实际适用的法律,现在虽然依旧保持其形式有效性,却被中止实施了——而在正常状态中,法律不仅是有效力的,也是在相当程度上有实效的——这种效力对实效的“溢出”就好比符号之表意作用相对于指谓作用的盈余。与此同时,发生一种与之相反的情势,即某些并不具有实在法规范性的行为(无论抽象抑或具体)却实际上展开,但这并非实施法律,也非违反法律,而是“不实施”法律,或者说,对这些行为的价值判断已经不能在法律范畴之内进行。至于悬法中的行动者与独裁中的行动者(即独裁者),其根本性的区别在于:悬法中行动者的无限权力并非由于被赋予了独裁统治权,而是由于曾经对其行动设定边界的法律遭到悬置,从而(法律上的)边界被取消,行动者置身于一个“法律零度”的空间。
当古罗马进入帝国时期,iustitium的语意逐渐由悬法转变为国丧。但二者的政治意涵却相互映照:正如共和时期悬法是对动乱的回应,帝国时期的国丧也是对动乱——因主权者之死而(可能)引发的动乱③——的反馈装置。主权者之死导致整个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停摆(法律的悬置被整合于葬礼中),照鉴出“主权者作为活的法律”这一不仅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也在现代的主权理论中锋芒强烈的对主权者的定位:罗马皇帝不受法律约束,而作为承载一切国家权力的肉身(这意味着主权者权威不是什么“普遍规范”的,而是紧密依附于人格的),其任何行动都呈现出鲜活的法律生命。也由此,主权者与例外状态的关系向我们清晰地敞开:由于作为法与无法之根本连结的主权者死亡,动乱便从他身上释放流窜至整个国家④。
至中世纪,例外状态概念紧密地扣合于必要性概念,这可以从一句被反复吟诵的法谚中窥伺一二:必要性无法律可循(necessity has no law)。对于该法谚有两种相悖的诠释:必要性不承认任何法律;必要性创造法律。只有前一种诠释是属于中世纪的,后一种诠释则是现代的标签。在中世纪的理论路径中,必要性并非法源,而是在个案中割断既存规范的适用,发挥使外在事实合法化的“法律拟制”功能。现代政治思考则试图创造一个规范与事实叠合的地带,将必要 性−例外状态纳入法律秩序中,并且以必要性−例外状态构成法律的真正源泉与最终基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学思考对例外状态的“搁置”:因为例外状态与规范统摄下的公共/私人生活格格不入,所以应当将之视作单纯事实驱逐出法学领域,或者用一个黑箱式的规范⑤将之收纳。但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例外状态这一政治学倾注强烈热情而法学却鲜有问津的地带,事实与规范的暧昧、政治与法律的纠缠暴露无余,也使得我们面对如下仿佛无解的政治学−法学困局:假如必要性是一种单纯事实,则以其为基础的例外权力在立法系统中毫无规范性依据,那么政治学者又谈何将必要性作为法源呢?为什么一定要将之锚定在法律秩序中呢?假如必要性是法源,为什么又不能被编码进既存实在法律规范,还被法学者不予过问?与此相关的两个悖论就是:例外状态以将自己排除在法律秩序之外的方式将自己铭刻入法律脉络之中;站在正常有效的法律秩序之外的主权者却仍属于该秩序。
每一个共同体都有面临例外状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正如阿甘本所洞察到的,当今“世界内战”已经使得许多国家卷入例外状态的漩涡,例外状态即使在民主政体中也成为一种(尽管出于政治策略性考量而未经言明的)“治理典范”。对此,如上所述,政治学者已经作出了持续的研究,而法学界则似乎始终像阿甘本说的那样“保持沉默”。然而,如果我们沉湎于“法治”“规范之治”的温柔乡,而对最根本的“界槛”弃之不顾,那么也无力真正明白法治本身,更在法治沦为某种光鲜妆饰时毫无察觉、甚至为掩藏于该妆饰之下的实质卖力站台。这不仅是理论的悲哀,也是实践的不幸。当然,或许有人会说,所有学科/知识都是有界限的,都应当圈定自己的阵地并心无旁骛地经营。诚然如此。但问题本身是没有界限的,我们所处的时代也不能容许我们以“各自为政”的托词画地为牢或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何况,无论最终如何界定例外状态,其作为从法律实施到法律悬置再到法律实施的过渡指示标,作为人类行动两股力量(规范−失范)关系最盘根错节的地带,作为政治神学逻辑显示出强大力量的空间,都是每一个希望澄清法律概念的法学者所必须正视的。在下面,笔者将继续沿着阿甘本的足迹,以规范−失范、神圣−主权者两组相互对应的概念为线索,以现代世界为主要时空背景,对作为政治与法律对话场域的例外状态理论作一番深入剖析。
二、规范与失范的引力场
现代政治学奠基人之一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在其不朽的名著《社会契约论》中写道:“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2]其呈现的图景囊括了连同主权者-国家在内的诸多一体两面、彼此抗衡又彼此贯通的概念组:制宪权−宪定权,权威−权限、失 范−规范,以及例外状态−法律状态。可以说,上述“主权者−国家”公式基本定型了西方政治法律的骨架,卢梭以降的学者也不过是立足于自身理论兴趣和时代命题对该公式不断进行丰富、充实和发展,抑或据此圈定各自的研究阵地⑥。
阿甘本无疑也是沿着上述双元结构脉络继续推进思考,他在《例外状态》一书的最后一章中写道:“……一个是严格意义上的规范与法律元素(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将它置于‘权限’的标题下),另一个是失范与元法律的元素(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权威’)。”[1](137)与此相应,贯穿人类行动领域的是两股相互纽结又背道而驰的力量:一股力量从失范走向规范,将人类各种行动模式以规范“结晶”,据此有条不紊地定轨政治生活;另一股力量从规范走向失范,法律被悬置——甚或有时直接被整体颠覆,比如表现为制宪权对宪定权的“爆破”——而进入例外状态。
阿甘本更加倾注热情的显然是例外状态和作为“元法律”(meta-law)的主权者。不过有必要首先审视上述双元结构或曰两股力量:当我们言说其中某一方元素或某一股力量时,通常存有怎样的理论意图和政治用心。然后对戡阿甘本的思想,才明白他对例外状态作出了怎样的反思。
在上述两股力量中,“失范→规范”的力量无疑被现代法治国家频繁论述,它标志着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以自己的理性“驯化”失序并安顿自由,也显示出与过去人治时代的决裂: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行动都不再受特定个体或特定群体意志之主观性——这往往被饱尝人治之苦的受害者愤怒地等同于偶然性或恣意性——的摆布与钳制,而是接受“去人格化的”规范指引与规约。与此相关的概念是“权限”(competence),即以法律授予权力或曰以法律证成权力合法性的同时,设定权力的界限,将权力纳入法律的统摄之下,使之无论被谁享有和行使,都是“规范化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权力主体被法律“遮蔽”了,其人格性因素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更确切言之,不允许人格性因素“干扰”规范之治。
“规范→失范”的力量则是法治国家希望永久将之封印的,因为它意味着政治生活被抛入一个没有法律——更确切言之,法律仅仅维存其形式有效性,而现实适用的数值则趋于零甚至等于零——的空间。在此,被认为是理性之光和自由之盾的“去人格化”的规范统治就此失效。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学者要么将例外状态潦草定义为“单纯事实”而避之不谈,要么以一个黑箱式的规范遮蔽对之进行严肃审视的目光,这大概就是出于人类对所谓客观性与安定性⑦的强烈渴望。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不同于上帝那样全知全能的存在,人类理性始终是有局限性的。以预先创制的规范一劳永逸地安顿现在和将来的政治生活只能说是一种天真的妄念,在人类行动领域中彻底放逐人格性因素也是一种幼稚的幻想。或者说,就像因为害怕溺水便把所有湖海都填平一样,因为畏惧人格性因素的主观色彩(其实是畏惧主观性可能导致的偶然性或恣意性),就对之进行剿杀的做法,无异于假定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毫无摩擦阻力的、惬意安详的梦境。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在某个时刻,总会由于某种原因面临法律对政治现实鞭长莫及乃至二者之间发生深刻断裂的情境,从而与例外状态相遇。此时,墨守规范是不明智的,人格性因素则应当被解除封印。即使在法律状态中,也不能做到彻底封印人格性因素,因为总会存在因法律与政治现实的缝隙而导致的法律漏洞,在这些漏洞的填补上,法律保持沉默,必须仰赖法律实施者本身;在例外状态中,人格性因素则以更加激烈的姿态释放出来,并从具体之中孕育出普遍。与此相关的概念是权威(authority),这是一个无法用法律覆盖但又与法律规范性联系紧密的概念。
阿甘本正是对处于规范末路亦是规范发端的例外状态倾注研究热情,并对与此相关的权威概念作出了严肃考察。他认为,在私法领域中,权威的形象可以在监护人那里观察到,监护人的权威使得被监护人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而在公法领域中,权威在主权者身上得到最极端的呈现,主权者权威使得另一个或一些主体的行为(无论抽象抑或具体)具有法律效力。这两个领域中的权威形象存在着并非偶然的可类比性⑧,即权威具有“使……具有法律效力”或“赋予……法律规范性”的属性⑨,这是一种依附于权威者人格的属性。如前所述,这种人格因素在例外状态中获得彻底的释放,而其结果就是权限的悬置(因为设定权限的法律被悬置了)。但随后,当从例外状态返归法律状态 时⑩——如果共同体长久驻留于例外状态,人民的福祉就得不到保障;假若例外状态是一场狂欢,这场狂欢必须有谢幕的时候,因为人民的福祉寓于常态之中——权限又被重新活化(因为法律恢复了实效)。由此可见,例外状态是一个对失范与规范、权威与权限之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观测的绝佳场所,让我们认识到彻底的“去人格化”统治不过是一场幻梦,也让我们认识到人格性因素与非人格性因素的纠缠。
当我们在谈到权威——而公法中最典型的就是主权者权威——的上述属性时,就已经开启了那个至今未衰的经典问题:法律的规范性根基何在?显然,法律自身无法回答上述问题,因为这一“自我证立”无论在概念逻辑意义上还是在经验现实意义上都难以达成。“法律效力并非人类行动的原初特征,而是必须透过一种‘授予合法的权能’,才能将其转移到人的行动之中。”⑨如果说法律规范性最终追溯至主权者,而主权者本身又是超脱于法律之外的存在,这应当被如何理解?同样,例外状态也存在一个类似的悖论式拓扑结构:例外状态以法律之悬置而保持其自身与法律的关系。而由于作为公共人格之主动面向的主权者正是在例外状态中行动——在法律状态中,公共人格则以其被动面向(即国家)而存在——因此,理解了其中一个悖论,另一个自然也就迎刃而解。那么接下来笔者就对阿甘本的主权/主权者概念作一番审视。
三、神圣的主权者
主权/主权者概念在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脉络中始终被投入高度的关注。在阿甘本看来,在主权/主权者概念背后,暗藏着一套贯通古今的神学逻辑。这就意味着,主权/主权者概念的神学意涵并非只存在于遥远的过去(16世纪的加尔文提出“上帝主权”概念[3],主权之神学色彩十分醒目);在世俗化进程势如破竹的现代世界,主权/主权者概念的神学内核依然没有被剥除。对此,可以从不同视角来表述。比如,曾经坐在政治体神龛之中的是上帝,现在却是人民(即人民被“封神”了)——整个启蒙时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所致力完成的就是这种主权的“交接”;又比如,正如上帝超脱于因果法则(即使这因果法则由上帝自己创造)的限定,主权者也不受法律约束;等等。不过本文无意于讨论前一种人类对神明之僭越意义上的主权者理论,而在于考察后一种,与例外状态“遭遇”的、俨然尘世上帝的主权者。这也是阿甘本例外状态思想的精华所在。
阿甘本对神学与主权学说之间的融贯性揭示得非常清晰,而在这种融贯性中,我们也得以一窥上述悖论式拓扑结构的究竟。
在神学中,“神圣的”(sacred)一词,意味着属神之人/事/物;与此相关,“使某人/事/物神圣”就意味将该人/事/物从人的世界或曰俗世移除而交付于神明。祭祀就是这样一个神圣化的实践操作。而祭祀却首先包含一种暴力——被献祭的牺牲品被暴力性地从人间驱逐。不过,将俗世与神圣分隔的祭祀,却确立了政治权威的神话,即恰恰是俗世“之外”的神圣,赋予俗世政治统治以正当性,奠定了俗世政治统治的基石。
在主权学说中,同样能看到神圣的强烈光芒。尽管在共同体中并非真的存在一个存在论层面上的属神空间,但却存在一个政治神学意义上的属神空间——例外状态。而主权者就是那尊神明。与例外状态相对的法律状态则相当于“俗世”:一如在俗世中上帝蛰伏而不再行神迹,在法律状态中主权者也蛰伏而“法治国家”登堂入室。法律状态与例外状态的相互转换,也就分别是一个“神明显圣”(法律状态→例外状态)与“神明隐居”(例外状态→法律状态)的过程,即在“法律状态→例外状态”的转换中,原本藏于神龛的主权暴力释放出来,取代规范之治;在“例外状态→法律状态”的反向转换中,主权暴力则被重新收归神龛,被排除于“去人格化”的规范之治。而正如祭祀确立政治权威的神话一样,法律状态与例外状态的分隔也恰恰成就了法治神话,即,例外状态为法律之普遍性提供强硬的根基,主权者权威构成法律规范性的来源。
由此可见,神圣与主权者具有同构性:二者都既在俗世−法律秩序之外,但又并不因这种被排除而绝对无涉于俗世−法律秩序,而是作为支撑俗世−法律秩序的基石,因此,呈现出一种以被排除在外的方式——至高的例外(sovereign exception)——而被纳入俗世−法律秩序中的图示。作为一个政治神学地带的例外状态则“仍旧以规则之悬置的形式而保持它本身与规则之间的关系。规则应用于例外上的方式,便正是不再应用于后者、从后者那里撤离出来”[4](25)。从而,“例外状态实际上就在它自身的分隔性中,构成了整个政治系统赖以安置的隐秘地基”[4](13,14)。
于是,那关于主权者作为“活的法律”的界定就是可理解的了。正是主权者赋予法律以规范性,并在法律的形式有效性与实际适用发生断裂时,以自己的行动重新整合与规划人类的政治生活,这一行动不能以实在法作为判断尺度,既是因为实在法已经被悬置了,也是因为主权者身上本来就涌流着法律最本真、最鲜活的生命。“主权者是活的法律的说法只能意味着他不受法律(此处的法律显然是指实在法——笔者注)拘束,在他身上法律的生命与一种全然的无法状态相互重叠。”[1](110)在此,阿甘本对“法”或“法律”的理解已经突破了实证主义法学的狭隘视野,直指人类政治生活的整体法则。而实证主义法学——尽管其对“规范之治”绘制的宏图让人敬佩——由于缺乏对政治法律的整全性认识,无法容忍任何不被实在法规约的权威概念存在,因此竭力以实在法限定主权者,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恰恰是无法理解实在法本身;或者说,实在法只能为在其边界之内存在的“权限”作出注脚,却无法囊括在其边界之外存在并对边界内部发生根本性作用的(主权者)“权威”。
综上,我们看到,法律状态与例外状态随着始终贯穿人类行动的两股力量——规范与失范的搏斗——而交替出现在人类的政治法律脉络中,并向我们昭示着彼此间的“相生相克”。如果说法律状态以普遍性的规范之治和对人格性因素的软禁来彰显人类的理性,呈现俗世的常态幸福,那么例外状态则以法律之悬置和人格性因素的爆发来回应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昭示神圣的例外。在例外状态中,法律的效力与实效被割断(形式上存在而实际上不被适用),与法律之疲敝相对的则是主权者的积极行动,主权者作为“活的法律”超脱于实在法的定义与判断,做自己所意愿和能够做的事,并为实在法奠定规范性基石,乃至重新打开法律空间。在此,法律与政治令人难以辨认地彼此胶着。
然而,阿甘本对例外状态和主权/主权者概念的政治神学思考并不意味着他和其他某些学者一样以“神圣”竭力抬高主权者的价值,相反,阿甘本对“神圣”心怀警惕与抗拒,甚至希望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完成对“神圣”的反动。为什么呢?在下文中,笔者就将继续循着阿甘本的思想,对照实践,推进对例外状态的讨论。当把讨论的时空范围收缩到现代世界,我们就会发现本文开篇的论断并非戏言:当今世界处于“法治”与“法外治理”同时极大化的张力场域之中。这也就意味着例外状态的常态化,也即“神圣”的常态化。此时,我们将惊讶地发现,上述辐射整个人类行动领域的双元结构之区分似乎被取消了,或者说,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而阿甘本对此作出的思考有力地刺痛了当代人类政治生活(尤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神经。
四、当代西方的政治法律实践:例外状态的常态化
当我们对例外状态的政治−法律意义作出剖析,或许有人会说,例外状态在人类历史的时间轴上是罕见的,在法治之旗(无论实至名归抑或名不符实)插满各个国家的现代世界,例外状态更是可以被认为只存在于学者的书斋中。然而,果真如此吗?阿甘本作出的考察则恰恰颠覆了这种认知。
首先对纳粹德国——如果以人类漫长的记忆为参考,这个兴亡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权,距离今天的我们非但并不遥远,简直就是恍如昨日——的法制作一番审视。这里并不纠缠于战后自然法学和实证主义法学对“纳粹法律究竟是不是法律”的论争,这类关乎法律概念与道德有无必然联系的问题不是此处讨论的重点。重点在于,法律规范持续性的沉默被纳粹政权下的人们习以为常:当希特勒被合法地授予权力之后,就迅速颁布《国家及人民保护令》(以下简称《保护令》),悬置魏玛宪法关于个人权利自由的规范;《保护令》的实施辐射了希特勒当政的整个12年,在这12年中,希特勒的政治敌人被除掉,几百万犹太人被屠杀,而这些杀戮行为既无所谓合法也无所谓违法,因为原本作为判断尺度的宪法规范已经被悬置了。对于丧命的政治敌人和犹太人来说,他们被剥落了法律身份而沦为赤裸生命(bare life),本应享有和行使的权利自由、本应受到的法律保护因为法律的悬置而沦为空话。可以说,在这12年中,纳粹德国一直处于例外状态,却又偏偏因为元首身为“活的法律”而具有合法性,并通过规则化的《保护令》之实施维持了12年之久,乃至陷入一种能够被恰当地称为“合法内战”的吊诡。阿甘本论述道:“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极权主义可以被定义为,通过例外状态的手段对于一个合法内战的建制。这个合法内战不仅容许对于政治敌人,也容许对于基于某种原因而无法被整合进入政治系统的整个公民范畴的物理性消灭。”[1](5)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当代,西方国家高举民主法治的旗帜,对现在和未来的人类美好图景侃侃而谈。但在阿甘本看来,实际情况却并没有比人人唾弃的纳粹政权好上多少,甚至毋宁说,纳粹政权所操弄的“例外状态的常态化”作为一种治理典范被继承。从暂时的例外手段到恒常的治理技术,这一“例外状态的规范化”——无论这个概念听上去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因为“例外”本身就意味着其无法被规范定义和限制) ——就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西方国家,使得例外状态与法律状态之间、专制与民主之间的区分变得难以确定。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即本文开篇提到的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后的一系列反应:《爱国者法案》颁布,将“法外空间”不仅辐射至全美境内,甚至跨越出国境(关塔那摩监狱是著名的范例之一);而总统小布什也不断自我宣称为“三军最高统帅”。对此,我们只要联系对例外状态常态化的思考,相关疑问就能获得解答:对于关塔那摩监狱中犯人所遭受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折磨,不是徒劳地质问人怎么能对自己的同胞采取如此恐怖的手段,而是意识到当一个空间因为“例外状态的规范化”而被打开时,其中被抹杀政治身份的赤裸生命无论遭遇何种对待都不是“违法”的——因为保障基本权利的法律已然被悬置了。对于小布什“三军最高统帅”的反复重申,不是虚弱地斥责行政权力过度膨胀,而是“必须放在这个总统宣称拥有紧急情势中之主权权力的脉络中思考。如我们所见,若对于这个资格的承担需要直接涉及例外状态,那么布什正试图创造一个这样的情境:在其中紧急状态成为常态,而和平与战争之间(以及对外战争与世界内战之间)的区分将不再可能”[1](31)。
可见,当代西方一些民主法治国家,并非像其标榜的那样是真正的“法治国”,或者说,其“法治”已脱离了通常理解的语境而落入例外状态的怀抱。“法的规范面因此可以被一种治理暴力在不受制裁的情况下抹除与违背;而在它对外忽视国际法、对内宣告恒 常性之例外状态的同时,却仍然宣称是在适用着 法。”[1](138)并且,与其说是政治情势与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真正的裂痕因此导致例外状态,毋宁说是出于某种目的有意在秩序中开启一个虚拟的漏洞因此进入例外状态,且恰恰以捍卫民主宪政之名对例外措施予以正当化。遗憾的是,这或许只是民主宪政灭亡的利器:“没有一种终极的制度性防护措施能够确保紧急权力被用于保存宪法的目的。只有人民自己意愿它们被如此运用的决心才能够确保……所有现代宪政体制中的准独裁规定,无论是戒严法、戒严状态或是宪法的紧急权力,都无法符合任何对暂时性的权力集中得以有效限制的严格标准。因此,只要条件变得有利,所有这些制度都很容易转变成为极权体制。”[1](12,13)
如果将这种例外状态的常态化联系上述阿甘本关于例外状态−主权者的政治神学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如果说维持例外状态与法律状态的分隔是人们既能够获得常态幸福、也能够对理性鞭长莫及的极端政治情势作出反应的必要条件,那么,例外状态的常态化则意味着模糊这种分隔,它企图将整个人类政治生活和行动领域全部抛入政治上的“属神空间”,即由主权者取代实在法进行日常治理。然而,正如在神学中上帝一旦行“神迹”就意味着任何不合常规(无论是不合自然法则还是不合伦理规范)的事情都能成为现实,并且毫不在意震撼人类的恐惧、愤怒等负面感情;主权者在例外状态中的行动往往涉及对生命的捕获与征用,而这种人们在规范的常态治理下被庇佑的对象一旦恒常性地暴露在主权者的行动领域中,就意味着政治−法律系统将自身转变为一部杀人机器。阿甘本认为,人类政治生活受这种“神圣”的祸害甚烈,应当从“神圣的”例外状态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对阿甘本来说并非重新维持法律状态与例外状态、(法治)国家与主权者的分隔——因为这没能真正铲除“神圣”之域——毋宁说,阿甘本主张一种更激进的方案:将上述人类共同体结构性的内在分隔予以彻底无效化或闲滞化,以无目的的纯粹手段代替对目的的执着。而阿甘本所理解的幸福生活就是“主权与法再也把握不了的一种生活”[5]。
五、例外状态与中国的政治−法律
尽管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思想发端于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与批判,但阿甘本并非一个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其理论视界也绝非仅仅收缩于特定地域。尤其当他洞察到规范与失范、法律状态与例外状态的互动其实辐射至“整个人类行动领域”时,他的例外状态思想也就具有了理论普遍性,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西方框架中,而是同时也启发着非西方国家。
以中国自身的历史来看,近代殖民地时期恰恰是一个绝佳的例外状态观察所: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被视作国际法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但其“主权平等独立”原则的适用范围只在欧洲内部,包括中国在内被欧洲国家殖民的亚非拉国家则并非完全的国际法主体。这就意味着,中国无法独立地对自身的前途命脉作出政治决断,而部分地处于由宗主国代为决断的例外空间之中。因此,当我们重读那段历史,或许从租界——作为欧洲列强享有治外法权的例外空间——视角来思考将开启一个新的政治−法律认知空间[6]。
而把目光投向当代中国,虽然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革命任务,但尚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某种意义上(相较于作为历史终结的“共产主义阶段”),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最终安定的社会形态,但该社会形态却将存续相当长的时间。此外,虽然“依法治国”已被确立为基本治国方略并被予以严肃贯彻,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经历着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转型(尤其提出经济“新常态”一词颇耐人寻味)以及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缺口都在不断被打开甚至扩大。面对上述情势,从例外状态及其恒常化的视角进行审视或许将促生新的问题意识和洞见:比如,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与其后阶段的法治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如何把握好二者的过渡。又比如,在当前复杂的政治法律实践中,与其一味呼号将权力(尤其行政权力)“关进笼子”,不如认真思考,在面对某些非常情势时,仅仅仰仗规范治理是否足以应对,行政权力的运行是否应当被设定一个弹性而非僵化的规范性边界。再比如,面对不断奔流涌动的新生事物和力量,与其过分简单地以“合法/非法”作出判断,不如筹划应当如何作出有效的鉴别与回应,如何将其中合理的成分纳入相对稳定的制度性框架中,等等。当然,中国在社会性质、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上都与西方存在根本差异,因此阿甘本对西方在恒常化例外状态下民主自由骗局的揭露与鞭挞,并不能被当然“舶来”适用于中国。我们对自身缺陷的反思,在借鉴西方理论之外,也必须立足本国情势坚持思考的独立自主性。
综观阿甘本的例外状态理论,在法治话语“制霸”世界的今天,似乎是个让人多少感到不适的不和谐音符。然而,或许正像自称为雅典人之“牛虻”的苏格拉底一样,阿甘本也叮咬着我们这个法治话语已然发生某种变异的时代。对例外状态的思考不仅在学理上促进法学对自身研究对象——法律——之概念的根本性了解,促进法学与政治学的交战亦是交流;更在实践上鞭策着我们去应对例外状态及其常态化对人类政治−法律生活的现实影响。不过,阿甘本基于对例外状态−主权者的政治神学反思所得出的“去神圣化”结论,却是十分激进的主张。对于人类未来的政治生活图景,是否有更好的描绘方案,也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
注释:
① 本文大致在例外状态-法律状态的双元结构意义上讨论阿甘本的例外状态理论。事实上,阿甘本还从生命政治视角开启了研究例外状态的崭新场域,并且生命政治也是阿甘本思想中备受瞩目之处。但本文鉴于主题和篇幅限制,对此不作论述。有关阿甘本生命政治的著作可参见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② 参见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阿甘本的例外状态理论建立在对施米特、本雅明等学者相关思想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就施米特与阿甘本的思想关系而言,阿甘本在承继施米特有关概念的同时也作出了批判。比如,其反对施米特将例外状态-主权的历史渊源追溯至古罗马的独裁,反对将例外状态理解为“权力的圆满状态”。而在对西方自由民主的反思批判上,阿甘本则走得更远:施米特通过对例外状态的研究批评自由主义的软弱,阿甘本则进一步揭示了例外状态的常态化对自由民主的侵蚀。就本雅明与阿甘本的思想关系而言,本雅明通过“纯粹暴力”“真实的例外状态”等构想试图将例外状态排除于法律秩序之外,阿甘本由此获得启发,进而作出“拆卸法律与生命之间一切关联”的激进主张。参见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 edited by Alex Murry and Jessica Whyt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 比如古罗马凯撒葬礼就引发了暴力叛乱,该葬礼也因此被极富深意地称为“煽动的葬礼”。
④ 这种无法与法之间微妙连结的另一种呈现是戏剧性的民俗庆典,“这些庆典乃是以无羁的放纵和正常的法律与社会阶层的悬置及倒转为其特征”(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113),作为一种吊诡的“合法的无政府状态”而存在。
⑤ 这个黑箱式的规范,就比如奥地利学者、纯粹法理论鼻祖凯尔森的基础规范(basic norm),它担当从事实到规范的逻辑转换之桥梁,将被认为是“事实”的例外状态一劳永逸地收纳,不再对之作任何讨论,理由是作为事实的例外状态不是法学研究的对象。
⑥ 卢梭之后的学者大多各自偏重双元结构的其中一元进行深入研究,偏重法律-规范-国家研究的通常是法学家,以凯尔森、哈特为代表;偏重例外-失范-主权研究的往往是政治学家,以施米特、阿甘本为代表。相关观点可分别参考汉斯·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H.L.A.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卡尔·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阿甘本的《例外状态》。
⑦ 规范统治恰恰是对客观性与安定性的回应。
⑧ 当然,二者之间还是存在重大差异的。比如,在私法中,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权威会随着监护人本身年龄的增长或精神状况的好转而不复存在;但在公法中,治者对被治者的权威却没有这样的限定条件。
⑨ “权威……总是隐含着一个它使之生效的外在活动。”Magdelain语,转引自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⑩ 这种“返归”显然不是单纯的“回到过去”,而是例外状态对旧法律状态的否定之后,再完成一次否定之否定。
[1] 吉奥乔·阿甘本. 例外状态[M]. 薛熙平, 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2] 让·雅克·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3] 登特列夫. 自然法——法律哲学绪论[M]. 李日章, 梁捷, 王利,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
[4] 吉奥乔·阿甘本. 神圣人: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 吴冠军,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5] 吉奥乔·阿甘本. 无目的的手段: 政治学笔记[M]. 赵文,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6] 苏哲安. 没有“世界”以后的主权欲望: 永久性的非常状态与生物政治——响应Partha Chatterjee的演讲[J]. 文化研究月报(创刊号), 2001(3): 7−8.
Dialogue between law and politics: On Agamben’s theory of state of exception
DONG Jingshu
(School of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China)
Agmaben’s thought of state of exception does not only propel legal theory to consider its fundamental question, but also faces up to the dialogue between law and politics, norm and anomie in the area of human behavior, and further makes a more powerful introspection into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In addi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practice, modern world is an area in which “rule of law” and “rule beyond law” are both powerful. On the one hand, “in the normative framework” are the standard words of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operation of power in fact always crosses the normative border. About this, only when we consider the state of exception seriously beyond the view of positive law, can we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the whole order of human’s common life. Furthermore, it is beneficial for us to think about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practice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amben’s theory of state of exception.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sovereign
[编辑: 苏慧]
2017−03−28;
2017−07−09
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青年专项课题“‘主权者—国家’二元结构中的纯粹法学研究”
董静姝(1987—),女,山西平陆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1.010
D90
A
1672-3104(2018)01−007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