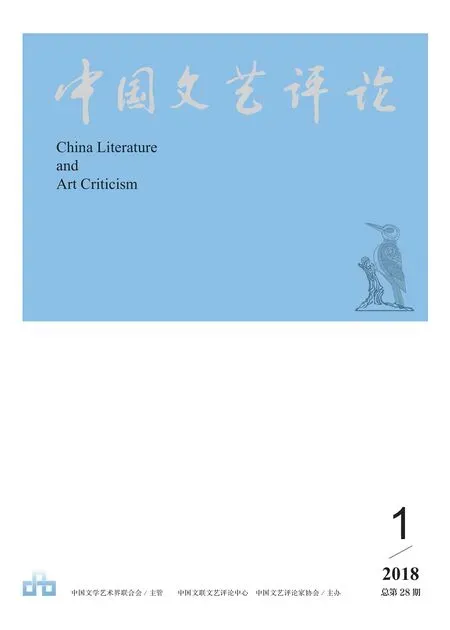当代中国文学的来路与走向
——访著名作家马识途
采访人:孙 婧

马识途简介
四川省作家。1915年生,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党内担任过不同的领导职务。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荣誉委员,四川省文联主席、名誉主席,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中国国际笔会中心理事。193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196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诗文著作颇丰。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沧桑十年》,纪实文学《在地下》,短篇小说集《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正式出版著作20本,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多篇。其主要的文学作品收录在2005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识途文集》中。一、“中国文学”是什么
孙婧(以下简称“孙”):
您从事文学创作七十多年,以丰厚和有分量的文学创作享誉文坛,今天我们想和您聊聊文学。马识途(以下简称“马”):
对于文学创作,有很多问题我不大弄得清楚,我曾经就这些问题与李敬泽有过交流,他也觉得这些问题很重要,值得很好的研究。现在我想将我们交流的问题同你们谈一谈,也请你们帮忙回答。当然,你们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人,这一方面肯定比我思考得更多。孙:
在文学创作领域,您提出问题,这本身就蕴含了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话题:知识分子如何以关注现实的能力,考察可见的当代文学。我们更愿意在与您的交流当中能对这些问题有进一步的深入和推动。马:
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当代的文学?能不能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文学语言来描述一下什么是中国的文学,或者说中国的文学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中国文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那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呢?这里面有三层意思。首先是“文学”,我们中国的文学是文学。其次是“中国特色”,中国文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再次是“社会主义”,中国文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
但是目前为止我发现还没有人对中国文学做出这样的定义——至少在正式的文件或出版物中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描述。我一直没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来这样表述中国文学。我觉得中国的文学一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假如离开了中国特色,这个文学恐怕就不能被称之为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了。中国文学一定要具有自己的特色。关于这一点我就不详细展开了。那么如何来理解“社会主义”文学呢?我们当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以我们的文学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学。
我曾经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界定,得到了作协一些同志的肯定,他们也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让我国的文艺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一来,我对中国文学的界定也就站稳了脚跟。
有人会问:如果中国文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那世界文学的定义又是什么呢?我认为世界各地各个国家的文学都有各自的特点和特色,各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也都是文学,每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各有特色。
当然,如果对中国文学做出这样的界定后——中国文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其他国家的人不愿意承认中国的文学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在意这个问题,中国的文学肯定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文学的定义,也希望你们能对此进行更进一步地分析、论证。
孙:
您说“中国文学”是您这几年一直思考的问题,这让我们遇到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一个作家该如何去创造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呢?马: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我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关于这一问题,你们可以研究研究。如果对中国文学的定义被这样界定下来后,很多问题也都跟着出来了。比如“中国特色”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特色”最主要指的是中国核心价值体系。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学一定体现的是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精神,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品中一定要体现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我们的文学要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话,也应该体现出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当然,关于这一问题有很多争论,很多人认为,为什么非得把文学与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等方面相联系。关于这一点,我在这里不想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文学一定要有中国特色。
中国的文学应具有“中国特色”,不仅仅指的是其内涵应体现中国核心价值体系,也指的是中国文学的文学形式也应具有中国特色。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形式?它应该是具有中国传统特征的文学形式,应区别与国外的文学形式,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文学经历了几千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语言、结构等,所以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学也应该传承这些特点。
二、文学应该是一种有方向感的写作
孙:
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当代中国文学的走向到底如何呢?马:
我觉得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在当代已发展出两种分支,一个是以传统主流文学为代表的雅文学,一个是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中国当代的通俗文学现在几乎可以称之为“网络文学”了。从每年的出版数量、阅读数量统计上都可以看出,当代有一部分人在读雅文学,有一部分则读通俗文学,也就是读网络文学。从五四以来一直到现代,雅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它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延续,然而从出版数量、阅读数量统计上都可以看出,以网络文学为主导的通俗文学的读者已占到总人数的50%以上。
有观点认为,雅文学会越来越边缘化,而网络文学会越来越兴盛,我不赞成这个说法,但从实际的统计来看,这确实又是当下的现实。一本网络文学作品印刷出来,一次可印50万册、甚至100万册,而雅文学一次最多印几万册,鲜有能印10万册、20万册的了。我在北京与中国作协的同志交流的时候,也谈到我们100位雅文学作家出版的作品数量抵不上10位网络文学作家出版的作品数量。从这个出版数量中可看出雅文学作品的读者和网络文学作品的读者数量之间的悬殊对比。
孙:
我在对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当下文学的困境,事实上,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也呈现出了文学本身的危机,或者说这是文学要解决自身危机的诉求。马:
我对当代中国文学这样的文学走向感到担忧。我思考的是,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应不应该这样两极分化下去,还是应该雅俗合流?是不是应该出现一种雅俗共赏、老少皆宜、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文学?这应不应该成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努力的方向?我们的文学是不是应该既发展雅文学也发展网络文学呢?当然,雅文学有雅文学的许多问题,网络文学有网络文学的更多问题。我觉得现在的网络文学对青年读者在思想引导上的影响是不好的,因为当下的网络文学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方面存在缺失,它太过于追求点击率,追求资本。目前有一半以上的网络文学是在为金钱服务,为资本服务。因此其中很多作品是“三俗”作品、是有毒的鸦片作品、是垃圾作品。而网络文学的兴盛也导致了原本主要出版雅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在图书出版上的转向。我并不是反对发展网络文学,而是觉得网络文学应具有雅文学的特质,同时不能妥协于资本。如果雅文学最终也向资本妥协、投降,那么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学还能具有中国特色吗?还能够是社会主义文学吗?“中国当代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这一问题,应该被明确地提出,中国文学的内涵、中国文学应该具备的特点、中国文学的创作方法等方面也都应该被明确下来。正是由于这种不明确,才导致了当代文学的危机。

当代大量的网络文学作品转化为电影、电视剧,传播于游乐场所,而一部网络文学能不能转化为影视剧,主要靠的是点击率,其中有些作品的点击率动辄几亿。如果这部作品是好作品,那么点击率高值得欣喜,但是如果一部作品不是好作品,也并不是在促进我们的思想意识水平,那么点击率高则令人担忧。一旦一部高点击率的网络文学作品出版成书或被拍成电影,我们的报纸就大肆吹捧,甚至专门设置作家稿费的排序,谁的稿费最多就成为作家榜之首。
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在鼓励什么?我不大赞成这样的做法。不能说谁的稿费最多,排第一,他的作品就好了。低俗、低水平的市民小说或者年轻的没有多少知识的青年所欣赏的东西,不能成为我们中国作者创作的主流。中国当前两个不同风格的创作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优点、自己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雅俗文学有意识的合流,提倡把雅文学向通俗文学靠一靠,把通俗文学在艺术性、思想性上提高提高,大家都靠过来形成真正的当代的文学,成为主流,能不能做到?现在看起来很难。我多少是有点悲观的,恐怕那一天自己会看不到。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真正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作为主流,能不能做到?我相信是做得到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对文学的走向我很不乐观,网络、影视媒体比出版社等的资本要大得多,他们都有资本掌控,所以占据巨大的利益空间。大部分资金被装入了投资人的口袋,其实我也并不反对这个,关键是如果做的这些事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就不能这样做了。现在谁也不敢说让他们不要这样做,不要搞网络文学,因为资本在我们的经济中占了相当厉害的地位。
我是搞创作的,面对现在这种局面,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有些忧心。大概20年前,我在《四川文艺报》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来讨论到底谁来坚持我们文学的边界,谁来坚持我们的文学传统,谁来坚持我们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我提出“文学尚文”。在北京,我提出中国文学面临内忧外患,内忧就是文学的低俗化的偏向,比较严重;外患就是外国的大资本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输入他们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文化霸权主义。实际上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着文化霸权主义的侵入,电影就是很重要的一种途径。这些不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雅文学吸取养分,而是从外国的这些东西中受到影响。一些所谓的作家发表了很多东西,我们都看不懂,当然也可能我是个文化老古董。现在一些年轻作家创作的一些文字的结构、文学的结构,我都很陌生,一些句法和我们中国语言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文学要用外国的文化、外国的结构、外国的语言来写,一些倒装的句子让人看不懂。《红楼梦》《西游记》流传至今就是因为有中国传统、中国作风。现在许多雅文学都不太重视中国自己的文学传统,而是过多学习外国的一些文学形式。有些就是想到外国去出名,我不太欣赏,外国人读中国文学其实也不是都能读懂的。
我们现在创作中存在的一些外国形式实际上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外国文学也有一些很优秀的内容,外国文学历史上也有一些很出名的作品,都很好,我们一定要去学他们。但是现在有一些人是想通过一些作品把我们的意识形态转变成他们的意识形态。假使我们都跟着他学,有很多问题就会出来。这些霸权是很有成绩的,在中东有很多国家都是这样被搞垮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很强的。我希望中国年轻的作家更多地研究中国的文学传统,吸收西方的好东西。我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要西为中用,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网络文学本来是我们传统文学的,就是被资本利益驱使,被低俗化,甚至破坏了中国好的文学传统。
四大名著都是好东西,采用优秀传统文化作品的结构、文化、语言。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两种文学的源流问题。这些文学源自何处,流往何方,网络文学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的雅文学是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的,这个源头其实就是中国文人从西方学习了先进的文学,来进一步发展中国文学,新文学,雅文学。而这些把通俗文学衬托为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包括金庸的小说在内都是通俗文学,但他也有优点,就是用中国话写中国的故事,不管怎么反对,金庸的小说在中国还是很行得通的。张恨水的社会小说,实际上也是中国俗文学传过来的,现在很流行。
我们的雅文学源于五四,受到外国和苏联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文学为政治服务,是从斯大林那里发展过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需要的时候为政治服务,这个我也是赞成的,但这不是我们唯一要研究的东西,如果一直作为政治的附属品和工具为政治服务,我们的文学永远不可能发展得很好。可见,我们的雅文学也曾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现在我们很关注文学的发展,这很好,但文学往哪里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艺的要求很好,文学的路子还是可以照现在这样发展。雅文学曾经为政治服务是吃了亏的,网络文学为金钱服务也吃了亏。一个为政治服务,一个为金钱服务,这都是文学之害,也不可能让文学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所以这两个文学是否能作为真正的中国文学,这是一个问题。这两个文学自己有自己的麻烦,自己有自己的问题。
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要怎么解决,还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别是网络文学发展路子的问题。网络文学的发展我们要考虑怎样用这个形式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我曾经向作协的专家提议,能不能动员一些雅文学水平比较好的、创作技巧比较成熟的作家,有意识地转移到网络文学,占领这一阵地,也用它的形式和技巧来创作,但是很难。雅文学的作家去做这些通俗文学的创作,他们是不干的、不愿意的。我们中国的雅文学作家是很多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少。这么庞大的队伍,不改革是不好的。正如现在提倡文化改革,否则这个局面难以维持。
网络作家有几百万,雅文学作家也有几万,这么大数量的作家为什么都要去爬那个金字塔(作家排行版),这个金字塔要有人爬,但并不需要如此大量的作家。我很奇怪有些作协的作家一年怎么创作了4000部长篇,有必要吗?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有的甚至都没出版,有的出版了也是无人问津,最终变为纸厂原料了。我觉得有几十部就差不多了,每年只有几部是优秀的,那剩下的3900多部有什么用啊。3900多个作家都去爬金字塔,都爬不上来,但是还要爬。我不反对爬高峰,但真正要爬高峰还是要有特殊的天分,特殊的勤奋,特殊的观察力、洞察力,真正有这些素质的人爬高峰,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去爬那个高峰。写一点通俗的,老百姓都懂的作品,也是做了点好事情嘛。
孙:这可能就是文学生产体系的症结所在,一方面我们鼓励作家积极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文学的方式对功利主义进行对抗,却又在无形中受资本的牵动与濡染。当我们把解决文学的困境变成一个方向性问题的时候,即越来越倾向以何种具体的方式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您给我们的思路是什么?
马:中国的雅文学还有许多需要加以注意,甚至需要加以改革的地方,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实质性的突破。我担任四川省作协主席有28年之久,自己也出版了几本好的作品,但在这方面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一直感到很惭愧。因此,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你们是专门的研究机构,可以运用大数据的方法,认真地做调查,搞明白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提出积极有效的应对主张。这是十分有必要的。其实,今天我想与你们讨论的,想请你们研究思考的也是这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关于文学方面的本质性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的一些提法还是存在偏差,对此我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向你们提出来,共同来研究一下,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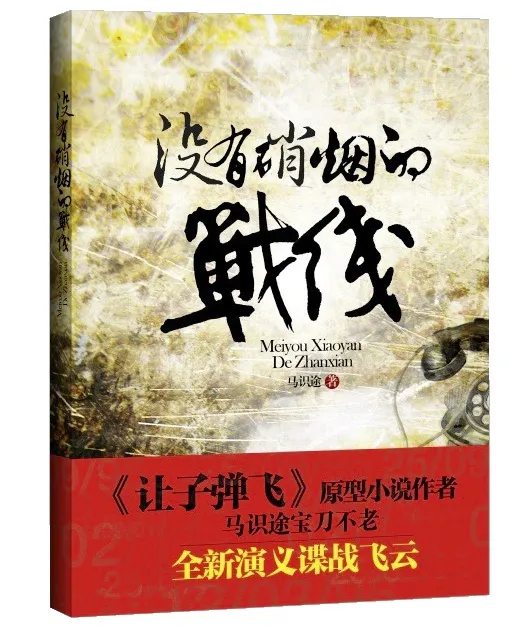
三、走向更广大的精神视野
孙:从创作到理论,从文本到批评,两者构筑了文学交往互动的系统。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当代文学的繁荣,需要我们的文学批评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
马: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大力发展文艺批评,大力发展评论,通过评论来培养引导读者。谈到文学批评,如我刚才说的,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文学批评到底应该怎么个批评法。这个问题我过去跟四川大学的教授们一起讨论过。我说,我们中国的文学批评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批评系统?我和川大的王世德教授说过,为什么我们的文学批评文章都是用西方文学批评的各种主义、格调来评论我们中国当代的文学?我觉得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有人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学评论系统流传下来,我却认为并不是没有,关键是看怎么去挖掘,怎么去组织。比如《文心雕龙》,难道不是一个系统吗?还有诸如“神韵说”之类丰富多样的品诗之法,品评什么样的诗才算是好诗。这些都是中国文学评论系统的组成部分。但很多学者却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学评论系统,故而现在只能从外国输入,只能使用外国的术语、观点。我是不赞成这一点的。我认为应该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学评论的体例和系统,国外的理论,我们要积极吸收其中先进的、良好的成分,但不是照搬过来。我们要认真梳理我们国家从古至今的文学批评思想,研究古人如何评判文学的好坏,这方面的内容其实是十分丰富的,如诗话作品数量就很庞大,其中包含了许多深刻的思想。但现在这方面研究极为薄弱,很少有人愿意去做这些工作。我的一个老朋友很有心,他很重视《文心雕龙》,下了许多功夫,把它翻译为现代汉语,已经出版了。这种努力就是好的,只是除了几个老夫子,似乎没什么人响应。我们就应该从中国自己的文献资源中去寻找文学批评的路子。总之,谈到文学批评,我的观点就是要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系统。这个工作很复杂,也很困难,光是一本《文心雕龙》就够许多人研究一辈子了。
又如,从古至今,对《诗经》、屈原等的研究文章就汗牛充栋,这些文章都有自己的一些道理在其中。至于有关其他中国诗词古文以及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就更多了。我们需要做大量的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梳理。有的大学,如复旦大学,做了一些工作,但还是不够。现在虽然出版了一些古代文论方面的书,但还没有建构起像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那样系统的一套东西。这项工作虽然很难,但不能因此不做这个工作,为了图方便直接从西方照搬,我是不赞成这样做的。不能只有外国文学批评的各种主义,而没有我们中国的主义。中国文化有几千年传统,内涵深厚,并非不如西方,为什么只强调外国的格调呢?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十分重视比较文学的研究,把中国的文学与外国的文学进行比较,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建立中国的文学评论系统所必需的。我知道他和他的团队做了许多有益的努力。曹教授曾把他主编的《中外文化与文论》杂志寄给我。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也很有水平,下了许多功夫。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梳理,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只有把这些工作做好了,才有可能建构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体系。目前,这方面工作还比较零散。
孙:
在《失语症:从文学到艺术》一文中,曹顺庆教授提出文论领域的“失语症”问题。他说所谓“‘失语症’,指的是20世纪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强烈冲击之下,西方所代表的话语规则逐渐成为一种主导的、普世性的权力话语,而中国传统话语的自身特质反而被边缘化,从而陷入‘失语’的状态,中西话语之间无法形成平等、有效的跨文明对话”。这样看来,曹顺庆教授提出的“失语症”问题和您刚才所说的观点是一致的。马:
是的。你们作为专门的研究机构,除了理论研究之外,评论也应该是很重要的工作内容,需要做很多努力。像中国的诗歌、书法等等,都有许多问题可以谈,如中国诗歌源于何处。中国诗歌在源头就很发达,如《诗经》《楚辞》,还有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等等。中国诗歌曾是中国文学的主流。现在却很少有人来研究中国从古至今的诗歌系统。新诗是中国现在的主流,但这个主流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中国五四时代的一批文人到英国后将英国诗歌的传统移植过来的,是用他们的格调来写我们中国的事情。一直延续到现在。因为写新诗很容易,所以诗人就多如牛毛了。这些东西,我并不反对。但不能因为有了新诗,就放弃中国几千年的诗歌传统,对这个传统不屑一顾。现在一些著名的诗人居然不读唐诗,不懂唐诗,而去学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我曾经和贺敬之、赵朴初一起发起中国诗词学会。我是发起人之一,先当了副会长,后来还当过名誉会长。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把中国的诗歌传统延续下去。虽然我们现在的古体诗水平不如过去,但这个系统不能丢弃。现在,新诗占据了中国诗歌的绝对主流地位,包括各种诗歌研究团体的研究,也几乎都以新诗为研究对象。古体诗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很少人懂得古诗的格律,也很少人愿意研究古体诗。许多人甚至瞧不起古体诗,认为是老古董。我发表过两篇文章,认为不能把古体诗送进棺材。我说,中国古体诗词并非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没有前途的夕阳艺术。我们四川搞了诗词学会,也搞了《岷峨诗稿》杂志。这份杂志我们是从1986年开始编的,30年了,现在还在正常运转,每年出四本。我自己现在还在创作古体诗,在我103岁生日时,我自己创作了一首七律。孙:您的文学创作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可以说见证了我们当代文学的起起落落。那么,回忆您个人的创作历程,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与我们分享。
马:关于我自己的文学经历,我倒不准备谈什么。当然,已经有很多介绍性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了,我自己是不大去关心的。我自己只是埋头于创作,这些年还在不断出书。王火跟我说过,他专门去查过,90岁以后还在坚持文学创作的,他只见过我一个。我前几年,一年还出了两本书,那时就已经过了100岁了。前不久,有一本书还在北京举办了首发式。目前,我还在创作一本书。我今天说的这些供你们参考。希望你们能为中国当代文学列出一些供研究和考察的题目。这些工作大有好处。你们也前途无量。
访后跋语:
说起马老的文章,很容易辨别时代,他在我们经历和未经历的生活里,捕捉人性,以他的识见和视野描述历史的气象。作为作家,我想学术研究应该不是他的兴味所在。与他聊天的话题,我选定在他创作的微观层面,想以此获得一些意义。初见马老,没有那些被“著名”包裹的强势气场,也没有令年轻一辈炫目的紧张,整个人就如同隔壁的老爷爷。这是我想象中的样子,那些慈祥和暖意洋溢在书房里,软软的,暖暖的。在简单的介绍之后,我们进入聊天的主题。而一开始,马老就强调略过自己的文学成就。中国文学的定义和方向是文学研究者不能回避的现象和问题,这样就使访谈带有了公共价值的烙印。深度的学术追索被马老从当下文学复杂的事实层面抽离出来,我不否认,这激起了思想的碰撞。他不是空洞的作家,他的写作是与中国文学生存的语境息息相关的写作。他的那些因为商业和资本元素对当代文学介入的忧心忡忡,那些对当代文学未来发展方向的高瞻远瞩,那些对文学研究者的殷切希望,都在显露着一个老作家的美好情怀。整整两个小时过去了,但谈起诗歌,他依然兴致盎然。对于我,这隐藏了一种动力,一种源自内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用在对过去自我的颠覆和新的自我的建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