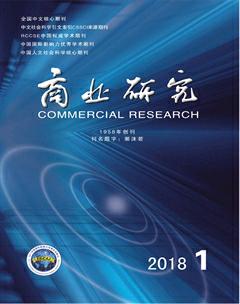北欧贸易区成型溯源
刘程
内容提要:中世纪盛期欧洲社会的物质积累激发了商品交换活力,引发了“领主-农民”二元结构和庄园经济解体。“黑死病”后社会经济结构再调整,物质积累和消费水平复增,市场交换成为常态,国际市场体系得以优化重组,北欧地区出现了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地理分工,确立了大宗贸易的内容和运行体系。14、15世纪专职贸易的汉萨商人建构起一个东起俄国、西至葡萄牙,北抵冰岛,南达意大利的贸易帝国,标志北欧贸易区初成。尼德兰和英格兰依靠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又以港口集散贸易取代汉萨同盟的转运贸易,先后主宰北欧贸易区,最终发展成现代贸易强国。经济体、贸易模式与贸易区间的深层关联对于积极谋求从生产大国向生产强国转变的中国具有启发意义——打造国家品牌,建构“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是参与或主导全球贸易的有效尝试。
关键词:北欧贸易区;经济社会结构;市场体系;大宗贸易;汉萨商人
中图分类号:F74;K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8)01-0028-08
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赞同近代欧洲的经济腾飞源于此前数世纪的物质积累和制度变迁。其中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尺就是贸易网络的广度、深度和交往频度。在中世纪,贸易模式沿革反映了商品经济(市场)诞生、扩张的一般历程。众所周知,自由交换机制下的商品经济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丰富的生产剩余和充足购买力。正如希尔顿较早指出的:“经济发展是以超过生存需要的社会总剩余生产量的增加为标志的,这是商品生产的基础”[1]。但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强烈的自给自足为特性,特别是在中世纪前期,欧洲经济展现出的是一种“刻板、钝滞和艰涩”的初级形态[2]。只因上层社会对异地商品存在有限需求才维系了中远程贸易的薪火相传。12世纪以后,歐洲经济-社会结构变动刺激贸易模式变革。其中大宗商品贸易(Large Bulk Commodities)作为远程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南欧(地中海沿岸)和北欧(北海-波罗的海沿岸)出现,先后经历了转运和港口集散两个阶段。期间,大宗贸易突破了初级贸易的内容和范围,标志欧洲社会完成了向参与度更高的市场经济形态的过渡。
“大宗贸易”在19世纪末已散见于德意志历史学派的著作,如比歇尔(Bücher)和迈尔(Meyer)在关于古代经济属性的论战中就提及早期海上贸易①的地位和作用。亨利·皮朗以后,关于“远程贸易”的各种分析或争论频出,经济史家和经济社会史家皆给予充分关注,著名者如M.M.波斯坦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等。他们最初聚焦于欧洲南北方“大宗贸易”的共性特征——如自治城镇(之后升级为城镇同盟或城邦共和国)在转运贸易中的垄断取向,等等。美国经济史家罗伯特·洛佩兹则对南北欧贸易作深入比较,发现14世纪北欧贸易的掌控者——汉萨同盟在集体行动的效率方面远胜于南欧意大利各分散城邦(如热那亚、威尼斯)[3]。洛佩兹还指出南北方的大宗转运贸易在商品结构、内容上存在明显差异:南欧地中海以丝绸、香料等奢侈品为主;北欧主要是谷物、羊毛、木材和纺织品等日用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差异决定了以后两地资本积累的路径差异。中世纪晚期里,南北方贸易发展的轨迹发生分流。除国际商路转变这一外因外,北欧经济社会结构的再变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北欧初步联结为一个整体,建构起生产-运输-消费的一体化经济单位,升格为内部相互依赖的稳定贸易区②。众所周知,对现代“贸易区”的定义主要在于考察是否达成普遍性经济联系和高依存度的商品往来关系。史实证明(后文将展开论述),14世纪的北欧大宗贸易已初步展现这两大特征,而汉萨同盟在北海-波罗的海建构的转运贸易体系就成为北欧贸易区成型的主要标志。17世纪以后,大宗贸易的主导权由垄断运输环节的汉萨同盟转向同时掌控生产和运输环节的尼德兰和英格兰,一种由区域内部供需关系驱动的贸易增长迅速超越旧的转运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度与量上实现飞跃。至此学界才意识到欧洲近代“起飞”与大宗贸易时期的北欧贸易区存在着特殊关联。而此前学界的研究视角或重在讨论中世纪盛期远程贸易的角色和特性问题,或过于强调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建设历程,对中世纪晚期国际与国别之间的区域单位缺乏深层考察,当前学界对研究视域的转向诉求便成为本文展开的空间和价值所在。
一、中世纪盛期的物质积累
探究贸易的发展概况须回溯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点——物质生产能力和个人收入水平上来。就前者而言,欧洲社会的物质生产、积累很早就开始了,但无疑中世纪盛期是最繁荣的一个阶段。自10世纪起,西欧趋于和平的外部环境为人口的稳定增长创造了条件。1100年时,以重犁具、三圃制和现代马具为标志的全面的农业制度成型。根据卡洛·齐波拉的粗略统计,到14世纪初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谷物收成与播种比率已达1:3或1:4,而在9世纪时这一比率常不足1:2,这意味着11-14世纪里单位谷物产量比之前提高了近两倍[4]。以收成和播种比率计算,巴斯认为13-15世纪英格兰(属于当时西欧相对落后的地区)谷物的平均收成比率分别是1200-1249年的1:37,1250-1499年的1:47[5]。佩因特在考察了270个男爵地产后发现,13世纪中叶这些地产上的庄园平均收入比1086年增长了60%,1250-1350年间又比之前增长了28%到32%[6]。
物质积累刺激商品经济复兴,撼动庄园体制,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转向为有限市场生产的规模经济。期间,农村土地经营的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被货币地租取代,加速了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从此时起,对每周工作的最多天数和以支付金钱代替劳役进行规定开始成为普遍性观念,并构成了庄园习惯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则[7]。在英格兰,地主阶层在1100-1300年间勉强维持了人口、经济增长造成的通货膨胀和收益之间的平衡[8]。在法国,因中央权力过度分化和碎化,地主的持有地面积相对狭小,只占全国土地的8%至12%[8]。法国乡村公社借机寻求自治,限定地租和税金额度,争得土地所有权。在德意志,东进运动扩大了耕地面积,缓解了人口的增殖压力,冲击了“老帝国区”的农奴制。部分富裕农民甚至有财力效仿王室、贵族而享受奢侈生活[9]。因此侯建新教授认为,正是此时个体农民在劳动生产率、商品率和储蓄率上的总提升推动了商品化进程。他考察发现13、14世纪里英格兰中等农户的商品率达到53%。而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农民有更多剩余产品可以出售,由此带动了城乡经济的商品化[10]。endprint
货币经济是衡量社会财富积累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3、14世纪里,英格兰货币总发行量不断上升:1180年货币流通量不足125万镑,但1218年上升到30多万镑,1247年达到40万镑,到1311年货币流通量约有110万镑。1180-1330年间,英格兰人口从200万增加到600万。这意味着人均货币持有量增加3倍以上——从1180年不足1先令上升到1330年的3-4先令[11]。其中劳工的收入增长最普遍:13世纪80年代南英格兰的建筑工周薪为9便士,到14世纪中叶时周薪已达18便士,较此前提高1倍。在乡村,14世纪初农收季节的雇工薪资较之前上涨了18%,脱粒和扬粒工的薪金上涨了6%,1320年左右的薪金水平涨到历史最高[12]。据经济史学家詹姆斯·罗杰斯估计,1311-1320年间农业工人薪金比此前半个世纪高出近20%[13]。其他领域的薪金水平也在上涨,如1279年时英格兰步兵日薪提升至2便士[14];在商业领域,14世纪初时小额银币在流通中的比例和利用率相较以往大大降低,商人普遍持有6先令8便士和3先令4便士的大额金币[15]。
但物质积累和货币收入的提升并不能完全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概况。对市场扩张行为的考察还需对社会劳动总产出与人口增长比率——个人平均收入率(或人均GDP)作综合考量③。仍以史料数据完备的英格兰为例,格雷姆·斯诺克思研究后发现,1086-1800年间英格兰人均GDP总体上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增长近8倍。布鲁斯·坎贝尔深入考察了1086-1300年间英格兰的GDP总量,得出增幅在130%-150%的结论[16]。彼得·林德特继续考察了1290-1688年间英格兰个体家庭的实际收入,估算增幅在110%左右。考虑到家庭规模缩减和通货膨胀等因素,实际人均收入约增加150%[10]。但中世纪盛期的物质积累只能说是为之后经济社会的再发展奠定基础,当时并未产生连续性变革效应。因为直到黑死病爆发时,作为商品经济主要参与者的城镇工商业者仍在维持简单再生产,地方市场依然狭小难以拓展。市场作为商品经济的基石,只有扩张到一定规模才能给商品经济带来充分活力——这一契机出现于黑死病后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再调整。
二、黑死病后社会经济结构调整
14世纪中叶爆发的饥荒、战争和疾疫“危机”具有双向特征:它一方面造成人口锐减,开启了近一个世纪的“饥馑时代”,导致社会对商品和雇工需求减少,打乱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但另一方面“危机”降低了总人口中失业者与就业不足者的比例,进而增加了劳动者的市场参与热情。通过抗争,农民与领主达成新的面向市场的租佃契约,传统的封建依附关系消失了,农民的生产自主性得以提高,进而激励他们提升劳动质量和劳动强度。14世纪晚期,自由劳动力的高工资与铸币短缺的困境进一步削弱了领主对土地和农民的控制。在北欧部分地区,领主与农民建立在租佃分成制基础上的货币关系渐趋淡漠[17]。法国和德国农民较早获得王室法庭授予的许可状,拥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两国土地贵族因庄园地租和税金收益入不敷出而倾向于为集权君主制政府服务,从相对高效的国家税收体系中获利[8]。在英格兰,因劳动力不足及农民抗争,领主阶层在黑死病后频遭削弱,到1400年时农奴制彻底崩塌。为维持地位和收入,领主们纷纷选择出租地产。1380-1420年间英格兰有近1/5至1/3的耕地转移到农民、商人和小乡绅手中,其中大部分转租给富裕农民。后者采取面向市场的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率以最大化获利。尼德兰农民则通过填海造陆制约领主制扩张:他们结成强有力的村社组织互助争夺土地产权以维系生存和多样化经营。此时各地乡村逐步完成了从劳役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这解除了佃农们的劳役不便,后者可以利用更多时间在其租地上创造更多收益。领主们进一步脱离土地:他们通过市场购买或与生产者协商来保证谷物供给,也不再自酿麦酒而改向当地酒商大宗购买[18]。社会结构的变化赋予生产者更多自主性,开启了面向市场的商业化和专业化生产浪潮,进而扩大商品交换的内容和范围,这就加速了经济结构的主动或被动调整。
在北欧,传统的耕作方式逐渐被放弃了,代之以普遍的谷物商品化[19]。如佛兰德和尼德兰海岸地带的富裕农民以大型城镇市场为导向,率先引入集约化生产方式。弗里斯兰因专门生产高价值的食用谷物而大获其利。据记载,该地富裕农民常在节日期间款待宾客,宴饮无度[9]。但1350年海平面上升后,弗里斯兰过于潮湿的土地逐渐不利于谷物生长,导致1400年的农业危机。因此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他们被迫通过扩大专业化水平和投资来提升劳动生产率[8]。与此同时,民众还将目光转向其他商品化更高的作物,如亚麻、菁蓝、葡萄等,希望用更少劳动产出更多作物。如英格兰的部分地区已完全转为牧场式农业,有的地区则扩大了藏红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20];佛兰德沿海地带发展起大规模养牛业,农场租地面积持续增长,平均超过20公顷[21];在波兰,自14世纪中叶起,日益扩张的市场网络激励着但泽、华沙和克拉科夫郊乡的农民专事经济作物生产,种植商品化蔬菜,饲养肉禽[22]。农业商品化和专业化为新一轮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原动力,为大规模贸易兴起奠定基础。
在城市,商业领域首先分化为专事批发的大贸易商和专事零售的小商贩阶层。前者从事多类贸易,掌控市政大权,是大宗贸易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后者受行会限制,经营活动较为单一,在贸易体系中扮演商品的中层或底层分流者角色。二者在贸易活动中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分销运营体系。贸易商阶层的强大提升了定期集市和城镇市场的地位,冲破了传统行会对商业的禁锢,加速城市和外地商业的联系,大宗批发贸易逐渐占据商业领域各重要部门。在制造业領域,11世纪以后兴起的工商业城市中纺织业占重要地位。此时为满足各级市场需要的纺织品皆集中在城镇内生产,纺织业成为城镇里最大的行业,纺织品成为市场需求最大的商品[23]。黑死病后,城市生产展现出多样性和深专业化,制成品的种类、质地和规模都有了极大提升。特别是乡村手工业兴起对受行会制约的城镇工业发起挑战,进而引起整个制造业的应激性变革——激励规模化生产,打破从业者的身份限制,吸引包括儿童和女性在内的新的劳动力投入到各个生产部门。endprint
一系列新变化提升了社会整体参与市场经济的频度与效率。据统计,黑死病后的两到三个世纪里,北海沿岸地区1/3至2/3的人口成为依靠工资的劳动者,为工资而劳动成为生命周期的一部分[24]。城镇内负担交税义务的中产阶层人数稳定增长,个人收入也较充足[25]。如英格兰劳工薪金平均增长40%-60%。1350-1400年间爱德华三世甚至两次颁布《劳工法令》试图限定普通劳工的薪金上限,但劳工薪金上涨的势头并未因之改变。期间普通木匠和优秀木匠的薪金分别增加了48%和42%,石匠增加了60%,砖瓦匠及其助手分别增加34%和90%,锯木匠增加70%。工匠薪金平均增加50%,女工薪金平均上涨100%[13]。经济学家JP布朗和SV霍普金斯详细考察了13世纪中叶至15世纪中叶英格兰南部地区建筑工人的购买力,发现他们的实际工资虽然直到1371-1375年才恢复到1160年的水平,但此后不断攀升,一直持续到1520年“价格革命”[15]。因此布罗代尔认为黑死病后的两个世纪里欧洲社会经历了普遍增长,进入“个人生活的幸福时期”[26]。与收入增长相同步的是社会消费水平的波动提升。随着基础商品总价格下跌或平稳,人口数量和资源比率的改善允许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进而催生出新的贸易方式,推动生产专业化[11]。中世纪中晚期里,对欧洲社会消费的考察主体同样要由贵族转向民众。此时平民收入比例递增,领主贵族的收入比例相对放缓、下降(但并不意味贵族的经济重要性下降了),这种此消彼长的波动趋势因习惯法下固定地租的不可撼动而扩大。如法国领主的收入在13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一直落后于通货膨胀的速度,处于停滞状态[8]。伴随普通民众薪酬、生活水平的提升,欧洲社会涌现出普遍性、新颖化的消费方式。特别是谷物价格降低后,人们可以把更多收入用在购买相较奢侈的商品上,对高质量的食品、制成品、住房和其他消费品产生广泛需求[21]。以农产品交换制成品的行为开始成为经济关系的主流特征。
在现存的遗嘱、账薄、婚契、嫁妆登记簿等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中,有关呢绒、布匹、金属器具、陶器、木质器皿、肉、奶酪、葡萄酒、水果、黄油和啤酒等消费量的持续增长皆证实了社会消费水平提升的事实。SR爱泼斯坦认为14、15世纪里西北欧社会的生活水平提升了60%-70%[27]。具体来看,14世纪法国的市民阶层已不再为生计担忧,普遍追求生活上的舒适感[28]。15、16世纪英格兰社会对香料的消费日渐普及:社会上层专供肉桂,普通人家多用桂皮[29]。低地地区大规模出售谷物、羊毛、奶酪、牲口和剩余农产品,地产主与市场联系紧密。意大利人的生活水平在1300-1500年间提升了近30%[27]。在同时期的波兰,农民享受到地租经济带来的好处,过上相对惬意的生活。据波兰史家估算,弗拉迪斯拉夫·雅盖洛(Wadysaw Jagieo)在位时 (1386-1434年),波兰社会日常饮食的整体水平已基本赶上西欧[22]。可以说,到15世纪末时从苏格兰到西西里,从葡萄牙到匈牙利的欧洲大部分地区,物质积累和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已相当普遍。与此同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对商品的生产、流通和交换提出更高要求,推动国际市场体系优化,最终建构起北欧贸易区的基本框架。
三、大宗贸易地理格局成型及北欧市场体系优化
14世纪里拓荒运动造成人口密度和自然禀赋的地区性差异,型塑起大宗贸易的地理格局。商品经济时代,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各地都会竭力开发对自己有利的资源——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提高效率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与人口密度较低地区的初级产品进行交换,这种地理分工创造出的专业产品迅速成为大宗贸易的核心内容[30]。在北欧,地区间彼此需求的自然禀赋催生出东方产粮区(主要是普鲁士、波兰)、西方制造品加工区(法国东北和低地城市,莱茵兰城市及英格蘭东部城市等)和东北方原材料供应区(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东岸)等专业化商品供给区。另有比斯开湾的盐产区,伊比利亚羊毛产区,加斯科涅葡萄酒产区,哈尔茨山和瑞典矿区,斯堪的纳维亚的林产品区及斯堪尼亚的青鱼,卑尔根的鳕鱼产区等。在城市内,生产部门进一步细化、分工,为大宗贸易供给各类制成品。专业化生产部门以纺织业为代表,另有器皿制造、武器加工、采矿、冶炼等部门。诸如低地地区的佛兰德呢绒、列日的武器甲胄以及莱茵兰的器具等皆实现了集约型、规模化生产。一地经济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它对其他地区商品的依赖就越强烈[31]。城市工业对原材料的需求,城市人口对谷物食品的需求都加速着地区间的互通有无。随着城市日益膨胀,市场供给的地理范围也随之扩大,旧有的地区性市场体系无法满足生产、生活的新需求,因此更需要远程贸易来维系商业平衡,这就加速了区域范围内的交往频率。快速交换的实现端赖于商人团体经营手段、交通要素(环境和工具)的改善④以及国际市场体系的优化。
12世纪以来日益繁荣的集市和城镇市场在欧洲搭建起多样化的商品交换网络,涌现出各类交易中心,到13世纪末时已形成国际-地区-地方三级市场体系的雏形[32]。黑死病期间,欧洲市场体系收缩、重组,展现出“现代”特征[20],为远程贸易提供新的运营载体,迎合了大宗贸易的发展需求。香槟集市衰落以来,城镇开始成为各等级体系的支配中心:它们在一种“组织化复合体”中相互依赖,在专门化和功能方面呈现多样性,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城市间的激烈竞争引发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吸引更多人口定居城市。随着城镇居民比例上升,地区内部清晰的城市等级格局显现出来。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卑尔根、哥本哈根、马尔默和卡尔马等城依靠与大陆的贸易联系形成网状格局;英格兰以金字塔状的城市(市场)体系著名于世,其全国性城市体系在1300年时大致形成,伦敦的领袖地位无可撼动;低地国家的城镇网络呈多中心形态,布鲁日、根特和伊普尔等城灿若群星。伊普尔在1315年有22,000人,根特有60,000人,布鲁日在1340年时人口达35,000,三市人口占全佛兰德总人口的18%,占财富的40%[33];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则形成“同心圆”状的市场体系。以人口和市区规模最大的科隆为例,它在13世纪就已形成一个西起亚琛,南至科布伦茨,北达多特蒙德,直径近110公里的经济圈。科隆商人从低地、纽伦堡和西班牙购进原材料,从加莱、英格兰和安特卫普购进呢绒和粗布进行再加工,然后分销其内部市场网络[34]。大卫·尼古拉斯将这种经济结构视为类似于“中心区位理论”(central-place theory)的多功能经济载体[34],德国学者则称之为“经济单元(Wirtschaftseinheit)”[35]。各单元之间往来互动频繁,相互层叠后形成“蜂巢式格局”,覆盖北欧各地的贸易中心或分中心,其中低地城市因区位、政策和工业化优势成为该贸易网络的中枢。布鲁日、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等港口城市先后成为该网络的商品集散地。endprint
此外,黑死病期间很多发展迟缓的中小城镇被完全湮没,具有区位、制度优势和商业活力的城镇、集市幸存下来,与中心城市结成紧密的层级市场体系。城镇数量趋于减少与竞争环境刺激市场分布趋于合理、便捷,进而降低成本增加市场利润有关。黑死病后,北欧投资活动更有吸引力,推动市场体系进一步整合,乡村集市开始发挥补充型市场的功能。集市吸引更多乡村人口涉足市场经济,使地方市场完全融入区域贸易体系当中。在城镇网络密集的地方,集市众多,地方特色浓郁且相距不远——至多十公里。大城市对商品的需求和销售同样也越加依赖集市市场。爱泼斯坦就将集市视为联结乡村与城镇市场体系的重要节点,认为黑死病后新出现的集市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混合功能:它们支持市场经济的扩张,成为对更为专业化的交易场所需求的一种有效反应。作为市场体系重组的一部分,新生市集在更为复杂的贸易结构与持续扩张的贸易模型内将地方贸易网络联结起来,加速一体化和需求弹性更大的消费品市场的兴起[28]。
四、汉萨贸易帝国与北欧贸易区成型
14世纪里,由商人携带商品进行海外旅行的原始形式被专职贸易的海外商业团体或代理机构取代。大宗贸易之初,北德意志汉萨商人利用区位、技术、信息和组织优势,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各地建起特许权贸易体系。他们在垄断北海-波罗的海大宗贸易之时塑造了北欧贸易区。汉萨时代的大宗贸易主要通过转运的双向渠道完成。首先,在各专业化产区或部门,生产者将其产品批发给次级市场(城镇或集市)的商人,再由后者经陆路和水路转运、汇集到河口或海港的集散市场(entrepot),这里聚集着各地的专职贸易商。中世纪晚期北海-波罗的海沿岸的主要商品集散港有伦敦、布鲁日、安特卫普、卑尔根、阿姆斯特丹、汉堡、不莱梅、吕贝克、但泽、斯堪尼亚、里加、纳尔瓦和诺夫哥罗德等,它们是北欧贸易网络的主要结点。其次是销售渠道。转运贸易商首先将大宗货物转运到第一等级城市的中心市场,然后再分销第二、第三等级市镇,最后由当地商人零售到周边乡村[26]。以汉萨商人在英格兰的贸易为例,位于伦敦的斯蒂雅尔德商栈集中来自北海-波罗的海的货物后再分配至(有时从布鲁日直接运往)英格兰的各汉萨分栈,如伊普斯维奇、诺维奇、大雅茅斯、赫尔和金斯林等。围绕小城镇和乡村的零售权⑤曾引起汉萨商人与英格兰商人的长期争夺。
某种程度而言,汉萨贸易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也可视为北欧贸易区的早期地理格局:低地地区和德意志西部作为汉萨海外贸易的中心区,与作为西部次中心的英格兰和法国北部一道,为汉萨商人提供工业原料和制成品,具体有英格兰的羊毛、北法的亚麻、布鲁日的呢绒、迪南特和列日的火炮以及科隆的武器、甲胄和器具等。北海南岸的比斯开湾和葡萄牙是汉萨海外活动的最西端。位于拉罗谢尔的汉萨哨站从该地购进大量湾盐;法国西南部的加斯科涅则为汉萨商人供应葡萄酒。波罗的海是汉萨贸易帝国的东方疆域,波罗的海北岸和东岸延伸为汉萨同盟的东方次中心区。如瑞典南端的斯堪尼亚青鱼市场一直由汉萨商人掌控。斯堪尼亚的国际集市通联着斯堪的纳维亚北端的边缘世界,主导着蜂蜡、木材、柏油和铜等产品的交易。波罗的海东岸的诺夫哥罗德是汉萨贸易帝国的东方支点,其东端边缘包括波洛茨克、维特博斯克和斯摩棱斯克,汉萨商人在此以制成品交换当地的亚麻、大麻和毛皮。在欧洲北端,冰岛为汉萨商人提供了硫磺、白鹰、海象牙和羊毛。14世纪初,冰岛人发明了腌鱼技术,此后挪威、冰岛的鳕鱼成为北海-波罗的海大宗贸易的重要内容,他们在卑尔根以腌鱼交易汉萨商人转运来的金属、香料和布匹等商品。苏格兰是汉萨商人北方贸易的另一终端。1297年斯特灵之战后,苏格兰军队和王国领袖安德鲁·穆雷和威廉·华萊士曾致信吕贝克和汉堡的市议会、市民,欢迎汉萨商人重返苏格兰,愿为他们提供新的贸易特许权[37]。在中南欧,汉萨同盟利用德意志南部与威尼斯的贸易轴线与北意大利诸城互通有无,购买利凡特奢侈品。鼎盛时期的汉萨同盟还将贸易触角伸向波希米亚,这得益于帝国皇帝查理四世的积极扶持。1375年查理四世出访吕贝克,与汉萨同盟建立贸易联系,给汉萨商人以关税豁免权和自由通行权,为吕贝克、汉堡和吕内堡商人建立商栈,鼓励他们出口铜、铅、银、锌等矿产和手工制品,输入它国商品,力求远程贸易途径其领地[38]。
总之,到15世纪初时,汉萨同盟已构建起一个以北德意志城市为核心,以四大海外商栈(伦敦、布鲁日、卑尔根、诺夫哥罗德)为支点,东起俄罗斯,西至葡萄牙,北达冰岛,南抵意大利的贸易帝国。这一贸易体系的边缘几经变动,但核心区域基本确定下来。17-19世纪里尼德兰和英格兰先后掌控了北欧国际市场的主导权,规范了北欧贸易区的现代范畴,孕育出原生型资本主义文明。它们建立起现代政府和国民经济体系后将大宗贸易升格为以本国港口为中心的集散贸易,取代了中世纪的商人转运形式。此后两国将其贸易手段从北欧推及全球,最终发展成现代贸易强国。
五、余言
黑死病后欧洲社会结构出现从共同体中心向个人本位,从领主权强制向个人自由发展的一般趋势;经济结构层面则出现从自给自足经济到市场化生产,从生活性消费转向投资性消费的系列变化。这些结构性变化成为北欧贸易模式沿革的关键因素。但中世纪的大宗贸易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课题,除存在经济社会史的结构分析路径外,还涉及许多其他领域,诸如有关商人组织、货币-金融的经济制度史以及航海技术史,甚至还要考虑地理因素、民族认同、宗教文化变迁因素,等等。而且对北欧大宗贸易的研究依然有待深入。目前学界仍驻足于对大宗贸易模式和内容的概括分析,未对不同时段的贸易总量做出有效的数理统计,因此无法对大宗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关联程度做出客观判断。所以在经济史外,这一课题的突破还需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等诸学科共同合作,将区域贸易史引入跨学科研究这一全新领域。另外,大宗商品贸易的概念从中世纪到现代不断获得新内容、新形式,其经济价值和社会功能也多有变化。近代以来,贸易史学家(如H尹尼斯和D诺斯)都强调大宗商品贸易(主要指初级商品和廉价制成品)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中的特殊功能。而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如何从大宗、廉价的商品贸易过渡到以优化生产主导商品贸易的可行性路径已成为各国竭力解决的首要问题。这对于当下正积极谋求从生产大国向生产强国转变的中国同样具有紧迫感。事实上,我们积极打造国家战略品牌,建构“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皆离不开中国特有模式的支持。所以从此层面来讲,探寻北欧贸易区成型及大宗贸易模式的沿革并非简单的一隅历史的复现,更是探寻国家发展、全球进步的现实价值所在。endprint
注释:
①中古世界的“大宗贸易”以海上贸易为主。因为就古代欧洲的交通条件而言,运载大宗商品的交通工具多依靠海船。陆路和河路则因道路废弛、战争、关卡和盗匪劫掠影响,大宗贸易只是局部存在。
②对于北欧贸易区的成型问题国内鲜见专门性成果。近年来沈汉教授曾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脉络有过讨论,他在文中指出世界市场(及各地区间的联系)并不是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欧洲旧大陆先是形成了地中海市场和北海-波罗的海市场,这两个市场联系起来以后才形成统一的欧洲市场。详见:沈汉.论世界市场的形成[J].贵州社会科学,2008(6):111-118.
③部分学者对此时欧洲的高增长率持怀疑态度,认为对高增长率持乐观态度的学者普遍忽视了1086-1688年间的通货膨胀和农民生存成本的提高,也没有虑及非自由农的可支配剩余产品等问题。但就整个中世纪欧洲的物质积累而言,递增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④14、15世纪里北欧的主要贸易商是德意志汉萨商人,他们拥有着相较复杂的运营模式、组织制度和工具技术,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作为独立课题展开,但本文暂不作详细讨论。
⑤零售权是中世纪商人行会的特许权之一,在中世纪前期有维护城市商业秩序的功能。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这种零售垄断权愈加不利于城市商业的扩展。外商与本地商人围绕于此的争夺有助于打破行会对城市商业的限制,导向良性竞争。但集权君主制建立后,商人行会的零售垄断权被君权所打破,零售自由成为国内市场统一的重要标志,而限制外商零售则转变为重商主义的一个特殊层面。
参考文献:
[1]R. Hilto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M].London: NLB, 1963:116.
[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资本主义的动力[M].杨起,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4.
[3]Robert Lopez. Trade and the Hanseatic League[J].in: S. Curry(edt). The 1300s(Headlines in History)[Z].California: Greenhaven Press Inc., 2001.
[4][意]卡洛·奇波拉.欧洲经济史[M].第一卷.贝昱,张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53-154.
[5]C.M. Cipolla.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 [M]. New York: W.W. Norton, 1976:120.
[6]J. Titow, English Rural Society, 1200-1350[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69:45.
[7][美]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 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392.
[8]Spencer Dimmock.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in England, 1400-1600[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2014:26,28,31.
[9]Werner Rsener. Peasants in the Middle Ages[M].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Stütz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2:91,105.
[10]侯建新. 资本主义起源新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82.
[11]Richard H. Britell.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nglish Society 1000-1500[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84-185,156.
[12]W. Jordan, The Great Famine: Northern Europe in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60.
[13]James Thorold Rogers. 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bour[M].Vol.1,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236-298.
[14]Peter Spufford. Money and its Use in Medieval Europ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234-235.
[15]H.P. Brown and S.V. Hopkins. A Perspective of Wages and Prices[M]. pp.13-59. 轉引自王超华. 西方学界关于英国工资史的研究[J]. 史学月刊,2010(8):15-22.
[16]Bruce Campbell. English Seigniorial Agriculture, 1250-145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406-410.endprint
[17]John Day. The Medieval Market Economy[M]. Oxford an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63.
[18]Christopher Dyer. Standards of Liv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c.1200-1520[M].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57-58.
[19]Marteen Park. The Dutch Republic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Golden Age [M]. Translated by D. Web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91.
[20][英]克里斯多夫·戴尔.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M].莫玉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76,170.
[21]Robert Brenner.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J].in: Peasants into Farm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Low Countries(Middle Ages-19th Century) in Light of the Brenner Debate[Z].edited by Peter Hoppenbrouwers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Trunout: Brepols,2001:311-322,3.
[22]Maria Dembińska. Food and Drink in Medieval Poland, Rediscovering a Cuisine of the Past[M]. Translated by Magdalena Thoma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9:11.
[23]David Nicholas. The Northern Land—Germanic Europe, C.1270-1500[M]. London: Wiley- Blackwell, 2009:310.
[24][荷]揚·卢滕·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M].隋福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65.
[25]David Nicholas. Trade, Urbanization and the Famil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Flanders[M]. Variorum: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1996:14.
[26][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M].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225.
[27]S.R.爱泼斯坦.自由与增长:1300~1750年欧洲国家与市场的兴起[M]. 彭凯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83.
[28]Frances Gies & Joseph Gies. Life in a Medieval City[M]. New York & London: Harper and Perennial, 2016:45,109-110.
[29]Ghillean Prance, Mark Nesbitt, The Culture History of Plants[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5:161.
[30]S.R. Epstein.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Europe,1000-150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90.
[31]Tom Scott. Town, Country, and Regions in Reformation Germany 1300-1600[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221.
[32]Charles Tilly. Cities and States in Europe,1000-1800[J].Theory and Society,1989,18:579.
[33]David Nicholas. Town and Countrysid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ensions in 14th- Century Flanders[J].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0, No.4, Jul.,1968:458-485.
[34]David Nicholas. Urban Europe, 1100-1700[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3:50-52.
[35]H. Ammann. Die wirtschaftliche Stellung der Reichsstadt Nürnberg im Sptmittelalter[J]. Nürnberger Forschungen, Band 13,1970:194-223.endprint
[36]Alexandra Livarda. Spicing up life in northern Europe: exotic food plant imports in the Roman and medieval world[J]. Veget Hist Archaeobot, 2011,20:143-164.
[37]C. Moriarty, The Voice of the Middle Ages, in Personal Letters, 1100-1500[M]. New York: Peter Bedrick Books, 1989:101-102.
[38][德]赫伯特·格隆德曼. 德意志史[M].第一卷(下).张载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90-191.
A Traceability to the Forming of Northern Europe Trade Are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eval Bulk Commodities Trade
LIU Cheng1,2
(1.History Colleg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China; 2.History Colle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In the high Middle Ages, the accumulation of material in European society stimulated the exchange of goods, leading to disintegration of “Landlords-Peasants” structure and manor economy. After the “Black Dea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of Europe had been adjusted, material accumulation and consumption levels recovered and increased, the market exchange had become norm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system got to optimize and reorganize. The Nordic Region had developed a geographical division which based on natural endowment, and established the content and operation ways of bulk commodities trade.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the Hanseatics who were professional businessmen had bulk a trade empire, that eastern to Russia, western to Portugal, northern to Iceland, and southern to Italy, marked the forming of the Northern European Trade Area. Netherland Republic and England Kingdom created a kind of Port Distribution Trade that relied on a powerful national economy and replaced the transshipment trade of Hanseatic, and ultimately developed into modern trade powers. The close connection among economy, trade model and trade area is enlightening to China, which is actively seeking to transform from a manufacturing country to a productive power. Now we try to forge the national strategic brands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of “Belt and Road” that are both the effective attempts of participating in or dominating global trade.
Key words:Northern European trade area;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s; market system;bulk commodities trade; Hanseatic League
(責任编辑:周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