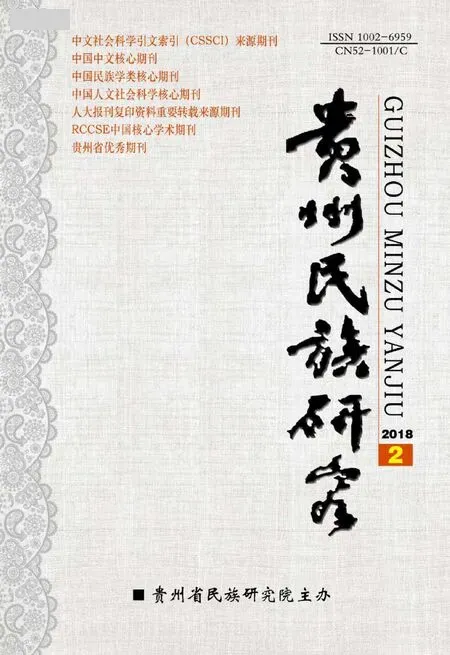美学视域下的《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的文化解读
肖燕姣
(西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500)
文化是人类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后,经过漫长的发展所形成的成果。《格萨尔》 《荷马史诗》是作为早期人类文明成果,在展示历史的同时,也整体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风貌。《荷马史诗》发端于古希腊,是希腊文明的杰出代表,而《格萨尔》出现在古代中国的文化区,所以,两大史诗在呈现出文化共性的同时,也展示了各自的民族性、地域性特点,尝试将人类早期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史诗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宗教文化为两部史诗奠定了文化底色
(一)奥林波斯宗教奠定了《荷马史诗》诞生之基
宗教属于人类早期基本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人类崇仰心理的重要呈现。《荷马史诗》是在古希腊神话、传说等基础上,经过文学加工逐步形成的。古希腊神话的出现和宗教有密切关系,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希腊神话也称之为奥林波斯宗教,该宗教是一神和多神的科学统一,不仅有主神宙斯,也包含其他的神。生活在奥林波斯山上的神灵,参与了发生在特洛伊的战争,他们自始至终都出现在《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爆发源自“金苹果”,雅典娜、赫拉、阿佛洛狄德都想拿到这个苹果,而这场战争的主导之神——宙斯,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控下进行着,并且每一个出场人物的命运已经预设。《伊利亚特》描写了太阳神阿波罗,惹怒了阿基琉斯,挑战阿伽门农的权威,雅典娜从天上降临到阿基琉斯身边,告诫其不要生气;阿基琉斯让其母亲向父亲宙斯请求帮助,后来雅典娜到希腊军队中,鼓励战士展开对特洛伊的战争,这时候阿基琉斯彻底愤怒了,带领军队积极应战,取得战争大胜后,便将赫克托尔置于死地,看上去是阿基琉斯完成的,实际上是神灵提前预设好的。奥林波斯宗教也贯穿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遇难到最后实现返乡,这些也都是神灵早安排的。波塞冬曾受神明指使,制造了大量灾难,但智慧女神则帮助主人公逃脱灾难。因此,希腊神话、奥林波斯宗教,为《荷马史诗》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础,特别是奥林波斯宗教中所蕴含的宗教文化观,体现在宿命论、神力上,尤其是拥有超自然的神力,[1]这是神明独有的神力与本领。生活在奥林波斯山上的众位神明自然都具有超凡的神力,特别是主神宙斯,他作为希腊人、特洛伊人的主宰,能左右人的生死,也能调配人的成功与失败,这样看来,特洛伊城是由奥林波斯的诸神所控制。
(二)苯教和佛教文化交织下的《格萨尔》
《格萨尔》中呈现出浓厚的宗教文化底蕴,全景式呈现了宗教文化,既有大量的宗教遗址,也有宗教理念。自然宗教突出泛神论,体现万物有灵,在史诗《格萨尔》中,不管是动物,还是普通的植物等,都有魂灵,比如山神、湖神、树神等,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寄魂物都呈现出灵魂观,再如《格萨尔》中提到的寄魂物是阿尼玛沁雪山,霍尔国的白账王、黑账王以及黄账王的寄魂物是白色、黑色和黄色野牛,然而,鲁赞王的寄魂物比如寄魂牛等多达9个。英雄格萨尔在战事来临之前,先想尽一切办法去毁坏敌方的寄魂物,这实际上是将人和大自然物结合在一起,让自然物获得灵魂。实际上,这些也隶属于自然宗教领域,《格萨尔》更强调了人文性质的宗教文化,主要包括苯教与佛教文化。苯教源自藏文化,是在藏族本土文化出现并渐渐发展起来的,苯教经典著作《大藏经》系统描写了自然崇拜,以及神山、战神和神湖等等,这与《格萨尔》中提到的“马赞”、“山赞”等理念本身有内在一致性。所以,史诗中存在大量自然崇拜,既有自然宗教,也有苯教的文化渗入,两者是相互交融的。[2]
佛教对藏族来讲,属于外来宗教,是经由中原、印度传入的,唐代的文成公主对佛教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史诗《格萨尔》的流传和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宗教文化和史诗在吐蕃王朝得到空前发展,历史上称此为藏传佛教前弘期;11世纪后,史诗发展逐渐完善,佛教也在这时渐渐兴盛起来,历史上称为后弘期。《格萨尔》诞生于该文化背景下,曾受佛教文化的长时间熏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些宗教文化在《格萨尔》中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3]《格萨尔》中存在大量藏传佛教文化。藏传佛教传至青藏高原后,与当地文化结合,并生成了佛教支派,和主流佛教差别非常大。《格萨尔》因受藏传佛教的长期影响,带有明显的藏传佛教印记:一是史诗中保存藏传佛教中的大量神灵,比如,观世音菩萨、莲花生大师、世尊阿弥陀佛、天父白梵天王等,神灵在天界居住,但也各自承担不同的人间事务,神灵决定人间每一个人的命运,就连英雄格萨尔的生死都是由神灵设置好了的,格萨尔只是按照神灵预设的步骤演出一场威武雄壮、惊心动魄的戏剧。善恶观属于人性、人生和道德层面的问题,是宗教文化的核心理念。善良是应认可的积极的、正面的思想与行为,能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让民众获得福祉;恶是负面的、应否定的行为和思想,这样不仅能全面推动社会发展,也能符合社会大众的基本礼仪,这样才能实现在相互斗争中实现发展,不仅对立相互统一。藏传佛教、苯教内存在善与恶的对立,并引发美丑、黑白与是非等的对抗。藏传佛教核心教义是善,《格萨尔》既然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自然表达了惩恶扬善的主题,格萨尔是善的代表,而魔王便成为恶的代表,伏魔降妖自然是惩恶扬善。善恶之间的斗争,最终善将战胜恶。格萨尔抑强扶弱、伏魔而投胎来到凡间,在历经长期的斗争,最终完成大业,回到了天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属于宗教中常提到的“轮回”。[4]
宗教文化为人类童年及早期意识形态,尤其体现在早期史诗中;《荷马史诗》 《格萨尔》向人们呈现了早期宗教文化的发展状态,是典型的宗教文化美,充分表明宗教文化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价值。宗教文化属于早期人类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对推动历史进步及全方位增进民众福祉,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财富。
二、人本主义文化得到了彰显
人本主义注重以人为中心,让个体价值得到满足与实现,“人”自然成为其出发点与归宿,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荷马史诗》 《格萨尔》中得到呈现。通过从不同视角来审视人本主义文化,能更好明确史诗的人本主义底色。[5]
(一)物质、精神双重利益追求的肯定
首先,这一张扬展示了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肯定。《荷马史诗》中爆发特洛伊战争,导致这场战争的表面原因是为争夺美女海伦,然而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为掠夺并占用更多的奴隶及财富。考察历史发展可知,当从氏族公有制逐步发展到奴隶私有制时,那个时代新兴阶级的欲望是占有更多的财富与奴隶,这在史诗中得到了赞许与肯定。阿基琉斯因为女俘虏被别人抢去,就敢于挑战权势更大的阿伽门农。而奥德修斯不惧艰难险阻,毅然回到故乡本身也存在财产方面因素,将财产带回家是为了增加财富,而回家后将敌人铲除则是为了保全财产。格萨尔的神圣职责是拯救百姓的苦难于水火之中,苦难正是源自魔妖的掠夺导致的物质匮乏,当一个魔国被征服后,格萨尔便将战利品分给部下及民众,比如,格萨尔在征服大食国后,其举行了财产分发仪式,并对民众讲道,将财产分发,是让民众都享受福禄,这是上天的安排。王绒察查根便根据格萨尔的安排,将财物进行科学分配。其次,人本观在精神层也有体现,在英雄时代,荣誉和尊严是第一位的,是其他任何财富都不能比的,尤其是阿基琉斯,其发动战争的直接诱因是为荣誉而战。[6]
(二)淋漓尽致展示个体自由意志
从整体的框架来看,不管是《荷马史诗》,还是《格萨尔》,都呈现了命运的安排、神灵的意志,阿基琉斯、奥德修斯、格萨尔等其人物的命运是由天神所掌控,然而,因为他们并未对神明的命运所屈服,而是在能掌控的时间与空间中,去全面展示个体的自由意志,将人的命运加以全面审视。发挥自由意志,不仅是抗拒神明本意,更是张扬了人本理念。从这里能看出,《荷马史诗》 《格萨尔》中讲到的英雄去展示个体的智慧与本领,并彰显了个体生命价值。史诗中的人本文化重点体现在人本文化方面,英雄文化作为激发民族崛起的时代精神,歌颂并弘扬英雄,成为那个时代发展的旋律。在《荷马史诗》 《格萨尔》中谈到的英雄,不仅本身有超出常人的英勇精神,还有超越常人的军事本领,其本身拥有半神半人的特色,也有天神之子,还有和神明之间存在血缘关系。不管是奥德修斯、阿基琉斯、赫克托尔,还是格萨尔等,都是在民族主义感召下,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努力拼搏,采用个体的身体和生命换回个人、集体的尊严、荣誉与财产,进而在对大自然或者对敌抗争中,展示个体的生命价值,特别是在那个张扬英雄的时代,这也展示了丰富的文化价值。[7]神本主义、人本理念是英雄史诗独有的文化特色。纵观人类长期的发展历程,将其粗略分成神明时代、英雄的时代与人的时代,特别是英雄的时代是从神明到人发展进程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该时代,不仅存在旧神本主义文化,也包含新人本主义文化,两者不仅相互排斥,也相互统一,达成二元共生的局面,这一特点在史诗中有较好的体现。
三、外在展示的风俗文化
英雄史诗的深层结构是人本文化与宗教文化,其外在的风俗文化也能让人感受到其厚重的文化底蕴。《荷马史诗》 《格萨尔》向人们呈现出许多风景。风俗文化是人们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风俗习惯,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较好呈现。风俗表现出保守性、稳定性和模式化的特点,展示出变异性与时代特色,呈现出史诗所描绘时代的风俗文化,让史诗更贴近生活。[8]
(一)独具匠心的战争风俗
英雄史诗《荷马史诗》 《格萨尔》都大量描写战争,阐述战争风俗,《伊利亚特》描写到在发生战争时,将领们身穿铠甲、头戴铜盔,手拿盾牌、铜枪,不管是集体冲锋,或者是单个决斗,都展示了英雄的本色,特别是对手间的决斗,都事先量出地面,然后再抓阄决定谁先进行铜枪投掷。在战斗过程中,不仅有车战,也有步战,也能看到马拉战车进行战斗的情境。在战争开始前,还要举行长老议事团会议,展示军事民主。在战争开始前,交战双方都要开展一系列的祈祷、献祭等活动,向神灵传达信息,并求神灵保佑,祭祀中最为重要的宗教祭祀是百牲祭,将牺牲围着祭坛一个圆圈,经参与祭祀的人举行简短的净手礼之后,每人抓一把大麦粉,按照祭司的安排开始祷告,祭司宣布祷告结束后,宰杀牺牲,再由祭司继续主持祭祀仪式,奠下美酒,举行集体会餐。《格萨尔》中谈到的每次战争开始前,天神将进攻命令下达给格萨尔,战争过程中,不仅有士兵之间,也有将领之间的拼杀,各种法术也齐上演,其中也有大量的占卜、祷告等仪式。
(二)普通的文化与家庭风俗
生活习俗是较为广泛的文化风俗,不管是《荷马史诗》,还是《格萨尔》中,都有体现。《荷马史诗》中全面展示了当时人们的餐饮、衣着以及丧葬等多个方面的习俗,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伊利亚特》中,通过赫菲斯托斯绘制阿基琉斯的盾牌画,插叙了希腊人的婚俗以及歌舞娱乐等。[9]《奥德赛》展示了家庭生活,特别是普通家庭中,丈夫远征未归,求婚者便向家中女主人求婚,进而达到挥霍、享用家产的目的。然而,奥德修斯之妻佩涅洛佩却表现出对丈夫、爱情的忠贞,采取多种方式故意拖延求婚人的爱意,而在其家中,牧羊奴、牧猪奴及一些奴仆有的一直忠诚,而有的则直接选择了背叛,通过全景式展示奥德修斯的家庭生活,呈现出贵族家庭生活。
《格萨尔》蕴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神秘气氛多,烟火味少,但是也描写了大量的生活风俗,比如衣着、赛马、饮食等,风俗文化在文化中处在重要地位,是深层次文化的外部显现。[10]风俗文化形成了史诗的社会风貌,其展示善恶美丑,在进入文学作品后,就成为独特的风景。比如,《格萨尔》中谈到了佩饰铜镜,这是用作装饰品,称之为"宝镜"。根据相关文献记载,铜镜只有巫师的服饰中才能佩戴,是重要的法器,象征着太阳的光芒,能除魔辟邪,诊治疾病,戴铜镜还能从镜子中拥有神秘的能量,这实际上是早期人类原始文化的展示,显示了铜镜的地位与作用。
总之,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解读《荷马史诗》、《格萨尔》,向人们呈现出价值。宗教文化作为两部英雄史诗的文化底色,奥林波斯宗教成为《荷马史诗》的源头,而苯教和佛教文化的交织演绎了《格萨尔》。此外,人本主义文化得到了彰显,物质、精神双重利益追求的肯定,并且淋漓尽致展示个体自由意志,最后,还能看到两部史诗所展示的风俗文化,既看到了独具匠心的战争风俗,也能很好领略普通的文化与家庭风俗,提升对《荷马史诗》、《格萨尔》这两部史诗的了解水平。
参考文献:
[1]韩伟,李雄飞.《格萨尔》史诗的文学意义[J].民族文学研究,2008,(2):70~74.
[2]褚娜.《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王》男性形象及文化内涵对比研究[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22):35~36.
[3]罗文敏.从《荷马史诗》看《格萨尔王传》[J].青海社会科学,2009,(5):103~106.
[4]陶铖.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美学建构之比较[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18~22.
[5]陶铖.荷马史诗与《格萨尔》艺术比较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29~33.
[6]王海.荷马史诗与《格萨尔》原始思维之比较[D].内蒙古师范大学,2008:20.
[7]程志敏.荷马史诗导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
[8]熊黎明.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叙事结构比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141~144.
[9]金石,彭敏.深度的挤压与广度的繁荣--论《格萨尔》的传播形态[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130~133.
[10]丹增诺布.浅析《格萨尔》史诗中的口头程式语[J].西藏艺术研究.2013,(02):5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