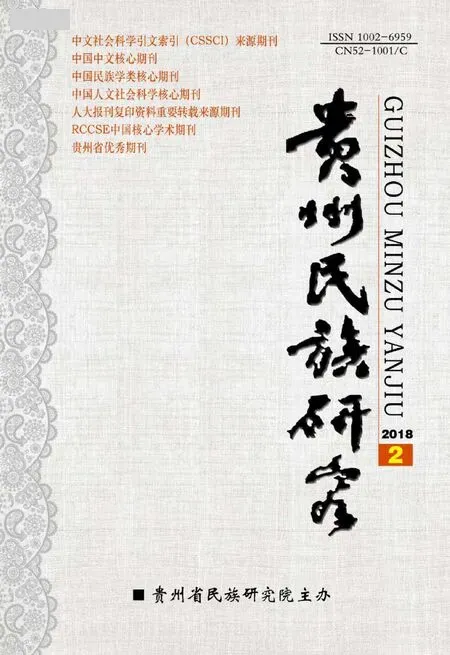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问题、原因和对策
——以云南省大理市白族为例
张艳华 吴大华
(云南大学 法学院,云南·昆明 650504)
大理市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州政府驻地,是大理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大理市是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幅员面积达1468平方千米,下辖10个镇、1个民族乡,共有20个居委会、109个行政村,全市人口61万人,其中白族占65%。1982年,大理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享有“文献名邦”的美誉。白族是一个勤劳智慧、勇敢善良、多才多艺的民族,白族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从大本曲、白剧、洞经古乐,到白族服饰、白族扎染、白族民居,再到三道茶、沱茶、雕梅,无一不体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是白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和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也是白族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大理市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存在的问题
从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我国于2004年8月加入)生效开始,特别是在2011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之后,大理市政府组织开展了大量的调查、整理、认定、记录、申请、宣传、展示等工作,使非遗的传承走上了正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保护事务日益受到重视、保护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加强,非遗日渐淡出了百姓生活。例如,以前白族村落的女孩要从小学习剪纸、刺绣的技艺,出嫁前要自己准备刺绣的新娘服饰、枕巾、帐檐,当妈妈之前又要为小孩准备刺绣的帽子、鞋子、围嘴,这是白族女性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但随着白族人的逐渐“汉化”,农村社会现在对白族女性已经不再有这样的要求,她们也就不再掌握这样的技艺。在位于海东农贸市场的省级非遗(白族剪纸、刺绣)传承人杨慧英的“慧英剪绣坊”中,铺面摆放的是普通的床上用品和机器绣的物品,手工绣的物品陈列在里面的房间里,可见购买后者的顾客并不多。再如,洱海鱼鹰驯养捕鱼技艺是洱海渔民古老的狩猎方式,但1987年《渔业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电力、鱼鹰捕鱼和敲舟古作业”,之后洱海范围内逐渐禁止使用鱼鹰捕鱼,鱼鹰捕鱼从谋生手段转变成短时期、小规模的表演旅游经营项目,但“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造成很多人的模仿,为了追求高效益,纷纷驯养鱼鹰开展鱼鹰捕鱼活动供游客观赏,造成洱海区域的生态破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为进一步加大洱海保护治理力度,2015年6月15日大理市政府发布《大理市人民政府公告》第6号,要求所有鱼鹰表演点在2015年7月10日前全部迁出洱海湖区,作为表演项目的这一传统技艺濒临绝迹。
(二)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非遗成了旅游业的附属。例如“三道茶”本是白族人民饮茶、待客的一种习俗,现在别说在白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就连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祝寿拜师、新居落成时都难觅踪影,顶多只冲第二道“甜茶”,寓意为日子甜甜蜜蜜、红红火火,却无法折射出“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人生哲理,本地白族年轻人对“三道茶”的感觉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想要喝到正宗的“三道茶”并不容易,反而外地游客在旅游景点、游船、城楼上却能轻易品尝到,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现象。“三道茶”似乎已经和本地人生活关系不大,却成了发展旅游和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从生活习俗蜕变成了旅游资源。
(三)非遗中的敏感元素被放大,歪曲了非遗的价值和功能。例如“绕三灵”本是白族群众为了求雨、祭祀、本主崇拜、娱乐而举行,但外界盛传的说法却是“白族情人节”“风流会”,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一传十、十传百的以讹传讹之后,一些白族群众参加“绕三灵”都显得遮遮掩掩、难以启齿,似乎不那么光明正大。诚然,“绕三灵”的歌舞中不乏有性暗示、男女传情的成分,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婚外恋、情人约会等情形,但这毕竟只是非主流。“绕三灵”本具有的“正能量”被弱化,其中的“小插曲”却无限放大,成为了本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外地人探秘猎奇的目标。“有关‘绕三灵’婚外性的过度发挥和想象,以及种种牵强附会的过度阐释,无异于意淫这个民间盛会。”国家级非遗(大本曲、绕三灵)传承人赵丕鼎说:“有人说‘绕三灵’是‘风流会’、‘借子会’,其实‘绕三灵’有好几百年历史的,以前确实存在,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早就没有了,男女对歌倒是多的。”
(四)非遗中的手工部分被机器取代,天然原料被化工原料替代。例如原来的“白族扎染”从扎花、浸染、拆线到漂洗、脱水,全都是手工操作,染料是板蓝根。在恶性竞争下,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规模较大的生产者改用脱水机、烘干机取代自然晾晒,用烫平机取代石碾压平整,用化工染料染色。在白族扎染之乡——周城,供游客参观的开放院落里盛有板蓝根染料的水缸只是作势和摆设而已,就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仕绅都坦白承认,“我的布料里,也只有五成用板蓝根染色”,这是因为,“传统植物染所用的原料板蓝根,其成本价格约相当于化工染料的3倍。加之工序复杂,对染工技术和经验要求高,算上染色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工和时间成本,植物染是用化工染成本的5倍。”
(五)非遗开发更注重形式,对实质内容的关注不够。例如“三月街”,政府每年对三月街的宣传造势声很大,很多外地人慕名而来参加这个所谓“千年赶一街”的民族节,但很多游客却是“盛兴而来、败兴而归”,因为三月街上看不到更多的民族特色商品,而充斥着随处可见的廉价商品和减价特卖的广播吆喝,与一般的露天市场无异,最古老的商品如牛马、家具等早已不见踪影,药材的种类很多但品质却无从保证,白族服饰也不如从前又多又漂亮,传统体育项目如龙舟、陀螺、秋千、射弩已于2007年开始不再举办,这让土生土长的大理人很是遗憾,感觉“每年赶三月街,就是去凑凑热闹。”“把‘三月街’的经济贸易功能提高到最重要的地位,而将民族文化传播与交流功能居于从属地位的做法,将会使大理民族文化失去其按规律发展的空间。”
二、大理市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遗已然成为“文化资本”。非遗作为老百姓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本不具有经济价值,但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却也无法独善其身,不得不和经济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从属于经济、为经济服务,被包装成各种“文化产品”供人们消费,成为了“文化资本”。近几年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可以说是丰衣足食。在老百姓的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精神需求日益增长,文化产品的价值愈加凸显,在作为交通枢纽、文化重镇和旅游名城的大理,智慧的白族群众很早就享受到文化产品带来的利益,意识到将自身具有的“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能够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大理的旅游业之所以兴旺发达的原因,除了拥有得天独厚的苍山、洱海等自然资源以外,还得益于其“文献名邦”的美誉、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描写的大理国、电影《五朵金花》讲述的故事以及白族人民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是大理的旅游产业这一支柱产业的坚强后盾,成为当地百姓谋生的重要手段和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文化产品作为“产品”,就要讲求经济效益,不可能赔本赚吆喝,但如果将成本收益的计算手段用在非遗产品的开发中,问题就出现了。因为非遗植根于农耕社会,对应的是天然材料、手工生产、慢工出细活,而在资源匮乏、人力成本高、生活节奏快的现代社会中,非遗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使消费者望而却步,特别是在前期推广、宣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消费者大多不知道非遗产品的真正价值,总觉得这些产品很土很原始,应该很便宜才对,高昂的价格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为了降低价格,一些商家就从降低成本方面做文章,用机器替代人工、用化工原料替代天然材料、简化工序,以实现非遗产品的快速生产,而游客大多是匆忙消费,根本来不及比较不同非遗产品存在的差异,在实行“价低者得”的无序市场中,传统非遗产品败下阵来,固守非遗产品的制作理念和制作工艺,无异于自取灭亡,久而久之,原生态的传统非遗就自然而然地渐行渐远并最终消失了。
(二)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使得非遗变成了大理的“文化符号”。当下,各地政府都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来到大理的游客,除了欣赏苍山洱海的自然风光以外,也很想体验大理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族风情,颇具特色的非遗即被打造成为吸引游客的人文资源,“三月街”“三道茶”“绕三灵”等就成为了大理的“文化符号”,让游客能够记住大理、怀念大理。一方面,作为代表大理的文化符号,政府在对外宣传时是着重强调的,这些文化符号作为桥梁和纽带,拉近了大理和世人的距离,增强了大理的感染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使大理以历史文化名城的姿态走进人们的心里。另一方面,游客来到大理后,作为文化符号的非遗成了消费对象,并且知名度越大的消费量也越大,这就使得非遗的开发利用势在必行。例如洱海游船、喜洲严家大院、张家花园的“白族三道茶歌舞表演”已经成为了大理旅游的代表性节目,游客一边欣赏阿鹏和金花表演的白族歌舞,一边品尝经过“烤、调、烹”的三道茶,从中领略到浓郁的白族传统文化。“三道茶有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文化底蕴,通过歌舞表演的形式加以展示,提高了大众参与性和知名度,每年的营业收入近2000多万元,是大理州文化和旅游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但是,作为一个符号,其价值并不在于本身那几个字,而是背后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三道茶”所展现的正是大理白族人民吃苦耐劳、热情好客、开放包容的性格。作为文化符号的非遗,应该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还应当是底蕴深厚的白族文化的体现,在开发利用某项非遗时,首先要充分地认识非遗的基本特征,深入地挖掘非遗的文化内涵,将该文化符号所传达的理念、精神和特色准确地通过文化产品的形式展现出来,使非遗的原真性、完整性落到实处,从而让游客真正感受到非遗的独特魅力,并非是一味炒作和过度宣传,而是“既有名也有实”,从而加深对大理文化的认识。但现实状况却是,政府在利用文化符号进行旅游宣传时说得天花乱坠、引人入胜,而在非遗开发利用中却稀里糊涂、得过且过,对其实质内容的关注不够,“雷声大雨点小”,保护工作流于形式和表面,反而使非遗受到“保护性破坏”,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文化符号的价值并非决定于其精美程度和宣传力度,而是取决于其所象征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和特色,作为文化符号的白族非遗,其价值来源于白族先民世代积累的生产经验、生活法则和意识形态,当代人在坐享其成地“开采资源”时,应着眼于保持甚至增加该项遗产的文化价值,而不能使其受到贬低和损害,缺乏游客口碑的非遗开发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将加速白族文化资源的枯竭,白族文化符号也将不再具备区别性和显著性,最终成为大理白族人民永远的遗憾和损失。
(三)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导致大理白族地区的“文化变迁”,非遗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成了“弱势文化”,急需传承和保护。例如每年一度的“三月街”诞生于物资匮乏和物流困难的农耕社会,白族人民从中可以买到平时无法买到的大件商品、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但在物资极大丰富和物流异常方便的今天,“三月街”原本的商品交易功能日渐削弱,人们去赶街,更多的是去赶场,赶的是热闹之场、文化之场、历史之场,而不是冲着购物去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直以来似乎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相比较经济落后地区的文化具有天然的优势,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和效仿,在大理地区也不例外,白族年轻人普遍穿着T恤、牛仔裤和运动鞋,吃着洋快餐,看着国外大片,听着流行音乐,说着汉语言,对白族文化不感兴趣甚至并不知晓。大理古城售卖的民族服装大多是具有民族风格的现代休闲服装,无法辨认具体民族,白族服装很少,且大多是小孩穿的,质量不好、价钱便宜,可以看出其用途仅为短期、过节或拍照时穿着,并非日常穿着。在离市区相对遥远、经济相对落后的海东、挖色、江尾等地,只有老年妇女还戴着包头、系着围裙、穿着对襟衫、戴着玉耳环。而在2017年3月被国家民委评为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民族特色村寨”的龙下登和下阳波村,这样的穿戴已经很少,老年妇女只是在干农活时腰间系一个民族刺绣小包用来装随身物品。大理古城的非遗博物馆每天都定时有洞经音乐和大本曲的表演,但观众寥寥无几,偶尔驻足的也是走马观花的游客,游客普遍反映听不懂也不好听,本地人宁可到隔壁的玉洱园去赏花都无暇来欣赏民间艺人的演出。诚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代化的步伐不可阻挡、乡土文化的变迁已是必然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观点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非遗因为时代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其固有的群众基础和生存条件,一些面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顺其自然地让它们被历史淘汰,没有必要去强行挽留,想留也留不住。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非遗是农耕文明最后的痕迹,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源泉,更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守住非遗就守住了人类的文明根基和精神家园,绝不能任由其自然萎缩和消亡,而是要在承认文化变迁这一客观现象的基础上,在主观上树立抢救和保护非遗的危机意识,并将这种意识落实转化为行动,否则其一旦消失殆尽将不可挽回、无法再生,千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
三、加强大理市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对策
(一)确立大理白族人民的主体地位,由他们来决定非遗的传承和保护。非遗作为“草根文化”,发端于民间、成长于民间,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一直默默无闻、自由生长,直到2006年4月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生效,作为缔约国的中国开启了非遗保护之旅,非遗进入了国家视野,得到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可和重视。“这是民族国家开始重新定位并审视自己已有文明的开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民族文化自觉的体现。”由此可见,从非遗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来看,其来源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实践,在老百姓集体智慧的沃土中茁壮成长,自古以来没有经过主流意识的引导,非常“接地气”,只有老百姓的创造性贡献才能使非遗历久弥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脱离了老百姓的生活,非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多的保护工作和传承措施都是徒劳无功。因此,“非遗的形式和内容是什么?如何保护和传承非遗?”这些问题应该由当地老百姓特别是非遗的来源群体来回答,“社区居民的认可是实施保护的先决条件,可以说社区居民的态度起着决定这些文化遗产命运的作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十五条也明确规定:“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即缔约国政府要努力让来源群体参与到非遗的保护活动和管理行为中,让他们有知情权和话语权,以此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其中第一条规定:“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应在保护其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首要作用”;第二条规定:“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力而继续进行必要实践、表示、表达、知识和技能的权利应予以承认和尊重”;第六条规定:“各社区、群体或个人应评定其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受制于外部对其价值的判断”;第七条规定“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群体和个人应从保护该遗产所产生的精神或物质利益中获益,特别是社区成员或他人对其进行的使用、研究、文件编制、推介或改编”;第十条规定“社区、群体和相关个人应在确定任何物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威胁(包括脱离情景、商品化和失实陈述)以及确定如何防止并减轻该等威胁时发挥重要作用”。即要求政府承认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对非遗的创造性贡献,在此基础上要确保他们在非遗的继续实践、价值评定、利益分享、排除威胁等方面具有主体地位。大理市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对于其内涵界定、实践方式、传承途径、保护机制等问题,应当由大理市白族群众来集体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人习惯对集体事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常言道“三个和尚没水吃”,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这种权利意识更加淡薄,那么,如何促使白族群众能够更便捷、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笔者建议,可以借鉴《著作权法》中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规定,由依法成立的非遗集体管理组织根据白族群众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权利,并在扣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后将所获收益用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事业。当然,非遗集体管理和著作权集体管理有些许不同:一方面,非遗集体管理组织是一个群体内部的自治组织,不是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开放型组织,因此这个组织从法律性质来说应该是代表机构而非信托机构,其成员应是本群体的人并由本群体选举产生,而不能由社会上的其他人担任。另一方面,非遗集体管理组织比起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来说,其职能不仅包括有权代表白族群众解释、宣传、开发、利用非遗,进行有关的诉讼和仲裁,还包括对利益的分配和使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只需要向权利人转付使用费,出于非遗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不建议非遗集体管理组织将所获资金转付给本群体成员,而应将其专款专用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事业上,这种对于公共资金的分配和使用行为就需要更加严格的监督和公示制度作为保障。
(二)结合大理市旅游业的发展情况,坚持走非遗的精品化道路。首先,在旅游业这一朝阳产业日新月异的今天,大理作为著名旅游城市,非遗的保护和开发不可避免地和旅游业捆绑在一起,2017年的大理市两会,提出了“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旅游城市的目标任务……加强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彰显绿色城市和人文城市特征。”旅游产业要向纵深发展,差异化、多样化、精品化的非遗产品将担当重任,游客在饱览大理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的自然风光后,再来领略大理多姿多彩、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才会觉得大理名不虚传,自己不虚此行,“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游客的口碑是最好的旅游宣传,有了游客的良好口碑,大理才能早日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在大理开启洱海抢救模式、迎来史上最严洱海治理令的同时,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也应更上一个台阶。其次,非遗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因其手工生产、天然原料、独创设计等因素导致其成本居高不下,但也正和居住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的城市人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健康环保的理念不谋而合,整齐划一、质量过硬的工业品只能满足现代人的物质需要,却无法承载他们的精神需求,而非遗产品恰恰能够通过手工艺人的一针一线、表演艺人的一颦一笑传达出浓浓的人情味和乡土情,现代化机器批量生产出的只是工业产品,而手工艺品则是体现个体差异和个性品味的,两者不能等同和混淆,也不能相互转化和替代,不能将工业产品的成本效益规则套用在手工艺品上,否则非遗产品就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人对有生命力的商品会绝不吝啬,前提是“物有所值”,如果是以机器替代手工、以新型材料替代天然原料、以统一样式替代个别设计,人们对这样的所谓“非遗产品”或是没有购买欲望、或是买后随手便仍,经济效益的甜头没有尝到,反而使非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大打折扣,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和损害,得不偿失。
(三)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良性开发中实现大理市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旅游业的发达、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增多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不应该是此消彼长、相互矛盾的关系,相反,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资金、契机和载体,应该成为后者的助推器。“大理好风光、世界共分享”,每年数千万的海内外游客来到大理,为非遗提供了庞大的受众和广阔的舞台,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对非遗进行良性的开发利用,最终实现其科学保护和有效传承。要对非遗进行良性的开发利用,就必须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移植到这一文化事业和制度体系中。首先,非遗是活态文化,其传承依赖于人,人力资源的持续供给很重要,要从政策层面增加非遗产品的“含金量”,吸引年轻人投身于非遗事业。笔者经过走访发现,无论是大本曲、绕三灵,还是白族剪纸、刺绣、扎染、彩绘,都存在传承人老龄化的严重问题。在大理市的农村,除了旅游业发展得比较好的如双廊、龙龛、才村以外,以老年人和留守儿童居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没有年轻人的参与,非遗的传承难以实现持续发展,最终将出现断层。这就需要在总体上加大对白族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力度,为非遗开拓生存空间,因为不同的白族非遗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例如,把白族传统民居保护好,白族民居彩绘才能有“用武之地”,也才能得以保存下来。如前所述,国家一味“输血”不如增强白族人民的“造血”功能,要将传统非遗产品和“山寨”非遗产品区分开来,严把质量关,加大宣传力度,使非遗产品真正成为文化产品中的奢侈品,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有了经济利益的驱动,才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自觉加入到传承队伍中来。其次,要处理好非遗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非遗是农耕社会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体现,但在人口急剧膨胀、人类物质需求日益增长的现代社会,非遗的开发利用必然会与环境保护的要求发生冲突。那么,既然在非遗领域需要引入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两者的指导原则一致,这一矛盾就迎刃而解了。一方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浪费自然资源为代价来换取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一些污染重、消耗大的非遗项目,必须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其实施,不能以“非遗传承”为借口来破坏生态平衡。例如大理石是苍山特有的奇石,传统白族家庭都使用木质雕花的大理石家具,为加强对苍山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开发利用,2002年大理州出台了《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苍山保护管理条例》,其中第15条规定:“保护范围内的彩花大理石实行定点限量开采。开采不得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该条文在2009年修订时未作修改。从2002年起,大理市开采量大幅度减少,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作为省级非遗项目的“大理石制作技艺”也就失去了其材料来源,大理石厂纷纷关闭,继续存在的大理石厂转向为主要生产小摆件,如笔筒、烟灰缸、花瓶、蒜臼等,商家经营思维的转换使非遗在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探索新的路径,为非遗传承营造必要的条件。例如作为省级非遗项目的洱海鱼鹰捕鱼技艺因洱海生态保护的原因已于2015年被取缔,但目前游客还可在洱源茈碧湖一带观看到该项传统技艺,虽然离开了其原生环境,但只要该非遗项目还能够传承,就可以说很好地破解了环境保护与非遗传承的矛盾这一难题。再次,开发利用非遗要谨慎行事、宁缺毋滥。非遗是几千年来老百姓行为方式的凝结和民族特性的反映,毁树容易栽树难,一旦非遗被不当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比不开发还严重,因为呈现给公众的是山寨、歪曲的非遗,会造成公众对非遗的误解、误读,“伪非遗”得以传承而“真非遗”最终消失了。
参考文献:
[1]刘德军.洱海区域鱼鹰驯养捕鱼活动的传承与保护.大理大学学报,2016,(12).
[2]杨丽娥.大理白族“三道茶”及其旅游开发研究.云南电大学报,2009,(3).
[3]吕华鲜,张娟.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变迁研究——以云南大理三月街为例.江苏商论,2010,(6).
[4]李刚.旅游开发对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以云南大理为例.对外经贸,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