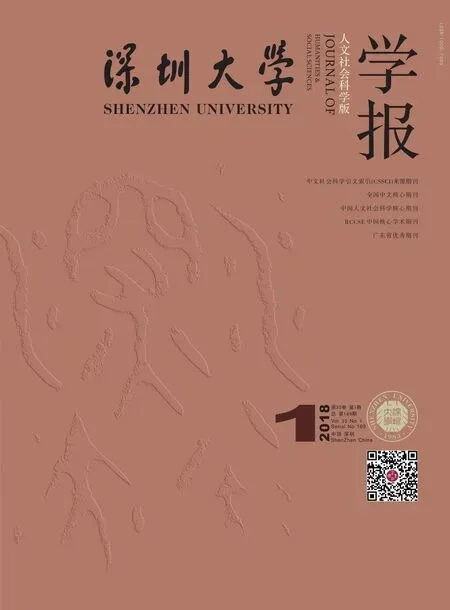东西方比较文学的未来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首先建立于19世纪的欧洲,大概一直到20世纪最后10年,它基本上是欧洲或欧美学术研究的专属领域。这并不是否认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学研究者们也积极参与了比较文学研究,更不是忽略东方和南美许多国家或地区,如印度、中国、韩国、日本和巴西等地比较文学学会的蓬勃发展和丰硕成果。这也不是忽视许多学者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这样的国际学术组织的真诚努力,他们都希望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促进真正全球范围内的比较。在此,笔者要向那些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就大力提倡和鼓励东西方比较的前辈学者们致敬,特别是我无缘识荆的法国学者艾田朴 (René Etiemble),还有笔者的故友至交佛克马(Douwe Fokkema)、迈纳(Earl Miner)、纪廉(Claudio Guillén)和欧阳桢等诸位先行者。因此,笔者说比较文学直到不久之前都一直是“欧洲或欧美”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并不仅仅是负面的意思,也并没有用“欧洲中心主义”这样的字眼来批评西方人的狭隘和偏见,或者抗议西方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笔者纯粹是在描述一个事实,那就是比较文学研究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几乎无一例外都只讨论欧洲或西方文学。例如,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库尔逑斯(Ernst Robert Curtius)、韦勒克(René Wellek)、列文 (Harry Levin)、 弗莱 (Northrop Frye)、 凯慕德(Frank Kermode)以及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等人的著作。达到那个层次、有那种声誉和影响的学术著作,几乎很少讨论欧洲传统之外的任何文学。比较文学在传统上一贯强调驾驭语言的能力,一定要从原文去研究文学作品,所以大多数西方学者都集中探讨欧洲语言背景下的文学作品,也就不足为奇。这恰好说明,他们做学问相当自律、十分严谨。
不过,在世界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确存在着经济力量、政治影响和文化资本不平衡的现象,也的确有西方优越感之嫌。这种优越感也许不自觉地反映在所谓世界系统理论当中,这种理论认定西方为中心,非西方为边缘。一些文学研究者,尤其是莫瑞蒂(Franco Moretti)和卡桑诺瓦(Pascale Casanova),就采用这一范式来讨论世界文学。卡桑诺瓦讨论她所谓“文学的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颇受学界赞赏,但她所理解的世界文学空间之形成,却显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在她看来,世界文学史开始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但很快就在法国建立起中心。随着欧洲列强在19世纪向外扩张,后来非洲和亚洲又在20世纪去殖民化,文学观念也逐渐散布到世界其他地区。卡桑诺瓦说:“随着去殖民化进程,非洲、印度次大陆和亚洲诸国才终于要求获得文学合法存在的权利。”[1](P11)换言之,20 世纪之前,在“非洲、印度次大陆和亚洲”,根本就没有可以在世界上称之为文学的东西。这里表现出的观点过度倾向于现代和西方,无视亚洲和非洲等非西方文学传统,甚而也忽略了欧洲的古典文学和文化传统。卡桑诺瓦特别强调巴黎是“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之首府,且宣称她以巴黎为文学空间的中心,乃是基于历史事实。她说:“宣称巴黎为文学之首府,并非高卢中心主义的影响,而是细致的历史分析的结果,这种历史分析显示出,文学资源在几个世纪里不同寻常地集中在巴黎,便逐渐使它得到普遍承认为文学世界的中心。 ”[1](P46-47)然而,世界历史绝非始自欧洲文艺复兴,有多个政治和文化中心的整个世界,也远远大于巴黎或法国的版图。欧洲之外还有其他文学和文化资源中心,例如波斯和奥斯曼帝国,还有早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就在东亚担当中心的汉、唐帝国,卡桑诺瓦对此不可能毫不知情。为什么她那“细致的历史分析”对这些都视而不见,像盲眼人一样,对欧洲之外广阔的文学世界全然无知呢?这未免太令人失望了,却也证明欧洲中心主义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仍然需要不断批评这种“井底之蛙”式的偏见和谬误。
其实,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大部分时候比较文学不仅仅是欧洲或欧美的天下,而且在有些情形下还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恐怕现在仍然如此。然而,作为一个比较学者和亚洲学者,笔者并不只是谴责欧洲中心主义,而是要谴责一切民族中心主义。还应该补充一句,即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思想狭隘的人都会以为自己的文化传统独特且优越,自我中心主义几乎是与生俱来、无处不在,不仅西方有,东方也有。但人类之优越,恰恰在于我们都有能力了解我们自己所居一隅之外的广阔世界,超越自己的局限、狭隘和孤陋寡闻;我们都可以知己知人、取长补短,消除自己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这正是我们可以从印度杰出作家和伟大诗人泰戈尔那里学到的弥足珍贵的价值观。在发表于1907年有关世界文学的一篇文章里,泰戈尔一开头的话就掷地有声:“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能力,其存在之唯一目的都在于与别的人建立联系。只有通过这种联系,我们才成为真实的自我,也才能达到真理。否则,说‘我是’或‘什么东西存在’,都毫无意义。”[2](P48)在泰戈尔看来,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其本性就注定了要与别的人形成联系。他用极具诗意的语言描述人的灵魂如何寻求他人,以实现自我的愉悦和圆满,而利己之心和虚荣心却勾结起来,阻碍“人的灵魂之自然追寻,使其不能畅通无阻地观照人性之完美。”[2](P49)人生在世,不能不做平淡乏味的日常工作来满足基本需求,只有文学能纯粹而酣畅淋漓地表现 “人性之完美”,因为“人生中高尚而永恒的一切,超越人之基本需求和劳作的一切,都自然呈现于文学,自动塑造出人类更伟大的形象。”[2](P54)对泰戈尔说来,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提供了理想的途径,可以把我们从乡野狭隘的观念中解救出来,与他人形成联系,于是他呼唤我们超越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他说:“现在已经是时候宣称我们的目的是要摆脱乡野的偏狭,在普世的文学中关照普遍的人类。我们在每一位作者的作品里,都要认识那总体,而在这总体当中,虽然所有的人都努力表达自己,我们却可以感觉到这种努力相互之间的关系。”[2](P57)泰戈尔是一位胸怀远大的人文主义者,他敦促我们“在普世的文学中关照普遍的人类”,把东西方放在一起,使全人类建立起互相的联系。
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世界所需要的,在当前尤其如此,因为目前在地球上不少地方都有太多的暴力和不确定性,都有人对于人的凶残,都有紧张的政治局势、窘迫的经济状况、暴力的军事冲突。很多这类问题都源于不同民族及其文化之间缺乏理解和共鸣。这也可以说明,在当代哲学和文学研究中,何以会如此关注伦理的问题。哲学家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说,“绝不能因为忠于自己的社群,就忘记了作为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对所有别的人负有责任”,他认为这一原则就是世界主义的核心观念[3](Pxvi)。阅读不同文学和文化传统的作品,最能够接触到与我们自己不同的东西,形成与他人的联系,培育我们对于其他人的道德责任感。阿皮亚提到彼得·辛格尔(Peter Singer)“著名的比喻”,以一种假想的情形来说明人的道德原则:
如果我正走过一个水并不是很深的池塘,看见有个小孩子溺水了,我就应该涉水过去,把那个小孩拖出水来,”辛格写道。“这就意味着会把我的衣服弄脏,但这可以说是微不足道,而我们可以肯定,一个孩子的死却是很坏的事情。[4]
辛格尔假定任何一个人遇到这样一种紧急情形,都会救那个落水的小孩子,但阿皮亚却对“辛格尔原则”心存怀疑,因为“我们确信我们会去救那个落水的孩子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应该这么做。”[3](P161)说来也真算得上是一种奇特的机缘巧合。辛格尔所提出的类比,几乎重复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性本善之说,而且孟子好像早已预料到阿皮亚那个为什么的发问。孟子坚信人性本善,人都有恻隐之心,而且他也是用救一个将要落水的孩子的类比,来论证人性本善。《孟子·公孙丑上》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比辛格尔早两千多年,他们的文本在地理和文化上都遥遥相隔,但都用将要落水的孺子这一意象,来论证人之自然本能和道德行为,两者之间的确有令人惊讶之相似。东西方文本虽然大不相同,却又有相通之处。这样出人意料的类似,就构成了东西方比较研究的内容。这样的文本证据,使我们认识到,尽管有文化、历史、政治和其他诸多方面的差异,人类还是有更多共同点,有更多可以共享之处。就像希腊人的“phusis”概念一样,孟子所谓人性与生俱来,是内在的。当他论证人性本善时,他把人性与自然中必然发生的事情相比,与水之流动相比。《告子上》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之所以要救落水的孩子,是由人内在必有恻隐之心所决定的,发乎自然,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是一种自动而无意识发生的行动,而不是盘算进退得失之后一个有意识的决定。
孟子认为人有四种根本的道德,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就是所谓“四端”,就像人的四肢或身体肌肤一样,生而俱有。这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论证人性皆善时,孟子不用抽象的预设概念,却大量依赖身体比拟和比喻,以具体的感觉为说。《告子上》又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芻豢之悦我口。”具体和抽象通过比拟联系起来。孟子正是用味觉、听觉、视觉来引出抽象的“理义”概念。通过把两种不同现象或情形联系起来,孟子的论述可以说代表了一种联想式或比喻式的哲学论证方式。也许有些更熟悉西方哲学话语的人会认为,孟子这种论证方式并不像真正的哲学叙述。然而,恰恰在西方,特别强调具体和经验式证明的认知科学,也对形而上预设的抽象概念提出了挑战。两位美国学者乔治·拉科夫 (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非常肯定地宣布说:“心智总是具体的。思想大多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大部分都是比喻。”他们很明确地说:“这就是认知科学三个主要的发现。过往两千多年来对理性这些方面预设的哲学思辨已经完结了。”他们指出,用身体比喻的论证来讲哲学道理,对西方思想来说是一种挑战,“一种从经验上说来负责任的哲学,就要求我们的文化必须放弃某些根深蒂固的哲学预设观念。”[5]也许我们不必把话说得这么绝对,但什么算是哲学,哲学论述可以有怎样不同的方式,我们的确需要有更开放的头脑和观念。换言之,我们对共同的人性需要更多同情和理解,同时也要欣赏人类的差异和多元。
然而,在当代西方大部分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几乎避而不谈共同的人性这个概念,甚至弃之如敝履。强调差异,则远远多于注重相同。对所有的比较学者而言,比较的基础是什么,从来就是一个避不开的问题。对于东西方比较文学而言,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迫切。当我们越过东西方的隔阂,把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文本、概念和表现方式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时,就有更多的人表示怀疑。的确,比较研究的目的真是如泰戈尔所说,是“在普世的文学中关照普遍的人类”吗?孟子所谓孺子将入于井的类比,与辛格尔的现代伦理学观点,真有可比性吗?任何从事东西方比较研究的人,都不能不面对这样的问题,而且最好先问一问自己,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大部分西方学者和普通学生对东方文学和文化所知寥寥,按理说对这类问题,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奇怪的是,很多人都会即刻给出否定的回答,只因为他们相信,就像英国19世纪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言,“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二者永不会相遇”(Oh,East is East,and West is West,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在西方当代学术中,尊重文化差异常被认为在道德上是值得嘉许的立场,但只讲差异,否认人类的共性,却完全有可能导致多元文化包容开放的反面,强调差异也完全有可能服务于种族隔绝和种族歧视的目的。
我们只要回顾稍早一点的时代,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吉卜林学会第一届会长是曾在印度当过殖民官的英国陆军少将莱昂利·查理·邓斯威尔(Lionel Charles Dunsterville)。1933 年,他在伦敦曾告诉那些崇拜吉卜林的会员们,说吉卜林“是我们姑且称之为帝国主义的毫不动摇的代言人。”[6](P372)邓斯威尔认为,作为帝国主义的大诗人,吉卜林讲出了东西方之间根本的差异。“东方人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丝一毫的传统都是——而且也应该是——与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和传统恰恰相反的。”正由于这样恰恰相反的对立,邓斯威尔坚决反对把宪法概念引入印度,因为他认为宪法是纯粹英国或者西方的概念,与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东方人也完全不可能理解。邓斯威尔抱着怀疑态度说:“我很怀疑‘constitution’(宪法)这个词怎么翻译成乌尔都语。”[6](P373)也许从政治上来说,我们如今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和邓斯威尔的世界已经大相径庭,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发现,他的思想在当代西方世界里仍然有很多信众,包括他强调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坚持认为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不可译性等等。当代西方很有影响的理论概念,例如库恩 (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所谓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incommensurability), 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谓中国乃是一“异托邦”(heterotopia),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谓“差异”(différance)等等,由此可见,东西方对立的观念在讨论跨文化问题时,仍然很有活力、影响极大。法国学者于连(Francois Jullien)于2000年出版了一本书,标题就点明贯穿他很多著作的主题:《从外部(中国)来思考》。在书中,于连说中国“基本上是有大量文献记载可以证明,其语言和历史传承都绝对是非西方的唯一一种文明,”所以他宣布,“严格地说,非西方就是中国,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7]于连认为,把中国当作欧洲的反面形象,西方人就可以更好地认识西方本身。因此,于连的书里经常罗列互相对立的概念和范畴:一个希腊,一个中国,两者恰恰相反,总是把于连的中国变成希腊的反面,于是无论他讨论什么问题,最后都会证明两者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美国学者理查·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于2003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的主旨一目了然:《思想的地理学:亚洲人和西方人如何不同地思考……以及为什么》。他在书中说,“人的认知并不是到处都一样……不同文化的成员在其‘形而上学’方面也不尽相同,即他们关于世界本质的根本信念很不相同……不同群体各具特色的思考过程也大不相同。”他所说的这些根本差异说到底,不过是一个老的刻板对立的印象,即“亚洲社会的性质是讲究集体,互相依靠”,而“西方社会则讲究个体,互相独立。 ”[8](Pxvi-xvii)
为了检测尼斯贝特的论述有没有道理,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定义古代希腊人的。他宣称,“希腊人比古代任何其他民族,事实上比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更有一种个人能力的明确意识——即他们能控制自己的生命,可以自由行动的意识。希腊人关于幸福的定义之一,就是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在不受制约的生命中去追求卓越。”[8](P2-3)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些证据,支持希腊人对于生命和幸福如此信心满满的健全看法,但如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算得上希腊悲剧中的经典例子,那其间的讯息却恰巧是一种缺乏个体能力的明确意识,或个体能力完全失败的意识,因为俄狄浦斯每每采取貌似由自身自由意志所决定的行动,都恰好把自己向那命中注定的悲剧更推进一步,他极力想要逃脱命定的悲剧结局,却始终无能为力。正如查理·西格尔(Charles Segal)评论说,“俄狄浦斯面对一种人的头脑所无法理解的神秘,生活在一个无秩序、无公理途径可循的世界里。”他的世界是一个悲惨而荒诞的世界,在那里“众神好像残忍而不公正,生活就是地狱。 ”[9](P74)在悲剧结尾处,合唱队的歌总结希腊人的命运意识,表达了一种幸福的观念,而这与尼斯贝特描述所谓希腊人个体能力的意识,“即他们能控制自己的生命,可以自由行动的意识”真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只要还没有到那最后的一天,当他可以说他的生命已到了尽头,再没有悲伤和痛苦,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活得幸福。[10]
俄狄浦斯当然不是一个普通人,因为他有非同寻常的智力,可以解答声名狼藉的斯芬克斯之谜,也拥有非比寻常的政治权威,可以君临底比斯,是一位仁慈而有担当的国王。如果我们从真实或虚构的古希腊人当中,去寻找具有“个体能力明确意识”的人,俄狄浦斯应该算是一位。然而,极具悲剧意味的是,他那非比寻常的个体能力带给他的不是尼斯贝特所描述的幸福,却恰恰是他的痛苦和失败。这里有一种受到远比人的能力强大得多的力量摆布和玩弄的悲剧意识,而那至少是古希腊人人生观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表现了古希腊人与诸神之关系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另一出伟大悲剧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即莎士比亚 《李尔王》里令人难忘的一句台词:“我们之于诸神就像苍蝇之于顽童,他们为了好玩而把我们随意杀戮。”[11]无论我们把俄狄浦斯理解为超能还是无能,我们都不能说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他的悲剧命运有力地驳斥了尼斯贝特所谓幸福的希腊人的笼统概括。《俄狄浦斯王》当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如果不能承认这出剧 “有一种神秘的命运注定之感,有众神意志”的悲剧意识,那样的解释就不可能有任何说服力[9](P75)。尼斯贝特过分简单化地概括整个古希腊民族,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如果尼斯贝特关于古希腊人十分笼统的概括没有说服力,我们难道还能相信他关于所有亚洲人和所有西方人笼统千百倍的概括吗?这不就是我们在更早一个时代早已见识过,那种东西方思维模式互相对立的陈旧观念吗?这样简单绝对的东西对立,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吗?
在文学研究中,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这个概念得到广泛讨论,也相当流行。艾米莉·阿普特尔(Emily Apter)《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性之政治意义》一书,就是以哲学和神秘主义之不可言说为模式申述这个概念的一本近著。她在书中提到“维特根斯坦所谓无意义的话,加上《逻辑哲学论》里一套 ‘das Unsagbare’(不可言说)和 ‘das Unaussprechliche’(不可表述)的词语……其中神秘主义和玄学的无意义话语占据了统治地位。”[12](P10)她还提到“关于禁止神圣经文俗语化的立法或历史上颁布过的禁令。”[12](P12)于是乎,阿普特尔所谓不可译者,首先是一个哲学上不可解决的难题,一个概念上的困境,然后又是一个宗教上的观念,是神圣之静默,神秘宗对一切语言和交往之否定,是不可言说、不可表述的逻各斯或上帝。但笔者在拙著《道与逻各斯》里曾经说过,“神秘宗的静默,无论是宗教的还是语言方面的,其实都会产生一种压抑不住的必须言说的强烈欲望,”于是一切神秘主义者都会落入一种 “反讽模式”(ironic pattern),因为他们虽然否定语言及言说有用,但他们的话却不是说得更少,而恰恰是说得更多,同时又宣称他们保持不可言说之神圣的静默[13]。“甚至最内在的经验也不可能逃脱想要表述的冲动,”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也这样描述神秘主义者的矛盾,“因为道在他心中燃烧。”[14]这种在心中燃烧的欲望,在文学中就找到了最有力的表现,所以爱略特 (T.S.Eliot) 说, 诗乃是 “a raid on the inarticulate”(对不可言说的袭击)[15]。沉默却恰好可以变成刺激诗的灵感,正如德国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用美妙的语言表述的那样:“Schweigen.Wer inniger schwieg,/rüht an die Wurzeln der Rede”(沉默。谁保持内在的沉默,/便触到了语言之根)[16]。但所有这些都并非不可译,因为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对语言的否定本身,也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而否定语言的“神圣的静默”,也常常在许多神秘主义者的著作中,激发出各式各样修辞手法辉煌地展示,使神秘宗的文章反而极具文学性和诗意。中国道家的《庄子》、古印度的《奥义书》(Upanishads)、欧洲神秘宗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著作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这些著作语言优美,比喻层出不穷,用激发人的讽寓和反语来讲述深刻的道理,不仅有哲人的洞见,也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这类著作当然都很难翻译,但也绝不是不可译,也就是说,并非不能够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为原来那种语言文化环境之外的读者理解和欣赏。
30多年前,克劳迪奥·纪廉曾说做东西方比较研究的人“大概是比较文学领域里最大胆的学者,从理论的观点看来,尤其如此。”[17](P16)他这句话说得当然很对,他们的确是最大胆的学者,因为东西方比较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区域,傻瓜才会急匆匆地跑进去,不仅受到专攻东方文学或专攻西方文学这两方面行家的挑战,而且也被不愿意脱离欧洲或欧美文学圈的西方比较学者们质疑。这些学者们通晓几种欧洲语言,觉得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准备从事比较工作,于是心安理得地固守安全地带,而对他们自己不熟悉、不懂得的跨东西方语言文化差异的比较,就总是怀疑、轻视,甚至排斥。纪廉说,在欧洲比较文学发展较早的阶段,东西方比较研究是不可能存在的。就在他写书的1980年代中期,“不少学者对偏离学科规范又越过民族文学范畴的研究,都抱着冷淡甚至厌恶的态度。”[17](P85)如果说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要求不是懂一种,而起码要懂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学传统,那么东西方比较则要求懂范围广得多、很不相同的语言和文学传统。这是一个十分广阔的“领域”,我每次走进这个领域都深深感到,自己不懂的东西,远远比自己懂的要多得多。《庄子·养生主》开宗明义:“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句话确实有道理,可以提醒我们,要随时以谦卑恭敬的态度去做学问,知道自己的无知。但早在1970年代,法国学者艾田朴就已经呼吁西方比较学者们要打破欧洲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去学习“梵文、中文、泰米尔文、日文、孟加拉文、伊朗文、阿拉伯文或马拉蒂文文学,”虽然这近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艾田朴却极力呼唤西方学者们去做那“不可能的事情”(A l’impossible,it est vrai,chacun de nous,je l’espère,se sent tenu)[18]。纪廉赞成艾田朴的意见,鼓励东西方比较研究,认为那代表了“比较文学最具前景的趋势。”[17](P87)现在应该是我们作出回应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回应纪廉,把东西方比较提升到学术研究一个更高的层次,回应艾田朴,去做那“不可能的事情”,也回应泰戈尔,建立全人类的联系,“在普世的文学中关照普遍的人类”。
归根结底,我们一方面要有自己文化的稳固根基,又必须摆脱自身民族中心主义的局限。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拥抱全人类的世界主义情怀,这两者并不冲突,在亚洲的环境里尤其如此。我的老朋友屈维蒂(Harish Trivedi)说得很对,“如果说西方关于民族的概念和实践与世界其他地方都显然不同,那大概是因为民族主义在西方兴起,导致了西方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而正是这种殖民使得民族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兴起。”[19]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民族身份认同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重要的身份,不能死死抓住不放。这里引用笔者十分尊重的一位印度学者充满智慧的论述,这位学者的家庭和泰戈尔以及这所大学都有深厚的渊源,那就是阿玛缇亚·孙。他认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场合都有不同的身份,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健全的身份认同是多元的,一种身份的重要性无须抹杀其他身份的重要性。”[20](P19)民族身份认同、宗教或文化身份认同都绝不能阻碍我们与所有其他人建立联系。他又说:“暴力的产生,都是把单一而具挑衅性的身份认同强加到容易上当受骗的民众身上煽动起来的,都是精于此道的战争吹鼓手们造成的。”[20](P2)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地球村”里。在西方学者和学生们当中,现在对非西方世界及其文学和文化,也有更大的兴趣和更多的了解,所以对东西方比较研究来说,我们有了比以往宽松得多的环境。但与此同时,今日世界也充满了冲突和局部战争、人道主义危机、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和移民、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痛苦和灾难。这些痛苦和灾难大多是由于我们的世界缺乏宽容和理解,尤其是不同文化、历史和传统之间的相互理解。所以说,东西方比较研究不仅仅是学院里的一种知识追求,而且对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和我们如何生活,都具有实际意义。笔者有一个强烈的信念,那就是当我们的世界更注重超越东西方根本差异的跨文化理解的价值时,我们就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不仅在理解方面更好的世界,而且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更美好的世界。
[1]Pascale Casanova.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M].Trans.M.B.DeBevois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2]Rabindranath Tagore.World Literature(1907)[A].Trans.Swapan Chakravorty.Ed.David Damrosch.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C].Oxford:Wiley Blackwell,2014.
[3]Kwame Anthony Appiah.Cosmopolitanism: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M].New York:W.W.Norton,2006.
[4]Peter Singer.Famine,Affluence,and Morality[J].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3(1),1972.231.
[5]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3.
[6]Lionel Charles Dunsterville.“Stalky” on “Kipling’s India”(1933)[A].Ed.Roger Lancelyn Green.Rudyard Kipling:The Critical Heritage[C].London:Routledge,1997.
[7]Francois Jullien with Thierry Marchaisse.Penser d’un Dehors (la Chine):Entretiens d’Extrême-Occident[M].Paris:éditions du Seuil,2000.39.
[8]Richard Nisbe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and Why[M].New York:The Free Press,2003.
[9]Charles Segal.The Greatness of Oedipus the King[A].Ed.Harold Bloom.Sophocles’Oedipus Plays:Oedipus the King,Oedipus at Colonus,&Antigone[C].Broomall,Penn.: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99.
[10]Sophocles.The Theban Plays:Oedipus the King,Oedipus at Colonus,Antigone[M].Trans.Ruth Fainlight and Robert J.Littma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9.63.
[11]William Shakespeare.King Lear[M].Ed.Burton Ruffe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131.
[12]Emily Apter.Against World Literature: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M].London:Verso,2013.
[13]Zhang Longxi.The Tao and the Logos:Literary Hermeneutics,East and West[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2.47.
[14]Martin Buber.Ecstatic Confessions[M].Trans.Esther Cameron.New York:Harper&Row,1985.7,9.
[15]T.S.Eliot.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1909-1950[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sh,1980.128.
[16]Rainer Maria Rilke.Für Frau Fanette Clavel[A].Ed.Ernst Zinn.S?mtliche Werke,12 vols[C].Frankfurt am Main:Rilke Archive,1976,vol.2,58.
[17]Claudio Guillén.The C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M].Trans.Cola Franze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8]René Etiemble.Faut-il réviser la notion de Weltliteratur?[A].Essai de littérature (vraiment)générale[C].Paris:Gallimard,1975.19,34.
[19]Harish Trivedi.The Nation and the World:An Introduction [A].Eds.Harish Trivedi,Meenakshi Mukherjee,C.Vijayasree,and T.Vijay Kumar.The Nation across the World:Postcolonial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C].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xiii.
[20]Amatya Sen.Identity and Violence:The Illusion of Destiny[M].New York:W.W.Norton,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