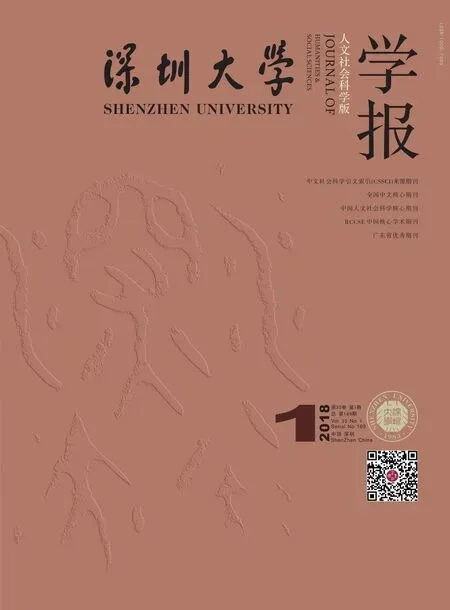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
本期栏目主持人:张晓红教授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主持人语:20世纪90年代以降,全球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格局发生了深刻的裂变。“铁幕”时代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1991年前苏联解体而终结,苏美两大阵营的政治冷战和军备竞赛退出了历史舞台,意识形态壁垒貌似完结,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同质化的语境日益豁显。然而,在国际和平的表象下,恐怖主义尘嚣日上,阿富汗、伊拉克、埃及、也门、叙利亚烽火不息,极端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毒瘤迅速扩散。2016年,英国上演了一场分裂主义的“脱欧”大戏,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竞选当中特朗普高喊反建制主义、反精英主义、反全球化等口号“出奇制胜”。鉴于此,如何改善冲突和促进对话依然是一个迫切而棘手的全球性问题。
如何理解和解释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交流问题,已然成为当今人文学者的当务之急。从汤因比的文明论、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之说,到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之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努斯鲍姆关于“培育人性”的呼吁,种种学说相得益彰而又互竞互颉。努斯鲍姆的观点发人深思。她认为,文学文本具有增进不同生活方式之间情感共鸣的可能,叙事性想象为“道德互动”(moral interaction)提供了绝对必要的准备,使我们成为富有同情心的倾听者、观察者、感受者和交流者,也使平等、自由、多样的跨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早在1907年,亚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就饱含深情地呼吁全人类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尤其是通过文学交流“在普世的文学寻找普遍的人性”。这种诗意的人文主义呼告,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现实意义。
本期分别选取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张隆溪和印度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屈维蒂 (Harish Trivedi)的最新研究成果,两篇文章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性和可通约性,并有着琴瑟和鸣的美感。两位重量级学者从东方学者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和批评欧洲中心主义框架下的种种理论话语。张文质疑“不可通约性”“不可译性”等概念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倡导一种超越文化、种族、宗教差异的东西比较研究,实现一种更加包容、多样、丰富的跨文化理解。面对国际比较文学的危机、挑战和机遇,张文用乐观自信的东方智慧回应了欧美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之死”“理论之殇”等悲观的危机论。张文赋予钱锺书先生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以新的内涵和意蕴。屈文印证了贝尼迪克特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核心观点,认为东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希腊、梵文化圈和汉文化圈这三个曾经繁荣昌盛的语言共同体,它们都承载着世界主义、世界公民、大都会等概念的特定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内涵。继而,屈文以几位当红印地语作家的创作为中心,考察了欧洲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可疑的、偏执的文学表现,一语中的地指出,世界主义是一个复数概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多义性和混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