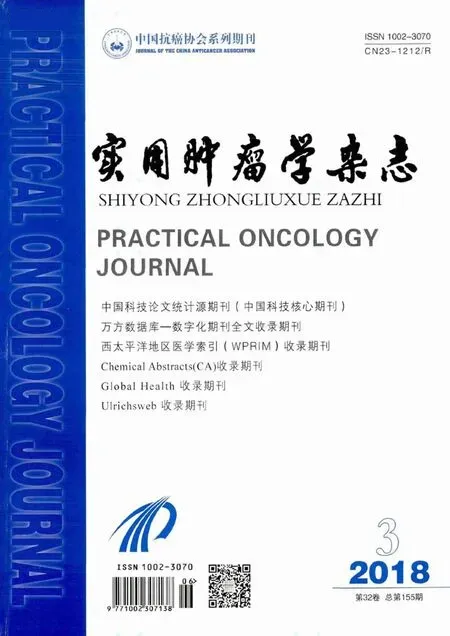麻醉药物对围术期癌症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马 超 综述 王国年 审校
大量研究表明,癌症可对机体的免疫功能产生抑制作用,使癌症患者的免疫系统发生异常变化,进一步导致癌症的恶化,严重影响癌症的治疗。手术作为治疗癌症的重要手段在临床中应用广泛,但手术引起的过度应激反应同样会引起免疫抑制,加速癌症的恶化,增加短期死亡率。同时,围术期内的低血压和低体温也会对癌症患者的免疫功能产生抑制作用。围术期内麻醉药物的应用可使由手术创伤和疼痛引起的过度应激反应受到抑制,但同时又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癌症患者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依据不同麻醉药物对围术期癌症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制定个体化的精准麻醉方案和癌痛镇痛方案,有助于提高癌症患者的围术期生存率,本文将回顾不同麻醉药物与围术期癌症患者免疫功能之间的关系,以便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1 围术期癌症患者免疫功能的变化
围术期内由手术创伤和疼痛引起的神经内分泌反应可抑制癌症患者的免疫功能,不仅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产生激活效应,还可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引起血浆中儿茶酚胺水平的升高和皮质醇激素的释放,并活化单核-巨噬细胞,激活特异性免疫中的淋巴细胞,产生IL-1、IL-6、TNF-α等促炎细胞因子。低血压是手术常见并发症之一,不仅会激活HPA轴和交感神经系统,还可降低组织灌注,导致细胞缺氧,诱导黏附分子表达增加,激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抑制Th1细胞,诱导Treg细胞增生[1]。低体温可活化神经内分泌系统,并抑制NK细胞活性和单核细胞的抗原呈递功能,促进促炎细胞因子生成[2]。
2 不同麻醉药物对围术期癌症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大量的临床研究发现,不同的麻醉药物主要作用于机体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并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围术期癌症患者的免疫功能,但也有研究显示,麻醉药物可直接作用于免疫系统和免疫活性细胞从而影响机体的免疫功能。由于目前的研究尚不能完全明确不同的麻醉药物对免疫细胞会产生怎样的生物学效应,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和总结不同麻醉药物与围术期癌症患者免疫功能之间的关系。
2.1 吸入麻醉药
吸入麻醉药可引起外周循环血中NK细胞减少,促进人体免疫细胞释放低氧诱导因子-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HIF-1),抑制IFN-α诱导的自然杀伤细胞(NK)毒性反应,促进高表达HIF-1因子的Th1向Th2漂移[3],并直接作用于神经内分泌系统,引起血浆中皮质醇激素水平升高,对NK细胞的活性产生抑制效应[4]。吸入麻醉药对线粒体膜电位有抑制作用,可促进细胞色素C的过度释放[5],并加快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在人体免疫细胞线粒体中的生成速度[6],导致T淋巴细胞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受到抑制[7]。七氟烷和异氟烷可抑制树突状细胞(DC)的抗原递呈作用,导致骨髓来源的抑制性细胞(MDSCs)在机体内不断增加,抑制中性粒细胞活性氧的非特异性免疫效应。同时,有研究显示,围术期内使用低流量的七氟烷、地氟烷可减轻其对中性粒细胞和部分特异性免疫中T淋巴细胞的抑制效应[3]。但是,是否可以通过改变气体流量来减弱吸入麻醉药对人体免疫功能的抑制,尚需进一步的临床观察及前瞻性研究予以证实。
2.2 阿片类药物
阿片类药物通过与μ-阿片受体(μ-opioid receptor,MOR)结合来激活HPA轴和交感神经系统,间接地对机体产生免疫抑制作用。HPA轴激活以后,可升高血浆糖皮质激素的水平[4],而交感神经系统活化可升高血浆中儿茶酚胺的水平[8],在临床研究中,这些神经内分泌反应均可导致围术期癌症患者的免疫抑制。阿片类药物直接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的具体机制尚有待研究,有实验表明,吗啡可特异性地结合T淋巴细胞表面的MOR受体而使细胞内cAMP的含量不断增加,激活与cAMP相关的PKA传导途径,抑制T淋巴细胞的活化,引起Th1/Th2漂移。吗啡可对NK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反应产生抑制作用,使中性粒细胞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引起单核-巨噬细胞程序性死亡[9]。小剂量的芬太尼可导致NK细胞的数量短暂提升,但对其活性的抑制程度却随着剂量的增加而增强。舒芬太尼作为一种强效阿片类药物,可显著地抑制NK细胞的免疫功能,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其可使机体的细胞免疫效应得到加强[10]。曲马多是一类弱阿片类受体激动剂,虽然也可激活阿片类受体,但不会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还能加强围术期免疫细胞的抗肿瘤免疫反应[11]。
2.3 静脉麻醉药
在保护机体免疫功能方面,丙泊酚要优于吸入麻醉药,丙泊酚虽然会对中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的免疫功能产生抑制作用,但不会影响NK细胞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丙泊酚通过降低中性粒细胞胞浆内钙离子水平,使中性粒细胞活性受到抑制,减少ROS的生成。丙泊酚可引起线粒体膜电位的下降,减少ATP生成,对巨噬细胞的趋化和吞噬功能产生抑制效应[12]。大量研究表明,丙泊酚既不会影响NK细胞的活性,对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也无抑制作用。丙泊酚可抑制肿瘤细胞介导的Th1/Th2漂移,维持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并具有增强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活性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和转移的特性,还具有通过调控DC细胞的异化水平而上调NK细胞活性的能力[13]。研究证实,丙泊酚可诱导Th细胞的活化,对于抗肿瘤免疫反应的维持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14]。
除丙泊酚对人体的免疫功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外,依托咪酯、硫喷妥钠及氯胺酮等大部分静脉麻醉药对人体的免疫功能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15]。体外实验发现,氯胺酮通过激活α和β肾上腺素受体来减弱单核-巨噬细胞的趋化作用,使中性粒细胞表面黏附分子在非特异性免疫效应中的表达受到抑制,并诱导淋巴细胞的凋亡[16]。苯二氮卓类药物通过与脑内中枢神经系统的苯二氮卓受体结合,增加神经内分泌系统中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的释放,对机体发挥镇静功能,其中主要用于麻醉前镇静的咪达唑仑可通过抑制STAT3的活化而对IL-6的释放产生抑制效应,减弱中性粒细胞的黏附及趋化作用。另外,咪达唑仑可损害树突状细胞诱导的Th1型免疫反应,干扰正常的抗肿瘤免疫反应[17]。
2.4 局部麻醉药
局部麻醉药主要应用于椎管内麻醉和局部麻醉,通过对外周神经传入纤维的阻断,使中枢神经系统无法接收到来自外周神经的伤害性信号,从而阻止神经内分泌应激反应的发生,保护患者的免疫系统功能[18]。当椎管内麻醉和局部麻醉与阿片类药物联合应用时,可减少其在围术期内的使用量,降低其对免疫系统的抑制[19]。但在离体细胞研究中,对于多种免疫活性细胞,局麻药仍具有很强的免疫抑制作用,利多卡因的临床浓度可抑制离体免疫细胞分泌免疫细胞因子的能力,并使NK细胞的活性受到明显地抑制[20]。动物实验发现利多卡因在体内或体外均可降低这些炎性细胞因子的上调,减弱中性粒细胞的黏附作用[21]。围术期静脉应用利多卡因可降低患者IL-6、IL-8和IL-1ra水平,抑制淋巴细胞的增殖能力[22]。
2.5 非甾体类镇痛药
非甾体类镇痛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可抑制环氧化酶活性,使炎性介质PGs的生成受到抑制,围术期应用可起到镇痛的作用。NSAIDs作为一类不含甾体结构的镇痛药,与阿片类药物联合应用时,可减少其在围术期内的使用[23]。NSAIDs对缓激肽的释放有抑制作用,可维持淋巴细胞的抗肿瘤免疫反应,抑制肿瘤生长,围术期应用可使肿瘤微转移发生的风险下降,因而临床上常用于癌症患者的镇痛治疗[24]。PGs不仅能对T淋巴细胞和DC细胞的活性产生抑制作用,还可通过对抑制性免疫细胞因子IL-4、IL-6和IL-10等活性的调升而直接影响免疫细胞的抗肿瘤免疫反应,NSAIDs可通过抑制COX受体而阻止PGs生成,保护围术期癌症患者的细胞免疫能力[25]。
2.6 其他
作为一种高选择性的α2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右美托咪定可与脑干中的肾上腺素能受体相结合,静脉输注引起患者正常的自然非动眼睡眠,并具有对交感神经活性的抑制作用,可抑制应激反应,维持血流动力学的稳定,围术期内发挥镇静、镇痛作用[26]。右美托咪定持续输注可降低全麻下胃癌根治术患者的炎症反应,改善免疫抑制,中高剂量改善效果更为显著[27]。右美托咪定与阿片类药物复合使用可产生一种非剂量依赖性的协同增强作用,降低其在围术期内的使用。但也有研究显示,右美托咪定可降低Th1/Th2比例,抑制CTL活性,抑制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反应[28]。
3 小结与展望
我们可以明确吸入麻醉药和阿片类药物的使用是围术期癌症患者免疫功能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减少和控制吸入麻醉药和阿片类药物的使用是避免围术期癌症患者免疫功能受到抑制的关键。丙泊酚可有效减少吸入麻醉药的使用,对机体的免疫功能影响轻微,还可降低术后肿瘤复发的可能,多种药物联合(如右美托咪定和非甾体镇痛药在围术期内的使用)可有效减少阿片类药物的使用。大量临床研究还表明多种麻醉方式复合(如大量应用椎管内麻醉和局部麻醉)同样可降低阿片类药物的使用,而局麻药除了在椎管内麻醉和局部麻醉的应用外,其对减少围术期癌症患者免疫功能抑制的其它应用方式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索。因此,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索不同麻醉药物通过更复杂、更长期的途径来提高癌症患者免疫功能、拮抗肿瘤对免疫系统的抑制以及加强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的可能,如丙泊酚的长期使用、不同麻醉药物对癌症患者的长期治疗等,这都需要更多的跟踪随访和大量随机、双盲、对照性的实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