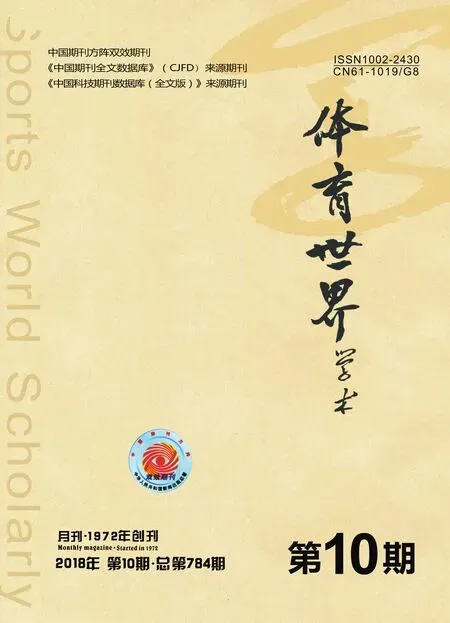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村落武术研究
——以一个地域村落为例
宋相川
1. 前言
1955年,美国人类学学者斯图尔德在其著作《文化变迁的理论》中提出了其主张的文化——生态适应的理论,即文化生态学[1]。文化生态学在解释文化变迁时,将一定的文化特征置于各种交互作用的环境因素中加以解释,认为文化的变迁是各种环境因素交互的结果[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武术的发展变化和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自然密切相关,由于不同地区文化生态环境的不同,传统武术在农村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文化生态系统即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内一切交互作用的文化体及其环境组成的功能整体[6]。文化生态系统的组成包括五个方面,是指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它不只讲自然生态,而且讲文化与上述各种变量的共存关系[2]。
本文将借助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从文化生态系统这一角度着手,对一个地域村落中曾长期存在农村民间武术团体的兴衰变迁进行考证。以探讨在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影响农村传统武术发展的交互因素,特别是对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影响。
2. 村落武术是时间和空间交互作用的产物
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选择了豫北地区滑县的一些村落作为调研的地区。滑县地处河南省北部,境内一马平川,交通便利。曾因县境内有古渡口白马津,古称白马县,为古代一重要的战略要地。县志载“自秦以降,白马之险甲于天下”,“亦历代战事必争之地也”[7]。因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每逢朝代更替或社会动荡不安之时,都会致使该地遭受连绵不断的兵灾。如清代末年的捻军过滑、天理教起义以及流窜于此的土匪卞起元都对该地造成了一些重要的影响。
在滑县西南部有一个小镇---牛屯镇,旧称牛市屯,曾为清代驿站。县志载:“清制各县驿传马递,专送各路紧要公文,滑分四路,牛市屯铺位南路之一铺”[8]。镇子的四周曾筑有寨墙,挖有寨壕,建有寨门。此种现象,并非个例。咸丰同治年间,社会动荡,时有土匪入境焚掠,民众纷纷筑寨防匪防盗。筑寨的高峰期即为咸丰、同治两个时期。县志多有记载,如“齐克肃,候选训导,城东白道口人。咸丰辛酉,东匪入境,克肃联合各村筑寨”。“刘作云,同治年间兵部武选司郎中,慈周寨人。出钱四千于缗,修筑寨堡,保金甚多,乡里称之”。
修筑寨堡仅仅是保护民众安全的外部屏障,更重要的一个手段是各村各寨习练乡团、乡勇,建立武力以自保。早在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县令孟屺瞻,奉府檄练乡团于牛市屯,滑县义勇争应之”。是时,来自几十个乡村的5000多人的乡勇聚集于牛市屯,使得牛市屯成为当时滑县乡勇最重要的聚集地。众多乡勇当中,不乏武艺高强之人,聚集了当时滑县的著名梅花拳拳师唐恒乐及徒弟仝全、齐大壮等。嘉庆18年10月27日官军围攻道口之时,孟屺瞻和其乡勇还被召去助战。自嘉庆癸酉以来直至民国初年,滑县的团练义勇都是当地防匪护村的主要力量,并多有阵亡,在当地县志中多有记载。
综上所述可知,清末民初该地区成为兵灾匪祸多发之地,习练乡勇成为广大的农村地区自保的最重要手段。自然环境及历史因素的交互影响,对该地区的习武风气有重要影响。时至今日,该小镇及周围的多个村落中仍保留着武术队、狮子队等民间武术团体,并在节庆时节进行不定期的演练。流传下来的传统武术的习练方式也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该地区的武术主要以各种对练为主,而对练套路中,又以器械为主,具有非常强的技击性和实用性。
3. 价值观念的变迁对村落武术团体的影响
价值观念是在人们的利益和需要基础上,在主体长期的价值活动中积淀而成的,是主体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以及自我认识。价值观念的实质是主体需要,利益的内化。
3.1 旧时村落,传统武术的技击性是农民选择习武的主要诉求
旧时农村,“王权不下县,县下唯宗亲”,宗族势力是乡村自治的重要基础,武力也是维护家族利益的重要手段。所以,吸引村民参与武术训练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武术的技击性。“学会夕阳掌,打架不用想”,是当地流传甚广的一句俗语,练武防身永远都是习武者的一个重要目的。有多少村民练习武术的目的是为了宗族冲突中保全自己,目前已很难说的清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农村社会里,由于各自家族人丁繁衍和经济发展的差异,家族之间常有强势家族欺凌弱势家族的情况。因此,家族男子习拳练武,保家防身,显得很重要。
3.2 文革时期,物质奖励的驱动是村民习武的重要因素
文革时期,该地区农村武术蓬勃发展。文革时期的农村体育的蓬勃发展,并非个案,在多篇文章中都描述了当时农村体育的繁荣昌盛,体育锻炼形式各有特点。该地区的农村武术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除却的政治因素以外,也与当时小镇的村支书对武术队的支持有密切关系。为了提高当时队员的习武热情而制定激励措施:练习武术者可以不用参加生产队的劳作,并由生产队补贴工分。练武强身又能获得工分,在满足自身兴趣的同时又能获得切身利益,很快就吸引不少村民积极投身到该项运动中。
除却经济奖励以外,农民内心对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也是促使当时农村武术繁荣的重要因素。在谈及练习武术的原因时,当地武术队的老拳师们强调最多的是“喜欢”二字,正是发自内心的对文化娱乐的需求才是导致文革时期当地村落武术队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事实上,正是由于当时农村文化娱乐生活的极度医乏,习武已成为当时人们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3.3 急剧变迁的社会结构对价值观念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价值观念的实质是主体的需要,利益的内化。村民们从事武术习练,从某种本质上来讲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所采用的工具。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及打工浪潮席卷这个村落,武术队成员对待同一事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转折,物质是否充裕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重要标杆。一些武术队员认为练武不能带来实际利益,渐渐失去了习武的兴趣。2002年春节期间,该镇文化站曾举行了一次全镇的武术队大比武。武术队成员在商讨此事的过程中,就有人表示练武已经没有实质意义。还有人要求参加比赛要有物质奖励。不难看出,此时武术队队员的心态、价值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早年参加武术表演的激情已经褪去,转而更专注于经济利益。
4. 经济发展对村落武术发展的影响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生产力得到空前大解放。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导致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已经开始着手发展经济。但是,由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惯性等特点,及其文化长期对某一特定环境人群的影响,即使环境已发生了变化,人们也会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坚持过往的一些生活习惯。加之八十年代农村文化娱乐生活仍然非常单调,练武仍然是武术队成员获取文化娱乐的主要手段,这也是文化的惯性使然。
但是,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经济利益。有研究者认为:人们过于追求经济的增长,注重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劳动,淡化了传统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传统民俗文化渐渐被农村所淡忘。此时,习武的目的性受到了该村镇武术队成员的质疑,他们认为单纯的习武已不能带给自身经济利益。伴随经济大潮出现的农村武术学校也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挤压了村落武术的生存空间。
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必然导致人们生活重心的转移。改革开放以后,打工热潮席卷全国,外出打工成了村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加剧了村民的对外人口流动。青年人向往城市的便利繁荣的生活,自然包括了武术队中的青年成员。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和劳动力人口迁移,农村学龄儿童大大减少,导致了村落武术人才的年龄断层和后备人才缺乏。
5.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村落武术团体的影响
斯图尔德认为,科学技术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致使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力。科学技术通过物化为某种具体的实物从器物层次开始对传统文化施行改造,全面促进人类文化从器物层次到价值观念上的变革。笔者认为,科学技术对农村传统武术的影响最大的当属传媒媒介及生产工具的革新。
5.1 现代传媒媒介对村落传统武术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
美国传播学者桑德拉·波-罗基奇就传媒媒介对人们的影响做了专门研究。他们在一个社区的有线电视网上播放他们专门制作的宣扬“平等”价值观的电视节目。他们发现,收看过这一电视节目的居民更突出“平等”这一价值观在其价值体系中的位置。波-罗基奇等人认为,这些观察足以说明电视媒介具有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潜力。传媒媒介的内容一方面可以强化人们固有的认知;而另一方面,现代传播媒介内容的多样化也会打破人们的固有认知结构,使人们的追求更加多样化。
20世纪80年代,武打影视剧《少林寺》《大侠霍元甲》《射雕英雄传》的热播,在强化青少年对武术的认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武侠剧中人物的高强功夫、行侠仗义的作风,都对当时农村武术热产生了重要影响。80年代农村武术的热潮和武侠剧的热播在时间上的契合,说明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随着各种传播媒介对竞技武术的大力推介及传媒手段、内容的多样化,可供人们选择的信息也越来越多,从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武术在村民生活中的地位。以往所注重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正迅速消解。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也使得农村青少年不愿意花费辛苦的努力去练习传统武术。曾作为重要文化娱乐方式的农村传统武术,在电视、网络及智能手机面前以逐渐淡出当地村民的生活。
5.2 生产工具的革新未能促使村落武术社团的发展壮大
科学技术通过革新生产工具而改变农村的生产方式。拖拉机、除草剂、大型联合收割机的相继投入使用,大大缩短了农民的劳作时间,将农民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虽然,生产技术发生非常大的进步,农业产量也有所提高,但是随着农民消费需求的增加、物价的飙升,单纯依靠出售粮食,已不能满足日常消费。所以,村民虽然有了更多的农闲时间,但是他们并没有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从练习传统武术,而外出打工却成了更多人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该村镇绵延存续了很长时间的武术队已变得可有可无。
6. 村落武术团体组织结构变迁对农村武术的影响
荀子说:“人生不能无群”。人是社会中的人,基于各种关系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中,构成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结构。南街村武术队的组织成员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基础上,聚集于一起。
6.1 传统村落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
费孝通先生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种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获得的。农村武术团体的组成首先是一个“熟人的社会”。但是在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乡土社会正在进入现代社会,而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对于农村来讲,这种陌生人社会的形成,并非是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导致的,其主要原因来自于人口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导致了成员之间日常接触减少;生活的环境的变化致使个体之间的价值关键出现差异;当他们对同一件事的认知出现较大差异的时候,导致成员之间的陌生感加大。
6.2 人员流动致使感情纽带的撕裂
在“熟人社会”里,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建立的组织结构具有天然情感的特点。成员之间依靠亲情、友情而维系。在这样的组织结构里,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成员的行为主要依靠风俗、习惯及世俗观念来维持。不仅如此,农闲时聚于一起习练武术也是成员之间交流感情、维系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武术队员之间的共同兴趣及师徒之间的感情纽带,对群体稳定起着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重复操作过程中强化了成员之间的情感。
熟人社会、天然情感等特点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农村的相对封闭性及人员流动的缓慢性。而改革开放却打破了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及加速人员的外出流动,曾经的重复性的生活方式变得支离破碎。更重要的是,人员流动增加武术队成员之间的距离,减少了日常生活中的接触,必然导致成员之间天然情感的淡漠,从而影响的农村武术队的向心力和号召力。
6.3 新的组织者威信的降低
传统武术,非常注重师徒关系。几千年来尊师重道的传统,在传统武术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传道授业方面尤为明显。在这个学艺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不是科学逻辑,而是那些世代流传下来的拳学传统[3],更重要的是师傅的权威性。武术队老拳师不仅是武术队的参与者,更是组织者和管理者。正式由于老一代拳师权威性,对维系武术队的向心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便于相关人员的组织和管理。
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辈拳师逐一离世;而新一代组织者的威信却稍有不及。特别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对新的组织者的权威性提出极大的挑战。2002年春节,该村落武术队组织者召集原武术队成员参加镇政府举办的武术比赛时,成员的积极性已大幅度下降。除了众多的因素以外,也表明了组织者的威信已大不如前。加之非正式社会组织对成员不具有强制约束性,致使群体结构具有不稳定的隐患。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极大冲击了原有的组织生态,多元化、物质化的价值取向,一起促成了武术队的分崩离析。
7. 小结
传统武术曾是农民的生活方式之一,更是他们头脑中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武术队、舞狮队等传统武术为广大农民热爱,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农村武术社团组织大多日渐式微,销声匿迹。
导致农村传统武术式微的因素众多,研究者或基于西方文化的强势、或基于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也有人认为是乡土社会自身的衰败导致的。而本文从村落文化生态系统的构成方面综合分析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传统武术式微的原因,特别是作为该村落传统武术载体的武术队的兴衰变迁。这些分析表明,农村传统武术的式微,或者说作为其载体的农村武术队式微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传统村落武术队的发展历程,其实质就是传统武术在农村传承发展的缩影。其背后,不仅仅有传统武术自身原因,更受文化生态环境的制约。因此,传统武术要想在农村持续发展,走得更远,必须要适应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农村文化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