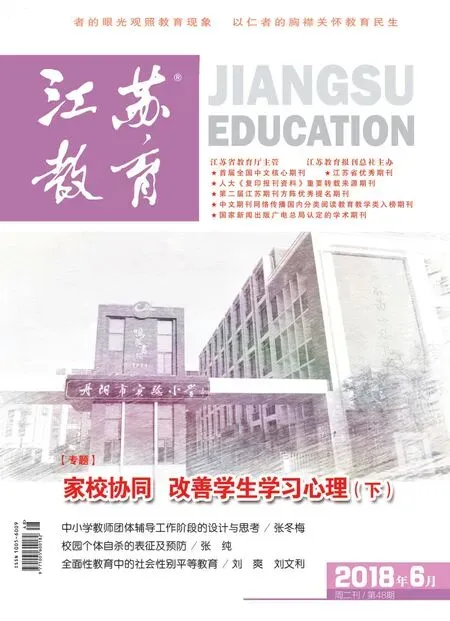基于自我同一性理论的校园欺凌预防与干预研究*
一、校园欺凌的形式、角色及其心理特征
校园欺凌是指一种多次发生的有意伤害别人的行为,其基础是欺凌者和受害者之间力量的不平衡。校园欺凌的形式包括身体攻击、财物勒索、言语侮辱、精神欺凌等。校园欺凌中的角色包括欺凌者、受害者以及同伴关系。
(一)欺凌者
相比于受害者,欺凌者一般身体强壮、孔武有力、体力较好、精力充沛。其心理特征为偏执、霸道、易激惹、攻击性强、低焦虑、高自尊、自我中心、成就感低、缺乏同情心。欺凌者通常学习成绩不理想,通过调皮、捣蛋或欺凌行为来博取他人的关注,以获得满足感和支配欲。
(二)受害者
受害者在生理上一般与欺凌者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性格差异明显:内向、害羞、胆小怕事,游离于同学之外,容易被同伴忽视,缺少友情,独来独往。受害者通常身体有缺陷、智力有障碍、不善于表达,或性格、行为怪异。长期遭受欺凌会给受害者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甚至出现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受害者对欺凌的反应分两类:
1.消极的受害者:孱弱、严重不自信,对欺凌行为采取回避态度,内心希望息事宁人。表现为恐惧和焦虑不安,没有防御行为,逆来顺受。
2.易怒的受害者:烦躁不安,受到攻击时会怒不可遏,有严重的报复意识和行为,甚至以极端方式残害欺凌者。消极的受害者在多次受到欺凌后,有可能以暴制暴,最终成为易怒的受害者。
受害者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当他们觉得自己势单力薄无法保护自己时,就可能借助外在力量,如加入不良组织,与欺凌者进行对抗,引发更大的暴力事件;或者用暴力行为对其他弱小者实施欺凌,由受害者变成欺凌者。
(三)同伴关系
同伴关系包括校园欺凌行为的协助者、附和者、保护者。协助者直接参与欺凌行动,仗势欺人,有些则迫于“同伴压力”而加入欺凌者群体以保护自己;附和者支持欺凌行为,为欺凌者摇旗呐喊、附和助威,间接参与欺凌行动;保护者有可能是欺凌者和受害者都认识的“中间人”,或是受害者的同伴、朋友,在欺凌行为发生时,保护者的作用不容小觑,当他们尽力保护受害者或寻求保护力量(如报警、报告学校)时,欺凌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就可能发生转化,从而终结暴力行为,或者保护受害者免受伤害;局外人则置身事外,认为校园欺凌与己无关,明哲保身。
二、自我同一性理论对校园欺凌原因分析的指导意义
“自我同一性”是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青少年发展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指人对自我发展一致性或连续性的感知,反映个体在青春期发展过程中看待和处理矛盾冲突的能力。埃里克森的自我意识理论有三个重要论述:
(一)“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埃里克森将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分为8个阶段,青少年处于第5个阶段——同一性对角色混乱。这一阶段是青少年由幼稚迈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青少年开始思索诸如“我是谁”等一系列人生重要问题。如果探索成功,他们就能建立“自我认同感”,就能够悦纳自我,经受人生挫折,健康成长;反之,就会进入长期的“角色混乱”或“消极自我同一性”状态,出现暴力行为,甚至形成反社会人格。
(二)“角色混乱”与“消极自我同一性”
角色混乱是指个体的角色与社会生活角色出现偏差,处于紊乱状态。这类个体无法正确认识自我,无法定位自我角色,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该做些什么。消极自我同一性是指个体的同一性与社会要求背道而驰,成为不被社会接纳的“边缘人”,可能出现反社会的人格特征。
(三)“自我同一性过剩”与“自我同一性缺乏”
自我同一性过剩,指个体沉溺于某个团体或角色中不能自拔,自以为这个团体是他唯一的归属,坚信自我的行为方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自我同一性过剩容易导致个人崇拜、狂热主义等偏激社会态度,形成“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自我同一性缺乏,指个体拒绝或逃避社会生活中本应承担的各种角色以及要履行的责任、义务,否认自我同一性需要。这类青少年容易产生暴力、吸毒等破坏或自伤的行为。
通过埃里克森自我同一性理论可以看出,校园欺凌的欺凌者和受害者等各个角色呈现出典型的“角色混乱”或“消极自我同一性”,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分别走向自我同一性的两个极端——“自我同一性过剩”和“自我同一性缺乏”。对于欺凌者来说,他们凌驾于同伴之上,用暴力行为解决问题,厌恶学习,得过且过,理想信仰缺失;对于受害者来说,他们游离于群体之外,自卑、懦弱,消极应付学习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挑战,缺乏交流沟通能力,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身心都处在焦虑、压抑、紧张的状态中。
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关键期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时期,形成期在高中阶段。如果学校能够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让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中感悟、体验、互动、收获,将有助于学生自我同一性的建立。
三、校园欺凌的预防
基于自我同一性理论对校园欺凌的分析,可以尝试借助积极心理学的理念构建“积极优势、积极情绪、积极关系、积极应对、积极成长”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预防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
“积极优势”即挖掘自身潜能和美德,发现并利用个人优势;“积极情绪”即积极调控自我情绪,提升主观幸福感;“积极关系”即建立协调、利己利他的人际关系;“积极应对”即提升耐受挫折、解决问题的能力;“积极成长”即积极适应社会生活,获得满意的自我效能感。要实现以上目标,学校需要积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多种多样,如主题班会、团体辅导、专题讲座、媒体宣传、学科渗透等,但最好的形式是全面开设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要以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现实状况为立足点,教育和活动的内容应该涵盖学生发展的各个方面。以高中心理健康教育为例(见表1):
四、校园欺凌的干预
校园欺凌的受害者通常得到的重视比较多,是心理援助和干预的主要对象。欺凌者因事情暴露而受到法律制裁或学校纪律处分,感到恐惧、焦虑;其他同伴关系目睹或实施欺凌行为,在欺凌事件暴露后有可能出现自责、自罪等复杂心理。他们都是心理干预的对象。在实践中,积极的心理疏解和认知重建有较好的疗效。
(一)逆腹式深呼吸
逆腹式深呼吸要求训练对象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关注身体的放松,特别是腹部的变化,这个时候他们没有时间考虑别的事情,从而达到身心平静的状态。动作要领是:坐着或躺着,两眼微闭,体验气息在身体里流动的感觉。吸气时腹部凹进,呼气时腹部突出。逆腹式深呼吸通常有3种递进的训练方法:
1.慢吸—快呼。慢慢吸气,想象把气息从脚底吸到头顶,再由头顶快速呼到脚底,把负性情绪都呼尽。方法熟练后,可引导训练对象想象自己的面前放着一根点燃的蜡烛,呼出的气息要尽力把蜡烛吹灭。当内心比较平静时,学习第二种方法。
2.慢吸—屏住呼吸—慢呼。想象气息从脚底慢慢吸到头顶,屏住呼吸,保持5~8秒,再把气息慢慢地从头呼到脚,暗示身体越来越放松,心跳变得缓慢而有力,心情变得更加平静。
3.慢吸—慢呼。想象把气息从脚底慢慢吸到头顶,再慢慢地从头呼到脚,暗示身体完全放松下来。
练习完逆腹式深呼吸,可以让练习对象睁开眼睛,也可以继续做其他练习。
(二)青草地冥想法
当校园欺凌的当事人出现应激反应而失眠时,可采用青草地冥想法帮助其入眠。
指导语:以一种放松的姿势坐着或躺着。轻轻闭上眼睛,感觉很安静、很放松,然后采用逆腹式深呼吸进行放松。当身心都达到放松的平静状态时,透过双眉间,“看到”自己正走在芳草萋萋的草地上。这块美丽的草地你或许来过,或许没来过,走在上面,你的脚底能感觉到泥土的松软,鼻子能闻到小草芳香的气息。你看到草地上开着不知名的小花,蜜蜂和蝴蝶畅快地飞舞着,头顶是一片蓝蓝的天空,阳光和煦地照在身上,感觉非常温暖。这时,你觉得有些累了,眼皮很沉重,于是你慵懒地躺在草地上。慢慢地,你躺在草地上睡着了……
(三)内观疗法
内观疗法被称为“自我观察法”,是日本学者吉本伊信于1953年创立的治疗方法。内观疗法通过反观他人为自己的无私付出,反省自我对他人的消极态度和不妥行为,产生后悔感、内疚感等,从而激发自我的诚挚、谦卑和感恩心理。
用内观疗法对欺凌者进行干预时,先以父母、兄弟姐妹等亲人为对象进行内观治疗,看看亲人们对自己付出了什么,自己曾有过哪些积极回应,自己在哪些地方有意或无意地给他们造成了伤害,感恩、愧疚之心被激发后,再以欺凌事件中的受害者为对象进行内观治疗,围绕“我从受害者那里得到了什么?”“我对受害者做了哪些亏心事?”“我给受害者带来哪些身心伤害?”三个问题进行深刻反省,然后提出今后的努力的方向,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弥补受害者身心受到的伤害,有计划地付诸行动。
(四)宽恕疗法
宽恕是疗愈心灵创伤的积极力量,这种方法主要针对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引导他们通过对欺凌者的宽恕释放内心的恐惧、愤怒,原谅别人,修复自己内心的伤痛。宽恕疗法分“五个步骤”进行干预。
1.回忆。通过逆腹式深呼吸放松之后,进入自己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境中,尽量回忆起各个细节,如欺凌者的言语、声调、肢体动作、周围人的附和、自己遭受的困境等。这一训练会使受害者感到痛苦,他们有可能会极力回避,心理咨询师要鼓励受害者完成这个阶段的训练。必要时可采用系统脱敏法协助缓解其痛苦,避免“二次伤害”。
2.移情。站在欺凌者的角度去分析: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在实施欺凌的过程中有什么心理冲突?当他们受到惩罚时有哪些身心体验?如果不及时对欺凌者进行心理援助或积极关注,他们未来的生活将会怎样?
3.利他。想想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曾做过哪些伤害他人(亲人、朋友、兄弟姐妹、周围人等)或小动物的事,他(它)们是怎样原谅自己的。用诚挚的心对他们表示歉意,并用书信的形式写下来。然后采用“空椅子”技术进行角色扮演,把书信内容大声念出来。
4.承诺。在公众场合或朋友、咨询师面前承诺对欺凌者的释怀,可以写《宽恕见证信》,让在场的人作为见证人在信件上签名,并郑重宣布信件内容,表达对欺凌者的宽恕、谅解。
5.保持。保持对欺凌者的宽恕。这一步很难做到,各种复杂情绪时不时会干扰受害者内心的平静。但在父母、朋友、咨询师以及其他“见证人”的陪伴下,受害者慢慢就能体验到宽容与接纳带给自己的轻松、愉快,逐步树立“给人机会就是给自己出路”的信念,昂首阔步地迎接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