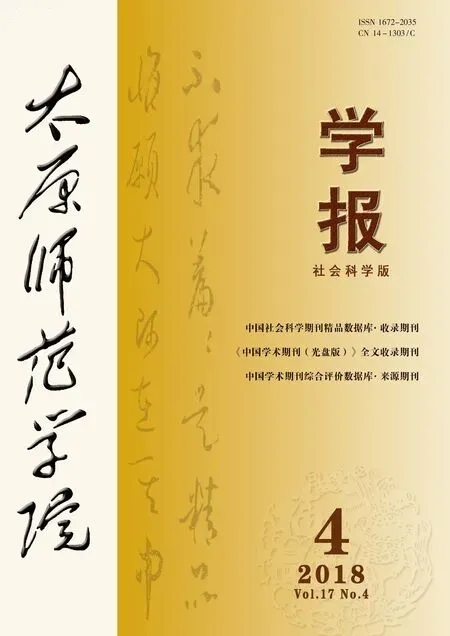90后作家的现代言说
——以顾拜妮短篇小说为例
(1.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387; 2.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近年来,90后写作已然成为了文坛的一道风景线,成为文坛一支重要的“新锐力量”,顾拜妮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她先后在《收获》《花城》等期刊上发表了《白桦林》《请掀起我的裙摆》《我和刘波》《天堂给你们,我只要现在》等十余篇短篇小说。与其他90后作家一样,顾拜妮向我们展现了她的青春与她眼中的青春,她的小说不只是超越了简单的青春写作,而是延续在现代社会的痛苦与矛盾之上,将叛逆的行为与虚妄的结局连接起来,呈现出独特的气质。围绕着一系列的青春故事,顾拜妮展开了对人性本质的探讨,使得她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深刻。
一、虚构与非虚构的双重视角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备受学者的关注。文学如何反映现实?现实如何在文学中得以反映?这些一直都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从2010年开始,《人民文学》开设了“非虚构”专栏,让“非虚构”写作进入作家和研究者的视域。由此,“非虚构”写作被学者研究与探讨,王晖、李国华等从独特叙述、特征及形式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探讨。笔者比较认同王晖教授的观点:“非虚构文学在叙述现实和历史时候所应该具有的超越感,这是对具体细节、事件等等的超越,最终进入到人的终极关怀上,实现形而之下与形而之上的完美结合。”[1]换而言之,“非虚构”不是流派,而是一种写作方式。笔者认为,“非虚构”写作将“真实”作为核心,而“真实”既包括客观世界中的真实,也包括心理体验上的真实。
对于“非虚构”写作的具体特征,王光利在《非虚构写作及其审美特征研究》中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采用第一人称写作,强调作者自身行动的在场感;注重体现故事的真实性,自身经历,情景的现场感,并力图在呈现生活的大背景下,叙说个人的命运与精神诉求。”[2]从这个思路入手,仔细分析顾拜妮的小说,会发现她的写作流转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非虚构的成长体验
顾拜妮在《死亡的主角(创作谈)》中提到:“生活属于管中窥豹,但是只蛤蟆也说不定……我希望用蚊子的视角切入世界,就没准备展示全貌,能写写一只蚊子的世界观我就挺知足常乐了。”[3]顾拜妮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在她的短篇小说中完成了她对生活的管中窥豹。
顾拜妮1994年出生,非常熟悉大学生及90后的语言方式和心理世界,所以她的小说可以通过对许多青春叛逆行为与日常生活叙事的描写,穿越浮华表面,直抵人性本质。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写作者,不同于张爱玲的反传奇,区别于王安忆从对普通人描写中寻找传奇,顾拜妮从青春中寻找人性的本质,凸显自己的虚妄与希望的纠结。所以,小说中青春女性的心理表现得尤为真实。
(二)“我”的在场
顾拜妮的小说除了改编自《阳羡鹅笼》的《绥安山下》及最新发表的《银翼》外,很多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白桦林》《表哥杨日》《金鱼》《请掀起我的裙摆》等短篇小说都以“我”为视角进行叙述,让叙述者的视角与小说人物的视角在作品中低调融合,具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白桦林》中开篇一句“我叫李稚,每天的工作只需要在舞厅里给别人看看场子,放放音乐”[4],将读者拉入到作者或说是李稚的叙事空间中,让读者跟随这个看场子的姑娘来了解她的世界。《请掀起我的裙摆》依然将“我”进行到底,讲述一个十二岁姑娘的青春萌动。最新发表的《天堂给你们,我只要现在》用“我”来引导刘宁,认识这个现代的世界,或说是完成“我”对刘宁的启蒙。《金鱼》中“我”与叔叔的交流,展现了我眼中的世界。《清明清明》《我不是张小军》等都无一例外地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一个个日常琐碎的事情,这种写作方式让顾拜妮以一种与主人公对等的身份参与到小说中。
“我”有了在场感,体现了作者行动的真实性,而且没有逾越小说所赋予的权力,让小说的真实性进一步扩大,也让读者明确感受到顾拜妮所要展示的世界与她所经历的世界是在一个平面上,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三)日常对话体叙事的原生态展现
顾拜妮的创作近两年呈现上升趋势,她也逐渐被文坛所关注。读过她的小说就会感受到在她的小说中对话很多,而且很日常化与口语化。一般来说,小说离不开对话,对话往往是作为语言的细节描写的一个方面,但如果靠对话推动叙事的话,估计很多人就会认为小说流于剧本形式,缺乏小说应有的厚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顾拜妮的小说《白桦林》中,“我”和李稚的对话贯穿全文,对苏生的等候与爱等事件发展的关键信息,读者都是从对话中获取的。
顾拜妮运用对话来推动故事内容的发展,故事代替了书中的某些叙事,成为小说主旨反映的重要依托。在小说中,第一人称“我”与其他人物的一句句对话投射出作者的世界与其对世界的看法及小说的主旨,如《天堂给你们,我只要现在》中第一句便是“‘反正去不了天堂’我说”,这句对话来自小说中间的问答,恰恰是小说的主旨所在。随后,作者通过叙事交代了背景、人物关系,对话模式又顺势展开,两个人看似随意的一问一答,却颇有意味。“我问道‘你相信爱情吗?’‘你爱他吗?’”接着又问“你有没有想过离开刘云飞”,刘宁回答道“离开?我已经丧失了工作的能力,非常不喜欢和人打交道,再说我为什么要离开?”到这里“我”试图引导刘宁,“你可以活得更有尊严,你可以拒绝他提出来的任何无理的要求,他是个成年人,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是他老婆,又不是他养的一条狗”,这些话让刘宁生气了,但我依然没有放弃对刘宁的启蒙,希望她可以看清自己的世界,拿出勇气,做出改变,最后刘宁问“你相信地狱吗”“反正去不了天堂”。这些看起来毫无章法、平淡无奇的对话,却包含了作者对待人生的态度——现代人有着深深的迷茫与虚妄,但是依然不放弃对人的启蒙与拯救,这恐怕就是顾拜妮小说的魅力所在吧。
《金鱼》中“我”和叔叔的对话,让读者和“我”都感受到了叔叔的生存困境,如果没有这次对话,如何能展现出“我”的矛盾——对叔叔的理解与疑惑?《我和刘波》中,“我”和刘大波的交谈也是小说的核心,通过我们的交谈引出了我们对刘小波的共同回忆,显得既真实又荒诞。从《银翼》中苗小东与江燕看到车祸的对话与江边骑行时的对话,可以看出苗小东由对婚姻的纠结到对婚姻未来有了憧憬。
顾拜妮的小说让人物与角色对等,也让人物对话自然地成为故事,以对话带动故事,以日常口语表现真实,同时刻画出了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让小说的真实感进一步加强,这是小说的成功之处。
顾拜妮将非虚构与虚构在小说中交织,通过主人公“我”的在场,让小说有了真实感,还采用日常对话体叙事的原生态推进。非虚构与虚构交织的写作特点,给读者展现了真实的成长体验,让顾拜妮在青春文学的场域中有了深邃表达的可能。文学进化论的核心观点是文学与心灵、人生具有相似之处,都是处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而顾拜妮这种独特手法的运用便给予小说人物回溯过去、直击现在、面向未来的连贯性。
交通工程建设是我国的基础性建设,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保障与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要不断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加强交通工程的质量控制。在混凝土施工中,应该结合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质量控制,确保施工进度和施工质量,保障我国交通工程交通施工的质量要求,促进我国交通工程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死亡与爱情的双重奏
罗兰·巴特曾说过:“从古代到先锋派的探索,文学都在努力再现某种事物。再现什么?再现真实。但真实并不是可再现的,正是因为人们不断地用词来再现真实,于是就有了一个文学史。”[5]91就像罗兰·巴特所说,真实的确不可再现,但爱情和死亡的叙事情节却可以让小说折射出现实。顾拜妮的短篇小说中,“死亡”和“爱情”成为两个主要的叙事情节,小说将“死亡”与“爱情”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死者”在文本中一直处于缺席状态,而爱情不可避免地与“死者”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让小说的主题更加沉重,把小说的冲突放置在爱与死的情节中更吸引读者。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提到:“死亡是讲故事的人能叙说世间万物的许可。他从死亡那里借得权威……”[6]105顾拜妮从《白桦林》开始,“死亡”和“爱情”就是她的小说中两个不可缺少的情节。这篇小说以李稚为叙述视角,故事在“我”和死去的苏生哥及廖志之间展开。为了等待(守着)爱的苏生哥,李稚一直在吴镇生活,等着苏生哥回来,就像朴树的《白桦林》歌曲中所展现的那样,这首歌曲表达的是对远方爱人的思念,所以这首歌也成为李稚对苏生哥爱的反射与写照。作品始终没有交代苏生的死因,但作品中却一直弥散着李稚对苏生的思念,苏生的不确定存在,或说是“缺席”,也给小说留下了想象空白,再加上廖志的到来,让小说在虚实之间摇摆。换句话,“死亡”给了李稚等待的理由,成为故事发展的动力。小说通过“死亡”与“爱情”的双重奏也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世界到底是荒凉的还是有情有义的?小说不是简单地向我们展示某个人的命运,而是借助这个人物的命运,给予我们自己生命中无法品尝的味道。
《清明清明》中写了“我”、刘宁和徐烨的故事,三个人一起去野炊,“我”和徐烨趁机偷情,而刘宁却意外落水而死。小说以“我”和徐烨在清明这天相遇,引出了刘宁的死,也让小说在现实与回忆中交织进行,死亡和爱情的糅合让作品有了张力。刘宁的缺席成为了“我”和徐烨之间无法弥补的裂痕,小说在叙述中处处充满了“我”的负罪感:“心里仿佛尘埃落定,游戏结束了,有代价,可至少我还不是一无所获。我抱着这只来之不易的米老鼠蹲下来,开始哭泣。以为他会问我为何哭,或者告诉我不要再哭了。而他只是在我身边,以同样的姿势蹲下来,摸摸我的头说:‘结束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不是你的错。’我听见我们同时长长地喘出了一口气,今天是清明啊。”“死亡”与“爱情”的互补性叙述,再加上戏谑和调侃的笔触,让这篇小说的主题愈发沉重。
《我和刘波》是窥探顾拜妮小说叙事脉络的典型文本。这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以“我”的口吻写了“我”和刘大波与刘小波之间的事。“我”与刘大波在刘小波的葬礼上相遇,小说也从这里开始,刘小波是一个运气极好的人,连葬礼都不一样——“他爸给他娶了个阴配的姑娘,是个护士,未婚”,“既是葬礼亦是婚礼”,他也成为“我”和刘大波回忆的对象,“爱情”和“死亡”贯穿其中,但看似久别重逢,现实中却都在试探猜测对方,还不如死去的人真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包装自己。
中年男人对待婚姻与爱情的纠结一直是小说家的偏爱,从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到顾拜妮的《银翼》都对此进行了描写。最新发表在《山西文学》上的《银翼》展现了顾拜妮的成熟,小说写了苗小东与江燕、小齐之间的纠葛。苗小东这个中年男人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有过婚外情的愧疚,还有着对现有婚姻的不满,三角的关系将小说的叙事也推向了一种矛盾,苗小东内心一直有着对婚姻的厌倦与对激情的追寻,但一次雨后的骑行,让苗小东仿佛“改邪归正”,感到了幸福,用《绥安山下》中的一句话就是“回家和李圆好好过日子”,生活回到了正轨。小齐的消失,可以说是“文本中的死亡”,小齐的缺席才让苗小东缺少了激情的习染,有了反省的空间,这是人物的选择与作者的态度。小说诙谐幽默,将“爱情”与“死亡”结合,说不清究竟是死亡给予爱情存在的可能,还是爱情让死亡存在?但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温度,冷暖自知。
顾拜妮的小说读起来调侃和戏谑的味道十足,连死亡和爱情这两个人生中最隆重的情节都不放过。刘小波葬礼的可笑、苏生的无缘的“消失”、“我”和徐烨的偷情、看到姐姐与男人发生关系的描写,这些都充满了荒诞意味。而这样的描写方式既给予了人物在这个世界中生存的合理化方式,也给了读者看世界的另一种视角与思考。
顾拜妮的小说采用“死亡”与“爱情”双重奏,更将死者的缺席置于重要的空间中,在这样的方式下,才让小说的文本有了荒诞的哲学意味。可以这样说,顾拜妮一直试图用青春的方式解构这个世界、看待这个世界。爱情是青春叙事的标配,面对青春的激情,写作者唯有通过死亡这种方式才能抵抗自己所准备经历的成人世界,正如本雅明所说:“吸引读者去读小说的是这么一个愿望:以读到某人的死来暖和自己寒颤的生命”[6]111。
三、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剥离
唐诗人曾认为,90后作家与80后作家相比,还在叙述自己的故事,离不开自己的生活,称之为“记忆的色彩”[7]。诚然,一方面,这是每一个作家必须要经历的阶段,或说是创作生涯的基础;另一方面,在记忆的基础上,所赋予生活的思想也不亚于90后之前的小说,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的剥离在人物、情节中都一览无余。这对于读者而言,阅读起来并不轻松,需要辨别是与非、虚与实。
从《白桦林》开始,顾拜妮的笔墨都以日常现实生活为依托,进而书写自己对世界的思考。现实生活成为顾拜妮小说的一个叙事基点,就像一条射线,无限延伸到日常生活的美好、凄凉、疼痛和无奈之中,她的小说贴切地讲述了生活中的细微小事,而且如此的不拘一格:早恋、偷情、执着、迷茫,
《表哥杨日》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我”和表哥的事,现实中看到了表哥的“缺席”的食指,就围绕这一细节,展开了故事的叙述。表哥是家庭里公认的好孩子,而“我”是反面教材,但是两人之间的差距在成长之后并没有显现出来,就像作者所说的“殊途同归”。杨日的食指是“我”一直惦记的事情,但是直到小说的结局,都没有找到答案,都是在猜测,回忆与现实穿插在作品中,慵懒的叙事反而更凸显了主题。小说中,提到莫迪亚诺的小说《暗店街》:“我觉得表哥是朦胧的,自己也是朦胧的,一切都是朦胧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与小说的主题不谋而合——朦胧、无意义,而恰恰那根食指让小说的现实感凸显、强化。《表哥杨日》中的现实与理想的剥离,让文本的叙事更加富有张力。
《金鱼》这篇小说讲了我与极少交流的叔叔的一场对话。面对这样少有交流的对象,作者却细致地描绘了叔叔的经历,不知道是对叔叔因为强奸入狱的理解还是疑惑?在小说中,叔叔问道:“你相信人会迷失在时间里吗?”最后,叔叔以“一条脱离轨道的金鱼,偶尔游到了时间的另一面”作比喻,这样叔叔的形象似乎更迷茫,总是看不清,处于朦胧状态,但这也是叔叔的生存的保护壳——迷失在时间里。这也是顾拜妮探讨现实与理想的一种路径——让人物迷失,但却无法逃离。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处境,但可以选择对待处境的方式——逃离、迷失,或是面对。
我不敢说顾拜妮一定深受卡夫卡的影响,但我可以肯定顾拜妮的作品里充满了与卡夫卡作品中相似的主题——对人的困境的普遍性探索,这也超越了青春叙事的一般内容。顾拜妮不同于卡夫卡的逃离,她试图去启蒙像《天堂是你们的,我只要现在》中的刘宁,也试图去理解叔叔的困境。总之,从自己的世界出发,书写自己眼中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现实与理想的剥离,这个世界如同雾里看花,只有自己的心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曾提到:“写小说意味着在人生的呈现中把不可言说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囿于生活之繁复丰盈而又要呈现这丰盈,小说显示了生命深刻的困惑。”[6]99纵观顾拜妮的小说,她对青春世界的独特体验以及对日常伦理的书写是令人关注的一个方面,她尽可能地给我们言说自己对于社会与生命的体悟——矛盾与追寻,我认为这恰恰也是顾拜妮短篇小说的生长点。
90后作家作品还没有太多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他们的成长,青春叙事恐怕已经不足以概括他们的创作。青春不单单是生活,更是态度,在逐渐的成长过程中,对生活的哲理性思辨也会越来越多地存在于他们的小说中。细读顾拜妮小说,会发现以下特点:采用非虚构与虚构的交织,让小说的真实感进一步扩展;死亡与爱情的双重奏让小说充满了荒诞意味;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剥离,让小说呈现了虚妄的一面,看出了她对世界的理解与阐释。顾拜妮的小说用调侃、戏谑的口吻,冷峻,甚至有些疼痛的笔调写出了自己独有的生命体验,亦叛逆,亦无奈;亦无悔,亦迷茫。这就是她的世界与她眼中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