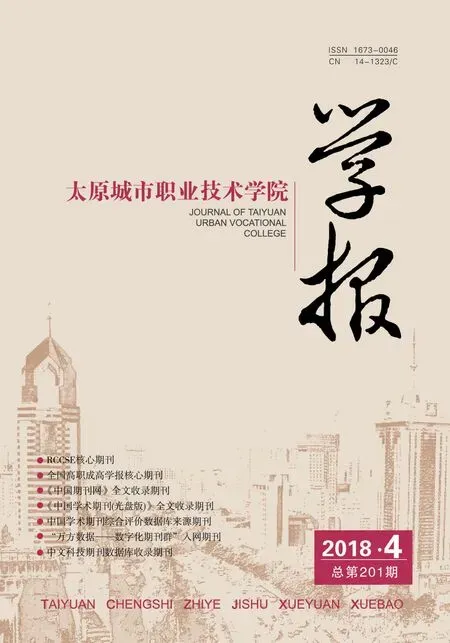元代赋论初探
乐荣荣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00)
赋论的兴起与发展是伴随着辞赋创作的兴起而发展的。汉代是赋创作的兴盛时期,伴随着对汉赋的评价,汉代赋论应运而生。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的古赋逐渐向徘赋发展,魏晋南北朝的赋论随之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唐宋时期,由于科举取士、古文运动、理学等因素的影响,赋从徘赋一变为律赋,再变为文赋,在赋论领域则出现了律赋与古赋之争的讨论。元赋在创作上,由于延佑设科、古赋取士等原因,古赋的创作超过了律赋。元代赋论上承宋金赋论,对宋金以来赋创作方面和赋论方面的弊病进行了批评与革新;下启明清赋论,对明清赋创作和赋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古赋辩体》之前的元代赋论
在《古赋辩体》之前,元代赋论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走向。刘祁、刘埙等人激烈地反对律赋,推崇古赋。同时也有王恽、阎复等人支持律赋,把律赋作为入仕的工具,但他们肯定的是唐宋时期的律赋,要求革除金代律赋的弊端。
刘祁(1203-1250)著有《归潜志》,共十四卷。《归潜志》中多次提到金朝律赋取士的弊端。如“金朝律赋之弊不可言。……其后,张承旨行简知贡举,惟以格律痛绳之,洗垢求癍苛甚,其一时士子趋学,模题画影,至不成语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喻,文风浸衰。”又例如“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弊。盖有司惟守格法,无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陈腐,苟合程度而已。其逸才宏气、喜为奇异语者往往遭绌落,文风益衰。”从上可以看出,刘祁认为金律赋多是模拟之作,过于追求格律、好为奇语,文风衰弱。
刘埙(1240-1319),宋末元初的学者,“祖骚宗汉”的代表,其赋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隐居通议》中,他是以推崇古赋为主。其《隐居通议》三十一卷,其中第四、五两卷为“古赋”。在“古赋”的总评和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中,能看出刘埙的赋学思想。首先,他论述了古赋的范围,其“总评”曰:作器能铭,登高能赋,盖文章家之极致。然铭固难,古赋尤难。至李泰伯赋《长江》、黄鲁直赋《江西道院》,然后风骨苍劲,义理深长,驾六朝,轶班、左,足以名百世矣。刘埙所谓的“古赋”当是指相对于宋元时文、律赋而言的古体辞赋,认为六朝的俳赋和唐宋元的律赋则不属于古赋的范围。第二,其评价古赋的标准:风骨苍劲、义理深长是古佳作的最高标准。他认为,班固和左思的赋虽然巨丽,但有损风骨和义味。六朝的赋则无可取。他认为李泰伯《长江》和黄庭坚《江西道院》是风骨与义理并存的佳作。第三,他认为作赋应该创新,自出机杼,尤其重视语意之奇。如评苏辙《御风词》时引黄庭坚语云:“学者当熟读《庄周》《韩非》《左传》《国语》,看其致意曲折处,久久乃能自铸伟词。”
刘祁和刘埙对金律赋的批评是比较激烈的,提倡古赋的主张是很明显的。元初赋论中还有另外一种倾向,王恽、阎复等人把律赋作为入仕的工具,他们肯定的是唐宋时期的律赋,要求革除金代律赋的弊端,对金律赋的批评态度相对和缓。
王恽(1227-1304),《玉堂嘉话·卷二》中记载了他的赋学思想。“作文字亦当从科举中来,不然,岂惟不中格律,而汗漫披猖,无首无尾,是出入不由户也。后学虽不业科举,至于唐一代时文、律赋,亦当披阅而不可忽,其中体制、规模,多有妙处。”从上可以看出,王恽认为应试的赋作,好处在于合乎规矩,有所制约。即使是不为应试而作,也当学习唐代的律赋,因其颇有值得学习的地方,由此可见王恽对唐代律赋的推崇。
阎复(1236~1312),他对赋的讨论比较集中,主要体现在《谢解启》中,这是一篇专门讨论赋的专篇。
“切惟辞赋之渊源,是乃古诗之糟粕。荀氏子发明其大概,宋大夫鼓舞乎后尘。……自兹以往,作者多。……百变金辽,无复旧家之风骨。拘之以声律之调畅,捡之以对偶之重轻。……鉴视前车,洗涤乎场屋百年之弊。……加程文律,度于古今骨格之内;取古今气,艳于程文规矩之中。自非卓尔不群之才,曷起褒然举首之选。”
《谢解启》中反映阎复的赋学观点主要有这几个方面:首先,他认为赋是古诗的末流。其次,他对赋的历史流变进行了梳理,并对每个时间段的代表赋家进行了评价。再者,他对辽金律赋的弊端进行了批评,认为金赋过于追求形式的雕琢,反而束缚了作家的才情,并且对把律赋作为得取功名的工具进行了批评。最后,希望革除“场屋百年之弊”,削除律赋“拘挛之态”,恢复赋作“丽则之风”,创作文辞义理兼备,既具科举程文形式,又具气骨的辞赋。可见,阎复亦深知金朝律赋取士的弊端,但他并不反对律赋本身,只是希望革除弊端而已。
二、《古赋辩体》中的赋学思想
祝尧,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其为仁宗延佑五年的进士,撰有《四书明辩》《策学提纲》《古赋辩体》等著作,今仅存《古赋辩体》。《古赋辩体》全面讨论了赋的起源、流变以及文体特点。
(一)溯源流、述流变、辩文体
《古赋辩体》中将赋的源头上溯到《离骚》。祝尧认可骚为赋祖、汉赋源于诗骚的观点。《古赋辩体·卷一》:“宋景文公曰:‘《离骚》为词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矩,至圆不能过规。’则赋家可不祖楚骚乎?然骚者,《诗》之变也。……原最后出,本《诗》之义以为《骚》……但世号楚辞,初不正名曰赋,然赋之义实居多焉。自汉以来,赋家体制大抵皆祖原意。”可见,祝尧最推崇的是屈原的《离骚》。祝尧不仅仅追溯了赋的源头,并且在其下,按照时代的先后,分析了赋在不同时期的流变。
《古赋辩体·卷三》: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则古今言赋,自骚而外,咸以两汉为古,已非魏晋以还所及。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
《古赋辩体·卷五》: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建安七子,独王仲宣辞赋有古风……六朝之赋,所以益远于古。
《古赋辩体·卷八》:然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
《古赋辩体》首次提出“楚辞”“两汉”“三国六朝”“唐”“宋”五体之说,对不同时代赋的发展情况和不同时期代表作家、作品进行了评价,并在这五体之中明确提出了“祖骚宗汉”的主张,梳理了赋的发展史。《古赋辩体》将不同体式的赋命名为“古体”、“徘体”、“律体”“文体”。祝尧用“古赋”一词,专指楚骚汉赋,历代以“祖骚而宗汉”为旨归的有“古辞”“古意”的非俳律之赋。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讲求“四声八病”,骈赋开始入律。至有唐一代,则已是“律多而古少”,乃至于“律之盛而古之衰也”。《古赋辩体》把宋代的赋定位为“文体”,并总结了其特点。
(二)本于情,归于“六义”的评价标准
《古赋辩体·卷八》:“然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至于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祝尧在评价赋时已经涉及到了“情”“辞”“理”之间的关系。这是祝尧评价赋的标准。祝尧明确提出了赋“必本之于情”的原则,并从理论上论述了作赋的“情、辞、理”三者之间的关系。
《古赋辩体·卷三》:诗人所赋,因以吟咏情性也;骚人所赋,有古诗之义者,亦以发乎其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于辞,其辞不自知而合于理。情形于辞,故丽而可观;辞合于理,故则而可法。
《古赋辩体·卷四》:长杨赋题注:盖赋之为体,固尚辞。然其于辞也,必本之于情,而达之于理。……故以赋为赋,则自然有情有辞而有理。
祝尧认为“情、理”是根本,“辞”是第二位的。赋这种体式,必然会“尚辞”,但其辞“必本之于情、而达之于理”,甚至是与其“有辞而无情,宁有情而无辞”。当然,能够“情辞两得,尤为善美兼尽”。从“以情为本”的观念出发,祝尧还评析了历代辞赋的不同价值与体格高下。在他看来,以楚骚为主的“古赋”,达到了情、辞、理三者的统一,是赋体的极则。反之,对于俳、律、文体之赋则多有非议之言。
(三)对作家、作品的评价
祝尧用“以情为本、归于六义”的标准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了评价,高度肯定“情”“辞”“理”兼备的作品,对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作品,其辞虽不丽,但亦动人,祝尧也肯定这类作品。祝尧反对的是那些不本于情,也不能归于六义,只追求华丽辞藻的作品。
《古赋辩体·卷五》:赋也。末段自“步栖迟以徙倚”之下,则兼风比兴之义,故犹有古味。以此知诗人所赋之六义,其妙处皆从情上来。(评王粲《登楼赋》)
《古赋辩体·卷六》:比而赋也。此赋虽亦尚辞,而其凄婉动人处,实以其情使之然尔。想明远当时赋此,岂能无慨于其中哉!(评鲍照《野鹅赋》)
祝尧“以情为主、归于六义”,从而纠正了只重形式技巧的律赋和只重议论说理的文赋之弊端,强调赋要像古诗一样具有“六义”和颂扬的作用,这是符合当时延佑设科、古赋命题的大环境的。同时,这种评价标准影响到后世的赋论,明清的赋论对这一问题关注颇多。
三、《古赋辩体》之后的元代赋论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代赋论,一方面受到祝尧《古赋辩体》“祖骚宗汉”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科举考试以古赋命题的影响,更加倾向于强调“古赋”的价值和地位,并且其实用性强,其中探讨了如何学习创作古赋。
陈绎曾的赋论主要体现在其《文荃》之中,《文筌》中的《楚赋谱》和《汉赋谱》各分赋法、赋体、赋制、赋式、赋格等五个方面。“赋制”和“赋式”主要是针对赋创作来谈的,论及的是赋在结构上的谋篇布局和语言句式。他的赋学理论主要体现在“赋法”“赋体”“赋格”当中。
“赋法”是关于赋的创作方法的论述。《楚赋谱》:楚赋之法,以情为本,以理辅之。先清神沉思,将题目中合说事物一一然在心目中……便以此情就此事此物而写之。陈绎曾认为不同时期的赋创作有不同的技巧,其强调要处理好“情”“物”“辞”“理”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正是他眼中楚赋、汉赋、唐赋的不同特点。
“赋体”方面则是其关于赋的体式方面的论述。《楚赋谱》:屈原《离骚》为楚赋祖,只熟观屈原诸作,自然精古。宋玉以下体制已不复浑全,不宜遽杂乱耳。陈绎曾最为推崇的是屈原的《离骚》,对于汉赋他也是比较推崇的,并认为要学习《文选》中所选的汉代的赋。唐代的赋他只论及“古赋”和“排赋”,对于“律赋”他认为“实非赋也”,所以没有论述。他这种“祖骚宗汉”的观点与祝尧的类似。
“赋格”是其对不同的赋的风格进行的评价,其中体现了他的品评标准。
《楚赋谱》:上,清玄,《骚经》,神情思精意真语趣;中,清婉、超逸、壮丽、清典雅、奇丽、顿挫、缒后、布置、顺布,《远游》。……凡楚格,短篇以格为主,中篇以式为主,大篇以制为主。而法,一也。
《汉赋谱》:上,壮丽;中,典雅;下,布置。
陈绎曾将楚赋分为上、下两品;而把汉赋和唐赋分为上、中、下三品,可见其对楚赋的推崇。在他的评价系统中,楚赋最不济也是中品,无下等之作。这就表明了他“祖骚宗汉”的倾向。
陈栎(1252-1334),宋末元初人,卒于元顺帝元统二年,其赋论思想体现在《〈两都赋〉纂释序》中:“律赋凿之以人,惟古赋鸣其天。科目次场有赋,以古不以律,丕休哉!《离骚》,赋之祖,降是舍汉何适矣?……学古赋者能以尚之熟班赋为监,则几矣。”从这篇序文可以看出,首先,陈栎肯定古赋,并且提出了古赋与律赋的区别:律赋过于追求形式技巧,古赋则天然成之。其次,他推崇《离骚》为赋之祖,并且提出《离骚》之下汉赋可学,于汉赋中比较肯定班固的赋。
程端礼(1271-1345),著有《读书日程》,按照朱熹“明理达用”思想,纠正“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之弊,详载读经、学习史文等程序;他有关赋的思想也体现在其中:
“读楚辞正以朱子《集注》详其音读、训义,须令成诵,缘靠此,作古赋骨子故也,自此,他赋止看,不必读也。其学赋次第详见于后。——韩文毕次读楚辞”
“欲学古赋,读《离骚》已见前,更看、读《楚辞后语》并韩柳所作,句法、韵度则已得之。欲得著题、命意、间架,辞语缜密而有议论,为科举用,则当择《文选》中汉魏诸赋、《七发》及晋问熟看。——学作文”
第一,程端礼认为近世的文风不若古人,文风渐弱,所以他认为作文应该学习古人。对于学习古赋的做法,他认为首先应该学习《离骚》并且要精通其中的音、义,然后学习《楚辞后语》以及韩愈、柳宗元的做法和句法。第二,要想把作古赋的方法应用到科举之中,则要从《文选》中汉魏诸赋、《七发》中去学习。从程端礼论赋来看,其赋论或者说《读书日程》这部书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四、元代赋论的特点
元代的赋论,一方面受到当时实行的文化政策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赋文学本身发展概况的影响。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元代赋论具有自己独特的面貌。首先是其“祖骚宗汉”的复古趋向。祝尧《古赋辩体》中直接提出要“祖骚宗汉”。“祖骚而宗汉”,由于批评家的标举而成为一代赋家的共识之后,直接影响到当时赋风的转变。其次是比《诗》论赋,追求载道。仁宗开科诏令,确立了“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的指导思想,这影响到赋创作和赋论上就表现为向经学、理学靠拢的姿态。赋论家在追溯赋的源流时,多从“古诗之流”出发来论赋,从而形成了比《诗》衡赋的思维为式,认为赋是“古诗之流”。元人又强调赋源于骚,又认为骚源于古诗。其次,在评价赋家和赋作品时,以“诗六义”为标准来评价赋,主张“为赋者固当以诗为体”。祝尧《古赋辩体·卷三》:“诗之义六,惟风、比、兴三义,真是诗之全体;至于赋、雅、颂三义,则已邻于文体。……经之以正,纬之以葩,诗之全体始见,而吟咏情性之作,有非复叙事、明理、赞德之文矣!诗之所以异于文者以此。赋之源出于诗,则为赋者固当以诗为体,而不当以文为体。”祝尧明确指出,赋应该以诗为体,不应该以文为体,并且他比附于“诗六义”,以此为标杆来评价作家作品。最后,元代的赋论重点探讨了“情”“辞”“理”之间的关系,并非常强调“情”的地位。《古赋辩体·卷三》:“情形于辞,故丽而可观;辞合于理,故则而可法。然其丽而可观,虽若出于辞而实出于情;其则而可法。虽若出于理而实出于辞。有情有辞,则读之者有兴起之妙趣;有辞有理,则读之者有咏歌之遗音。”这也影响了明清的赋论,明清赋论对这个问题关注颇多。
文章以祝尧的《古赋辩体》为核心,梳理《古赋辩体》前后的赋论,能够了解《古赋辩体》前后元代赋论的联系与发展。元代辞赋批评律赋的弊端,推崇古赋,主张祖骚宗汉;于赋文辞华丽外注重赋的抒情性等特点,不仅在辞赋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时代面貌,并且对革除律赋创作上的弊端,重构汉赋经典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不仅影响了元代的赋创作和赋论,同时也影响到了明、清辞赋理论与创作发展的方向。
[1]上海古籍出版社.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刘埙.隐居通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王恽.玉堂嘉话[A].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66册)[C].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4]李修生.全元文(第九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5]王冠.赋话广聚(第一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6]李修生.全元文(第八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7]程端礼.读书日程[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709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