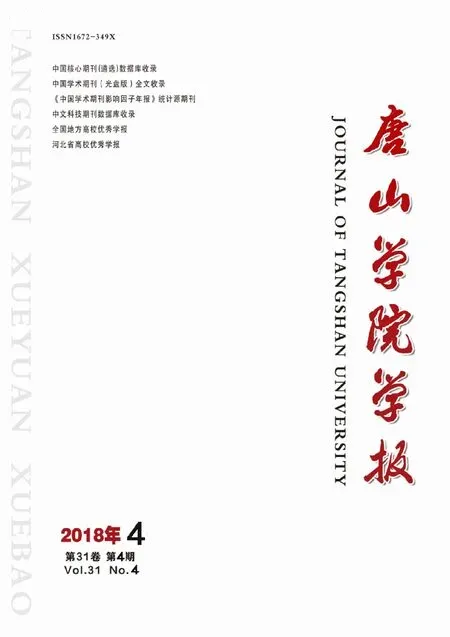实事求是的史学成果与“先驱者”的时代光辉
——访李大钊研究著名学者朱成甲
邹兆辰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37)
一、“殚精竭虑、理性至上”的李大钊研究“三部曲”
访谈人:学术界有学者称您研究李大钊有“三部曲”,我们就从这“三部曲”开始吧。首先,请您回顾一下您研究李大钊的历程。
朱成甲:北京行政学院的侯且岸教授在《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我的李大钊研究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殚精竭虑 理性至上——评朱成甲的李大钊研究三部曲》。我想,“三部曲”的提法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三部曲”的说法基本概括了我的李大钊研究历程。那就是:1983年发表了我的李大钊研究第一个成果《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发表在《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这是第一部曲。1989年7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全书42万字。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再版了这部书,这就是第二部曲。200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李大钊传》(上),这是根据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的要求撰写的,全书62万字。这也就是我的李大钊研究的第三部曲。
访谈人:您为什么选择李大钊作为您的研究对象呢?
朱成甲:李大钊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重要历史地位的人物,我对李大钊研究重要意义的认识也是伴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而不断加深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思想理论界的拨乱返正,我国史学界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先,需要突破的问题集中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1980年2月,彭明教授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中提出了10个问题并进行论述。他指出,要分析历史人物成长的时代和社会条件,要具体地分析人物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不要回避和篡改历史事实。彭先生的这些论述都是有的放矢、切中时弊的,在史学领域内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发挥了先导性的积极作用。其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李新教授又连续发表《文与史》《史论》《文笔、论笔、史笔》3篇文章,都刊登在《历史研究》上,对于长期流行的种种非科学、反科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反驳,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得到进一步的弘扬。我的李大钊研究,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开始的。
1978年,在准备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的过程中,我试写了一篇《李大钊早期民主思想》的文章。按照当时流行的逻辑与思维定势,我就很直接地得出了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时期最早反袁,因为他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之类的结论。不过,这时候我终究已经受到了70年代后期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新理性的启迪,于是把得出的结论与李大钊自己的文字仔细加以对照,越对照越发现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按照当时的情况,我写的这篇文章当时也不是不能发表,但我还是要坚持立言从慎的原则,决定文章不发表。但是,说李大钊最早反袁容易,说李大钊一度拥袁难。这不仅是学理的问题,更是社会常识。可是,由于新理性的驱使,我当时宁愿选择“难”,这一头钻研下去竟花费了四年多时间。
由于当时我读到的仅仅是《李大钊选集》,我认为如果就以这些文章来对李大钊在辛亥革命后未曾反袁反而一度拥袁的情况下结论,就未免有些轻率。正好这时,我得到吴家林好友的帮助,看到袁谦同志为主任的北京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同志长期搜集、准备出版的《李大钊文集》的书稿。这样,就使我对自己所发现的问题能够有把握地作出论断。
但是,这时候我还是不愿意发表这篇文章。因为这时候仅仅是弄清了“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却没有弄清楚“为什么”。这样,我的文章即使写出来也是底气不足,缺少深度。所以,我下决心要拓宽研究视域,就是要研究相关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首先,要研究袁世凯和清末的“新政”;其次,要研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第三,要研究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研究了这三大系统,又花费了三年多的时间。直到1983年,才最终决定发表我研究李大钊的第一篇论文《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
1983年的这篇论文,事实上已经标志着我的专著已经基本准备就绪。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动笔,将出版社要求交稿的时间又推迟了两年多,以便我能够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直到1987年7月才交稿,时隔两年后的1989年7月终于出书。它就是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
访谈人:您已经做了非常充分准备,为什么过了几年您的书稿才完成呢?
朱成甲:这是因为我没有想到写作中会遇到那么大的困难。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逐渐呈现出来。主要是将李大钊和近代中国联系起来研究,这比单纯研究李大钊本人难度大多了,因为它的研究范围预想不到地扩大了。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和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要求我不得不这样做。这样,我花费了比研究李大钊本身材料多得多的时间去研究与之相应的背景,去研究与之相关的大量事件和人物,同时也自然涉及到与这些事件、人物的联系问题与评价问题。正因为有了这个追求,我花费了较多的时间深研这个问题,但仍感到时间不够。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觉得还有必要再费一些时间去进行研究,因为我总觉得对一些问题研究得还是太少、太肤浅。
另一方面,李大钊早期思想不仅和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和众多的历史人物密切相关,而且它所反映的内容也多是属于重大的理论问题与学术问题,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增大了研究的困难。比如,有一些极为容易触犯忌讳又长期没有获得科学解释的问题,像如何看待一定条件下的改良与革命的问题,绝对斗争与相对调和问题,如何看待民主与专政、自由与专制、民治与个人集权(独裁)问题,如何看待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清末新政等问题,都是过去无法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与科学说明的问题。当然,虽然现在有条件进行研究,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却不能不花费更长的时间和精力来探讨。
访谈人:10年之后,为什么人民出版社又再版了《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呢?
朱成甲:我的这本书出版后,许多朋友想看到这本书,但就是买不到。比如,1989年秋,我把这本书送给了当时《人物》杂志的主编马连儒编审。一年后,马先生告诉我那本书不久就被陈茂仪、姚洛、谢云三位老同志拿去传着看,书店都买不到。再如,1991年底,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同志从广州出差回来,见面后告诉我,他和当地教育界的同志谈到这本书,都说不知何处能买到。当时海外也有一定的需求。鉴于这种情况,再版的问题摆在了眼前。为此进行过两次征订,国际书店的征订数达到230本,其中日本东方书店订了98本,香港三联书店订了80本。这都说明海内外读者对这本书是有需求的。
由于书的传播不广,有些在书中已经纠正的错误还在继续延续。比如被收入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李大钊1913年冬去日本之前写的一首赠给友人的诗《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书中对该诗的解释,称“天问”是“郭厚庵”,说当时他是参加孙中山“二次革命”的“讨袁军”。这本“诗抄”当时影响很大,印行约七十万册。我的这本书已经考证清楚,这里的“天问”根本不是“郭厚庵”,而是白坚武。“天问”所从的军,也根本不是“讨袁军”,而是镇压“二次革命”的“袁军”。像这样根本性的谬误,以后并没有纠正过来。如,1990年9月出版的李克寒选编的《革命烈士诗词精选》仍然沿用这种错误的解释。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本著作还未能得到广泛传播。
正因为社会上对这本书有这种需求,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10月再版了《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这本书。当时,正是纪念李大钊诞辰110周年之际,出版社的同志为了赶在10月出版,做了大量辛勤的工作,满足了社会各方面对这本书的需求。
访谈人:您为什么又走出了第三步,开始撰写《李大钊传》呢?
朱成甲: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9年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关怀和支持对李大钊的学习、宣传和研究。1994年,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根据1989年党中央纪念李大钊百年诞辰大会的精神,对李大钊研究作了进一步的规划部署,决定实施重新编辑注释出版《李大钊全集》和撰写出版《李大钊传》两项工程,并呈党中央获准。对于前一项工程,我也曾承担了部分任务,全书于1999年完成,胡锦涛总书记亲临该书出版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于撰写《李大钊传》这一项任务,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委托我承担重任,独立撰写。
原来设想的《李大钊传》是准备撰写一部50万字的全传。但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根据李大钊这个人物的特点与其实际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内涵,需要写一部百万字的全传,分成上下两册,才能够比较全面、深刻地再现这位伟大的人物。所以,其难度也就远远超出了原来的预料。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到2009年9月,完成了上部的撰写,大约62万字。
我因身体等原因没能完成全传的撰写,深深感到愧疚,觉得对不起李大钊研究会。但李大钊研究会的会长王学珍同志对我毫无不满之意,反而安慰我说:“已经努力了,写成半部也好,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就是写了半部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特别的努力,总编辑赵剑英同志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特殊的支持和关照,仅仅三个月的时间,该书就与读者见面了。
访谈人:现在大家都很关注您的《李大钊传》(下)的写作情况,现在进展情况如何?
朱成甲:大家都很期待与关心《李大钊传》(下)的写作情况。《李大钊传》(上)出版时,我已76岁。我想按我写作的习惯,如果要写下册,大约仍需10年。所以,对于自己身体是否可以胜任感到缺少把握。于是,决定改变计划,拟写两个专题性著作:一是《李大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是《李大钊与中国“大革命”》。第一部著作完成后,看情况再决定是否进行第二部著作的写作。我的这个计划,也曾告诉过友人。例如,2014年,张静如先生在评《李大钊传》(上)的文章中就说:“这部著作只写了上卷,按上卷的规模还应有中卷、下卷。可是我问老朱后边怎么办,他说不想按传写了,准备写两个专题性著作。不管怎么写,希望早日看到后边的成果。不过,年纪不小了,悠着点。”由于其他任务在身,现在力争尽早完成第一部著作。大出所料,张静如先生于2016年8月29日仙逝。好友言犹在耳,思之痛心。
二、改革开放的时代与史坛的优良传统是李大钊研究不断前进的动力
访谈人:您的李大钊研究如果从1978年算起,至今正好是40年,它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进行的。您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大家公认您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我国学术界李大钊研究的最高水平。现在回顾一下这个历程,您觉得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朱成甲:回顾这几十年来的李大钊研究,让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学术界的前辈、朋友们对我的研究的热情关怀和支持。这可以说是推动我把李大钊研究持续不断进行下去的力量。
记得我的《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一文在1983年底发表以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收到了李良志教授的来信,当时我还不认识他。他在信中告诉我,李新同志在他主持的“写作班子”一年一度的春节聚餐会上,大为赞扬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认为材料扎实、实事求是,提倡大家也应该这样来搞研究。李新同志在这样一个英才云集的场合对我这后辈的文章作如此赞誉,使我感到既荣幸又惭愧。
积极关注和支持我这篇文章的还有刘桂生教授。刘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就研究李大钊,并且多有创获。80年代以来,他曾以李大钊的思想研究为题多次在法、德等国家的知名大学讲学。1984年10月,在乐亭召开的纪念李大钊诞辰95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刘桂生教授。他说,《光明日报》刊登了《历史研究》的目录,就感到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当时,他和李新同志在广州,他立即很高兴地告诉了李新同志,一致认为这个选题好,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像刘先生这样一位崇尚学术的学者,对我的一孔之见竟然如此厚爱,使我非常感动。
1984年2月,我又接到了当时并不相识的张静如先生的来信。张先生对我的文章的态度,我是十分关注的。因为他是李大钊研究最早的开拓者,是发表李大钊研究专著的第一人。另外,我的探讨与张先生过去之论是不同的,张先生对我的“异端”之论究竟持什么态度,我当然不能不介意。通过研究张先生的来信以及他以后在一系列会议上充分肯定我的新探索的态度,使我感到张先生其人其言是至诚的、朗廓的。他在后来的会议上,又对自己在开拓期本是属于某些难免的不确之处,总是极为虚怀若谷地表示自省之意。张先生的这种风范,确实难能可贵。
访谈人:您这里所说的几位先生对您的文章的关注与支持大都是在1984年前后,后来在您的著作《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的出版前后,又得到哪些学者的关注支持了呢?
朱成甲:这里我首先要谈一谈著名史学家李新和刘桂生二位先生,他们不仅在我的文章发表后给予热情的鼓励,更在1987年11月我的专著即将出版时为这部书写了序。他们在序中指出:坚持从客观事实出发,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以李大钊的早期思想来说,他曾经接受过改良主义、调和主义等思想影响,曾经一度对袁世凯认识不清,表示拥袁的态度。曾经对当时的革命党人持有种种批评。在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征途中,他曾经经历过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是李大钊自己的文字中所明白表示了的。该书严肃冷静地对待这些事实,在严格地弄清这些事实的前提下,进一步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经过这样的一番细致工夫,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就被系统地、真实地清理出来了。他们在序中还说:不把李大钊当作孤立的个人,而是把他和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文化气氛、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考察,是本书的又一个特点。可以说,李新、刘桂生二位先生的序言对本书的特点作了最好的概括。
1989年8月,研究五四运动的著名史学家彭明教授看到了这本书,他当时就明确指出:“成甲,你写这本书很不容易。这些年来,我国的学风不好,可是你竟能不受干扰,扎扎实实地搞研究,用了近十年时间写出这样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确实难能可贵!这种精神和学风,很值得提倡!”
丁守和先生对于本书在学术上的一点贡献也不惜余力地给予护惜和传扬。他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文章进行了评论,同时还对本书作了全面的学术鉴定。他认为:第一,本书第一次系统、全面、客观地清理和叙述了李大钊早期思想发展的具体过程,从多方面澄清和纠正了长期以来在李大钊研究中存在的严重的曲解和误解,使人们在这方面的了解和认识达到科学的实事求是的阶段;第二,本书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理论剖析;第三,本书在人物研究的方法上作出了积极可贵的探索。丁守和先生认为,著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重要思想家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在李大钊研究中学术水平最高和最有分量的著作。
访谈人:在您的书出版不久,可以看到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在比较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评论您的这本著作,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朱成甲:好的,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发表的文章有:杜蒸民的《贵在求真与创新——朱成甲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简评》(《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2期);黄侯兴的《李大钊研究的新贡献》(《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5月25日);徐思彦的《李大钊研究的重要进展》(《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舒芜的《让时代来解释人物——一本知人论世之书》(《读书》1990年第9期);丁守和、李林的《李大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评朱成甲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新华文摘》又随即转载);杨义的《从一部书看治学品格》(《群言》1991年第2期)。后藤延子是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教授,也是李大钊研究卓有成效的学者。她在《东方》1990年第116期撰文指出:朱著是李大钊研究中“出类拔萃的著作”,“是中国解放后李大钊研究中水平最高的专著”,“值得花很多时间精读”。
访谈人:我看到刘桂生先生在《清华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上发表一篇《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跋》的文章,对于您的这部著作对中国李大钊研究所作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能谈谈具体情况吗?
朱成甲:好的。刘先生的文章说:我国李大钊研究曾长期存在着一些重大史实性错误。如把早年——辛亥革命时期的李大钊说成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把他当时的政治思想觉悟说得比孙中山和黄兴还高,是他,而不是孙、黄“最早”认清袁世凯盗权窃国的“反动本质”,“首先”发表反袁文章。这种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的论断,长期被认为是正确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这种状况,三十余年无人提出异议。由此可见,它的产生和存在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误解与曲解,究其思想根源,是和我国现代史研究中长期流行的某些先验性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紧密相联系的,是和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历史论述的框架和理论逻辑相适应的。如果不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纠正原来的某些缺点与弱点,如果不使历史论述的角度在逻辑上作出新的实事求是的调整,要想彻底纠正李大钊研究中的种种违背史实之论断,是很难办到的。正是在这一方面,朱著本身蕴含着的史学功力、文化眼光得以充分展示,并以学术贡献之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
三、李大钊研究归根到底是由于“仰范前哲”
访谈人:从我们上面的谈话可以看出,您对李大钊的研究是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启动了,到今天已经进行了40年。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能够坚持这样长的时间,这是很罕见的。您在研究的过程中必然会对自己这项研究的意义认识得越来越深刻,它是推动您把研究持续下去的力量。可以谈一谈您的体会吗?
朱成甲:好!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我几十年来坚持李大钊研究,归根到底是由于对李大钊的崇敬与信仰。正如唐代大史家刘知幾所说:“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所以,李大钊的崇高人格与奋斗精神,几十年来始终是推动我深化研究的力量。
李大钊从“束发受书”之时起,即深感“国势之危迫”,立志“深研政理”,去寻求“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因此,他曾接受以追求和平改良为途径、实现君主立宪政治的改良主义;曾经坚决拥护并捍卫由暴力革命而来的民主宪政制度,即民主主义。在这两大政治潮流中,他都起过不同凡响的作用。但是,李大钊仍不停止自己的探索,不断与时俱进,终于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又率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是20世纪中国在孙中山之后又一位“登高一呼”、率先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人。
李大钊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与伟大复兴,为了实现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的崇高理想,不惜献出最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思想理论、业绩、崇高人格与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发扬与继承。这里我要引一段著名学者张申府先生关于李大钊人格与人生的典型意义的话。他说:“他应该说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訾议的。他的思想的前进,他的行动的积极,他的为人的纯洁,他的对人的温厚,他的道德的高尚,他的革命情绪的热烈,所有这些兼而有之,真可说是一时无两。”
我还记得一件事:2006年,我在江西婺源发现李大钊亲笔写给友人的对联,遗憾的是对联的上联不见了,所以赠送的时间、对象都无从查考。这副对联的下联是“量才常以玉为衡”。上面所说张申府先生对李大钊的评价,就是符合这一联语的基本精神的。据考证,这副对联的全联应该是“改过每将人作鉴,量才常以玉为衡”。我们从这副对联的内容来看,如果不是送给林伯渠、张申府这两位友人的,那也应该是送给与他们当时大体相当的友人。
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人格,并且又以洁白无瑕的玉来作为完美人格的比喻和象征。《礼记》就说过:“君子于玉比德焉。”李大钊赞美友人在量人的时候,习以为常地以“玉为衡”,这自然也是李大钊自己习以为常的人生指针。因此,我研究李大钊,首先是出于对他的完美人格、崇高精神的深刻感受,愿以“玉为衡”的精神,来对他进行探讨、研究与评价。
访谈人:我看到在您的《李大钊传》(上)一书的《后记》中,您特别论述了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优秀人物。您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朱成甲: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回顾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在我对李大钊的研究过程中,毛泽东的这句话总是经常回响在我的脑海里,有时甚至会情不自禁地留下感动的热泪。我深切地感受到,在毛泽东所说的这些优秀人物中,李大钊实在是最为典型的“可歌可泣”的一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还提到过四个“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们就是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毛泽东正确地说明了中国优秀人物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直至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但是,对于究竟谁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率先地找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优秀人物?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有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也和严复、孙中山同样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有条件使他能够率先地去接受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这些问题,毛泽东在当时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而客观的历史过程中,事实上是不可能没有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随着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经过我国学者的努力,这些问题终于都有了比较正确的合乎历史实际的回答。可以说,李大钊这位优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是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的。只有他的人生历程,才具有回答上述问题的最完整答案的条件。在中国共产党人中,也和孙中山、严复一样苦心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并且真正作出杰出贡献的,就是李大钊。中国的历史过程本身告诉人们,只有那种首先向西方的思想文化寻求救国的政理和真理的优秀人物,才有条件、才有可能率先寻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并运用于革命实践,而建党本身就是首创的伟大实践。通过对李大钊传记所反映的李大钊从“束发受书”之时起,即“矢志于民族解放的事业”并开始去寻找救国真理的艰辛经历,能进一步体会到毛泽东上述论断的深刻与正确,就能进一步认识到李大钊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寻求救国真理的“可歌可泣”的一个最光辉的典型。
访谈人:您曾经专门撰文谈到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本特点,是立志通过“深研政理”来救中国,您可否进一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朱成甲:好的。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在中国近代史上众多探寻救国真理的优秀人物中,为什么李大钊能够起这种率先作用?我觉得这其中的原因、条件和所揭示的历史与人生意义,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它既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时代的必然性,同时也反映李大钊这位杰出人物具有回应历史呼唤的特殊条件,具有立志追求真理而又能找到真理的人生机缘、动力与内在逻辑。
我认为,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本特点,是立志通过“深研政理”来救中国。留日回国后,仍“深研政理”,继续回答“再造中国”的重大理论问题,直至找到马克思主义。“深研政理”是他走上为中国革命开辟历史新纪元之路的关键,也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本特点。
李大钊的以“深研政理”为特点的爱国主义,是中国现代爱国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李大钊认识到,中国原先的爱国主义已不足以应对时代的需要。正是由于他敏锐地感受到中国原先的那一些爱国救国的思想理论的严重不足,才立志要“深研政理”,以求对救国问题在一些根本性的理论方面有新的更好的解决方法。
李大钊立志“深研政理”的实质,是科学理性的爱国主义。在中国近代众多有志报国的优秀人物中,像李大钊这样立志以“深研政理”作为救国根本之途的救国的方法、路径选择,实在少见。相反,倒是追求强兵救国、强商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国会救国、立宪救国、革命救国、国粹救国以至于医学救国、文学救国、体育救国、拳术救国,等等,如灿烂群星。李大钊“深研政理”的救国选择,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首倡科学理性爱国的先声。
究竟什么是现代国家的立国精神?从历史与现实看,为什么要追求与实现这种立国精神?中国原先的立国精神是什么?为什么必须改进?如何改进?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显然都必须经过“深研政理”,依靠科学理性才能解决。
李大钊从立志“深研政理”到找到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毛泽东曾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毛泽东所说的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可歌可泣的过程,李大钊应是最典型的。
访谈人:您认为李大钊通过“深研政理”找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有哪些主要的理论成果呢?
朱成甲:我觉得李大钊可歌可泣地“深研”与探索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至少有以下四方面。
一是首创“以人为本”的“民彝”政本论。他将“民彝”,即以人为本的近代人本主义,作为立国的基础与为政之本。
二是首创人天合一、能动转化的青春国魂论。1916年5月,李大钊完成《青春》一文的写作。这是一篇“改进立国之精神”的大政理,是重铸国魂、民魂的哲学著作。他创造出一种青春的宇宙观、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与人生观,有力地批判中国人当时流行的悲观、颓废情绪,从哲学理性上树立起昂扬、乐观、再造青春中华必胜的信心。《青春》是中华民族告别衰朽、再造青春的精神宣言。
三是首倡人生理想契合宇宙本体的真理论。李大钊认为,历史上任何教主或圣哲,都必须接受真理的检验而不能高于其上。他不仅将真理作为爱国的标准,而且作为人生的标准。这种理性爱国的真理人生观,是他率先“迎受”马克思主义以救国的主观条件。
四是“迎受”时代新潮流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研究现代政理,必须首先研究人类历史的共同方向与时代潮流,这是李大钊的信条。远在十月革命前,从1917年2月起,他就开始研究欧战并特别重视俄国由二月革命兴起的革命潮流,并称之为“俄国大革命”。十月革命后,他更大声疾呼,连续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要“迎受”这一世界新潮流。他特别告诫人们,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李大钊正是在率先“迎受”这种新潮流中,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纪元。
李大钊指明了历史发展的新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深刻揭示了十月革命新潮流的实质与意义,即赤旗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功业”。李大钊率先揭示出,真正要解决中国的救亡与复兴问题,中国必须学十月革命。李大钊对十月革命新潮流一系列最深刻的阐释与最热忱的欢呼,对中国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产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至为重要。
访谈人:这就是说,李大钊“深研政理”的结果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有密切关系的。
朱成甲:确实如此。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老革命家林伯渠“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的诗句,应是最为深刻而正确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根本特点,是它先有一个思想创建的阶段,然后才进入组织创建。组织创建是从1920年陈独秀回到上海以后才开始的,但思想创建,则是从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新潮流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首先需要产生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这种先进分子的最突出表现,就是接受最新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接受俄国十月革命新潮流的一整套思想理念。毛泽东曾说,五四时期“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共产党成立的最主要的思想创建的任务。自然,李大钊不仅承担起上述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赞成”俄国十月革命的任务,而且他还使这些先进分子初步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1919年5月,李大钊完成划时代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培养中国共产党思想创建阶段的先进分子提供了最重要的党课教材。
访谈人:今年,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4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您一直没有中断对李大钊的研究,您是当代学者中对这位革命先驱者研究最深入的一位。您认为李大钊当年的艰辛探索对我们认识中国发展道路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朱成甲:不错,改革开放40年了,我们党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中华民族最美好的新时代,同时也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的事业与理想在中华大地上实现最为大放异彩的时代。这里,我想对李大钊与中国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问题,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所谓中国发展道路,归根到底,就是要解决建什么样的“国”?立什么样的“群”?两者是何关系的问题。中国人几千年素来只知有朝廷,并不知这个道理。直到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才开始懂得这个道理,并立志奋斗来解决。李大钊从“束发受书”开始,就“矢志”“深研政理”、追求“真理”,以解决这个问题。他率先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他为中国寻找发展道路的最伟大的思想成果,是对于我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文明所作出的最杰出的历史贡献。
访谈人:最后,谢谢您接受访谈。您的谈话,不仅回顾了个人研究李大钊的过程,而且指出了我们继续深入学习李大钊、研究李大钊的重要意义。无论对李大钊研究者还是广大读者都有深刻启发,在很多问题上都提高了我们的认识。
祝您身体健康,在李大钊研究的道路上继续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