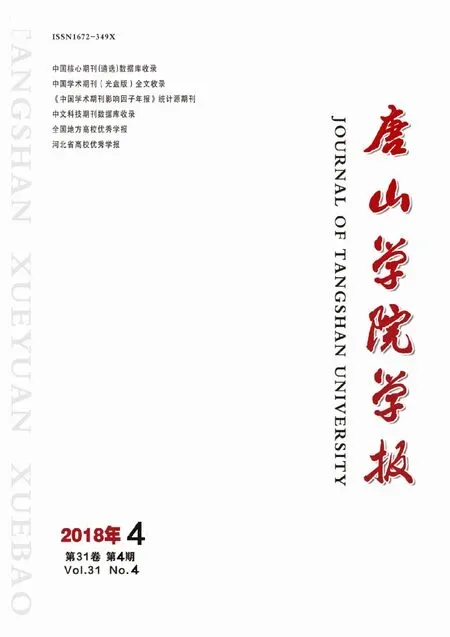《宝剑记》对《水浒传》的继承与创新
王 凯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自称中麓子、中麓山人或中麓放客,山东章丘人,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戏曲作家。他“七岁善属文,读书一见辄成诵,又即知声律吟咏之学”[1]1033。嘉靖八年(1529),李开先二十七岁,进京赴考,中进士。次年,被委派在户部任事。三十岁时,授户部主事,后又历任吏部考功司主事、稽勳司员外、文选司郎中、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等职。他为人正直,执法严明,敢于直谏,拒绝贿赂钻营之徒。平日里,他与王慎中、赵时春、唐顺之、吕高等七人诗酒唱和,并称“嘉靖八子”。后因抨击批判夏言内阁的腐败政治,被削职为民,与他处于同一时代的戏曲家冯惟敏曾称赞他:“完全名节,不降志随邪!”[1]1034四十岁时,李开先返回故乡章丘,修建亭园、藏书楼,并与同乡好友乔龙溪、袁西野等人结成词社。自此以后,一直过着著作的生活。隆庆二年(1568),李开先患脾病,不久离世,享年六十六岁,代表作有传奇《宝剑记》《断发记》,散曲《中麓小令》《四时悼内》《卧病江皋》,院本《园林午梦》《打哑禅》,杂著《词谑》《画品》《诗禅》等。
一、《宝剑记》对《水浒传》的继承
《宝剑记》是李开先戏曲方面的重要代表作,其与梁辰鱼的《浣纱记》、王世贞的《鸣凤记》,并称“明中叶三大传奇”。《宝剑记》是对《水浒传》的改编加工,主要取材于《水浒传》第七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到第十一回“林冲雪夜上梁山”这段故事。两者一为传奇,一为小说,相较之下,虽然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也可以明显看出《宝剑记》对《水浒传》的继承印迹。
(一)主要人物设置的继承
《水浒传》第七回至第十一回写“林冲落草”这段故事所涉及的主要人物,在《宝剑记》中都有提到,其承担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也基本没有变化。
林冲:《水浒传》中的林冲是“林冲落草”这一故事里的主人公,他绰号“豹子头”,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2]97,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妻子是张氏,岳父是张教头,好友是陆谦、鲁智深,顶头上司是太尉高俅。《宝剑记》对林冲主要人际关系的概述与《水浒传》基本类似,但又有所补充。传奇提到,林冲姓林名冲,字武师,汴梁人氏,父亲叫林皋,原为成都太守,不幸早亡,母亲健在,且与林冲、张氏住在一起。另外,传奇对林冲的为官履历也有所交代,林冲先为征西统制,曾因毁谤大臣之罪被贬为巡边总旗,后又做了禁军教师,在故事最后被封为都统,兼管军务破虏将军。
张氏:《水浒传》中的张氏常以“林娘子”代指,其丈夫是林冲,父亲是张教头,贴身丫鬟是锦儿,最后被高太尉威逼亲事,自缢而亡。张氏在“林冲落草”这一情节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出场次数极少,小说对她的描写也十分吝啬。《宝剑记》中的张氏叫张真娘,其主要人际关系与《水浒传》相似。在推动剧情发展方面,她的地位较《水浒传》有所削弱,但作者有意褒扬,不惜花重笔进行刻画,这使她的个人形象更趋饱满,成为《宝剑记》中仅次于林冲的第二号人物,最后被册封为洛阳郡夫人。
锦儿:《水浒传》中为张氏女使,张氏两次被调戏时,都由她传话给林冲,在张氏自尽之后嫁人。《宝剑记》中亦是张氏女使,其事迹与《水浒传》稍有不同,林冲落难后,高朋调戏张氏,在高朋的淫威下,她代替张氏嫁给高朋,为保全名节自缢而亡,最后被封为义烈贞姬。
林母:《水浒传》无此人,《宝剑记》中为林冲母亲,姓李,闻得林冲落草梁山后,为了不连累儿媳张氏,自缢而亡,最后被册封为贤德夫人。
宝剑(非人物):《水浒传》中为宝刀,是林冲误入白虎堂的导火索。《宝剑记》中为宝剑,林冲祖公公林和靖传留,是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一条主线。
鲁智深:《水浒传》中原为经略府提辖官,后出家为僧,与林冲交情甚厚,林冲落难后,曾在野猪林救下林冲,并护送林冲至沧州。《宝剑记》中亦如是。
公孙胜:《水浒传》中为梁山一百单八将之一,绰号“入云龙”,他在落草梁山之前与林冲并未结识。《宝剑记》中官拜参军,与林冲为好友,曾在沧州救下林冲,后弃官。
王婆:《水浒传》“林冲落草”故事无此人。《宝剑记》中为林冲家邻居,林母自缢身亡以后,曾给予张氏极大帮助。
王进:《水浒传》中为东京禁军教头,“九纹龙”史进的师父,因得罪高俅,逃至延安府。《宝剑记》中亦为东京禁军教头,后违抗高俅命令放走张氏与王婆,逃至延安府。
高俅:《水浒传》中原为一浮浪子弟,后成太尉,深得皇上宠幸,无恶不作。《宝剑记》中亦如是,其结局与《水浒传》不同(后面详述)。
高朋:《水浒传》中的高衙内,号“花花太岁”,高俅的干儿子,曾调戏张氏。《宝剑记》中叫高朋,其他事迹同《水浒传》。
陆谦:《水浒传》中为高俅府内虞侯,林冲好友,后设计陷害林冲,被林冲刺死在山神庙。《宝剑记》亦如是。
富安:《水浒传》中为高俅府内虞侯,后设计陷害林冲,被林冲刺死在山神庙。《宝剑记》亦如是。
(二)故事情节内容的继承
除了主要人物设置方面,在故事情节上,《宝剑记》也继承了《水浒传》很多内容。《水浒传》第七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主要写高俅设计陷害林冲。高衙内在岳庙里调戏张氏未果后,又派心腹陆谦将张氏诱骗至陆谦家里进行调戏,此次又未成功,高衙内便忧郁成疾,太尉高俅为满足儿子心愿,便设下计策,以比刀为名将林冲骗至府内白虎节堂。《宝剑记》第九出至第十一出承袭《水浒传》中这一故事,写的也是林冲误入白虎节堂,其基本情节与《水浒传》相类似,但事情起因与《水浒传》出入颇大(后面详述)。另外,《宝剑记》中的这一情节又增加了些许内容,在林冲误入白虎节堂之前,作者巧妙增设了第十出“解梦”,这一出为接下来的事情剧变作了铺垫性的预知。
《水浒传》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写林冲被高俅陷害后发配沧州,由董超、薛霸两名官差押解,因两人收受高太尉贿赂,便企图在野猪林杀掉林冲,幸好鲁智深赶上,才救得林冲一命。《宝剑记》第十六出至第二十出也有此内容。稍有不同的是,关于林冲刺配沧州的原因,《宝剑记》较《水浒传》又有了更为详细的补充。《宝剑记》第十六出至十八出中提到,林冲在误入白虎节堂后被关押在大牢,张真娘救夫心切,瞒着婆婆写下冤词,去冤鼓楼前自刎,朝廷这才批准开封府尹杨清办理此案。正所谓“高殿师纵子淫乱,杨府尹决断分明”[1]751,林冲这才幸免于死,被发配至沧州从军。
《水浒传》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是林冲个人人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林冲个人性格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小说讲了林冲在发配沧州以后,再次遭到高俅等人的陷害,陆谦、富安贿赂沧州牢城管营、差拨,设法派林冲去看守大军的草料场,因大雪压塌草厅,林冲只好到附近的山神庙暂住一夜,却凑巧听到了陆谦、富安等人的谈话,得知自己差点被他们害死。当夺命的利剑再一次指向自己,压抑在林冲内心深处的仇恨终于得到了空前爆发,他怒不可遏,提枪杀死三人,最后在走投无路之下落草梁山。《宝剑记》第三十三出写此情节,与《水浒传》相比,其过程略有删减,事情起因则较为详细,《宝剑记》第三十出至三十二出,详细交代了此次林冲被害的具体原因,高朋欲得到张真娘,他为了让真娘对林冲死心,就派陆谦、富安去沧州加害林冲。传奇详细写了他们密谋的整个过程,这在《水浒传》中是看不到的。
(三)“忠奸斗争”主题思想的继承
“忠奸斗争”是《水浒传》的重要思想之一,其突出表现为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以宿太尉和张叔夜为首的忠臣力主对梁山起义军进行招安,以高俅、童贯等为代表的奸臣竭力反对招安。《水浒传》第八十二回写道:“寡人闻宋江等,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与国家出力。都是汝等嫉贤妒能之臣壅蔽,不使下情上达,何异城狐社鼠也!”[2]1024当梁山起义军正式接受招安以后,朝廷方面又出现了信任这支起义军与消灭这支起义军截然相反的两派,“忠奸斗争”仍在持续。《水浒传》第八十二回,枢密使童贯给皇帝奏道:“这厮们虽降朝廷,其心不改,终贻大患。以臣愚意,不若陛下传旨,赚入京城,将此一百八人尽数剿除,然后分散他的军马,以绝国家之患。”[2]1036这一计谋恰巧被忠臣宿太尉得知,宿太尉上奏皇帝让梁山起义军去征辽,这才解救了这场危机。待征辽结束后,宋江等梁山好汉本该受到朝廷封赏,却遭到了蔡京、童贯等人的拖延。后又征田虎、征王庆,直至最后征方腊成功后,宋江等人才受到封赏。尽管如此,“忠奸斗争”仍不能作为整部《水浒传》的主旨,梁山好汉与贪官污吏、地主豪绅的对立更多的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与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对立,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忠奸斗争”的表现。因此,“忠奸斗争”只能算是《水浒传》主要思想之一。
继《水浒传》之后,明代李开先的《宝剑记》承袭了“忠奸斗争”这一思想。其第一出中的【鹧鸪天】已表明了主旨:“一曲高歌劝玉觞,闲收风月入吟囊。联金缀玉成新传,换羽移宫按旧腔。诛谗佞,表忠良,提真讬假振纲常。古今得失兴亡事,眼底分明梦一场。”[1]751《宝剑记》中的林冲是忠良之士的代表,他幼承父业,习读诗书,曾在军门立下大功,官任征西统制之职,“因见圆情子弟封侯,刑余奴辈为王,小人拨弄威权,盗窃名器”[1]752,就上书弹劾高俅、童贯等奸臣,结果被贬为巡边总旗。后来,幸蒙张叔夜举荐,才做了禁军教师。虽然他官卑职小,却依然心怀天下,胸中充满了无限的报国热情。他痛恨在朝高俅等人“拨置天子采办花石,荒淫酒色,宠幸妓女李师师,致使百姓流离,干戈扰攘”,虽“每怀苦谏之心”,却“愧少回天之力”[1]757。在妻子的劝说下,他决定再次上书弹劾高俅等人。表曰:
提典羽林军提辖官臣林冲谨奏……今宣尉使童贯,乃刑余小人;太尉高俅,实斗筲末器。滥叨重任,不输蹇蹇之忠;久玷清班,大肆营营之计。奸细结为心腹,贤良视若寇仇。欺君误国,奸比赵高;擁众盗兵,权倾董卓。异卉珍禽,蛊惑圣志;土工木作,靡费民财。以致星彗冲天,旱蝗遍地。祸将不测,事岂宜迟?伏愿皇上,或加两观之诛,或效三苗之竄,以迴天变,以答人心。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1]762
这篇表章言辞犀利,矛头直指高俅、童贯等奸臣,忠奸斗争十分激烈。可是,这次上书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高俅和童贯非但没有收敛,双方的斗争反而愈演愈烈。《宝剑记》第十一出,写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第二十出,写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第三十三出,写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第五十出,写高俅父子被碎尸万段。以林冲和高俅的斗争为代表的忠奸斗争一直不断持续着,其作为主旨思想,贯穿于整部传奇的始终。一些曲词也可以为证:
第二出,【醉翁子】:豪放,匣中宝剑无尘障,知何日诛奸党?自奖,虽不能拜将封侯,也当烈烈轰轰做一场。[1]753
第四出,【武陵春】:弓挂扶桑无用处,英雄人已白头。虎斗龙争个个休,不如一笑得封侯!堪恨当年奸佞者,接踵乱神州。胡尘风起暗龙楼,长叹为君忧。[1]757
第二十出,【玉交枝】:苍天听启:愿林冲死为厉鬼,森罗殿上诛奸辈。那时节去报亲帏。千里英魂不复归,数茎残骨终抛弃。[1]789
第五十出,【滚绣球】:你有秦赵高指鹿心,屠岸贾纵犬机。待学汉王莽不臣之意,欺君董卓燃脐。但行处弦管随,出门时兵甲围。入朝中百官悚畏,仗一人假虎张威。望尘有客趋奸党,借剑无人斩佞贼,一任你狂为。[1]844
二、《宝剑记》对《水浒传》的创新
《宝剑记》是由《水浒传》改编而来,除了在人物设置、故事情节、忠奸思想等方面继承了《水浒传》中的很多内容之外,《宝剑记》又有所创新。这使《水浒传》“林冲落草”的故事以一种新型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耳目一新,久久难忘。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人物形象的蜕变
《宝剑记》中的林冲较《水浒传》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由被动忍让到主动出击。《水浒传》中的林冲重在隐忍,他是沉默的,低调的,抑郁的,只要敌人不危及自己的生命,他也绝不反击。有人认为,“林冲一生,只是一个怕字”[3],这句话很准确地概括了林冲个人的性格特征。《水浒传》第七回,当林冲看见有人调戏妻子,正要打时,“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2]99。这里的“软”不仅仅是写林冲手软,更从侧面烘托出林冲性格的软弱。林冲在被贬至沧州的路上,受尽了董超、薛霸的折磨,他也一味地忍受着,不敢有丝毫反抗。《水浒传》中的林冲只有两次大的抗争,一是第十回,写林冲杀死陆谦、富安等人,一是第十九回,写林冲在梁山火并王伦,而这两次抗争也都是林冲被逼到绝境时的无可奈何之举。《宝剑记》中的林冲却发生了质的蜕变,面对黑暗势力的压迫,林冲由被动忍让变为主动进攻。《宝剑记》第二出:
下官姓林名冲……因见圆情子弟封侯,刑余奴辈为王,小人拨弄威权,盗窃名器,因谏言一本,乃被奸臣拨置天子,坐小官毁谤大臣之罪,谪降巡边总旗。幸蒙张叔夜举荐,做了禁军教师,提辖军务。[1]752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冲曾因看不惯奸臣的所作所为,向皇上谏言,结果却以“毁谤大臣之罪”被贬官。即便这样,他也并没有向黑暗势力妥协,《宝剑记》第六出,写林冲再次上奏弹劾高俅,当黄门大人劝阻他时,他却言道:“我林冲职分虽微,圣上宠恩难报,今日死且不避,惧那奸党怎的?”[1]763这与《水浒传》中软弱隐忍的林冲形象产生了鲜明对比。
第二,由草莽英雄到忠臣义士。关于这一点,今人评价道,《宝剑记》把“草莽英雄的性格士大夫化了”[4],这里指的正是林冲。《水浒传》中的林冲是一个武夫的形象,他性格急躁、冲动、好武,一见到鲁智深就要与之结为兄弟,一见到娘子被调戏就要动手打人,一见到宝刀就忘记了家中的烦恼。他没有什么大局观念和雄心壮志,只想与妻子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他与高俅的矛盾是源于高衙内调戏林娘子,实则是属于自己与高俅的私人恩怨。与之不同的是,《宝剑记》中的林冲成为了一名心忧天下的忠臣义士,他胸怀壮志,有着较高的政治理想抱负。他与高俅的矛盾也不是出于私人恩怨,而是源于“忠奸斗争”的不同立场,林冲是朝廷忠臣的代表,他曾先后两次弹劾高俅等奸臣,其出发点是为君为国。到了第三十七出“夜奔”,林冲被逼至绝境时,他也是“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1]817。即便是身至梁山,林冲的愿望也是“专望招抚,再报君恩”[1]825。他记恨的只是高俅、童贯等危害朝廷的奸臣,对于皇帝却并没有丝毫怨恨,而且一直称其为“明君”,这是中国古代“忠君”思想在封建士大夫心灵世界的深刻渗透,也从侧面反衬出林冲忧国忧民的高贵形象。
《宝剑记》中的张氏较《水浒传》有了更大变化。在《水浒传》中,张氏常以“林娘子”代指,她漂亮贤惠,看重贞洁,出场次数虽少,却是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人物。因为她漂亮,被高衙内调戏,才有了林冲误闯节堂一事,并最终逼得林冲走投无路,落草梁山。聂绀弩先生说“《水浒》全部都是轻视妇女的”[5],恐非虚言。到了李开先《宝剑记》,张真娘(林娘子)形象已较《水浒传》更趋深刻、形象、具体化了,她贤惠端庄、爱夫敬母、深明大义,在林冲担心官小言轻、有心上谏却又犹豫不决时,是她劝说夫君要为国尽忠、正直敢言;在林冲被骗入节堂、打进牢狱之时,是她瞒着婆婆写就状词、击鼓诉冤;在婆婆身死、无钱下葬之时,是她典卖金钗、为母送终。她曾自尽三次,虽都被救下,却给人以极大的心灵震撼。第一次是为夫申冤,期望能借自己的死引起朝廷重视,为林冲洗脱冤屈;第二次是不甘被高衙内欺辱,为保全名节寻个自尽;第三次是千里寻夫不成,孤苦无依,宁愿选择自尽与家人团聚。《宝剑记》中的张真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丰富饱满、个性鲜明的忠贞人物,俨然中国古代封建女性的楷模。这其实反映的是李开先个人的封建价值取向,也是其有意为之。
(二)情节脉络的调整
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脉络方面,《宝剑记》对《水浒传》虽有继承,但也有所调整。先看《水浒传》中“林冲落草”情节的发展脉络:
高衙内调戏张氏——林冲误入白虎堂——林冲刺配沧州——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林冲棒打洪教头——林冲风雪山神庙——林冲雪夜上梁山。
《宝剑记》中的内容较《水浒传》更加丰富,根据情节发展的先后顺序,可大致勾勒出一条主线:
宝剑出匣——林冲上奏——林冲解梦——误闯节堂——林冲入狱——真娘探监——击鼓诉冤——刺配沧州——鲁达救兄——真娘受辱——高朋害病——富安献计——林冲除奸——林冲夜奔——林母自尽——真娘葬母——义聚梁山——真娘求死——锦儿代嫁——锦儿自尽——千里寻夫——义释真娘——梁山起兵——真娘出家——梁山招安——冤仇终报——破镜重圆。
相较来看,《宝剑记》的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其继承了《水浒传》“林冲落草”的发展主线,同时又有所调整和增删,比如高衙内调戏张氏一事,在《水浒传》中位于故事发展的开端,其对整个故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宝剑记》中,这件事却被安插在林冲刺配沧州之后,其地位和影响已较《水浒传》大大削弱了。再比如《宝剑记》中“林冲上奏”“真娘探监”“击鼓诉冤”“林母自尽”“真娘葬母”“锦儿代嫁”“千里寻夫”“真娘出家”等情节,在《水浒传》中是看不到的,其对丰富情节内容、填充人物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中心矛盾的位移
《水浒传》“林冲落草”这一情节的中心矛盾是林冲和高俅之间的矛盾,矛盾的根源是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调戏林冲的娘子张氏。高俅身为朝廷重臣,林冲的顶头上司,当他得知儿子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张氏以后,不仅没有对儿子进行严加管教,反而纵容其子的所作所为,诸如诱骗林冲至白虎节堂,买通董超、薛霸杀害林冲,火烧草料场等事,这都是在太尉高俅的默许下进行的。林冲与高衙内之间的矛盾就转成了与高太尉之间的矛盾,其作为这段故事的中心矛盾推动着情节一步步地发展。从表面来看,《宝剑记》的中心矛盾与《水浒传》相类似,矛盾双方都是林冲和高俅。但是,两者却有实质性的区别。在《水浒传》中,林冲与高俅的矛盾源于高衙内调戏张氏,实际上为两者私人恩怨,属于“小我”。而《宝剑记》中的林高矛盾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林冲和高俅两个人,而扩展为以林冲为代表的忠臣和以高俅为代表的奸臣之间的矛盾,其源于忠奸两大势力的相互抗争,属于“大我”。《宝剑记》第二出【醉翁子】:“豪放,匣中宝剑无尘障,知何日诛奸党?自奖,虽不能拜将封侯,也当烈烈轰轰做一场。”[1]753匣中“宝剑”即暗示着林冲自己,扫除奸党、为国建功是林冲的政治理想,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曾先后两次弹劾高俅、童贯等奸臣,其出发点是为国为君,并不掺杂与高俅个人的恩怨情仇。高朋调戏张真娘一事也发生在林冲被贬沧州之后,此时的林冲并不知情。也就是说,《宝剑记》中的林冲是一心为公的,他与高俅等奸臣的矛盾是源于忠奸斗争两大阵营的不同立场,中心矛盾的根源和实质已较《水浒传》有了极大转变。
(四)起因结局的颠覆
《宝剑记》“林冲落草”故事的起因与结局较《水浒传》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是《宝剑记》创新的又一重要方面。众所周知,《水浒传》中“林冲落草”故事的起因源于高衙内调戏林冲的娘子张氏,林冲与高俅父子结下冤仇,这才有了“豹子头误入白虎堂”“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等情节。《水浒传》中这段故事的结局并不美满,林冲在刺配沧州之后再没见过妻子张氏,后在随梁山大军征讨方腊之时,染上风瘫,留在杭州六和寺养病,半年后不幸病故。妻子张氏被高太尉威逼亲事,为保全名节,自缢而死。高俅、童贯等依然在朝为官,享受着荣华富贵。《宝剑记》与《水浒传》明显不同,其起因于“林冲上奏”。他向皇帝谏言,高俅、童贯等奸臣大兴土木,采办花石,“搔动江南黎庶,招致塞上干戈”[1]762。这件事情得罪了高俅、童贯等奸臣,他们便一起设计陷害林冲。《宝剑记》的结局与《水浒传》截然相反,梁山在接受朝廷招安后,林冲被加官二级,后又被封为都统,兼管军务破虏将军,妻子真娘被封为洛阳郡夫人,女使锦儿被封为义烈贞姬,林母被封为贤德夫人,高俅父子落得个“割腹剜心,碎尸万断”[1]844的下场。林冲大仇得报,且能与妻子真娘破镜重圆,获得封妻荫子的高级别待遇,这与《水浒传》是截然不同的。
三、《宝剑记》改编的进步性与现实意义
改编是一次新的创造,中国古代的很多戏曲都是通过其他文学艺术样式改编而成的,李开先《宝剑记》就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吕天成《曲品》评:“才原敏赡,写冤愤而如生;志亦飞扬,赋逋囚而自畅。此词坛之飞将,曲部之美才也。”[6]从某种程度上说,由《水浒传》改编而来的《宝剑记》是有其进步性与现实意义的,它在明代戏曲史上的价值不容小觑。
首先,《宝剑记》凸显出明中叶反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思潮。与《水浒传》“官逼民反”的主题相比,《宝剑记》的主题主要表现为“官逼官反”,两者虽只一字之差,其折射出来的反封建性程度却是天壤之别。由“民”到“官”,其造反的性质已发生极大转变。诚然,《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也有朝廷官员在内,如林冲、关胜等,但下层平民占据着绝大多数,其归根到底仍是一场反抗北宋封建专制统治的农民起义。《宝剑记》中的反封建性则主要集中于林冲一个人身上,他的身份是“官”,而非“民”。概言之,林冲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是有着较高社会地位的。那么,从原则上来讲,林冲与高俅等人应属于同一个阵营,是不应该有什么冲突的。可是,当林冲看不惯高俅的作为时,他依然上书弹劾高俅,高俅也三番五次设计陷害他,直至逼反林冲。试想:连官员都忍受不了朝廷昏聩起身反抗,下层民众又怎能忍受?这就给人以很大冲击,其表现出来的反封建性也就更加强烈。
其次,《宝剑记》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个体生命的思想解放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明中叶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开始萌芽,人们越发注重个性的张扬与自我意识的表达。这与明代兴起的“阳明心学”也有很大关系。“阳明心学”肯定人欲,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兴起之后,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接受,长期以来被“程朱理学”束缚的人欲终于得到了空前的释放,这对明代后期的思想大解放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李开先显然受到了这一影响,他在《宝剑记》中塑造的林冲就是个“个性解放”的角色。林冲身为朝廷官员,居然起兵造反,公然与朝廷对抗,当他带兵包围汴京时,朝廷迫不得已降旨招安,为了表现诚意,还将高俅父子解送军前,让林冲报仇。在与朝廷谈判招安的事情上,林冲显然握有更大的主动权,《宝剑记》第五十出,当林冲见高俅父子仍未解来时,言道:“左右,传吾将令,兵不许前进,亦不许后退。看有什么人来。”[1]842林冲的强势态度倒像是在“逼宫”,这在古代封建社会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是不可想象的。《宝剑记》如此刻画林冲形象,显然是一次挑战权威、突破传统的深刻实践,同时也是一次对个性解放思想的有力弘扬。
再次,《宝剑记》是李开先个人心灵世界的直接映现。李开先所处的时代,正值明代正德、嘉靖年间,这段时期的社会政治极其黑暗,前有宦官刘瑾专权,后有夏言、严嵩父子把持朝政,他们结党营私,无恶不作。李开先为官以后,清正廉明,还曾投身于反权奸的斗争,后被免官打回原籍。尽管如此,李开先仍是“寸心犹恋阙”,他依旧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朝堂为国效力,这与《宝剑记》中的林冲“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1]817的性质是一样的。雪簑渔者在《宝剑记序》中写道:“是以古之豪贤俊伟之士,往往有所托焉,以发其悲涕慷慨抑郁不平之衷。”[1]749显然,《宝剑记》就是李开先抑郁不平、复杂矛盾的心灵映射,作品中的林冲实际上就是现实中的自己,当官,罢官,又寄希望于复官,这正是李开先内心所企望的。姜大成在《宝剑记后序》也说道:“古来抱大才者,若不得乘时柄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岁月,暗老豪杰,奚不可也?”[1]852李开先所谓的“乐事”就是创作传奇《宝剑记》,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其创作《宝剑记》的动机。
李开先借“水浒”故事成功改编了一部传奇《宝剑记》,其与梁辰鱼的《浣纱记》、王世贞的《鸣凤记》齐名,在明代曲坛占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并称“明中叶三大传奇”。这三部传奇中“鲜明的忠奸对立观念、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成为明清传奇的重要主题,遗泽后世,厥功非浅”[7]。尽管如此,《宝剑记》也是有其不足之处的,前人评价其“生硬不谐”,“以致吴侬见诮”[8],也有人评价“且此公不识炼局之法,顾重复处颇多”[9],这些评论虽也有失考量,但还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