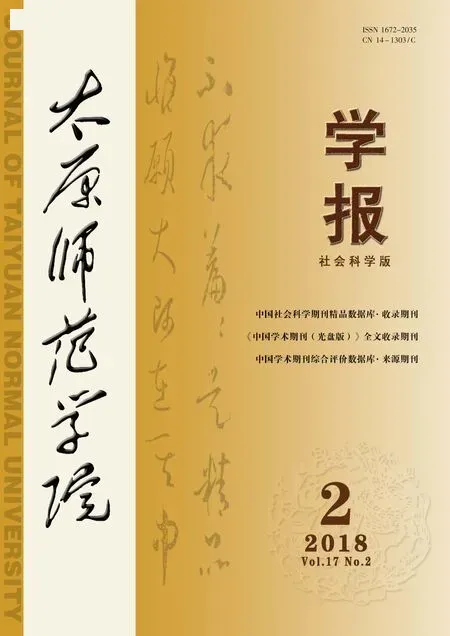和而不同:试论中外艺术创作中的共鸣与差异
(辽宁大学 艺术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当我们漫步在烟波浩渺的世界艺术长廊里,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面对一部特定的世界艺术精品时,其具体的题材、主题、人物、框架,或者一个片段、一个细节、一个结尾,会使人产生似曾相似之感,从而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它的精神兄弟——在另一个迥异的历史时空的一部作品。因为人类共通的精神世界,不同的生活体验也能造就相似的精神感悟。不难发现,在不同年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前提下,艺术家们的创作中存在着高度相似的情况,但只是相似,而不是相同。通常来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后来的艺术家有意向前人借鉴之后进行的创作,如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王实甫的《西厢记》、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来源于英国古老传说,一般认为莎士比亚根据已有无名氏的剧作改编而成;王实甫创作《西厢记》之前有元稹的《莺莺传》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取材于《新约圣经》,在达·芬奇之前,这个基督教圣经中最重要的故事几乎被所有宗教画家描绘过。另一种情况是艺术家们并没有彼此沟通,或者谁借鉴了谁、谁影响了谁,而仅仅是不约而同的巧合。
事实上,这种创作相似性的存在可以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来解释。“和而不同”是指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和”是指有差别的、多样性相似或统一,有别于“同”。这一传统文化精神也是一种美学精神,即肯定一种多样化的统一。在艺术世界里,“同”是雷同,是遭到鄙弃和否定的,“和”则是作品追求的理想化境界。“和而不同”可以体现在同一个作品的内部,如《水浒传》中,同样是描写小叔子杀掉淫荡嫂子的事件,既有武松杀潘金莲,又有石秀杀潘巧云;同样是勇士只身打虎的情节,既有武松打虎,又有李逵打虎。“和而不同”也体现在不同作品之间,如曹禺的话剧《日出》、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与好莱坞电影《魂断蓝桥》,三者都以一个沦落风尘的妓女为主人公,陈白露、玛格丽特和玛拉,都曾是纯洁善良、对未来充满浪漫幻想的少女,但残酷的社会现实逼迫她们走上歧途,最终以自杀终结悲剧命运。无论哪种“和而不同”,事件、人物形象或命运的“和”都不能掩盖作品之间丰富的差异性。即便故事框架相似,但其中具体的人物、情境、事件、细节、环境等等,都各具时代、民族、文化背景或细节的独特性,我们看到的是同中有异的绝妙境界,读者丝毫不会有雷同之感。本文将关注这种创作的相似性,通过比较,探寻不同作品更丰富的意义世界。
现象一:《樱桃园》与《狗儿爷涅槃》中历史的车轮声
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戏剧《樱桃园》(1903年),描写了一个美丽而庸俗的女地主安德列夫娜,她只知享乐,追逐情人,面对樱桃园将被拍卖的现实无所作为。作品像一首忧伤的挽歌,预示了俄罗斯封建社会的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作品的结尾,在拍卖庄园之日,安德列夫娜还不知死活地在家里举行舞会,拍卖消息传来她又痛哭流涕,最后再次远赴他乡追逐情人。作品结尾写道:“传来一个遥远的、像是来自天边外的声音,像是琴弦绷断的声音,这忧伤的声音慢慢地消失了。出现片刻宁静,然后听到砍伐树木的声音从远处的花园里传来。”
“遥远的、像是来自天边外的声音”,“琴弦绷断的声音”,打断了得过且过、庸俗苟且的女地主们的现实生活。这声音像是突然发出,来自历史深处,或来自神秘的宿命,它对安德列夫娜来说似乎是措手不及的,但却是必然的。当即将被新时代所淘汰的地主阶级,在重重危机中还悠然自得、奢侈糜烂之时,历史的车轮不会为他们暂驻、停留,在“砍伐树木的声音”中,它们隆隆驶来,坚定且无可挽回。“砍伐树木的声音”,既是实指樱桃园的毁灭,更是象征历史车轮的无情逼近。
应该说,契诃夫对于樱桃园的未来是充满忧虑的。被拍卖的樱桃园被新兴资本家罗伯兴收购,他将毁掉樱桃园建起别墅。樱桃园不仅代表着地主阶级的没落,还代表着一种浪漫、诗意、温情的田园生活,摧毁它的是追求金钱、利润的资本社会,后者无情地抡起斧子,砍伐树木,破坏生态。尽管被时代的车轮碾过的地主阶级的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未来的前景却不容乐观,甚至充满了陷阱和危机,这代表着作家的矛盾心态。
樱桃园里的历史声响同样出现在锦云的话剧《狗儿爷涅槃》(1986年)中。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探索戏剧中的代表作品,剧本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有着沉重精神负担的老中国儿女“狗儿爷”形象。狗儿爷的父亲当年“跟人家打赌,活吃一条小狗儿,赢人家二亩地,搭上自个儿一条命”,“狗儿爷”名字的来历暗含着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强烈渴求和历史命运的悲剧性。背负着延续千年的对土地、粮食、大门楼的生命欲求,“狗儿爷”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抢收了地主的芝麻地,在解放区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下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和房产,这段时期是“狗儿爷”人生辉煌的顶点。然而随着“大跃进”和“合作化”的到来,“狗儿爷”的土地、家畜又被收归集体所有,“狗儿爷”被逼疯。新时期到来后,农民等来了好政策,“狗儿爷”的儿子大虎,走上了与父辈不同的路,开始开矿办厂,并准备把妨碍通车的大门楼推倒,这遭到“狗儿爷”的反对。对“狗儿爷”来说,当年地主家的大门楼是自己的悲惨的发家史,是人生梦想实现的标志,但当新旧两代人为此冲突时,最终妥协的是“狗儿爷”,他放了一把火烧掉了门楼。剧本的结尾写道:
满台大火。巍巍门楼被火焰吞没。
人声、马达轰鸣声,雄浑地交织在一起,直响到终了。
有人喊:“推土机来啦!”“快救火呀!”
陈大虎、祁小梦上,二人的神色象是刚刚从火里钻出来。
陈大虎老爷子呢?
祁小梦走了。
陈大虎菊花青?
祁小梦牵去了。
陈大虎快——你和连玉大叔张罗救火,收拾利落,天亮推土机就要来了,一分钟也耽误不得。
祁小梦你呢?
陈大虎找爹去!(快步跑下)
祁小梦去哪儿——
传来陈大虎的声音:“风水坡——”
火渐熄。
马达声大作。推土机隆隆开入。
大火烧掉旧门楼,也埋葬了中国农民的旧时代,同时也照亮了未来的美好新生活。新的历史时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农民过上新生活,剧作家对此充满乐观的期待,它必定是热闹、人声鼎沸的,“人声、马达轰鸣声,雄浑地交织在一起”,象征着新时期的农民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终于可以实现几千年来的发家梦。最后一句“推土机隆隆开入”,是不可阻挡的时代车轮,它开启了新的时代,代表着光明、希望。在这背后,“狗儿爷”与儿子大虎形成对比,而事实上这体现出剧作家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作为时代“新人”的大虎们会在未来的生活中自由驰骋,但“狗儿爷”却并不会实现向新人的过渡,只能作为新旧过渡的桥梁存在,他更多的存在于过去。
契诃夫和锦云都在作品中用象征的手法预示了时代的车轮、历史的车轮迅疾向前迈进,不可逆转。但两相比较的话,却会发现他们对此迥然不同的态度:契诃夫满腹忧虑,樱桃园里“砍伐树木的声音”带动起读者哀怨的情感,几乎促使人想要去阻止。而锦云笔下“推土机的隆隆声”则是毫不迟疑的,充满乐观积极的态度,使人恨不得再去助推。联系到两位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作品中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则不难理解这一基调上的差异。契诃夫生活在19世纪后期沙皇俄国的反动统治时期,剧作家更多的是批判现实;锦云活跃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繁荣时期,剧作家更多的是肯定现实。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安德列夫娜代表着没落的地主阶级,哀其不幸中更多的是嘲讽;锦云笔下的“狗儿爷”则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他有保守的一面,但更多地承载着中国农民在旧时代的血泪,对农民主人公的基调,不是嘲讽,而是热爱,因为“狗儿爷”就是我们民族的父辈。
现象二:《亨利四世》与《河边的错误》中疯癫者的现代隐喻
皮兰德娄的戏剧《亨利四世》与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中都出现了疯癫者的形象,两位作家最终都采用以非理性的疯癫来应对理性的现代社会的方式,在思想深层存在高度相似性。
皮兰德娄是意大利戏剧家,代表作《亨利四世》(1922年)为他带来了享誉世界的声望。剧本描写二十年前,主人公在一次庆典中装扮成11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当他骑马接近自己所热爱的女子时,马被情敌刺伤,他落马昏迷。苏醒后他发了疯,并以亨利四世自居。亲友把环境布置成皇宫的样子,雇佣“枢密顾问”陪伴他。剧本开端,他已恢复神志,他痛苦地发现情人已被情敌夺去,自己虚度了年华,“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完了”,“好像一头饿狼赴了已散的宴席”。两鬓斑白、心灰意冷的他,深感生命虚度,不禁怒火中烧,用剑将情敌刺伤。他清醒地意识到,为避免刑罚,自己将不得不继续扮演一个疯子的角色——做他的“亨利四世”。
皮兰德娄制造了相反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主人公疯癫非理性的世界,另一个是周围貌似文明理性的世界。可这两个世界又是颠倒的:貌似理性的文明世界由卖淫的娼妇、下流的嫖客和骗子老手组成,他们在生活中带着假面具干着丑恶勾当;主人公的疯癫世界里充满胡言乱语、嬉笑怒骂,事实上却代表着经受现代文明禁锢的人,在无穷痛苦之中挣扎、对自己命运的无从控制以及对自由的渴望。由此,皮兰德娄通过疯癫者的世界的真实性隐喻了现实世界的荒诞本质。
主人公“亨利四世”假装疯癫的精神历程,与余华小说《河边的错误》中警察马哲高度相似。《河边的错误》(1987年)是先锋小说家余华的实验系列作品之一,小说虚拟了一个侦探故事:在神秘的河边,么四婆婆惨死。负责此案的警官马哲经过重重波折,发现杀人犯就是么四婆婆收留并悉心照顾的疯子。因为在法律上无法将疯子绳之以法,疯子逍遥法外且又犯下多起杀人惨案,忍无可忍的马哲开枪打死疯子,为逃避法律的制裁,在妻子和局长的哀求下承认自己是疯子,进了精神病院。疯子连环杀人却总是能够免于刑罚,疯子被警察枪毙,警察最终成为清醒的“精神病人”,这是现实社会理性的非理性呈现,这里有对“文革”的暗喻,所谓的社会文明秩序只是表象,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真正占居支配地位的是无序和混乱,小说最终所体现的是对世界“荒诞”本质的揭露。
作为刚刚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皮兰德娄,与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余华,有着相似的对理性的怀疑,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着对现实的悲观感悟:两个主人公最终都为了躲避惩罚,而假装疯癫,说明人类的理性在非理性的疯癫面前束手无策,即便是作为人类理性产物的法律,也对一个非理性的行为失去了惩恶扬善的作用。由此可见,我们素来坚信和依赖的客观世界是多么脆弱,支撑这个世界的道德规范、价值判断和理性思维,竟在突如其来的疯子造成的意外灾难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所不同的是,《亨利四世》中的主人公将疯狂和清醒集于一身,他经历了从清醒到疯癫,再到清醒,最终假装疯癫的过程,也就是主人公最终同时具备了疯癫和清醒,并用疯癫战胜外部理性最终获得了胜利。《河边的错误》中疯癫者的形象则由两个人分饰,开始时疯子代表疯癫,警察代表理性,他们各自独立,后来警察枪杀疯子,疯子死去,但疯狂的因子并未消除,而是转移到警察身上,枪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疯癫,所以剩下的就不再是一个理性的警察,而是疯癫和理性合而为一的警察,疯癫并不能被消除,它仍然继续,并实现了对所谓理性社会的胜利。
从文明的视域来看,与其说疯癫是病理现象,不如说它是文明的产物,是一种话语的建构。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鲁迅笔下的狂人,都是经典的疯癫者。疯癫者的形象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为充满斗争和痛苦的世界是根据像尼采、凡·高、阿尔托这样的人的作品大量涌现这一事实来评估自身的。”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这段结语揭示了疯癫与世界之间复杂的胶着关系。在皮兰德娄和余华的笔下,亨利四世和警察马哲都陷入疯癫给理性设置的陷阱,理性在其中迷失并最终陷入疯狂。真疯子和假疯子的隐喻内涵,直指世界本质的荒诞,预见了人类的生存现实,并对理性自身进行消解与追问。
现象三:《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旧约全书》与《高加索灰阑记》中的“二母争子”
“二母争子”的故事原型,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和现代德国戏剧文化中都曾出现过,除了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较明显地受到中国元代戏剧家李潜夫的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的影响外,基本未见相互影响的痕迹。这说明世界文化在发展中各自有自己丰富的文化土壤,结出的是迥然有别的智慧果实。
《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中记述了一个二母争子的故事,妓女张海棠嫁给土财主生下一个儿子,财主大妻不能容忍,与奸夫合谋毒死财主,又为争夺遗产谎称儿子是自己生的,张海棠不从。这宗争儿案由包拯审理,他叫人用石灰画成一个阑,把孩子放中间,令张海棠和大妻拽拉,谁把孩子拽出来,谁就是孩子亲生母亲。大老婆狠命拉扯,张海棠怕扭断孩子的手臂,不敢用力,结果大老婆拽出了孩子,包公也看出了谁是孩子的亲妈,作出了公正判决。
这一中心情节与《旧约全书》中的所罗门王断案颇为相似:两个女人争夺一个孩子,都说自己是孩子生母,所罗门王说:“把这孩子劈成两半,一个人分一半也就是了。”一个女人大惊失色,恳求道:“把这孩子给她吧,杀不得!”另一个女人则情绪稳定。所罗门王因此判断出谁是孩子的生母。
李潜夫戏剧中“画阑拉子”的安排更富于动作性和观赏性,适合戏剧舞台演出。而《旧约全书》中“劈成两半”的语言威慑,则更适应宗教教义的传达。因为中心情节的相似,曾有学者认为李潜夫受到《旧约全书》的影响。而事实上世界各国文化中,如《圣经》《古兰经》《佛经》,以及中国东汉时期典籍《风俗通义》中都有类似事件记载,所以几乎无法追溯到底李潜夫受到哪个源头的影响,我们关注的是李潜夫之前还没有人将这一故事铺排成一个独立的复杂的艺术作品,有的仅仅是只言片语的简略记录。李潜夫的《灰阑记》着重传达的是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价值观念,这在《旧约全书》中是并不突出的。强调血缘亲情的无可取代,直到现在也仍然在东方民族中有稳定的表现。
布莱希特是一位与中国文化渊源颇深的德国戏剧家,他的戏剧《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以及他的举世闻名的“间离”“陌生化”戏剧理论,都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其中《高加索灰阑记》即是受到李潜夫《包待制智赚灰阑记》的启发,但又生发出完全不同的深刻内涵。在格鲁吉亚的一场暴乱中,总督夫人在自己逃跑时把儿子扔给女仆格鲁雪。为了保护孩子,格鲁雪多次死里逃生,并不惜牺牲婚姻幸福去为他找个父亲,没有血缘关系的格鲁雪与孩子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母子感情。天下太平后,总督夫人为了遗产想从格鲁雪那里夺回孩子,法官也采用了包拯的办法,这时孩子的亲生母亲即总督夫人却不顾孩子死活使劲拉扯,格鲁雪以一颗慈母的心不忍孩子受苦而放手。法官最后判定真正疼爱这个孩子的女人才是孩子的母亲。在布莱希特看来,孩子不应判给那个毫无母性的亲生母亲,而应判给那个为他历经磨难没有血缘关系的格鲁雪。这里表达的价值观是,母爱不是天然的,世间的一切权利也都不是天赋的,正如山川土地不应属于地主,而应该归于能够耕种土地、热爱土地的人,孩子也理应属于具有慈母心肠、能够保护他呵护他的母亲。所以这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布莱希特在孩子、母亲与土地、农民之间作了置换和隐喻,借此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和立场。
三个“二母争子”的故事,在共同的情节下生发出不同的环境、人物、事件以及思想观念,这必然是由时代、民族、文化的差异,以及阶级、政治的差异造成的,而显然,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将这个故事原型提升到更高远更深刻的艺术等级,超越了血缘关系的母子之爱更恢宏,体现出更广阔的社会价值观念,同时它的政治隐喻又增加了它的厚重感。
现象四:《你是对的——如果你认为是的话》与《罗生门》对事物相对性哲理的演绎
尽管这两部发表于20世纪上半期的作品分别属于戏剧和电影两种艺术类型,但都借助了相同的叙事手段,演绎出共同的哲学主题,进而传达出各自带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思想内涵。
《你是对的——如果你认为是的话》(1917年)是皮兰德娄的一部哲理剧、寓言剧。剧本通过描写一座意大利小城市的好奇市民们试图搞清两个古怪的、经历过地震的外来人的真实情况,传达出相对论和不可知论的哲学思想。一个叫邦扎的人和他的妻子住在一栋房子里,他的岳母弗娜拉太太住在隔壁公寓。人们不曾看到母女之间往来,母亲解释说,她单独居住是不想干扰女儿的生活。邦扎说,自己的太太有精神病,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于几年前的地震中,现在的妻子为了使弗娜拉太太高兴假装是她的女儿。对此弗娜拉太太说,邦扎疯了,他现在的妻子是她的女儿,是他的第一个和唯一的妻子。妻子最后出来说:我是弗娜拉太太的女儿,是邦扎的第二个妻子。就我自己来说,你相信我是谁我就是谁。剧本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人们的争论没有结果,三个人之间不确定的亲属关系表明这样一个哲理:真理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是主观的东西,由于每个人的观点不同而有所不同,人们寻找共同的真理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
这个故事与黑泽明导演的日本经典电影《罗生门》(1950年)在情节构架上存在极高的相似度。强盗多襄丸见到武士的妻子貌美而起歹心,把武士绑了起来,强暴了武士的妻子,武士对妻子不仅毫无怜悯,还满是鄙夷,妻子很是气愤,于是挑拨武士和强盗打起来,强盗用短剑杀死了武士,这个过程被樵夫看到,樵夫偷走了武士身上的短剑。这伙人被抓去衙门,每个人都有一套美化自我的说辞:强盗说自己很英勇,和武士比剑,赢得美人心;武士的妻子把自己形容为贞女烈妇,强调自己被男人抛弃后的痛苦,并为自己的罪恶开脱;死去的武士则通过灵媒把自己的死归咎于真砂的背叛和不贞,称自己是不堪屈辱切腹自杀,试图挽回一个懦弱无能的男人的尊严;唯一知道真相的樵夫则因偷了短剑,不肯吐露真相。《罗生门》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编造谎言,他们各执一词,分别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表述证明,真相被掩盖在谎言之下,扑朔迷离,但观众最终还是追索到了真相。电影突出强调了人性的软弱、自私,同时在结尾部分,通过贫穷的樵夫愿意收养弃儿的举动,表达了对人性的乐观态度:人性中尽管善恶交织,但善总是更有力量。影片四个主要人物对事实的阐述形成四种说法,有部分信息的重叠和相互印证,更多的是彼此迥然不同,这种叙事策略与《你是对的——如果你认为是的话》完全相同。
在《罗生门》和《你是对的——如果你认为是的话》中,都表达出鲜明的相对论哲学思想,但前者与可知论和乐观主义相联系,后者与不可知论和悲观主义相联系。在两部剧中,人物都带有潜在的面具,那是他们给社会看的脸。在《罗生门》中,面具和隐藏在面具后面的真实情况是可以区分清楚的,即真实情况最终是可以被掌握的;在《你是对的——如果你认为是的话》中作者表达的是,要充分了解每个人隐藏在面具后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的,真理不断发生变化,而且由于每个人的观点不同而有所不同,体现出怀疑主义和相对论思想。《罗生门》中,黑泽明告诉观众:人世间确实存在自私自利泯灭人性的严酷现实,但与之相对,人道主义也是永恒的,人终究是可以相信的,体现出积极入世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也是作为“电影天皇”的黑泽明重要的电影思想——人道主义最终会取得胜利。《你是对的——如果你认为是的话》则通过人物身上种种夸张的言行和矛盾冲突,透露出极大的痛苦和悲伤。人在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中,个体的人必然陷入失败的悲剧命运。这是关于不幸的现代人的叙述,是悲观主义人生观的演绎。皮兰德娄独特的美学观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精神氛围中形成的,体现出置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思想界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思考和困惑。
上文中,笔者举出四组例子来说明古今中外艺术创作中相似性现象的存在,通过分析,我们在原本看似毫无联系的作品与作品之间、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实现了超越历史时空的灵魂对话与交流,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精神历程的同步性与差异性,以及在同步性与差异性背后蕴藏的丰富性与多义性。正如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所说:“世界的意义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不可计数的意义。人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是无限的,我们面对现象,应当寻求多种多样的解释。”[1]
[参考文献]
[1] 冯俊.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转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