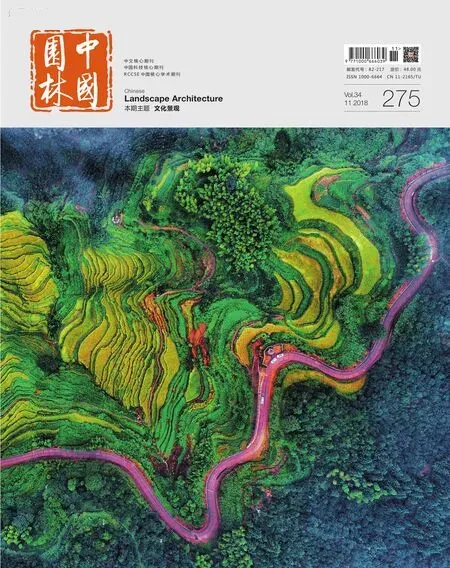“浙派”的“气骨观”
——陈从周造园思想的另类解读
朱宇晖
1 浙派的后身与“气骨”的源头
陈从周先生出生于民国的文化蒸腾之际、浙东的山水烟云之间——这是1 500年前,谢灵运等山水诗人开创中华山水审美的地方,也是800年前,南宋画院、浙派画坛与西泠印坛的巨子们驰骋笔墨才思的地方,还是民国以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之江大学的学子们拓展艺术与文化新局面的地方——陈先生成长、浸淫于斯,耳濡目染,天赋独秉,情之所钟,贯彻终生。
如他在论及浙江海盐绮园时所给予的、超越苏扬二地的难得盛赞:“能颉颃苏扬两地园林,山水兼两者之长,故变化多而气魄大。但又无苏州之纤巧、扬州之生硬,此亦浙中气候物质之天赋,文化艺术之能兼所致”[1]——“变化多而气魄大”六字中,已隐含着特殊的空间逻辑感悟与推许,“浙中气候物质之天赋,文化艺术之能兼”句,更指出“浙中”自然与人文环境对其园林、建筑空间逻辑的综合影响。
又如陈先生在论及杭州西湖建筑风格时的特殊流露:“我想西湖不同于今日苏扬一带的古典园林,建筑物的形式不必局限于翼角起翘的南方大型建筑形式;当然红楼碧瓦亦非所取,如果说能做到雅淡的粉墙素瓦的浙中作风,予人以安静恬适的感觉便是。[2]”
陈先生所钟爱的“安静恬适”而“雅淡”的“浙中”风土建筑风格,今日仍能在浙江全境,尤其是浙南温州、台州等地广袤的乡村中,见到种种余绪,如建筑檐口的水平向充分伸展、“亲地”而行、勾连交叠、迤逦不断;如建筑檐口、阶台、院落空间与山形水势的连绵交织、穿插共振;如建筑用材的本色凸显、质感饱满;如建筑装饰的相对集中精约(至中晚清时,部分地域变得浓烈满铺,并非其典型面貌)——笔者曾尝试借用南朝文人谢赫《画品》一文中,论及绘画“六法”时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八字,对这一建筑风格逻辑做概括。
“气韵”指浙中风土建筑跨越建筑、空间与自然环境的特殊浑成感、流动性与弹性,通常依靠线条来引领。一根浙中民居檐口线条往往能在奔驰转折之际,时而化作墙脊线、台阶线甚至坡脊线、树梢线条,时而融入下一组建筑的檐口,继续其融通天地、曼妙不羁的“行走”历程。
“骨法”指这一整体浑成的线条行走过程中的力感化、质感化、体积化甚至地域化、风土化、精神化——如建筑的猛然直角转折,随坡跌落,或适度耸起、放大,如建筑木构部分的不事髹漆装饰,如建筑石构部分的刻意保持粗糙质感甚至自然表面……这与徽州等地风土建筑以马头墙(北地风土建筑则多以厚重山墙)反复切割、包裹建筑檐口与空间,强调建筑体积而非流动性的做法有很大不同。
这种气韵与骨法并重的建筑与空间营造现象,或许是古代“覆压三百余里”整体化建筑营造传统的遗风,既利于遮风避雨、保护墙体与台基,又便于博采阳光、亲近自然、融通功能、展现仪式。这样的营造风格虽可散见于长江以南的广袤地带,但在浙闽一带尤为典型,杭州一带亦有相当体现。
而论及其生成的人文艺术环境,恐怕很难不言及最自觉化的线性审美艺术——中华书法,以及与之相关的绘画、雕塑、金石等众多中华文化艺术领域。如山水画的“十八皴”、人物画的“十八描”、金石中的单刀平冲、雕塑中的披帛衣纹,甚至散文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苏轼语)的文气,这些中华艺术门类大多暗含着画面感、线条感的艺术表达,暗含着气韵与骨法逻辑,而在浙江一地积累尤为深厚。王羲之、马远、李渔、吴昌硕都是其薪火相传者,此外不胜枚举。
陈从周先生恰恰就成长在这样的艺术、人文与建筑空间环境里,并得天独厚地兼备着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建筑、造园各领域的修养,并以岁月涵化,以逻辑打通,仿佛是上天特殊的赐予与造就——气韵与骨法并重的线性艺术基因,贯穿在陈先生的艺术气脉里,并最终落实在传统建筑与园林研究的坐标系上。
陈先生曾坦言将浙江兰溪人、明末清初艺术天才李渔作为自己的榜样:“……李笠翁是戏曲家、园林家,书画琴棋,各艺皆精,我也是个杂家,做杂家比专家难,而治园一定要懂得各艺,融为一体,才能造出诗情画意的园林。去年李笠翁故里,浙江兰溪造了一座纪念性小园,名‘芥子园’,要我题副对子。我握笔一蹴而就,上联为‘高艺谁云绝响’,下联为‘流风我是传人’”[3]——这是“越人陈从周”的难得畅怀倾吐。
其实,李渔还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重视“宾白”的剧作家,既重视气韵感的唱段,又重视骨法感的定场白、冲场白、旁白——这一点,作为资深曲友的陈先生该是了然于胸的。
2 艺术观与园论的气骨并重
陈先生的气骨修养源自浙派文艺传统,跨越诗词书画多领域,最终涵化、内化,自觉于心,贯注于造园一隅,激发出璀璨光华。
如陈先生行文论道,往往骈散错杂,总在悠长舒缓的散句之间,陡然以四字句,甚至四六句式,作凝练惊艳的描摹或提升,长句如气韵奔涌,短句如骨法顿挫,予读者以难得的阅读快感与观念升华。如“花墙间隔得非常灵活,山峦、石壁、步石、谷口等的迭置,正是危峰耸翠,苍岩临流,水石交融,浑然一片,妙在运用……”[4],再如“寺址十之八九处于山麓,前绕清溪,环顾四望,群山若拱,位置不但幽静,风力亦是最小……”[5],这简直近于骈四俪六句式了,却又妙入无痕,动人心扉。
再如陈先生授课,也如天花纷坠,纵横奔逸而不离其宗,记得多年前一次,陈先生代表同济大学延请昆曲名家梁谷音先生来校作讲座,梁先生示范讲解了她在《活捉》一剧中的各种情态把握,刹那满堂溢彩,顾盼神飞——讲座甫毕,端坐前排、担任主持的陈先生起身畅谈感想,一时娓娓不绝,阐发万端。台上的梁先生伫候许久,终于忍不住,偷偷从陈先生身后向台下的我们轻挥素手,微笑示意,一番“倚门回首”,便“含羞”走了——而陈先生犹自妙论不断呢。
再如陈先生的绘画,盛年时享誉海上画坛的代表作《一丝柳一寸柔情》,正是在气韵悠长柔缓的柳丝之上,刻画一双小鸟团团而栖,墨色浓重、姿态凝练,骨法十足——在当时的海上画坛,这种以大面积舒缓纯粹来烘托局部凝练突变的画面布局,似乎蔚为一时风气。
再如陈先生论及书法:“中国书法一定要直写,横写就不成其为艺术了。俗话说,‘字怕吊’,就是写得好不好,直不直,气韵通不通,一挂起来就美丑毕露了。[3]”再如诗文:“造园如缀文,千变万化,不究全文气势、立意,而仅务辞汇叠砌者,能有佳构乎?文贵乎气,气有阳刚阴柔之分,行文如此,造园又何独不然,割裂分散,不成文理,籍一亭一榭以斗胜,正今日所乐道之园林小品也。盖不通乎我国文化之特征,难于言造园之气息也。[6]”陈先生还坦言:“我能达此境界,实在得力于对志摩散文和诗的爱好”[3]——诗文修养对先生艺术境界的纵向提升与横向关节打通显然至关重要。
至于陈先生擅长的造园领域,相关言论就更多了,如其在代表性名篇《说园》系列末尾言及:“故造园要以极镇静而从容之笔,信手拈来,自多佳构。所谓以气胜之,必整体完整矣。[7]”再如“中国艺术,讲的是气韵,园林亦然。没有气的园不成其为园,只能称农场。[3]”而其在《西湖园林风格漫谈》一文中谈得更宏观而跨越:“西湖在整个的绿化问题上不能不有其主要的树类……正如画一样必定要有统一的气韵格调,假山有统一的皴法”——这是综述绿化、绘画与掇山的气韵浑成。
陈先生在《说园(五)》中其实也谈论了骨法问题:“质感存真,色感呈伪,园林得真趣,质感居首,建筑之佳者,亦有斯理,真则存神,假则失之。园林失真,有如布景。书画失真,则同印刷。故画栋雕梁,徒眩眼目。竹篱茅舍,引人遐思”——这里的园林质感化与生活化也是“骨法”的表现。
而当陈先生对比苏扬二地的造园风格时,气与骨这对概念就表达得更为清晰而独到了:“余尝谓苏州建筑与园林,风格在于柔和,吴语所谓‘糯’。扬州建筑与园林,风格则多雅健。如宋代姜夔词,以‘健笔写柔情’,皆欲现怡人之园景,风格各异,存真则一”[7]——“雅”近气韵,“健”多骨法,其意似指扬州园林较能平衡二者,而苏州园林则韵重于骨,当然实则陈先生更属意于浙江海盐绮园的堤岸蜿蜒、山岛竦峙,气骨飞扬,即“变化多而气魄大”,前文已经备述。
反面的例子,如《续说园》中:“今则见园林建筑又仿舞台装饰者,玲珑剔透,轻巧可举,活象上海城隍庙之‘巧玲珑’(纸扎物)。又如画之临摹本,搔首弄姿,无异东施效颦”——这是气韵与骨法质感两失的例子。再如“叠石重拙难……对全景作彻底之分析解剖,然后以轻灵之笔,随意著墨,正如颊上三毛,全神飞动……明代假山,其厚重处。耐人寻味者正在此。清代同光时期假山,欲以巧取胜,反趋纤弱……没有质性,必无佳构”[8]——这里的“质性”,似也可以理解为质感化、体积化的掇山“骨法”。
而其在实际操作,如指导江苏高邮文游台建设时称:“文游台有三个烘托:参天的古木烘托高台,台下面的小建筑群烘托上面的高大建筑群,环台的水烘托整个建筑群。曲水环廊,文游台就可以收‘口’了”[9]——高台乔木耸峙出的、丰碑般的体积与纵向节奏,正是骨法的最佳体现,而台下水平低伏的“小建筑群”与“环台的水”则共同谱写出横向流动的气韵,这里的画面感与章法逻辑是很清晰的。陈先生在论及苏州天平山庄与杭州孤山景区营造时,也有类似的精彩表述。
其实,陈先生被诸家解析的各种园论中,“有法无式论”似重点表达“气韵”的奔腾不定,而气骨并重即是“法”——“所谓‘法’者,脉络气势之谓,与画理一也”[8]。“动观静观论”似以“动观”为气韵的恣意流淌、以“静观”为骨法的顿挫凝注。“神气论”似以“神”近于骨法、“气”近于气韵。“质感存真论”中,质感即是骨法[10]。而如“水随山转,山因水活”这样的表述,水之如气,山之如骨,就更为清晰了。
其实陈先生以其饱含六朝烟水气之身、气韵丰沛之才,也非一味倾向于“有法无式”,当其论及苏州网师园时,称“其设计原则很简单,运用了假山与建筑相对而互相更换的一个原则(苏州园林基本上用此法。网师园东部新建反其道,终于未能成功)”[1]——这已经触及明末以来中国传统文人园的普遍布局规律了,也就是总以建筑隔水面山,相互转换。
3 后工业时代的“文艺复兴”与气骨回归
一些学者认为,清乾隆中叶以来(似可笼统称为“后乾隆时代”),中华文化与艺术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笔者角度看,这表现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的艺术创造与审美传统在各领域的丧失。这在传统建筑与造园领域表现得也很突出,如屋顶的过度柔曲陡峻,柱身的细高无力,雕饰、彩饰的堆砌泛滥,建筑组群处理的支离破碎,建筑空间组织的扭曲造作,掇山的穿凿弄巧,绿植的主题涣散——种种积非成是,至今积重难返。梁思成先生曾将中国建筑史的明清阶段笼统概括为“羁直”;张良皋先生生前曾疾呼中华建筑的“文艺复兴”;曹汛先生也曾呼唤在这一领域“陶铸风雅、涵养正声”——如果说,这场中华建筑与空间的“文艺复兴”与“气骨回归”终究会到来,那么陈先生早就以他独特的专业视角与理解力,成为其先觉者和有力的推动者。
笔者也以为,1952年的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固然是时代的必须与必然,却也令中国传统的“泛文人”“泛艺术”甚至“泛气骨”社会脱胎换骨——原本诗、词、书、画、拍、曲、造园浑然一体,传统田园社会横向浸润渗溢的文化艺术脉络关节,被日益严整而细密的工业社会纵向专业分野切断了。原本深具东方特征、恢宏融通的艺术共振现象逐渐消失,艺术通才与巨人日益罕见,园林化与艺术化空间的创造者与使用者往往都缺少必备的文化艺术素养与创造力、理解力——在这样尴尬的语境里,陈先生以其穿越时代、融通艺林之身横空出世,几乎以一人之力,重新接续起被工业时代长期割裂的社会筋脉,重构了中华文人大众与中华传统建筑和造园艺术的互动互哺,成为面向全社会的艺术“气骨”启蒙者。
难忘的20世纪80年代,从朦胧诗坛的巨子,到摇滚歌坛的教父,从美术界的新潮,到小说界的井喷,直至建筑、造园界的《说园》、方塔园——众多振聋发聩、长垂史册的文化、艺术与建筑、造园现象一起,蔚为“文艺复兴”般的盛况。
这其中,也有着来自浙派山水之间的气骨苏醒与助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