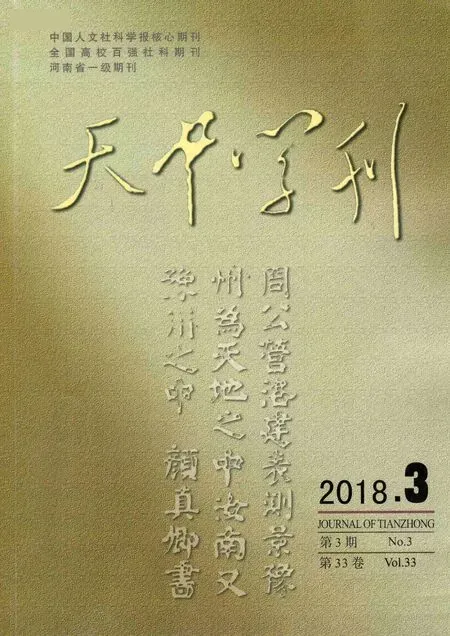身体、行为与意识
——评《抓握与理解:手与人性的涌现》
崔中良
(1. 大连理工大学 哲学系,辽宁 大连 116024;2. 滁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心―身”问题一直是西方关注的问题,从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到后来的认识论都是对“心”与“身”的讨论。意识问题是近代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也被称为“意识难题”,其解决方案各式各样。柯林 · 麦金将这些方案总结为四个进路:物理主义还原论、非还原论、超自然的神秘主义和取消主义,它们被称作“DIME模型”[1]。麦金是新神秘主义的代表,其最重要的观点认为,现代人类不能运用现有的科学知识来解释意识,需要一些神秘力量才可以解释。但麦金并不会因为现代人类无法解决意识问题而放弃对意识的探讨,他尝试运用各种自然科学成果来研究意识。麦金立足于当代神经生物学、脑科学、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成果,结合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资源,探究人类认知模式的局限性[2]。麦金认为,现代人类不能理解意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范式问题,我们通常用自身的认知结构来理解意识,其中空间的概念是最突出的,自此,“理解意识需要来一次彻底的‘范式革命’,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有一种全新的认知结构”[3]。人类身体的特点不可能改变人类的认知结构,那么就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研究意识[4];既然大自然制造出了意识,那么我们就要在现有的人类认知结构基础上学习大自然;大自然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进化,正是通过进化,人类才具有了意识。《抓握与理解:手与人性的涌现》这本著作就是在此背景下,通过研究手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探讨身体与世界在人类意识中的关系。虽然早在达尔文时期就有关于手与认知关系的的研究,但本书从新的视觉和范式来论述手是如何在意识的涌现中发挥作用的。该书从哲学的视角,结合生物学、人类考古学、胚胎学,对人类意识的起源做了详细的探讨和研究,对于意识研究、认知科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基本内容介绍
《抓握与理解:手与人性的涌现》分为 15个章节,从解剖学、功能、情感、认知、艺术、哲学等视角,探讨了人的手及其动作在人类意识出现和高级意识中所起的作用。
第一章从人类历史的角度论述人类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人类的历史对人类的现代形式有什么作用,为什么人类是这么的不同,或者从哲学的角度说,现代人的出现为什么可能,并回顾过去学界对手与人类关系的研究。麦金认为,手是抓握的工具,因此也是人类认知产生的根源。麦金通过进化论思想,探讨人性的起源,关注人类心理进化,同时也从解剖学和行为学上考察手的作用。因此,本章主要概括麦金思想的渊源及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和意义。
第二章主要总结了进化的两个原则:祖先特质保留和逐渐增加适应。祖先特质保留,是指自然选择过程会保留人类早期特质,早期的形式会一代一代传递下来,后期形式会修改前期形式并逐渐保留下来。因此,进化程度最高的器官仍然保留着早期祖先的形式,并不是突然产生的。例如:哺乳类的脚和鸟类的双翼都是来源于鱼类的鳍,它们分享了早期鱼鳍的解剖学特征;哺乳类动物的内耳来源于爬行类祖先的腭骨。生物体在进化时有一个预变的过程,每一次变异都是动物祖先在先前结构平台上进行的。因此,进化是与过去紧密结合的,同时也是一点点地向前适应并走向未来的,早期的形式为后期的变革设定了参数。
第三章详细概述了人类进化史。早期人类祖先是生活在树上的,在此阶段人没有语言和社会合作,人类当时的四肢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生活方式,手和脚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是由于环境的影响或者是后代的体格太大、太重不适合在树上生活,人类祖先就不得不下到地面。于是,人类的四肢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以适应当时的地面生活,逐渐向人的方向过渡。在过渡到人的过程中,手起着桥梁的功能,手的解放使得人类大脑必须发展平衡能力,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脑的其他功能。总之,人类能够成为今天的样子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类生活环境的改变。人是一个非臂跃动物,是被驱逐出树林的居住者,但同时也是有手的专家和生物进化的成功者。
第四章考查了手的特点和动作。手的抓握有两种类型:有力抓握和精细抓握。精细抓握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差别,工具的使用需要精细抓握,这样的抓握能够让手更灵活地掌控和操作,写作可能就是来自这种精细抓握,精细抓握促进了大脑的发展。大脑神经组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手的,拇指在大脑中所占的脑神经组织相当于整个腿的面积。在大脑神经组织中,不仅手的运动占有首要位置,甚至手的感觉和知觉也占有大量的脑组织。人类的很多文明都与手的教育有关,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看法,而将大脑看作手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认为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是手的部分,身体是手的仆人。
第五章和第六章探讨了手与工具和语言的关系。人类祖先从树上下来以后,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使用工具,工具替换树枝,工具成为人类抓握的首要物体。语言首先并不等于声音,而是手语。工具的使用促进了手的灵活性,也促使了手语的出现。语言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由于基因等生物突变引起的,语义与句法也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有一个前适应阶段。在语言出现以前,人类已经具有了思维。作者认为有三个理论可以解释语言与手的关系:(1) 手抓握某物就像语言中的主位与述位的关系。(2) 抓握行为理论:由于抓握的对象不同,要求人们使用不同的手型,抓握的手型就代表了所抓握的物体,因此指称出现,手语也就相应形成。(3) 模仿理论:手可以模仿自然和复制事件,情景可提供说的意向,由于此时人类已经具有思想,同时还具有技术思维,这些原因促使人们将手作为交流的工具。
第七章指出交际中的明示与抓握是息息相关的,各种明示动作都有其产生的背景。例如,引诱的手势最开始的意思是抓住某人同时将某人拉向自己。拒绝一般是手心向外,这表示做推的姿势。再见的手势最初是轻拍某人来安慰别人的意思。这些肢体动作失去了其行动的对象,但仍然能够模仿原初的行为和表达的意义。作者通过抓握的各种姿势来证明抓握与明示的关系,论述了拇指的重要性。与猿猴相比,人类的拇指比较长,更适合不同的抓握姿势,因此就能有不同的抓握方法,如展示性的抓握、移动性的抓握、减弱性的抓握等不同方式。这些抓握方式经过进化,逐渐演化为更加姿态性的抓握。另外,人类的手和手臂不够长,无法触碰所有我们看到的事物,因此我们就用虚拟的抓握方式来表示实际的触碰。
第八章论述了话语出现的原因。口语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手语有很多缺点,相比口语来说手语表达更具有效性,这是因为手语是平行加工,而口语是线性的。口语替换手势语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人类生活的需要,口语可以解放手和眼睛,做更多的任务让人类更加容易地生存,人们可以一边说话一边用手做其他事情。另外,手语还受光线的影响。人类的早期语言形式更像作家,时刻都在用手书写,只是书写在空气中而已。因此,现在的口语交流仍然需要手势语的参与。麦金认为,正是生活和人类的进化逼迫人类使用嘴巴来表达语言,而舌头就像人类的手一样能够灵活地运动,所以大脑中有很大部分是控制舌头运动的。表达就是一种运动,不管是用手语还是口语。
第九章提出手塑造着我们的心灵。手在个人的智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人类的大脑有很大一部分是负责手的。手是人类的重要感知运动器官,因此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和渠道。人类思维中最基础的概念图式都与手的运动特别是抓握运动相吻合。在表达上,手和身体都可以表达思想,同时也是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
第十章着重论述了选择在人类认知中的重要性。作者认为手不是思想的唯一来源,嘴也是思想形成的重要平台,因为其他动物也有思想。选择是人类认知的重要方面,因为在选择的时候意味着被选中的物体要比其他物体更重要。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最开始是一个照相式的思维,没有选择的能力,但是嘴为选择认知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嘴能够辨认出能吃的东西和不能吃的东西,由于对实体的选择,人类能够将这些选择的感受进行抽象化,因此嘴的抓握就变成了认知的理解。在选择认知的基础上,人类的认知开始逐渐发展,人类可以通过眼睛和心灵理解物体的特征并形成心理图像,因此人类的认知来源于身体的运动。
第十一章从进化论和自然选择两个方面考察了感知的起源。感觉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食草动物不甘于被猎杀。随着自然选择和动物的自身进化,感觉动物从低级向高级演进,最后发展成人类,因此人类是具有感觉的。作者总结认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心灵”经历了三次进化:(1) 由于躲避被捕食,出现了基本的感觉;(2) 选择性的认知出现,为第三阶段语言的出现做了基础;(3) 人类通过使用手和工具来发展语言,从而使得语言得以进化。因此,人类思想的进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感知阶段、认知阶段和语言阶段。
第十二章从生存论上论述了抓握的意义。人类的心智与占有有关,而这种占有可以追溯到人类手的抓握和口的选择。心灵的构成与人在占有物体时所使用的抓握有关。抓握还可以产生人类的情绪,当失去抓握的东西时、抓到不好的东西时、完全失去抓握能力时,我们就会焦虑、失落,等等。因此可以说,人类的各种心理、心智、情绪和心灵都是由抓握产生和组成的。
第十三章总结指出人类的文化就是一部关于手的历史。人类的文化本身就是由手产生的,手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源:(1) 从艺术上来说,手是创造的工具。早期人类将手印刻在山洞里,这是人类艺术的早期形式,人类用手制造的工具塑造整个世界;(2) 由于人类制造的工具都是按照手的需要做成的,因此我们的科技文化在原初上就是手的文化;(3) 写作主要依靠手来进行,而写作在形成人类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4) 从广义上来说,做游戏和运动占有人类文化的很大一部分,而手是天然来做游戏的,人们在社会交际中,如打招呼、装饰、指称时都需要手的参与;(5) 手与宗教有着重要的关系,如在基督教中人们用手画十字,用手来祈祷,等等。
第十四章指出人类仍然遗留祖先的野性,即森林残渣。虽然现代的人类与过去的人类祖先有明显不同,但是现代人仍保留一些人类祖先的残余。我们天生就具有过去人类祖先的本领,如小孩喜欢荡秋千、爬树等;人类喜欢森林,实验也表明,如果人们在树木繁茂的地方做事的效率更高;人类喜欢比较高的东西,如比较喜欢摩天大楼。人们一般将好的事物比作在高的地方,天堂在上面,地狱在下面,因此可以说人类的心灵仍然居住在高处。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不能完全与过去的猿猴区别开来,人类还具有人类祖先的一些特征,它们隐藏在我们深处,森林之脑隐藏在现代之脑后面,无意识是森林之脑的仓库。
第十五章对人类未来表示了担忧。手是人类智能的最重要明证。由于人类智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设计了各种自动化工具,很多事情都不需要手的操作。麦金认为这对人类未来发展是一个极大挑战,为避免出现人类悲剧,我们应该认识到手的作用,应该信任我们的双手,应该崇拜我们的双手。
二、评价
《抓握与理解:手与人性的涌现》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将人类进化特别是手的进化与人类意识的产生联系起来,很好地结合了进化论和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论述意识的起源,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追溯手对于人类的意义。麦金认为手在人性产生和意识进化各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为其研究意识的产生提供了观念基础,而且为其“思想建筑术”中研究大自然的进化论提供了解释。神经科学研究也证明了手的重要性,在大脑皮层中控制手的神经几乎占据了整个神经网络的一半,也正因如此在语言中关于手的动作的词要比其他部位的动作要多很多。麦金运用进化论的观点详细论述了自然选择在感觉的出现、手的出现、工具的使用、语言的出现等方面的作用,指出正是手的出现才使得人类不同于其他物种,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部手的历史。关于手的作用,作者更强调拇指的重要性。猿类也有像手一样的身体结构,为什么就没有出现人类一样的心灵呢?麦金看到人类的拇指要比猿类长,从而能做出各种灵巧的动作,如汉语中的打、端、推、拉、扒、挖、捧、接等。正是这些动作,才让人类的大脑神经变得更加活跃,相应的人类的大脑神经元也相对要多,因此正是这种自然选择的原因才使得人类的手在人性的涌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除了论述手的重要性之外,麦金论述了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也表达了对未来科技发展的担忧。麦金认识到,早期人类使用的工具就是科技出现的雏形,正是因为工具的使用才促使了手的灵活,从而导致人性的出现,人类新技术的出现都是以人类手能最大掌握世界为目的,因此科学技术时刻体现了手的重要性。但是,现在人类以科技为衡量真理的标准,科技上肯定的都是正确的。在科技大行其道的社会中,科技的发展超出了人类最开始使用工具的目的,似乎要超出人类的控制;科技的无限发展除了会带来社会问题之外,更多的是人不再以手作为科技的出发点,而是更多地减少手的使用。因此,麦金对人类的未来有着深深的忧虑。这也表现了他思想的矛盾性,如陈丽、刘占峰所述:“就麦金的自然主义二元论而言,尽管它是一种自然主义,但作为一种后现代立场,它又不认可激进的取消主义和乐观的建构自然主义,它试图‘向科学主义的心脏插一枚道钉’,以抵制科学的狂妄。”[5]麦金担忧的人类未来的情景短期内似乎还不会出现,但是假如人类不再使用双手和身体,按照麦金的观点,人类将失去人性,这也为人类科技的无限发展敲响了警钟。
虽然麦金对手的论述非常翔实,对进化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描绘得栩栩如生,但也有老生常谈之嫌。斯坦因在评述本书时指出,本书的一些观点并不太新鲜,对于手和工具的使用,马克思在其经典理论中都有详细的论述,除此之外本书还有一些不足和漏洞[6]。麦金论述人性的涌现,主要依赖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手的解剖结构变化、手的工具使用、语言出现甚至是感觉的出现都依赖于大自然的选择。虽然麦金的解释在一部分上是合理的,但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解释人类意识的产生,我们并不能证伪,这就如于小晶和李建会所说:“在自然选择是不是唯一的进化动因方面存在广泛的争议。”[7]另外,麦金的进化思想更多强调大自然的选择,并没有强调人类的适应,似乎人类在大自然的选择面前没有任何主动性,这样我们就不禁迷惑:为什么是人类祖先从树林中走出来,而其他猿猴就没有这样做呢?这就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怪圈。
麦金反对传统的笛卡尔的二元论将心灵与肉体看成是两种不同的实体,但并没有完全跳出笛卡尔的二元论,虽然他指出意识(心灵)不能用人类现有的认知结构来理解,但是他已经预设了意识是一个实体。而随着认知科学和意识研究的发展,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传统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的缺点。传统的认知科学只是将人类的认知看作属于大脑的活动,因此是与身体无关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研究范式的不足,最新的认知科学和外部主义观认为,人类的心灵或认知是大脑、身体和环境相互作用产生的。麦金虽然不完全同意认知或心灵来源于大脑,而是将手的重要地位凸显了出来,但他只是在大脑中加上了一双手,仍然是有局限的。手虽然重要,但人类身体的其他部位也随着自然选择而进化,人与猿类的不同不仅仅表现在大脑和手上,人类的视觉、听觉、嗅觉、性欲等都与动物不同,正是人类身体的整体不同于其他动物才导致现代的人类产生,人才有了更高级的认知。根据神经科学的研究,控制人类身体某一部位行为的不仅仅是身体该部位的神经,与之相关的其他部位也会因此被激活。因而,如果将人类的历史仅仅看作是手的历史,就显得太片面和狭隘。本书中的很多例证,都是作者自己推断和想象出来的,并没有相关的调查和实验,虽然有些地方在通常情况下似乎合理,但也不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总的来说,麦金对手在人类意识产生和发展中的论述,为意识困难的解决和认知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研究尽管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证明,但毕竟为意识产生的解释增加了一种研究进路。麦金将意识的产生归结为手的进化和工具的使用,对于“意识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他将人类的心灵与身体紧密结合起来,强调身体的首要性,为认知的具体性研究提供了支持,也与近年来认知科学领域中发起的非笛卡尔的第二次认知革命遥相呼应。但遗憾的是,麦金仍然是以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为研究起点,将意识或心灵看作是一个类似于实体的对象,在本质上仍然没有跳出笛卡尔的圈围。
[1] MCGINN C.Problems in philosophy: The limits of inquire[M].Oxford:Blackwell,1993:31–35.
[2] 刘明海.麦金的新神秘主义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7):25–30.
[3] MCGINN C. The mysterious flame: Conscious minds in a material world[M].New York:Basic Books,1999:59.
[4] MCGINN C.Can we solve the Mind–Body problem[J].Mind,New Series,1989(7):349–366.
[5] 陈丽,刘占峰.概念革命能否解决心身问题:兼评柯林麦金的先验自然主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7):9–14.
[6] STERN E.Embodied cognition: A grasp on human thinking[J].Nature,2015,524(7564):158–159.
[7] 于小晶,李建会.自然选择是万能的吗?:进化论中的适应主义及其生物哲学争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6):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