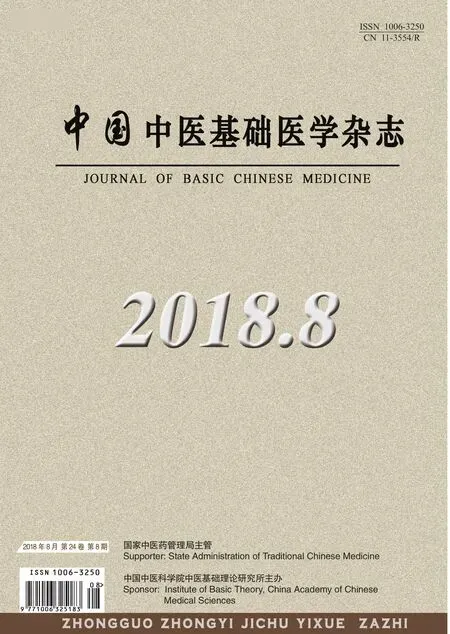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理论在《黄帝内经》英译研究中的应用❋
冯文林,李知宇,宫 齐
(1. 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广州 510515; 2.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州 510632)
佛经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翻译活动,对我国本土翻译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早在公元65年向我国传播,而我国的佛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1]18-19。据马祖毅研究,从东汉末年到北宋末年佛经翻译大致分为草创期、发展期和全盛期以及基本结束期等4个阶段[1]22。《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中后期,历史上曾经向周边的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传播。近1个世纪以来,《内经》(特别是《素问》)英译本就达13部,还有法译本、德译本等。本文拟探讨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理论在《内经》英译研究中的应用。
1 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理论
1.1 支谦与《法句经序》
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最早的翻译思想存在于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据记载,支谦在《法句经序》中强调佛经翻译因时代不同、语言变迁和迥异、语境变换、名物亦不同,所以翻译起来确实不易(“名物不同,传实不易”[2]273),并以“审得其体”[2]273指出,安世高等人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2]508。然后支谦进一步指出,理想的翻译文本是文质彬彬(文质相称),相得益彰,并以“因循本旨,不加文饰”[2]273的言辞指出佛经的译本并非不需要刻意的文饰,而是应该根据译文(汉语)语言的运用与表达意义的需要而契合并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不刻意去追求因文饰而修饰,才能真正达到“文质调和,畅达经意”的效果[3];支谦还以“辞朴而旨深,文约而义博”[2]273来评价佛经译本应当言辞朴实无华、平易近人,而且表达的意旨也应当深远宏大,成功的佛经译文既要简明扼要,又要体现其义理博大精深[3]。
1.2 道安与“五失本,三不易”
道安是我国东晋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佛经翻译代表人物,其对佛经的翻译作出了卓越贡献。道安虽不懂梵文,但他专心研究并亲身实践,最终总结佛经汉译的经验,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等翻译思想,为后世佛经等典籍翻译奠定了基础。据记载,道安的“五失本”认为,翻译梵文佛经时,容易使译本失去佛经本来面貌的有5种情况:一是梵文佛经的词序是颠倒的,故汉译时必须改从汉语的语法;二是梵文佛经的表述是质朴的,而汉人喜好华美,佛经汉语译文必须作一定的修饰才能达到汉文读者的满意;三是梵文佛经中同一意义往往再三反复,佛经汉译时不得不删除繁杂的部分,使其表述趋于简单明了;四是梵文佛经在结尾处总是将前文复述作一段或1000字或500字的小结,佛经译成汉文时也需删除这些复述的小结;五是梵文佛经中论述已告一段落将要另谈别事时,又把前面论述的话再次重提,然后才开始谈论别事,佛经汉译时则必须删除重提的前话[1]38。所谓“三不易”是指使佛经译文很难明确表述佛经原旨的三种情况,一是古代圣人先贤是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来讲经说“法”的,因为古今时代与风俗习惯的变迁,要使古代思想适应现今社会的潮流变换是非常不容易的;二是把古代圣人先贤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才疏学浅的浅识者,以适应后世民众的理解能力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三是佛祖逝去后不久,释迦牟尼的大弟子阿难等一些对佛学有造诣的人在创造佛经时,都是本着兢兢业业而又反复斟酌的态度,但是现在却由凡夫俗子来传译佛经,而且又与造经时事隔达千年之久,也是非常不容易的[1]38。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体现了译文由于佛经原文的语言、文化、时间、风俗习惯等不同或者变迁而有所差异,致使翻译佛经失去了本来面目以及感慨翻译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3 鸠摩罗什与意译
后秦僧人鸠摩罗什在我国的佛经翻译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梁启超称为“译界第一流宗匠”。罗什在译法上一改以往直译、硬译转而倡导意译原则(“曲从方言,趣不乖本”)[4]。罗什还独创了译经文体,即在意译时不再拘泥其原本形式,使诵读佛经者更能理解与接受其译本;文字上运用自如,使佛经的翻译兼具文学素养而自然生动、契合妙义,创造出一种外来语和汉文都非常协调的美感语体,故在传译上缔造了空前的盛况[4]。对于那些很难在汉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语,罗什一方面用原有的汉字来翻译佛经的概念,使之具有新的意义;另一方面力求对译名重新更正,坚持对其音译,避免一词多译和理解上的歧义,基本还原了佛经的原貌,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作,还创造了独特的四字句为主的行文体制[4]。罗什在翻译态度上庄重严谨,而且还开设译场,对佛经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功不可没,并指出译者需要具备学识渊博、翻译态度庄重严谨等修养[4]。
1.4 彦琮与“八备”
我国北朝末年及隋初僧人彦琮的《辨证论》,是我国翻译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相对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其中载有的“八备”学说较早且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本身的问题,亦即对佛经译者的思想道德修养、个人品德行为、语言素质等的要求,是做好佛经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8个最基本条件:第一,虔信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此条体现译者的意志;第二,在即将踏入译场之前,首先牢记佛教的戒律,不惹旁人讥疑,此条以译者首先要品德端正、忠实可信等体现了译者的道德修养;第三,通晓佛学经典,对佛学的两派之论都能融会贯通,不存在暗昧疑难的地方,此条是对译者要博览经典、通达义旨等佛学方面知识储备的要求;第四,要涉猎中国经史,潜心研究典籍,兼擅文学,以避免译文过于疏拙,此条体现了除精通佛法以外,译者还要通晓中国文史哲方面的知识;第五,要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武断固执,此条是必须重视译者在个人品德方面的修养;第六,潜心治学,淡泊名利,不想出风头,此条再次强调了译者要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第七,要精通梵语,熟悉正确的译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此条是对译者语言素养方面的要求;第八,兼通中国训诂之学,如要阅读《苍颉》《尔雅》等语言文字工具书,精通篆书、隶书等不同字体的写法,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此条仍然是对译者语言素质方面的要求[1]54。
1.5 玄奘与“五不翻”
唐朝人玄奘既是我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佛学家,也是我国古代翻译史上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其精通三藏兼谙梵汉两种语言,在翻译实践中总结并提出了“五不翻”原则。所谓“五不翻”就是指在翻译佛经时,译者遇到5种情况可不必按意思译成汉文,而是用梵语发音的汉字写法来代替,也就是进行音译,虽然翻译时只是将原文语词照搬,但等到讲经时再进行全面讲解,层层展开解释[5]。
1.6 格义与合译
“格义”是指佛教传入我国的初期,为消解同我国中原本土文化间的分歧,佛经翻译者采用以我国人民群众所熟知本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经典中的意义道理、名词概念术语等内容,比拟或者配附佛经中的相关“事数”,以双方文化的杂合(不是融合),使佛经中深奥的意义和道理得以被我国人民群众所理解,进而推动佛教在我国的发展。佛经译者力图使自身的“他者”身份在与之相比较而言的作为“异域”的中原文化语境中获得接纳和认同,所以“格义”是佛经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权宜之计;虽然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的意义道理,来比附佛教中相关的“事数”难免有违佛法本义,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个宗教思想为顺利进入异域得以快速发展,任何一个哲学思想的抽象被认同,都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个接受、继承、创新发展不断演变的过程[6-7]。
“合译”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译者分头负责、同心协力合作而进行的翻译。在佛经翻译初期,据记载历史上曾经有西方各国僧侣之间的合译以及西方僧侣和中国僧侣之间的合译,随后开始采用的“译场”翻译佛经的方式是合译的一个很好的演化和例证。除佛教经典的翻译外,中国译学史上尚有科学著作以及文学作品等合作翻译的情况[8]。
2 古代佛经翻译理论在《内经》英译中的应用
2.1 翻译不易
支谦指出的“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和道安的“三不易”,都强调了翻译的不易。李照国、张清华皆认为,由于《内经》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语言表述晦涩,致使其中蕴含的医学理论深奥难懂。另据统计,历代著名的注本已多达400多部,且各注本对《内经》中同一句话的注解表述也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加上涉及《内经》方面的许多文献资料历经2000多年中的多次动荡,大都难以真正地保存下来,就算能够流存下来可考据的文本,或存在着字迹不清,或难以考证等众多问题,致使《内经》方面文献的白话今译已经颇为不易,而且尚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探讨争论的问题,更何况是对《内经》的英文翻译,便更是难上加难[9-10]。
2.2 “不加文饰”
支谦“文质并举”的翻译思想不仅对后来的佛经翻译极具影响力,而且对《内经》翻译也有借鉴意义。如李照国[9]翻译《内经》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译古如古,文不加饰”,是支谦指出的“不加文饰”的演化。李照国[9]指出在翻译《内经》的过程中,为尽可能地保持《内经》原文的结构形式和原有的表达方式,尽量采用不增词的翻译方法,但鉴于《内经》古文的文简趣深,所以翻译《内经》时倘若不增加字词,时常很难将《内经》原旨表达清楚明白,所以认为但凡为表达需要而必须增词的地方,均统一将其置于中括号[]中,使读者不仅一目了然地看懂,而且还能理解译者的良苦用心,更能有效地防止衍文的出现[9]。
2.3 读者可接受性
道安在“五失本”中指出的译文必须作一定的修饰以使读者满意[1]38,以及鸠摩罗什指出的“意译时不再拘泥其原本形式,使诵读佛经者更能理解与接受其译本”[4],都体现了读者可接受性的问题。《内经》译者对翻译时2种不同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以及行文习惯等差异的体认,所以翻译时不得不对句法结构进行调整,必须考虑译入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对于重复繁琐之处可加以删略。刘九茹在评析吴连胜、吴奇父子《内经》英译本的基础上指出,为了让译文所传达的信息被读者理解,译者只有从译文接受者的角度出发,将中医典籍中包含的基本理论和精华译成英语并把信息的意思表达清楚,才能实现译本的信息传递和交流的功能,促进中医药学的国际交流[11]。邴漫青以《内经》英译为例指出,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有效使用翻译补偿策略,可以提高中医术语翻译的准确性,使其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空缺现象得以解决,有助于读者可接受性,促进中医翻译实践的良性发展,并推动中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12]。
2.4 译者素养
鸠摩罗什指出的译者修养以及彦琮“八备”所强调的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必须具备的8个条件,都是我国对“译者主体性”最早的诠释。兰凤利在探讨“谁”立足于“在翻译《素问》之后”的命题中,明确地指出《内经》译者的中医学学术背景和一定的中医古籍(版本、训诂、校勘)等相关的学科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以及较强的古代汉语阅读和理解能力等,都是作为《内经》译者首先必备的条件。其次,《内经》译者必须具备的还有扎实的译语语言功底(最好能达到地道的程度)和良好的翻译素养,而且作为一名合格的《内经》译者,所应具备的素质还有对译入语的医学文化意识形态以及译入语接受者意识形态等的觉悟,译者的这些必备条件对《内经》的英译过程影响很大,也意味着译者主体性对《内经》译文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可见,兰凤利对《内经》译者必备条件的阐述与彦琮的“八备”说有异曲同工之处[13]。雷燕等以朱明、李照国、Maoshing Ni和ILiza Veith等的《素问》4个英译本的某些译文为例,认为译者的知识结构、双语能力及翻译前确立的翻译目的、方法等主体性因素对译文质量会产生较大影响[14]。
2.5 音译
鸠摩罗什为避免歧义而坚持对译名的音译,玄奘的“五不翻”理论是关于音译法适用原则的系统论述,对于今天的中医音译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任荣政在对“五不翻”理论进行逐条解读与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阴阳”“气”翻译实例对中医英译中音译法的应用原则进行了探讨[15]。李照国英译《内经》时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二是“与时俱退,立足实际”,具体认为,尽管古代和现今在思维认识的方式、表述时所用的语言结构和思想意识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倡导“与时俱退”理念有时很难落实,然而李照国仍然建议《内经》译者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尽可能地回归到《内经》时代,目的是为避免因以今释古而可能出现的误译现象,所以在英译《内经》中某些蕴含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时均提倡音译,并在有关音译概念术语之后,建议采用小括号将现行近似的英文对应词作为文内注解附上,以便读者能快速、完整、准确地理解相关概念的实际内涵[9]。李照国提倡的音译加注释翻译法是非常值得推广的,但他提出的译者在思维方式上尽可能地回归到《内经》时代,就与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所提出的由于时代变迁而避免运用古味有些许不一致。
2.6 格义
佛经翻译的“格义”思想在《内经》对外传播中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可以用西方文化或西医学词汇来比附《内经》中的某些内容,从而达到有效对外传播的目的。杨静、李永安等认为,不能借口中西医隶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而将两者对立起来,另创造一套词汇去翻译中医;由于中西医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体和疾病,所以对人体组织结构、器官功能、病理状况及疾病治疗等众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或者说不少中西医学术语理应存在语义的共核,译者在翻译《内经》中的中医术语时,倘若西医学系统中有与之相对应的词或词组,《内经》译者可以尽可能地直接借用西医学中对应的词或词组,以西医学词汇为桥梁,因为这样翻译易于被西方译入语读者快速理解并接受《内经》原旨,所以翻译和传播《内经》等中医典籍的普及性也较强[16-18]。其实笔者认为,在用“格义”法翻译《内经》的同时,建议加入相关的注释,毕竟中医学与西医学是在两个不同文化底蕴下形成的医学,所以倘若以西医学词汇翻译《内经》近似术语,加上相关的注释予以清晰明了地补充说明的话,则更能彰显《内经》原文的旨意。
2.7 合译
“合译”在《内经》翻译中也有体现。在《内经》英译史上曾经有过加拿大Henry C. Lu 等首次合译《内经》,以及吴连胜、吴奇父子全译《内经》,而最为著名的“合译”当属德国著名医史学家文树德牵头全译的《素问》。据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德国柏林洪堡大学Charité医科大学中国生命科学理论、历史、伦理研究所所长、汉学家文树德(Paul U Unschuld)主持并在中国学者郑金生、张同君协助下的《黄帝内经素问》英译注释系列著作的最后一本《黄帝内经素问译注》。曾参与此次《素问》研究与翻译课题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郑金生认为,该《素问》译注本重点突出了翻译与注释的结合,在翻译方法、解读视角以及关注热点等方面独树一帜,与众不同,所以该《素问》译注本不仅可以帮助世界读者更好地领略中国古代医经的风采,扩大《内经》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为东西方古代文化精髓的探讨与比较研究提供更多、更可靠的文献基础[19]。
3 结语
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堪称最早并具有规模的翻译活动,对后世在哲学思想、语言、词汇和文学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回顾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理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即翻译的不易、“不加文饰”、读者可接受性、译者素养、音译、格义、合译等方面,迄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内经》英译研究中仍具有启示作用和应用价值。在大力提倡西方翻译理论的今天,系统整理中国翻译理论以发展和促进《内经》等中医典籍的翻译实践,也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