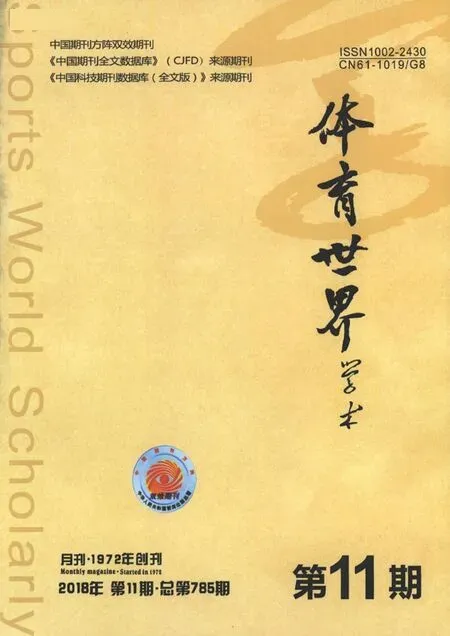贵州毛南族佯僙人打猴鼓舞口述史研究刍论
陈国余 郑一凡
1. 前言
据史籍和方志记载,唐朝以前就有佯僙蛮在贵州境内繁衍生息。1990年,在民族识别中,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贵州佯僙人被认定为毛南族。对于毛南族佯僙人而言,如何在新的族名下维持自己原有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世代传承的祭祀性仪式舞蹈——打猴鼓舞便成为一个理想的核心纽带之一。“打猴鼓舞”,佯僙话称为“叶烔满”[1],发源于贵州省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甲坝村甲翁组,是毛南族村民在丧事习俗中,由巫师表演的民间舞蹈,流传至今已有200 多年的历史了[2]。打猴鼓舞反映巫术礼仪、丧葬驱魔、敬奉精灵等内容。在深夜冷寂之时,敲起铜鼓,打起皮鼓,伴着鼓点,轮流跳打猴鼓舞能活跃灵堂气氛。由于毛南族地处深山密林,交通闭塞,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而打猴鼓舞又是和巫术祭祀仪式及宗教法事结合起来的,所以得以较好地流传和保存[3]。正因如此,早在2008年毛南族佯僙人打猴鼓舞便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彰显了国家对打猴鼓舞的高度重视。
2. 口述史方法与猴鼓舞研究的新突破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毛南族佯僙人打猴鼓舞的研究却长期比较薄弱,不仅是成果数量上与打猴鼓舞在毛南族佯僙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而且就是在为数不多的既有成果中,绝大多数也都是从单一视角进行比较泛化的平面描述或特点分析,缺失了打猴鼓舞存活的纵深历史背景和具体文化语境,也忽略了打猴鼓舞本土传承人或操演者的 “主位”立场和观点。这容易导致原本生动鲜活的仪式活动被硬生生地从其社会文化空间中剥离出来,经过过滤与肢解,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近年来,毛南族佯僙人打猴鼓舞的传承实践受到非遗保护因素的影响,也出现了一种越来越简化、过度表演化、逐渐偏离传统本体内涵的趋向,引起了一些本土文化传承人群、民族干部和专家学者们的深切忧虑。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急剧变迁,毛南族佯僙人传统打猴鼓舞正在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传承断链危机:村寨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能操演并传承打猴鼓舞者越来越少;随着老一辈传承人的相继去世,那些嵌化(embedded)在他们脑海中的打猴鼓舞历史记忆和具身化(embodied)到了身体里的操演技艺本体,也随之永远消失。显然,回到田野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运用目前业已十分成熟的口述史研究方法去“重新发现”和抢救记录正在消逝或剧变中的毛南族佯僙人打猴鼓舞本体内涵和深层文化意义,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开展的一项重要学术任务。
3. 毛南族佯僙人打猴鼓舞口述史研究方法举例
采用口述史的方法对毛南族佯僙人地区广泛传承、但正面临严重传承危机的打猴鼓舞进行研究,将主要通过采集、记录、整理、分析和研究,围绕打猴鼓舞“舞师”人群、普通操演人群、主要受众人群等各相关人群来开展。口述的内容以村寨本土人群主要关于打猴鼓舞传承发展形态的“主位”表述为主,也包括一些相关外来人群的“客位”表述。具体来说,将包含如下几种研究方法。
3.1 田野调查法
本方法主要是通过客位观察和参与式观察,摸清打猴鼓舞传承的状况,并为口述史的采集物色潜在的人群对象。在后续的口述史采集记录过程中,田野调查法仍将会经常被用到,藉以搜集相关背景材料与口述人的口述材料进行参照佐证。在田野调查中,将尤其注重实施“协同民族志”田野工作法,充分发挥当地调查协作人的作用,让当地毛南族佯僙人也成为研究者,以便使我们能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看待和研究毛南族佯僙人打猴鼓舞。
3.2 多形式访谈法
对具有代表性的打猴鼓舞口述史采集对象进行多种形式的访谈,包括开放式、结构式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等,主要是通过与访谈对象单独的、互动、面对面交谈的形式,达到课题的口述史搜集目标。重点对典型村寨的“舞师”人群、普通操演人群、主要受众人群进行焦点访谈,记录其个人生命史,以及他们与打猴鼓舞之间的生动鲜活的故事。
3.3 系统综合记录法
对打猴鼓舞的仪式表演过程,要以录音、录像、摄影等多种方式进行全程记录。对于口述史访谈,也要采取笔录、录音、录像等多种方式进行全面的记录;而且要特别注意记录语境或语气,注意观察受访者的语言、表情、情景,以确保对其口述能有正确到位的理解。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场景下的访谈人,要进行分类记录,以便之后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归纳共同的整体特点和个性差异,实现对打猴鼓舞传承人群的全面正确认识。
3.4 主位和客位交叉法
本研究将运用主位(emic)分析法,从当地人视角去理解毛南族佯僙人打猴鼓舞,听取本地人如何看待和解释他们的打猴鼓舞。同时,也将运用客位(etic)分析法,从文化的外来观察者的角度来研究打猴鼓舞。通过主位与客位的结合,可以获得对毛南族佯僙人打猴鼓舞的更为全面的认知。
4. 基于口述史料的毛南族佯僙人打猴鼓舞历史发展
以口述史为资料分析打猴鼓舞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解读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尤其是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藉此反思当前毛南族佯僙人打猴鼓舞在传承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症结。
原始形态的打猴鼓舞是丧事的重头戏,在葬礼上跳打猴鼓舞就是为了纪念死去的老人和活跃灵堂气氛,是毛南族佯僙人传统孝道文化的主要体现。作为祭祀性舞蹈的打猴鼓舞能够稳定地传承并广泛流传于毛南族佯僙人地区,无疑与当地巫师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巫师是“开丧超度”祭祀仪式的主持人,在毛南族佯僙人地区具有很高的威望。在毛南族聚居区,凡老人去世,严格规定要举行“开丧超度”祭祀仪式,打猴鼓舞作为丧葬活动的重要环节,自然而然得到他们高度的认同。作为丧葬专属活动的打猴鼓舞大多数属于师徒传承,其传承授受具有口传心授、不立文字等特点。只有对目前仍然健在的打猴鼓舞老人进行口述调查,才能抢救急剧消亡的原始形态的打猴鼓舞的记忆与历史。
在1949年后,特别是1960~1978年间,打猴鼓舞作为毛南族佯僙人“地方性知识”的“小传统”被政府认为是封建的、愚昧的、糟粕的活动,被作为“四旧”而取缔。与此同时,操演者更是被挂黑牌游行、关进“小黑屋”等方式进行批评教育,从而使得打猴鼓舞的展演和传承活动完全被中断,处于濒危失传的状态。基于这种大背景下,打猴鼓舞作为民间仪式的“小传统”自然就没有生存空间,基本上退出了毛南族佯僙人日常生活。但是关于这一段历史的集体记忆,需要我们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去挖掘整理。
1980~2000年,国家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社会利益关系、价值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文化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样板戏,“双百方针”又被政府重新认可和贯彻[5]。1981年,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舞蹈协会向全国发出联合通知,决定成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动员和组织全国力量进行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普查、收集和整理编写工作。猴鼓舞老人们看到,过去被视为封建迷信活动的打猴鼓舞现在被国家认可,具有公开展演的合法性。与此同时,曾经被政府抓起来进行批评教育的巫师为了维护自己在毛南族佯僙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利益,以及不想他们的丧葬活动包括打猴鼓舞在内继续背负着“迷信”的标签,于是与政府部门所肯定的文化类别和事项接轨。巫师的打猴鼓舞通过破例地传承给“局外人”,从而使得打猴鼓舞能够合法地、安全地传承下去。
21世纪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猴鼓舞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在非遗的保护下,为了满足地方政府的需求,打猴鼓舞必经进行“重构”,以便更好地在舞台上表演。譬如,地方政府在节日活动、重要庆典中都会邀请毛南族佯僙人来操演打猴鼓舞,借助它的表演制造热闹场面,以表达对政府成就的肯定。其次,卡蒲毛南族风情园是地方政府和旅游公司一起开发的旅游景区,打猴鼓舞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成为了当地旅游景区的“亮点”,也促进旅游景区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再者,打猴鼓舞在非遗保护下,出现了偏离传统本体内涵的趋势。原始形态的打猴鼓舞最初是由巫师在葬礼上操演的仪式舞蹈,用以纪念死去的老人。然而在非遗的保护下,打猴鼓舞在传承的动机、时间、人数、程序、服装、动作、场景等均发生明显的变化,逐渐成为了地方政府政治经济需求,从而使得打猴鼓舞的传统本体内涵发生偏离的趋势。
5. 结语
“文化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民族传统文化一些因素在社会发展背景中,或消失、或重生、或再造、或嫁接、或同根再生、或新瓶旧酒,然而不论是哪种方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没有任何传统是一成不变,传统本身也是不断生成的,也需要不断地扬弃和发展”[6]。毛南族佯僙人打猴鼓舞在文化时期被政府作为“四旧”而遭禁止,然而全国民族民间舞蹈抢救运动中又被重生,接着在国家非遗的保护中又被再造,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从而成为地方政府经济政治的需求。尽管打猴鼓舞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越来越过度表演化、逐渐偏离传统本体内涵的趋向,但仍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关键符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