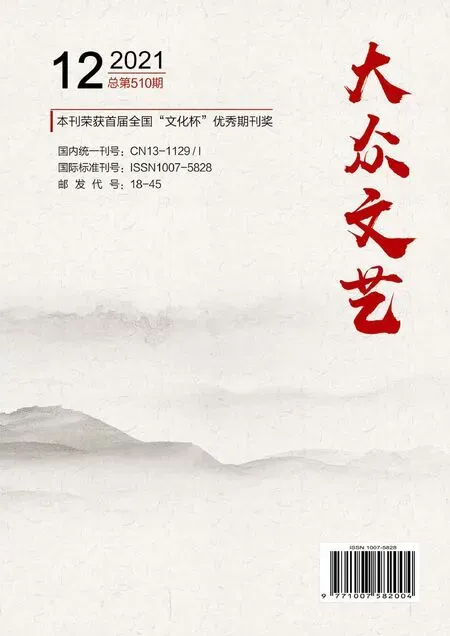论《登楼赋》的悲剧意蕴
李文青 张喜贵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214000)
有“魏晋之赋首”(《文心雕龙•诠赋》)之名的《登楼赋》,是不能被忽略的有着悲剧意蕴的名篇之一。悲剧意蕴包括两个层次:第一是构成悲剧的浅层意蕴,即现实的“苦难意识”或“人生悲剧感”;第二是悲剧的深层意蕴,是人在面临悲苦命运时奋不顾身的抗争精神。若作《登楼赋》时,王粲仅有对悲剧人生的体验和悲悯,逆来顺受或麻木不仁,而没有重拾希望,那么,悲剧意蕴便荡然无存。同时,王粲的追问与希求只能换来无尽的失落与彷徨,更增添其悲剧意蕴的厚重之感。
一、思乡怀归之悲
《登楼赋》的创作背景离不开“豺狼方遘患”和无伯乐赏识的命运遭遇。根据王国维悲剧理论,王粲被迫离开长安,投靠刘表,避难荆州,是“盲目的命运之者”1使然。但他被“心多疑忌”的刘表所冷落,滞留荆州长达十五年,则是“由于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逼之不得不如是”2。在他流寓荆州12年后,愁苦靡诉,于是“登高可以当归”以求渲泄思乡、爱国之情,登上城楼,挥毫作下《登楼赋》。
荆州美景触发了他思乡的情深意笃,“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流寓荆州被闲置,以异乡之美来反衬思乡之情。以“曾何足以少留”收尾,回应开头“暇日以销忧”,可见登楼未能“销忧”,这种曲笔反衬是王粲写思乡之情的独到笔法,更将其悲剧意蕴抒发到极致。之后他以典故自喻——尼父、钟仪、庄舄,这三种不同阶层的人代表了所有的游子——“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赋文至此、“忧”的情感由思乡之恋推进到怀归之悲,其悲剧意蕴更加凸显。
笔者认为赋中怀归之情确有归乡,却又不拘限于“乡”。首先,作品中所指的“吾土”不是作者的真正故乡(或称第一故乡),而是指十六年前离开的国都长安。“吾土”的含义被扩大,其悲剧意蕴便从个人扩大到整个国家。其次,赋中引用钟仪、庄舄之典故,亦不仅抒发异乡之思。据《左传》和《史记•陈轸传》记载,王粲所引之人皆为爱国者形象,他们的怀归之情不仅局限于家乡,而是整个故国。
思乡与归国不可分割,赋中所抒之情达到了新的高度。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家国情怀在赋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其悲剧意蕴也得到了渲染,而更显厚重凄凉。
二、壮志难酬之苦
王粲的忧思,不只是思乡与爱国之悲,亦有壮志未酬之苦。引起他思乡怀归的直接原因,便是王粲流离荆州十几年,壮志难酬的惆怅苦闷。当时,“立德、立功、立言” 是文人志士的心灵寄托,寄世之情无疑是儒家思想悲剧意识的基础,这成为窥探其悲剧意蕴的另一视角。
“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3根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王粲出身豪门世家,自幼受到儒家入世精神的熏陶,从小立志建功立业。但当时战乱频繁,因其祖父王畅和刘表有师生之谊,故而凭世交之情南迁避乱。然初到荆州,“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悦,不甚重也。”4以至于在荆州“身穷”、“居鄙”,过着“潜处蓬室,不干权势”(曹植《王仲宣诔》)的生活。
王粲对于自己的思乡怀归之情并不肯吐露痛快,根据王粲对荆州之主刘表的政治表现,他早已日渐失望,由此便可推测其难言之隐——王粲的“怀土”并不是想效仿张季鹰思妒鱼炙脍而归乡,而是希望逃离荆州,另择施展才华之地。尾段前四句“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中,本《离骚》“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恐美人之迟暮”之意。此非纯粹“求田间舍”之人所语。加之,他以“袍瓜徒悬”和“井渫莫食”自拟,借此隐喻自己虽不得志但并不是庸才,德才兼备却不为他人所知。“惧袍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两句,是全赋情感之纽结点,其悲剧意蕴渐渐达到顶峰。
这正是王粲投靠刘表十二年以来“不知所任”的悲痛写照。这对有着“累世豪族”的传统,又渴望驰逞才华、前途光明的王粲来说,无疑是痛苦的煎熬。尼采说,“一个痛苦的世界对于悲剧是完全必需的。”正是在这样的悲剧命运,赋中孤愤不平、“愀怆悲恻”、郁郁不得志的悲剧意蕴方可喷发到极致。
三、希求与担忧之矛盾
思乡怀归与壮志难酬只是王粲对即将结束的整个荆州时期生活的回顾。《登楼赋》作于王粲刚依附曹操不久但尚未受封之时。易地而处,可以推测王粲的心态是希求与担忧的矛盾结合体。朱光潜则认为:“对悲剧说来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5王粲孤身面对悲剧并没有消沉,他仍心怀希求,但展望换来的却是彷徨、担忧与无期的等待。这种矛盾亦是他悲剧意识的体现。
对于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作者有着强烈的希求与向往。在荆州的十几年,王粲血气方刚却年华虚度,不得不发出“惟日月之逾迈兮”的无尽感慨。他企盼能在“河清”之际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参考当时形势,天下混战,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逐步扫平袁氏的残余势力,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因此,东汉名存实亡,王粲已无法借助帝王的力量,依附曹操的势力而施展抱负倒是有一定希望。
王粲依附曹操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作者依附刘表不被重用,“刘表雍容荆楚……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6第二,王粲作为有识之士,只有“识时务者”才不会明珠暗投,换句话说,王粲将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文武并用,英雄毕力”的曹操身上。他劝刘琼降曹时说:“曹公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7“应天顺命,以归曹公”是明智之举。第三,曹操用人强调“唯才是举”,不仅对支持自己的人“设天网以该之”(曹植《与杨德祖书》),而且对反对过自己的人有时也能雍容大度,委以重任。因此,王粲希望借曹操之力报效国家、建功立业之说可以成立。赋中归依曹操充满希求的真情流露并非偶然。
但是,王粲在对新生活充满希冀之时,又心存怀疑、担忧、与彷徨之忧。对应赋中的“惧袍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惧”“畏”的对象是什么?刘良在《六臣注文选》中曾经指出:《登楼赋》“述其进退危俱之状。”8但他并未阐明“危惧”何事何物。笔者认为,若单单指过去的荆州生活,那么赋中的悲剧意蕴就是一种对以往悲剧的回忆,但事实并非如此。王粲“危惧”的还有归依曹操的未知生活。
首先,虽然另择新主,但他依旧担忧悲剧命运的重演。其次,王粲当时虽归曹操,但未受封,前途迷茫,吉凶未卜。曹操对自己是否真正赏识,能否做到“唯才是举”,自己能否报效朝廷,这一切皆无亲身体验,王粲不得不有所担忧与“危惧”。再次,王粲归依刘表时,曾为刘表起草《与袁谭书》、《与袁尚书》时攻击过曹操。曹操是否怀恨在心也未可知。
综上,王粲的畏惧、担忧与彷徨甚至盖过了希求的情绪。“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将这种痛苦的矛盾寓于景中,内心“凄怆惨恻”在最后的“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中暴露无遗,从“忧患意识”上升到一种“生命悲剧感”,9悲剧意识由此而被全面唤醒,其悲剧意蕴也更令人动容。
四、结语
《登楼赋》作为文学价值极高的名篇,其主题思想不仅仅是抒发了个人思乡怀归、壮志难酬之惆怅,更深层次的是对从对天下苍生的关注,以及对国家未来的忧虑。而在这种希求的追寻与迷茫的担忧中,王粲往往感受到的,是体会到生命存在形式无所依傍的孤独感与无助感。徘徊失路的正直耿介者在乱世下的“销忧”,10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使得《登楼赋》的悲剧意蕴终于达到顶峰。
注释:
1.2.邬国平,黄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册[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476-477.
3.4.6.7.陈寿.三国志•魏书•王粲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4:105-108.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06.
8.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吕向.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2:101.
9.肖晓阳.建安诗歌的悲剧意蕴[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1(1).
10.王进明.王粲《登楼赋》与李安讷《次王粲〈登楼赋〉韵》之比较[J].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6,30(03):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