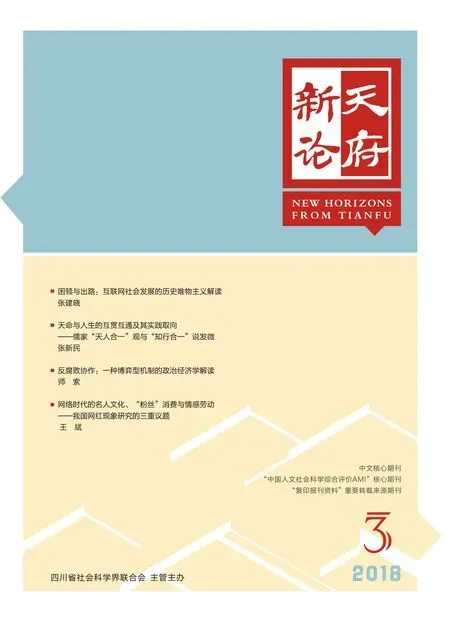阅读史视域下纂修《四库全书》的历史意义
温庆新
近年来,有关阅读史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然而,学者主要关注当今多样媒介与多元价值对阅读活动的影响。从阅读史视域关照中国古代书籍的编刻、文本价值及书目纂修,研究仍方兴未艾。而读者对中国古代书籍编刊影响的典例,莫过于 《四库全书》的纂修。目前,学界对《四库全书》纂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纂修过程、编目思想及学术价值等方面。从阅读史视域探讨纂修 《四库全书》的缘由及意义仍较薄弱。乾隆曾指出: “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故予蒐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21页。明确提出以 “文 (籍)”切入,从文治道统角度对彼时各种学术进行规范与引导。这种官方意志的主动介入,导致彼时的阅读活动皆须围绕清代政教思想展开,从而对彼时的文献生产、消费及社会文化的衍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从阅读史视域探讨 《四库全书》的纂修,将有助于还原 《四库全书》践行乾隆 “稽古右文、聿资治理”②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0年,第1页。意图的路径,进而探讨其书籍史意义。
一、《四库全书》与清代统治者确立阅读活动的 “官定”文本
由于清代纂修 《四库全书》时,首先对所录书籍的版本来源、版刻形态、版本源流等书籍的物质形态与物质实体,进行关注、筛选;但当有关书籍被予以收录或著录于存目时,清代统治者则更加注重书籍的文本意义,关注阅读者通过阅读的过程获取书籍的文本内容时所可能产生或接受的文本背后的意义。这种做法显然是把书籍当作了一种类似于信息载体 (或文本载体),从而将书籍当作是影响政治走向、社会发展、文化变革乃至人伦彝常的重要推动力,以便最终实现 “稽古右文、聿资治理”的意图。乾隆曾指出:“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7页,第518页,第1-2页。这种 “正人心而厚风俗”的思想,就是注重书籍改变时人观念与进行道德整束的重要媒介。因而,从 《四库全书》的收录到 《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清晰可见清代统治者更加注意,甚至有意引导、控制书籍意义的生成渠道及其可能结果。
为了实现上述意图,清代统治者在纂修 《四库全书》时,则须对书籍的文本、物质形态与阅读三大要素进行全面管控。其中,对阅读活动的管控尤显重要。因为阅读活动是阅读者从书籍获取文本意义的中间环节,书籍的意义也只有通过阅读活动才能最终生成。而书籍意义的生成则是书籍影响政治、社会及阅读者的最主要方式。从这个角度讲,纂修 《四库全书》势必与清代统治者限定彼时阅读活动相联系。那么,清代统治者如何通过纂修 《四库全书》而对彼时阅读活动进行限定呢?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曾提出阅读史的研究可从五个方面展开,即 “What” (读什么)、“Where”(在哪读)、 “When” (何时进行)、 “Why” (为何而读)、 “How” (怎么展开),②Robert Darnton,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enn: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77.以探讨阅读活动的读者与文本、时间、地点及周遭环境的关系,挖掘阅读活动对书籍意义生成的影响。据此而言,从阅读活动中的读者、文本及与周遭环境关系等角度看,清代统治者通过纂修 《四库全书》来限定读者阅读活动的方式,亦隐含上述五种典型路径。
首先,《四库全书》作为清代中叶以降的阅读者所能够接触到的最主要的阅读文本,是清代统治者进行官方意志与文本、阅读者三方交相沟通的主要中介物。而为实现对阅读活动各个环节的管控,清代统治者试图指定 《四库全书》作为彼时阅读活动的 “官定”文本,并通过各种形式展开对各类书籍非关 “官定”因素的审查。这种做法,并非试图以此 “官定”文本作为深入挖掘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内在自我感观,而是清代统治者以此建构文化传播价值体系的重要突破口,以便对书籍的书写内容与知识体系进行甄别、筛选。
乾隆四十一年 (1776)六月初三日 《上谕》,曰:“至于 《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朕勤加采访,非徒广金匮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7页,第518页,第1-2页。这种做法虽然客观上促使了当时 “天下”文献得以被有效查询并刊刻。经过乾隆三十七年 (1772)至乾隆四十三年 (1778)之间全国范围多频次的大规模征书,当时的 “四库馆阁”聚集了 “天下”文献中的多数。这几次大规模的征书,涵盖了 “历代流传旧书”“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的 “诗文专集”、以及 “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乃至 “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障、寿言等类”等各种文类。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7页,第518页,第1-2页。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又颁布 《上谕》,指出征书的目的在于 “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与其细者可 “游艺养心之一助”。然而,透过征书而得的书籍无法立即有效践行上述意图,且 “违碍本朝”者亦不在少数,不得不进行大规模清查。这就使得 《四库全书》所收录之书经过了 “四库馆臣”的多次 “撤改”、“抽毁”、“重校”乃至重新 “缮写”,⑤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4页。以致多少改变了该书的原始形态与内容。可见,从 “人间未见之书”的书籍原始形态,到 “公天下之好”时的书籍形态与内容,二者并不完全一致。 “公天下之好”时的书籍形态,已是经过彼时政统意图的筛选,属于一种以彼时政教意图为指导而重构的新书籍形态与文本特质。
其次,清代统治者试图通过纂修 《四库全书》展开书籍的审查。这种审查主要是清代统治者透过 “寓禁于征”的思路展开。其确立 “官定”文本的方式,大略有以下几种。
一是对书籍进行道德方面的审查。清代统治者通过对所涉书籍 “责任伦理”作用的强调,以强化阅读者对 “官定”书籍的意义之认同,从而突出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乾隆三十九年 (1774)八月曾谕旨两江、两广各省督抚,言:“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7页,第239页,第4页。邓实:《销毁抽毁书目合刊》,国学保存会,光绪三十三年 (1907)。此即是从 “正人心而厚风俗”的角度,采用目的先行的方式进行人伦道德审查,以免 “潜匿流传,贻惑后世”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7页,第239页,第4页。。这种意图在 《四库全书》中随处可见。如 “小说家类存目” 《避暑漫笔》提要指出:“是编皆掇取先进言行可为师法及近代风俗浇薄可为鉴戒者,胪叙成篇。其书成于万历中。当时世道人心,皆极弊坏,修发愤著书,故其词往往过激云。”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0年,第1223页,第434页,第512页,第435页,第553页。就是从 “人心”之于统治不利影响切入。也就是说,此类审查之举的背后意义在于:清代统治者试图在 《四库全书》中建构一种既已进行内涵限定与意义规范的道德标准,使得此类标准能够发挥引导或介入阅读者道德观念成型之类的作用,最终以符合彼时统治所需的思想来限定阅读者道德观念的主体内涵。换句话讲,通过道德审查,清代统治者以其所需的道德观念替代、或部分淹没了书籍的原始意义与道德指向,从而影响阅读者道德观念的形成。此类做法的最大影响是:最终促使全国范围的多频率、大规模、长时间的书籍查禁活动。其中,《四库全书》就不录不利于人心教化的通俗文学,并极力加以贬低。④温庆新:《从目录学角度谈 〈四库全书总目〉不收通俗小说的缘由》,《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年第11期。如认为 《西厢记》“使人阅看,诱以为恶”⑤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3页。,即是个中典型。
二是对书籍进行知识方面与形式方面的审查。这种审查主要体现在对明人书籍与通俗文学的查禁与剔除上。在清代统治者看来,“有明一代,八比盛而古学荒,诸经注疏,皆以不切于时文,庋置高阁,故杂采类书,以讹传讹,至于如此。”⑥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0年,第1223页,第434页,第512页,第435页,第553页。又说: “明自万历以后,国运既颓,士风亦佻,凡所著述,率窃据前人旧帙,而以私智变乱之。”⑦纪昀 ,等 :《 四库 全书 总目》 ,中 华书 局,1960年 ,第1223页, 第434页 ,第512页 ,第435页, 第553页。这就导致明人著述往往存在繁简不当、详略未得,援引多滥载琐碎,不得著书章法要领及体例规范等知识论方面的问题。如指出朱国祯 《大政记》:“编年纪载,繁简多有未当,殊乏史裁”⑧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0年,第1223页,第434页,第512页,第435页,第553页。,认为李濂 《祥符文献志》 “所录皆明一代之人,而至于盈十七卷。时弥近则易详,亦时太近则易滥,固志乘之通病耳”,⑨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0年,第1223页,第434页,第512页,第435页,第553页。即是此类。不过,清代统治者对书籍的知识审查,更主要体现于对所收书籍违碍清代政统思想的各种查禁;尤其是,诋毁彼时政统思想的明人诸多著述,更是遭到严厉查禁。上引乾隆所言 “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低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即是典型。其中,最著名的查禁案例莫过于钱谦益。钱氏被冠以 “不能死节,腼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狺,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而被查禁。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7页,第2394。当然,此类查禁,仍以 “励臣节而正人心”为指导。尤其是,当时更是贴出 “为立法劝谕饬缴伪妄书籍以期净尽以免后累事”的告示,指出: “若书既违碍,并无裨益于身心,更有关于身命,亦何必存留不缴,以致贻累及身,更累及于子孙,留以贾祸。人虽下愚,断不为此。”(《奏缴咨禁书目》)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7页,第239页,第4页。邓实:《销毁抽毁书目合刊》,国学保存会,光绪三十三年 (1907)。所言亦以 “违碍”与 “裨益于身心”两方面展开。据此看来,清代统治者对书籍知识方面的审查,仍以道德审查的结果为评判的主导,而非简单地进行纯粹意义上的知识讹误之类的审查。而对所收书籍的形式审查,主要体现于审查民间对官刻书籍的任意删改、翻刻等方面。据研究,“清代寺院藏经,是和统治者提倡刻经及颁赐密切相联系的。官府的经书除免费颁赐各地大寺院收藏外,经版还可供各地寺院僧俗 ‘请藏’刷印。”①傅璇琮,谢灼华:《中华藏书通史》(下),宁波出版社,2001年,第1002页。也就是说,当时若要翻印官刻书籍,是要事先 “请藏”审批的。这就从书籍的物质形态与版刻源流等方面,全面规范或管控书籍的物质形态,从而进一步限定了 “官定”文本的权威性。
上述做法,促使清代统治者以官方的权威性,对书籍的生产进行严格规范,并通过 《四库全书》的纂修,从根本上限定阅读者阅读的文本来源。同时,以人伦彝常的形而上建构,来限定阅读文本的意义指向及运行方式,最终解决阅读者 “读什么”(What)的问题。
二、清代官方意志与阅读活动的场所及文本来源
那么,彼时阅读者能够在哪些地方阅读到 “官定”文本呢?乾隆曾指出:“词馆诸臣及士子等有愿睹中秘书者,俱可赴翰林院,白之所司,将底本检出钞阅。”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42-2143页,第1768页。自乾隆九年 (1744)起,翰林院已成为纂修 《四库全书》的办公之地,收贮有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 《四库全书》等大型书籍。也就是说,清代统治者要求阅读活动的主要开展场所,是内府、翰林院等官方的藏书地。
《清史稿·艺文志》曾说:“高宗继试鸿词,博采遗籍,特命辑修 《四库全书》,以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与其事者三百余人,皆极一时之选,历二十年始告成。全书三万六千册,缮写七部,分藏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热河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综阁、杭州文澜阁。命纪昀等撰 《全书总目》,著录三千四百五十八种,存目六千七百八十八种,都一万二百四十六种。”③赵尔巽,等:《清史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81页。上述 “七阁”是允许 “词馆诸臣”钞阅的,文汇阁、文综阁、文澜阁等 “南三阁”更是面向社会开放。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上谕》曾指出纂修 《四库全书》的目的在于:“原以嘉惠士林,俾得就近钞录传观,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俾观摩之宝,殊非朕崇文典学、传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全书本有总目,易于检查,只须派委妥员董司其事,设立收发档案,登注明晰,并晓谕借钞士子加意珍惜,毋致遗失污损,俾艺林多士,均得殚见洽闻,以副朕乐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42-2143页,第1768页。据此,士林学子虽说可赴 “南三阁”对数量颇为可观的书籍文献进行 “钞录传观”,但其所 “传写”的文本已是 “用光文治”的 “官定”版本。这就通过阅读活动的地点限制 (即限定 “Where”),进一步对阅读者的阅读行为与日常阅读内容进行有效引导与强力钳制。
同时,纵观顺治至光绪朝的 “官学”教育措施,可以发现清代统治者曾多次颁赐藏书于学官,试图通过教育的方式,进一步强化 “官定”文本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比如,顺治九年 (1652)规定 “嗣后直省学政将 ‘四子书’‘五经’,《性理大全》 《资治通鉴纲目》 《大学衍义》 《历代名称奏议》《文章正宗》等书,责成提调教官课令生儒诵习讲解,务俾淹贯三场,通晓古今,适于世用。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意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通行严禁。”⑤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八,光绪二十五年 (1899)重修本。就是强调以 “钦定”“颁赐”的书籍作为教育启蒙及思想规范唯一 “范本”的典型;甚至限定不利政教的书籍的传播。这种做法,一方面进一步从书籍流通的角度扩大 “官定”文本的流传面,另一方面则强化阅读的活动场所与活动过程必须时刻处于彼时官方的管控之下。
上述对阅读活动场所的要求与文本来源的限定,实系清代统治者试图对书籍的生产与流通施加影响的表现。它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书籍的生产、流通乃至普及传播,以及玩愉功用的张扬。同时,也导致书籍的整理与相关书目的纂修,是站在与国家政治层面同一层次的高度,紧随彼时的政统意图。从清代阅读史的演变史迹看,此类做法所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促使有清一代的统治阶层、知识界与书目编纂者,依旧从彼时的政教需求出发,以传统书目的知识结构为导向,继续否定诸如已被罢黜的通俗文学、被查禁的明人文集等书籍的阅读、乃至意义的挖掘与延展 (晚清以降受西方知识结构影响而改变图书分类体系的书目除外)。这就促使清代 “四库馆臣”在关注阅读文本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内容特质之外,更加关注文本 “边界”之外的意义、乃至强化此类被 《四库全书》所录书籍在清代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及其文化担当。
不过,彼时的书籍查禁活动,虽然对生产、收藏乃至阅读 “触碍书籍”者,提出了诸多惩罚措施。但这种查禁行为客观上激发了作为普通读者的民众的好奇与猎奇心理,仍旧狎携相关作品,进行隐性阅读。以致这种书籍查禁活动,毋宁说是从官方层面对相关书籍的阅读活动,作了一番生动宣传。乾隆三年 (1738)颁布的 “禁淫词小说”限令曾说:“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饬所属官,严行查禁,务将书板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一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①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1页。此类禁令虽罗列了对参与传播 “淫词小说”者的详细审查与惩罚措施,然 “有仍行造作刻印者”云云,则表明彼时朝廷查禁已广泛激发普通大众阅读 “禁书”的兴趣。也就是说,清代统治者郑重其事地对戏曲与小说进行限定的举动,恰恰说明戏曲与小说在当时大行其道的实情,以致形成一种带有普遍特征与群体共性的阅读现象。从这个角度讲,清代朝廷虽然严控阅读活动的各个环节,使得阅读者在阅读活动过程中的个性体验与心灵启悟,不断受到来自官方的严控;但普通读者对于书籍政教意义之外的追逐仍屡禁不止,客观上导致了在书籍传播过程中的政教意图、文化启蒙之于读者的影响,也仍将持续下去。这就更加显现出彼时统治者纂修《四库全书》所意图实现文治教化的重要性。此举使得 《四库全书》的纂修意义,超越了书籍的形制、版本及生产、消费等传统书史研究的范畴,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②王玉超:《论 〈四库全书总目〉对举业文献的著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更是蕴含浓烈的文化史、社会史及思想史方面的价值。
要之,清代统治者通过征书、查禁、颁赐及纂修并开放 《四库全书》等多样举措,在书籍的生产、流通及传播效果等方面,以国家权力予以强制管控的方式,试图改变当时阅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行为,从而限定阅读者对所阅读文本的意义讨论。
三、《四库全书》与阅读活动的过程展开及意义指向
可以说,清代的阅读者、国家与阅读物 (书籍)三者的关系,可表述为:通过书籍,清代统治者以政教意图主动介入,迫使阅读者接受彼时的官方意志,最终促使阅读活动靠向彼时的政教意图,进而对彼时乃至其后的文化传播与学术衍变施加影响。也就是说,清代统治者试图以政治强权为保障,充分关注阅读展开过程中的知识传播效果,以便从清代政教思想与国家意志等方面对阅读活动进行有效限制。
据前所述,清代统治者将作为阅读者的士大夫阶层与普通大众的阅读行为,通过政权的强制推动与权力的支配等方式,控制书籍的生产与刊刻、文本的形态与内容,进而影响书籍的传播 (包括内容传播、形式传播与传播范围、意义导向)。上引乾隆所谓 “词馆诸臣及士子等有原睹中秘书者,俱可赴翰林院,白之所司,将底本检出钞阅”,就明确指出士子所能接触到的书籍本文,必须以内阁或翰林院所藏为据。也就是说,清代统治者要求阅读者所阅读的文本,不得与 “官定”文本存有偏差。乃至要求:“翰林院及大臣官员”等知识阶层所 “欲观秘书者”,除须 “请阅”外,在 “钞阅”过程中要 “随时存记档册,点明帙数,不许私携出院,致有遗缺。如所抄一本,文字偶有疑误,须行参校者,亦令其识明某卷、某页、某篇,汇书一单,告之领阁事,酌派校理一员,同诣阁中,请书检对。”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7页,第2页。这里除了清代统治者对书籍生产的严格要求外,更是对 “官定”文本内容严控的体现。这种意图的实现,得益于乾隆所提出的嘉惠士林之举。彼时统治者试图提供 《四库全书》及颁赐 “官定”文本,给知识群体及社会大众进行无偿阅读、钞录,鼓励民众阅读已经过审查且集中展现当时 “官学思想”的 《四库全书》,以最终影响阅读的发生及其所带来的知识效应与社会效应。虽说允许 “将底本检出钞阅”的做法,势必会进一步扩大 “官定”文本的流传范围与影响力,但此类做法也因此限定了文献的主体内涵,强化 “官定”文本作为书籍流通的唯一合法性与有效性,从而试图将普通读者的阅读行为变成一种符合清代政教需求与道德规范的内省式或修炼式阅读。此举从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阅读者自身的阅读意图之于文本意义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讲,清代读者 “为何而读”(Why)的文本内容与内涵、意义,必定是要符合彼时政统所需的。
同时,此处对阅读文本的内涵限定与阅读活动的效果预判,主要是试图建立导向利于政统、惩劝教化之一面的渠道。《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曾指出:“今于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瘴,用著劝惩。”②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0年,第17页,第18页,第19页。这就对编入 “总目”的书籍,进行大到 “国纪朝章”,中到学术源流,小至作者爵里、文字差异的全方位考订。试图以此官方颁布的刊行本作为阅读的 “指定”文本,从阅读的内容、阅读的意义等各个方面进行规范指导,最终实现惩劝的意图。换句话讲,《四库全书》是从图书的知识论内容与价值论意义两方面,限定了被阅读文本的本质特征与意义的可能指向。
在这种情况下,编排 《四库全书》以成 《四库全书总目》的过程,就是以国家意志进行书籍的编目,进一步实现国家意志、读者阅读与书籍传播三者的有效统一。换句话讲,《四库全书总目》是以精准的理论总结,进一步对 《四库全书》乃至同类相关书籍的意义,作出示范意义的严格限定与指导。这在可看作是 《四库全书总目》“总序”的 “凡例”中,多有体现。如 “凡例”云:“文章德行,在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今所录者,如龚诩、杨继盛之文集,周宗建、黄道周之经解,则论人而不论其书。耿南仲之说 《易》、吴开之评 《诗》,则论书而不论其人。凡兹之类,略示变通,一则表章之公,一则节取之义也。至于姚广孝之 《逃虚子集》、严嵩之 《铃山堂诗》,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而广孝则助逆兴兵,嵩则怙权蠹国,绳以名义,匪止微瑕。凡兹之流,并著其见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见圣朝彰善瘅恶,悉准千秋之公论焉。”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0年,第17页,第18页,第19页。就对如何挖掘 “文章”与 “德行”的意义及方法,提出了 “论人而不论其书”、“论书而不论其人”的原则,试图剔除不利 “见圣朝彰善瘅恶”的言语。又如, “凡例”云: “九流自 《七略》以来,即已著录。……今但就四库所储,择其稍古而近理者,各存数种,以见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备,不复搜求,盖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④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0年,第17页,第18页,第19页。就明确指出 《四库全书》的图书收贮标准与清单目录的展开,皆以 “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从而限定非此道书籍的被收录与流通。所谓 “著其见斥之由,附存其目”云云,就进一步明确罢黜相关书籍的政教缘由。甚至,乾隆要求纂修 《四库全书总目》要指明 “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7页,第2页。。此类意见就从理论层面将清代统治者进行书籍生产、流通的指导思想,展露无遗。由此可见,清代统治者试图明确 《四库全书》的收贮图书原则,以此对阅读者的思想认知及其过程进行干预,最终限定阅读者阅读活动的思想语境与意义导向。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统治者并不关心谁是 《四库全书》的真正阅读者。从前引乾隆三年 “禁淫词小说”的限令可知,彼时统治者对购买且直接阅读的普通读者、书商等发行方 (亦是一类可直接接触书籍文本的重要读者)、管理者 (作为官方管理的实行者在进行书籍审查时亦需进行文本阅读)等诸多可能展开阅读活动的直接阅读者或潜在阅读者,进行管控与处罚的行为。这其实是以彼时的政教思想为主导,从宏观层面对阅读者人群作进一步限定的体现。也就是说,彼时统治阶级试图从作者、出版者、印刷者、销售者、管理者及阅读者等,诸多可能以书籍为中介物而展开交流的人群及其“交流圈”①芬克尔斯坦,麦克利里:《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页,第32页。,进行全方位管控,甚至阻隔不同人群间对于书籍文本的 “阐述交流”。此类做法并非关注 “作者 (author)脑海中的理想读者”②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7页。,而是从彼时的社会实际出发关注当时阅读活动的潜在施行者,以此作为一种宏观审视彼时阅读活动的依据,从而促使彼时阅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与阅读时的人生感悟、价值关怀,皆要受限于彼时官方意志的禁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乾隆十九年四月颁布《钦定学政全书》卷七 《书坊禁例》“盗言宜申饬”条所言:“阅坊刻 《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 《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查康熙五十三年,奉禁坊肆卖淫词小说。臣请申严禁止,将 《水浒传》毁其书板,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而悍俗还淳等语。查 《定例》,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裨文业诸书,其余琐语淫词,通行严禁,违者重究。是教诱犯法之书,例禁森严。今该御史奏请将 《水浒》申严禁止等语,查琐语淫词,原系例禁,应如所奏请,敕下直省督抚学政,行令地方官,将 《水浒》一书,一体严禁。亦毋得事外滋扰。”③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522页。此处所言 “教诱犯法之书”,表明清代统治阶层与知识阶层忧虑市井流民阅读 《水浒传》之后对彼时社会秩序、民俗道德及风气习气的反面影响,着重关注 《水浒传》对于市井流民日常生活的渗透。囿于文献缺失,现今已无法有效还原市井流民进行阅读活动的过程与细节,但清代统治阶层对市井流民阅读活动所产生结果的关注,与 《四库全书》不录通俗小说一道,构成清代统治阶层对市井流民阅读活动的多重钳制方式。据此而言,清代统治者纂修 《四库全书》与 《四库全书总目》时,并非关注彼时阅读者本身的阅读行为,而是试图赋予此类阅读行为能够与彼时官方意志相连的意义圈定方式,最终形成以国家组织为主要手段推动文本意义生成的意图。意即要求或限制阅读文本的意义生成,必须符合清代政教意图等彼时特殊的历史语境,强调阅读活动及其展开过程,服务于清代政治、社会与文化建设所需的 “公共空间”意义,从而具有显著的 “文本的社会化”④芬克尔斯坦,麦克利里:《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页,第32页。特征。当然,此类意图实现的关键,即是 “官定”文本的编纂与强制推广。
总之,清代统治者首先通过 《四库全书》的规范阅读,来限定阅读文本的内容内涵与文本意义,对阅读活动的过程进行引导,从而限定文本意义的生成。同时,通过纂修 《四库全书总目》,进一步从理论层面限定阅读活动的意义指向。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实现限定并规范阅读文本与阅读活动的政教价值与思想语境,最终解决 “为何而读”(Why)与 “怎么展开”(How)的问题。
四、余 论
从书籍的生产初衷、流通过程及传播效果看,《四库全书》的纂修是清代统治者试图通过对阅读活动的文本、内容、形式、传播渠道及传播意义进行控制,达到收归人心以利于教化的意图,最终建构一种统治者所需的阅读信仰与知识谱系。这种以国家意志为主导而建构的阅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并非导向阅读者充分激活文本意义的独特价值,而是淡化阅读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强化或规范阅读者阅读的过程及对文本内容的阐发,从而强制改变阅读者的阅读习惯,关闭阅读者影响文本意义生成的非官方渠道。也就是说,《四库全书》的纂修,首先预判了阅读者对文本意义生成的可能性结果,并进行符合彼时政统所需的引导,促使 《四库全书》的传播范围与意义指归,皆能得到合理有效的管控。这就很大程度上限定了乾嘉时期的阅读群体借阅读的活动,来挖掘其所阅读文本的可能意义,更是限定了阅读者基于阅读而引发的生命伦常之类的哲思。也就使得当时的阅读活动,势必由一种原本相对个性化与私人化的 “心灵”体验,全面转而向意义固定化的国家意志靠拢,从而有意淡化阅读活动中阅读者的兴趣爱好与审美标准,阻隔阅读者与阅读物之间的双向交流与互动,限定阅读者阅读时的闲适心态与自由精神的发挥。此类做法,使得彼时通过征集汇编的书籍,皆能被纳入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作为一种文化物品乃至教育必需品而出现。可见,清代统治者以主动介入的方式来影响图书的出版与被阅读的活动环节,最终实现保护统治者的国家利益与价值导向的意图。这与西方书籍强调私人化阅读的习惯与个性化体验的文本意义生成方式迥然有别。
当然,为了使论题较为集中,本文主要从清代统治者的纂修意图分析 《四库全书》的历史意义,而对 《四库全书》纂修之后时人实际阅读活动的还原以及此类阅读活动对 《四库全书》 “经典化”意义生成的客观影响,所论仍较为欠缺。近人张之洞 《輶轩语》 (1875)曾对彼时四川学子指出:“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又说 “《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①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14681页。明确提出通过阅读 《四库全书总目》来了解学术门径、进而了解古人学术思想的治学思路。这种对 《四库全书》及 《四库全书总目》实际阅读的行为,对 《四库全书》的历史意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述及,此处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