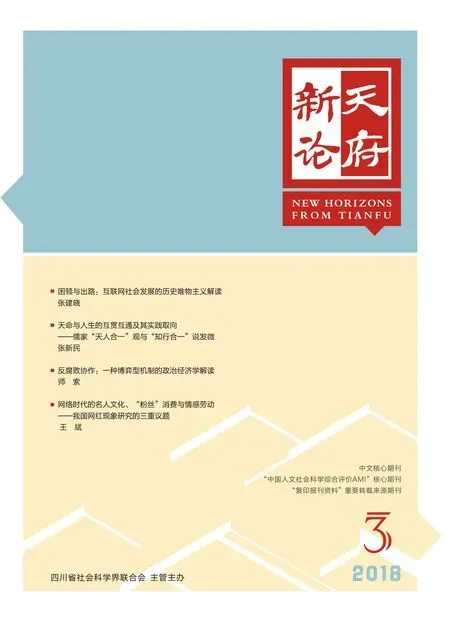“濯足”书写的唐宋转型
陈 可
“濯足”本意指浣脚去垢,是一项日常的身体清洁行为,经由语义与图释的双重展衍,呈示出特殊的文化样貌。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至晚唐间 “濯足”语义的梳理,探讨这种日常行为如何经过虚实相与的联想、构设,完成概念的定型;进而对宋代 “濯足”书写征状进行分析,解读其对 “适身”体验的热衷以及由此建立的生活美学,并以归隐主题为例,着重探讨了唐、宋间 “濯足”书写的差异;全面再现 “濯足”概念在宋型文化中的生存状态,或可有助于唐宋转型的细节研究。
一、先秦至晚唐:虚实相生的语义流变
儒家文化体系首先对 “濯足”进行了定义,最早的文献记载见 《孟子·离娄》:“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①焦循:《孟子正义·离娄章句上》,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497-501页。这里建构了关于濯足的原始命题:清水濯缨,浊水濯足,劝喻 “世事皆在于自我的处置和选择”,“濯缨”与 “濯足”的对立强调儒家适应环境、积极能动的主体理念。汉代重析先典、注经成风,又有了新的释义:
……缨在上,人之所贵,水清而濯缨,则清者人之所贵也;足在下,人之所贱,水浊而濯足,则浊者人之所贱也。……清,斯濯其缨,浊,斯濯其足。贵、贱人所自取之也。……清斯喻仁,浊斯喻不仁,言仁与不仁,见贵、贱亦如此也。②赵岐:《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5910-5915页。
赵岐将 “清浊之择”与 “贵贱有别”相联系,将 “濯缨” “濯足”的具象行为升华为 “仁与不仁”的抽象命题,以相对负向的涵容确立了 “濯足”书写的初级指涉:浊—贱—不仁。
西汉间,“濯足”又化用了道家文化增持并固着了另一重涵义。《楚辞·渔父》中屈子既放,游于江潭,渔父以 “淈泥扬波”“哺糟歠醨”①洪兴祖:《楚辞补注·渔父章句第七》,白化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179-181页,第179-181页,第179-181页。劝之未果,遂去且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②洪兴祖:《楚辞补注·渔父章句第七》,白化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179-181页,第179-181页,第179-181页。此中的渔父同样引用了 “濯缨濯足”的命题,劝慰屈原选择一条与世沉浮、避祸全身之路,谣词以水之清浊暗喻世道的清明和黑暗,以 “濯缨濯足”的区别处置论证“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③洪兴祖:《楚辞补注·渔 父章句第七》,白化文点 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179-181页 ,第179-181页, 第179-181页。的观念。此间的濯足与孔子 “自取”式的积极干预相反,它强调的是 “顺势而为”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故此成就了遁世、逍遥的隐逸主题,并在后世传承中经久不衰。
秦汉之际,儒学和道学的共同加持生成了 “濯足”最初的文化指代。作为对状命题的负极,“濯足”书写携其比喻的虚指属性进入文学领域。相对于头、面而言,跋泥涉水的足部是人体相对污浊的部位,因此,先秦 “浊水濯足”的思路一方面来自于生存资源有限的客观环境,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清浊与尊贱的相应类比。污浊的部位若得到清洗则意味着通体清洁,而身体的清洁引申至精神领域,就生成了去除俗污、清风避世的指向。这种从实入虚的想象,让 “体”与 “神”交融贯通,达成 “异质同属”之态,这也正是中式先哲外感风物、内悟心神的思维方式,又恰是此种虚实相与的思路,为 “濯足”语义的发展增生了拓换无端的空间。 《太玄赋》里扬雄以 “踞弱水而濯足”之句描绘高蹈自由、不与流俗的形象,将 “濯足”从固化的对状命题中解离出来,赋予其独立的文学喻指。这种从 “浊水”到 “弱水”的转换,便是上述思维拓展的一个典型, “濯足”与清水的逆向搭配,带来语义属性从负极向正极的偏移,以足部的清洁来喻示精神的净化,是对先秦命题相反相成的升华,而这种趋势在魏晋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呈现。
时至魏晋,“濯足”分生出了虚指与实涉两个层面,各自衍化开去。虚指的层面,清洁 “目标”从身体向精神的引申,催生了意义叠加的喻指,“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左思 《咏史》)以“濯足”之举形容精神界域的高洁放旷、清峻通脱,此种不慕权贵、意在林泉的意识抉择也是魏晋风流最得体的注脚。“朝弹冠以晞发,夕振裳而濯足。”(陆云 《纡思》)“临世濯足,希古振缨。”(夏侯湛 《东方朔画赞》)等也均表达了同样的隐逸林野、舒啸山岗的名士气度。至于 “揔辔扶桑枝,濯足汤谷波。”(陆机 《前缓声歌》) “假翼鸣凤条,濯足升龙渊。” (陆机 《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诗》)“吸朝霞以疗饥兮,降廪泉而濯足。”(挚虞 《思游赋》)“浮沧波而濯足兮,入三山而解裳。”(阳固 《演赜赋》)则皆以 “濯足”之态虚构理想的艺术形象, “濯足”之处由 “浊水”一跃为“谷波”“龙渊”“廪泉”“沧波”,表明其文学指涉完成了正向的升级,虚指成分在原生命题的比喻义上更进一步,通过 “拟态”构生出充满人文意味的综合暗示:从陆机 “凤梧龙渊”的儒式赞励,到挚虞 “识穷达、任天命”的玄致推思,再到阳固 “守冲寂以无为”的道家意态,皆被熔炼于 “濯足”的主体形象之内,言传意会着更为抽象、高格的人文内涵。
实涉的层面,“濯足”以本生义首次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方驾扬清尘,濯足洛水澜”(《日出东南隅行》)是对春游佳人清颜淑状的描绘,“临涯咏吟,濯足挥手”(《洛禊赋》)是对上巳节民众出游的春景展演,“扬素波以濯足,溯清澜以荡思” (《归田赋》)则是以山水体玄的具体举措。“濯足”以具象行为进入文学领域,一方面表明文学自身有了发展,表述对象虚实有括、更为丰繁;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佳人艳容的直白肯定,还是对民风开放的热烈描摹,抑或是对 “体散玄风,神陶妙象”的汲汲求索,都是魏晋文士在任诞真率、适性超脱的意识形态下所作出的举动,实体化的“濯足”正是这种清流气质在文学表达中的天然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虚实两路的 “濯足”书写,皆以流丽典雅的文辞写就,与魏晋士人的气度仪容有着内在的通融。
如果说 “濯足”在魏晋人的意识领域中获得了雅致的虚化,那么大唐气象不仅承续着这般风致典雅,更平添一笔雄放,“晓策六鳌,濯足扶桑。” (司空图 《诗品二十四则·豪放》)藉道悟之真消纳人间万象, “濯足将加汉光腹,抵掌欲捋梁武须。” (皮日休 《奉和鲁望独夜有怀吴体见寄》)抒发远世的疏狂。此外,“濯足”更被塑造成典型意象:对归隐之志的强调,有李白 “终当游五湖,濯足沧浪泉。”(《郢门秋怀》),有李颀 “葛巾方濯足,蔬食但垂帷。”(《不调归东川别业》);对林泉之乐的渲染,有王维 “漱流复濯足,前对钓鱼翁。”(《纳凉》),有皮日休 “量泉将濯足,阑鹤把支颐。”(《五贶诗·华顶杖》);对友人的赞誉,有杜甫 “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寄韩谏议》),有白居易 “濯足云水客,折腰簪笏身。”(《招王质夫》)。唐人一方面借濯足 “出尘”之属喻取 “出世”之意,另一方面又以直观的美誉奠定了林下之享的优雅风范。“濯足”意象的生成纳取了唐诗与生俱来的风雅之气,与之相关的审美范式统统被打上典雅、高致的烙印。
雅化的虚构从中唐开始出现了分歧的声音,先是韩愈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山石》)放弃了虚构,后有白居易 “脱袜闲濯足,解巾快搔头”(《何处堪避暑》)背离了雅化。“濯足”书写的状态一路走向实化与通俗。尤与惯常清雅指向不同的是,白诗中 “濯足”与 “搔头”的联袂出现,塑造了一个避雅就俗的形象,诗人用 “脱袜” “解巾”的平俗打破 “衣冠楚楚”的约束,在个体的自适与官场的牵绊之间做出了取舍,从而以 “拙退有分、荣耀无求”①白居易:《白居易诗集校注》,谢思炜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2328-2329页。的价值观念,劝慰遭逢贬谪的友人。这里的 “濯足”明显消解了临流高逸的属性,转而以近乎粗鄙的形态出现在文献之中。从此而后,“俗化”的声音几见沉浮,附着在 “濯足”语义上的高端印象悄然间开始溶散,消极的意味寸滋缕生。晚唐之际,李商隐甚至将 “清泉濯足”列为 “杀风景”②魏庆之:《诗人玉屑》,王仲闻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501页。“《义山杂纂》品目数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杀风景,谓清泉濯足,花下晒裈,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之首品。可见 “濯足”之举已走向唐人品味的 “大忌”。
二、适身体验与生活美学:“濯足”书写的宋代转型
“濯足”经唐诗的培植成为意象,雅致与虚化的书写征状一路亢进,至晚唐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审美疲劳。有宋一代的文人粉墨登台,建立起新的审美秩序。不同于唐式 “濯足”对耽于泉林、遗世独立等的精神渲染,宋式书写将笔墨的焦点转移至具象的体感摹状,逐渐生成了倾向于适身、从欲、戏乐等属性的市民化特征,进而在此般日常俗行的体验中,建立了平实理性、旷达通脱的生活美学。
比之唐,宋 “濯足”书写的总体见载量骤增,唐诗言及 “濯足”者一十七首,宋诗则翻升至百首③该数据由 “《全唐诗》在线检索系统”、“国学大师 《全宋诗》检索系统”平台提供。;单人作品中亦如此,唐单人作者对 “濯足”一题的书写仅偶尔为之,宋单人作者则喜反复载写。个中翘楚,非苏轼莫属,其诗作中多次出现有关 “濯足”的记录:
我来方醉後,濯足聊戏侮。(《白水山佛迹岩》)
波生濯足鸣空涧,雾绕征衣滴翠岚。(《过岭二首》)
一笑翻杯水溅裙,余欢濯足波生隘。(《与胡祠部游法华山》)
褰裳试入插两足,飞浪激起冲人衣。④苏轼:《二月十六日,与张、李二君游南溪,醉後,相与解衣濯足,因咏韩公 〈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乐而忘其在数百年之外也。次其韵。》,《苏轼诗集》,王文诰集注,孔繁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第198-199页。
投篙披绿荇,濯足乱清沟。⑤苏轼:《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灭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庢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於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苏轼诗集》,王文诰集注,孔繁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第122-129页。
山头望湖光泼眼,山下濯足波生指。①苏轼:《至秀州,赠钱端公安道,并寄其弟惠山山人》,《苏轼诗集》,王文诰集注,孔繁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第411-412页。
诗中对 “濯足”的描绘,不同于唐代一味的虚意指涉,而全部来自于苏轼的亲身体验,也有别于晚唐对 “清泉濯足”的鄙视,反倒充满了清畅欢悦、自得其乐的情绪。“趾间生波”的欣享欢脱,“飞浪冲衣”的形骸放浪, “翻水溅裙”的无拘无束,都为 “濯足”注入了新的美学意义,从白居易“濯足”起始的追求个体自适的倾向,至此得到全面发展,诗人以 “弃拘束”的解衣浣足,化解着案牍劳形,缓释着羁旅疲惫,同时在更深度的层面上消化着人生所赋予的荣枯与穷达。
这种对濯足之乐的体感描绘,为宋代濯足书写建立了一个新的审美范式,文人们放弃了对其抽象意义的凝铸,转而将感受的焦点移位到切实的适身体验,以体感的描摹替代形象的构设,传达经验与情绪。“清泉濯足冷,紫菊染巾香。”(宋无 《已亥秋淮南客中怀故里朋游寄之》)“濯足涧泉碧,洗耳松风寒。”(程公许 《行至罗江代者爽期得史者书复还涪滨径走富乐山中借馆》) “曲肱野店睡斜日,濯足溪桥鸣细波。” (陆游 《蛾眉村旅舍作》) “濯足就寒流,憩锡投古寺。” (释文珦 《放浪诗》)“乱流两白足,何日踔疏逸。” (项安世 《濯足万里流》) “天风吹散发,山月照濯足。” (朱继芳 《沧浪风月》)“山夫伸足承下沫,阴风凛凛生毛发。”(蒲寿宬 《濯足瀑下》),等等。
以苏轼为首的宋人执著于体感的直观描摹,将切身之触、目击之状、耳遇之声等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并赋予其天然纯粹、积极美好的书写征状。历来的人文传统,对适身之举的追嗜描述往往予以否定或是婉转的表达,荀子肯定 “人欲之养”,却将口、鼻、目、耳、体的感官享受导向 “礼者养也”②王先谦:《荀子集解·礼论篇》,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346-378页。的目标;枚乘铺陈 “练色娱目,流声悦耳”,用极尽能事的官能描绘,试图阐释一种更高级的身欲满足,却必须要托举一个 “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③枚乘:《七发》,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二十,中华书局,1958年,第474-478页。的核心。宋前,适身体验的书写节奏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先扬后抑,“节制”与 “消除”作为关键词,与之交互而生。而待宋时,一以贯之的旋律出现了顿挫之音,对身体感受的耽嗜,变得直观而坦荡,濯足书写对适身体验的满足,自然也不吝于趋向嗜好之境地。例如,苏轼除了在诗中数次言及濯足之乐,其 《秦太虚题名记》中也有 “出雷锋,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④苏轼:《苏轼文集编年校注》,李志亮点校,巴蜀书社,2011年,第219-223页。的记载,周必大在 《泛舟游山录》中还特意回忆了 “顷年尝同章茂之兄弟剧饮于草堂,濯足偃松间”⑤李德辉:《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第374-382页。。
对适身属性的认同,甚至获得了权力上峰的肯定。《齐东野语》记载了高宗命画师为吴郡王作画一事,⑥周密:《齐东野语·吴郡王冷泉画赞》,张茂鹏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184页。该画 “图庄简野服濯足于石上”,并诗赞曰 “扫除膏粱,放旷林泉”。尽管该事件一直作为君臣相谐的典范流传,然细究起来,意味深长:此图成于吴郡王 “私下”濯足的 “次日”,这惊人的“即时性”显然来自于皇帝的授意,包裹在皇恩垂慈之内的分明是具有控制意味的告诫,皇朝的掌权者以对外姓皇亲 “濯足”之举的褒扬,来潜在地表达自己的意图——鼓励有裙带关系的臣子逍遥乐世,而不是过多地介入政治,该图对 “野服”的着意描绘也指明了这一点。
依上述,宋时濯足风行的重点不再是唐时的精神指向,而是由追求 “适身”开始,沾染了从欲与戏乐的属性。“濯足玩水云,纵目观野烧。”(吴芾 《和楼大防韵》)“吹衣信和风,濯足解双履。”(张耒 《感春十三首》) “下马古道侧,濯足清溪边。” (文同 《二里溪濯足》)这些记载充涌着闲适、自由和欢愉,所称颂的乐趣来自于基础、直观的感官之享,是不需要经历文化训练也能获取的快感,明显出自市民化的审美取向。这取向通俗易纳,由下而上给精英阶层的娱乐带来新的模式,文化精英们择其缓身心、释天性,一洗 “久在樊笼里”的倦怠。
如此,唐人需要跻身翘首方能涉及的灵魂高逸,变成宋人欣欣取之的平常戏乐。相比于唐人“举身憩蓬壶,濯足弄沧海”那昂头高眺的姿态,俯首躬身成为宋人濯足专有的姿势—— “波生隘”“涧泉碧”“江无波”乃至 “乱流两白足”皆由低头俯视的视角得来, “乱清沟” “插两足” “就寒流”“承下沫”也非屈身就水的体态不能完成。姿态的伏低,促使宋人的主观审美走向了平实与细致,如果唐人以长焦全景式的取像定格了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的高深之致,宋人则以微距特写的镜头捕捉了 “濯足溪桥鸣细波”的微观之美。这是因为,唐型文化 “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①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1972年。故整个文化系统处于与外界不断交流的开放状态里,唐人的濯足书写,便总是洋溢着主动与天地交接的狂放感、拓外感,动辄弄沧海、扶桑,势要搅动万里长流;宋型文化 “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②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1972年。其体察与思考转向内心和细节,蕴含着持心守性、躬体实践的敛聚之态,故常状绘水波、微鸣乃至体感、素心。“濯足”书写从半空里的虚致之象转移到足下、身周的可感之境,语义指涉也由唐时的抽象浑融,化为宋式的具实可触、细致入微。
当然,宋人的 “濯足”书写并未在适身、戏乐的维度一味地沉溺,而是藉此建立了新的生活美学。苏轼将 “濯足”作为独立题材写入诗歌 《谪居三适·夜卧濯足》,记载了谪地艰辛的生存状况,而后发出 “冠履装沐猴”的自嘲。诗人以濯足之 “适”,浇沃了精神的根系,体感慰藉虽然短暂,却培生了趋于恒定的从容心境,这正是苏轼旷达通脱的人性写照。诗人对琐碎平庸的生活事件进行文学再现,在常人极易忽略的生活细节里,发掘哲理,培植意义,为 “濯足”注入平静淡泊、自持自适的生活美学。而这种通过 “濯足”表达的人格风范,亦得到了世人的认同与追摹,苏辙有 《次韵子瞻谪居三适其三夜卧濯足》,同样是在南谪忧苦环境的记录之后,萌生了 “名身孰亲疏,慎勿求封侯”的价值观;又有张九成 《读东坡谪居三适辄次其韵》,抒发 “生平苦寒痹,一洗皆已瘳”的快意。
苏辙、张九成所承续的不仅仅是凡俗入诗的美学观念,也是士人在逆境之中疏朗达观、秉持自我的精神内核,它暗含着个体自适超越冠履劳形的价值趋向,更是一种以对适身体验的智性追逐来直面起伏人生的哲学策略。在离弃 “濯足”高雅美学的进程里,宋人愈发认同了 “自适”的重要,“雅”是需要不断修习、收束情性的过程,而 “俗”是就坡放驴式的散漫随意,宋人对于自体舒适的寻求,自然令 “濯足”的价值取向趋于俗实,而这样的俗实并非真正的放荡无忌,反而来源于深广而持重的人生体悟。正如陆游写 “土釜暖汤先濯足”(《宿野人家》),是因为 “老来世路浑谙尽,露宿风餐未觉非”。见惯百态,然后坦然语俗,这是宋式 “濯足”对于困顿人生的消化和持守。
三、“濯足归隐”的唐宋诗叙变迁:主体强调与时序紧迫
主体的强调和紧迫的时序,是宋人建立的有关 “濯足”书写的审美范式。下文拟以 “濯足”的归隐主题为中心,考察唐、宋诗中濯足书写状态的差异,力求窥探两代士人观念的变化以及文化转型的细节。
宏观而言,唐式 “濯足”的主体多为虚设的形象,而宋式主体则为书写者本人。譬如描绘林野之逸,王维的 “漱流复濯足,前对钓鱼翁。”(《纳凉》)仅仅勾勒出一个正在濯足的点景人像,主体视角则在静态的画面之外进行隔空审美;而文同笔下的 “濯足清涧滨。……待我如佳宾”(《夏日闲书墨君堂壁二首》)则是我入此境,此境著我,高喧着主观体验。又如赠念友人,杜甫 “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寄韩谏议》),其 “濯足”喻指需经虚构的 “美人”完成;而乐雷发 “洞庭濯足共题诗,今听骊驹话别离”(《赠别陈东甫呈尚书钟公》)的濯足行为则是由诗人携友共同完成。
数例可见,宋式 “濯足”主体的凸显成为引人瞩目的现象,得以强调的不仅有形式上的人称代词,还有宋人感受天地、思辨万物的独立人格,它所承载的情感与志向的投射,诠释着士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而这种人格的生成,离不开人文环境与主观致知的交相孕育。以对隐逸主题的表述为例,唐人惯将意义链接到一个 “非我”的艺术形象之上,储光羲 《樵父词》:“清涧日濯足,乔木时曝衣”便刻意清雅化了 “樵父”之形;又如李颀 《渔父歌》: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亦是将“渔父”的形象进行了诗意化的重构。事实上,抛开审美体验不谈,单纯考察作者传达情绪的方式,会发现这其中存在着从上而下的意义灌注,显然,砍柴樵夫不会具备 “荡漾与神游,莫知是与非”(《樵父词》)的境界,垂钓老翁又怎能发出 “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辛苦”(《渔父歌》)的喟叹,仙词逸句的深处乃是唐人借客体形象投射价值倾向的委婉。与此相反,宋式书写则直接简省了作为意义中转的客体形象,直接将 “濯足”设置为主体行为:
我欲濯缨渠濯足,一生输与钓鱼船。(项安世 《曲湘湾》)
顷刻谐我意,翛然已忘形。濯足临潺湲,披襟望青冥。山中真可乐,世路空营营。(孔武仲《水上清风覆以乔木》)
我虽冠屦缚,心乐只园静。濯足卧禅扃,幽梦堕蒙顶。(胡融 《葛仙茗园》)
宋人归隐借己身之 “濯足”单刀直入地表达认同和实践,不类唐人隔山打牛,在主体与诉求之间还要插入一个 “濯足”的客体形象。书写转变强调了主体的存在,情志的表达因此而有了更为迅捷、强烈的意味,这判然不同的呈述方式来自于唐、宋间士人的心态变迁,变迁的原因则在于两代之内,士人归隐的质地发生了改变。
入世的使命召唤和归隐的情性追求,是贯通古今的悖论,取舍之度,唐宋有别。生于进取型的社会,李唐天下的士人将人生价值大多融于政治理想的实现。相对而言,唐人的归隐或是进取不得的权宜之计,或是待诏终南的战略部署,以 “濯足”表达的唐式志隐,大多只是流于传统,故这种言不由衷的诉求,只能借助客体形象的外化来完成,这个 “濯足”的客体形象,就是唐人在迫切的应世需求和传统的高致审美间设下的一道缓冲墙。赵宋帝国的 “右文”政策更大限度地促进了士人政治价值的实现,综唐一代科举取士年均不足30人,宋代则扩增至176人,①马端林:《文献通考·选举考二至五》,中华书局,2011年。所谓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如此,作过稷契之辅、历经宦海沉浮的宋士人,对 “濯足”指涉的归隐产生的求索与体味,恐怕才更为真切与深刻。而且,宋代的归隐条件明显优于前朝,在科举之外,帝王定期访下野之贤,隐者可以因之入仕,即便 “坚辞”仍能获得名号和赏赐。②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何况,宋隐并非只能选择于山林僻静处独善其身,著书立说、聚众讲学,乃至培植后进、施惠乡里,亦都被纳入 “隐”的模式。更有甚者,“吏隐”之说以身执吏务而心在林野的状态,更新着世俗对于隐逸的认知。
相形之下,宋隐的概念更加宽泛,比唐隐易得、易施,因此,宋人言隐,便少去许多顾虑。对隐者陶渊明,王维斥责其 “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偶然作六首》),杜甫则讽曰 “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说明唐人对无法 “齐家”的只身之隐颇有介怀,而到了宋朝,观念便宽缓多了,苏轼赞陶 “贵其真也”,王应麟则直呼 “杜子美讥其责子,王摩诘议其乞食,何伤于日月乎?”③王应麟:《困学纪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宋人对陶隐的称誉,将隐逸的价值引向自主解读的维度,认为 “开门出仕,则跬步朝市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④苏轼:《苏轼文集编年校注》,李之亮点校,巴蜀书社,2011年,第152-155页。在这样的价值导向下,罗大经一段有关濯足的自述便可称谓宋隐的范本:
余家深山之中……随意读 《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乌知此句之妙哉!①罗大经:《鹤林玉露》,王瑞来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304页。
对情性与学理的追求,构建了新的价值体系,人生意义的实现可以是适身养性、读书著文,而不再仅仅苑囿于政治抱负,与 “山妻稚子”共啖 “笋蕨麦饭”营构了生存的新美学——粗食布衣的齐家之隐,亦可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如此,宋人从意识层面便开始淡化 “显隐”矛盾,又在实施层面杜绝了严苛的评定标准,及言 “隐”,其诉求自比唐人轻松、真实,是以主语之 “我”开始高频度出现,主体的凸显加强了诗的 “句化”倾向,令濯足诗出现了 “文”的叙事特征,客观上成为 “以文为诗”潮流下的一个分支。
主体强调引发了新的书写征状:文字时序变得紧迫。因为主语的频现,量化并缩短了主、谓语间的距离,而这个距离映射的是从主体到诉求之间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的缩短促使文字层面的表述出现了趋向急迫与迅捷的状时之语。相比于宋人,唐人的归隐总要克服诸多精神与物质层面的矛盾,不免些许的迟疑,这促使 “濯足”之志多被描绘成一个遥远的目标,诸如 “终当游五湖,濯足沧浪泉”之类,“终当”将 “濯足出世”的实施推迟到无限的尽头,而在那之前,诗人尚为自己预留了大段时间去谋帝王之术。文化传统将归隐视为精神高格,社会流风则驱使士人汲汲功名,在内外互斥的矛盾里,唐人只得将 “濯足”的期限尽量延迟,以求得当下的缓释,然而 “显隐”对立所造成的心灵困境对唐人来说似乎是永恒的,从王绩的三仕三隐,到孟浩然的 “红颜弃宣冕”,再到皮日休的林下苦吟,终唐一代的隐者似乎都有着几分被动,语言层面的慕隐与真实的生活所需之间到底蜿蜒着一道错裂之痕。弥补这一裂痕的是宋人的 “濯足”书写, “明朝解缆沧浪外,濯足船头唱竹枝。” (蒋旦《柘川渔火》)“平生志气隘九州,直欲濯足万里流。”(仇远 《和李致远秀才》)“漱石漱流俱可意,濯缨濯足且随时。”(朱翌 《观乌龙山瀑布》)从 “明朝” “直欲” “随时”的状时之语中,不难体会呼之欲出的渴求、内外交谐的自在,紧迫的时序指明了诉求的晓畅,而晓畅来自于身心的调伏,唐人那里尚需通过形象外化来实现的精神目标,已然内化为宋人的主体意识,他们不以类型化的指涉表达志归的愿景,却以充盈活泼的主观世界调和遭逢与际遇,从字里行间渗透了慕隐与内需的融通。
唐式濯足对 “显隐”的处理,有着潜在的断裂之感:以客体形象寄托心绪,本身已经打断了主体和心绪之间的纽带,一种无法直言出口而只能借助客体才能抒发的情志,归根结底并不能获得内心彻底的认同。宋式 “濯足”就圆融得多,苏轼前往属县灭决囚禁之余,有 “濯足乱清沟”的轻松戏乐,文同 “濯足清涧滨”之后仍会发出 “还愧拥千骑”的喟叹。唐人无法调和的断裂,在宋人的内里走向弥合,不问俗务的超然和心系家国的责任不再是全然对立的两极,“在隐”与 “在仕”虚实轮替、互为表里,在宋人的主体意识中水乳交融,臻于化境。以 “濯足”书写的归隐主题下,唐人在类型化的极致追索中患得患失,宋人则在两方调融的中间地带寻得了自我。
四、结 语
文献的长流中,“濯足”的概念几经附生与汰洗,在语义与图释的交错中,熔铸成别样的文化情涵。从先秦到晚唐,“濯足”的语义进化虚实相生。两宋之际,对 “适身”体验的热衷催生了趋向于市民文化的书写征状,进而构建平实通脱、自守自适的生活美学。“濯足归隐”在唐、宋诗叙中的变迁,体现在 “主体强调”与 “时序紧迫”之上,深层原因则来自于不同类型的文化间的差异。对此的研究,亦有助于补充唐、宋间文化转型的部分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