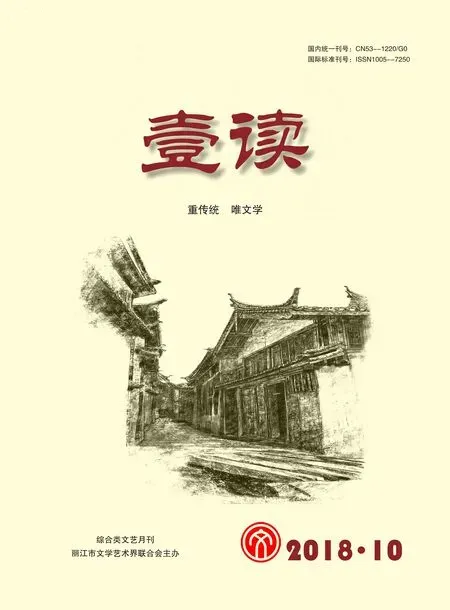奔腾的云南
陈洪金
怒江:亘古奔腾之江
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给每一条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河流,都取了一个藏文名字。怒江在进入云南之前,叫那曲河。当它一路经过连绵不绝的雪山,带着圣洁的雪水一路南下,这条小河一边奔涌前行,一边不停地成长起来。当它进入云南境内的时候,生活在滇西北群山里的怒族人便给它重新取了一个亲切的名字:“阿怒日美”,“阿怒”是怒族人对他们自己的称呼,“日美”则是“江河”的意思,这个词的整体含义便是“怒族人居住区域的江”。在汉语里,怒的外在形态之一,便是咆哮。而咆哮这个词,同时也被描述猛兽的吼叫声、河水奔腾时候发出的巨大声响。这时候,当我们发现,一条江,用“怒”来命名的时候,便会在内心里暗自去猜想——这条江肯定有着飞溅的浪花和震耳欲聋的涛声。
事实也是如此。
滇西北是一片由群山组成的海洋。高耸入云的山峰是滔天的海浪,深不可测的峡谷是幽暗的波谷。在这里,亚洲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的冲撞与挤压,构成了连绵不绝的高山峡谷,比如,高黎贡山海拔高达4000多米,碧罗雪山海拔在4500米以上,太子雪山海拔6054米,梅里雪山6740米,这样的高山密布在滇西北地区,形成的山峰与江面落差往往在2000-3000米之间。江河流经滇西北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场山与水之间展开的战争。怒江流入云南,便在这些层层叠叠的群山里左冲右突,仿佛一头猛兽在森林里一路狂奔。从松塔到马吉,从丙中洛到支鹿马登,从碧江到亚碧罗、六库,群山把岩石、岸壁当成壁垒来阻挡水的行程,江河用巨浪和怒涛当成刀剑杀出一条血路。最后,二者彼此妥协,刚劲的群山留下了一些水,浇灌了满坡的森林和村寨,盛怒的江河也因此得以冲出重围,一路狂奔而去。这个横亘在天地之间的江河与高山的战场,便是被称为东方大峡谷的怒江大峡谷。
怒江大峡谷的存在,总是有着许多雪山与它相对应。众多的雪山上珍藏着的积雪,在天气变暖的时候,便融化成千万条溪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怒江里来。一路上,每一个溪水滋润过的地方,便形成了森林、草甸、湖——那些或大或小的湖泊,比如高黎贡山的听命湖,碧罗雪山的干地依比湖、恩热依比湖、瓦着低湖,它们仿佛从天堂里遗落到人间的珍珠,把从天而降的水分,收藏了千万年。那些森林和草甸生长着数以万计的植物,长满了贝母、黄连、虫草、雪茶、雪莲、雪当归、党参、杜仲等名贵药材,栖息着形形色色的虎、豹、熊、山驴、马鹿、麂子、獐子、野猪、猴子、豺狼等走兽,有雪鸡、白鹇、箐鸡、雉鸡,鹦鹉等各种飞禽,隐藏着鲜为人知的虫蛇。这里成了名符其实的生物基因库。
当然,在幽深的怒江大峡谷里,还散布着一个又一个村寨。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一个个民族的名称,当它们由汉字拼写出来,呈现在纸面上,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但是,当我们身临其境,步入其中,才发现,原来,怒江大峡谷所孕育与怀抱的,绝不仅仅是多姿多彩的峰峦、林涛、野花、飞鸟、走兽,还有更多神秘的、朴素的、善良的人们,与这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江生死相依。怒江把群山分割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大峡谷,飞鸟的翅膀可以轻易地把它们送到任何一个它们想去的地方,人的脚步不可能踩过江水。但是,鸟能过江,人作为比鸟更具高智力的生灵,也必须过江。于是,一种在世人看来非常特殊而在当地人看来却特别寻常的交通工具出现了,那就是溜索。之所以称之为“索”,在古代,人们把足够长的绳子固定在箭尾,用强弩射到江对岸去,然后再把藤索引过江去,绷紧了,固定在两岸的岩石上。过江的人们,双手抓住一根倒“V”字形状的木叉,卡在藤索上,仿佛飞鸟掠过江面,迅速地滑过江去。再后来,藤索换成了铁索、钢绳,木叉换成了滑轮,怒江奔腾不息的江面上,便有行人不断地采用这种方式,往来于江的两岸。莽莽群山、深深峡谷,使得怒江流域至今没有火车、高速公路,溜索依然横跨在江面上,见证着这里的人们年复一年的往来。就这样,在怒江边上,穿云过雾的人们,用他们在江面上的身影,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着他们爬山的艰辛和过江的惊险。
在怒江大峡谷里,水往往呈现它暴戾的脾性,但是,它也有充满了温情的时候。怒江流过的地方,同时也有许多温泉。居住在群山里的傈僳族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劳累之后,便会到这些温泉里来洗澡。这些温泉,便成了他们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好去处。久而久之,也便形成了一个叫做“澡塘会”的节日。每年春节,正月初二到初七,人们从远远近近的村寨里出发,带上粮食和炊具,带上美酒和蔬菜,带上毯子和被子,来到怒江边的温泉,不分男女老幼,所有的人,都脱去世俗生活里厚薄不一的外套、长裙、短靴之类的束缚,一起泡在温泉水里,洗去劳碌,洗去病痛。深山,天浴,一大群人泡在温泉水里,陌生的、熟悉的,邻近的、遥远的,都被一汪温暖的水怀抱着,浸泡着。曾经的忧伤随着从水里蒸发出来的水雾飘走了,曾经的苦闷随着潺潺的流水淌走了,曾经的饥饿与寒冷,也随着涛声远去了。在这里,裸露成为一种常态,无论是老妪还是少女,无论是壮汉还是美女,都可以把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自然的袒露出来,让内心像一个孩童一样袒露出来。这里只有笑声、歌声和舞蹈。夜幕降临的时候,温泉边燃起了篝火,人们唱起了远古的歌谣,吹响了葫芦笙,爱情,也在这样的情景里嫩芽一样悄悄地生发出来,多情的男子,怀春的女子,在夜色的掩盖下,在篝火的映照下,在树丛的遮掩里,在花香的包围中,用情话、情歌传达彼此的爱意。
怒江在群山里穿行,阻挡住了外面的人们探寻的目光以及望而却步的足迹。因此,这个区域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封闭的、幽暗的、神秘的。在忙碌的所谓文明世界里,因为浮躁而内心疲惫的人们,无数次用他们的文字表达了对“世外桃源”和“香格里拉”的神往。当他们在某个时刻,无意间发现个群山怀抱,江河奔腾的陌生世界,便发出了一种感叹——这里就是他们苦苦追寻了许多年的理想世界。其实,这里从来都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很久以前,就曾经有人来过。是的,有人曾经来过,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过。在《圣经》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一百多年前,一些西方传教士从遥远的西半球,从英国、法国的某座教堂陆陆续续来到这里,来到傈僳族群众中间。他们在悬崖上建起了教堂,十字架面前与人们同唱赞美诗,在村落里教人们酿造葡萄酒,在村道边对人们讲摩西十诫。就这样,祖祖辈辈生活在深山里的傈僳族,竟然与基督教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耶稣、天国、圣经,在怒江流域,成了傈僳族的民族宗教。圣父、圣子、圣灵成为傈僳族内心里的精神寄托。
一个性格刚烈的男人,也有他温柔的一面。怒江也一样,当它突破横断山脉重重的阻挡,携带着飞溅的浪花奔入潞江坝的时候,便显示出了它祥和文静的一面。在潞江坝,因为地势平坦,江面也便开阔起来。在怒江的上游,高耸入云的雪山、草甸、冰川海拔通常都在四千米以上,但是,当它来到了海拔只有640米至1400米的潞江坝,怒江在潞江坝的流淌,震耳欲聋的巨流变成了潺潺如语的波影。在怒江大峡谷,如果说怒江是一曲气势雄伟壮阔的交响曲的话,那么,在潞江坝,怒江则是一首柔情千回百转的小夜曲。正是因为这样的情有独钟,在怒江水的滋润下,潞江坝成为一个从高原山地向丘陵缓坡地带过度,从高原冷凉地区向热带雨林地区过度的温暖的、湿润的地方,这里生长着众多的植物,龙眼、荔枝、香蕉、甘蔗、香料烟等独具特色的作物开始出现,热腾腾的江风从江边吹向两岸的野地、田畴、密林,沿路的庄稼、作物随着热气马不停蹄地生长,硕大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着绿油油的光芒,沉甸甸的果实在热风里摇晃,水,沿着潞江坝那些茂密的植物的根须,日夜不息地向着茎叶、鲜花、硕果的旅程一路吹唱着跋涉。就在这条充满了水分的路上,高大的榕树撑起了浓荫、修长的凤尾竹摇曳出了款款柔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历史里一路走进来,居住、行走、相爱、繁衍、老去。潞江坝一直被怒江的涛声洗涤着、抚摸着,寨子与村庄,却越来越紧密地连在一起,人们在夜色里枕着怒江水的涛声,把生活过得情深意切。潞江坝的温暖与热烈,用它肥沃的泥土、明亮的阳光和绿意盎然的植物接纳一群又一群南来北往地逐水而居的人。到他们的脚印抵达潞江坝,便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把它当成了最后的故乡,从此与这个地方终老一生。这样的情结,使得汉、傣、僳僳、德昂、回、彝等多种民族世世代代居守着一江春水,歌声、舞蹈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点缀着这里的富饶与宁静。顺着水流,一种信仰也在涛声里溯流而上,并且在这里成为一种迷人的景象。在一些傣族村寨里,佛塔在碧绿的大榕树和翠竹的掩印中,微微地露出它的尖顶来,圣洁的白色与灿烂的金色交相辉映,袒肩的僧人、幽密的诵经声隐隐约约地传出来……这样的意境告诉我们,小乘佛教已经从遥远的南方来到这里,与怒江水一起泽润一方水土,感动一个又一个寨子里虔诚的人们。
怒江在群山之间穿行,两岸都是一片辽远的天地。人来,要过江,人往,也要过江。在来来往往之间,一座座桥梁横跨在江面上,承载了千百年来络绎不绝的脚印。当人们离开,桥还在那里,仿佛一个沉默不语的老人,在岁月里历经风吹雨打。怒江沿路南下,千里万里的行程中,总是有许多桥梁隐藏在山影里,映照在江水中,让人们从不停息地往返。比如,在龙陵县与施甸县之间的分界线上,一座叫做惠通桥的古桥,就用它的通与阻、断与续,告诉我们,它在一段漫长的时光里,曾经遭遇了怎样的喜悦与忧伤、屈辱与荣光。一百多年之间,惠通桥曾经第六次修建。其中最让人不能忘记的一次,是在20世纪40年代,它曾经被中国人炸毁,随即又修建。这一段时间,整个世界都被战争笼罩着。在滇西,日本军队从东南亚诸国绕道进攻云南,计划通过攻占云南,占领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斩断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而与此同时,中国与国际社会援助的唯一通道就是著名的滇缅公路。横跨在怒江之上的惠通桥便是滇缅公路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关津要隘,曾经幽居在滇西深山里的惠通桥,突然间成为事关中国抗战全局的重要关节点。从1940年10月28日至1941年2月27日,日本空军先后对惠通桥进行了6次空袭,共出动飞机168架次,投弹4000余枚。面对远去的时光,面对这一串简单的数字,如今我们已经无法体会到,当惠通桥在战火里摇摇欲坠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命运,曾经面临着怎样的危急。当惠通桥始终横跨在怒江上的时候,一个古老的民族,曾经有过怎样的欣慰。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危急局面,依然在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把一座桥引向毁灭。1942年5月4日,日本军队攻陷龙陵县城,紧邻的怒江作为天然的屏障,阻挡日军继续深入。这时候,在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战争里,为了保全大片国土不被异族践踏与蹂躏,惠通桥被自己人炸毁了。在苍烟夕照里,在江流的呜咽中,惠通桥残存的铁链垂挂在江水里,见证着一场战火的残酷、血腥、野蛮与无情。同时也见证了一场抵抗的悲壮、刚烈、执着与无畏。1944年8月1日,惠通桥见证了战争的另一个局面,中国军队开始从怒江上的各个渡口全面反攻日军,惠通桥第六次横跨在怒江上,承载着中国军人沉勇的步伐,输送源源不断的战略物资,收复曾经失去的国土。惠通桥见证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艰难崛起的身姿与豪情。
历史已经远去,怒江还在流淌。滇西的山,紧紧拥抱怒江之后,目送它一路远去。怒江在云南的最后一段航程依然是一片崇山峻岭,在南信河口,群山依然紧紧相连,村寨依然点缀着同样的田野和山林,鲜花依然盛开着同样的颜色。但是,就在这南信河口,怒江与另外的一些河流一道,进入了另一个国家——缅甸。由此,怒江的激流还没来得及回望一下它在中国的一路行程,便被缅甸热气腾腾的土地所接纳,同时也被换上了一个新的名字:萨尔温江。每一滴水都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奔入大海洋,滔滔的怒江水,从青藏高原上千里奔波,同样也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当它被称呼为萨尔温江的时候,虽然前路还很遥远,但是,它终归已经走完了大半行程,出了缅甸,印度洋就到了,那是一个更加温暖的怀抱,一个永不醒来的美梦,正在酝酿着它无法预知的另一个轮回。
红河:开满民族之花的常春藤
红河是诸多发源于云南省境内的最具特色的河流之一。这是一条红色的河流,它从云南高原的土地里诞生,在云南的红土地上流淌,一路蜿蜒离开云南,抵达的还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当它奔流,浪花是红色的,当它静止,波纹是红色的。红色,构成了它最基本的颜色。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它所依附的高原,泥土是红色的,就像一个孩子,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了母亲的容颜,也便知道了自己的面貌。但是,当红河流过森林的时候,它会变成绿色,当红河流过稻田的时候,它会变成黄色。当红河流过梯田的时候,它的颜色,便是天空和云朵的颜色。红河,其实是一条开满鲜花的河流,那些花朵,便是云南土地上的一个个神秘而古老的民族。
红河从云南大理州巍山县一座叫做额骨阿宝的山峰诞生的时候,这个陌生的名字,便注定了这条河流肯定会经历许多沧桑,让我们探寻的目光充满了深情。额骨阿宝,是云南高原上一个最为古老的民族用他们古老的语言给红河的源头命名的,它的意思就是:“一条弯弯曲曲河流的父亲”。这个民族就是彝族。红河从巍山发源,流向云南广阔的土地,直至南海。彝族也经历了一个与红河水的流淌一样漫长的过程。在巍山这片土地上,彝族的先民在这里逐渐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并且于公元738年建立了一个王国:南诏。南诏国的建立,让中国历史记住了巍山。随后,大理国又在洱海之滨建立,在云南形成了长达八百多年的地方政权。彝族,在云南大地上歌唱、舞蹈、祈祷、祭祀,沿着红河的流向、金沙江的流向,沿着在红土高原上叶脉一样延伸的众多河流的流向,走向四方,成为了云南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回首那漫长的岁月,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彝族人,始终把巍山当成他们的祖居地,一次次探访,一年年回归,在那里寻找他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的辉煌。如今,在巍山,在额骨阿宝的周围,彝族与回族、傈僳族、白族、苗族等许多民族居住在一起,生活依旧在继续,古歌依旧在吟唱。
红河的第一段是礼舍江。它从巍山的额骨阿宝出发,由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鼠街进入了南华县,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南华县红土坡,楚雄市八角、中山、西舍路乡,双柏县鄂嘉镇,至三江口与绿汁江汇合,进入双柏县内叫石羊江,在双柏三江口与绿汁江交汇后出州境,流至新平段称嘎洒江,再下至元江县称元江。礼舍江平行穿插奔流于哀牢山脉之中,它在南华县这个被称之为“九府通衢”的滇中要道一直向着南方流淌。南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狭长地带,它作为云南中间的交通要道,周边与思茅、楚雄、大理三地州和景东、牟定、弥渡、祥云、姚安、楚雄六县市接壤,东距昆明197公里、州府楚雄37公里,西距历史文化名城大理175公里,北距四川省攀枝花市225公里,国道320线(滇缅公路)、省道217线(南华至攀枝花市)、楚大高速公路(楚雄至大理)、广大铁路(广通至大理)经过县城和两镇一乡,是川、黔、滇通往滇西、缅甸、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咽喉要塞。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满眼都是行色匆匆的外路旅客的地方,却也是一块宝地,礼舍江在这里弯弯曲曲地流淌,每一朵浪花都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浓郁的香气。这种香气,源于土地,源于森林——南华县满眼是山,满山都是森林,森林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生菌。每到夏季,在那些鲜为人知的树丛里,山坡上,石缝中,涧溪边,野生的菌子,灵芝、松露、松茸、牛肝菌、鸡枞、青头菌,被当地人采摘了,把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市场塞得满满当当的。这时候,整个南华县城里便飘荡着野生菌浓浓淡淡的香气。循着这股香气,远远近近的人们,便不约而同地赶来这里,汇入到野生菌交易的洪流中去。就这样,南华县城,这个曾经马帮铃声此起彼伏的古老的小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又重新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地方,全省各地的野生菌,都沿着各不相同的道路,在南华县城集中,当这里的野生菌如同一条河流,源源不断地走向国内外,南华县,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承载了中国野生菌王国的荣光。红河却一路远去了,伴随着红河的流淌,一个人也从这里走出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他就是郑和。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郑和是昆明晋宁人,但是,从他在少年时间开始,郑和就离开了晋宁,来到南华,在一家郑姓人家渐渐成长,然后走到北京,成为明朝第二位皇帝明世祖朱棣的亲信。后来,郑和率领着大明王朝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出访世界各国。在郑和的航程上,他见到了红河最后归属太平洋。礼舍江里的水与太平洋里的水究竟有什么不同,也许只有郑和本人才知道。
双柏是一个被礼舍江用心地倾听过的地方。这里是古哀牢国的腹地,彝族、哈尼族、苗族等18个少数民族散布在这里的田野里、河湾中、缓坡上、密林间生活了千百年,哀牢山与红河,把云南划分为滇东与滇西,而居住在这个分水岭区域的人们,尤其是彝族支系罗武、罗罗、阿车,在双柏这个地方把彝族古老的民族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们喜欢在歌声里追溯往事,于是在这片土地上产生了彝族创世史诗《查姆》和叙事长诗《赛玻嫫》,这些古歌,由彝族的祭司毕摩在火塘边悠扬地唱起来,倾听这样的古歌,人们仿佛回到了比古歌还要古老的岁月里去,天地、自然、祖先、神灵,都在古歌里复活了;倾听这样的古歌,千里万里之外的彝族人,在歌声里找到了他们最初的根与源,看到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在云南的大地上漫游的旅程。他们还喜欢在欢乐的时候跳舞,彝族是一个崇拜火的民族,是一个崇拜老虎的民族,在双柏,人们在属于他们的节日里,燃起火把,穿上象征着老虎的衣服,在他们的寨子里、森林空地上,在田野中跳起了属于他们的舞蹈,在这样的时刻,人们与他们的图腾合为一体,神灵以动物的形态呈现在天地之间,让空气里的每一粒尘埃,都承载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风调雨顺的祈盼。礼舍江水流走了,双柏的大地从未改变过,时至今日,他们还跳着那些从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舞蹈,彝族传统舞蹈老虎笙、大锣笙、小豹子笙已经成为彝族古傩仪式和中国彝族虎文化的活化石。
每一个云南人都深爱着各自脚下的土地,每一个云南人提起建水,都会为之着迷。中国人有一句流传得非常广泛的俗语: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建水的许多事物,也都呈现了它的双面性。比如河流,在建水,长长短短的河、渠、溪、涧,都要汇入到几条相对要大一些的河流里去,但是,即使这些被崇敬、被信赖的河流,最终也是分别归属于两条更大的河流,比如泸江河、曲江河、塔冲河、南庄河等属南盘江水系,坝头河、玛朗河、龙岔河等属红河水系。最后,红河向南,南盘江向东,各自从建水的土地上奔向不同的入海口。建水的人,也与他们身边的河流一样,分别创造的不同的文化群落,让这片土地成为个性鲜明的一个区域。据统计,在建水,生活着汉族、彝族、白族、傣族、壮族、苗族、回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藏族、景颇族、布朗族、布依族、阿昌族、哈尼族、锡伯族、普米族、蒙古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水族、满族、独龙族等26个民族,也就是说,云南所拥有的民族,建水几乎都已经有了。众多的民族散布在建水的乡村与城镇,劳作、行走、歌唱、恋爱、老去,比如,在彝族人的火把节里,村村寨寨杀羊宰牛,全村人欢聚一堂,喝陈年佳酿,吃陈年谷米,话新年丰瑞。晚上,全村人点燃火把,唱着歌、跳着舞,到田野间游行,驱除魔孽,迎接丰收。在哈尼族人的苦扎扎节里,人们杀猪祭龙,祭龙仪式后,各户从稻田采来新穗,碾出新米,染黄饭,煮红蛋,聚在一块摆长街宴,同享共乐。晚上,全村男女跳芒鼓舞,唱“哈吧咦”,彻夜狂欢。在让人不由自主地感慨:建水简直是一个展示民族文化的舞台,每一个人身上,都隐藏着一个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足迹。
同样让人赞叹的,还有汉文化在这里创造的辉煌。很早以前,建水就汉文化在这个地处滇南、少数民族众多的地方传播了,人们在建水建起了书院、私塾,读四书五经,品老庄哲理,写诗词歌赋,建亭台楼阁,建水这个地方,出现了孔庙、朱家花园、张家花园、曾家花园、杨家花园等一大批典型的汉族建筑。当然,建水也出了一大批文化人,他们在建水读书,中科,四处为官,其中,有一位叫做萧崇业的明朝人,万历皇帝派他率船队渡海册封琉球(今冲绳岛)中山王。中山王以重金酬谢使臣,崇业慨然谢绝。在一路的行程中,他把自己在海上的经历和见闻以诗歌、散文的形式写下来,形成作有《却金行》《航海赋》《南游漫稿》等诗文。云南是一个到处是山的地方,他却一路远去,走到了当时被认为天之涯海之角的地方,后人称其为继大航海家郑和之后“滇中航海第二人”,他的诗文则被誉为“开云南海外文学第一页”。
云南的天空是美丽的,但是更美丽的还是云南的大地。云南的大地是美丽的,但最美的是元阳的梯田。在元阳,大自然把最多的宠爱都给了梯田。1300多年前,哈尼族元阳县各族人民开山为田,引水种地,建成大小水沟4653条,开垦梯田19万余亩。水从天上的云朵里滴落到山顶的树叶上,水从树叶滑落到土地里,再从山顶上流下来。一路上,梯田把那些清澈的水收积起来,在元阳县勐品、硐浦、保山寨和阿勐控一座座山,仿佛都穿上了一件水做的锦衣。在那些梯田里,天空在水里变得特别的蓝,星星在水里变得特别明亮,每一朵云从梯田上空飘过,都要在那些梯田的水里洗个澡,然后才离去。清晨,云朵在梯田里是金黄色的,正午,云朵在梯田里白得灼目,薄暮时分,云朵在梯田里是橘红色的。一年四季,元阳的梯田里生长着的庄稼不断地变换着鲜艳夺目的色彩。置身于大地之上的流光溢彩之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家们,找到了一个让他们无论怎么变换镜头也不能完全收藏的人间天堂的美景。2013年6月22日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红河哈尼梯田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诗意地生活在元阳的人们,除了哈尼族,还有另外一些少数民族,他们共同守护着云南最美丽的土地,创造了一个个独具特色的民族节日,哈尼族的“昂玛突”、“开秧门”、“苦扎扎节”,彝族的“火把节”,苗族的“踩花山”,瑶族的“盘王节”,傣族的“泼水节”,壮族的“三月三”等节日,使得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季节,都有歌声、美酒、舞蹈在蓝天下,大地上呈现。这里的每一个女人,都是勤劳的、智慧的、爱美的,她们从大自然里汲取了灵感,把花朵、云彩、泉水、树木、飞鸟、走兽、游鱼的形态做成衣服,穿到身上,于是,我们在元阳的山村、野地、水边、林间,都可以看到色彩浓艳的彝族的日月系腰服、苗族的百褶裙、瑶族的马尾帽、壮族的系腰带、傣族的花腰服。元阳,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地方。
红河还有一个名字:元江。元江同时也是一个县的名字,元江县还有着一个明亮的、热烈的、生机勃勃的称号:红河谷中的太阳城。这里青山惹眼,绿水怡人,四季花果飘香,民族风情浓郁醉人,琳琅满目的各种热带水果美味可口,四季鲜花竞相开。同时,元江也是一个多种气候同时存在的地方,一个县,五个气候类型,即热带、亚热带、北温带、南温带、寒带,形成了“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山顶穿棉衣,山腰穿夹衣,山脚穿单衣”的独特现象。这样的气候,让元江成了一个物产丰富并且多样的地方,芒果、荔枝、香蕉、菠萝、芦荟、茉莉花等众多的植物遍布在全县各个地方,让元江成了一个水果满目,四处花香的地方。尤其是元江的金芒果节,以芒果为代表的水果,在这个节日里呈现在人们面前,整个元江都弥漫着水果的香味,品尝水果成为一个节日里最幸福的事情。好地方每一个人都喜欢。这里聚居着傣族、哈尼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因此,这里又是歌舞的海洋。尤其是元江的竹竿舞,更是让无数的人在欢乐中忘记了忧愁,竹竿舞是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各少数民族的一种群众性的民间舞蹈活动,是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相互认识、交流的活动。千人共嬉的竹竿舞在平坦宽阔的场地上举行,66对舞杆在锣鼓等民族乐器的伴奏下,随着音乐节奏的快慢,手中的竹竿不断地分合击拍,竹竿一开一合,一上一下,有节奏地发出整齐的声响,给人一种悦耳的感觉。青年男女们随着竹竿的节奏,用单脚或双脚在四对竹竿之间灵巧地跳动,当一对竹竿分开时,在竹竿的空隙中左跨右跳转身腾挪,时而双腿跳,时而单腿跳,时而侧身跳,时而腾跃跳,青春在这样的节奏里挥洒得淋漓尽致。
蒙自和个旧是红河流经途中最值得回顾的地方。蒙自古以来都是滇南文化重镇,顺着红河水的方向,蒙自成为了云南对外交流的窗口,清末民初曾是云南省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当时云南80%以上的进出口物资通过蒙自转运,云南第一个海关、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邮政局、第一个外国银行、第一条民营铁路、第一个外资企业、第一个驻滇领事馆、第一个火电站等诸多“第一”先后在这里产生。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合大学迁至云南,其中文法学院设在滇南重镇蒙自,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一大批著名教授均在蒙自任教,更是让蒙自成了一片文化的沃土。如今,蒙自同样是滇南地区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地方。相比之下,蒙自是一个文化重镇,个旧则是一个矿产资源富集的宝藏之地。个旧的地下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已探明的锡、铜、锌、钨等有色金属储量达650万吨,其中锡的保有储量90多万吨,占中国锡储量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铍、铋、镓、锗、镉、银、金等稀贵金属,霞石储量约30亿吨,为全国霞石储量之冠。 在个旧,开采锡矿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大的产锡基地,同时是世界上最早的产锡基地,因此,个旧很久以前就已经被世人称之为中国“锡都”,个旧,在中国的西南一隅,在云南的南部,以它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中国冶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源于大地母亲的血液,滋润着人类在漫长历史里的成长。
红河从不停息地向着远方奔涌而去,用河湾、滩涂、码头、界碑的形式,把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区别开来。这些地方却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一衣带水。红河流到河口县,它在中国的旅程就要结束了。河口,因为红河,也成为中国漫长边境线上的一个口岸城市。在这里,红河水与滇越铁路、昆河公路一起走出国门,转瞬之间,红河的浪花便与火车、汽车一起踏上越南老街市、谷柳市的土地了,一片与河口人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同样的情感去接纳它,拥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