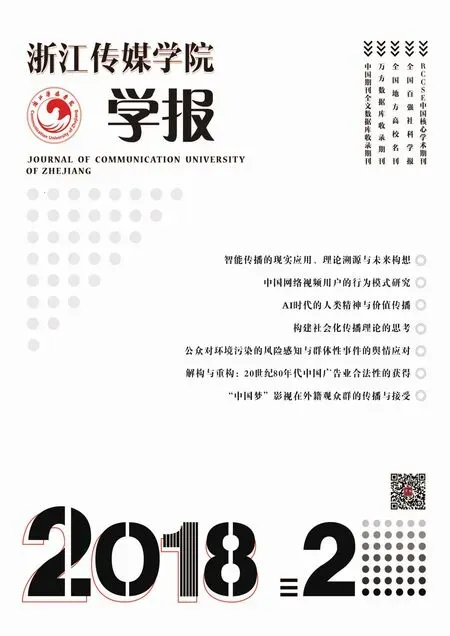莎士比亚戏剧中病理现象的美学研究
徐群晖
莎剧中的医学病理现象研究最早始于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该学派试图用动力学去解释临床医学中的精神病态现象。随后,琼斯、霍兰德、拉康等学者也分别根据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学说对莎剧主人公的精神病症现象做了进一步阐释。1997年,伯纳德·派里斯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霍尔奈的新精神分析学理论对莎剧主人公的精神病态现象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莎剧主人公的精神病理现象主要源于文化环境下的心理防御机制。[1]关于莎剧中的生理性病理现象,R.P.Robertson在1959年发表的论文《Shakespeare and medicine》中指出,莎剧描写的鼠疫、梅毒、坏血病,痛风、癫痫、风湿、创伤、精神病、老年病等病理现象具有医学上的真实性。[2]1989年,美国加州大学神经学助理教授Fogan.L的论文《The neurology in Shakespeare》进一步从神经医学角度对莎剧描写的癫痫、眩晕、颤抖、脊椎伤残等神经系统病理现象的真实性进行了深入研究。[3]2009年,Martin Boxer在论文《Biodiversity,Medicine,and Shakespeare》中指出,莎剧不仅真实描写了病理现象,还提供了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医学知识。[4]从国内的研究情况来看,基于文学与临床医学学科的交叉学科研究所获得的莎学研究成果近乎空白。以弗洛伊德、琼斯、霍兰德、拉康、Bernard J.Paris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阐释了莎剧中基于恋母情结或文化心理的精神病理现象问题。然而,上述学说虽然能合理解释莎剧中的精神性病症现象,却缺乏当代临床医学方面的科学依据。以R.P.Robertson,Fogan.L,Martin Boxer为代表的医学学者,立足病理学、神经医学、生物医学等临床医学学科,论证了莎剧中部分医学现象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从而建立了跨学科研究莎剧的新视角。但是,上述学者对于莎剧中的病理的研究较为零散,没有系统性地揭示莎剧中的病理现象对莎士比亚剧作成就的重要价值。特别是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莎剧文本描述的病理现象需要被重新认知,而其承担的美学价值也需要被重新阐释,从而使受众可以公正地评价已经成为历史经典的文本。
一、莎剧中的病理现象与性格美学
莎剧中的医学现象特别是精神性病症现象,与莎剧中的典型形象塑造有着重要关系。从现代医学角度研究莎剧中的病理现象,有助于深入阐释莎士比亚在以人物性格为核心的典型形象塑造方面的剧作成就。史雷格尔指出,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成就体现在“性格描绘的望尘莫及的真实性上,无比的独创性上,谁能胜过他呢?他兼容近代人的各种独特的艺术优点……甚至连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放荡、怪诞和缺陷。”[5]结合现代医学心理学理论研究表明,史雷格尔提到的“怪诞和缺陷”,并非凭空想像,而是源于对病态人格的现实主义描写。关于莎剧人物的病态人格,布利奇指出:“莎剧人物在性格方面,显然有许多矛盾,有时一个人前后不象是一个人。”[6]布拉德雷也提到了莎剧人物存在的精神分裂倾向:“凡是描写主人公以完整的灵魂来对抗敌对力量的这一类型的悲剧,并不是莎士比亚类型的悲剧。”[6](31)由于受医学知识水平的影响,以往的受众难以对莎剧人物的病态心理进行透彻的理解。正如牛津大学莎学家斯图厄特教授指出:“现代心理学由于揭露了双重和三重人格这类现象,可能会出人意料地把莎士比亚表面上的矛盾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给搞清楚。”[6](214)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为揭示莎剧表现的医学现象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真实描写了李尔王的精神分裂症。该病症的核心特征是感知、认知、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方面的分裂和障碍。幻觉或妄想是该病的本质特征。[7]而李尔王和奥菲利娅在遭遇挫折后,在精神分裂症方面最关键的特征就是神智错乱,出现幻觉或妄想。李尔王因被两个女儿赶出家门而神智错乱,发疯后将正在逃亡的埃特加当成了自己:“你把你的一切都给了您的两个女儿,所以才到今天这地步吗”(《李尔王》第二幕第四场)。过了一会儿,李尔王又将其当作了哲学家:“让我先跟这位哲学家谈谈。天上打雷是什么缘故”(《李尔王》第二幕第四场)。当时在场的肯特伯爵这样描述李尔王的表现:“他的神经有点儿错乱起来了”(《李尔王》第二幕第四场)。在《哈姆莱特》中,莎士比亚真实表现了奥菲利娅的精神分裂症状:“她的神气疯疯癫癫,瞧着怪可怪的……她说她听见这世上到处是诡计,一边呻呤,一边捶她的心,对一些琐琐屑屑的事情痛骂,讲的都是些很玄妙的话,好像有意思好像没有意思……是她父亲的死激成了她这种幻想”(《哈姆莱特》第四幕第五场)。因此,结合精神病医学的理论成就表明,上述莎剧主人公的语言、行为混乱现象属于精神分裂症的外在现象。
莎士比亚通过对病理现象的真实描写,实现了社会环境的典型形象塑造,从而从现实主义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形势、生活条件等社会状况。特别是莎士比亚生活的英国社会在经历英法百年战争、红白玫瑰战争、英西战争等连年战乱后,又经历灾荒和瘟疫的侵袭,因此,与医学现象相关的社会生活内容,必然成为莎剧的重要典型形象。1594—1596年,英国经历了连续三年的灾荒和瘟疫。1602年,伦敦再次经历瘟疫,死者达数万人。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科利奥兰纳斯》《暴风雨》《雅典的泰门》《李尔王》《安东尼和克莉奥佩屈拉》等作品中提及的瘟疫现象,无疑与这一历史事实有着直接联系。同时,莎剧通过病理现象,深刻揭示了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现实,从而使其作品在反映社会历史的深广性方面,达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顶峰。在《雅典的泰门》中,莎士比亚通过热病(天花)、痨病和癞病等病理来比拟社会现实问题;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莎士比亚用绞肠、脱肠、伤风、肾砂、昏睡症、瘫痪、哮喘、膀胱肿毒、坐骨神经痛、灰掌疯、水泡疹等病症来比拟社会现实问题;《泰尔亲王配力克尔斯》中用肺病来比拟社会病症。通过对病理现象的描写,莎士比亚生动展示了社会这一“绝对完美的形体”所承受的“损伤”,从而揭示了社会环境使人类“丢失本性,陷入混乱中去”的残酷现实。[6](232)因此,Richard David认为整个莎剧可以理解为一部精心策划的史诗。[8]
由于病理问题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因而呈现出强大的情节构建功能。特别是病理问题自身的紧张性因素,往往成为莎士比亚情节发展的重要依据。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劳伦斯神父让朱丽叶服下麻醉药后,装死逃避了父亲的逼婚,但因为迟醒而未能阻止罗密欧的自杀。劳伦斯祖父的信使因为瘟疫而未能将朱丽叶假死的信息及时送达罗密欧,最终导致了两人的悲剧。在《辛白林》中,王后让大臣研制的毒药被换成麻醉药,而伊摩琴因病把这个麻醉药当作灵丹妙药吃下后,被误认为已死,安葬在克洛登旁边。伊摩琴醒来后,又将被割去头颅并穿着他丈夫服装的克洛登当作了她的丈夫。在《终成眷属》中,海伦娜因为治好了国王的瘘管症,得到了国王的帮助,从而得以实现爱情梦想。在《亨利四世》中,福斯泰夫还利用梅毒和痛风病去敲诈桃绿蒂。在上述作品中,医学麻醉、瘘管症、梅毒、痛风病等医学现象都已转化为莎剧的情节建构因素。这也表明,在莎剧中“所有的艺术都有一种设计在起作用”,而医学现象通过自身的紧张性因素使莎剧情节产生“逻辑的结局”。[9]
二、莎剧中的病理现象与伦理美学
由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医学现象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内涵,因此,呈现出鲜明的伦理倾向性。首先,莎剧中的医学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启蒙运动时期倡导的崇尚科学的理性精神。Fogan.L等医学学者证实了莎剧表现的鼠疫、梅毒、坏血病、痛风、风湿、创伤、精神病、老年病、癫痫、麻醉等医学现象的科学合理性。[3]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辛白林》《泰尔亲王配力克尔斯》中,莎士比亚还描写了通过药物暂停生命知觉的医学麻醉现象,从而体现出先进的医学理念。莎剧通过医学现象体现出的理性精神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0]因此,莎剧中的医学现象表明,“他的全部创作都洋溢着一种力求劈开事物外壳以探明事物内核的精神。他所以达到这个高度,借用哈姆莱特的话来表达,是因为他描写的不是好像不好像,而是事物的本来面貌。”[11]
其次,莎剧中的医学现象充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伦理现象。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入开展,个人主义思潮日益盛行。理查三世、爱德蒙、伊阿古等人令人发指的施虐心理或破坏性心理,则深刻反映了启蒙时期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潮。而李尔王的精神分裂症、哈姆莱特的忧郁症、奥瑟罗的偏执性精神障碍等戏剧人物在个人主义伦理力量的迫害下所产生的病态心理,深刻地反映了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伦理价值对人性的戕害。此外,在《一报还一报》《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雅典的泰门》《泰尔亲王配力克尔斯》《亨利四世》《辛白林》《皆大欢喜》等作品中,莎士比亚还真实描写了梅毒等性病的泛滥问题,从而揭露了启蒙时期对人性欲望的过度张扬所致的享乐主义思潮。
莎剧中的病理现象,真实表现了不同伦理价值的冲突引起的身心反应。由于戏剧人物内心的“前后矛盾表明存在冲突,就好像体温升高表明身体有病,两者都是确定不疑的。”[8]因此,莎剧中的身心病理现象与不同伦理力量的冲突,特别是善与恶之间的伦理冲突有着重要联系。在莎剧中,“那引起痛苦和死亡的激变的主要根源决不是善……相反地,主要的根源在任何场合下都是恶……而这个恶它只有靠自我折磨和自我糟蹋才能加以克服。”[6](53)于是,“在有集团的利益关系的社会里,不同观念在冲突,而在私人选择的领域里,不同观念也在冲突。象莎士比亚这样伟大的艺术家,便在剧作中同时利用社会与个人两个选择的领域。”[6](226)而这种善与恶之间的伦理冲突对于个体场域而言,则主要表现为身心病理反应。正如,布拉德雷对黑格尔的基于伦理力量冲突的悲剧观进行修正时指出,悲剧的冲突并不仅仅存在于两种伦理力量之间,而在于“精神的自我分裂和自我耗损”。[12]因此,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身心病理反应,实质上是戏剧人物“自我分裂和自我耗损”的外在显现。
通过哈姆莱特、麦克白、李尔王、奥瑟罗等剧中人的病理现象,莎士比亚展示了不同伦理力量在个体身心场域内的“自我分裂和自我耗损”。特别是在《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的忧郁症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伦理观念的内在冲突。父亲被害、母亲改嫁的悲惨结局使哈姆莱特又深刻体会到个人主义伦理价值导致的社会异化问题。于是,哈姆莱特因内心冲突而陷入忧郁症:“我近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一点兴致都提不起来,什么游乐的事都懒得过问;在这一种抑郁的心境之下,仿佛负载万物的天地,这一座美好的框架,只是一个不毛的荒岬……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不,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从临床医学来看,抑郁症表现为以持久性的情绪低落为主要症状的心境障碍。主要表现为以下症状:情绪低落,悲观绝望;思维迟缓,反应迟钝;有自卑、自责情绪和自杀企图。[7](116)由于莎士比亚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哈姆莱特的忧郁症,T.S.艾略特认为哈姆莱特的性格明显背离了正常人的行为方式:“哈姆莱特的反应好像过了头……他的厌恶是母亲引起的,但是……他的母亲并不足以引起他如此强烈的厌恶感;他的厌恶笼罩并超越了他。”[1](45)
而莎士比亚通过病理现象,深刻体现了不同伦理价值的内在冲突和两难选择。莎士比亚在热情歌颂个人主义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又通过哈姆莱特的忧郁症、李尔王的精神分裂症、麦克白的精神分裂症、奥瑟罗的偏执性精神障碍等病理问题,对个人主义社会伦理的异化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正如英国莎剧评论家丹比指出:莎士比亚戏剧表现的“新人——是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我不怀疑如果要求莎士比亚必须站到某一边时,他会赞成李尔,而不赞成高纳里尔和里根;赞成葛罗斯特而不赞成爱德蒙。但是莎士比亚在这两种简单的选择外还有另外的选择。”[6](254)同时,莎剧通过身心病理现象表现伦理倾向的剧作手法也表明,莎剧中的身心病理现象是社会或政治伦理问题的象征或隐喻。因此,莎剧中很多政治和国家问题的现实冲突是通过道德和心理的方式解决的:“哈姆莱特是国家心理中心,国家是通过他的心理表达的。他的心理问题的悲剧性解决方式就变为国家问题的有益的解决方式。”[9](293)通过医学身心现象,莎士比亚不仅将个体的身心反应转化为社会历史因素,而且还把社会历史因素转化为个体的动机、情感等反应。[13]
三、莎剧中的病理现象与悲剧美学
莎剧人物因病理问题而遭遇到的身心折磨,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恐惧和怜悯效果。观众“看到他们在毁灭,彼此吞噬,摧毁自己,往往带着可怕的痛苦……悲剧就是这种神秘的典型形式,因为悲剧揭示出灵魂受到压抑、发生冲突和遭受摧残,而灵魂的这种伟大在我们心目中就是最高的存在。”[6](36)莎剧通过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病理现象的残酷性,并将其上升为“能够施加于我们身上的那种残酷”,从而把人类的“大脑、心脏和神经末梢暴露在社会现实之后的折磨人的真理面前。”[14]从而使其“以恐怖充满我们的心,以感动我们的心去怜悯”。[15]同时,病理现象的刻画带来“可怕的、悲惨的和意外的遭遇”,还体现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净化功能:“医生能用毒药排除折磨肉体的病毒,他的本领并不胜过悲剧诗人,因为诗人凭借诗中巧妙地表现激情之力量能洗净观众心中的莫大烦乱。”[12](82)
通过心灵辩证法展示的“精神的自我分裂和自我耗损”[12](485),是莎剧表现悲剧效应的重要手法。因此,莎剧在运用病理现象方面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揭示出人的心灵的复杂辨证法,揭示出一切使生活变为悲剧的东西是如何在心灵里表现出来的。”[11](369)而以病理现象为基础的心灵辩证法的运用,使莎剧超越了当时传统道德剧的艺术特征,呈现出鲜明的现代美学风格。特别是莎剧对病理现象的真实刻画,使审美主体从戏剧情节中分离出来对生命的完美性进行审美观照,进而使受众“脱离了统一的、‘真实的’世界”。[9](211)而病理现象产生的生命完美性体验,使莎剧产生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布莱希特认为戏剧“必须运用一切手段破除幻觉和移情”,使审美主体“采取距离化的审视和批判态度”。而正是莎剧中的心灵辩证法带来的生命完美性的体验,使布莱希特认为莎剧也“充满了间离效果”。[9](207)因此,莎剧对病理现象的刻画,有效地打断了戏剧情节的发展进程,从而在审美主体与剧情之间为审美主体留下充足的思考空间。
在《哈姆莱特》《李尔王》《麦克白》《奥瑟罗》《雅典的泰门》等悲剧作品中,莎士比亚通过以精神性疾病为基础的心灵辩证法,有效地强化了悲剧效果。在《麦克白》中,麦克白为了篡夺王位,谋杀了国王邓肯,然而,强烈的负罪感导致他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发作。临床医学表明:急性短暂性精神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行为、思维紊乱,伴有幻觉或片断妄想,妄想内容较离奇,日常生活与社会功能可部分损失或严重受损。[7](113)而麦克白在刺杀班柯后认知、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等方面都明显出现障碍,以致他在招待群臣时出现班柯鬼魂的幻觉:“你瞧那边!瞧!瞧!瞧!你怎么说?我什么都不在乎。要是你会点头,你也应该会说话。要是殡舍和坟墓必须把我们埋葬了的人送回世上,那么我们的坟墓都要变成鸢鸟的胃囊了……去!离开我的眼前!让土地把你藏匿了!你的血液已经凝冷;你那向人瞪着的眼睛也已经失去了光彩”。于是,麦克白夫人非常尴尬,不得不向客人解释:“他从小就有这种毛病。请各位安坐吧;他的癫狂不过是暂时的,一会儿就会好起来”(《麦克白》第三幕第四场)。在《奥瑟罗》中,奥瑟罗在伊阿古的恶意挑拨下,陷入了以妒嫉妄想为症状的偏执性精神障碍。从临床医学理论来看,该病的妄想内容与生活处境密切相关,具有现实性、逻辑性、系统性等特点。而嫉妒妄想是偏执性精神障碍的常见表现,主要表现为怀疑配偶不忠,易出现监视配偶和暴力攻击行为。[7](100)奥瑟罗的妒嫉妄想虽然与伊阿古的挑拨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偏执性人格是奥瑟罗陷入偏执性精神障碍的内因。伊阿古非常了解奥瑟罗的偏执心理:“像空气一样轻的小事,对于一个嫉妒的人,也会变成天书一样坚强的确证;也许这就可以引起一场是非”(《奥瑟罗》第三幕第三场)。于是,奥瑟罗在没有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就陷入对笞丝德梦娜与凯西奥私通的猜疑之中。“我想我的妻子是贞洁的,可是又疑心她不大贞洁”(《奥瑟罗》第三幕第三场)。强大的疑虑使他开始搜集证据来印证自己的嫉妒妄想:“你必须证明我的爱人是一个淫妇,您必须给我目击的证据……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证明她已经失节”(《奥瑟罗》第三幕第三场)。正是在这种偏执性精神障碍的作用下,被凯西奥拣到的那块手帕就成了奥瑟罗认定妻子出轨的可靠证据。
同时,莎剧通过病理现象为基础的心灵辩证法展示“精神的自我分裂和自我耗损”的过程,也呈现出丰富的审美现代性内涵。正如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既与启蒙运动、现代科学、社会制度等目的合理性因素相关联,又与宗教、审美、伦理等价值合理性因素相关联。而审美现代性则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超越,实现主体性价值。[16]莎剧中的病理现象深刻反映了以人性解放为内涵的启蒙主义理性价值观所致的人性扭曲,从而揭露了个人主义价值内在的目的合理性因素与价值合理性因素之间的分裂,进而张扬了人的主体价值。因此,莎剧中基于病理现象的审美现代性内涵,深刻体现了“在信仰或理想的动摇甚至幻灭之后对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义、对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深刻反思”。[9](452)通过病理现象为基础的心灵辩证法,成为莎剧的悲剧性效应的重要源泉,通过它,莎剧表达了崇高化和非英雄化、合理性和荒诞性、理想主义和悲观主义等层面的审美现代性内涵。
通过莎剧人物的病理现象所表达的荒诞意识,构成了莎剧审美现代性内涵的主体。因为,病理现象体现了“对人的处境的无益和荒诞的强烈感觉”,从而对目的合理性因素与价值合理性因素分裂所致的人与社会的异化问题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意识形态和主题戏剧提出政治解放办法……实际上什么也拯救不了。”[9](260)莎剧人物在身心疾病的折磨中走向毁灭的悲剧表明:“所有的价值和文明遭受痛苦的亵渎而崩溃。这是我们所无法控制的,因而是真实的。”[9](260)而莎士比亚通过病理现象揭示的以荒诞意识为主体的审美现代性内涵,实质上是对个人主义价值泛滥所致的社会异化问题的反思和批判。特别是通过病理现象揭示的“所有的价值和文明遭受痛苦的亵渎而崩溃”的荒诞意识,既是对启蒙时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质疑,又是对导致人与社会异化的社会环境的反抗。同时,莎剧对精神病态的关注,使莎剧人物以非英雄化、非理性意识为特征的荒诞意识,有力地消解了以英雄化、和谐化、理性化为特征的传统美学观。由于“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也对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现存的政治、历史、宗教、道德和价值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9](452),因此,以荒诞意识为主体的审美现代性内涵及其呈现出的主体性价值和相对主义美学风格,必然成为莎剧的悲剧性效果的重要源泉。
四、结 语
上述研究也表明,莎剧中的病理现象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莎士比亚化”有着重要的关系。莎士比亚化是通过典型形象反映社会历史本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总结。由于莎剧中的病理现象在典型形象、伦理倾向和悲剧性效应等方面承担着重要的剧作功能,深刻体现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17]而莎剧通过病理现象呈现的“精神的自我分裂和自我耗损”,深刻反映了个人主义伦理价值所致的人的异化问题,从而深刻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7](586)同时,以病理现象为基础的心灵辩证法,深刻展示了以荒诞意识为主体的审美现代性内涵。特别是其呈现的主体性价值和相对主义美学风格,由于“蕴藏着对于现存秩序的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反抗能量”[9](453),必然成为莎剧的悲剧性效果的重要源泉。
参考文献:
[1][美]伯纳德·派里斯.与命运的交易[M].叶兴国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5.
[2]R.P.Robertson.(1959).Shakespeare and medicine.TheLancet,273(084):1210.
[3]Fogan.L.(1989).The neurology in Shakespeare.ArchiveNeurology,(12)8:922.
[4]Martin Boxer.(2009).Biodiversity,Medicine,and Shakespeare.JournaloftheAmericanMedicalAssociation,301(14):1437.
[5]杨周翰主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314.
[6]杨周翰主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22.
[7]范俭雄,张心保主编.精神病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100.
[8]Richard David.(1953).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Epic or Drama? Allardyce Nicoll.(eds).ShakespeareSurvey.Volume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tiy Press,139-142.
[9]田民.莎士比亚与现代戏剧——从亨利克·易卜生到海纳·米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86.
[10][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72.
[11][苏]阿尼克斯特.莎士比亚的创作[M].徐克勤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48.
[12]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485.
[13]Edward Bond.(1992).TheActivistsPaperinPlays:FourM.London:Methuen Drama,127.
[14][英]阿诺德·欣奇利夫:荒诞说——从存在主义到荒诞派[M].刘国彬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73.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
[16][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34.
[1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