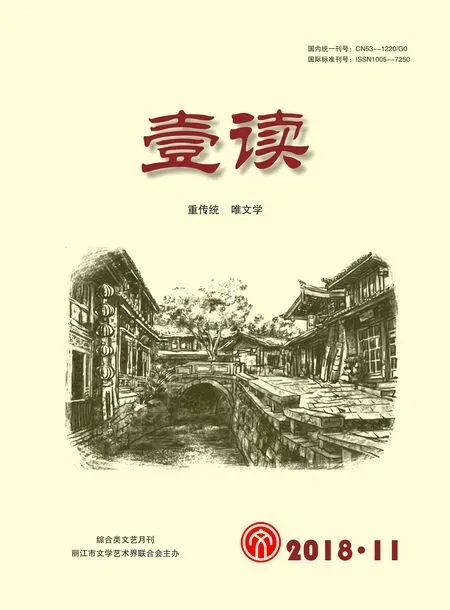丽江古城黄山村
牛耕勤
“狮子斩腰”
丽江古城黄山村,纳西语称“瓦古”,也就是汉语“坡头”或“坡上”之意,因它座落在狮子山坡上而所得地名。狮子山又称“黄山”,在明代木土司时就有此汉名,《徐霞客游记》中就有“黄峰”的记录。狮子山是民间的称谓,是与丽江坝子中的龟山、蛇山、象山相联系的,是丽江吉祥山脉之一。
狮子山还有小狮山,原民主广场西北的小山坡便是。
在明代,作为木氏土司衙署及家院“托鲁”(汉意为“靠石”或“靠山”)的狮子山,是不可随便开发和践踏的。据说改土归流后,丽江儒学教授万咸燕在大破丽江龙脉中,也破了木氏“靠山”狮子山的龙脉,开山凿石修了一条山道,就是现在的黄山村(瓦古)至“瓦托”(狮子山背后)的上山下坡之路,也就是民间所传的“狮子斩腰”。斩腰后的狮子是不可能腾跃起来的——让降为土通判的木氏再也翻不了身。
虽然木氏没有再出现木增这样的杰出人物,可民间却代有新人出,甚至在破过龙脉的束河出了一个政绩显著的云南省长。
狮子山修了山道之后,没有马上成为村落,比古城其他村落的形成要缓慢得多。因为这里要爬山下坡,更要紧的是缺水,因而每天要下山爬坡到四方街卖鸭蛋桥边的西河里挑生活饮用的水。所以过去有“有女不嫁瓦古(黄山村)”之说。
村落的形成与修建了山丫上的接风楼相关。而接风楼是在“狮子斩腰”后才修建的。这从修建接风的民间传说中可以得知。
接风楼的传说
为什么接风楼没有修建在鹤庆到丽江最接近的八河,而大绕一圈建在需要多走三五倍路程的狮子山丫口上呢?
原来新任的流官来丽江任职时,丽江要派人用大轿到东元蛇山白塔处去迎接。那里是观赏丽江风光的一个好地方,站在那里往丽江望去,一派青山绿水蔟拥着一座美绝人寰的玉龙大雪山,真如人间仙境。可那座落在金虹山下的流官府城,由于远眺和视角的关系,难以看到瓦屋栉比以及迅速发展起来的全貌,远处看只像个小不点儿的让人心寒的地方。
于是,选择在视线和角度最好的“狮子斩腰”坡上——瓦古,建了土木结构的上覆青瓦的二层的接风楼。用大轿抬着新任到丽江的知府和知县,不走捷近之路(从八河过万字桥到县署和府署),而是绕一大圈后,从狮山背后(西面)爬山抬到接风楼,在接风楼款待他们的同时,让新任的丽江父母官一睹东面坡上流官府城那气势不凡、层叠有至的府衙署、雪山书院等府署建筑群,和一片黑压压的民居村落以及纵横的街道。岂能不让新官刮目相看,激荡心房!
这就是接风楼的由来,是为了迎接新官,不惜绕道爬坡,给新来丽江上任的知府、知县,在接风楼接风洗尘的同时,让他俯瞰将要工作和生活的丽江府城,留下一个美好的最初印象。
机智人物阿一旦
阿一旦是纳西族的机智人物,他的故事在丽江家喻户晓。他不是传说人物,而是真有其人。
阿一旦是古城人,家住黄山村(瓦古),当是祖辈从外地迁居在这里的被同化的纳西人。他可能是清代道光年间人,这可以从他在万字桥溪落当时丽江四大诗人——“马牛羊(杨)三(桑)畜一同坐”的故事中看出。
他长期被木老爷(土通判)雇用做事,常用他的聪明才智跟木老爷开玩笑,使木老爷常常上他的“当”而出了不少“洋相”,便产生了一些风趣的故事,例如:《公喜母喜》——碰上生孩子的头客要喝冷水而产生的风趣的故事;以新碓换旧碓的《木家败,木家旺》;让木老爷《上楼下楼》等,这些故事反映了木氏由土司降为土通判的社会地位,成了与阿一旦平起平坐的平民。事实也是这样,中国有句话叫“凤凰落毛不如鸡”。
我最欣赏的是阿一旦的荒诞故事《张飞战岳飞》(整理后名“张飞杀岳飞”),一个是三国人,一个是宋朝人,虽然都名“飞”,但相隔好几个朝代,800多年时间,怎么会在一起撕杀?阿一旦用宗教中的轮回转世的手法,让张飞转世在岳飞时代,在南天门相遇,便如见仇敌开始“张飞战岳飞,战得满天飞”。不管结局怎样,却是用一个荒诞故事的手法,成为经典的民间故事,有其值得称道的地方。
阿一旦是古城人,发生的故事大都与大研古城的人和事有关,后来的整理者,将其他机智人物的故事,都“整理”成了《阿一旦的故事》,这好象是合理的,从人物的塑造上来说也比较丰满。不过,作为民间故事,流传的地点是很重要的,我在丽江六区大山中生活工作之余搜集民族民间文学时,虽然听到过机智人物的故事,但从没有听说“阿一旦的故事”,反而动物的故事比丽江坝子的多得多。这是民间文学的地域(生活)性使然。
发生在大研古城百岁坊和拔贡家的“十月开牡丹”的故事中,讲的是把诗人都邀到和家赏花吟诗,这是古城的习俗,丽江清代民国诗人中不乏此类诗作,阿一旦心里不平,来一番奚落也是可能的。
总之,阿一旦是真有其人的,他的家就在黄山村。只要我们一经“定位”,就可以分明哪些是“古城阿一旦的故事”,哪些是改编的“阿一旦的故事”。
被报复的猎人
这个流传在大研古城里的故事,发生在古城黄山村。这个故事说的是有个喜欢打猎的人,打伤了一只狮子山上年老成精的白狐狸,而遭到祸殃……
传说接风楼附近,有个经常打猎的汉子,有个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管山神(东巴经典神话中属主宰自然的“署”类)对他说:“不要去打猎了,即使看见野兽也不要去射杀。如果还去,那对你及家里人都不会有好处的。”
汉子醒来时,天已大亮,便一股碌从床上爬起来。他好生奇怪,把平时不离身的弯把火枪习惯性地拿起来,放上火药后,不放枪(铅)子,便挂在墙上。他心想再不能去打野物,上山时放一放没枪子的火药枪,过把瘾算了,便出门去做别的事。
想不到的是,家里人拿着竹扫把低头扫地时,在他屋里看见一个圆圆的铅子弹在地上,她想可能是他不注意时枪口一朝下,这铅子从枪管里溜下来掉在地上的。便捡起铅子,取下猎枪,仿着平时看见他灌火药铅子一样儿,把铅子从枪管里灌进去,并想象着又一次吃到野味的美好感觉。
猎瘾如烟瘾,改不了上山打猎习惯的他,又扛起猎枪,走出家门,朝山林走去。他想,即使遇见野物,放它一枪,因没有铅子,“轰”地一声吓吓野物,过过猎瘾也好。
他在狮子山林里转了一大圈,连只松鼠的影儿也没碰见,便百无聊懒地来到白马龙潭上面的向阳坡上,只见一只被人们认为是年老成精的白狐狸蜷伏在那儿,正晒着冬天里温暖的太阳。
他情不自禁地抬起枪,瞄准了白狐狸,但梦境在他脑子里回放……猎人便缓缓地放下来。但他又想起枪管里只放了火药,没放铅子,放一枪只不过吓它一下而也,根本伤不着一根毫毛。他便重新抬起枪,对准它扣动了板机,“砰”的一声,一颗圆溜溜的铅弹,从他枪管里飞出,立刻穿过白狐狸的大腿。
受伤的白狐狸一蹦老高,便一路滴血,一路哀叫而去……
猎人呆若木鸡,双眼发直,他哪里想到枪管里会飞出子弹,而且射中白狐狸!想起那天早上做的梦,他害怕极了。
自那以后,不知为什么,他的神经便出现了问题,家中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跟着患起病来!
这怪异的故事在小小的古城里,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哪敢上山去打猎?!
安然无恙的狮子山,成了老鹰、喜鹊、乌鸦和一种纳西语叫“近甘”的类似喜鹊的飞禽们栖息的乐园,也成了狐狸、松鼠等小走兽的乐园。
阙拔贡
阙开恩(1825—1896),十七岁入雪山书院,生员。因成绩优异,成为吃上皇粮的廪生。二十五岁赴京朝考一等,成为拔贡,授七品京官,在清代最高学府国子监当助教。但由于家里催他赶快回来,便辞去职务回到丽江古城黄山村,在家中办私塾。
在“乱世十八年”初,也就是咸丰六年(1856),投笔从戍,成为清军杨玉科的幕僚,也可能是师爷,转战于滇西等地。因曾写信给杜文秀将领马如龙,使他倒戈投靠于清军。因此,立了军功而得到六品官同知。
同治十年(1873),战乱结束后,任马龙州教授。光绪十四年(1888),回到故乡丽江,任雪山书院山长,是丽江雪山书院中唯一的拔贡山长。在他之前都是举人以上的山长。
阙开恩任雪山书院长后,本来在书院中讲学的满肚子学问的李玉湛,便辞职回家,因为他是举人,并以诗文著称,而阙开恩只是拔贡,他感到怀才不遇,心中愤愤不平。李玉湛以真才实学创作的诗文流传至今天而不衰。
阙氏的孝子贤孙
阙拔贡的叔叔阙华是个大孝子,他的事迹记载在《光绪丽江府志·孝友志》中:“阙华,字乐秋。谨慎简默,厌世俗之浮靡,时以礼自防闲。事亲孝,其父好饮酒,喜怒不常,一日华偶失父意,父怒而逐之,使别居,华号泣求之。不允。
(华)每日黎明自外至其家,问寝视膳,愉色惋容,仍供子职。父怒曰:“吾不以汝为子也,复见我何为?”乃以杖击之。华仍引昝自责,次日又至,亦如之。如是者凡五月,父悔悟,复相待如初。
亲殁治丧,俱遵朱文公家礼,不用浮屠斋荐。邻里亲友笑而非之。华终不以为意。年七十无病而殁。”
父亲酗酒时,偶然使父亲不如意,父亲便将阙华赶出家门。而阙华一如既往,每天天一亮就到家中服侍父亲,从不间断,一连五月,使父亲大为感动,悔悟到当初自己的不是。这是何等感人的大孝子!
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在丽江古城遭到前所未有的“乱世十八年”,阙华的两个十来岁的儿子,阙开中和阙开泰,做出舍身救叔的感人之举。《光绪丽江府志·孝友志》载:“阙开中、阙开泰,(阙)华之子也,性孝友。咸丰戊午(1858),从其叔阙萃避难左蒲,夜半忽有盗数十人,劫其家,焚其庐。时开中方十六岁,开泰甫十三岁,私相议曰:‘急扶二叔避后园荆棘中,庶可免祸。叔三人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言未毕,盗已至前,厉声叱曰:‘汝二人黄口稚子,尚未足污吾刃,盍速去!’
开中兄弟跪而泣曰:‘此老者乃我之叔父,年已衰迈,乞免箠楚,愿以身代。’盗不应。兄弟以身障蔽其叔,捍卫甚力。盗怒,遂伤其叔,掠其财物而去。有顷,众盗中一人回顾曰:‘彼二童虽幼,不如杀之。以绝后患。’并伤及其兄弟焉。其家人延医调治,半年始癒,至今脑后尚有疮痕云。开中于同治壬申(1872)中文庠。”
这是多么可歌可泣的事迹,不愧为民族青少年典范。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尤其是现在。
阙氏父子堪称古城孝子贤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诗人杨菊生
黄山村的村落形成较晚,因而清末至民国年间才出现弄墨舞笔吟诗作赋的文人。诗人杨菊生就是其中一位。他的诗明白如话,又不失诗的韵味,因而时任丽江县太爷的诗人何文选作对联称赞他的诗:“……,诗在苏欧李杜间。”说杨菊生的诗作已在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苏轼,北宋文学家,史学家诗人欧阳修,唐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四者之间。虽然说得有点夸张,但也说明杨菊生的诗不是无根底,无造诣一般之作。
杨菊生生于清代同治三年(1864),考取贡生后,曾赴京朝考,却名落孙山,失意归来的他受指云寺木大喇嘛的聘请,到文峰寺给喇嘛教汉文书,之后到中甸任教达二十余年。
在文峰教书期间,颇具诗才的他先后吟了三四十首诗,如《初到文峰寺》:“空从海上聘长游,辜负名山几度秋。三十七年今一到,方知此地胜瀛州。”此诗当作于1901年,是同和庚吉、王成章等赴京朝考后,一路旅游而回,37岁才头一次到了文峰寺,才知道这里的景致是那样的美,简直胜过了瀛州。接着诗人写道:“海上归来百念灰,聊开绛帐住山隈。春风有意培桃李,取向阶前次第栽。”(《栽花》)此诗表达了考举落榜后的不快之心,也透露了在文峰寺教书时,有意栽培桃李的愉悦之情。
许多人都不清楚杨菊生是大研古城的哪个村子的人,据我确切了解他是黄山村人。其实在他的文峰寺《石(灵)洞望远》诗中便可以得知:“已上层楼更有楼,烟鬟无数望中收。僧童问我家何处?指点黄山柏树头。”“黄山柏树头”说的是黄山村。
《记得山中好十首》是杨菊生在寺中教书时,清静无喧,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心得之作。他最后写道:“可能欲尘弃,长此住文峰。”
第二年,他又去赶考,落第后《重到文峰》:“郡城西南二十里,文笔高峰特地起。中有古寺最清幽,课读一年曾到此。……碧鸡山前失意归,家居又过一年矣。生来结就名山缘,新春扬鞭复戾止。”也就是说在文峰寺给喇嘛教了一年书后,第二年又去赶考,也没有考上,便又到寺中教书。
1926年,木大喇嘛圆寂后,杨菊生才到中甸教书。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出口成章的他可能吟有数以千计的诗作,但因社会变革,加之“文革”,已荡然无存!这是十分可惜的。
2014年,我在丽江古城区政协文史委抢救整理出版的《杨菊生诗稿》,计有230余首。他在文峰寺所作的《晓起见雪》中说:“我不学画强学诗,意境终嫌欠涵蓄。天公游戏亦偶然,白描高手定谁属。”可知他的诗作直抒胸臆,自自然然,没有雕琢的痕迹,是白描的高手,也是纳西族历代诗人中独具一格的,是值得研究的。
诗人王竹淇
黄山村的举人王竹淇(1864—1933),也是民国时期的丽江诗人,他所著的《退省斋吟诗集》共有十二卷,可能有一千多首,在同时代丽江纳西族诗人群中,也算高产的一位。《新纂云南通志·文苑志》载:“王成章,字竹淇,丽江人。光绪已丑(1889)举人,里居不仕,开门办学。性倔疆,出语凝重,有不可于意事,辄庭争座质,声动左右,长吏目慑之不顾也。其为诗,若决江河,浩溔演迆,若无涯涘然。有时箝波东流,蓄为澄潭小沚,亦具澹远之致。丽江诗人著作富者,以成章及杨遂侯(即杨菊生)为最云。”可惜经过“文革”,现只剩卷二、卷八、卷十二,计220余首。
我认为历代丽江纳西族诗人的作品都是民族文化遗产,因而为王竹淇十二卷诗作只剩四分之一而扼腕叹惜。
丽江古城只不过是十几个村落组成的小不点儿的滇西北边陲之地,但是从明代出了土司诗人群,到清代出了民间诗人群,到民国出了更多的诗人群,真是不可思议,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如今成为丽江低俗的“麻将賨”,原是古城诗人为交流作品的高雅“文化賨”。
在赵银棠老师的《纳西族诗选》和《纳西族文学史》中,选辑和参考的王成章诗集是卷八和卷十二。在我们抢救整理古籍之中,除得到卷八、卷十二之外,还得到了长诗卷,也就是《退省斋吟诗集》卷二,是和仕华提供的,我为之幸运,因为能把丽江诗人作品抢救过来,就能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唯有文化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灵魂。
卷二为《丽江石鼓歌》《玉泉秋月》《雪山行》《金沙江行》等七言长诗30首,也是尚无披露过的一本长歌卷。在《丽江石鼓歌》中诗人与众不同地吟道:“此鼓远弃南荒外,江干寂寞委革莱。既无文字纪年月,焉有骚客题歌诗?俨然石中隐逸品,不肯炫耀求人知,完全太璞此终古,皎皎昭质应无亏。何来好事木土府,矜伐战功镌肤辞。遂令宝物受污辱,白圭元壁增瑕疵。对此摩挲发长喟,石不能言心伤悲。”这是丽江诗人都吟有“石鼓”诗作,而与众不同的吟韵。
《玉泉秋云》中,对“龙潭倒影”这一绝美景色,作了精彩描绘“……倒影更有雪山雪。玉龙蜿蜒吞明珠,掀波震荡老蛟窟。岂有玉山圮瑶池,恍认珠宫裂贝阙。冯夷击鼓嫦娥奔,烨烨电光掣列缺。山色树色兼雪色,混为一气满地白。目眩心惊舌频咋,神怡意会口难说。”
《雪山行》中,诗人面对的玉龙大雪山是那样的圣洁:“古雪不减新雪增,照耀寰区表清洁。山耶石耶骤难分,云耶雪耶终难别。千秋皎洁无所污,万古峣峣不曾缺。”甚至于“嗟我生长于斯邦,欲游自愧乏仙骨。日对名山默无言,山灵应笑我陋劣”。如同所有的丽江纳西人对玉龙大雪山这护佑民族之神“三多”的化身,是那样的崇敬,“三多神”是那样的圣洁无比。
诗人道:“从来人杰由地灵,古语流传岂恍惚?”有这么一座拔地而起的雄奇圣洁的玉龙大雪山,丽江肯定不乏杰出人物。
而今“雪山之名播全球,不难到处逢人说。地以人重不予欺,山与人兮足相埒(等同)”。这里诗人指出了怎样去呵护名播全球的玉龙大雪山。
王竹淇在六十自寿诗(八首)中自我评价他的作品“文探两汉词深厚,诗学三唐句雅驯”。怪不得他作了千多首诗,即便是深更半夜,一时兴起也从床上爬起来作诗,甚至做梦也在吟诗哦句。
“滇南两任司儒学”。1897年及1900年王竹淇先后任禄劝和永善教谕。回家便办私塾,慕名而来的学子极多。
废除科举制,推行新学制后,1909年及1911年他曾两任丽江劝学(教育)之长。他与时俱进,身体力行,为推行新学,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性情耿直的王竹淇,做了一件最能打动丽江人民的事情。1929年,在云南的“胡龙之争”中,为切断胡部张汝骥的后路,龙云电令鹤庆、丽江县长等拆掉架设于丽江通往永胜的金沙江山金龙桥!
毁桥容易,建桥难。尤其是人背马驮的时代,金龙桥是关系到丽江人民日常生活的交通要孔。作为丽江士绅的和进士(庚吉),王新爷(竹淇)等,考虑到丽江人民的切身利益,不能为军阀混战而给百姓带来长久的灾难,便坚决反对拆掉金龙桥。
卢汉率部赶到鹤庆后,见鹤庆不执行电令,就将商会长和士绅等立即枪毙,并勒令丽江县太爷等马上到鹤庆去!不愿去送死的县太爷陈嘉荣招来和进士、王成章等人议事。
和进士首先表示愿意为民请命到鹤庆去。王成章也义不容辞地说:“进士去,我也去!”在场的除了县太爷,周冠南等表示愿意去。为地方百姓的利益,几个丽江的士绅都带上纳西人临死时少不得衔口物——“绍少”,也就是作好死的准备去鹤庆,此行凶多吉少!
古城人泪别了他们,都认为他们将一去无回。几位士绅到了鹤庆,见了卢汉以后,激动的王竹淇首当其中,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对卢据理力争:“民为贵,君为轻……再说丽江收到电令时,张汝骥的部队已过了金龙桥……”看他激动得不能自已的样儿,和进士都为他着急而悄悄拉了一下他的后衣摆说:“阿忍受拉默(慢点儿说)”。
卢汉看了电令,看着几位饱学的丽江士绅,没有再开杀戒,而是放他们回去。
丽江的父老得知王竹淇、和进士等从鹤庆凯旋而归,扶老携幼到下八河五里牌去迎接。
狮乳泉
《光绪丽江府志·水利志》这样写道:“半月泉,在狮子山麓光碧村,一名狮乳泉 ,甃(砌)石为潭如半月,故名。村人赖此灌溉汲饮。”可知丽江最为著名的在光碧村的三眼井半月泉,又名“狮乳泉”。还有一个“狮乳泉”在黄山村的半山腰,即在那棵很有年纪的老槐树上面的杨家院内。老实说,作为古城人,我曾无计其数地上去下来过黄山村那石径斜的山坡路。但从来不知道这里的民居家中躲藏着一口可谓“纯净水”的小巧的水井,在民间传为“狮乳泉”,却不是志书上所记载的“狮乳泉”。
改革开放以后,在2.3丽江大地震以后,狮子山头竖起了一座木结构的冲天高楼——万古楼,过去称为“有女不嫁瓦古”的黄山村,成了游客观光景点之路,封闭已久的石磴路两边的铺面,都噼哩啪啦地对开放起来。
连黄山村的年轻人都不知道的狮乳泉开始抛头露面。我在此时才知道这里有个镜子般明净的小水井,明代时便在民间传为“狮子乳”。
这从水井背后依山而建的楼层上,宣统二年(1910)八月王成章作的,并叫他的弟弟王锡章书写的《是亦池歌二十韵》中可以得知:
黄山山半路崎岖,磴道盘曲劳行趋。
高楼数间宅一区,西川旧族杨雄居。
绝壁飞来百余尺,峥嵘峭立西南隅。
下有小池浏其清,息与寻常沟渠殊。
夏不陡涨冬不竭,琼浆玉液常涵濡。
煎茶酿酒沁肺肠,味擅甘美如醒醐。
莫嫌狭小水清浅,鱼虾游泳颇容与。
四时花卉倒垂影,互相辉映云霞铺。
世俗相传“狮子乳”,是耶非耶疑有无。
回忆丙戌庚寅岁,旱魃为虐河水梏。
僧道祈祷少灵验,男妇奔走愁号呼。
蒲苇藻荇生尘埃,鰋鲤鲦鲿饱鸢鸟。
惟此池水幸无恙,澄莹秀澈涵清虚。
二十年前著奇异,目所亲见良非诬。
嘉名肇锡是亦池,不以柳州辱以愚。
……
从王竹淇二十韵的长歌中,我们知道在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黑龙潭水从二月枯干到六月,十六年庚寅(1890)又一次干涸。不过这狮乳泉一直没有干枯,真是个好水井(是亦池)。
当时这口井肯定对黄山村居民的饮水也作了贡献,虽然诗中并没有指出。
结语
狮子山头黄山村的形成是在“狮子斩腰”以后,尤其在修建了为丽江流官洗尘的接风楼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村落。
黄山村是外来杂居户最多的村落,因而成为大研古城姓氏最杂的最多的村落,比西营盘(振兴巷)还要多,除了和、木二姓外,有邱、阙、王、杨、苏、兰、李、赵、施、刘、潘、桑、程、陈、黎、徐、奚等姓。这也是没有富商的一个村。由于不同姓氏较多,被丽江的文人用姓氏编成了五言的顺口溜:“奚黎兰苏徐,……潘阙木。”
黄山村是清代大研古城往来于藏区的茶马古道的主要村落,也就是必经之地。古城人形容从藏区驮运回山货药材的大商家的马帮之多,往往会说:“头骡已到家中,尾骡还在瓦古(黄山村)。”
这里的民居多为平房,较之城中房屋普遍低矮,这与后来才发展起来而未产生大(商)户人家有关。由于形成村落较晚,清末才出了举人,拔贡(阙拔贡),民国时期才出了杨菊生,王成章等诗人,都出生于1864年——那不幸的“乱世十八年”中。举人王竹淇一生写了千多首诗,自认为“文探两汉词深厚,诗学三唐句雅驯”。他的名气好似稍逊杨菊生,这大概跟何文选县长赠给杨菊生对联的评论之句有关。当然吟诗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清代著名的丽江纳西诗人牛焘,只自选了290首辑成四卷,其余都不惜割爱,但都是精品和上乘之作。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76年“2·3”大地震后,狮子山上修建了旅游景点万古楼,曾一度清静冷落的黄山村,一改旧貌,街道两旁的平房都改建成楼房,纷纷开起了客栈。游览万古楼,鸟瞰古城全景的游客,穿梭不息,真个旧貌换新颜。
黄山村也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清代出过机智人物,民国出过著名诗人。而今有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副教授和云峰,丽江纳西族第一个电影男主角演员,并获华标新人奖、金鸡奖最佳主角和配角演员提名奖的邱林等,在这里是值得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