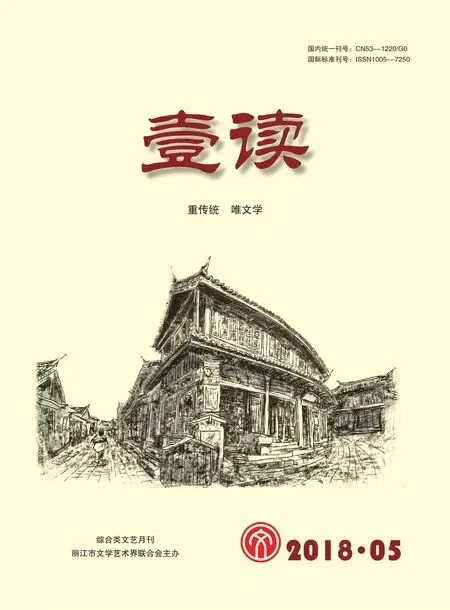时间里的乡村(组诗)
华秀明
村庄速写
锄头让土地长高
一把镰刀
又把长高的部分割掉
许多水井站在地下
它们忠实于自己的本分
从井底到井沿
面色红润的女人
每天都能从中
打捞出
波光粼粼的日子
起伏的山冈上
羊的叫声充满了颤音
杨柳清新
河流总是
沿着弯曲的远方生长
黄昏的某个烟囱里吐出白烟时
梦一样的房屋
像旧时代的火车头
拖着一列青山
在河岸上,与流水并行
关马山以西
从这条路上走去,关马山以西
有大片的杨树林
经过一片沼泽。如果你
迎面逢上
一个口袋里装满秋风的人
替我转告他
冬天就要来临
他的羊群,要走出金黄的杨树林
南方向南
一条叫做金子沟的溪流旁
他的女人正在用
一把燕麦草
清洗他装酒的器皿
午后的素描
午后的院子,东北角
那只老母鸡像一台掘土的机器
两只爪子
不断向后抛出土粒
一只鸡仔,被它母亲连同土粒
一起抛了出去
在地上,松果似的滚了几滚
又凑上前去
这一幕发生在去年秋天
午后的老家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乡下的秋天
秋天的乡下,到处是一些奇妙的感觉
比如劈柴,远处的人
看到那把斧头落下去很久,才听到响声
生前棵棵独立的玉米秸
一把镰刀让它们亲密地拥抱
蚂蚱在枯草尖上,振翅弹腿
谷草垛旁
热烘烘的阳光让人昏昏欲睡
一只母羊
在收割完水稻的田埂下生产
它发出激荡田野的叫声
远处那只公羊充耳不闻
刚订婚的小花,在她情郎的手背上
咬出一个月牙形
一匹马为了爱情,驮着三百斤的豆子
跑到邻村去了
它的主人在路上骂骂咧咧
老头与乌鸦
老头在山脚下种了一辈子玉米
到了秋天,他的玉米
一部分
成了乌鸦的口粮
最后一个秋天
所有乌鸦扇动着黑色的翅膀
扯起喉咙
发出短促而凄厉的叫声
仿佛,它们要把吃下去的
粮食吐出来
还给死去的老头
雪天
没有一棵树会被枝上的花朵
压断枝头
当然冬天的雪花除外
来自天空的力量太强大了
它超过了
一棵树对它内部的评估
为了迎合一场
对地面爱得死去活来的大雪
天空降低了她的高度
林子里传来了
第一根枝条折断的声音
路边。一只受惊的兔子启动
它弹跳的装置
向那边的桉树林奔去
黄昏过后
黄昏过后,有一些明亮的事物
出现在窗户那头
那是我阳台上的花盛开的朵
白天,我在那里施肥,浇水
偶尔用一把生锈的剪刀
剪去枯萎的时光
就这样,为了让一些植物
在夜里看上去
是在天边发光
我倾注了无法计量的时光
二月,在乡下
二月,在乡下
看阳光滚过的麦田
那时,麻雀还停在光秃秃的树枝上
喜鹊的叫声
让梅花的身影闪过山洼
站在地下的水井,养活杨柳
一样养活了炊烟
在山冈平缓的弧线上
我们看见
一只温柔的母鹿
朝这边张望
我们从远方赶来
我们高举着小小的火炬
从远方赶来
一路上。夜风向后
吹出了
一面红色的小旗子
母亲站在村口
大风扬起了她的头巾
我们从远方赶来
仿佛就是为了
向黑夜中的母亲交出
手中那面
呼啦啦的小旗子
我要去一座青山脚下
我要去一座青山脚下
拜访一个老人
传说他在南山牧羊,北山种豆
他的舌头下面
压着一万卷发黄的经书
穿过大风呼啸的山口
我问过
一个逆风而行的人
他的言语
一再否定青山绿水
他用手背揉着眼
一百年前,他说,祖先在那里升起
笔直的炊烟
现在那里只剩下风
午后三点
我贪恋冬日午后三点的阳光
一只灰鸽子在檐下低鸣
院子的西北角
我备下一把藤椅
矮几上
我为自己沏了一杯茶水
我不喝咖啡
这个下午,毫不相干的事情
与我隔着一道院门
我用一张旧报纸遮挡脸上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