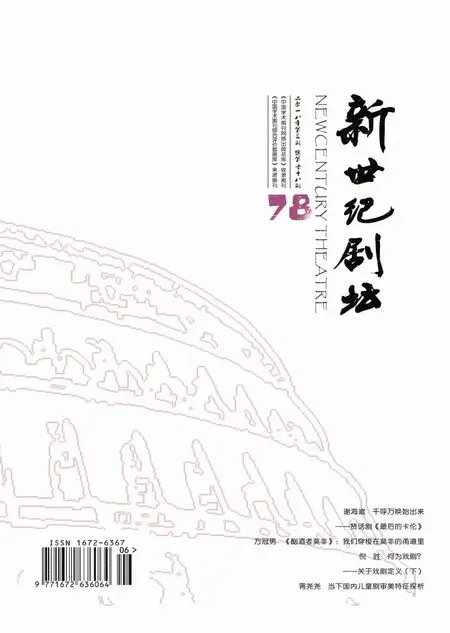再论经典:“萨本”世界电影史的三种倾向性
寻茹茹 沈 鲁
1979 年出版的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在世界电影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不但促进了电影史学科的构建与发展,而且对各国电影史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例如,中国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无论是史学研究方法还是写作体例内容都受到“萨本”世界电影史的影响。作为梳理世界电影史的巨著,“萨本”史料翔实、论述严谨,涉及到对近五十多个国家及地区电影历史的梳理,尤为可贵的是不遗余力地搜集被此前欧美电影史学家们所忽略的广大亚非拉地区国家的电影生产情况与史料。但是,与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官修正史”不同,萨杜尔《世界电影史》的编撰完全是个人行为,正如亨利·朗格卢瓦在此书序言中所指出:“萨杜尔令人钦佩之处正在于他的自觉意识。”[1]“萨本”对史料的考证、记录与辨析有一定选择性,“萨本”的编撰、评论具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性”,显示出史学家的某些“偏私”。辨析“萨本”的史学“偏私”,找出此书的“倾向性”,是阅读“萨本”的《世界电影史》的前提,更是了解、学习世界电影史的前提。纵览“萨本”《世界电影史》,其倾向性大致可以分为艺术倾向性、社会倾向性与地域倾向性三个方面。
一、萨杜尔社会身份辨析
历史研究要求客观、中立,应是站在第三者位置的书写。但是,史学家——历史的书写者,注定有其各自特殊的立场。历史学家总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而且他所面对的过去又和他所处的现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做到绝对的独立与超然是不可能的。同样,电影史家也会面临这一挑战。因此,研究“萨本”《世界电影史》的倾向性,首先要辨析书写者——乔治·萨杜尔的社会身份。
出生在艺术气氛浓郁、电影历史悠久的法国,萨杜尔从小痴迷电影。少年时期的萨杜尔是路易·德吕克创建的电影俱乐部会员,是法国南锡电影活动的核心人物。受到1920年代法国“迷影运动”的感召,卡努杜、德吕克和爱浦斯坦等人的迷影情结,在萨杜尔身上得到了传承。对电影的无限热爱,是萨杜尔编撰《世界电影史》最根本的驱动力。与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的相遇让萨杜尔的迷影情结与政治信仰发生了关联。通过路易·阿拉贡,萨杜尔结识了一些法共艺术家和当时的超现实主义团体。从1930年开始,萨杜尔开始为法共杂志撰写文章,成为忠诚于无产阶级的“战斗知识分子”。二战期间,与安德烈·巴赞一样,电影成为萨杜尔“现实的避难所”,他于1940年就开始着手搜集早期电影史料,撰写《世界电影史》。萨杜尔的影评阵地是长时间影响法国左翼艺术家的《法国文学》杂志。《法国文学》与《新批评》《法国银幕》和《欧洲》并称为法国“四大左翼杂志”,是战后法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刊物之一。1944年萨杜尔开始为《法国文学》撰写影评专栏。
萨杜尔是一个苏维埃主义者,他曾三次访问苏联并面见斯大林,约见了很多苏联导演和作家,对前苏联电影的研究非常深入。后期研究陷入对斯大林的崇拜中,直到1961年赫鲁晓夫报告出来后,萨杜尔开始进行严峻的精神反思。20世纪50年代萨杜尔夫妇受邀来到中国交流访问,当时筹备《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主编程季华就负责接待萨杜尔夫妇。
二、“萨本”电影史的社会倾向性
基于以上的阶级立场、社会身份和道德信仰,“萨本”《世界电影史》编撰侧重了社会学批评,强化了电影作品的“社会功用”,突出了评判的“社会倾向性”与意识形态性。萨杜尔认为电影要表现本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应该唤醒人民的民主反抗意识,具有本国的民族特色、人情味与人道主义精神,电影要为社会进步扮演重要的角色,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从某种程度上看,“萨本”把电影史当作表达自己政治立场和社会批判的工具,而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文本。“萨本”电影史在辨析、筛选和评价电影文本、电影现象及电影流派之时,尤为强化“社会进步性”,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对电影流派和具体作品进行评述之时,萨杜尔强调“反映现实生活”的重要性。例如,“萨本”中对英国“布莱顿学派”的描述:“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浓厚兴趣,对先进技术的追求以及描写社会问题的倾向,是1902年英国电影的特征。例如,威廉·保罗一度倾向于社会问题的描写。”[2]萨杜尔认为1930年之后的英国电影,即英国的纪录片电影,也具有相似的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所以萨杜尔认为这是英国电影的传统之一。具体到电影文本分析,“现实性”也是评判其优劣的重点衡量标准。例如,“萨本”对卓别林《安乐街》的评价:“影片中对社会的讽刺和批评,却远比它们的娱乐意义更为重要。”[3]
第二、“萨本”会经常用“人情味”“人道主义”这些词评析电影作品及导演,体现出萨杜尔关注电影对底层大众的表现。例如,“萨本”对美国纽约纪录学派的描述:“以保罗·斯特兰德为中心的纽约学派,就其作品的完美性和勇敢精神而言,却大大超过被人过分吹嘘的英国学派。”[4]萨杜尔严格区别了美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对美国电影中表现人道主义的纪录片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在描述具体电影作品与电影导演时,萨杜尔也会用此标准来衡量。例如,在评价希区柯克与黑泽明这两位著名电影大师时,萨杜尔用“人道主义”这一标准做了区别对待:“希区柯克主要的错误是他满足于故事情节的巧妙安排,而不注意这些情节所蕴含的人情味。”[5]对黑泽明的描述则是:“黑泽明那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很自然地和世界知名作家的作品结合在一起。”[6]
第三、“萨本”还强调电影揭示社会问题。例如,对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评析:“恐怖、幻想和犯罪,固然是表现派影片最显著的特色,但是这些影片更多的是有意或无意描写战后德国的混乱情况,似乎在召唤一个致命的妖魔(暗指希特勒)。这些影片中的表现主义手法正如一种变相的比喻,为威玛共和国初期的德国命运做了写照。”[7]对待德国这一造型性、表现力极强的电影流派,“萨本”更多的是从揭露社会问题,从社会倾向性进行评析。
三、“萨本”电影史的艺术倾向性
虽然萨杜尔在《世界电影史》前言中强调电影的“综合论”研究方法,在书中也贯彻了从“企业”“经济”“社会”和“技术”等方面较为全面梳理世界电影的发展,但是,“萨本”仍是将电影艺术的历史作为研究的最终目的。萨杜尔认为,电影史首先是作为艺术形式的电影的历史,电影的经济与技术则是放在第二位,例如制片人、发明家、企业家并没有与艺术电影的创作者得到同样的关注和对待。所以说,“萨本”《世界电影史》具有明显的艺术倾向性。
萨杜尔有意将电影史描述为电影艺术的发展史,除了与法国艺术电影悠久文化的浸染有关,还受到西方“唯杰作”传统的影响。西方主流美学理论一直把中央的位置留给艺术家。艺术作品不仅常被看作是形式特征的范例,而且也常被看作是艺术家的想象力与表现力的具体体现。这种以艺术家为中心的美学观点认为,艺术的历史就是对个别艺术作品的检验,而这些作品足以反映出创作者的天才。“萨本”是一部符合作者价值判断标准的优秀的作者作品史。对于“萨本”来说,研究电影艺术的历史就意味着鉴别和评价过去产生的伟大的电影艺术作品,并在电影史中推崇具有艺术价值的影片和艺术家,把电影理解为伟大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伟大作品。所以,电影艺术作品最重要的是创新性,而不是类型与模式。根据“唯杰论”的原则,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萨本”对哪些杰出的电影艺术家、电影作品进行了肯定与赞赏,又有哪些电影人与电影作品遭到了艺术上的批评。
(一)“萨本”的褒奖倾向
“萨本”赞赏的法国电影艺术家,包括:费雅德、林戴、阿贝尔·冈斯、让·维果等等。例如,“我们还是比较喜欢费雅德,而不喜欢稍嫌呆板的彼雷,因为费雅德象一个忠实的薄记员那样,正确地记录了真实情况,对每一米胶卷的使用都非常认真。……正如在费雅德的优秀作品中一样,我们可以看出从冈斯和爱普斯坦、普克塔尔和费戴尔一直到雷诺阿和卡尔内的法国电影的连贯性。”[8]萨杜尔很是赞赏费雅德,赞赏他的作品的艺术性,更赞赏法国电影的传统。
“萨本”最赞赏的美国电影艺术家是格里菲斯与卓别林。萨杜尔称格里菲斯为天才,认为他是“当时在电影界中占第一把交椅的人”。“萨本”评价《党同伐异》:“这部影片是格里菲斯艺术达到最高峰的标志,同时也是美国电影艺术达到最高点的标志。”[9]除了格里菲斯,萨杜尔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家就是美国演员查尔斯·卓别林,“德吕克说,卓别林已超过它的老师麦克斯·林戴,可以和莫里哀相提并论。当时爱里·福尔在谈到夏尔洛这个角色时,说卓别林使人想起莎士比亚。”[10]将卓别林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可见萨杜尔对卓别林的评价之高。
(二)“萨本”质疑之声
在“萨本”中出于艺术价值的标准,萨杜尔会推崇、赞赏“杰出”的电影艺术家及电影作品,同样,萨杜尔也会以此标准去批评、质疑电影史上一些电影人及作品,显示出“萨本”电影史编撰的个人倾向性。
对于法国电影人,“萨本”质疑了两位元老级的电影导演,一位是卢米埃尔,“卢米埃尔和他的摄影师对电影的贡献虽然很大,可是停留在某种技术水平上的卢米埃尔的现实主义却没能给予电影以它所应当具备的主要艺术手法。”[11]这虽不是批评,但是出于艺术的衡量标准,萨杜尔认为卢米埃尔的电影贡献只在技术。对于初创时期的电影来说,从艺术上进行苛求,难免过于牵强。另一位是梅里爱,萨杜尔对他态度也很谨慎,“梅里爱利用特技,经常是使人感到惊奇。它本身成了一个目的,而不是一种表现的手段。”[12]
“萨本”质疑的两位早期美国电影人是爱迪生与埃德温·S·鲍特。“萨本”对爱迪生争取“专利权战争”的史实书写,充满了嘲讽。“爱迪生对于这种翻印行为毫不感到羞耻,他认为这是收回自己的财产。”[13]对于美国早期的导演埃德温·S·鲍特,“萨本”评价其作品:“他的《一个美国消防员的生活》,实际上是一部很幼稚的拙劣作品,很可能是抄袭威廉逊的一部影片,而威廉逊本人则有模仿了很久以前路易·卢米埃尔的一部作品。”[14]这里否定鲍特,是因为萨杜尔觉得他只会受人影响,缺乏艺术家的个性。
四、“萨本”电影史的地域倾向性
“萨本”作为世界电影史巨著,记录了近五十多个国家的电影发展历史。但是,在电影地域梳理方面,并非平均用力,呈现较为明显的地域倾向性,具体体现在:对法国电影史记录详细而全面、对美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持反对态度、对苏联电影持肯定态度、为亚非拉第三世界电影积极发声。
(一)详细而全面的法国电影史
“萨本”对法国电影史的梳理非常详细,呈现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60年代法国“新浪潮”电影之间法国电影发展的全貌。法国电影史散布在“萨本”电影史的第二章《卢米埃尔和梅里爱》、第三章《布莱顿学派和百代的创业》、第五章《法国与艺术影片(1908-1914)》、第九章《法国的印象派》、第十一章《法国和世界的先锋派电影》、第十五章《法国的诗意现实主义》、第二十七章《新技术与新电影》,共有七章涉及到法国电影史料,占全书体量近30%。
作为法国人,萨杜尔对本国电影史料的占有一定会多过其他国家,这是无可厚非的。同时,法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中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895年卢米埃尔放映影片开始,电影与法国的历史渊源就已奠定。作为与好莱坞电影相区别,承载着艺术传统的法国电影,从印象派、先锋派、诗意现实主义,再到法国“新浪潮”运动,法国电影对电影艺术的发展与成熟、变革与创新,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每个电影史学家在编撰世界电影史,尤其是艺术电影史时,都必须浓墨重彩的所在。
但是,“萨本”对法国电影史的梳理仍有两处遗憾:首先,由于时代所限,法国电影近代历史,尤其是法国新浪潮运动的史料整理与评析较少。只在最后一章简单提及,没有具体展开,这是遗憾之一。其次,“萨本”电影史的陈述表达基本客观,但是仍时不时出现对法国电影潜在的偏袒。例如,在第十二章《好莱坞的建立》中,提及在好莱坞发展的外国电影人,萨杜尔有如此表述:“除了英国人卓别林之外,只有法国人在美国电影中占有地位。”[15]即便是客观史实,萨杜尔的法国之心仍是清晰可见。所以说,“萨本”对法国电影有抬高与偏袒之嫌,这是遗憾之二。
(二)作为假想敌的美国好莱坞电影
基于萨杜尔的社会身份、阶级立场和政治信仰,萨杜尔反对美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对好莱坞的文化霸权。“萨本”电影史就是要联合起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一起对抗好莱坞。所以,“萨本”电影史是一部第二、三世界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竞争与对抗的历史,又是一部艺术家与艺术创作对抗好莱坞为主导的制片厂体制的历史。“萨本”在做历史阐释与分析之时,会有意无意把好莱坞当作假想敌进行比较与评析,具体表现如下:
第十二章《好莱坞的建立》描述了第一次世纪大战之后好莱坞发展的重要十年。这是美国电影征服全世界的兴盛时期,也是好莱坞建立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自格里菲斯失势之后,金融资本家所重视的不是导演,而是电影明星。后者成了制片公司的一种工具或商标。从这时期,影片的真正主人是制片人。”[16]萨杜尔对好莱坞“制片人”制度的唯利润论进行了批评。对好莱坞海斯的“伦理”法典也加以嘲讽:“把电影变成了颂扬美国生活方式及其主要工业产品的工具。”[17]在第十四章《美国电影十五年》中,也是好莱坞电影发展的第二黄金期。萨杜尔揭露与挖掘好莱坞制度的根本缺陷:“在金融巨头们的命令之下,好莱坞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制造腊肠的机器’,这一机器无论是对杰出的题材或者对最突出的个性,一概都无情地加以扼杀。”[18]将好莱坞电影的制片体系比喻成“制造腊肠的机器”,其轻蔑态度溢满纸张。萨杜尔对好莱坞经典电影《飘》与《公民凯恩》的评述都不很高。
“萨本”从反对好莱坞电影霸权的立场出发,使电影史的书写产生明确的倾向,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反霸权的霸权。一种声音压倒另一种声音,抬高第二世界电影,刻意压低好莱坞的电影影响和地位。对第三世界的关注也仅是着眼于第三世界对好莱坞的对抗。对于好莱坞的影响,萨杜尔只看到消极的一面,没有看到好莱坞的引进给世界各国电影业带来的文化标准和产业刺激。“萨本”以政治标准衡量好莱坞商业历史,通过与第二、三世界的对立性比较而建构“好莱坞电影”的形象,导致了读者对好莱坞的误解、扭曲和简单化,对好莱坞电影的评析缺乏公允与客观性,这是“萨本”在地域电影梳理中最大的遗憾。
(三)赞誉有加的苏联电影
因为萨杜尔是一位苏维埃拥护者,“萨本”对苏联电影往往赞誉有加。全书共有四章(第十章、第十六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七章)谈及到苏联电影,所占比重仅次法国、美国电影,具体如下:
在第十章《苏联电影的勃兴》,“萨本”记录了苏联电影的“四位大师”(维尔托夫、爱森斯坦、普多夫金、杜甫仁科)的作品及创作情况。在本章结尾处,萨杜尔表明了之所以衷情苏联电影的原因:“从1919年电影事业国有化的法令颁布以后,电影在苏联已不再是一种金融投机的工具,生产影片的目的也不再是为投下的资金增值利润了。电影由此在本质上成为一种文化的工具、一种‘真正民主的极大众化的艺术’(普多夫金),为千百万观众表达出他们的思想、感情、愿望和意志。苏联电影创造者从最初时期起就认识到他们是‘灵魂的工程师’。”[19]萨杜尔之所以衷情于苏联电影,是因为苏联电影模式反商业化、反好莱坞电影。但是,萨杜尔没有认识到这种模式中愈加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当然这一时期苏联电影的艺术程度的确也很高。
第十六章《苏联电影的新高涨》,这一阶段的苏联电影做了一定调整,萨杜尔继续支持肯定:“苏联这种明显的对形式追求的轻视,并不意味着在艺术方面的退化。……在电影方面,形式的简化是和影片内容的丰富并行不悖的。苏联电影追求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0]萨杜尔对此阶段苏联电影作品的评价,例如《夏伯阳》:“标志着一个堪与苏联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相比拟的新兴盛时代的开端。”[21]《夏伯阳》中“英雄”颂歌模式已然形成,政治意识形态明显加重,但是萨杜尔仍是高亢的赞誉,缺乏冷静与客观的分析。
(四)弥足珍贵的亚非拉电影
上世纪50-60年代法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殖民地危机,这场危机(以阿尔及利亚为代表)的最终结果是法国失去了大片殖民地而获得了关于“民族”“独立”的自觉意识,促使文化界重新认识世界文化的“版图”和“格局”,因此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电影的新气象自然会受到“萨本”的关注。萨本用了四个独立的章节(第二十三章拉丁美洲、第二十四章远东的电影、第二十五章印度和亚洲的电影、第二十六章阿拉伯世界和黑非洲的电影)来检视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发展全貌,以前几乎没有电影史学家如此完整、系统地对西方以外国家的电影历史发展进行学理化的梳理和叙述。对于亚非拉地区电影的全面书写,这在电影史的书写中还是第一次,体现了萨杜尔对第三世界电影的重视程度,这些电影史实的梳理在世界电影史上弥足珍贵。
对于“亚非拉”电影的整理与评述,以“中国电影”为例进行说明。“萨本”概述了从19世纪初到50年代中国电影的发展情况,同时涉及到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的创作。中国电影各个时期代表性的电影人及电影作品均在“萨本”描述之中,虽然中国电影所占篇幅简短,但却相当精准,时间、地域跨度广泛而恰当。另外,值得一提是萨杜尔对中国电影评析的口吻,例如:“蔡楚生与郑君里合作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是对蒋介石统治的有力控诉。”[22]很明显,萨杜尔对中国电影的评述在意识形态上明显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站在一起,这是与苏联情怀一脉相承的阶级立场。“年轻的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使人回想起苏联初期影片那种蓬勃的生气。它受苏联影片的熏陶,也受游击区电影的经验以及同国民党半合法斗争的经验的影响,最后它还受最古老而仍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的影响。”[23]萨杜尔对中国电影的传统分析,较为准确。
虽然“萨本”无意中过多注意了亚非拉国家及地区对好莱坞对抗的部分,但是对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电影的关注,对电影民族特色的强调,仍是“萨本”电影史最有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所在。“来自亚洲的一系列新发现已经为人所知,人们对拉丁美洲寄予的希望也正在实现,而非洲则正在觉醒。在50个国家里,民族和人民正在成为日益增多的影片的素材,而劳动阶级——电影的主要观众——也给予这些影片以影响。”[24]
结语
综上所述,萨杜尔编撰《世界电影史》存在着明显的个人倾向性。作者的现实身份与学术背景让他站在反对电影霸权的立场,用一种充满了学术激情的态度进行电影史写作。电影史在“萨本”中不仅仅是一部艺术的发展史,更承载了作者寄予其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宣传工具的重任。“萨杜尔像一位复仇者,他作为法官站在好莱坞的霸权与好莱坞的竞争者之间,为同好莱坞竞争者呐喊助威。”[25]“萨本”的偏私必然会对其电影史研究与判断产生一定影响,所以说“萨本”是一部个人化的历史书写样式。另外,读者们乐于看到萨杜尔以情绪化的笔触将自己的偏见传达出来。“萨本”在文本中充满情感色彩的讲述语言让读者阅读起来感到易于接受,把原本枯燥的电影史描绘得异常生动。“萨本”承认自己的偏见,他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激情让他的偏见公开化,他并没有声称自己是一位神或者法官。因为他的历史文本是作为普通畅销书而为大众写作的大众读物,这是认识“萨本”电影史的关键所在。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M].徐昭,胡承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4、45、151、309、317、553、163-164、83-85、143、150、20、25、33、67、257、247、249、304、228、355、362、564、565、648.
[25]李靖.乔治·萨杜尔与大卫·波德维尔电影史比较——电影史的史学个案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