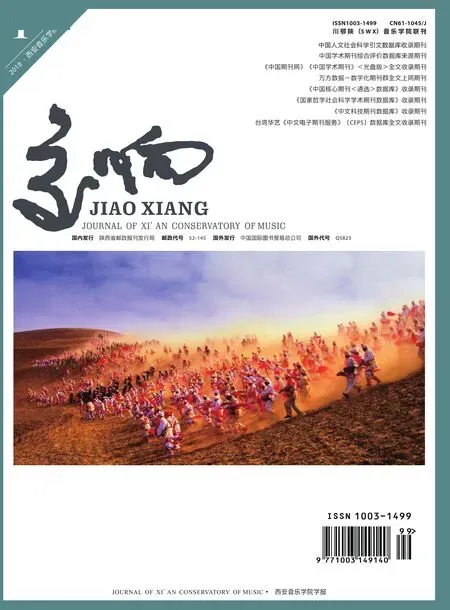清代乐论的美学追求及诗乐关系之解体
●韩 伟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5)
清代是中国学术的最后鼎盛时期,梁启超曾将之与西方文艺复兴等而视之,这一说法虽有过誉之嫌,但从中不难见出清代学术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概而言之,学术和思想是支撑清代理性传统的两极,同时,两者亦互为表里,学术方面的成就已无需多言,思想层面的贡献则需要深入挖掘。清代乐论是清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构筑清代思想大厦的重要基石,对清代乐论及其与文学关系的讨论,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观照中国古代思想史、美学史的流变状态;另一方面则可以更好地洞察“乐与诗”这对姊妹艺术,在古代思想终结期的最终关系以及理论层面的互渗是否依然存在。
“淡和”与宋学
清代的文艺思想总体上以复古为主,就音乐与文学而言,这种复古是在各自领域分开进行的,音乐与文学的天然一体性不再成为文学创作和思想言说的指导。所以在清代,音乐美学与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在乐论领域,讨论的核心问题仍囿于复古还是革新的层面,并未表现出多少新意,反而更为僵化、固定。就复古层面而言,较突出的代表是汪烜,又名汪绂,在其所著的《乐经律吕通解》中“淡和”是最主要的指导原则。在《乐经律吕通解·乐记或问》中,他认为《乐记》的主旨可以用“慎所感”三字涵盖,《乐记》承认人内心的种种情感是“感于物而动”的结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直言“《乐记》大旨不外‘慎所感’三字之意”,并将之与宋代周敦颐的“淡和”理论进行了嫁接,称:“先王知声色之迭感为无穷也,于是定为淡和中正之声容,以养人之耳目而感其心,使咏歌舞蹈之,以与之俱化,而妖淫愁怨之音则放之使不得接焉,是先王慎感之道也。”[1](P32上)
汪烜撰作《乐经律吕通解》的目的是“补《乐经》之阙”,因此在遵循《乐记》固有思想的基础上,亦借助宋代理学思想对之进行充实、补缺,在他看来“先儒中惟以周、程、张、朱之说为主”[2](P203下),《清史稿·儒林传》亦称其学“以宋五子之学为归”[3](P13152)。由此可见,其对周敦颐思想的接受是不争的事实,在乐论思想层面,周敦颐在《通书·乐》中提出的“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思想便被汪烜移植到了自己的思想之中,甚至在《乐经律吕通解》卷五中将《通书·乐上》的内容全文引用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对周敦颐的“淡和”概念,汪烜是直接使用的,当论及郑卫之音是否合律时,他说:“乐贵淡和,八风从律,其声便自淡和。不和固不是正乐,不淡亦不是正乐。《周礼》‘禁其淫、过、凶、慢’,曰慢者,举甚而言,不是不好听,却是忒好听,忒好听而无分际,亦是不成声。”[1](P37上)可以看出,他将“淡和”作为衡量理想乐音的标准,即使郑卫之音音调如何悦耳动听,但若不淡、不和,也是被否定的对象。这种僵化的文艺思想便导致了汪烜注定无法成为清代一流的学问家、艺术家,充其量也仅是清代学术浪潮中汉学与宋学争锋过程的一抹微弱的浪花。
然而,这抹浪花的形成绝不是无缘而孤立的,正相反,它恰是众多暗流激荡、碰撞的缩影和产物。早在清初王夫之的乐论思想中就已经表现出对“淡和”的推崇,在其《礼记章句》中有一段对《乐记·魏文侯》篇的解释性文字,《乐记》原文中当魏文侯以“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为由向子夏请教时,子夏有一段将古乐与新声进行对比的话,王夫之对这段话进行解释时说:“金、鼓、拊、雅、其音皆浊,以之节乐则乐平而不激也。‘语’,谓以乐理论德行。‘道古’,即乐以道先王修齐治平之功德。乐声冲淡,舞容简肃,故视听有余而可以酬问也。”[4](P937)很显然,“乐声冲淡”、“舞容简肃”是其对古乐的认识。王夫之不仅是清代学术的开创者,也是清代学术中追摹宋学风气的奠基人,其生活于明清之际,一方面受到心学余续之影响,以“宗濂洛正学”为家族荣耀;另一方面又身逢乱世,有易代之悲,这导致他的学术思想中既带有宋明理学的基因,又不乏经世致用的现实观照。这些方面,在其乐论思想中便有所投射,他认为乐的本体是“太和之气”,而“太和之气”是天地之气、阴阳之气和合的产物,这种观点很显然带有周敦颐、张载理学思想的影子。“太和之气”在人身上的具体化便产生了“情”,而情就是音乐的产生基础,所以他说“太和之气凝之于人则发见于情,而乐由是以兴”,又“心和而后乐以作”,这种观点以及论证逻辑,实际上一方面继承了《乐记》“乐由中出”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将之纳入了理学的框架之下。进而,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心和”的外在表现就是“声和”,即“乐生于心之动机,动而正则声和,动而邪则声淫,各象其所乐也”[4](P929)。因此,在王夫之的乐论思想中便构成了“太和”、“心和”、“声和”之间较完善的论证体系,结合上文谈到的“乐声冲淡”观点,便可以认为他眼中的“声和”的具体表现就是冲淡之音,这种声音既是上古音乐的理想状态,也符合人性本静的理学要求。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类似,经历了明清易代,且对清初的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他们的一些主张都以文化基因的潜在形式,影响着整个明代文艺走向。
按此逻辑,可以说上文汪烜对“淡和”的强调是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的,王夫之对宋学的推崇,不仅为汪烜提供了参考,亦对清代中后期的朴学产生不小影响。汪烜主要生活于雍正、乾隆朝,是徽派朴学的代表人物。一般认为,徽派朴学以汉学为取法对象,但实际情况则并非如此,以徽州朴学的奠基者江永为例,其宗承汉学的形象更多是被徽州后学戴震等人建构起来的,戴震尝言:“盖先生之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5](P181)将之划入郑玄一脉。而实际上,江永本人却对朱子之学情有独钟,钱穆先生对此进行过考证,并最终认为“大抵江氏学风,远承朱子格物遗教则断可识也”[6](P340)。结合上文对汪烜的分析,可知钱穆先生对徽州朴学的认识当是准确的。正是基于徽派朴学的理学根基,才使得汪烜的乐论思想中带有周敦颐等人的影子,这种倾向除了在直接注释《乐记》的时候有所体现之外,亦出现于其他方面,比如《〈立雪斋琴谱〉小引》中称:“其间篇什,酌以淡和,或怡然自适,或凄以哀思,或远杳清冥,或和平广大,而要必以祇以庸,约乎中正。如或音调靡漫凶过,稍乖和淡者,皆置不录。”[7](P414)这是汪烜对琴音的认识,“淡和”或“和淡”是其评价琴音的主要标准。
清代著名的经学家、音韵学家江永在其《律吕新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故古乐难复,亦无容强复,但当于今乐中去其粗厉高急、繁促淫荡诸声,节奏纡徐,曲调和雅,稍近乎周子之所谓淡者焉,则所以欢畅神人,移风易俗者在此矣。若不察乎流变之理,而欲高言复古,是犹以人心不安之礼,强人以必行也,岂所谓知时识势者哉。”[8](P545)这段话具有一定的纲领性意义,认为没有必要执着于复兴古乐,只要“近乎周子之所谓淡者”,今乐亦是古乐。因此,“淡”就成了其沟通古今的纽带,是主宰古今音声的“流变之理”。可以说,江永总的指导原则是要实现对“淡”的皈依,即是说只要能实现声音的淡和,便没必要僵化地固守古乐、古器、古度量衡,因此在江永的理论中已经表现出古与今、雅与俗、义理与考证之间的统一了。考据的目的在解经,解经的宗旨在致用,这一过程中对义理的把握是关键,古今差异只是外在形式的差异,义理则是贯穿古今的内核。由此可见,江永理论中带有汉学、宋学的双重特征,前者是手段,后者为目的,无怪乎众多学者常常对江永的学术背景问题游移不定。进一步言之,江永的这种学术倾向与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派的学术旨趣是有所交叉的,以江永为代表的徽州朴学与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文派,两者同出安徽,在思想倾向上相互浸染应该是非常可能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宋儒以“淡和”为主的审美观在清代仍具有较大影响,乃至学术领域的朴学以及与之存在密切联系的桐城文派都难以与之决然脱离干系。
“尚实”与美学
客观而言,清代乐论异常复杂,与前代乐论相比,没有较为清晰的脉络,甚至略显芜杂。这与明代以来市民文艺的勃兴,以及启蒙思潮的涌入不无关系。总体来看,清代乐论表现出了明显的崇实、尚用倾向,不再过分执着于前代的理论标准和道德准则,虽然王夫之、江永、汪烜等人的理论中仍带有一定的保守成分,但他们仅代表清代乐论的一维,更多的时候,清代学者开始以较客观的态度看待音乐,并形成各自的理论。
如上文所述,江永的理论虽然仍带有理学的影子,但外在表现上则是通变而尚实的,除了江永之外,这一潮流中还包括毛奇龄、徐大椿、徐养沅、李塨等人。毛奇龄是清初重要的经学家和音韵学家,也是明清之际引领学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其对程朱理学进行较尖锐的批判,在《四书改错》一书中将矛头直指朱熹,并以此为突破口对宋学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故全祖望称其“所最切齿者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齿者为朱子”[9](P986)。与这种总体倾向相一致,其所著《竟山乐论》便带有破古立新的特征,据四库馆臣考证,该书以明人《唐乐笛色谱》为依据,其中不乏对司马迁《史记·律书》、蔡元定《律吕新书》的攻击性言论。[10](P510)我们知道,司马迁《律书》作为对汉代以前律学观点的总结,是带有明显的神秘性色彩的,而蔡元定则是朱熹弟子,其书带有浓厚的理学气息。毛奇龄对两者都不完全满意,所以在《竟山乐录》中才另辟蹊径。在毛奇龄看来,汉代以后的乐论普遍带有神秘性,他说:
自汉后论乐,不解求之声,而纷纶错出,人各为说,而乐遂以亡。如乐之有五声,亦言其声有五耳;其名曰宫曰商,亦就其声之不同而强名之作表识耳。自说者推原元本,妄求繇历,溷元太乙,必溯其声之所自,名之所创,而至于何声为宫,何调为商;仍不之解,至有分配五行,旁参五事,间合五情、五气、五时、五土、五位、五色,神奇窈眇,聆其说非不卓然可听,而究之与声律之事绝不相关,此何为也?故徐仲山曰:吾遍观乐书,而深恨乐亡之有由也。[11](P293下)
在毛奇龄看来,汉代以后以阴阳五行比附五声的诸种做法都是“与声律之事绝不相关”的,而这些往往是清代之前乐书的主要内容和指导思想,所以他不无极端地称“乐书逾备,则乐逾不明”。与此同时,他在该书中还传达了另外三层意思,一是认为度量衡是“亡乐之具”。这种观点与上文提到的江永的观点颇为相似,时过境迁,如果一味迷信前代尺寸而无视现实,则音乐必然脱离实际,所以他将之称为“欺人之学,不足道也”;二是认为“乐书不是乐”。音乐是鲜活的艺术存在,其生命在于节奏、旋律,但乐书往往只能记载乐理,而其所载“非乐声也”且“乐书不言声”,所以应该科学的看待乐书;三是辩证地看待俗乐、番乐、雅乐的地位。其衡量乐音优劣的标准是是否为自然“人声”,因为音乐的根本是人,“重人声,人声苟善,虽俗乐、番乐,在所必取”,以此为出发点,他不主张贵雅贱俗,甚至认为“番乐难习,俗乐稍易,最下不足学,则雅乐矣”。
整体而言,毛奇龄试图传达的是其“勿过尊古,勿过贱今”的文艺主张,这一方面是其否定宋学、追摹汉学的学术倾向的展示;另一方面也无形中为“尚实”学风、文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与毛奇龄的观点一脉相承,徐大椿在《乐府传声·源流》中称:“可变者腔板也,不可变者口法与宫调也。苟口法宫调得其真,虽今乐犹古乐也。”徐大椿生活于康熙至乾隆年间,其人精通音律,经学方面以注解《易经》成就最高,学术主张虽尚古法,但更勇于疑古,这一点在其《乐府传声》中便有所体现。这段引文中,“口法”是指唱曲之方法,即气息运用及起承转合之法,“宫调”指南曲、北曲中固有之曲调。只要两者能够符合规则,那么“今乐犹古乐”。
与毛奇龄、徐大椿相类似的另一个人物是徐养沅,他主要生活在乾隆朝,著有《律吕臆说》、《管色考》等论乐典籍,前书中较具代表性的成就是客观地对雅乐、俗乐以及两者关系的讨论,在《律吕臆说·雅乐论》的开篇他就指出“夫雅乐者,非于俗乐之外别有一声节也,就俗乐而去其繁声即为雅音”,对雅乐、俗乐的讨论几乎是老生常谈,但是徐养沅则带有两方面考虑,首先是客观现实,在他看来魏晋以后,真正的雅乐已经不复存在,“三代雅乐不亡于秦而亡于魏晋也”,所谓雅乐仅是后世自己命名的产物,是相对的概念,并非有统一的内涵;其次,否定宋儒空谈律吕的做法。徐养沅认为雅乐的存在基础是黄钟律管,对它的长短,每个朝代都有众多看法,但结果仍莫衷一是,加之理学的参与,又使最终的律准带有政治色彩和神秘气息,所以徐养沅在《管色考》中便直言:
宋儒论乐辄曰高几律,下几律……此皆律学失传,儒生徒骋臆说,毫无真见,故其失如此。……窃意乐固以律为重,然惟三代以上可用,今黍尺难凭,葭灰不验,论乐者只宜理会五声,不必空谈六律。……俗乐虽俗,不失为乐;雅乐虽雅,乃不成乐。是何也?则以俗乐求声,各有师承;雅乐求律,惟凭胸臆故也。[12](P503下-504上)
这段话足以表明徐养沅对待宋儒的态度,在他看来,俗乐不仅有群众基础而且也存在明显师承线索,与之相比,雅乐则往往是某些人主观臆造的产物,更加不合理。由此足见,徐养沅的客观性音乐态度。
其实,至迟在康熙、雍正朝以后我们对音乐的看法,已经开始受到西方音乐理论的影响了,这也是清代乐论客观化潮流的助推因素之一。这一点在李塨的思想中便有所体现。李塨是清代著名的哲学家,其最初受学于大学者颜元,反对程朱理学,崇尚实学,并形成了当时具有广泛影响的颜李学派,对于颜、李学术思想的进步意义,梁启超称“其见识之高,胆量之大,我敢说从古及今未有其比。因为自汉以后二千年所有学术,都被他否认完了”[13](P123)。除此之外,他后来又与毛奇龄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受到了毛奇龄的重视。与毛奇龄的交往过程中,在音乐思想方面受到了深刻影响,毛奇龄曾将所著的《竟山乐录》送给他两部,李塨读罢,对毛奇龄以知音视之。康熙三十八年(1697)冬,两人初次见面,期间毛奇龄又送给李塨自己“所著礼乐经史诸书共二十七种”[14](P1262)。次年,两人再次相会于杭州,李塨继续向毛奇龄请教乐理,并“投受业刺于河右(毛奇龄人称河右先生),以学乐粗就也”[14](P1264),自此之后两人正式确立了师徒关系。事实上,李塨后来无论在经学还是在乐论层面较之毛奇龄都更为精进,影响也更大,其乐论思想除了与毛奇龄保持基本的一致性之外,甚至更加彻底,在其所著的《学乐录》卷三中他说:“天地元音今古中外只此一辙,辞有淫正,腔分雅靡,而音调必无二致。孟子曰‘今乐犹古乐’、‘耳之于声,有同听焉’,诚笃论也。今中华实学陵替,西洋人入呈其历法算法,与先王度数大端皆同,所谓天地一本,人性同然。不知足而为履,必不为蒉者也,乃于乐独谓今古参商,而传习利用之音为夷乐、俗乐,亦大误矣!”[15](P805)这段话表明不仅雅俗差异在其思想中不复存在,夷夏之别也不再是问题,将“西洋人”基于近代数学基础上的律学知识,与“中华实学”同样看待,这种观点表明中国传统乐学已经开始有让位于近代律学的趋势了。
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可以看出清代乐论表现出两种主流倾向,一是“尚淡”,一是“尚实”,前者来源于对宋学的继承,后者则发端于对宋学的否定。表面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而实际上,清代学者对待宋学的态度是相对辩证的,精神上的遵行与学术上的反拨往往是彼此缠绕的。或者说,精神层面对“淡”的推崇更加像一种思想策略,这种策略表面看来承袭宋学而来,实际上则是为本时代的思想建构和学术发展服务的,所以“淡”与“实”是清代思想史、美学史中一体之两面,前者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味道,目的是让思想、理论乃至生活回归平易,后者则是保证达到这一理想的实践措施。由这种错层式的接纳,我们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清代桐城派、阳湖派乃至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性灵说等文艺潮流的此起彼伏的内在原因了。
“诗乐一理”及其解体
下面讨论的问题是,清代乐论是否与文论存在互动?同时,这种互动的表现方式是怎样的?客观而言,清代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总结期,诗与乐、文与乐的关系已经变得微乎其微,诗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文字艺术,歌诗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文章更是多以义理、考据为手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诗乐合论的尝试就绝对不存在,尽管这种理论声音所起的作用可能不够明显,但仍然有必要对这种情况作一定的梳理。具体而言,清代很多学者仍然秉承“诗乐一理”的认识,并试图通过以乐理类比文理的方式实现乐论对文论的干预。
“诗乐一理”主张的奠基性人物是王夫之。王氏处于明清易代之际,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其思想中既有传统的因素,也不乏革新的成分。其“诗乐一理”思想就带有一定的传统色彩,在《张子正蒙注·乐器篇》中他说“此篇释《诗》、《书》之义。其说《诗》而先之以乐,诗与乐相为体用者也”,又说“正《雅》直言功德,变《雅》正言得失,异于《风》之隐谲,故谓之《雅》,与乐器之雅同义。即此以明《诗》、《乐》之理一”[16](P280)。在王夫之看来,诗与乐都是人情感外化的产物,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而且音乐之律调与诗歌之声律本质上是一致的。除此之外,两者在移风易俗的外在功能上也是统一的,于是他进一步指出:“声音之动,治乱之征,……古之教士也以乐,今之教士也以文。文有咏叹淫泆以宣道蕴而动物者,乐之类也。”[17](P547-548)这段话表明王夫之仍然执着地坚信“乐与政通”,将国家丧乱与亡国之音放在一起来讨论,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有助于教化和风俗的文学作品,也属于“乐之类”。由以上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夫之无论在音乐本体论角度,还是在功能论角度都没有对传统乐论有所超越,也更加没有脱离宋学的论证窠臼,正是在这种逻辑体系之下,他进而将“淡和”之美重新推向了前台。由于其主张“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序》)、“诗与乐相为表里”(《读四书大全说》),所以在其理论体系中乐论必然影响文论,这也就构成了他著名的“诗乐一理”观念。
王夫之之后,对于“诗乐一理”,学者们更多的时候是将之作为中国文艺的一种原初形态和理论传统进行认知的,而并非是针对现实而发的理论倡导。学者们即使承认“诗乐一理”,但面对音乐与文学实际,也不再过多宣扬这种观点了,反而更多地采取了理论比附的方式。乐理与文理的相互比附,首先表现在音乐领域。兹节录数例:
乐之有五音,犹律诗之有四声;乐之有十二律,犹诗之有八病。不知四声不能为诗,不知八病则诗不工;不知五音不能成乐,不知十二律则乐不雅。(徐养沅《律吕臆说·俗乐论二》)
弹琴如作文,右弹如实字,左手如虚字。文章中之实字,亦有轻有重,有正有侧,有宾有主,有详有略。(蒋文勋《琴学粹言·右手纪要》)
乐曲以音传神,犹之诗文以字明其意义也。(祝凤喈《与古斋琴谱、补义·制琴曲要略》)
夫神情之足与不足者,如作文之练字练句,其字之义同,而其字音之平仄重轻,较有强弱,而有胜宜,收音如之。用调,犹之练句也。(祝凤喈《与古斋琴谱、补义·乐奏明调收音起接传神说》)
这几则材料中,第一则是从声调、律吕角度将音乐与诗歌进行类比的,音乐中的五音、十二律与诗歌中的四声、八病相比附,四声为作诗之本,五音为音乐之本,八病为作诗之规则,十二律为决定音乐雅俗的标准。徐养沅的这种类比方式,很显然是基于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传统,以及永明声律论中格律问题与音乐中音律问题的相通性的基础之上的。第二则材料,是从虚实结合的行文角度展开的。文章写作需要注意虚实配合、轻重适当、详略有序,弹琴某种程度上是以音乐的形式在叙述情节、表达感情,两者在道理上是相通的。第三、第四则材料同出《与古斋琴谱》,该书名为琴谱,实为琴论专著。两则材料中第一条讨论“传神”问题,“传神写照”本源自绘画领域,在魏晋时期被广泛运用于人物品评,后来逐渐向文学领域渗透。诗文传神主要依靠字词乃至句法的灵动,与此同理,音乐之传神也需端赖音符的灵动跳跃。第二条材料可与第一条互相参照,音乐领域中音符和调式的运用如同文学中的炼字、炼句,表达相同的意义,因字句的精炼程度不同,会在形式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美感,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音乐。以上分析可以纠正我们一贯的观念,即总是站在乐论影响文论的角度看待问题,实际情况则并非如此,很多时候音乐领域也会从文学领域吸收养分,从而促进音乐的表达。因此可以说,乐理与文理的关系并非仅停留在“乐”影响“文”的一维模式之下,反之亦然。但是,这绝不是说两种模式是平分秋色的,客观来讲,两者之间的关系仍主要体现在“乐”对“文”的影响。下面将具体讨论之。
以乐理比附“文章之理”是清人借鉴音乐现象、音乐理论的第一种方式。在义理层面探索文章与音乐关系,最为典型者是刘大櫆。作为桐城文派的中坚力量,他十分重视文章的节奏,称:“文章最要节奏;譬之管弦繁奏中,必有希声窈渺处。”[18](P5)很显然,他以音乐的节奏变化况喻文章的节奏变化,在他看来节奏的根本是音节,这里的音节并非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音节,而是由字、句甚至篇章构成的声音之节奏,所谓“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刘大櫆的理论主张与同为桐城派的方苞和姚鼐不同,方苞论文以“义法”为主,“义法”虽兼具内在义理层面和外在形式层面,但其理论仍不免偏于扬道,与之相比,刘大櫆更推崇“神气”,这一概念则偏于“文”的层面,正是由于刘大櫆的中介作用,姚鼐才提出了著名的“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桐城纲领。可以说,姚鼐对“辞章”的重视,与刘大櫆的神气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那么,在刘大櫆的理论中“神气”与“音节”是什么关系呢?首先,他将“神气”看成是行文之根本,称“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其次,他又将音节看成是“神气”的实现方式和显现方式,他说:“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歌而咏之,神气出矣。”[18](P6)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构成了“音节—神气—文章”的内在理论线索,音节是刘大櫆理论中最为基础的因素。
如果继续推演就会发现,刘大櫆眼中具有理想特点的“音节”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金石之声。在其《论文偶记》一文中他进一步总结称:“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18](P12)此处进一步证明刘大櫆的神气观是与音节相关的,其试图通过音节来实现神气,而音节的最高层次便是自然铿锵的金石之声。与刘大櫆的这种观点存在因袭关系的是姚鼐,他的诗文主张较早期的方苞、刘大櫆更加抽象,在《答翁学士书》中他说:“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采色之华。故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19](P93-94)这里他强调“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才有节奏之美,其理论的抽象性在这里表露无遗,在刘大櫆的体系中,音节是神气的表现途径,先有音节之美才有神气之体现。但是在姚鼐的理论中,则恰好相反,主观之意与客观抽象的气相互结合,产生文辞,进而才有声音、节奏的规则。在《复鲁絜非书》中,姚鼐将“气”又分成了阴阳二气,称“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19](P102),紧接着姚鼐用音乐比附文学,认为阴阳失衡必然带来刚柔失范,进而优劣之文相继产生,其道理如同五声、十二律的配合情况必然逃不过高明欣赏者的耳朵一样。如此看来,姚鼐在对“气”与“意”的重视方面,当受到了刘大櫆“神气”思想的影响,但在讨论它们与文学、音乐的关系方面则与后者有所差异,表现出了自身的独特性。
相比于用乐理比附文理,清人更多时候是以乐理比附“诗歌之理”,这种现象更具普遍性。清代的诗歌理论到了乾嘉时期趋于成熟,其标志是翁方纲“肌理说”的出现。将“肌理说”目为清代诗论成熟的标志,绝不是说它已经无懈可击,而是说在翁方纲的理论中体现了对诸种诗学主张的综合和反思。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都对翁方纲有所影响,加之这一时期的朴学风尚,以及桐城派的古文理论,这些都是翁方纲“肌理说”产生的现实土壤。针对“神韵说”,他说“今人误执神韵,似涉空言”(《神韵论上》)认为“神韵”有凌虚蹈空的弊端,因此其诗论否定唐诗、明诗的无所依傍,而推尊宋诗的细密,以苏黄为取法对象。在他看来,“肌理”既是“义理”更是“文理”,而“文理”恰与格调和音声相关。在其《复初斋文集》中专列《格调论》上、下讨论格调问题,下面一段需要注意:
诗之坏于格调也,自明李、何辈误之也。李、何、王、李之徒泥于格调而伪体出焉,非格调之病也,泥格调者病之也。夫诗岂有不具格调者哉!《记》曰“变成方,谓之音”,方者音之应节也,其节即格调也。又曰“声成文,谓之音”,文者音之成章也,其章即格调也。是故噍杀、啴缓、直廉、和柔之别,由此出焉。是则格调云者,非一家所能概,非一时一代所能专也。古之为诗者,皆具格调,皆不讲格调。格调非可口讲而笔授也。……于是上下古今,只有一格调,而无递变递承之格调矣。至于渔洋,变格调曰神韵,其实即格调耳。而不欲复言格调者,渔洋不敢议李、何之失,又唯恐后人以李、何之名归之,是以变而言神韵,则不比讲格调者之滋弊矣。然而又虑后人执神韵为是,格调为非,则又不知格调本非误,而全坏于李、何辈之泥格调者误之,故不得以不论。[20](P421)
这段话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为格调说正名,认为格调本身并无问题,只是经过明代前、后七子的错误理解和施用,才使其变得僵化。“格调”是古往今来为诗者都应遵奉的规则,甚至王士祯口中的“神韵”亦是“格调”之变体;二是,以音乐之格调比附诗歌之格调,从而丰富“格调说”的内涵。认为对“格调”的推崇始于古代乐论,《乐记》所谓的“变成方”、“声成文”都是针对格调而言的,音乐中的“方”与“文”就是最初的“节”与“章”的划分和安排,两者不同的组合方式,便会体现出不同格调气质。因此,翁方纲眼中的“格调”偏重于指音声在流淌过程中不同的节点划分以及段落安排,它们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作家特色,而其所推崇的“肌理”,某种程度上也是格调的一种。
事实上,在翁方纲之前就已经有人从音乐和格调的角度对诗歌之美进行规定了,这个人就是叶燮。叶燮诗论带有纠正明代前、后七子乃至公安派的特点,客观层面推崇理、事、情三方面,主观层面讲究才、胆、识、力四方面的主体能力。在其《原诗·外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诗家之规则不一端;而曰体格、曰声调,恒为先务,论诗者所谓总持门也。……言乎声调:声则宫商叶韵,调则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吕,铿锵乎听闻也。请以今时俗乐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声调,先研精于平仄阴阳。其吐音也,分唇鼻齿齶开闭撮抵诸法,而曼以笙箫,严以鼙鼓,节以头腰截板,所争在渺忽之间。其于声调,可谓至矣。然必须其人之发于喉、吐于口之音以为之质,然后其声绕梁,其调遏云,乃为美也。使其发于喉者哑然,出于口者飒然,高之则如蝉,抑之则如蚓,吞吐如振车之铎,收纳如鸣窌之牛;而按其律吕,则于平仄阴阳唇鼻齿齶开闭撮抵诸法,毫无一爽,曲终而无几微愧色。其声调是也,而声调之所丽焉以为传者,则非也。则徒恃声调以为美,可乎?[21](P45-46)
在这段话中,叶燮将体格和声调看成是诗家应遵守之规则,实际上这也是他诗美理想的重要方面,其中体现了其诗论的唯物特征。“体格”之“体”相当于制度、规则,“格”相当于形体、特征。相较于“体”,“格”是彰显个性和灵动性的方面,与后来翁方纲的“格调”更为接近。这段话中,一方面,叶燮将声调看成是诗歌创作的重要规则,其与“体格”同样重要。声调的核心内涵是“中乎律吕”,具备铿锵之声。另一方面,在强调声调的同时,亦承认人声的重要性,否则纵使“度曲者”如何进行规定和预设,缺少演唱者喉、口的参与,也体现不出乐曲的美感,所以最终他诘问称“徒恃声调以为美,可乎”?这种对“体格”和“人声”的重视体现出了叶燮理论中一贯的综合性倾向,前者源自明代前、后七子的“格调”理论,后者源自公安、竟陵等诗派的主体化倾向,但两者都无一例外的与音乐美相关①。
遗憾的是,清代除了在戏曲领域表现出音乐与文学的互动之外,其他文学样式中已经很难看到两者的相互影响了。本文所论述的“乐论借用文论”以及“文论借鉴乐论”的情况十分有限,而且客观而言,这种借鉴更多时候往往是一种理论言说策略,或者说更像是一种例证引用,其在总体理论中的权重则微乎其微。理论言说层面如此,创作实践层面则更是如此,清代文学不以诗歌见长,且诗歌的徒诗状态已经根深蒂固,文章领域以桐城古文为其中翘楚,无论早期的方苞、刘大櫆、姚鼐还是稍晚的曾国藩,虽都推崇“辞章”,但却绝无以音乐入文的尝试。就清词而言,早期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派词,后来张惠言、周济等人代表的常州词,或者推尊南宋或者取法风、骚,他们更多将注意点放在风格、词境、语言的锻造层面,对文学性的重视已经淹没了音乐性因素。
综上所述,清代乐论的“尚淡”、“崇实”倾向并未对文论和文学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原因是随着音乐文学传统的消失,音乐与文学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的关系都变得疏离。即使清初王夫之有“诗乐一理”的主张,但这一观点更多是从诗、乐的起源和功能角度表达的,现实性并不强,尽管刘大櫆、翁方纲、叶燮等人都有以乐理比附文理的尝试,但都未真正将乐论的“淡”与“实”灌注于文学理论和实践。所以,可以说清代乐论与文论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乐论中的“淡”与“实”倾向更多是时代思潮的理论映射,即便文论中偶有这种倾向,也是根植于时代精神,乐论的中介作用微乎其微,这是清代乐论与文论关系不同以往之处,同时也预示着中国古代乐论美学潜力的消亡,以及音乐文学实践的终结。
注释:
①前、后七子的格调理论中,“自然之音”是其最核心内涵,这与以往对前、后七子的认识不同,将另有专文论证。
[1]汪烜.乐经律吕通解[M].续修四库全书本[G].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汪烜.理学逢源·例言[M].续修四库全书本[G].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王夫之.礼记章句[M].长沙:岳麓书社,1996.
[5]戴震著;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0.
[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汪烜.《立雪斋琴谱》小引[A].见吴钊等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8]江永.律吕新论[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G].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
[9]全祖望著;朱铸禹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外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1997.
[11]毛奇龄.竟山乐录[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G].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
[12]徐养沅.管色考[M].续修四库全书本(第 115册)[G].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14]冯辰,刘调赞.李恕谷先生年谱[Z].颜李学派文库(第四册)[G].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15]李塨.学乐录[A].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16]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8]刘大櫆.论文偶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9]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文集[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翁方纲.复初斋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G].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1]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