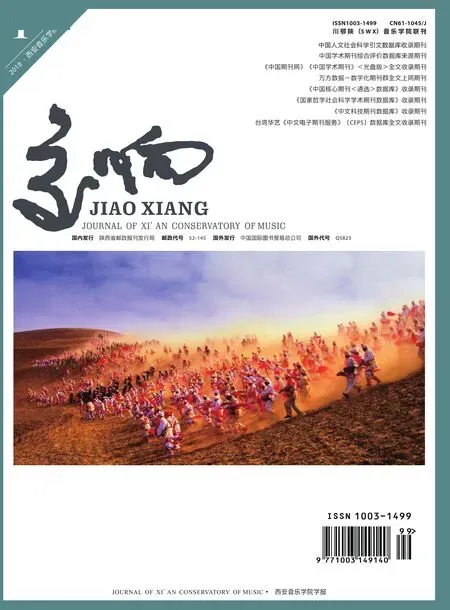中古伎乐与乐伎的二重关系之于音乐发展的历史影响
●夏滟洲
(西安音乐学院“一带一路”音乐文化高等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1)
对中古(西晋至唐末)时期伎乐与乐伎相关问题的研究,系笔者承担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古良贱乐人社会身份的形成与中古伎乐的转型”(项目编号:11BD041)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内容主要涉及中古乐人阶层的形成与完善、乐人与恩主的互动、乐人迁移聚合对音乐文化形成与新变的影响方面。
研究主体由二部分组成。绪论为研究相关的学术准备,针对从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向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的音乐形态转变发生,提出研究主旨,考察当时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特殊群体——以音乐为职业的乐人的历史活动。第一部分是“乐人-制度篇”,历时地阐述了乐人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及乐人存在形态。研究集中论述了中古时期基于乐伎(人)与伎乐的二重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以人为中心的音乐史,分析了从国家层面到新型恩主制的转变中,以乐人为中心的主体作用的发挥,对中古伎乐歌舞走向品类专门化、表演生活化和题材情节化的独立发展过程。第二部分是“伎乐-文化篇”,通过中古时期所用娱乐节目分析、史料挖掘,共时地分析了中古乐人流动迁移与聚合路线,认识中古伎乐演化线索和过程,最终揭示出,从西周时的“金石之乐”向中古时期的“歌舞伎乐”的巨大转变中,音乐本体发展的必然性与乐人主观的创造性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在具体的研究中,笔者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论证材料的运用上,以历史文献、今人成果、考古文博材料的广泛搜集、解读,乃至多重并用。采取社会史、音乐学和历史文化地理等研究方法,建立起历史、音乐、地理三个坐标轴的研究领域,考察音乐文化传播交流并揭示其历时状况,研究中古时期国家音乐制度及乐人社会身份问题,探讨中古音乐文化变迁与伎乐演化过程。围绕伎乐品类与内容和伎乐作品的生产与传播途径,通过阐释中古乐人制度及其完成中国音乐从先秦时期的“金石之乐”向中古时期的“歌舞伎乐”巨大转变的路径,揭示以人—音乐家为中心的中古音乐生活发展历史。归纳起来,有三条明显的线索:
一是从乐伎(“人”)和伎乐(“乐”)的内在关系入手,面对中古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宫廷乐署机构作用下移的外在环境,乐人群体在迁移汇聚、新的恩主制及趣味作用等内在动力激励下,中古时代伎乐发展的历史影响:(一)中国音乐文化内部地域差异缩小,区域音乐文化逐渐整合,南北音乐虽然存在区域性但同一性增强;(二)生存于社会底层的乐人,在整合旧曲和促进新声的传承传播中,重新完善了与中华传统相适应的、系统化的音乐制度,并在文化累积中形成了“华夏正声”的新观念,预示了隋唐音乐新的活力。
二是由于永嘉之乱,从西晋宫廷流出的“洛阳旧乐”,历经:(一)北方各朝宫廷对雅乐的整理创革和胡乐的汇聚,再到北周对雅乐兴置回拨;(二)最受人激赏的清商乐在发展中经南地四朝的建设,成为宫廷音乐的主流。在隋代,中古诸乐汇入长安后,宫廷所做音乐整顿中,“洛阳旧乐”的地位虽然得到强调,并列多部伎,但其“始具宫悬之器,仍杂西凉之曲”[1](P314)[2](P3616)的特点,表明用于教化的雅乐和按儒家礼制整理的祭祀用乐因吸纳俗乐而边界模糊,最终到唐时,雅俗区隔终至清晰。
三是中古时期长期动荡中,(一)中原世俗生活中赏乐之风勃兴,俗乐新声纷呈;(二)内迁的各少数民族加快和汉族融合的步伐,多元文化并置融合汇聚北魏,即使中古以前的文化得到了新的发展,又为隋唐文化的繁荣作了重要准备。在这一背景下,生成了诸如胡乐和新俗乐等具有广泛社会性、娱乐性、消遣性的歌舞娱乐节目。作为中古伎乐演化历程中出现的艺术形式,新俗乐以独立形态、多样风格传世,突出雅俗之分特征和娱乐功能,为中古伎乐向宋以后俗乐转型做出了铺垫。
由上可知,本项目从整体上聚焦于中古乐伎(人)与伎乐的二重关系研究中。这是音乐学研究①和社会史研究都十分关注的内容。就中古乐伎而言,考察这些居于社会底层的人的生存与生活状况,及其在世俗社会、法律层面中的地位获致;对应中古文化活动,分析乐伎音乐活动及其创造成果中蕴涵的伎乐形式与内容。从而建立起一个历史坐标,探寻伎乐与乐伎二者间的内在关系,根据伎乐作品生产源头与传播路径研究伎乐品类、传播方式的形成,考察中古伎乐的演化,意在揭示从“金石之乐”向“歌舞伎乐”的转变中,音乐本体发展的必然性与乐人主观的创造性双重作用。
社会史对人的研究,共时上包括外在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活动方式内容和人的身份地位、消费结构等内在深层次的内容。贱籍乐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在社会生活、职业活动、文化生活乃至政治生活领域进行高层次活动,虽然其自身的诉求难以满足,但其所从事活动的社会性、文化性书写了中古音乐历史的发展轨迹。表面上,中古社会是一个以良贱为标准来区分社会身份等级的社会,从事乐事活动的乐人及其活动的接受者各自有着自己的功能需求,如此致贱籍乐人会形成一种趋于良口的获得性身份。中古历史情境形成前提,是秦汉之后,音乐文化下移逐渐变成一种专门技术,导致擅长音乐之技者——乐工所为本是贱业。魏晋时期由于挣脱了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藩篱,社会思想的解放、城市的发展、时代文化大放异彩,人、人才、人的个性被发现,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开放,带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人性、人权的萌芽与觉醒,还让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底层激发了很大的爆发力和创造性。音乐艺术更为突出地表现了时代的解放,愈加多变、新颖的舞蹈服饰、音乐辞藻、表演形式,使魏晋以来的音乐艺术进入自觉,一种自成系统的、便捷的、规范的模式化思维和音乐创制规律逐渐形成;正是以乐人与恩主为中心的主体作用,及国家层面实施的集中习艺和管理制度(乐户-乐籍制度),中古伎乐开始发生转型,自此开辟了中国音乐历史歌、舞、乐走向品类专门化、表演生活化和题材情节化的独立发展之路,且又能结合在一起或部分组合演奏的新的时代。另一方面,中古统治阶层在加强政权时,通过建立良贱秩序,制定和实行户籍(乐籍)制度,加强控制乐人群体、保障享乐的目的,由是一来,在国家以维护宗法制度和社会等级身份为宗旨的法律规定下,乐人来源得以保证,并在强化乐人世袭制度中,一种预期式的制度又使乐人群体得以累世增长。可见在外在制度规约下,乐人在总结前代、融合南北风格、加上自身的创造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传统音乐形式规范、创作机制、节拍节奏观念的稳态成分,传承千年。
社会史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关注乐人活动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关系,社会变迁中制度对乐人传承传播音乐的制约虽然存在,但并不影响民间乐事活动的生长。历时上,根据乐部聚合与伎乐演化构建出一个历史情境。从音乐地理学角度观察中古乐人流动迁移与聚合路线,分析乐工的逃奔之所,即以城市(都城)为中心进行的音乐文化交流,虽然各怀其技,但都带有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普遍性、同一性。中古诸朝积极加强乐工团体接收与音乐制度建设的做法,使乐人群体能够立足一地按照音乐艺术的一般规律,以一种内在行为的音乐传播方式完成文化传播和技艺传承。这一历史情境中,乐人们汇聚一地,还要受制于区域文化取向、知识背景等人文因素,包括岁时节日文化体系的形成、演艺舞台的固定化、听众结构的分化和音乐作品传播所产生的多种效应,这些都是影响伎乐发展的文化背景,决定着人的接受与转化能力。我们根据音乐的社会性质去探寻音乐的精神内涵,面对生存接受恩主或受命国家的乐事活动,凭借作品展示乐伎个人才华与风格,展示一种职业态度和契约精神,同时让享乐作为一种价值,深深地镶嵌于岁时节日、听众阶层、舞台聚落之中。不同时节、不同聚落中的人们在音乐欣赏活动均会受到该阶层的支配,与其说是娱乐,还不如说是通过娱乐来强化该阶层的趣味和维系该阶层的社会组织。这其间,不论哪个时节、哪一聚落、哪一阶层,不变的是乐人的演释,是喜闻乐见的伎乐。可见,中古伎乐的演化离不开乐人自身组织化、职业化、商业化的技艺创革,他们遵循传统文化秩序,不考虑其他外在的意义,从社会分工角度积极地完成音乐文化的传承,在交汇的城市形成了各具特定文化内涵的类型化特征。
乐伎与伎乐,是中古社会音乐文化的承载者与生成物。伎乐之“伎”,是人与技术的结合,是中国古代艺术赋予人特定的称呼,是东方文化独有的文化现象。不同于“妓”,“伎”代表的是歌舞艺术,从业者需要接受长期专业的乐舞学习、训练,这一类人即乐伎之“伎”,不同于“奴”但近似“奴”,业贱,入贱籍,是特定历史、地理、文化形成的产物,靠技艺生存,虽然可能被主人色艺兼收,但其主要职责是从事歌舞创作与表演。乐伎所形成的社会阶层,初见于北魏的“乐户”。东魏至北齐、北周不仅设立乐籍,还一直继承北魏将罪没之人一律列为乐户的做法。原本是对罪犯的一种惩罚手段,因罪没成为乐家的子弟却促成了伎乐专门化或专业化发展之举。至唐初,将罪没一律入乐户的做法虽有更改,但乐户世袭、永世不能脱贱籍的规定却自此立下,延续到了清朝。中古时期,在国家法律层面,乐伎有预设的身份等级,分良贱,受恩主供养,依附于他人,几乎无人身自由,居于社会底层,相比汉时“富显于世”的乐伎、倡家,有天壤之别。乐户非一般编户齐民,属官管贱民,无放免手续,不得脱籍,不得与其他户籍通婚。除了朝廷偶然放免改为平民之外,很少有乐人能得到普通民户身份。乐人身份的制度化几乎彻底隔绝了乐人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尽管如此,中古乐人创造的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音乐传承关系延续数千年不断,具有突出的历史影响。
国家层面的音乐制度,旨在管理所用诸乐的服务对象及目的,强化宫廷音乐系统的正统性和高贵性。制度背后,是乐人的活动。中古社会的动荡,使乐署机构时存时亡,以致大量音乐沦丧。在乐工的流动和乐部聚合中,“伎乐”正声成为主导,于流亡迁移之中保证了传统音乐在交流中发生新变,俗乐不断更新,胡乐辗转入华,他们的活动轨迹清晰和音乐传承方式独特。不论中古音乐机构如何更名变化,乐人社会身份一贯卑微,境遇恶劣。特别在长期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乐户累世化存在,命运多舛、朝不保夕,生命和尊严常常被践踏,即使因为色艺出众获得一定社会地位但也是“可富难贵”;面对政权林立的时代,一方面雅乐沦亡、礼仪尽失,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前途不明;另一方面乐户还是诸政权争夺的主要对象,当辗转于乱世、颠沛流离的乐人偶有聚集,便将其技艺传承于世,主动地肩负起音乐传播的重任,推动了中古伎乐的传承、发展与演化,开启了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第二次重大转折之路。伎乐类型的兴衰变化从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不同时期统治者的趣味与需求,以及音乐生活与社会现实、政治追求之间的微妙关系。
恩主制是东晋南朝社会用乐的主要方式,旨在满足了恩主享乐之需,体现贵族身份和威仪。随着几次大的战乱中,人口流动加剧,民族交流频繁,乐工们无法获得稳定的政治庇护,不得不寻求新的恩主,只有频繁流动于贵族门阀之间。寄生于恩主堂下,衣食有保障,音乐传播才有经济条件。作为恩主家私产,乐户可以任意处置,交换、买卖、当赌注。家养乐伎,并可与其他贵族攀比;同时也给乐人提供了音乐活动的资金、场地等必要条件,音乐表演中的协作、新的品类借此有了发展。由于恩主的攀比心态,造成了不少乐种如鼓吹的中原化、世俗化进程,根据主人喜好与需求创作的新作品迭出。
魏晋之后,宫廷、贵族和新的恩主以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及其娱乐和享受的需求促进了唐代伎乐的繁荣,折射出乐人伟大的创造性,但其社会地位仍然卑微。在唐代等级分明的社会里,乐人良、贱地位被严格区分。唐律将乐户的义务与待遇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唐代的开放政策不仅乐人之用规模前所未有,不少乐人的活动并非全然受制度化限制,他们可以游走于宫廷与民间之间,为多种场合提供音乐服务。诸官贱民中,乐工地位最高。各类乐人中,雅乐所用乐人地位最高。与南北朝时的恩主制不同,唐代商业文明初兴之时导致新的恩主结构出现,从而使得既往表现为一种契约关系、宗法家族约定的恩主制走向衰落。以乐户为媒介的音乐创作与表演活动,为建立专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行乐体系打下了基础。
中古文化交流发生多元,既在汉族和内迁的少数民族之间,又在宫廷与民间之间,还在南北地域之间,因交流形成的大融合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从敦煌莫高窟壁画所反映的中古时期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及对各窟中与音乐歌舞相关的壁画的分析,不难发现发生在中古时期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存在。敦煌壁画所见南北朝时期伎乐表演不仅规模宏大、用乐奢华、效果辉煌,还反映了中古伎乐雅俗交融的发展趋势。就在宫廷与民间的互动中,由于经济发展、城市繁荣,文化需求,民间文化勃兴,实质在于“学在王宫”的下移。汉室倾倒,诸侯割据,乐师流落于民间,“王宫之乐”失去了稳定的根基。加之儒家失去“官学”的政治支持,学校渐兴,“私乐”、“私学”盛行,宫廷乐师将宫廷音乐体系带到了民间,成为民间俗乐革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发生在规范化的雅乐体系与富于创造性的胡乐、清商乐间的交融,使中古音乐获得了不竭动力。所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也是音乐歌舞的创造者。南北朝民间音乐的发展正是源自民间社会的巨大力量,培育了中古伎乐发展的主流。
中古伎乐随乐人的流动迁徙而发生的历史间、区域间、族属间交流与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中古音乐的风格资源。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区域类型和民族生活的多样化。从历史层面,隋唐多部伎反映出的音乐文化面貌,风格浓郁的清商乐传统,特色鲜明的外域外族音乐,地域色彩清新的俗乐新声,出自乐工之手。历史的断裂与连续造成文化的断层,深刻地影响宫廷雅乐发展式微。从文化地理层面,广阔的地域由于交通不便造成隔绝,形成了南北文化明显的地域特征;多元性、异质性的民族文化随着冲突与融合的发生,民族间的文化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于是,在分裂的年代,从西晋宫廷出逃的太常乐工队伍分走他乡避难,最后又被虏获而带到胜利者所在的政权中心地。如洛阳、凉州、平城、建康、长安等都城,迎来各族乐人。固有的音乐传承体系破坏之后,在仅存的有生力量中,传统音乐文化零星地得以为继;流散中形成的新声,则在乐人创造中,带着典型的文化趋异性。
因为战乱,中古伎乐的演化始于被动之中。适逢盛世,伎乐演化成型于唐代。它以博大的胸怀、恢弘的气度,承继汉以后建立起的宫廷音乐系统和社会性文艺系统,总结了近六百年来中原文化发展以及与异族文化交流的成果,吸收了当时域内外各族音乐文化的精华。唐初改订多部乐,建立起完备的伎乐体系,彰显了皇权的威严,体现了唐代宽容、兼容的文化态度,增添了蓬勃旺盛的文化生命力。唐代燕乐之繁盛,显露出民间俗乐与宫廷雅乐并存,形成雅俗并流的乐舞格局。二部伎的革新标示出唐代文化发展新路,伎乐成为提升品位、歌功颂德的重要艺术形式。唐中后期音乐文化在多元、深层次的发展中,基于植根于民间的散乐百戏,发展出了新的社会性音乐品类,走进寻常生活,为宋代音乐品类的细分做了新体裁的准备。雅乐、俗乐明确区分,乐事活动演出重心由宫廷贵族府邸、寺庙走向市井,成为中古伎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音乐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通过人与社会接触;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是人类的行为模式,又是人类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正是由于乐人的中心作用,保证了政权频繁更迭之中音乐传统得以不断重建与恢复,在社会性文艺建设中得以创新与不断充实。正是由于一个个身份卑微的乐人付出的沉重代价,换来了从相和大曲发展为歌乐舞一体的、更为宏大、完美的唐代大曲;从鼓吹乐的传入、清商乐的兴盛,到十部伎出现;从重雅轻郑的雅俗对峙,到燕乐法曲响彻两京宫闱时雅俗合流的新局面。正是由于中古乐人对新的文明生成时所发挥的直接作用,开创出了中古伎乐辉煌的时代,建立起了华夏人民审美中的秩序与规则意识,奠定了中国音乐注重平缓、含蓄、深沉、连贯、流畅的时空和谐观念。或者换言之,音乐创造了中古乐人!
注释:
①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音乐学家郭乃安就发出呼吁“音乐学研究应该关注人”。参阅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
[1][唐]魏徵等撰.隋书(卷14)·志第九·音乐中[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第 142)·乐二·历代沿革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