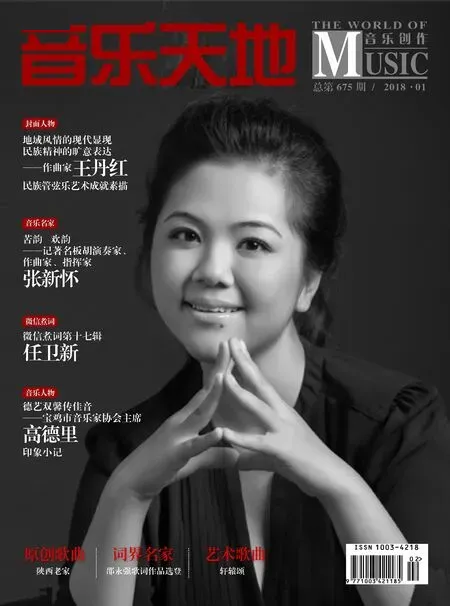微信煮词 第十七辑
任卫新
进入创作状态要就发力很猛
本人和王晓岭开玩笑,说他的面相有一讲,古人曾有话评:行如病虎,立如眠鹰。这是属于是深含不露,但是很威猛的品相。据说作为军事家,当年有“战神”之称的林彪就是此面相,而且是非常典型的一例。看似不强壮,但是特别能打仗。
其实,本人要说的是,我看我们写歌词的作者,也要有如此“行如病虎,立如眠鹰”的品相,平时看似沉默不语,但只要是一旦进入了创作状态,就发力很猛。
唱段可不是一般的歌词
本人看戏剧,就看结尾。中国最伟大的悲剧生死处理,就是《窦娥冤》六月天降红雪。中国最伟大的悲剧浪漫结尾处理,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前者的天地气象烘托,后者的美丽幻化渲染,足以堪称奇绝。中国前贤们这种戏剧艺术处理上的智慧才华,本人甚至认为完全可以媲美莎士比亚。有了如此的情境设计,你说在这里写出的唱段它能不感人吗?
回头再看我们今天,有些号称音乐剧的那些唱段,不是出自于强大的戏剧冲突中不说,只说那些唱段文字本身的构成基本不是唱段。丝毫没有戏剧理念的肌理的意识,而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串儿接着一串儿司空见惯的抒情歌词连缀。不行你就是不行,不行你不服不行。
情感比技巧更为重要
本人曾不止一次经历过这种现象,就是一首歌曲写出来,因为没有试唱的歌手,于是,作曲家就自己试唱录制歌曲小样。大家听了以后感觉不错,于是就通过了。因为作曲最知道自己曲子的感情,所以艺术处理的很投入,嗓音条件可以忽略不计,反倒更显真切,不矫情,于是本人总有另外一种担心,生怕专业演员一唱,把感觉全给唱没了。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主创团队工作期间,我们曾约屈塬创作了关于汶川地震的一首《呼唤》的歌词。当时审听就是作曲王备自己演唱录制的小样,歌曲一下通过。后来正式由毛阿敏录唱,显然就多了些职业味道,少了些灵性的感觉。央视《国家舞台》栏目采访《复兴之路》主创团队,于是,本人创意,让王备专门录唱了一遍来进行登台演唱。结果大家还是认为王备唱的好。真像作曲所说的,歌唱家能唱出作者作品的百分之七十感觉,已然是上天了。
光写歌词不算是个音乐文学家
有一种说法,只能写歌曲旋律的,准确来讲不算是作曲家,应该算是歌曲作家。甚至有人更损,把只能使用阿拉伯数字的简谱写曲调,不会配器不会写交响乐、舞剧等的曲作者,戏称是“阿拉伯”作曲家,甚至是“柬埔寨”作曲家。确实这种揶揄有点过分。
本人与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微信交谈,建议重新恢复音乐文学专业,以便培养歌词创作和歌剧创作的专门人才,特别是民族歌剧的创作的专门人才奇缺。黎光说是个好主意。
因为目前的歌剧创作,写歌词不会编剧,编剧不会写歌词,甚至有的歌剧编剧是电视剧编剧。虽懂戏剧,但不懂舞台,不懂音乐,更不会写歌词,写出的歌剧唱段根本没法谱曲,这怎么行?所谓音乐文学是一门专业,其概念不仅包括歌词,也包括歌剧。光写歌词不算是个音乐文学家。
小歌词里有着大学问
小歌词里有着大学问。就连本人也有些常识概念不清。有人写了一首名为《古丽》的歌词,是专门写给一位维族姑娘的。按常规解释维吾尔族语中的“古丽”是花儿的意思,也是一般女孩的泛称。在大体上可以说没什么问题。
但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中国歌词群里的一位维吾尔族姑娘指出来了,她告诉大家:维吾尔族把所有未婚的女孩都称作古丽,如果专门指定是一个人的话,古丽是不能单独作为名字使用的。打个比方:就像韩国人称呼男人时名字后面加“俊”一样。而这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阿依夏木,家人和朋友平时称呼她时,就是阿依夏木古丽。由此可见常识不能忽略。
方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所谓歌曲,就是通过演唱造成语言的延长与美化。就民歌与地方戏曲来说,这种语言的延长和美化完全是根据方言来形成的。豫剧就是河南方言的味道,评弹就是吴侬软语的的味道。这是基本常识。方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因此,本人虽然祖籍河北,生长内蒙,但是,在歌剧《二泉》的编剧中,专门研究了无锡方言写入唱段,赢得称赞。
有些所谓文化管理机构发文,作出文艺节目里不允许使用方言这样的相关规定。本人认为,非但不能不许用,反而要保护方言。提倡各地方电视和广播都应该有自己的方言节目。不妨再问一句:那少数民族的语言你敢取吗?那香港节目中的方言你敢取吗?如果,山西梆子不用山西方言那还叫什么山西梆子?。
认真弄明白每一个字
写歌词有时需要较个真。在大家讨论《兰花花》时有人说到,持陕北民歌为“蓝花花”而不是“兰花花”的观点,是因为在歌词中明确就有“青线线那个蓝线线”的原因。于是笔者问陕西尚飞林:青线线到底是啥颜色?是青天的那种蓝吗?按照本人理解,青应该是黑色。比如常说的,一挽青丝。肯定是黑头发不是蓝头发。因此,所谓青线,其实就是黑线。
记得小时候,外婆做针线活儿常说,你把那青线板儿递给我,就是指的缠着黑线的线板儿。当然,青草,青菜甚至青年,对这“青”字也各有一解。但是,用在与布匹衣着有关方面,本人觉得,还是应该当做黑色来讲。如,青布,青衫。当然,另外,青史之青不然,乃是在青竹之简刻传于是为青史留名。又弄明白了一个字。
别总认为什么宝刀不老
都说宝刀不老,宝刀是不老。可人毕竟不是宝刀,人的身体不可能具有和宝刀一样的那种材质。人这把刀怎么会不老呢?所以,成熟的老作家再成熟也是下坡路趋势的成熟。不成熟的年轻作家再不成熟也是呈现上升趋势的走向成熟。两种生命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必须承认。
所以,本人非常关注年轻的新生力量的成长趋势,要必须向年轻人学习,感受他们生命的心率,感受他们对事物的反应,尽量争取能做到理解,如果做不到理解,也要尽量做到了解。哪怕是东施效颦,哪怕跟着他们后面气喘吁吁地奔跑,尽量别掉队就行了。
空泛的歌词太多了
几年下来,深有感触:谁要是能把中国梦给写经典了,那可真就是大人物了。因为,不是由衷感发,而是概念入手,基本大概差不多都属于社论歌和口号歌。没有任何感染力。
其中,有一首曾经每天滚动播放:高山的梦想是巍峨,大海的梦想是辽阔。猛一听,不错。仅从措词和借喻比兴上看,也是堪称非常娴熟老道那种。本人问歌手:那阿尔卑斯山不也是山吗?那地中海不也是海吗?难道,也都做你中国梦吗?顾此失彼,毫无基本的逻辑概念,没有血肉的情感根基,如此缺乏信服力空泛的歌词太多了。多少词曲作者居然攻不下这样一首好歌来,是应该感到丢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