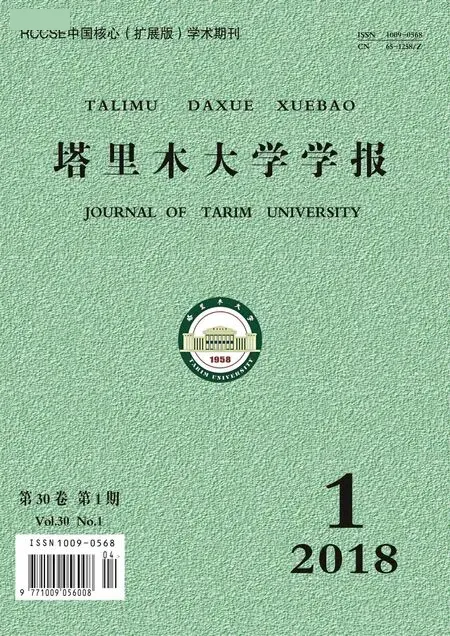纪录片《塔里木河》的叙事技巧与视听表达
叶颖文 肖 涛 王中伟
(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纪录片《塔里木河》共有十六集,每集三十分钟,用河流为线索,串联起两岸人民生活与情感,体现了新疆这片广袤土地的风情与人情。该片是新疆纪录片中的上乘之作,其创作理念扩大了民族文化的表达空间,将人文与情感并置书写,运用故事化手法讲述新疆母亲河——塔里木河的沿岸风土人情,从沿岸生活人们的日常生活切入,深入见证了各个民族人民“活态”文化与他们之间的感人情感。
1 理念创新:通过结构重塑家国认同
《塔里木河》的创作理念在新疆纪录片中算是翘楚,与以往较为单一的重视政治言说与文献宣教的新疆纪录片不同,《塔里木河》将政治言说与主流价值观内化在剧情叙事之中,看似讲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情感,却将新疆各族人民与内地无法割舍交融的关系凸显其中,暗含着多元文化、国家认同的主题。
这种理念创新的核心在于叙事的结构,通过结构进行建构重塑价值观念。所谓结构,是指通过对人物生活故事中一系列事件的选择,将之组合/叙述成一个具有意义的序列,以激发和表达特定而具体的情感与价值。[1]
《塔里木河》的叙事结构构思十分精细,例如在第九集《渡口》中,歌舞团团长为了在新婚的维吾尔族同学婚礼上做表演,特意去佛教中心学习了壁画上的动作,将壁画的内容融入到舞蹈当中,最终第一次在维吾尔族的传统婚礼上表演了源自佛教的舞蹈。这一集为了阐释多元文化的主题,利用了维吾尔族婚礼这一主线,把维吾尔族新人、舞蹈团团长、来自厦门的壁画修复师和他同事的故事串联起来,表现了新人对幸福的渴望、舞蹈团团长对多元文化的坚定、修复师们对佛教壁画的奉献。最主要的是这个剧情结构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即通过设置悬念来传达更主流的价值观念。《塔里木河》在解说词中说到:“由于信仰和文化不同,传统的维吾尔族婚礼都只跳本民族的舞蹈”。那么,对于寻常受众来说,就可能会存有这样的疑惑:既然如此,歌舞团团长为什么还要在维吾尔族的传统婚礼上表演源于佛教的龟兹舞蹈?在影片的最后,团长亲自给出了答案:麦西莱甫也好,龟兹古舞也好,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传统文化,都是祖先留下来的瑰宝,是每一个当代的龟兹人都应该加以保护和传承的对象。这一集的叙事巧妙的把文化多元的主题通过纪录片内部结构表现了出来。
在以往纪录片对新疆的塑造上,大多以呈现“文化奇观”、“异域风情”为主,有意无意地将新疆形象建构的特殊而又遥远。虽然记录某种区域性、民族性的文化片段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如果在较长的时间里,一个地方的纪录片创作大多局限于这些区域性、民族性的文化片段,那么很可能在客观上塑造了一个文化、习俗、信仰上的多重“他者”形象。其无形中导致了如下后果:过分突出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弱化了中华文化的普遍性,强调了地方民族却忽视了共同的情感文化联系,突出了地域认同但缺少了国家认同,这极不利于多元文化生态的发展。
《塔里木河》在吸收先进人文纪录片的创作经验之上,将地缘文化与人之间的情感结构在一起,“国”、“地区”、“家”三者交织在一起,把亲情、爱情等大众共通的情感作为情感线索贯穿于纪录片当中,将新疆独特文化与普遍情感结合,尤其在剧情的设计上,充分利用结构,精心选择和串联安排故事以表达价值观。在社会和自然共生、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的过程中讲述地方性文化遗产的现状,将完整的活态的文化场域表现出来。这就使得《塔里木河》呈现的文化非常丰富,把汉族、塔吉克、柯尔克孜等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生活画卷展示在观众面前,其中很多剧情的结构都在表现内陆与新疆水乳交融的关系:天南海北来新疆种植捕鱼治沙的人,去北京圆梦的维吾尔族家庭,新疆艾德莱斯绸走向国际化的征途……
从这种明显转变的创作理念来说,《塔里木河》可以称得上是新疆纪录片创作史上的里程碑。
2 选材叙事:平民化与故事化
从叙事手段或者说是策略上来看,“艺术方式”的叙事是以特殊的结构模式、“讲述”方式,乃至材料元素来讲述故事。[2]关于纪录片“艺术方式”的叙事并不是简单的陈述史实,也并不以提供某种“正确可靠”的知识为最终目的,而是在保证记录片内容真实的基础上,对人类审美力量、文化内涵与人文情怀的诗意倾诉。
2.1 选材平民化,通过个体反映群体
《塔里木河》选取了沿岸最普通的百姓与他们之间的故事,将充满地域特色风光的描写让位于平实的生活。例如第八集《礼物》中阿卜杜热合曼总是花很多时间为沙棘林去除伴生植物,而妻子并不理解自己,两人一言一语的争吵充满了平凡的生活气息,《塔河》完整的保留了这部分内容,即表现出阿卜杜热合曼的性格特点,也通过他个人反映出以河流馈赠为生的人对自然的尊敬与爱护。在第十集《家园》当中,托乎提买提与吴青峰两位老人,一个捕鱼,一个种稻,勤劳的他们创造了这片鱼米之乡。在下游,101岁的维吾尔族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的种植棉花。这些平凡的选材与叙述视角都让河流与它的子民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更加的凸显出来,正是由于这种深沉的感情积淀,才使得《家园》中讲述的邻里之情、母子之情更加动人。再如第一集《源起》中,高山上的塔吉克人认为“一生只爱一个人,但是知音总是难觅”,第十集中101岁老人说:“我生在这里,就在这里老去。”这些平民化的叙述深刻表现了塔里木河两岸人民对土地的眷恋,他们朴素美好的价值观在塔河两岸温情脉脉的舒展,经过河水的冲刷,更加平凡而有力。
2.2 叙事故事化,通过戏剧反映生活
纪录片内容逐渐过渡向故事化的讲述方式是一种向电影叙事逐步靠拢的趋势,《塔里木河》也大量的运用了故事化的叙事技巧。例如在第一集《源起》中,描绘了塔里木河源头帕米尔高原上塔吉克人的生活风貌,着重描写了柯尔克孜族香港·买买提一家,父亲为了送孩子们去上学,要走过长长的山路,把孩子们送到镇上的学校后,镜头又跟随着父亲顺着来路回到大山深处,归途中他孤独的背影夹在苍凉的大山中显得无力又渺小,白雪朔风的环境让父亲布满皱纹的脸显得格外让人心疼,画面中孤独的触感仿佛从电视中蔓延了出来,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个故事感动。第六集《前方》中,离婚的大辫子姑娘热撒拉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失败的婚姻并没有打倒她,她开了一家蛋糕店,参加各种自己喜欢的活动,日子依然慢慢的向前走,她看似平淡的人生却充满了向上、积极的新价值观念,让人敬佩的同时也让人知道了现代维吾尔族女性独立、自信的生活。而在和田,阿热克瓦一家三个儿子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内地的新疆高中班,这让阿热克瓦一家都踏上了去北京的圆梦之旅。内陆与新疆的对比性是明显的,但是父亲要去北京看升国旗的愿望却让一种深刻朴实的家国情怀流露出来,塔里木河子民热爱故土,也热爱祖国的感情通过一家人的“圆梦之旅”绽放出来。
这些围绕在塔里木河两岸发生的故事记录着这一片土地蕴含的希望与未来。《塔里木河》每一集都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些细碎的生活构成了每集共同的主题,将沿河的风土与人生谱写成人与河流的壮歌。
3 镜头语言:内藏寓意寄托情感
3.1 俯拍强调环境特色
每集《塔里木河》的片头,运用俯拍、航拍将河流总貌、南疆地形壮阔表现的淋漓尽致。在第八集《礼物》当中阿卜杜热合曼被当地政府聘为护林员,当他扛着工具走向林地的时候,一直是用俯拍镜头,让他背后的林地占据画面的一部分空间,直到人物越来越小,树林的广袤越来越凸显,这在无形之间也凸显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阿卜杜热合曼说“感谢大自然的馈赠”的同时,镜头也塑造了同样的含义。
3.2 特写表达情感寄托
《塔里木河》中使用了大量特写镜头,这些特写镜头或者用于突出强调,或者用于寄托情感。例如在第一集《源起》中,父亲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镜头好几次拍到了父亲的鞋子——非常传统的柯尔克孜族鞋,而两个孩子却穿着旅游鞋。这也反映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孩子们拥有更广阔、更现代化的未来,父辈虽然坚守传统,却对孩子们的未来抱有更广阔的希望,上学就是父亲希望的寄托,一种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一种对现代化的渴望,一种对朴素的坚定和执着就这样悄然无声的传递给我们,这些特写镜头就像一个又一个隐喻,强调时代,也说明现在。在第八集《礼物》中,阿卜杜热合曼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沙棘炖鸽子,当阿卜杜热合曼开玩笑说“女婿吃的肉好小”时,镜头则一直对着憨笑的女婿,这个笑容的特写让这一集流淌出平凡真实的幸福气息。温馨的家庭生活充满了平实感人的气息,那种真实,略带羞涩的微笑,寄托着这一家人深厚的感情。
3.3 长镜头与纵深镜头突出纪实性
第十一集《刀郎》中,在介绍海丽盘村刀郎人已经从游牧狩猎转向了农耕生活时,一个长镜头从葡萄林的中间匀速划过,葡萄林规模之大被这个镜头表现出来,从游牧到农耕,文明的转变竟然如此迅速彻底,广袤的葡萄林是那么繁茂,生活的蜕变反映出整个民族逐步现代化的步伐,生活越来越好,记录一片树林,却折射出岁月与文明的碰撞与交织。第十五集《瀚海》中,渔民在博斯腾湖上乘船航行的纵深、俯拍村庄的镜头都有着十分强烈的观察气息,让这里的生活呈现出一种原始感,也突出了纪实性。另外,长镜头与纵深镜头还运用在了捕鱼等动作场景当中,将塔里木河的辽阔与渺茫用镜头慢慢的刻画出来。在段落的过渡中,镜头从山河风景上划过,舒缓了画面节奏,让观众对故事有了回味的时间,也给了解说词表达内涵,提炼精华的机会。
3.4 广角镜头夸张苍凉感
广角镜头在第十六集《楼兰》当中出现数次,在博物馆解说员去楼兰古城的路上,眼望车窗外的沙土地。一望无际的灰色沙漠被广角镜头夸张的改变了形状,土地变成了荒凉的球形,风沙如同气流一般涌动,整个画面显得怪异苍茫,令人感觉此刻仿佛不是去楼兰,而是去探索另一个曾经繁荣而现已湮灭的星球。疏离与空旷的时空被广角镜头完整的呈现出来,在疾风的吹动下,似乎唤醒了楼兰沉睡千年的梦。
4 声音运用:深化呈现人文意境
4.1 解说塑造文化阐释力
当下,纪录片解说词越来越精致、考究、得力,特别是对于《塔里木河》这种传播文化为主的电视纪录片,解说词不仅帮助观众理解纪录片内容,还起到深化纪录片的主题的作用。其一,创设文化情境。例如第十二集《信仰》,解说词为:“传说只有真正的英雄,才能看到正好投射在河流曲折处的九个太阳。”这一句解说词承担了开篇铺垫的作用,通过传说让纪录片叙事进入相应的文化意境。在《信仰》中,艾尔登在博物馆,配合的解说词为:“东归画卷铺展,历史大门洞开,血,仍未冷,梦,还滚烫,艾尔登如有神灵附体,进入到祖先的精神世界。”这类解说措辞有力,运用历史与传说的讲述,创造出来凝重而沧桑的文化意境,让观众对文化充满了敬畏之情,其对文化的阐释,对主题的提炼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二,挖掘文化底蕴。依然是在第九集《渡口》,在介绍龟兹古渡时,这样解说这座老城的历史:“东汉时期,就曾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户府,商旅驼队丝路文明延续着这里的繁荣岁月,如今每逢集市,当地百姓还是喜欢聚集在这里,按照传统的方式交易买卖……”从历史到现在,昔日文明延续成了一种民间的习惯,也让这座城市的人文气息跃然而出。解说词在这里就起到了突出文化底蕴,塑造历史意境的作用。《塔里木河》每一集的解说词都充满了诗意,除了发挥解说词的必要功能以外,几乎每集都有对文化、情感、人心的的诗意描述,这些解说深化了每集的人文主题,表现文化与历史交融的内涵。
4.2 音乐增强艺术感染力
《塔里木河》除了开篇的歌曲以外,还有现场音乐及少数民族载歌载舞或者一家人在吃饭休闲时的音乐,这些音乐一起构成了《塔里木河》整体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第四集《宝物》中,在介绍采玉时,流传于和田的《采玉歌》缓缓响起,并由此引出对河流的赞美,这里的音乐就成为了整体叙事的一部分。因为音乐是跨越文化和疆土的情感抒发语言,渲染气氛是其更为主要的功能。例如在第十六集《楼兰》结束时,配合楼兰遗址与充满文化意境的解说词,音乐淡淡的响起,钢琴声舒缓而充满情感,将结束时的画面定格在一种奇妙的美感之上,影像虽已结束,余音却久久回绕。此外,片中有时轻快的乐曲也弥补了剪辑上的沉稳剪辑带来的倦意,让画面更有趣味。
4.3 环境音凸显空间表现力
一般来说,纪录片中的声音除了解说词之外,还有前期拍摄过程中同步录制的客观声音。这些都是创作的宝贵素材,也是构成视听系统的重要质料。爱因汉姆说:“声音产生了一个实际的空间环境,它有巨大的空间表现力。”[3]在《塔里木河》中,送孩子上学的父亲脚踩冰雪时发出的咯吱声,渔船在河水上捕鱼时呼啸而过的风声,河水拍案的惊涛声,剪树枝时的碰撞声,都是恰到好处的体现着真实,这种塑造现实的能力是其他声音无法比拟的。现场的环境音就是真实感的最佳体现,如果去掉这些环境音,整个影片的表现力就会大大降低。
5 结语
新疆是一个有着丰富人文资源的宝库,是一个可以为纪录片创作提供诸多创作题材和灵感的宝地。[4]复杂多样的地缘、血缘、神缘、语缘,使新疆各族人民拥有着各不相同又相互影响、多元一体而又各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为包括《塔里木河》在内的新疆纪录片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如何把那些“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5]的内容挖掘出来、弘扬起来和传播开来等方面,《塔里木河》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塔里木河》深刻的哲学思索、诗意的人文意境、细腻的情感故事、深厚的家国情怀,写实描摹的日常生活,意味深长的文化传递,不仅让观众在审美上感到愉悦,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奇观化与他者化的新疆形象,从而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传播。
[1] [美]罗伯特·麦基. 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原理[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39.
[2] 李显杰. 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39.
[3] 王建林. 浅谈影视声音的空间艺术[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5(4): 56.
[4] 古丽扎尔·铁木尔, 阿迪夏·夏合热曼. 新疆是纪录片创作人的宝地[J]. 电影评介,2008(5): 12.
[5] 敬天林. 当代,二百年和两千年的文明对话[N]. 光明日报,2014-06-23(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