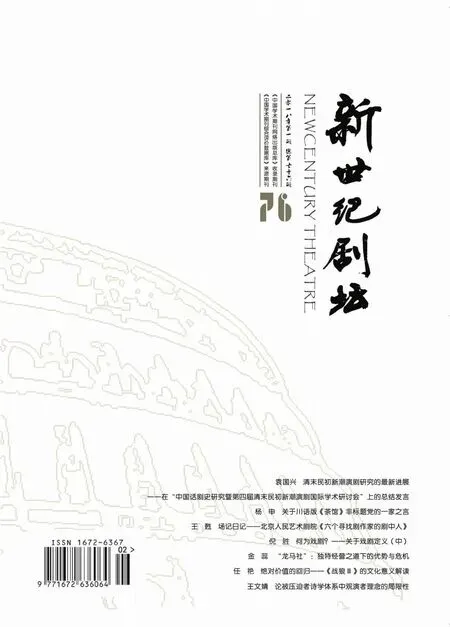《毛猿》中“沉思者”姿态的戏剧意韵探索
《毛猿》是尤金·奥尼尔的一出象征独幕剧,长久以来,这个剧目大多是以表现主义为标签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之中,研究者对于剧中出现的五次沉思者姿态这一手法鲜有关注。奥尼尔在这部剧中设计的五次扬克以沉思者姿态出现是有所深意和设计的,这可以与他的面具观结合理解。沉思者的姿态外化了扬克的心理活动,展示了自我求证的历程。同时,这样的处理方式形成了审美的阻碍与延长,让观众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有更为深入的思考。此外,沉思者本身意义的化用形成对社会现实的讽喻,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毛猿》的主人公扬克是一个像毛猿一样的怪人,他孑然一身,头脑简单。他没有父母、亲人,也没有受过教育,有的只是超人的体力和一堆奇怪的想法和自尊。起初,他终日在大游船的锅炉房中安身,后来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存在,几经折腾,四处碰壁,最终死在了动物园的大猩猩笼子里。这个戏剧作品有许多值得关注的象征意象。例如“毛猿”本身的象征意义,“笼子”的象征意义等等。就目前的研究来说,学界对于这部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对于这部作品的初探,研究的焦点是这部作品的表现主义特征,肯定了这部作品中表现主义的艺术成就和价值。20世纪90年代,对于作品的研究延伸到主题之上。认为《毛猿》这部作品表现了人在社会中被异化的主题,揭示了主人公扬克从踌躇满志、自命不凡到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原来无足轻重、毫无地位的心理发展过程,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高度发展的美国社会中普通人失去归属、仿徨无望的心态。进入到21世纪,随着研究数量不断增多,研究的视角也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出现了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话语系统等诸多研究视角和方法。也是在这一时期,《毛猿》中的象征意象逐渐被关注到,出现了关于“笼子”的象征意义研究,“黑白色彩”象征意义研究等。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和视角,《毛猿》中五次出现的沉思者姿态的象征意义还没有得到关注和研究。结合奥尼尔的面具观,笔者认为,作品中的沉思者的展现是奥尼尔对于面具应用的变形,这其中不仅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值得我们探讨,同时还有巨大的艺术空间和审美价值值得我们挖掘,作品中“沉思者姿态”的反复出现不是无意义的,它既是作者面具理论的直接体现,又深化了作品主题的表现。
一、扬克的自我求证:主人的心理历程
奥尼尔在《关于面具的备忘录》中说道:面具本身就是戏剧性的,它从来就是戏剧性的,并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进攻性武器,使用得恰到好处,它比任何演员可能作出的面部表情更微妙,更富想象力,更耐人寻味,更充满戏剧性。[1]面具在西方戏剧世界销声匿迹了数千年之后,20世纪的美国剧作家奥尼尔将其重新挖掘出来,进行创造性的变形,将其用来进行人物心理的展现,将人头脑中的不可见的心理变化以面具为载体进行呈现。奥尼尔对面具的大量运用,让面具超越了道具的意义,赋予其崭新的生命力。不仅如此,奥尼尔在面具处理中,不局限于面具的形式,而是将其进行变形,出现了有形面具、无形面具、面具表情等多种形式,而《毛猿》中的沉思者就是奥尼尔对于面具的一种变形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我们能够通过面具的表达,体验扬克自我求证的过程,感受到主人公的心理历程和变化。
剧中第一次出现沉思者这一面具变形是在扬克受到米尔德里德小姐的侮辱之后。“扬克没有洗过脸和身子,他跟他们形成了对照,一个黑黑的、沉思的人。他坐在前面的一张板凳上,恰象罗丹《沉思者》。”[2]我们可以看到,沉思者的面具是一种无形的处理,并没有使用真实的物的面具,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进行呈现。这里的沉思者姿态让扬克与周围的人形成对比,此时的扬克对于现实一无所知,他的心中踌躇满志,他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总有办法对米尔德里德小姐的侮辱进行报复。这一次的沉思者姿态中带着自信和不与周围人为伍的个性。
第二次沉思者姿态出现在伙计们对扬克的调侃之后,扬克对于米尔德里德的愤怒再次被激起。
七嘴八舌的声音:洗洗去,扬克。
扬克:(忿恨的)噢,我说,伙计们,别管我。你们没看见我正在思考吗?
大伙:(跟着他冷嘲热讽地重复那个字眼)思考!
扬克:(跳起来)是的,思考,思考,那就是我要说的,怎么啦?(大家默默无言,他对于常常拿开开玩笑的一句话,却突然大发脾气,这把大家弄糊涂了。扬克又坐下,还是那副《沉思者》的姿态。)[3]
这样的面具也让我们开始看到了扬克心中出现的一点点不安。曾经以为自己是这个社会中心的、对这个社会充满价值的扬克现在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米尔德里德的言语攻击让他看到了他们根本不是在同一个世界之中,他的存在价值遭到了质疑,正是这样的质疑让扬克的内心开始隐隐出现不安,这样自我怀疑的心理变化通过沉思者的姿态外化出来,展现出扬克自我认证之路的开始。
第三次扬克以沉思者的姿态出现是第一次受挫,被扔进监狱之后。灯光照过最前面那间牢房笨重的铁栅栏,揭露了一部分室内情况。可以看见扬克关在里面。他低头弯腰坐在小床边上,姿态就像罗丹的《沉思者》。[4]这里对于扬克的心理表达进一步深入。扬克不相信自己身处在监狱之中,保持沉思者的姿态像是在维持着自己仅有的自尊。
第四次沉思者姿态的出现是在狱中得知米尔德里德的时候,“他坐下,姿势象罗丹的《沉思者》,身边一只手里拿着报纸。”[5]这一次沉思者姿态的出现是扬克内心情绪最为激烈和分裂的一次。扬克得知了米尔德里德制造出了全世界一半的钢铁,原以为自己能够顶事,却发现自己最终处于钢铁的牢笼之中。沉思者的姿态以静为动,虽然动作不激烈,但是却通过独白反映内心的激荡,形成对比。扬克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曾经引以为傲的自信只是盲目自大,自己的存在遭到了否定,另一方面,这激发了他的怒火和反抗,想要化身为火,消灭压在头上的钢铁。沉思者姿态反映了扬克的思考和内心的变化。
第五次沉思者姿态的出现是在剧本的最后一场戏中。“有一个笼子上挂着一块招牌,上写着‘大猩猩’。那个大野物蹲在板凳上,姿势很象罗丹的《沉思者》。”[6]这里的沉思者姿态第一次换了一个身份,变成了动物园中的大猩猩,这里通过这个面具变形的姿势实现了扬克与大猩猩的互位。经历了这些的扬克已经不再思考,扬克无法在这个时代中向前走,就想着要往后退。这里沉思者姿态的转移完成了对扬克心理的侧面刻画,扬克最终没有实现它的报复理想,也没有回到过去,只是和命运一直斗争,为肯定自己的价值做出种种努力。
综合来看,我们能够从文本中看到五次沉思者的出现是有所设计的,沉思者姿态的出现伴随着扬克心中的变化。从第一次的踌躇满志,到第二次的不安怀疑,第三次自我麻痹和强撑,第四次的存在遭到否定的无奈和怒火,第五次的无处可归。扬克从航船的笼子走进了监狱的笼子,再走进了动物园中的笼子。沉思者面具的变形出现让我们在热闹的情节之外,感受扬克的心理变化,跟随着他一起思考,一起看清他的处境,一起发现世界一直在支配着他的真相。
二、审美阻碍与延长:沉思者意象的陌生化
沉思者姿态反复出现打破戏剧写作常态,引起读者的关注。《毛猿》中沉思者姿态的一再出现也是陌生化戏剧手法的实践和应用,这样的设计给观众造成审美的阻碍和延长,让观众对于戏剧中的情节和人物有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陌生化”理论最早缘起于什克洛夫斯基,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主要是更新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陈旧的感觉,将人的思想从原有的关系中解放出来。放弃机械化的方式,通过诗语的复杂化、创作性的变形和结构的延宕等方法来完成对日常事物的展现,让人们从之前熟视无睹的事物中产生新的发现,也感受到事物本身的超出寻常,感受语言最初所具有的“诗性本质”。
在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的引入下,陌生化开始进入到戏剧理论领域。布莱希特在《论实验戏剧》[7]中对陌生化做了这样的解释:“把一段普通的时间或者一个平凡的人物性格进行陌生化处理,首先意味着简单地剥去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己经被人们熟知的东西,从而制造出对它的陌生和新奇感。”而且他认为古老的戏剧中借用面具的原因就是让其显得陌生化,不仅在于观众要体会到这种效果,演员也需要。
在这一理论提示下,奥尼尔笔下的扬克多次以沉思者姿态出现似乎可以有不同认识,沉思者的多次重复出现一反文学创作的常态,让观众对于这一反常现象产生关注,这种创造性的结构安排引发观众思考,开始猜测剧作家这一情节设置的原因,感受沉思者姿态面具之下隐含的作者的真实意图,感受这种形式传达出的情感倾向和思想内涵。
除了这样反常态的文学结构造成的陌生化之外,沉思者形象与扬克身份的不符也形成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扬克没有受过教育,却每时每刻都在思考。沉思者的姿态面具与扬克本身的人物形象并不相符。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扬克以沉思者的姿态出现本身就是一种陌生化的形式,人们从这样的反常之中体会扬克心理的变化和分裂。这种心理的呈现和分裂并没有通过独白的方式呈现,而是以面具变形的方式进行,这样的处理带动了观众与扬克一同思考,延长了审美的时间。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布莱希特和奥尼尔对于“陌生化”的戏剧处理方式都是要造成审美的阻碍与延长,但是与布莱希特所提倡的“间离效果”不同,布莱希特提倡观众与戏剧的分离,认清戏剧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区别,引导观众从戏剧之中到戏剧之外。奥尼尔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想通过面具使自己的剧作更加真实,更贴近观众。他认为,面具的采用就像把戏剧的灵魂植入了演员身上,使演员能更真实地把握角色。更重要的是,面具营造出来的氛围要让观众觉得更真实,完全没有距离感,这样才有利于煽动观众的情绪,达到共鸣的效果。因此,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奥尼尔创造性地对面具进行改造,才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扬克以沉思者姿态出现的无形面具。这样的方式既完成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又让观众深入其中,传达出扬克不是个体存在,而是工业社会之中的你我这样的主题。
三、社会动荡与沉思:沉思者的讽喻意义
对社会的讽喻首先来自于《沉思者》这个雕像本身的意义。《沉思者》是法国雕塑大师罗丹的雕塑名作。这座人体坐像本是罗丹的巨型雕塑《地狱之门》中的一部分,他高踞于地狱之门的门槛之上,在他的下方,是地狱之门上一组组在罪恶、苦难、绝望中挣扎的人像群雕。他俯身低头,手撑着下巴,仿佛为眼前惊心动魄的惨景所震动,正陷于痛苦的沉思,《沉思者》之名正是由此而来。在《毛猿》中,奥尼尔化用了沉思者这一雕像,以面具变形的形式将其呈现在扬克身上,采用了沉思者本身的寓意,即对于整个社会悲剧的注视和思考。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让人类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家园,进入到一个高度机械化的时代。但是人们面对这样的悲剧却无可奈何。人本来和自然是一体的,正如老水手派迪所说的,那些人都是海的儿子,就像海是他们的亲娘。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里,在钢铁的压迫下,他们只能被关在黑漆漆的船舱里,看着机器敲打、摇晃、跳动,用煤灰塞满他们的肺。沉思者的化用是借用扬克的沉思来看到这个时代的悲剧。在资本主义时代中,很多人已经失去了与自然的一致,同时,他们却没有在这个社会获得精神的一致,于是,他们焦躁不安却找不到出路,在天上地下都找不到归宿,只能悬在半空之中。如果说罗丹的沉思者注视的是在罪恶、苦难、绝望中挣扎的人像群雕,那么奥尼尔对于沉思者的化用就是在展示工业社会给现代人带来的精神悲剧。
此外,沉思者姿态出现的场景设计也别有新意,以一种沉思和喧闹的对比展示着社会的浮躁和不安。扬克每一次以沉思者姿态出现的时候,总是配合着周遭嘈杂的环境。第一次和第二次以沉思者姿态出现的时候,船舱中充斥着七嘴八舌的声音。第三次和第四次在监狱中出现的时候,周围满是监狱中人的嘲笑,这样的喧嚣与躁动形成了沉思者扬克与现实社会喧嚣浮躁的对比,形成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讽喻。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被高度发展的社会异化,社会的发展和资本的累积强迫着他们不断向前才能生活,人们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也没有思考的时间,甚至在这样的躁动之中连静下来的机会都没有。这里的沉思者与周围环境的对比,形成了对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的讽刺。
由此可见,《毛猿》中五次沉思者的出现并不是偶然,而是作者的面具观在戏剧中的创造性实践。五次沉思者姿态的出现让观众透过面具看到真实,外化了扬克在自我求证之路上的心理变化,同时,化用罗丹的沉思者形象,完成了对于工业社会中人类异化的现实讽喻,并通过“陌生化”的戏剧方式,形成了审美的阻碍与延长。可以说,沉思者姿态的设计是奥尼尔戏剧艺术的个性表达形式,更加印证了奥尼尔是一位具有诗性的剧作家。
注释:
[1][美]尤金·奥尼尔.戴面具的生活[M].郭继德等译.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80
[2][美]尤金·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M].荒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18
[3][美]尤金·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M].荒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19
[4][美]尤金·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M].荒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33
[5][美]尤金·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M].荒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37
[6][美]尤金·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M].荒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47
[7][德]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M].刘国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14